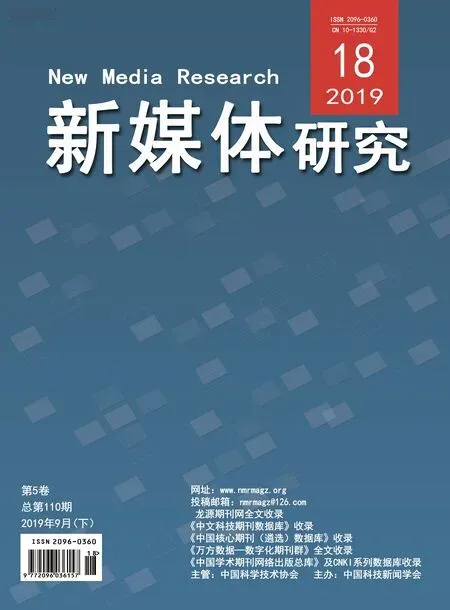微信朋友圈中的身體傳播倫理問題淺析
徐燕萍
摘 要 微信朋友圈作為一個基于強關(guān)系和弱關(guān)系交互連接形成的虛擬社群,其空間內(nèi)存在的各種身體傳播行為值得探討,但我們更應(yīng)該關(guān)注這些身體傳播帶來的倫理問題,如語境坍塌造成的傳播隔閡,身體被規(guī)訓(xùn)、主體認(rèn)知被顛覆以及社交焦慮等問題,并對之進行反思。
關(guān)鍵詞 朋友圈;身體傳播;倫理問題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21)18-0014-03
在海外社交應(yīng)用Instagram上,曾發(fā)起過“ins對抗現(xiàn)實”運動,用戶通過發(fā)布一張真實圖片與一張精修圖片的對比圖像貼,以諷刺該應(yīng)用上的完美圖像,呼吁大家避免將真實與虛擬的身體形象進行比較。在國內(nèi)社交媒體軟件微信上,同樣存在這一現(xiàn)象。如今,微信已成為人們每天社交、工作使用最頻繁的應(yīng)用,朋友圈內(nèi)的身體傳播也千姿百態(tài),大致可分為真實呈現(xiàn)與精心塑造兩類。在互聯(lián)網(wǎng)空間,身體的在場比離場似乎承載著更多的符號意義,帶來的傳播效果和社交效應(yīng)也更為奇妙,但同時也存在著各種不確定性和負(fù)面影響。文章聚焦微信朋友圈內(nèi)的身體傳播,研究身體傳播作為一種新的傳播路徑,其具體傳播行為有哪些,以及會帶來哪些身體傳播倫理問題,并對此展開反思與展望。
1 身體傳播簡述
傳播學(xué)者彼得斯曾提出過一個有趣的問題:在人類的交流中,身體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缺席?在蘇格拉底與耶穌對傳播觀念的解讀中,彼得斯選擇了后者,在彼得斯看來,身體不可能無限程度地被壓制,在日常的交流情景中,身體是否在場仍然具有重要意義[1]。彼得斯對于交流、身體的觀念在中介化傳播的今天具有重要的反思與啟發(fā)意義。新媒體時代,媒介技術(shù)的發(fā)展使得交流具備了各種可能性,身體也完成了從在場到不在場再到擬在場的系列過程,眼下探討的問題,已變成“交流時身體在多大程度上在場”以及“如何在場”。身體在傳播學(xué)領(lǐng)域的回歸,也可以用“具身性”這一新興概念進行理解,具身意味著身體與周圍世界融為一體,身體泛化為媒介的一部分。
過去,傳播以面對面的交流為主,離開了身體人們便無法進行交流互動,此時身體在傳播中扮演著至關(guān)重要的角色。隨著媒介技術(shù)的發(fā)展,報紙、廣播、電視相繼出現(xiàn),傳播已不再需要身體作為媒介,呈現(xiàn)出一種“去身體化”的趨勢,身體逐漸為傳播學(xué)所忽視。如今,隨著智能媒體的發(fā)展,以人工智能、AR、VR等新興技術(shù)為代表,使得身體再次成為一種媒介,且能夠跨越時空限制,達(dá)到虛擬在場狀態(tài)[2]。由此,身體在傳播中的意義再次凸顯,對身體與傳播展開研究也成為熱點趨勢。關(guān)于身體傳播,目前學(xué)界尚未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一般指的是身體問題與傳播研究相結(jié)合的傳播類型,如近年來火熱的人機具身互動、虛擬現(xiàn)實技術(shù)等。本文認(rèn)為,身體傳播本質(zhì)上是身體、媒介以及環(huán)境的互動融合,智能媒體時代的到來讓研究者普遍關(guān)注到了技術(shù)與身體之間的關(guān)系,未來仍有深度的探討空間。
2 微信朋友圈中的身體傳播
與智能媒體相同,社交媒體的發(fā)展是促使我們重新面向身體傳播的另一重要因素,尤其以微博、微信兩類社交平臺為代表。在大眾傳播時代,以學(xué)者麥克盧漢的觀點為主流,我們將媒介視為身體的延伸,忽視身體本身。但社交媒體的出現(xiàn)使得我們的身體再次回歸,在社交平臺上,我們能夠基于身體進行各式各樣的“社交表演”,將身體作為實現(xiàn)傳播的媒介[3]。2021年1月19日,在微信公開課PRO“微信之夜”上,微信創(chuàng)始人張小龍分享了一組數(shù)據(jù):每天有7.8億用戶進入朋友圈,1.2億用戶發(fā)表朋友圈,其中照片6.7億張,短視頻1億條。可見,微信朋友圈是當(dāng)下一個龐大的社交平臺,其在很大程度上已經(jīng)改變了我們的行為方式和與周圍世界的互動方式。而用戶在朋友圈內(nèi)的身體傳播,一般可分為真實呈現(xiàn)與精心塑造兩類。
2.1 真實呈現(xiàn)
考察朋友圈內(nèi)的身體傳播,考察對象應(yīng)為朋友圈內(nèi)的活躍用戶。微信朋友圈是基于圈主與熟人間的關(guān)系搭建而成的虛擬社群,一般而言,朋友圈中的熟人是基于趣緣或業(yè)緣關(guān)系,如因共同興趣愛好相識的社會群體、同事、師生、同學(xué)關(guān)系等。在這種強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存在兩類用戶群體,真實呈現(xiàn)、記錄自我的是一類。這類用戶對自我感到自信,在朋友圈內(nèi)敢于展示真實自我,對發(fā)表的照片、視頻不會進行過多修飾,也會大膽吐露自己的真實想法。這些在朋友圈呈現(xiàn)真實自我的用戶主要是為了滿足自身對信息和社交的需求,其線上社交與線下社交行為并無太大差異,在朋友圈內(nèi)的身體傳播一定程度上也能夠給熟人以親切感。
2.2 精心塑造
與真實呈現(xiàn)自我的用戶相反,另一類用戶密切關(guān)注著自身、他人在朋友圈內(nèi)的一舉一動,這類用戶在發(fā)表朋友圈之前,會精心修飾自我的圖片,視頻,并配上一段出彩的文案,逐字逐句都是經(jīng)過悉心打磨的,甚至觀眾都是通過分組精心挑選后的觀眾。這些在朋友圈內(nèi)精心塑造自我、展現(xiàn)“前臺表演”的用戶,大部分渴望通過不斷增加的點贊、評論量滿足自我的虛榮心,以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本[5]。當(dāng)虛擬身體與現(xiàn)實身體差距過大,現(xiàn)實中被人拆穿、識破時,他們也會感到焦慮,但仍不會放棄在朋友圈內(nèi)呈現(xiàn)他人眼中的自己,這類用戶大多迷失了真實的自我,內(nèi)心充滿了因偽裝而日益累積的抑郁、焦慮和恐懼感。
3 微信朋友圈內(nèi)身體傳播帶來的倫理問題
3.1 語境坍塌,造成傳播隔閡
語境是人際交往中的一個重要構(gòu)成因素,在面對面交流時,處于同一語境是交流雙方實現(xiàn)無障礙溝通的前提條件。人際交往屬于小范圍的傳播類型,面對不同的交往對象我們往往需要結(jié)合具體的語境去調(diào)整、組織自己的語言和行為表現(xiàn),以準(zhǔn)確傳達(dá)自身意圖,這在線下交流場景中也是易于實現(xiàn)的。在社交媒體發(fā)展普及之前,我們對人際交往尚有一個整體的把握,能夠根據(jù)不同的交流對象確定不同的交流語境。而微信朋友圈作為一個線上社交平臺,包含了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群體傳播等各類傳播類型,傳播范圍被進一步擴大,在線下易于識別的語境到線上就會面臨坍塌的問題,這一問題尤其困擾著慣于在朋友圈內(nèi)真實呈現(xiàn)自我的用戶群體。
在朋友圈內(nèi),好友少則數(shù)十人多則數(shù)千人,這些好友或基于強關(guān)系,或基于弱關(guān)系連接,彼此之間存在著多個圈層,如同事、好友、親人等[7]。當(dāng)用戶在朋友圈內(nèi)發(fā)布一些動態(tài)時,往往都是在特定語境下針對特定人群所發(fā)布的動態(tài),雖然能夠通過分組對好友實現(xiàn)批量管理,但由于人數(shù)眾多難免產(chǎn)生紕漏,相應(yīng)地不同圈層的好友會在不同語境下產(chǎn)生不同的理解,對傳播者發(fā)布的動態(tài)進行誤讀。簡言之,不同于線下社交,線上社交中傳播對象更復(fù)雜、傳播范圍更廣泛,消解了線下社交中人際交往的特定語境,使得用戶失去了對于交流語境的掌控,無法與每一個受眾處于同一個語境中,這必然很容易造成傳受雙方的傳播隔閡,為傳播者即圈主帶來不必要的誤解。
3.2 身體馴化,顛覆主體認(rèn)同
“圓形監(jiān)獄”由英國社會理論家杰里米·邊沁提出,后福柯將其稱之為“全景敞式監(jiān)獄”,在圓形監(jiān)獄中,犯人處于隨時被監(jiān)控狀態(tài)并對自身是否被監(jiān)控一無所知。對于在微信朋友圈內(nèi)謹(jǐn)言慎行的用戶而言,朋友圈就相當(dāng)于互聯(lián)網(wǎng)虛擬空間中的“圓形監(jiān)獄”。在這類用戶看來,朋友圈是一個被凝視的空間,每時每刻都有不同的人在“監(jiān)視”自己的動態(tài),關(guān)注自己的一言一行。為了符合他者凝視的期待,這類用戶會根據(jù)他者的凝視、他者的審美對自己的身體加以重構(gòu),其在朋友圈所發(fā)布的身體影像無一不是精心構(gòu)造過的,尤其是女性用戶群體,對于好友的看法、評價較為敏感,因此也更注重朋友圈內(nèi)的“前臺表演”。
而展現(xiàn)完美身體影像的過程,同時也是身體被他者凝視所規(guī)訓(xùn)、主體認(rèn)知被顛覆的過程。海量的點贊與贊美性評論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用戶的虛榮心、自尊心,看似帶來了更多的社會資本,但這實際上是以用戶對自我真實身體的犧牲為代價的,更是于無形中將他人、社會對于身體的標(biāo)準(zhǔn)納入了用戶自身的話語體系之中,失去了對自己身體的主體性認(rèn)同,這一過程也是用戶身體被馴化的過程。2020年在各大社交媒體平臺流行的“BM風(fēng)”是對女性身體進行規(guī)訓(xùn)的典型案例,“one size fits most”的品牌標(biāo)語使得女性熱衷于以展示身體獲取社會資本,這與朋友圈內(nèi)精心修圖、塑造自我的用戶群體類似,其本質(zhì)上都是身體逐漸被馴化、主體認(rèn)同被顛覆的過程。
3.3 擬態(tài)環(huán)境,形成社交焦慮
從技術(shù)可供性的視角出發(fā),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技術(shù)使得身體的虛擬在場成為了可能,使得用戶能夠在微信朋友圈內(nèi)進行自我呈現(xiàn),豐富了我們的社交形式。然而,技術(shù)也在某種程度上主導(dǎo)著用戶的情感。社交媒體時代,對于悉心“經(jīng)營”微信朋友圈的用戶群體而言,朋友圈已然成為了自己精心建構(gòu)的一個“擬態(tài)環(huán)境”,當(dāng)這類用戶長期沉浸在朋友圈這一“擬態(tài)環(huán)境”中,會理所當(dāng)然地將朋友圈內(nèi)的虛擬身體當(dāng)作現(xiàn)實,忽略現(xiàn)實中真實的、各種各樣的身體[10]。當(dāng)回到現(xiàn)實,朋友圈中的身體在場也僅僅是一種虛擬在場,是身體的一種相對在場,只有當(dāng)面對面時身體才能夠達(dá)到絕對在場,而此時用戶精心塑造的虛擬身體就會被識破,社交焦慮也由此產(chǎn)生。
當(dāng)精修過的照片無人點贊、評論,用戶必然會產(chǎn)生落差感,對自我感到懷疑,甚至刪除動態(tài)。更為重要的是,線上社交與線下社交并非是完全獨立的,朋友圈內(nèi)的身體虛擬在場也并非意味著完全離場,總有一些好友了解自己的真實樣貌。久而久之,這類用戶逐漸會對自己的樣貌、身材感到不滿、焦慮,社交壓力也會逐漸增大。正如雪莉·特克爾所言:“社交網(wǎng)絡(luò)無時不刻的在線帶來了無限的焦慮。”微信朋友圈有著典型的自我中心主義的社交結(jié)構(gòu),繁華表象的背后,卻是無盡的孤獨與焦慮,一些用戶通過選擇逃離朋友圈避免這一困境,近年來不斷減少的微信朋友圈用戶使用率也足以證明[11]。對微信朋友圈有一個明確的界定,避免陷入自我中心主義社交,是用戶使用朋友圈前應(yīng)深度思考的問題。
4 反思與展望
如今,在虛擬社群微信朋友圈之中,似乎人人都有完美的身體、完美的生活與完美的關(guān)系,但這些完美大多都是虛偽的,與現(xiàn)實有著鮮明對比。社交媒體促成了身體的虛擬在場,使得我們可以在朋友圈內(nèi)進行真實呈現(xiàn)與精心塑造兩類身體傳播行為,一般而言,更多用戶傾向于第二種身體傳播,敢于真實呈現(xiàn)自我的往往是少數(shù)用戶。然而,無論是真實呈現(xiàn)還是精心塑造,都會帶來相應(yīng)的倫理問題,如語境坍塌造成的傳播隔閡,太過注重自身形象導(dǎo)致的身體被馴化、主體認(rèn)同被顛覆以及現(xiàn)實與虛擬的破裂所帶來的社交焦慮問題,此外還有注意力被分散、網(wǎng)絡(luò)欺騙等其他倫理問題。我們無法拒絕媒介的技術(shù)化,身體、媒介與技術(shù)的融合這一趨勢也無法改變,但在賽博空間中,我們應(yīng)保持清醒的自我認(rèn)知,理性辨別真實與虛偽,人的理性是任何技術(shù)都無法代替、模仿的。
身體傳播作為身體在傳播學(xué)領(lǐng)域的回歸,背后離不開技術(shù)的加持,但若技術(shù)僭越了我們的肉身,顛覆了我們真實身體的主體性,傳媒失去了人文關(guān)懷,這是無法容忍的。我們應(yīng)當(dāng)進行思考,人是否能夠完全泛化為媒介的一部分。在朋友圈內(nèi),我們將身體作為媒介進行身體傳播,或是為了進行社交,或是為了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本,或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與自尊心。我們在朋友圈內(nèi)進行著各式各樣的身體演繹,在這些身體傳播背后,卻是以我們主體性的旁落為代價的。在身體傳播普遍流行的當(dāng)下,我們絕不能忽略身體在場的交流,如何進行人文關(guān)懷也應(yīng)是社交媒體時代的關(guān)注重點,身體的虛擬在場始終是一種相對在場,肉身的神圣性始終不可侵犯。如何平衡虛擬身體與真實身體,值得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xiàn)
[1]劉海龍.傳播中的身體問題與傳播研究的未來[J].國際新聞界,2018,40(2):37-46.
[2]于姣博.試論人工智能寫作技術(shù)對新聞傳播行業(yè)的影響[J].漢字文化,2021(12):166-167.
[3]甘露穎.“自嘲與狂歡”:社交媒體中的“小丑語境”解讀[J].新媒體研究,2021(10):81-83.
[4]馮廣圣.報業(yè)“一體化”轉(zhuǎn)型模型構(gòu)建[J].新聞與寫作,2018(3):94-96.
[5]裴敏.風(fēng)格·抵抗·收編:伯明翰視角下“飯圈”文化時代性解讀[J].新媒體研究,2021(7):78-80,88.
[6]李越,吳斯,馮廣圣.UGC視角下的網(wǎng)絡(luò)社區(qū)內(nèi)容分層管理個案研究:以站酷社區(qū)s為例[J].東南傳播,2019(7):121-123.
[7]楊鑫,馮廣圣.基于趣緣的隱性連接下文化的狂歡:基于“驚雷”“淡黃長裙”現(xiàn)象的考察[J].東南傳播,2020(11):83-85.
[8]馮菊香,劉俊怡.抖音短視頻中農(nóng)村青年女性媒介形象建構(gòu)[J].新媒體研究,2021(6):81-84.
[9]呂志文.構(gòu)建與解構(gòu):“男性向”網(wǎng)絡(luò)小說改編劇分析[J].藝海,2020(7):82-83.
[10]馮菊香,鄒嘉楠.認(rèn)同與重塑:網(wǎng)絡(luò)游戲社區(qū)中擬態(tài)關(guān)系的影響研究[J].新聞知識,2021(2):21-26.
[11]彭佳妮,馮廣圣.“擬在場”:網(wǎng)絡(luò)社交禮儀功能辨析:以微信“拍一拍”為例[J].東南傳播,2021(3):130-132.
[12]位云玲,馮廣圣.算法新聞推薦的社會責(zé)任反思[J].新聞知識,2020(9):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