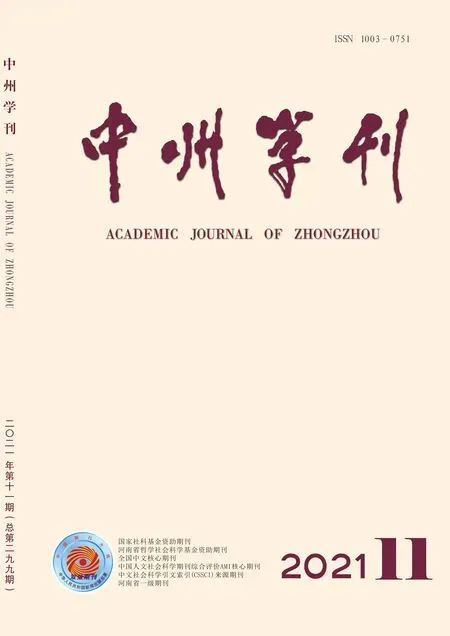農(nóng)民協(xié)商能力與農(nóng)村社區(qū)協(xié)商系統(tǒng)質(zhì)量關(guān)系研究*
——基于鄉(xiāng)村建設(shè)行動中三個(gè)農(nóng)村社區(qū)協(xié)商實(shí)驗(yàn)的比較
張 大 維 張 航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xiàn)綜述
1.問題提出
近年來,協(xié)商民主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中的作用不斷彰顯,進(jìn)一步推動協(xié)商民主尤其是農(nóng)村基層協(xié)商民主的發(fā)展是民主政治建設(shè)和鄉(xiāng)村建設(shè)行動的必然要求。目前,國際上的協(xié)商民主理論經(jīng)歷了制度、實(shí)踐和經(jīng)驗(yàn)轉(zhuǎn)向,已發(fā)展到了第四代的協(xié)商系統(tǒng)理論階段。①但是,國內(nèi)關(guān)于協(xié)商系統(tǒng)的研究還較少,基層協(xié)商實(shí)踐中高質(zhì)量的協(xié)商系統(tǒng)仍不完善,其中一大瓶頸便是各參與主體協(xié)商能力不足。較早將協(xié)商能力與協(xié)商質(zhì)量關(guān)聯(lián)起來進(jìn)行研究的是約翰·德雷澤克,他認(rèn)為協(xié)商系統(tǒng)的協(xié)商能力越大,其協(xié)商質(zhì)量就越高。②
在我國農(nóng)村基層社區(qū)協(xié)商中,包括政府部門、社區(qū)“兩委”、社會組織和各類農(nóng)民等多元主體的協(xié)商能力均會對整體協(xié)商能力提升與高質(zhì)量協(xié)商系統(tǒng)達(dá)成產(chǎn)生影響,如社區(qū)“兩委”對協(xié)商的認(rèn)知和操作能力、政府對協(xié)商的指導(dǎo)部署和回應(yīng)能力③等都會顯著影響協(xié)商績效。其中,農(nóng)民的協(xié)商能力特別值得關(guān)注:一是農(nóng)村社區(qū)協(xié)商中多元參與主體中農(nóng)民的協(xié)商能力相對欠缺;二是農(nóng)民作為農(nóng)村社區(qū)協(xié)商中涉及最廣泛的要素,是鄉(xiāng)村振興中最重要的主體,不容忽視。④提升農(nóng)民的協(xié)商能力,有利于推動人民當(dāng)家做主的落實(shí),提升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的能力。因此,本文探討的協(xié)商能力主要指農(nóng)民的協(xié)商能力。
在農(nóng)村基層協(xié)商實(shí)踐中,受社會經(jīng)濟(jì)、個(gè)體差異、制度保障等諸多條件影響,農(nóng)民往往要么不參與協(xié)商、要么有參與無表達(dá)、要么有表達(dá)無實(shí)效。究其原因,農(nóng)民的協(xié)商參與有其自身邏輯,最重要的就是受其協(xié)商能力的制約,同時(shí)這種協(xié)商能力具有內(nèi)在的階梯和階序。那么,我國農(nóng)民協(xié)商能力的內(nèi)核是什么?存在哪些要素和標(biāo)準(zhǔn)?究竟何種組合與構(gòu)成能夠推動協(xié)商系統(tǒng)高質(zhì)量運(yùn)轉(zhuǎn)以達(dá)成有效協(xié)商?針對這些問題,本文擬對協(xié)商能力要素與框架的已有研究進(jìn)行梳理,從協(xié)商系統(tǒng)理論視角出發(fā),根據(jù)國際慣例與本土實(shí)際,嘗試提出適合中國農(nóng)民協(xié)商能力的分析框架,并運(yùn)用框架模型對山東省Z縣、Y縣和安徽省T縣三個(gè)“國家級”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實(shí)驗(yàn)區(qū)圍繞鄉(xiāng)村建設(shè)行動開展的協(xié)商實(shí)驗(yàn)進(jìn)行分析,評估案例所展現(xiàn)的協(xié)商系統(tǒng)的能力與質(zhì)量類型,以期為相關(guān)理論研討和實(shí)踐探索提供參考。
2.文獻(xiàn)綜述
國際學(xué)界關(guān)于協(xié)商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gè)方面:第一,協(xié)商質(zhì)量視角。德雷澤克開創(chuàng)性地從民主質(zhì)量視角,建構(gòu)了真實(shí)性、包容性和因應(yīng)性的有效協(xié)商系統(tǒng)框架,以推動協(xié)商能力建設(shè)。⑤妮可·庫拉托將協(xié)商能力作為分析民主質(zhì)量的一個(gè)組成部分,并應(yīng)用在菲律賓政黨制度和政治體系研究中,建立了公共空間、授權(quán)空間、傳播機(jī)制的協(xié)商能力分析框架。⑥第二,協(xié)商系統(tǒng)視角。塞拉納·佩德里尼從經(jīng)典的協(xié)商標(biāo)準(zhǔn)(如尊重和合理性論證)以及擴(kuò)展的協(xié)商形式(如講故事)來理解公民和政治精英兩種不同政治身份的協(xié)商能力和質(zhì)量。⑦唐貝貝認(rèn)為,協(xié)商能力建設(shè)是一個(gè)使公民參與政治體系、積累民主經(jīng)驗(yàn)的過程,具體可通過社會能力、制度能力和協(xié)商系統(tǒng)三個(gè)維度來實(shí)現(xiàn),這三個(gè)維度分別側(cè)重于公共領(lǐng)域、授權(quán)空間和協(xié)商行為者。⑧卡洛琳娜·米萊維茨等人則通過對國際組織案例的研究,認(rèn)為協(xié)商能力有兩大類相關(guān)因素:一是內(nèi)含包容性、真實(shí)性、公共空間、話語紀(jì)律的“高質(zhì)量協(xié)商能力”(協(xié)商輸入);二是內(nèi)含賦權(quán)空間、傳播、反饋回路的“外部效應(yīng)協(xié)商能力”(協(xié)商輸出)。⑨簡·蘇伊特等人進(jìn)一步指出,協(xié)商能力是指公民參與協(xié)商性政治決策的能力,包括一組資源和能力,協(xié)商能力可以幫助公民在做出政治決定之前與他人進(jìn)行協(xié)商。協(xié)商能力集中體現(xiàn)在信息資源和情感能力兩方面,前者提供事實(shí)知識,后者提供必要的同理心。⑩第三,協(xié)商心理視角。較具代表性的是朱莉婭·詹斯塔爾的觀點(diǎn),她從心理結(jié)構(gòu)視角,證明了復(fù)雜思維能力作為衡量協(xié)商能力的潛在有用性,并認(rèn)為其對女性和持更開放觀點(diǎn)者的影響更為顯著。
國內(nèi)學(xué)者關(guān)于協(xié)商能力的研究主要有兩條進(jìn)路:一是組織的協(xié)商能力分析。王維研究了參政黨的協(xié)商能力,認(rèn)為協(xié)商能力是個(gè)體因素、組織因素、制度因素的有機(jī)結(jié)合和綜合運(yùn)用。孫發(fā)鋒認(rèn)為中國社會組織協(xié)商能力是社會組織在協(xié)商活動中體現(xiàn)出的力量、能量和本領(lǐng),由政治把握能力、內(nèi)部治理能力、利益代表能力、調(diào)查研究能力、對話溝通能力五種要素構(gòu)成。二是個(gè)體的協(xié)商能力探討。李笑宇將公民的協(xié)商能力界定為邏輯推理能力、言說能力、判斷能力以及樂于表達(dá)的性格,他還認(rèn)為協(xié)商能力受經(jīng)濟(jì)、教育、文化、性格等多方面的影響。談火生以浙江省溫嶺市的民主懇談為例研究了代表的協(xié)商能力,認(rèn)為協(xié)商能力可以通過制作議題手冊和邀請專家培訓(xùn)等方式來提高。筆者所在團(tuán)隊(duì)運(yùn)用協(xié)商系統(tǒng)理論,發(fā)現(xiàn)設(shè)置開放協(xié)商論壇、多元化協(xié)商信息傳播以及體系化協(xié)商流程可以有效提升農(nóng)民的協(xié)商能力。此外,筆者及其團(tuán)隊(duì)還探討了社區(qū)能力與協(xié)商能力、協(xié)商質(zhì)量之間的關(guān)系,認(rèn)為社區(qū)能力的不同導(dǎo)致協(xié)商系統(tǒng)不同類型的形成,從而呈現(xiàn)不同的社區(qū)協(xié)商能力和協(xié)商質(zhì)量。
綜上所述,國際上已有文獻(xiàn)大多基于協(xié)商系統(tǒng)的分析,分別從國際事務(wù)、政黨事務(wù)、政治體系、身份和性別差異等方面對協(xié)商能力進(jìn)行了探討,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與測量指標(biāo)兩個(gè)方面。不難發(fā)現(xiàn),國際學(xué)界對協(xié)商能力的研究雖然已有突破,但相關(guān)要素框架尚未關(guān)注農(nóng)民這一協(xié)商主體,更未對中國經(jīng)驗(yàn)加以闡釋。而國內(nèi)關(guān)于協(xié)商能力的研究相對較少,且呈現(xiàn)以下特點(diǎn):首先,研究對象多集中于政黨、社會組織的協(xié)商能力,對農(nóng)民的協(xié)商能力涉及較少,這與國際研究的進(jìn)展相似;其次,研究視角缺乏對國際學(xué)術(shù)前沿的追蹤,已有研究要么集中在微觀的協(xié)商論壇,要么在宏觀的公共領(lǐng)域,運(yùn)用協(xié)商系統(tǒng)理論對協(xié)商能力進(jìn)行考量尚處于起步階段;最后,研究內(nèi)容尚未系統(tǒng)建立探討協(xié)商能力的分析框架與測量指標(biāo)。因此,基于對國內(nèi)外協(xié)商能力研究現(xiàn)狀的把握,推動對農(nóng)民協(xié)商能力分析框架的建構(gòu)既具有理論意義,也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
二、協(xié)商能力階梯:高質(zhì)量協(xié)商系統(tǒng)的分析框架
對國內(nèi)外文獻(xiàn)梳理可見,將協(xié)商能力置于協(xié)商系統(tǒng)中進(jìn)行研究很有必要。早期協(xié)商民主理論的批評者們認(rèn)為,多數(shù)協(xié)商民主實(shí)證研究都集中在“如一次性的小組討論或同一小組或同一類型機(jī)構(gòu)的單獨(dú)討論事件”上,協(xié)商民主因其有限的適用目標(biāo)、實(shí)現(xiàn)形式、參與主體出現(xiàn)了“窄化”傾向,遭遇解釋力不足的質(zhì)疑。對此,協(xié)商民主論者提出了協(xié)商系統(tǒng)理論予以回應(yīng),該理論的重要優(yōu)勢在于運(yùn)用系統(tǒng)性方法超越既有的對單個(gè)協(xié)商機(jī)構(gòu)和協(xié)商過程的研究,從整體上考察它們在整個(gè)協(xié)商系統(tǒng)中的相互作用,以產(chǎn)生一個(gè)健康的協(xié)商系統(tǒng)。德雷澤克等人認(rèn)為,協(xié)商能力建設(shè)是由協(xié)商系統(tǒng)不同部分之間相互關(guān)系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可以在不同制度中以不同的方式體現(xiàn)出來。不容忽視的是,農(nóng)民的組織化參與和個(gè)性化表達(dá)可謂是協(xié)商民主參與的“一幣兩面”,真實(shí)的協(xié)商民主并不可能只存在有序的主體參與,因?yàn)閰f(xié)商主體的差異化偏好必然導(dǎo)致不同的協(xié)商表達(dá)與訴求,統(tǒng)籌考慮不同形態(tài)的協(xié)商主體參與同樣離不開系統(tǒng)視角。總的來說,在協(xié)商系統(tǒng)理論框架下分析協(xié)商能力,既能統(tǒng)籌考慮微觀公眾論壇和公共協(xié)商領(lǐng)域,又可注重對話等協(xié)商方式之外的亞協(xié)商方式,還實(shí)現(xiàn)了協(xié)商與決策的銜接。
在借鑒和吸納國際已有協(xié)商能力要素標(biāo)準(zhǔn)基礎(chǔ)上,結(jié)合筆者研究團(tuán)隊(duì)對本土農(nóng)村基層協(xié)商民主實(shí)踐的長期觀察,從協(xié)商系統(tǒng)視角分析協(xié)商能力,筆者發(fā)現(xiàn)本土化的社區(qū)協(xié)商能力主要表現(xiàn)為參與意識、規(guī)則掌握、溝通互動、技術(shù)技能、包容決斷五個(gè)方面,這五個(gè)要素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協(xié)商能力的強(qiáng)弱。同時(shí),這五個(gè)要素構(gòu)成了協(xié)商能力的階梯:一是參與意識。參與意識可視為行動者相關(guān)行為的心理動機(jī)或狀態(tài),積極的參與意識會轉(zhuǎn)化為自覺的參與行為。參與意識是農(nóng)民協(xié)商能力形成的基礎(chǔ)性條件,沒有參與意識,其他能力無從談起。因此,參與意識在能力階梯中處于第一梯度。二是規(guī)則(程序)掌握。規(guī)則是約束行動者必須、可以或禁止采取相關(guān)行動的規(guī)定。規(guī)則掌握體現(xiàn)著農(nóng)民協(xié)商能力的主動性條件,主動了解協(xié)商規(guī)則有助于農(nóng)民合理表達(dá)自己的意見,這是確保協(xié)商治理制度化的必然選擇。因此,規(guī)則掌握處于第二梯度。三是(真實(shí)的)溝通互動。安德烈·巴赫泰格在《牛津協(xié)商民主手冊》中將相互溝通視為協(xié)商的最低限度,具體包括權(quán)衡和思考共同關(guān)心的問題偏好、價(jià)值觀和利益。協(xié)商民主的過程實(shí)質(zhì)上是參與者之間溝通互動的過程,這種溝通的真實(shí)性離不開秩序保障,因此溝通互動處于第三梯度。四是技術(shù)技能。技術(shù)技能指的是參與者在協(xié)商中擁有的產(chǎn)生話語民主的一種優(yōu)勢,是技術(shù)技能突出者能夠借此對其他參與者的觀點(diǎn)與協(xié)商結(jié)果產(chǎn)生顯著影響的能力。技術(shù)技能彰顯著參與者的專業(yè)性,因此技術(shù)技能是第四梯度。五是包容決斷。包容決斷是一個(gè)復(fù)合概念,其中包容是協(xié)商系統(tǒng)的最大特征,決斷是建立在充分協(xié)商要素基礎(chǔ)上起關(guān)鍵作用的環(huán)節(jié)。包容是決斷的前提,決斷是包容的目的。包容決斷可以理解為參與者在對不同觀點(diǎn)充分傾聽的基礎(chǔ)上做出的最優(yōu)決策。這種理想狀態(tài)需要以參與者的公共性為依托,所以包容決斷是第五梯度。在這五大要素組成的階梯模型中,農(nóng)民協(xié)商能力就像梯子上的臺階層層遞進(jìn),協(xié)商能力隨著階梯的上升也依次提高。
協(xié)商能力的五要素和階序性,實(shí)際上形成了協(xié)商能力的分析框架,即協(xié)商能力可以從五個(gè)要素及其對應(yīng)的特征加以測量。協(xié)商能力框架有以下要點(diǎn):第一,協(xié)商能力是這五個(gè)要素的函數(shù),農(nóng)民在協(xié)商參與中具備的要素越全面和高級,其展現(xiàn)的協(xié)商能力越強(qiáng),越可能達(dá)成協(xié)商系統(tǒng)的高質(zhì)量,進(jìn)而達(dá)成好的社區(qū)治理,實(shí)現(xiàn)社區(qū)善治。第二,當(dāng)目標(biāo)群體的五個(gè)要素有所缺乏時(shí),所呈現(xiàn)的協(xié)商能力與協(xié)商系統(tǒng)質(zhì)量并不能處于理想狀態(tài),比如當(dāng)農(nóng)民的溝通互動并不真實(shí)、流于形式時(shí),其展現(xiàn)出的協(xié)商能力就不充分,協(xié)商結(jié)果也不能全面反映農(nóng)民的訴求。第三,協(xié)商能力五個(gè)要素有其相對應(yīng)的特點(diǎn),分別是基礎(chǔ)性、主動性、秩序性、專業(yè)性、公共性,這些特點(diǎn)是衡量相關(guān)要素的指標(biāo),特點(diǎn)的彰顯程度不同會形成不同的協(xié)商組合,進(jìn)而決定協(xié)商能力的高低。第四,協(xié)商能力五個(gè)要素呈現(xiàn)梯次推進(jìn)的狀態(tài)。能力次序的形成受到協(xié)商開展的邏輯順序的影響,同時(shí)前一階段要素的具備往往是后一階段要素呈現(xiàn)的前提與基礎(chǔ),前者缺乏時(shí)后者也較難形成。因此,只有重視滿足協(xié)商能力的要素及其順序,才能達(dá)到較高層次的協(xié)商能力,從而達(dá)成協(xié)商系統(tǒng)的高質(zhì)量(見圖1)。當(dāng)然,協(xié)商能力階梯模型能否解釋中國實(shí)踐,還需從案例中加以考察。

圖1 協(xié)商能力階梯模型
三、鄉(xiāng)村建設(shè)行動中三個(gè)農(nóng)村社區(qū)的協(xié)商實(shí)驗(yàn)案例
2018年1月,民政部首次在全國選取48個(gè)縣市區(qū)作為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實(shí)驗(yàn)區(qū)開展試點(diǎn),山東省Z縣、Y縣和安徽省T縣入選其中。2019年年底至2020年年初,筆者所在研究團(tuán)隊(duì)代表民政部對Z縣、Y縣和T縣進(jìn)行了中期評估,重點(diǎn)就每個(gè)實(shí)驗(yàn)區(qū)的一個(gè)協(xié)商實(shí)驗(yàn)案例進(jìn)行現(xiàn)場觀摩和考核。實(shí)地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三個(gè)實(shí)驗(yàn)區(qū)的協(xié)商主題均圍繞鄉(xiāng)村建設(shè)行動(包括村莊規(guī)劃、基礎(chǔ)設(shè)施、環(huán)境整治、公共服務(wù)、農(nóng)村消費(fèi)、城鄉(xiāng)融合、投入保障、農(nóng)村改革8個(gè)方面)的相關(guān)內(nèi)容展開,但具體的協(xié)商議題有差別,表現(xiàn)出的協(xié)商能力特征、協(xié)商系統(tǒng)類型、協(xié)商質(zhì)量高低各有不同。從以上建構(gòu)的協(xié)商能力階梯和協(xié)商質(zhì)量分析框架來看,三個(gè)農(nóng)村社區(qū)協(xié)商實(shí)驗(yàn)案例形成了一組比較樣本。基于協(xié)商系統(tǒng)視角,這三個(gè)案例總體呈現(xiàn)以下三種樣態(tài)。
案例一是Z縣D社區(qū)的土地流轉(zhuǎn)協(xié)商。D社區(qū)二村位于鎮(zhèn)政府東北8公里處,是社區(qū)的中心村,有185戶676人,黨員22名,2019年村集體經(jīng)濟(jì)收入約為50萬元。二村自2013年開始將農(nóng)戶與集體的600多畝土地流轉(zhuǎn)給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精品園,每畝價(jià)格為800—1000元。在協(xié)商組織方面,D社區(qū)二村的協(xié)商實(shí)踐依托村委會開展,并未成立專門的村級協(xié)商組織。在協(xié)商主題方面,該村由3名村民代表提出土地流轉(zhuǎn)的協(xié)商主題,協(xié)商會議決定其余300多畝土地是否進(jìn)行流轉(zhuǎn)。在協(xié)商主體方面,共有24人參加了協(xié)商會議,包括社區(qū)“兩委”成員、居民代表、駐村工作組,人員構(gòu)成由村“兩委”指定,并未邀請種田大戶與會。在協(xié)商場所方面,協(xié)商會議在村會議室召開。在協(xié)商進(jìn)程方面,首先由村黨支部書記作為主持人提出議題,并對議題進(jìn)行簡要分析,然后參會者挨個(gè)表態(tài),均持肯定意見,最終參會者24人舉手表決一致同意。在協(xié)商結(jié)果方面,協(xié)商代表全票通過,下一步村“兩委”將入戶征求意見,再召開戶主會做出最終決定。
案例二是Y縣K社區(qū)的大廳重建協(xié)商。K社區(qū)位于縣城北10公里處,覆蓋3個(gè)自然村,共有980戶2450人,黨員206名,2019年社區(qū)集體收入達(dá)800余萬元。在協(xié)商組織方面,K社區(qū)的協(xié)商實(shí)踐依托居委會開展,未成立專門的村級協(xié)商組織。在協(xié)商主題方面,社區(qū)既有的紅白理事會大廳條件較差,開展相關(guān)活動多有不便,故社區(qū)一名退休老干部提出重建紅白理事會大廳的協(xié)商主題。在協(xié)商主體方面,共有20人參加了協(xié)商會議,包括社區(qū)“兩委”成員、居民代表、老黨員、婦女代表、退休老干部、居務(wù)監(jiān)督委員會成員,同時(shí)還邀請了鎮(zhèn)政府規(guī)劃辦、經(jīng)管站、民政辦等相關(guān)人員,具體的人員構(gòu)成由社區(qū)“兩委”選定。在協(xié)商場所方面,協(xié)商會議在居民議事室召開。在協(xié)商進(jìn)程方面,首先由黨支部書記作為主持人提出議題,并對議題進(jìn)行簡要介紹,然后代表發(fā)言,除18人持同意觀點(diǎn)外,還有2位代表以“可以裝空調(diào)改善”“能將就”為由反對,在聽取其他代表發(fā)言后,反對者立馬表示了贊同。在協(xié)商結(jié)果方面,隨著相關(guān)業(yè)務(wù)部門發(fā)言完畢,協(xié)商議題順利通過,后續(xù)還需居民(代表)會議通過后組織建設(shè),落實(shí)期限為1年。
案例三是T縣X社區(qū)的農(nóng)戶換田協(xié)商。X社區(qū)位于鎮(zhèn)中心,由3個(gè)行政村合并而來,轄33個(gè)居民組,總?cè)丝谟?365人,黨員90人,2019年社區(qū)集體經(jīng)濟(jì)收入為14.3萬元。在協(xié)商組織方面,T縣在全縣174個(gè)村(社區(qū))均成立了專門的協(xié)商組織——協(xié)商委員會,X社區(qū)也不例外。在協(xié)商主題方面,社區(qū)以農(nóng)戶換田為協(xié)商主題,由于兩個(gè)居民小組部分土地互有交叉,相當(dāng)數(shù)量農(nóng)戶的取水、耕種等受到影響,因此X社區(qū)圍繞換地協(xié)調(diào)事宜開展協(xié)商。協(xié)商主題由居民向所在居民小組組長反映,議題符合該縣民政局制訂的《協(xié)商目錄》對協(xié)商議題的規(guī)定,于是協(xié)商委員會按協(xié)商流程開展協(xié)商。在協(xié)商主體方面,共有20人參加了協(xié)商會議,包括社區(qū)“兩委”成員、居民代表、鄉(xiāng)賢能人、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理事會和監(jiān)事會成員、居民小組代表、普通居民與換田當(dāng)事人,其構(gòu)成包括協(xié)商委員會成員以及利益相關(guān)方。在協(xié)商場所方面,三輪協(xié)商分別在社區(qū)議事廳、農(nóng)戶家中以及田地現(xiàn)場召開。在協(xié)商進(jìn)程方面,由于與會方利益分歧較大,協(xié)商委員會基于公共利益至上原則做通居民小組代表的工作,又通過居民小組代表對重點(diǎn)農(nóng)戶進(jìn)行情感說服。在協(xié)商結(jié)果方面,經(jīng)歷三輪協(xié)商后,協(xié)商雙方順利簽署換田協(xié)議,協(xié)商委員會負(fù)責(zé)監(jiān)督并作為見證方簽字,社區(qū)集體經(jīng)濟(jì)股份合作社理事會和監(jiān)事會成員負(fù)責(zé)土地丈量與補(bǔ)償費(fèi)用核算。
四、案例社區(qū)協(xié)商能力和協(xié)商系統(tǒng)質(zhì)量的比較及其類型轉(zhuǎn)化
從上述比較中可知,三個(gè)社區(qū)協(xié)商案例展現(xiàn)出了其強(qiáng)弱不同的協(xié)商能力以及相對差別的協(xié)商特征,并對應(yīng)著高低各異的協(xié)商系統(tǒng)質(zhì)量。同時(shí),在協(xié)商能力階梯中,隨著協(xié)商能力的提升,協(xié)商系統(tǒng)也朝著更高質(zhì)量推進(jìn)。
秦鐵崖耐心勸說:“目前,依你的實(shí)力,想剿滅風(fēng)云八虎,打敗八虎的總后臺德公公,比登天還難。請相信我,這事我能了結(jié)。”
1.Z縣D社區(qū):土地流轉(zhuǎn)的“咨詢型協(xié)商”
從Z縣D社區(qū)二村在土地流轉(zhuǎn)協(xié)商中展現(xiàn)的協(xié)商能力看,其呈現(xiàn)“咨詢型協(xié)商”的特點(diǎn)。第一,參與意識方面。在D社區(qū)二村協(xié)商實(shí)踐中,協(xié)商主題與村民收益密切掛鉤,已流轉(zhuǎn)土地的村民嘗到了甜頭,其他村民也想搭上土地流轉(zhuǎn)“順風(fēng)車”,所以村民對此次協(xié)商會議的參與意識較強(qiáng)。只有當(dāng)參與者了解或愿意了解某個(gè)特定問題時(shí),對該問題的協(xié)商才會有效。可見,較強(qiáng)的參與意識顯著影響協(xié)商能力,進(jìn)而提升了協(xié)商系統(tǒng)的質(zhì)量。第二,規(guī)則(程序)掌握方面。雖然縣級層面制定了協(xié)商指導(dǎo)規(guī)程24條和指導(dǎo)目錄56項(xiàng),但各村(社區(qū))在協(xié)商開展階段,仍以收集意見建議為主,體現(xiàn)為咨詢形式,相關(guān)規(guī)則(程序)實(shí)際上并未有效運(yùn)轉(zhuǎn)。在對D社區(qū)二村的協(xié)商進(jìn)行觀摩時(shí),筆者也發(fā)現(xiàn)農(nóng)民的規(guī)則(程序)掌握效果一般,主要靠主持人引導(dǎo)。第三,(真實(shí)的)溝通互動方面。D社區(qū)二村在此次協(xié)商實(shí)踐中,由于本次會議旨在征詢村民意向,不涉及與種田大戶進(jìn)行價(jià)格探討,代表在發(fā)言時(shí),均對土地流轉(zhuǎn)持肯定意見,缺乏反對意見以及代表之間的討論,現(xiàn)場氣氛較為沉悶,總體上參與者溝通互動情況不夠理想。第四,技術(shù)技能方面。D社區(qū)二村圍繞土地流轉(zhuǎn)開展協(xié)商時(shí),主要是村民代表在場,與會的駐村工作組不具備專業(yè)性,并未邀請相關(guān)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管理部門、種田大戶與會,因此協(xié)商會議技術(shù)技能含量不高。第五,包容決斷方面。包容性被協(xié)商系統(tǒng)論者視為核心要素,只有在包容性基礎(chǔ)上做出合理的協(xié)商決斷,才能具備充分的合法性。而在D社區(qū)二村協(xié)商案例中,因缺少溝通互動與反對意見,包容決斷因素彰顯不足。總體來看,在Z縣協(xié)商案例中,村民協(xié)商參與意識雖然得到激發(fā),但規(guī)則(程序)設(shè)置并不明確,溝通互動浮于表面,只是簡單的問題咨詢和意見收集,同時(shí)也缺乏專業(yè)人士加入,包容決斷方面略有欠缺。Z縣D社區(qū)的農(nóng)民并未在協(xié)商議事中體現(xiàn)出較強(qiáng)的協(xié)商能力,協(xié)商主要是為了聽取群眾意見,整體呈現(xiàn)應(yīng)對性咨詢特征,是一種“咨詢型協(xié)商”。
2.Y縣K社區(qū):大廳重建的“回應(yīng)型協(xié)商”
從Y縣K社區(qū)在協(xié)商中展現(xiàn)的協(xié)商能力來看,其呈現(xiàn)“回應(yīng)型協(xié)商”的特征。第一,參與意識方面。農(nóng)村社區(qū)是“熟人社會”,人情往來是關(guān)系維系的紐帶,紅白理事會大廳作為人情往來的重要載體,與每一位村(居)民息息相關(guān),因此K社區(qū)除指定的居民代表參會外,還有老黨員參與,展現(xiàn)的參與意識較強(qiáng)。第二,規(guī)則掌握方面。會議大體按照“提出議題—與會人員討論發(fā)言—專業(yè)人員發(fā)言—形成決議”的既定程序開展,當(dāng)?shù)鼐用駥f(xié)商規(guī)則與程序的掌握情況較好。第三,(真實(shí)的)溝通互動方面。會議出現(xiàn)了反對者,其在聽取其他意見后有所反思,由此可判定當(dāng)?shù)剞r(nóng)民具備一定的溝通互動能力。第四,技術(shù)技能方面。4位相關(guān)業(yè)務(wù)部門同志參會回應(yīng),從專業(yè)性上為參會者給予指導(dǎo)意見,極大提升了代表的協(xié)商技術(shù)技能。第五,包容決斷方面。兩位反對者在聽取其他代表發(fā)言后改變了自己的觀點(diǎn),協(xié)商會議也在此基礎(chǔ)上做出了最終決斷,可以認(rèn)定K社區(qū)農(nóng)民的協(xié)商包容決斷能力尚可。總體來看,在Y縣協(xié)商案例中,居民展現(xiàn)出較好的協(xié)商參與意識,對于規(guī)則(程序)具有相當(dāng)程度的了解和運(yùn)用,形成較為良性的溝通互動,同時(shí)通過邀請業(yè)務(wù)部門與會回應(yīng),增加了協(xié)商的技術(shù)技能,初步具備了包容決斷特質(zhì)。盡管還存在上升空間,但Y縣K社區(qū)農(nóng)民已經(jīng)在協(xié)商議事中顯現(xiàn)出一定的協(xié)商能力,社區(qū)和業(yè)務(wù)部門也通過協(xié)商會議在一定程度上回應(yīng)了群眾需求。顯然,這是一種“回應(yīng)型協(xié)商”。
3.T縣X社區(qū):農(nóng)戶換田的“包容型協(xié)商”
從T縣X社區(qū)在協(xié)商中展現(xiàn)的協(xié)商能力來看,其呈現(xiàn)“包容型協(xié)商”的特征。第一,參與意識方面。有8位居民小組代表、普通居民作為利益相關(guān)方代表主動參加協(xié)商會議。這在三個(gè)案例中數(shù)量最多,因此判斷當(dāng)?shù)剞r(nóng)民協(xié)商參與意識較強(qiáng)。第二,規(guī)則掌握方面。T縣曾經(jīng)通過問卷形式向全部174個(gè)農(nóng)村(社區(qū))群眾調(diào)查對協(xié)商民主的知曉度,調(diào)查方式為隨機(jī)抽查,問卷包括與協(xié)商規(guī)則相關(guān)的問題,X社區(qū)共有31人參與調(diào)查,其中18人得到100分,11人得分在80—99分之間,因此可以認(rèn)為當(dāng)?shù)鼐用駞f(xié)商規(guī)則掌握能力較強(qiáng)。第三,(真實(shí)的)溝通互動方面。兩個(gè)小組就換田事宜共開展三次協(xié)商,雖然X社區(qū)干部通過多種方式說服雙方代表,但換田協(xié)議仍因歷史遺留問題、部分農(nóng)戶對置換價(jià)格不滿意等情況而多次擱置,最終協(xié)議在找準(zhǔn)利益平衡點(diǎn)后得以順利簽署。在此期間,利益相關(guān)者表達(dá)充分,溝通互動真實(shí)性較高。第四,技術(shù)技能方面。協(xié)商系統(tǒng)理論認(rèn)為協(xié)商還應(yīng)妥善利用非協(xié)商方式。當(dāng)協(xié)商民主發(fā)生在農(nóng)村場域,鄉(xiāng)土社會既有的協(xié)商資源可以在推動協(xié)商落地時(shí)發(fā)揮重要作用。X社區(qū)在協(xié)商中邀請鄉(xiāng)賢做工作,運(yùn)用鄉(xiāng)賢“感情”“道理”“面子”等特殊的技術(shù)技能,具有較強(qiáng)的鄉(xiāng)村情景適用性,因此可以認(rèn)為當(dāng)?shù)剞r(nóng)民在技術(shù)技能方面能力較強(qiáng)。第五,包容決斷方面。協(xié)商屢次無果后,X社區(qū)反復(fù)借助公共集體利益和“情感牌”方式提升參與者的包容能力,最終做出了雙方都能接受的協(xié)商決斷。可以說,農(nóng)民的包容決斷能力隨著協(xié)商進(jìn)程獲得了極大提升。總體來看,在T縣的協(xié)商案例中,居民協(xié)商參與意識較強(qiáng),對于規(guī)則(程序)掌握情況較好,具備真實(shí)的溝通互動,運(yùn)用人情的技術(shù)技能推動協(xié)商,最終做出最大限度包容參與者訴求的決斷。T縣X社區(qū)的農(nóng)民在協(xié)商議事中展現(xiàn)出較強(qiáng)的協(xié)商能力,以廣泛性參與和包容性協(xié)商發(fā)揮了自身在村莊事務(wù)中的積極作用,是一種“包容型協(xié)商”。
從以上對三個(gè)案例協(xié)商能力和協(xié)商質(zhì)量的評估比較中可以看出,三種協(xié)商類型呈現(xiàn)了協(xié)商能力的階梯遞進(jìn)和協(xié)商質(zhì)量的形態(tài)轉(zhuǎn)換邏輯。
一方面,協(xié)商能力階梯呈現(xiàn)著遞進(jìn)的過程。整體上看,從參與意識到包容決斷五大要素形成能力階梯,如同一個(gè)個(gè)臺階,階梯所處的高度代表協(xié)商能力的強(qiáng)度和協(xié)商質(zhì)量的高度。如T縣X社區(qū)的農(nóng)戶換田協(xié)商較好地具備了五大要素,協(xié)商能力自然也就較強(qiáng)。其中,處于能力階梯中的相對位置越低的要素越容易實(shí)現(xiàn),反之位置越高的要素越難實(shí)現(xiàn)。如技術(shù)技能、包容決斷兩大要素均屬于較高階段的協(xié)商能力,較難實(shí)現(xiàn)。此外,階梯之間存在進(jìn)階關(guān)系,只有滿足位置較低的要素后才可以“向上攀升”,進(jìn)階下一個(gè)要素。如滿足了參與意識這一條件后,就可以考慮規(guī)則(程序)掌握因素,若參與意識條件不具備,通常下一因素也即規(guī)則(程序)掌握因素也難以考慮。
另一方面,協(xié)商系統(tǒng)質(zhì)量會隨著協(xié)商能力的變化發(fā)生形態(tài)轉(zhuǎn)換。當(dāng)協(xié)商能力較強(qiáng)時(shí),相應(yīng)轉(zhuǎn)換的協(xié)商系統(tǒng)質(zhì)量較高,反之則較低。德雷澤克等人指出:“當(dāng)平衡的信息、專家證詞和由主持人監(jiān)督等條件都具備時(shí),則可認(rèn)為是一種安排良好的協(xié)商過程,此時(shí)普通人也有能力進(jìn)行高質(zhì)量的協(xié)商。”由于協(xié)商議題篩選、議程設(shè)置、規(guī)則執(zhí)行、組織架構(gòu)等環(huán)節(jié)的不同,以及農(nóng)村社區(qū)歷史傳統(tǒng)、村民個(gè)體差異等因素的影響,Z縣、Y縣和T縣三個(gè)協(xié)商案例所呈現(xiàn)的農(nóng)民協(xié)商能力各有差異,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協(xié)商系統(tǒng)質(zhì)量(見圖2)。在Z縣“咨詢型協(xié)商”中,雖然農(nóng)民的參與意識得到激發(fā),但協(xié)商主體未得到充分考慮,意見表達(dá)不夠全面,更多的是一種意向征詢或咨詢,協(xié)商系統(tǒng)質(zhì)量打了折扣。在Y縣“回應(yīng)型協(xié)商”中,若干反對意見被提出后,其他代表的發(fā)言引發(fā)了反對者的理性思考,最終在業(yè)務(wù)部門的介入及回應(yīng)后反對者打消了疑惑,體現(xiàn)出一定的協(xié)商系統(tǒng)質(zhì)量。在T縣“包容型協(xié)商”中,協(xié)商雙方充分溝通互動,運(yùn)用多種協(xié)商手段,經(jīng)過多輪協(xié)商后形成了書面協(xié)定,協(xié)商系統(tǒng)的質(zhì)量較高。隨著社區(qū)協(xié)商能力的提升,協(xié)商質(zhì)量也會發(fā)生相應(yīng)轉(zhuǎn)換,如Z縣隨著社區(qū)協(xié)商能力的提升獲得了協(xié)商系統(tǒng)質(zhì)量的提升,所處位置會攀升到Y(jié)縣所處的位置。

圖2 三種協(xié)商類型在協(xié)商能力與協(xié)商系統(tǒng)質(zhì)量框架中的位置
五、基本結(jié)論與啟示
新發(fā)展階段需要高質(zhì)量發(fā)展,民主協(xié)商也需要高質(zhì)量發(fā)展。通過協(xié)商能力階梯框架的建立,可以探究高質(zhì)量協(xié)商系統(tǒng)的實(shí)踐邏輯。農(nóng)民協(xié)商能力的提升,一方面能推動農(nóng)村基層協(xié)商系統(tǒng)高質(zhì)量發(fā)展,加快鄉(xiāng)村建設(shè)行動的開展,開創(chuàng)鄉(xiāng)村振興新局面;另一方面能向世界講好中國協(xié)商故事,推動中國協(xié)商經(jīng)驗(yàn)“走出去”,為全球協(xié)商民主理論的發(fā)展表達(dá)“中國話語”。因此,對協(xié)商能力的研究有著實(shí)踐和理論的雙重意義。在借鑒國際已有要素標(biāo)準(zhǔn)及把握中國協(xié)商實(shí)踐特點(diǎn)的基礎(chǔ)上,筆者嘗試提出包含五大要素的農(nóng)民協(xié)商能力階梯,并對在鄉(xiāng)村建設(shè)行動中產(chǎn)生的三個(gè)農(nóng)村社區(qū)協(xié)商實(shí)驗(yàn)案例進(jìn)行實(shí)證分析,評估其協(xié)商能力和協(xié)商系統(tǒng)質(zhì)量。通過上述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結(jié)論。
第一,協(xié)商系統(tǒng)理論和方法的引入能夠較好地評估和發(fā)展農(nóng)民協(xié)商能力。將農(nóng)民置于協(xié)商系統(tǒng)中,從系統(tǒng)的整體視角出發(fā)思考農(nóng)民協(xié)商能力的提升,克服了既有研究就農(nóng)民談農(nóng)民的“微觀傾向”。從Y縣K社區(qū)和T縣X社區(qū)的協(xié)商案例分析可見,它們都是站在協(xié)商系統(tǒng)的高度,通過專業(yè)人士、鄉(xiāng)賢的引入,以協(xié)商系統(tǒng)中的技術(shù)技能增加協(xié)商的專業(yè)性,成功彌補(bǔ)了農(nóng)民協(xié)商能力的不足。
第二,中國實(shí)踐的協(xié)商能力分析框架內(nèi)含五大要素并具有相應(yīng)的特點(diǎn)。中國特色的農(nóng)民協(xié)商能力框架主要包含參與意識、規(guī)則(程序)掌握、(真實(shí)的)溝通互動、技術(shù)技能、包容決斷五種要素,這五種要素分別對應(yīng)基礎(chǔ)性、主動性、秩序性、專業(yè)性、公共性等特點(diǎn)。當(dāng)相關(guān)要素具備時(shí),意味著農(nóng)民處于相對應(yīng)的協(xié)商能力階段;當(dāng)要素情況較好、種類較全時(shí),農(nóng)民所對應(yīng)的協(xié)商能力處于較高水準(zhǔn)。如在T縣X社區(qū)案例中,五種相關(guān)要素都已具備且比較充分,農(nóng)民所展現(xiàn)的協(xié)商能力也較高。當(dāng)然,農(nóng)民協(xié)商能力分析框架雖然針對的是農(nóng)民,但該框架對中國城鄉(xiāng)基層社區(qū)和相關(guān)領(lǐng)域同樣具有一定的借鑒性。
第三,協(xié)商能力框架內(nèi)部存在著階梯關(guān)系。五種能力構(gòu)成一種階梯模型,其中能力階梯的最底端是參與意識,最頂端是包容決斷,在框架階序內(nèi)部存在層層遞進(jìn)的關(guān)系。能力從低端到高端的發(fā)展既契合了協(xié)商實(shí)踐邏輯順序,其拾級而上又體現(xiàn)了農(nóng)民在協(xié)商能力方面走向成熟。一般情況下,階梯底端的能力得不到滿足時(shí),高端能力也無從談起。如在Z縣D社區(qū)二村的協(xié)商中,協(xié)商會議的意見表達(dá)不夠全面,致使后續(xù)幾項(xiàng)農(nóng)民協(xié)商能力的培育都受到影響。
第四,協(xié)商系統(tǒng)質(zhì)量的高低總體上可以通過協(xié)商能力來辨識。當(dāng)農(nóng)民有較高的參與協(xié)商的能力時(shí),他會在規(guī)則范圍內(nèi)提出自己的訴求,在與他人的交流中理性思考,并充分借鑒專業(yè)人士的意見,最終充分包容各方意見并在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礎(chǔ)上做出最佳決斷。此時(shí),我們可以認(rèn)為協(xié)商系統(tǒng)可能是高質(zhì)量的,這種高質(zhì)量源于農(nóng)民協(xié)商能力的提升。
第五,高質(zhì)量的協(xié)商系統(tǒng)有助于鄉(xiāng)村振興的實(shí)現(xiàn)。從理論上講,協(xié)商系統(tǒng)高質(zhì)量運(yùn)轉(zhuǎn)的最高目標(biāo)是達(dá)成高的協(xié)商績效,亦即治理有效,從而促進(jìn)鄉(xiāng)村振興的實(shí)現(xiàn)。從實(shí)踐出發(fā),文中三個(gè)案例均屬于鄉(xiāng)村建設(shè)行動,當(dāng)協(xié)商系統(tǒng)處于高質(zhì)量運(yùn)轉(zhuǎn)時(shí),其就為鄉(xiāng)村建設(shè)行動的開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進(jìn)而推動鄉(xiāng)村振興的實(shí)現(xiàn)。
基于以上結(jié)論,還可以得到以下啟示:一方面,在鄉(xiāng)村建設(shè)行動中要為培育農(nóng)民協(xié)商能力創(chuàng)造條件。農(nóng)民協(xié)商能力是農(nóng)村基層協(xié)商能力的核心要件,農(nóng)民這一協(xié)商主體的參與能力不能成為協(xié)商民主的“短板”,各級政府應(yīng)當(dāng)采取針對性策略有效提高農(nóng)民的協(xié)商能力,為協(xié)商系統(tǒng)高質(zhì)量運(yùn)轉(zhuǎn)和協(xié)商實(shí)踐的高層次發(fā)展貢獻(xiàn)力量。另一方面,在鄉(xiāng)村振興中要通過系統(tǒng)化路徑提升協(xié)商質(zhì)量。協(xié)商能力是協(xié)商質(zhì)量提升的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目前還存在一些影響協(xié)商質(zhì)量提升的相關(guān)因素,諸如協(xié)商議題篩選、議程設(shè)置、協(xié)商結(jié)果與執(zhí)行監(jiān)督等協(xié)商系統(tǒng)環(huán)節(jié),因此需要借助協(xié)商系統(tǒng)視角,從宏觀層面的協(xié)商出發(fā)提升協(xié)商質(zhì)量,為農(nóng)村社區(qū)有效治理貢獻(xiàn)協(xié)商的力量,從而找準(zhǔn)理解中國道路的基礎(chǔ)性進(jìn)口。需要注意的是,階梯順序是從一般意義上提出的,在不同的地區(qū)、場景、條件、事項(xiàng)等的協(xié)商過程中可能會有區(qū)別,有的要素可能缺失,有的甚至可能調(diào)換順序。因此,通過進(jìn)一步理論歸納與實(shí)踐探索,完善與修正協(xié)商能力框架將是未來的拓展方向。
注釋
- 中州學(xué)刊的其它文章
- 面向小農(nóng)戶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性服務(wù)演進(jìn)脈絡(luò)及供需復(fù)衡路徑*
- 宋金元時(shí)期冷兵器的技術(shù)管控及其對戰(zhàn)爭的影響
- 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代表達(dá)的創(chuàng)新路徑探析
——以河南衛(wèi)視“中國節(jié)日”系列節(jié)目為例 - 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我國網(wǎng)絡(luò)安全治理:特征、挑戰(zhàn)及應(yīng)對
- 現(xiàn)代性的雙面書寫
——論當(dāng)代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中的宏大敘事 - 新世紀(jì)文學(xué)編年史書寫的價(jià)值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