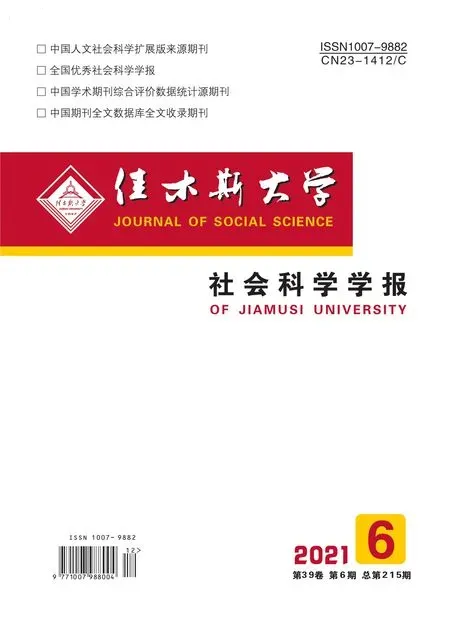馬克思的有機自然觀及其當代價值*
張 賽,劉 魁
(1.江蘇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無錫 214000;2.東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南京 210000)
工業革命與現代化給人類帶來了豐厚的物質財富,令人類歡呼雀躍。但隨之而來的是以環境污染、人口爆炸、能源短缺、物種滅絕等為特征的生態危機,如同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人類頭頂。面對病毒般侵略的生態危機,人類需要反省對待自然的態度、觀念和行為,重新樹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正確準則。馬克思重新詮釋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合理關系,反對近代以來將自然視為機器和實體的機械自然觀,給我們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馬克思既承認自然自身作為生命有機體的一面,又強調人類的主體性,將自然作為人類肢體延伸而同人類化作有機整體。因此,有必要系統地闡明馬克思的有機自然觀,包括其基本內涵及時代價值,為緩解甚至解決生態危機,清除人與自然之間的對立關系,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提供重要的理論基礎。
一、馬克思有機自然觀的理論淵源
馬克思在借鑒和批判伊壁鳩魯樸素能動自然觀、黑格爾唯心主義有機自然觀和費爾巴哈唯物主義抽象自然觀的基礎上,將各種理論精髓和自身思想火花、實踐經驗科學地結合在一起,創造性地以唯物主義和有機論的視角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形成獨特的有機自然觀。
(一)以伊壁鳩魯為代表的樸素能動自然觀
馬克思比較分析了伊壁鳩魯與德謨克里特自然哲學之間的差異,肯定伊壁鳩魯對宗教目的論的批判,獲得關于自然界深刻的唯物主義認識,進而論證人類自由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描繪出一個自由和自我決定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漸漸厘清人類與周圍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
伊壁鳩魯超越了德謨克里特原子論的機械性和決定性,認識到偶然性和自由的可能性,人類的思想不再歸結為自然面前被動的感覺。“原子脫離直線而偏斜卻把伊壁鳩魯同德謨克利特區別開來了。”[1]30原子偏離直線的運動在德謨克里特那里是不存在的,但是只有第二種運動才能較好地解釋偶然性。只有原子的偏斜,相互碰撞和沖擊,才能產生自然界各式各樣、豐富多彩的事物。因此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是一種能動的、偶然性的理論,馬克思明確指出,“因此,從歷史上看有一個事實是確實無疑的:德謨克利特使用必然性,伊壁鳩魯使用偶然,并且每個人都以論戰的激烈語調駁斥相反。”[1]27正是這種偶然性、原子偏斜打破了“命運的束縛”。人類的能動性得到了極大的張揚,這說明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
但是,伊壁鳩魯將自由歸結為單純存在于自我意識中的自由,面對外界現實不做合理的抗爭,而是追求精神和自由的獨立。馬克思認為伊壁鳩魯“抽象的個別性是脫離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發亮。”定在的自由不能離開自我意識外化產生的物質性存在,定在的自由就是現實的自由,只有丟掉抽象的個別性而使其成為物質才能到達自由彼岸。自由的實現絕不僅僅是自我意識和觀念中的自憐自艾。馬克思指出,“由于有了質,原子就獲得同它的概念相矛盾的存在,就被設定為外在化了的、同它自己的本質不同的定在”[2]。
而定在中的自由并不絕對,需要進一步需要人類客克服自身的制約,達到自在自為的狀態。人類具有外在自然和內在自然兩種束縛,即人類內在野蠻的、非理性的欲望沖突,還有外界的物質環境。人的自由問題如同原子之間的排斥離開現實的排斥僅僅停留在自我意識之中,定在中的自由和自在自為的自由都無法實現。人與人之間只有建立起社會關系,在人與人之間相互作用的關系之中,人類才能擺脫定在的純粹自然狀態和孤立個體的野性狀態。
馬克思認為,自由的問題不能抽象地理解,實現自由絕不能將人與周圍環境割裂開來,把二者對立起來的方法也是不可取的。人類不能被看作是抽象的個別性,要將人類與周圍環境的相互聯系和作用綜合起來考察,這樣才能夠解決自由問題。這個時候馬克思已經看到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和緊密聯系,人不能脫離自然存在,必須將其放在周圍環境中對待。人與環境是密切聯系和相互作用的,否則只會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只有在環境中人的自由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二)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唯心主義有機自然觀
眾所周知,黑格爾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他的偉大之處在于建立起全面的、百科全書式的唯心主義體系,覆蓋美學、倫理學、法學等諸多領域,并極大發展了辯證法。黑格爾從既是實體又是主體的唯心規定即絕對精神出發,描述絕對精神自我發展的歷史,揭示了其發展的階段和內在必然聯系。黑格爾在絕對精神自我發展的第二階段——自然哲學,主要論述了他的唯心論有機自然觀。總體上來看,黑格爾將自然界視作一個理念透視下辯證發展、相互作用的有機系統,雖然從根基和過程中貫徹著絕對精神。
首先,在黑格爾那里,自然的存在是理念自身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自我異化和外化的結果。黑格爾宣稱,“自然是作為他在形式中的理念產生出來的……外在性就夠成自然的規定,在這種規定中自然才作為自然而存在”。“自然是自我異化的精神。”[3]20黑格爾這里對自然的闡述是清晰的,在他的哲學建構中,自然是理念的否定性存在,是理念自身內在矛盾擴散開的結果。同時外在性構成自然的規定,這就是自然的起因和本性。這里的外在性是相對理念內在而言的,不是指自然界相對人類在內的外在優先性,理念的自我異化使得自然獲得自身規定性而得以自我顯現。
其次,黑格爾認為自然界是一個由眾多階段夠成的活生生的、統一的整體。黑格爾指出,“自然必須看作是一種由各個階段組成的體系,其中一個階段是從另一個階段必然產生的。”[3]28自然不是自然科學上所凝固的孤立的靜態物,而是運動發展著的有機的整體。自然整體在內在本性決定著自身由一個階段不斷發展轉化為另一個高級階段。
最后,自然是一個活生生的整體,自由貫穿著自然發展的整個過程。有機統一體可以自己產生、創造自己,維持自身的可持續發展。這是一種內在目的性的自我復歸的循環過程。“概念按照發展的使命,進行合乎目標的發展,或者如果人們愿意的話,也可以說是進行合乎目的的發展。”[3]34“真正的目的論考察在于把自然看作在其特有的生命活動內是自由的,這種考察是最高的。”[3]8自由恰恰是自然發展的內在合目的性,也正是自然的這種內在目的使得自然是由各個階段組成的體系,呈現出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自然是一個統一的理想的有機整體或生命。
黑格爾自然觀中的唯心的部分雖不可取,但是自然觀中有機、整體思想有其合理之處,不應遮蔽。黑格爾關于自然界中無機領域向有機生命領域的發展,以及將自然界作為一個活生生的有機整體來看的觀點對以后現代科學中控制論和系統論等科學理論產生很大影響,尤其對馬克思有機自然觀的建立產生深刻的影響。馬克思很好地吸收了其中關于有機體思想的合理之處,并指出精神外殼下的自然的謬誤,“對他說來整個自然界不過是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重復邏輯的抽象而己。”[4]179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馬克思建立其深刻的關于自然實在的有機自然觀。
(三)以費爾巴哈為代表的唯物主義抽象自然觀
費爾巴哈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唯物主義代表,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唯物主義抽象自然觀基礎上深入了解到自然的生成屬性,破除了黑格爾絕對精神的迷障,認識到有機生物與環境之間存在一種特殊的有機關系,在實踐的基礎上將人與自然聯系起來,給有機自然觀的建立打下良好基礎。
費爾巴哈認為自己的哲學是“新哲學”,以區別過去傳統的唯心主義哲學,他經常講自己的哲學的基本內容就是兩個:自然界和人。他認為,自然界是一個客觀的存在,是一個現實的、感性的無限的、永恒實體。自然界在時間和空間上是無限的,是無意識的,不是上帝或者某種絕對精神、純粹邏輯派生出來的,自然界由于自身的原因而始終存在和變化。這是與黑格爾的哲學理念針對相對的。費爾巴哈指出,“我所說的自然界,就是人拿來當作非人性的東西而從自己分別出去的一切感性的力量、事物和本質之總和。”[5]591人類應當按照自然界或者客觀世界的本來面貌認識各種事物和現象,自然界不依賴于人的精神,是在任何精神狀態之外存在的。
費爾巴哈在物質本身找到了自然的基礎。自然界涵蓋了我們所所知的一切事物,如果我們的感官覺察不到他們,那么這些事物根本不存在,不存在任何不可感知的“自在之物”。費爾巴哈強調物質世界是客觀的、豐富多樣的,而且這種多樣性在起初就是這樣,并不是由于背后某種精神實體的作用而派生出來的。
費爾巴哈可以說是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但另一方面他的自然觀又是抽象自然觀,認為自然界是直觀的、純粹的。自然是人類生存的物質本真基礎,是人們感性活動的對象性存在。自然界在外部保持著優先地位,人類在自然界中獲取生活資料,依賴自然界,但是我們居住和生活的世界并不是始終如一的世界,而是人化后的自然界。對此,馬克思深刻地指出,“這種先于人類歷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費爾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個自然界,也不是那個除去在澳洲新出現的一些珊瑚島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對于費爾巴哈說來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6]
總體而言,費爾巴哈那里的自然觀是一種抽象的唯物主義自然觀,他沒有看到自然界中人的超越性、能動性的一面。這種抽象自然觀對于馬克思反對唯心主義的“自我意識”學說起到過渡性、批判性的作用,馬克思批判費爾巴哈的抽象自然觀,汲取其中唯物主義的合理養分,為形成現實的唯物主義有機自然觀做了扎實的基礎。
二、馬克思有機自然觀的基本內涵
馬克思的有機自然觀是馬克思借鑒近代自然科學發展,運用有機論的視角和方法來看待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之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思想理論,是相對過去割裂人與自然關系、將自然當作抽象實體而言的一種有機論的自然觀。馬克思既承認自然是一種先天性的客觀存在,是一個原生的自我發展著的生命有機體,又看到自然在歷史過程中成為人類派生的無機身體存在,人類將自然納入自身機體生長共同進化。在綜合分析之后,馬克思用“新陳代謝”來形容和表述勞動中人與自然的關系。
(一)自然是原生的生命有機體
馬克思將自然看作內部相互依存、持續運動的有機生命體。馬克思指出,“但是同時應當要求我們的作者對自然界作更深入的研究,把自己對各種元素的初步感性知覺提高到對自然界有機生命的理性知覺。在他面前出現的將不是混沌的統一體這個幽靈,而是有生命的統一體這個精靈。”[2]332自然不再是機械式冷冰冰的靜態實體,而是動態化的內含人類在內整體生成物。
“世界表現為一個統一的體系,即一個有聯系的整體,這是顯而易見的……”[7]663“我們所面對著的整個自然界形成一個體系,即各種物體相互聯系的總體,而我們在這里所說的物體,是指所有的物質存在,從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如果我們承認以太粒子存在的話。這些物體是互相聯系的,這就是說,它們是相互作用著的,并且正是這種相互作用構成了運動。”[7]409這種自然有機體包括時間和空間上的各種存在物,大至宇宙星系,小至行星地球,是包括充滿勞動分工的人類社會甚至其他智慧文明在內的大系統。
自然界是生命的統一體的精靈,其內部之間各種元素總是保持著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狀態,統一于自然生命共同體之中。自然界的各種事物部分服從于整體,從生命整體角度而不是先天個體差異本身出發,做著不同職能的活生生的運動,經歷著從繁榮昌盛到衰落死亡的過程。“它們在不斷地相互轉化,單單這種轉化就形成了地球的物理生命的第一階段,即氣象學過程,而在有生命的有機體中,各種元素作為元素本身的任何痕跡全都消失。”[4]178
當然,在哺育出人類之后,自然界雖然保持著優先地位,但是情況已經大大不同。
(二)自然是人派生的無機身體
馬克思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為與人分離的自然界,對人說來也是無。”[4]95與人毫無關聯、時空上遠古久遠的、處于未經勘探的原生自然,固然有其自在價值,但是如果永遠不能與人類發生物質交換,滿足人類審美、道德和心靈的價值需要,那也是虛無縹緲、毫無意義的。
那么自然的意義和價值何在?馬克思給出了答案。馬克思指出,“從理論領域說來,植物、動物、石頭、空氣、光等等,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學的對象,一方面作為藝術的對象,都是人的意識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無機界,是人必須事先進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糧。”[4]95正是自然界豐富多樣的各種動草木魚蟲、飛禽走獸的存在,才使得人類自然科學中各種數據、各種公式能夠得出,讓人們擁有可靠的對象得以研究,為人類的藝術創作提供素材,人文社會科學中各種形象、理論才能夠出現和擁有存在的價值。因此,自然界是人的必須事先加以認識和消化的現成的精神食糧。“實踐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現在把整個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材料、對象和工具——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4]97因此,人類從自然界獲得直接的生活材料和間接的實踐工具,通過勞動和工具延長自身的肢體,使得自然成為自身的無機身體從而與有機身體合二為一,不斷地維持自身的生存、繁衍和發展。
在馬克思看來,人類將外部自然納入自身機體,也就是在進行物質生產活動,再生產整個自然界。人類在使得自然化作與人一體的無機身體之時,同樣在改造整個無機界,“動物只生產自身,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4]131人類生產出自然界從未有過且不可能生產的產品。因此,人類是屬人的具有自我意識的類存在,能夠依照自身目的去改造自然界。
馬克思指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所以,關于他通過自身而誕生、關于他的產生過程,他有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世界歷史就是在人與人結成的社會關系中通過實踐勞動創造出來的。實踐勞動是一所架在人與自然之間的橋梁。
因此,自然是作為人類肢體的延伸即無機身體通過勞動與人類一體化。人類通過勞動將外部自然(直接或間接的生產工具、生產資料等)納入自身機體生存系統,既保證自身機體的生存與發展,又延伸自然演化下的肢體。“人類在實踐活動中已與外部自然相耦合而形成一個新的生命有機體,外部自然作為人的身體的擴張,構成‘人的無機的身體’,而人則借助于把自然物本身變成他的活動的器官,去支配和控制這一生命有機體。”[9]207
(三)人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
新陳代謝一詞最早是由1815年一位德國生理學家提出的生理學現象,30年代和40年代被大部分德國生理學家所采用,表示人的身體內部“身體內與呼吸有關的物質變換”。1842年,德國農業化學家李比希在《動物化學》一書中,擴充了這個概念的內涵,使之具有農業化學和生理學的含義,得到更加廣泛的使用。生態馬克思主義者福斯特認為,“新陳代謝”概念的生理有機體的使用,至今仍然是研究有機體與周圍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系統方法論的關鍵范疇。生物體復雜的新陳代謝交換使整個機體(或特定的細胞)從自身所處的自然環境中汲取物質、能量,并且通過各種形式的新陳代謝生物化學反應將它們轉化為機體發育所需的營養組織成分。此外,新陳代謝概念過去經常用來表示有機體與其生長環境之間的調節過程,控制著二者之間復雜的物質交換。自然界充斥著這樣的新陳代謝,這在當時已經成為眾所周知的事實。
馬克思沒有停留在李比希等人對“新陳代謝”的使用,而是以“新陳代謝”來描述勞動中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馬克思在兩種意義上使用新陳代謝這個概念。其一,人類通過勞動在自然與社會之間引起的新陳代謝相互作用。這里的自然和社會是指在兩個開放互動的相對系統,他們之間進行能量、信息和物質的傳遞、轉換等。其二,馬克思社會層面上使用新陳代謝概念,即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異化產生出的復雜的、交叉性的動態關系,以及引起的人類非自由問題。如果說第一種的新陳代謝概念對于社會與自然之間互動關系具有特定的生態意義,那么第二種則是具有十分廣泛的社會意義,尤其是對于資本主義社會引起人與自然之間新陳代謝斷裂的批判。福斯特認為,新陳代謝概念,以及包含著的物質交換和調節活動的觀念,使得馬克思對于來源于人類勞動的人類和自然之間復雜的、動態的相互交換給予更加完整而科學的描述。
“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10]馬克思以新陳代謝詮釋出自然和勞動是人類生存的一般條件,勞動是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人類利用勞動調節自身生命活動及維持與自然物質交換平衡。同樣的,新陳代謝斷裂還具有社會批判的意蘊。新陳代謝斷裂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使得土地費力下降,日益貧瘠和釀成城市中不斷增長的普遍污染現象。在資本主義社會,由于資本主義中大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增加了對土地的剝削,食物和服裝纖維源源不斷從農村進入城市,使得土地營養成分流失,變成一個“不可修復的斷裂”問題。
馬克思的“新陳代謝”概念“抓住了同時作為自然和肉體存在的人類生存的基本特征,這些特征包括了發生在人類和他們的自然環境之間的能量和物質交換”。[7]519
三、馬克思有機自然觀的當代價值
馬克思有機自然觀在當今時代發展仍然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價值,其有利于深化國內外學者對馬克思自然觀的進一步認識,利于反思當前人與自然的沖突關系,樹立人與自然整體協調發展的意識,促進社會上良性循環經濟的發展,推動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一)樹立人與自然整體協調發展意識
自然并不是游離在自然界之外,而是身處在自然界之內,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類站在自然面前是一種受動性存在,作為自然界的一分子,即使人類滅亡,那么自然仍然可以演化和培育出新物種。那么保持對于自然的崇敬和尊重是必要的,遵循自然界的規律行事。但是自人類掌握各種科學知識、技術工具以來,其主動性大大增強,以自身的角度去揣測和分析自然的屬性,自然的本質不再能夠自如的展現在人類面前,這樣就造成人與自然之間的分離。人類以外在對象的異在來使用自然材料,以打量器物的態度來掃描事物,從事生產活動,使其成為頭腦中工具化的抽象,這樣造成人類與自然之間深刻的裂縫。人類自認為對于自然界的奧秘和規律了然于胸,可以按照自身的任意意愿去改造自然。可實際上,“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11]116
人類必須站在自然界之內,作為自然界的一分子,將人與自然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與自然共處。在人與自然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中,各自敞開心胸,真誠相待,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諧發展。人類需要認識到,人類是由自然和勞動創生出來的。人類應該在自然和自身創造過程中,在創造的世世代代的物質資源和精神資源中,將自然的發展與人類社會發展統一起來。由此看來,馬克思有機自然觀有利于人類認識到世界與人命運同體、休戚與共,樹立人與自然整體協調發展的意識。
(二)推動社會發展良性的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是一種強調資源節約和循環利用的經濟發展模式,將經濟發展活動中物質和能源合理和循環持久利用,形成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正反饋流程,盡可能較小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馬克思有機自然觀認為,人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關系是通過勞動來控制和調節的,人類必須團結起來作為社會化的人合理調節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以實現人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破壞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循環斷裂。馬克思認為應當通過一系列改革措施恢復物質、能力的流通于交換,這些具體措施有廢料再利用、節約利用原材料、提高資源利用率等,與循環經濟的“減量化、再使用、再循環”原則基本符合,或可稱之為馬克思的循環經濟思想,這些為中國發展良性的循環經濟提供了思想支撐和實踐借鑒,有利于刺激與應用在循環經濟的發展上。
所謂的廢料,幾乎再每一種產業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每一種廢料都不是絕對的無用物,需要人類對其構成元素和性質加以分析,選擇其中可以再次使用的要素投入到再生產之中。循環再利用同時就是一種節約,而機器改良的使用也會較少廢棄物的排放,這又是一種節約。廢料的減少和循環利用離不開科學技術的進步、工業機器的改良。
可見,馬克思有機自然觀蘊含著豐富的循環經濟思想,有利于環境與發展的協調發展,實現從末端治理到源頭控制,從利用廢物到減少廢物的質的飛躍,在現實和實踐上推進新時代中國循環經濟的良性發展。
(三)促進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馬克思有機自然觀有助于在實踐和行動上給予生命共同體構建指導,推進新時代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構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在克服勞動異化之后,勞動實踐得到升華,社會化的人通過合理調節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人與自然的矛盾徹底得到解決。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才能置于共同控制之下,人與自然之間的生命臍帶重新恢復。人類不再受自然的統治和物的壓迫,私有制被消滅,人類能夠得到全面自由的發展。而人類對自然不再抱有敵意,而是當作肢體的一部分和延伸,愛護人類的無機身體,在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統一過程中讓自然展現出自身的本質。自然不再作為人類的外在物和對立物,而是作為維持自身與其他生命形式的整體環境,人類也不再游離在自然界之外,而是身處自然界之中,與其他物種族群一同生存和生活在生命共同體之中。
我國在吸收和繼承馬克思生命共同體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和思想。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12]自然是包括山、水、林、田、湖、草等的有機整體,是各部分要素相互依存而不斷發生新陳代謝運動的生命有機體。人因自然而生,人與自然是一種和諧共生關系。人類必須統籌治理好山水林田湖草系統,從政策和制度上加強生態環境管理和保護,加深自然中氣候變化周期、生物循環原理等規律認識,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堅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今天的智慧城市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典范,將人類、技術、自然有機融合在一起。智慧城市中的經濟發展遵循了聯系和發展的原則,這樣的經濟模式考慮了城市環境的可承受能力,不僅努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同時也盡可能保護環境。[13]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是馬克思有機自然觀的繼承和發展,有機自然觀為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提供了基本理念和實踐指導,有利于推進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構建。
馬克思的有機自然觀,在發生學的意義上重新詮釋了原生自然機體和次生人工機體,并且深度探討了歷史發展中人與自然之間通過勞動進行的新陳代謝相互作用,蘊含著豐富的內涵。馬克思的有機自然觀為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提供了基本理念和實踐指導,對于破除人與自然之間的二元對立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