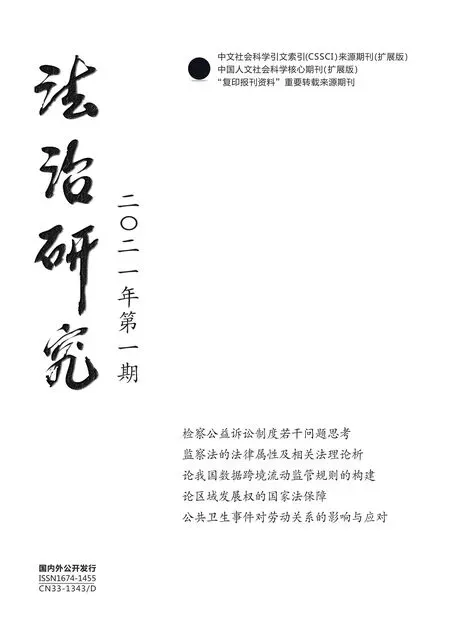共同犯罪司法擴張現象之批評
——以律師與當事人形成共犯為視角
何 萍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律師被指控與其當事人形成共同犯罪的案件屢見于報道,在全國范圍內廣受關注的有青海的林小青案件。林律師在北京大成(西寧)律師事務所執業,為青海合創匯中汽車服務有限公司提供常年法律顧問服務,但后者被指控為“套路貸”公司,林小青等17人因詐騙等不同罪名被指控。2019年4月9日至10日,西寧市城中區法院公開開庭審理17名被告人涉“套路貸”一案。林小青在其中被控詐騙罪和敲詐勒索罪兩罪。此案在網絡上廣受質疑,隨后西寧市城中區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2019年8月20日,林小青收到了法院送達的準許撤訴裁定書。①黃雨馨、單玉曉:《青海律師“涉黑”被控兩罪 開庭后檢方撤訴獲批》,載財新網,http://china.caixin.com/2019-08-20/101452884.html 。近期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的律師呂某某上訴案也廣受關注。合肥市人民檢察院指控,徐某某、邵某某等人拉攏親屬、律師以及多名社會閑散人員,從事非法放貸和討債活動。在從事上述活動過程中,通過實施“套路貸”和暴力、軟暴力催債的方式,侵占被害人財物,牟取了大量非法利益,并形成了以徐某某、邵某某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檢察機關認為,曾經為徐某某、邵某某代理案件的律師呂某某,明知徐、邵通過“套路貸”等方式侵占被害人財物,仍積極為其代理多起虛假訴訟,并教唆他人作虛假陳述、制造虛假證據,因此呂與徐、邵等人構成共同犯罪。2019年10月,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了宣判,判處呂某某構成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并處罰金15萬元。②王翀鵬、程王:《合肥“涉黑”律師呂先三一審因詐騙罪獲刑十二年》,載《新京報》2019年10月31日。該案經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定呂某某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并處罰金人民幣6萬元。
律師是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專業人員,一般而言,律師在業務活動中了解當事人的相關情況。如果當事人在經營活動或者日常生活中有違法犯罪行為,律師在向當事人提供訴訟或者非訴業務中,是否有可能與當事人形成共同犯罪?對這些問題的深入探討有助于厘定共同犯罪的邊界,廓清罪與非罪的模糊界限,也有助于化解律師等專業人員的刑事責任風險。
二、共同犯罪理論之分歧
關于共同犯罪的共同關系應該在什么范圍內存在,刑法理論上有兩種觀點,即“犯罪共同說”和“行為共同說”。根據“犯罪共同說”,成立共同犯罪,要求數個犯罪人必須構成相同的罪名,即二人以上只能就完全相同的犯罪成立共同犯罪。而根據“行為共同說”,共同犯罪是指數個犯罪人實施了共同的行為,而并不要求數個犯罪人的行為成立相同的罪名。即各行為人以共同行為實施各人的犯罪也可以成立共同正犯。③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57-358頁。通過對比可知,根據“犯罪共同說”,共同犯罪成立的范圍被嚴格限定,有利于刑法保障機能的實現。但是“犯罪共同說”認為成立共同犯罪需要數人共同實施一個犯罪事實,未免使得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圍過于狹窄。“行為共同說”認為共同犯罪無需出于共同的犯罪意思,即使一方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而另一方沒有共同犯罪的意思;或者一方有犯罪的故意,而另一方只是出于過失,都可以成立共同犯罪。“行為共同說”大大擴大了共同犯罪的范圍,似為行為共同說的缺憾。④參見劉憲權主編:《刑法學》(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4-215頁。
根據《刑法》第25條之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由此,傳統的刑法理論普遍認為,成立共同犯罪需要滿足三個條件:一是二人以上的主體條件;二是具備共同犯罪故意的主觀條件;三是犯罪人實施共同行為的客觀條件。⑤參見高銘暄主編:《刑法專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1-333頁。這種對于共同犯罪的成立強調要有“共同的故意”以及“共同的行為”的觀點,實際上是遵循了“犯罪共同說”的共同犯罪理論。這種理論對司法實踐的影響是,凡是被認定為共同犯罪的案件,都被定性為相同的罪名。如果認為各行為人因為故意內容不同而構成不同罪名的,就不認定為共同犯罪。
但是,隨著犯罪構成理論的發展,近年來不少學者推崇大陸法系的三階層犯罪構成理論或者提出了違法性、有責性的兩階層犯罪構成理論,并對共同犯罪的成立前提是否應為符合同一個犯罪的構成要件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有學者提出,共同犯罪是一種違法的形態,共同犯罪中的“犯罪”是指違法層面上的犯罪,區別于完整意義上的“犯罪”,完整意義上的“犯罪”應當包含符合構成要件的違法和責任這兩個層面。所以,對共同犯罪應當采取“行為共同說”。換言之,共同犯罪是指數人共同實施刑法上的違法行為,而不是共同實施特定的犯罪。例如,只要查明甲、乙共同對丙實施暴力導致丙死亡,就應認定二人成立共同犯罪,并將死亡結果歸屬于二人的行為,至于甲與乙的責任則要根據各自的故意內容分別確定罪名。所以,在甲、乙二人成立共同犯罪時,對二人所確定的罪名可以并不相同。⑥同前注③,第358頁。
在筆者看來,無論是根據“犯罪共同說”的觀點,抑或根據“行為共同說”的觀點,對具體案件的定性在很多場合可以說是殊途同歸。“犯罪共同說”限縮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圍,如果各行為人故意內容不同,不構成共同犯罪,對各個行為人根據各自的故意內容分別認定。而“行為共同說”卻擴張了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圍,認為只要共同實施了違法行為,就可以構成共同犯罪。但是,在對各行為人確定罪名時還是得根據各自的故意內容分別予以認定。如果對于各行為人是根據他們各自的故意內容分別確定罪名的話,那么對于他們“是否屬于共同犯罪”這個問題其實并無實際意義,因為司法機關對于具體案件的處理歸根結底還是在于對各行為人定什么罪以及處以何種刑罰。“是否屬于共同犯罪”如果對于定罪和量刑產生不了實際作用的,似乎只是理論上的空談而已。
然而,采用“犯罪共同說”和“行為共同說”在是否承認片面共同犯罪問題上有明顯的區別。所謂片面共同犯罪是指參與犯罪的行為人中,一方有同他人實施犯罪的共同故意,并協力于他人的犯罪行為,但另一方并不知情他人給予的協力。⑦參見劉憲權主編:《刑法學》(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24頁。這種只有一方有合意,即所謂的片面合意是否屬于刑法中的共同犯罪在理論上有不同的見解。“犯罪共同說”強調各共同犯罪人之間需要有共同的意思聯絡,也即共同故意應該是全面的、雙方相互的意思聯絡。而“行為共同說”則強調各共同犯罪人之間行為的共同,在主觀上并不要求有相互的、雙方的意思聯絡,只要對犯罪行為有認識即可。極端的“行為共同說”甚至認為一方故意、一方過失同樣有可能構成共同犯罪。可以看出,“犯罪共同說”和“行為共同說”分別是完全共同犯罪和片面共同犯罪的理論基礎。⑧參見林亞剛、趙慧:《論片面共犯的理論基礎》,載《法學評論》2001年第5期。
在德國、日本等采用正犯和共犯區分制的國家,對于片面共同犯罪有全面否定說、全面肯定說和部分肯定(否定)說之爭,我國的刑法理論界對這一問題的爭論基本上沒有擺脫德、日刑法理論的影響。⑨參見劉明祥:《單一正犯視角下的片面共犯問題》,載《清華法學》2020年第5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刑法對于共同犯罪的規定不同于德、日刑法。我國的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很顯然,“共同故意犯罪”與“故意共同犯罪”在語義上是不同的。既然“共同”一詞修飾了“故意”,可見我國的共同犯罪強調各行為人之間應當具有犯意的聯絡,而且“共同”應當不同于“片面”。而日本刑法第60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的,都是正犯。日本刑法第61條、第62條規定,“教唆他人使之實行犯罪的”是教唆犯;“幫助正犯的,是從犯(即幫助犯)”。⑩張明楷譯:《日本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頁。《德國刑法》第26條、第27條規定,“故意教唆他人故意實施違法行為的是教唆犯”,“對他人故意實施的違法行為故意予以幫助的,是幫助犯。”可見,在德、日刑法中,共同犯罪人之間并不強調共同的故意,只要故意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幫助他人犯罪的都可以成立共犯(教唆犯和幫助犯),而被教唆人、被幫助人是否明知他人在故意教唆或者故意幫助在所不問。鑒于此,片面共同犯罪也是共同犯罪的觀點在德、日刑法理論中成為通說,畢竟,在德、日刑法中有關共犯的法律條文并沒有“共同故意”的要求,片面合意也可以構成共同犯罪在文義解讀上沒有障礙。?同前注⑨。但是,我國的共同犯罪規定不同于德日刑法。另外,我國的共同犯罪人并不如德國、日本一樣分為正犯和共犯(教唆犯和幫助犯),而是分為主犯、從犯、脅從犯和教唆犯,即在單一正犯體系下簡單借鑒正犯和共犯區分制的德日刑法理論,并不具有說服力。
但是,問題還在于,我國有關共同犯罪的規定,除了刑法總則的規定外,刑法分則還有一些條文規定了共同犯罪。例如,《刑法》第156條關于走私共同犯罪的規定,“與走私罪犯通謀,為其提供貸款、資金、帳號、發票、證明,或者為其提供運輸、保管、郵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論處”。《刑法》第350條關于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規定,“明知他人制造毒品而為其提供前款規定的物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論處”。前款規定的物品是指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劑。這兩條有關共同犯罪的規定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前者強調了行為人之間的“通謀”才可以構成共同犯罪,而后者只是“明知”一定的事實并提供幫助的就可以認定為共犯。這種區別對待是有一定的道理。第156條是“提供貸款、資金、帳號、發票、證明,或者提供運輸、保管、郵寄或者其他方便的”,這些活動從表面上看是一些正常的業務行為,如果沒有證據證明行為人與走私罪犯通謀,即沒有與走私罪犯形成走私犯罪故意的聯絡,是不能認定為走私罪的共同犯罪的。但是第350條不一樣,該條規定的提供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劑,這些都不是普通物品,是屬于國家管制的易制毒化學品,如果明知他人制造毒品還向其提供易制毒化學品的,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以及行為的客觀危害性就達到了以刑罰處罰的必要性,盡管沒有通謀,但是刑法分則條文將其擬制為共同犯罪。類似的刑法分則條文還有如刑法第198條第4款規定:“保險事故的鑒定人、證明人、財產評估人故意提供虛假的證明文件,為他人詐騙提供條件的,以保險詐騙的共犯論處。”分析這一規定可知,故意提供虛假的證明文件,這并不屬于正常的業務活動,即使與詐騙犯罪分子沒有通謀,仍然構成保險詐騙罪的共同犯罪。有觀點認為,這一條文是片面共同犯罪在我國刑法中的具體體現。?同前注⑦,第224頁。只要查明鑒定人、證明人、財產評估人是故意提供了虛假的證明文件,即使詐騙犯罪分子并不明知他們是故意提供了虛假的證明文件,就可以認定構成共同犯罪。另外,1998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第1條第3款規定:“明知用于騙購外匯而提供人民幣資金的,以共犯論處。”這條規定同樣不需要雙方的通謀,雖然一方明知對方騙購外匯,但是另一方并不需要要明知。這些刑法分則條文都是擴大化的共同犯罪的規定,與刑法總則有關共同犯罪的規定并不相契合。由于刑法分則對于共同犯罪有以上這些規定,使得片面共同犯罪究竟應否承認的爭論更加撲朔迷離。否定片面共同犯罪的觀點認為這些刑法分則條文是法律擬制,不能將片面共同犯罪擴大到其他犯罪的認定,而肯定片面共同犯罪的學者則會認為這些刑法分則條文是注意規定,是有關片面共同犯罪的提示性規定。
三、共同犯罪司法擴張之現狀
對于片面共同犯罪問題我國學者各抒己見,理論上有很多爭論。持肯定說的有陳興良、姜偉、李敏等學者,持否定說的則有張明楷、趙秉志、何秉松等專家?參見高華:《論片面共犯》,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如果說理論的爭論不分上下,各有千秋,那么司法實踐中則肯定說越來越居上風,共同犯罪的認定有不斷擴張之趨勢。這與共同犯罪的“行為共同說”理論越來越領先于“犯罪共同說”理論不無關聯。在早期的刑法理念中,“犯罪共同說”占據主導地位,而目前“行為共同說”似乎有超越之趨勢。這種理念的變化直接導致了司法解釋中一些具體內容的變化。比如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8條規定:“挪用公款給他人使用,使用人與挪用人共謀,指使或者參與策劃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處罰。”根據相關立法解釋,挪用公款罪中的“歸個人使用”既可以歸自己使用,也可以歸他人使用。也即挪用公款罪中可能涉及挪用人和使用人相分離的情況。那么使用人在何種情況下可以與挪用人構成共同犯罪呢?根據此條司法解釋,使用人必須與挪用人共謀,指使或者參與策劃取得挪用款的,才可以構成共同犯罪,如果使用人只是明知此乃公款但仍予以使用的,并不構成共同犯罪。然而,近年來的司法實務界似乎普遍認為,如果行為人主觀上明知他人正在實施犯罪行為,其客觀上實施的行為對于犯罪結果起到了一定的幫助或者促進作用的,就可以認定為是共同犯罪。這種共同犯罪不斷擴張的情形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的司法解釋中十分普遍,以下司法解釋可見一斑。2010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網絡賭博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第2條規定?該條規定:“明知是賭博網站,而為其提供下列服務或者幫助的,屬于開設賭場罪的共同犯罪,依照刑法第303條第2款的規定定罪處罰:(一)為賭博網站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空間、通訊傳輸通道、投放廣告、發展會員、軟件開發、技術支持等服務,收取服務費數額在2萬元以上的;……”,2011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7條規定?該條規定:“明知他人實施詐騙犯罪,為其提供信用卡、手機卡、通訊工具、通訊傳輸通道、網絡技術支持、費用結算等幫助的,以共同犯罪論處。”,2013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敲詐勒索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7條規定?該條規定:“明知他人實施敲詐勒索犯罪,為其提供信用卡、手機卡、通訊工具、通訊傳輸通道、網絡技術支持等幫助的,以共同犯罪論處。”,2013年9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8條規定?該條規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尋釁滋事、非法經營等犯罪,為其提供資金、場所、技術支持等幫助的,以共同犯罪論處。”,2016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4條(3)規定?該條規定:“明知他人實施電信網絡詐騙活動,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共同犯罪論處,但法律和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1.提供信用卡、資金支付結算賬戶、手機卡、通訊工具的;…… 5.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支付結算等幫助的;……”,2019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 第5條規定?該條規定:“明知他人實施‘套路貸’犯罪,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相關犯罪的共犯論處,但刑法和司法解釋等另有規定的除外:(1)組織發送‘貸款’信息、廣告,吸引、介紹被害人‘借款’的;(2)提供資金、場所、銀行卡、賬號、交通工具等幫助的;(3)出售、提供、幫助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4)協助制造走賬記錄等虛假給付事實的;(5)協助辦理公證的;(6)協助以虛假事實提起訴訟或者仲裁的;(7)協助套現、取現、辦理動產或不動產過戶等,轉移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的;(8)其他符合共同犯罪規定的情形。”等等。
以上多個司法解釋在對于共同犯罪的認定方面有幾個特點。第一,構成共同犯罪的主觀方面都沒有要求雙方“通謀”,也即放寬了“共同故意”的要求,只要明知對方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給予幫助的,即可以構成共同犯罪。第二,在“明知”的內容方面,有的司法解釋明確提到了明知他人實施詐騙、敲詐勒索、誹謗、尋釁滋事、非法經營等具體的犯罪,有的司法解釋則比較寬泛地提到了明知是賭博網站、明知是電信詐騙犯罪活動、明知是“套路貸”犯罪(套路貸并不是具體的犯罪)等并不是具體的犯罪活動。第三,在客觀方面都是提供了一些幫助,或者是發送貸款信息,提供資金、場所、銀行卡、賬號、交通工具等,或者是提供通訊工具、通訊傳輸通道、網絡技術等支持,或者是予以辦理公證、提起訴訟或者仲裁等。
不難發現,這些司法解釋大大擴大了共同犯罪的認定范圍,根據這些司法解釋的規定,只要主觀上是“明知”,客觀上提供了一些幫助,即便提供的是一些表面上似乎中立的業務行為,都可以構成共同犯罪。總體而言,這些解釋在兩個方面對于共同犯罪的認定是值得商榷的。一方面,片面合意可以構成共同犯罪,即提供幫助的行為人與正犯之間即使在主觀上沒有犯意的溝通聯絡也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另一方面,中立的業務行為提供者只要主觀上明知他人有違法犯罪行為,將不得以行為中立性的理由而被豁免,中立業務行為的提供者將與他人形成共同犯罪。根據目前的司法實踐,只要成立共同犯罪,幫助者就與正犯構成相同罪名。因此,青海律師林小青代理的當事人被指控構成犯罪后,其本人也被指控構成詐騙罪、敲詐勒索罪兩罪,盡管事后被檢察機關撤回起訴。安徽的律師呂某某也因當事人被指控犯罪而其本人被一審法院判處構成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
筆者認為,司法實踐如此寬泛地認定共同犯罪的范圍是值得深入探討的。首先,司法解釋是否可以突破刑法總則第25條有關共同犯罪概念的規定,對于“共同故意”擴展到片面合意的范圍。前文提到的制造毒品罪的共犯、保險詐騙罪的共犯畢竟有刑法分則具體條文的規定,而且這兩個犯罪并非屬于最常見最普通的犯罪,制造毒品罪的共犯囿于原材料的特殊而并不屬于常見情形,保險詐騙罪共犯則涉及保險事故的鑒定人、證明人、財產評估人等特殊主體,因此也不屬于常見高發的犯罪。然而這些司法解釋的規定則涵蓋了賭博罪、詐騙罪、敲詐勒索罪、誹謗罪、尋釁滋事罪、非法經營罪等一些最常見的犯罪,這對司法實踐產生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司法解釋任意超越刑法總則條文的規定是否有違罪刑法定原則?其次,片面合意的證明如果要達到刑事訴訟的證據證明標準其實在司法實踐中是十分困難的。眾所周知,雙方的、全面的、相互的共同故意容易證明,比如在某時間某地點多個行為人有商量有謀劃,或者有通話記錄,或者有短信聯系等等,至少還有多個共同犯罪人的口供可以相互印證。而在片面合意的情況下,一方并不知情,當然無從指證另一方的犯罪故意和犯罪行為,而故意提供幫助的這一方如果矢口否認主觀的明知,避重就輕地交代是出于過失提供了幫助的話,司法機關是很難將其繩之以法的。盡管“明知”的認定可以采用推定的方法,但其實證明的難度相當大。因此,片面共犯在理論上似乎可以論證,而在司法實踐中舉步維艱。刑法理論是為司法實踐服務的,主張片面合意也是共同犯罪的學者的良苦用心是為了避免那些主觀上有惡性、客觀上實施了危害社會行為的人逃避法律責任的追究,但其實片面共犯理論在實踐中很難運用。根據刑事訴訟的證據規則,對于片面合意的行為人定罪要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是十分困難的。行為人拒不承認是常態,即使有老實坦白的,根據刑事訴訟證據要求,只有被告人口供而沒有其他證據可以印證的,也不能定罪量刑。而且,因為沒有雙方的通謀,正犯的故意內容與幫助者的故意內容未必相同。提供虛假證明材料的人究竟是詐騙或者合同詐騙的故意,還是保險詐騙的故意,抑或敲詐勒索、虛假訴訟的故意都很難查證,如果說提供虛假證明的人是基于概括的故意,完全依賴于被幫助者的行為性質來定性,則未免有客觀歸罪的嫌疑。更遑論司法實踐中對“明知”的認定采用推定的方式往往忽視行為人的合理辯解,犧牲了法律的公平正義價值。
四、律師與當事人形成共同犯罪之困惑
隨著法律服務市場的不斷拓展,律師執業的刑事責任風險屢屢見于報道。在李莊案件時代,刑法第306條規定的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通常被簡稱為律師偽證罪。刑辯律師們認為刑法第306條是對刑事辯護權的限制和對刑辯律師的職業歧視,是一把懸在辯護律師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然而隨著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規定了虛假訴訟罪以及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打擊套路貸、掃黑除惡的相關司法解釋以后,民商事律師執業的刑事責任風險突然陡增。如果律師在民間借貸案件中代理原告,雖然明知被告方已經支付過高利息,但仍然隱匿相關證據,出庭代理原告,便有可能構成詐騙罪的共同犯罪;如果律師明知當事人有實施“套路貸”的犯罪行為,依然為其起草、修改借貸合同,便可能構成“套路貸”系列罪名中詐騙罪、敲詐勒索罪等共同犯罪;如果律師明知某公司通過電商平臺非法集資,卻依然擔任該公司的法律顧問,為公司的日常經營提供法律意見,便可能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共同犯罪;如果律師的當事人涉黑涉惡,律師甚至被指控為是黑社會性質組織、惡勢力集團的成員。
律師與當事人如此輕易地被認定為構成共同犯罪的司法實踐是否存在問題?這種簡單套用共同犯罪的概念,機械地引用相關司法解釋的情形,表面上看似乎沒什么問題,但是如果深入探究則會發現從共同犯罪的通常理論來看,如此認定共同犯罪是十分粗鄙的。如果按照“犯罪共同說”,共同犯罪的成立應當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為。具體而言,在主觀方面,數個共同犯罪人需要對其所實施的共同的行為所引發的嚴重危害社會的結果具有認識,并對希望或者放任該結果的發生具有意義上的聯絡。在客觀方面,要求各共同犯罪人為了共同的犯罪目標,相互配合地實施了犯罪活動。在對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過程之中,律師是否對當事人實施的犯罪行為具有“明知”的認識?這種“明知”必須要審慎查明。即使推定律師“明知”當事人的犯罪行為,但律師提供法律專業知識的業務行為的故意與當事人的故意內容是否相同?按照“行為共同說”的理論,只要各行為人之間合力加工的,即使故意內容不同,也仍可成立共同犯罪。但是,按照“行為共同說”的觀點,即便成立共同犯罪,在對各行為人定罪量刑時還得根據各自的故意內容來確定。也即如果當事人構成套路貸犯罪、詐騙罪、敲詐勒索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乃至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等,即使律師對于當事人的這些犯罪事實都是明知,但是律師如果沒有與當事人通謀,僅僅從法律角度提供專業知識的,律師的故意內容與當事人的故意內容不可同日而語。按照“犯罪共同說”理論,律師與當事人不構成共同犯罪。按照“行為共同說”理論,即使構成共同犯罪,也應該根據各自的故意內容予以定罪。也即,即使律師違反了職業操作規程,逾越了中性業務行為的界限,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律師的違法行為也應該更符合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虛假訴訟罪等犯罪。
事實上,從“中立幫助行為”理論出發,律師的行為即使并不妥當,也不宜認定為犯罪行為。關于刑法是否能夠處罰中立的幫助行為,學界展開了深入而廣泛的爭論。中立幫助行為,是指那些主觀上不追求非法目的、客觀上屬于不具有刑事違法外觀的日常行為,但是實質上對他人的違法犯罪行為起到了助益作用的行為。這類行為在客觀上對正犯的實行行為起著實質上的推動作用,更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長法益受侵害的風險或者加強法益的受侵害程度。?參見付玉明:《論刑法中的中立幫助行為》,載《法學雜志》2017年第10期。中立幫助行為的特征是幫助性、中立性、對象的不特定性以及可替代性。關于刑法是否能夠處罰中立幫助行為,大陸法系刑法理論界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可被概括為全面處罰的觀點和限制處罰的觀點。全面處罰觀點認為,只要主觀上是故意,客觀上具有因果關系,就能夠成立幫助犯。全面處罰的觀點未考慮到中立幫助行為所具有的特殊性,會對公民自由和社會正常運轉造成不當的限制,已逐步被淘汰。目前為數不少的學者認為,從對公民自由和社會正常運轉進行保護的角度出發,應嚴格限制處罰中立幫助行為的范圍。21參見陳洪兵:《論中立幫助行為的處罰邊界》,載《中國法學》2017年第1期。
近年來,我國也有不少學者對于中立幫助行為的可罰性問題提出了一些主張。張明楷教授認為,如若僅能大體上對對方可能會實施犯罪行為有所認識,則不應將日常生活中的幫助行為認定為幫助犯。但是,如果明知對方正在或者將要立即實施實行行為,卻將對方運往犯罪現場、向其出賣工具或者實施其它有助于對方的實行行為的,則應認定為幫助犯。22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47頁。這種觀點是從主觀上區分了明確的故意以及概括的故意。如果有明確認知的,可以構成幫助犯,如果只是概括性的認知,則不宜認定。但是,張明楷教授后來對這一觀點又進行了補充,他指出,只有將正犯行為所具有的緊迫程度、行為人是否對法益有保護義務、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小等作為考慮因素,才可以得出妥當的結論。例如,如果他人的殺人行為并不緊迫,或者A只是大體上估量對方未來可能進行犯罪,則對于A所實施的具有日常性的行為,不能認為其構成幫助犯;相反,如果A向正在參與斗毆之人出售刀具,則此行為可以被認定幫助犯。23同前注⑥,第385頁。這種觀點是從客觀以及主觀兩個方面予以限制中立幫助行為的可罰性。可以說這種觀點比較綜合,也比較普遍。持類似觀點的還有周光權教授,其對于日常行為構成共犯是從法益的侵害程度、主觀明知以及客觀上對于正犯的影響等多角度進行了嚴格限縮。24參見周光權:《刑法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頁。需要指出的是,數年前廣受關注的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案件中,辯方提出了“技術是無罪”的命題,引發了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廣泛熱議。根據判決文書載明的內容得知,快播公司的緩存服務器下載、存儲并提供淫穢視頻傳播,屬于傳播淫穢視頻的實行行為,且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不適用于中立的幫助行為理論。因而辯方以行為的中立性來否定快播公司及各被告人責任的意見,不被法院采納。最終法定代表人王欣等依然被認定為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6個月,罰金100萬元。從該判決書內容來看,法院認為快播公司具有實行行為,因此不適用于中立幫助行為理論,換言之,如果快播公司沒有實行行為,則屬于中立的幫助行為,那么快播公司就未必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
中立幫助行為既可能是業務行為,也可能是日常生活當中的行為。律師向當事人提供服務的行為也可被歸類為中立的業務行為。結合中立的幫助行為理論及《律師法》第29條規定25《律師法》第29條規定:“律師擔任法律顧問的,應當按照約定為委托人就有關法律問題提供意見,草擬、審查法律文書,代理參加訴訟、調解或者仲裁活動,辦理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務,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如果律師在擔任法律顧問、代理參加訴訟、調解或者仲裁活動的,其為了維護當事人的利益而實施相應的業務行為,如果沒有逾越邊界的,即使明知其當事人有違法犯罪行為,也不應當認定為當事人的共同犯罪。所謂逾越邊界是指律師不是在提供意見,草擬、審查法律文書,出庭訴訟,提供辯護意見等,而是幫助當事人跟蹤索債或者在網絡平臺上幫助當事人吸收資金等等。
另外,《律師法》第38條之規定認可了律師享有為當事保密的權利和義務。26《律師法》第38條規定:“律師對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有關情況和信息,應當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準備或者正在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嚴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事實和信息除外。”律師對于當事人而言,保守當事人秘密是律師義務,但是對于其他機關、團體以及其他人而言,律師享有職業秘密的特權。換言之,即使在國家機關面前,律師也有權拒絕透露當事人的秘密。但是律師的這一特權具有相對性,即如果當事人實施的行為可能或者已經對國家或公共安全以及他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脅或者實際侵害的時候,律師便不再享有這一特權。這說明律師的職業秘密特權在一定情況下得讓渡于重大利益的維護,這種重大利益是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他人的人身安全。這表明,只有在面臨即時的、重大利益受損的情況下,律師才沒有保守秘密的職業特權。
總體而言,中立幫助行為是具有特殊性的,也即雖然其在客觀上可能對他人實施犯罪活動的進程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其本身又是一種正常的業務活動或日常行為。正因為如此,對于中立幫助行為之處罰,必須權衡打擊犯罪和保障公民自由的兩個方面。只有在中立幫助行為明顯違反了法律的禁止性之規定,且提升或制造了法律不允許之風險時,實施該行為的人才有可能構成幫助犯。
五、限縮共同犯罪認定之路徑
如前所述,司法實踐中對于共同犯罪的認定有擴張化的趨勢。但是我們也看到一些司法解釋對于一起參與犯罪的行為人給予了區別對待,甚至予以出罪。例如,相關司法解釋272013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以單位名義實施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的,對于受單位指派,僅從事勞務性工作的人員,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責任。”指出,單位實施領導或組織傳銷活動的犯罪行為的,對于在單位內部履行單位分派的任務且從事的是勞務性的工作人員,通常情況下無須追究刑事責任。該司法解釋將單位的主管領導與普通員工區別對待的精神十分正確,這種理念應當在司法實務中予以推廣。應當看到,在單位犯罪中,通常是由單位的領導主導,即單位領導對犯罪行為具有直接支配力,而一般從業者無法對犯罪的進程起到支配作用,對于犯罪行為的發生不起關鍵作用,因此,不宜將這類人認定為單位犯罪當中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并予以追究刑事責任。再比如,在賭博犯罪中,如果從寬泛的共同犯罪定罪思維出發,受雇傭為賭博犯罪提供幫助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存在著明知,在客觀上為賭博犯罪提供了便利的,似乎可以構成共同犯罪。但是,有關司法解釋明確規定,除了參與賭場利潤分成或者領取高額固定工資的以外,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可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282014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利用賭博機開設賭場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條規定:“對受雇傭為賭場從事接送參賭人員、望風看場、發牌坐莊、兌換籌碼等活動的人員,除參與賭場利潤分成或者領取高額固定工資的以外,一般不追究刑事責任,可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這種將開設賭場的犯罪分子與為其提供幫助的行為人予以區別對待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眾所周知,賭博罪的構成必須以營利為目的,開設賭場罪雖然法律條文沒有明示“以營利為目的”,但是開設賭場的行為本身包含著行為人的以營利為目的。而受雇傭的人只要沒有參與賭場利潤分成,沒有領取高額的固定工資,這些人員的行為充其量也只是一個謀生的手段,與“以營利為目的”開設賭場的經營行為有著天壤之別。應當承認,以上列舉的兩個司法解釋對于司法實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也恪守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體現了刑法的謙抑思想。但是正如上文提到的,目前還有大量的司法解釋甚至一些刑法分則條文使得共同犯罪擴張化的現象十分明顯。筆者認為,在共同犯罪的認定方面,我們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嚴格把關以體現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體現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
第一,共同犯罪的認定還是要根據刑法總則第25條對共同犯罪概念的規定,強調各行為人之間應當具有共同的故意和共同的行為。共同的故意應該包括共同具有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而且相互之間應當有犯罪意圖的溝通和聯絡。如果刑法分則條文對共同犯罪另有規定的,則可以根據特別條款優于普通條款的規定來認定。因為刑法總則是對于犯罪和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而刑法分則條文是對刑法總則內容的具體化和明確化。也即,片面合意的情形除非有法律條文明文規定,否則不宜認定為共同犯罪。司法解釋對于片面合意的內容擴大為共同犯罪的規定,其實是有違罪刑法定原則的。
第二,嚴格把握對于“明知”的認定。司法實踐中對于明知的認定往往采用推定的方法,“明知”與否當然不能僅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的說辭。但是在采用推定方法時,即根據一個已知事實推定出一個未知事實時,一定要依據經驗法則和邏輯規則,從事物間的常態聯系上得出一定的結論。特別要注意的是,僅僅是“明知”,不必然推導出構成共同犯罪。“明知”的認定只是構成故意犯罪的前提,只是符合某些犯罪的構成要素而已。“明知”不等于“通謀”,不等于“具有共同的故意”。片面合意、心照不宣只能說明行為人是“明知”,但還不能證明是行為人之間的“通謀”或者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
第三,隨著刑法的不斷發展完善,刑法條文越來越精細,罪狀越來越明確。罪刑法定原則的應然結果是“一個蘿卜一個坑”。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之前,相當多的司法解釋對于提供網絡技術幫助的,只要具備主觀上的明知,即可以認定為共同犯罪。但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明文規定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等網絡犯罪,根據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對于行為的精準定性還是要尋找最匹配的刑法條文。我們可以看到,在2015年之后出臺的一些司法解釋,雖然也提到了主觀上明知、客觀上提供網絡技術幫助的,可以認定為共同犯罪,但是緊接著又提到:“法律和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如上文提到的《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4條(3)規定:“明知他人實施電信網絡詐騙活動,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共同犯罪論處,但法律和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又如,《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 第5條規定:“明知他人實施“套路貸”犯罪,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相關犯罪的共犯論處,但刑法和司法解釋等另有規定的除外:……”顯然,根據刑法修正案的內容,相關行為定性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或者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更為妥當,更加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這應當屬于“法律另有規定”的情形。
第四,對于中立的幫助行為或者中立的業務行為,不能因為對他人的違法犯罪活動有一定的認識,就可以認定為共犯。中性業務活動原則上不認定為共犯,除非違反了業務操作規程,逾越了中性業務行為的界限,并且制造或者提升了法益侵害發生的危險。結合律師的業務行為而言,即使律師明知當事人的違法犯罪行為,律師提供法律專業幫助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與當事人的故意及行為并不相同,律師與當事人不構成共同犯罪。根據“行為共同說”的共同犯罪理論,即便律師的行為逾越了法律邊界,根據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律師的相關行為也只能被認定為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或者虛假訴訟罪等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