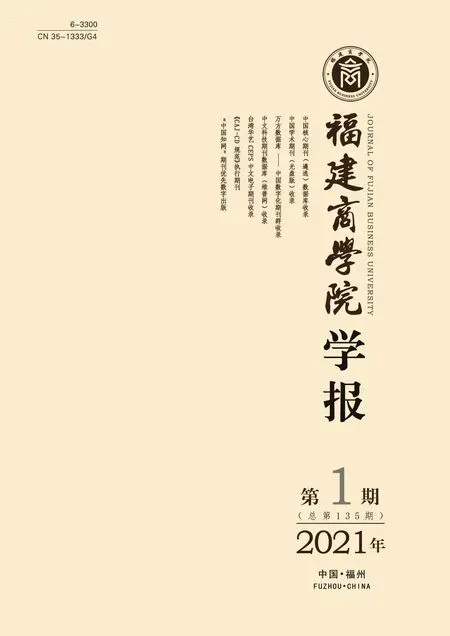客體論到主體論的轉向
——新時期“文學是人學”命題論爭及其反思
劉皇俊
(云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云南 昆明,650500)
文學創作的主體是人,文學表現的對象是人,文學接受的主體依舊是人,文學史是一部“人”不斷發現自身、認識自身、表現自身、定義自身的歷史。五六十年代社會話語的禁錮,割裂了五四以來的“人的文學”傳統,也遮蔽了文學表現的多種可能性。1978年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開創了中國社會的新時代,隨之而來的新啟蒙主義開啟了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新紀元。思想文化的“祛魅”是政治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二者是新時期歷史語境下同質異構的結果。中國新時期的文學創作和理論是新啟蒙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文化部門一起,擔負著實現現代性文化目標、推動中國擺脫思想禁錮的宏大使命。“文學是人學”的命題伴隨著時代的洪流,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迎來了自己的春天。在歷史“合力”的作用下,中國現代文學理論開啟了從客體論到主體論的轉向。
一、新時期思想禁區的解封
(一)文學觀念的解禁
從社會歷史角度來看,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觀念解禁是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結果,也是思想文化層面對政治改革的呼應。文學觀念的“祛魅”是作為政治改革、思想文化解放系統之下的一個“子系統”呈現的。厘清了這一點,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就顯得尤為重要。
文學的發展同政治文化息息相關,政治文化規約了文學的發展向度。“1949年7月2日召開‘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一致確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為指導文藝的總方針,‘工農兵方向’為文藝運動的總方向。”[1]隨后,全國范圍內的文學創作、研究、運動都要在這“一觀”“一話”的指導之下進行。客觀上這一指導思想做出過巨大貢獻,影響了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文學實踐,但“五十年代后期開始的極左思潮卻一步步將它‘漫畫化’僵化”[1]46,也致使整個中國的文學創作走入了困局。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觀”“一話”所倡導的實際上是一種“文學反映論”,是一種強調客體而非難主體的文學觀。“反映”是對主客體關系的理論概括,盡管它宣稱主體是能動地對客體進行反映,但是在極“左”思潮和主流社會話語的影響下“能動的反映”被消解了,創作主體不可能也不允許自由地選擇反映對象。辯證唯物主義的“反映”被僵化、禁錮、制約,表現在文學創作領域就是“高、大、全”“假、大、空”式的人物形象和模式化的革命樣板戲。這一時期的“文學反映論”實際上是以客體為中心,遮蔽了主體能動性的機械反映論。
1978年末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線,和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伴隨著這一偉大的歷史轉折和思想的空前解放,文學創作也迎來了新的春天。早在五十年代,中國的理論家們就曾試圖打破理論“禁區”,紛紛著文從人性、人道主義、階級等各方面論證文學“人”的本質,試圖將文學從“規制”中解放出來,但都以失敗告終。客觀上“打破禁區的嘗試”雖然失敗了,但也為下一次論爭積累了經驗,奠定了理論基礎。乘著政治改革和新啟蒙主義的歷史之勢,人性與人道主義在七十年代迎來了新的曙光。
新時期的文學觀念解禁以對“人”本質的重新思考為邏輯起點,以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認識為理論基礎,從“階級論話語體系”內部為人性存在的合法性尋找法理依據。1979年朱光潛發表《關于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的問題》一文,開宗明義,當前文藝界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解放思想,沖破極左思想憑空為創作設置的種種禁區。“首先就是人性論這個禁區”[2],朱光潛以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人本質力量的論述為基礎,肯定了“人性”在文學創作中的合理性。他指出:“人性論和階級觀點并不矛盾,它的最終目的還是為無產階級服務。”[2]39-42雖然從論述中不難看出,朱光潛并未完全脫離時代階級論的話語體系,他從階級的角度入手為“人性”辯護,并從法理上消除了“人性”與“階級的對立”。但是,這是歷史時代所決定的,他不得不從“階級斗爭話語體系”內部尋找“人性”存在的合法性,援引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并以此為辯護基礎。由此可見,即使在思想解放開始后,理論家們突破“禁區”的嘗試依舊是小心翼翼的。隨后,汝信發表《人道主義就是修正主義嗎?——對人道主義的再認識》一文,支持朱光潛的觀點,從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系入手,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對于“人”的關注,從哲學層面呼應了朱光潛的觀點。哲學、文藝界相繼發聲、互相呼應,文學觀念的解禁以哲學認識為理論基礎,哲學認識的解禁又以政治改革為先決條件,社會各個領域的“解禁”嘗試最終開啟了文學觀念的解放大潮。
(二)文學實踐的解禁
一個時代的言說方式和表達主題暗藏著一個時代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文化。曾經不可觸及的言說禁區,在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的雙重外力下被打破,人道主義與人性這塊荒蕪已久的文學沃土正待開掘。
新時期的文學實踐誕生于“文革”的創傷之中,并以五十年代人道主義文學的萌芽為基礎,乘著新啟蒙主義的歷史浪潮,在新一輪的“西學東漸”中展現出多元、開放、自由的姿態。“傷痕”“反思”“人性”都是這一時期作家們熱心表現的主題,作家們熱心歌頌人性、揭露創傷、批判迫害,踐行著“人”的文學觀、創作觀、價值觀。
盧新華《傷痕》講述“進步”青年王曉華和“叛徒”母親劃清界限,一別多年后母子天人相隔,抱憾終生的故事;馮驥才《啊!》、古華《爬滿青藤的木屋》與《芙蓉鎮》描寫階級斗爭和政治迫害致使社會扭曲、人被異化的荒誕現實;魯彥周《天云山傳奇》以羅群的悲劇命運為敘事主體,揭露政治迫害對人性的摧殘;張賢亮《靈與肉》《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戴厚英《人啊,人!》等作品通過敘寫知識分子遭受的非人待遇,反思極左思想,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撫慰傷痕累累的“人”;劉克《古碉堡》從藏族女性曲珍的悲劇上升至對整個民族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的觀照。作家們向人們展示出一個個“非人”的世界、一個個“駭人”的故事,以“非人”的描寫呼喚人性、人道、人倫,他們是對苦難有著切身體驗的作家,他們寫于受難、痛于悲劇,但不陷于苦難和悲劇,而是以此為武器反思苦難背后的邏輯。
新時期人道主義文學在文學實踐的解禁中展現了強大的生命力,作家們在文學實踐中不斷深化對人的理解,將同情、寬容、博愛的人道主義思想灌注于文學實踐。他們不僅僅停留在“情感敘事”的層面,還灌注了新啟蒙主義所帶來的“啟蒙精神”,以“受難者”的視角,揭露文革迫害、批判極左思潮、表現新的啟蒙要求,將思想啟蒙與文學創作相結合,接續了五四“人的文學”傳統,真真正正實現了文學實踐的解禁。
二、“文學是人學”的命題
(一)“文學是人學”命題之源
文學是人類特有的精神創造的產物,是人本質力量對象化的結果,是人性對世界的饋贈,它的孕育生長必然受到人的靈魂、情感的滋潤和規約,而這種滋潤和規約概括起來就是人道主義。因此,文學應該是“人學”。
1957年《文藝月報》刊發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一文。錢谷融從文學表現的對象、題材論述了“人”之于文學的意義和價值,熱情歌頌、贊揚了“人”的文學,呈現出鮮明的人道主義文學思想傾向。他將文學的作用歸納為改善人生,提高生活以至于達到“至善至美境界”[3]。偉大的作家之所以令人敬佩,是因為他們在作品中“贊美”“潤飾”“歌頌”了“人”,使得“人”的形象高大了。
錢谷融在《論“文學是人學”》中表述的觀點與高爾基的觀點十分相似,甚至直接援引高爾基所用的概念、詞義。顯然,錢谷融試圖從前蘇聯那里繼承“人學”命題立論的法理性。在階級斗爭占據話語權的年代,將理論之源訴諸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似乎是最穩妥安全的做法。高爾基也是從創作主體、表現對象、價值取向等方面對“文學是人學”進行了闡釋。他曾坦言自己畢生從事的工作是“人學”,文學是“創作典型”的工作,文學要塑造“大寫的人”[4]。此外,錢谷融還援引季摩菲耶夫語“人的描寫是藝術家反映整體現實所使用的工具”[3]3,以此為基礎批判文藝反映觀基礎之上的“主體工具論”,即文藝家將表現人當作其實現反映“整體現實”的手段和工具。在錢谷融看來,“主體工具論”既不符合藝術創造的邏輯,也不符合文藝家創作的實際情況,季摩菲耶夫“整體現實”的概念界定是含糊不清的、空泛的。如果說作家將反映“整體現實”作為創作任務,那么作家勢必“削足適履”,以消解人物形象的獨特性為代價,反映所謂的“整體現實”。但是文藝家在進行藝術創作時,并不會依照此種思維邏輯,反而是以人物的獨特性為核心,追求人物形象的靈性,而這也正是文學作品價值之所在。錢谷融的論斷是合理的,他從反映論內部尋找到了“人學”命題立論的合法依據。
新時期“文學是人學”命題的內涵不僅限于文學表現的客體和創作接受的主體。從本質上說,它是“人道主義”的文學表達,是五四“人的文學”傳統的延續。“五四”時期以周作人為代表的文藝批評家將西方人道主義精神灌注于新文學,熱心提倡文學關注人生、表現人生、凈化人生。新時期重提“文學是人學”命題,不可能繞開這一文學傳統。周作人的“人的文學”本質上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5],而在這一點上錢谷融是與其一脈相承的。在錢谷融看來,文學的價值在于懲惡揚善、塑造人性、表現具體的人,文學表現對象是“具體的在行動中的人”,作家應該“寫出他的活生生的、獨特的個性”[3]3。而“個性”一詞指的是單個“人”的獨特性、個體性。換言之,文學所關注的對象——“人”既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大寫的人,又是具體意義上的、個體的人。
(二)“文學是人學”命題之辯
早在五十年代“雙百方針”提出之時,中國的文藝家們就曾對“文學是人學”命題進行論爭。但由于極左思想和主流話語的規制,這場打破“禁區”的嘗試很快就失敗了。他們遭遇了來自兩方面的批判和打擊:一方面來自文藝界內部,主要以張學新、柳鳴九、蔣孔陽為代表,從革命與反映、階級與人性的角度、人道主義的理論漏洞等方面對巴人等人的觀點予以批判;另一方面的壓力來自于政治領域。周揚在第三次文代會上指出:“資產階級人性論,是用‘資產階級和平主義’來調和階級對立,否定階級斗爭和革命,散布對帝國主義的幻想”[1]276。隨后,毛澤東提出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場關于“人性與文藝”的論爭也就戛然而止了,一直到七十年代才被重新提起。如果說來自文藝界內部的批判還算是學術領域的理性探討的話,那么來自政治領域的壓力便是在學術之外的階級斗爭。而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以階級論囊括人性,以至于否定了超越階級的共同人性,以階級的解放代替個性的解放”[6]。錯誤將兩個話語體系的概念強行放到一起,將人道主義打上資產階級的烙印,將其納入階級斗爭的思維模式中,從根本上宣判人道主義的“非法”,這顯然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歷史發展規律。
1980年伴隨著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歷史潮流,錢谷融發表《〈論“文學是人學”〉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綱》一文揭開了新時期“文學是人學”討論的序幕,標志著人道主義文學的回歸。錢谷融在文中表示,既然文學表現的對象是人,那么“非以人性為基礎不可”[7]。“人性”是讀者接受的興趣所在,也是作者創造的中心。文學作品之所以能跳出歷史時空的限制,在千百年之后還能引起人們的共鳴,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性”二字。質言之,文學的價值尺度在于“一切都是為了人 , 一切都是從人出發的”[7]13。
值得注意的是,重提“文學是人學”實際上是一種“主體論”復歸的表現。在反映論、客體論的話語時代,主體一直處于被壓抑、被忽視、被遮蔽的狀態。主體自由的高揚在極左思想家看來是資產階級那一套,是修正主義復燃的導火索,必須徹底鏟除。隨著七十年代“人學”命題的復歸,主體獲得了新生,中國文藝界正由客體論轉向主體論,而這也符合文藝發展的規律。因為文學藝術最重要的價值就是獨創性,而獨創性取決于充滿能動性的“人”(即主體),沒有人自由獨立的精神創造,文學藝術無從談起。古希臘柏拉圖講“詩興的迷狂”“神靈憑附”,中國古代講“性情”“性靈”,都是對文藝之中獨創性的闡釋。“人”是天地間自由的靈長,而由“人”所創造的文藝勢必包含著人的審美意識、情感體驗、人生體驗,這是文藝的生命之源、價值之源、魅力之源,抽去了“人”便空無一物。
三、新時期“文學是人學”命題論爭的反思
(一)新時期“文學是人學”命題的貢獻
新時期重提“文學是人學”的命題,不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結果,更是五十年代被壓抑的人道主義文學回歸的結果。在歷經種種苦難之后,“人學”命題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參與到中國新時期“現代性”敘事的歷史建構之中,并為之貢獻了核心的精神基因。
首先是人道主義的復興。隨著“文學是人學”討論的開始,人道主義作為文學討論的“副標題”進入了學者們的視野。在“十七年”與“文革”時期,人道主義被視作資產階級思想而納入階級斗爭的話語體系中被大加批判。新時期重提“文學是人學 ”,立論的邏輯起點就是“人道主義”。據此理論家們紛紛從各個角度予以論證,在客觀上擴大了人道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影響,豐富了人道主義的理論內涵。而人道主義在中國“現代性”敘事的歷史建構過程中,又貢獻了人性、本我、自由、情感、人道等重要的價值內涵。
其次是文學主體論的復歸。人既是文學創造的主體亦是文學表現的客體。作為“人”特殊的精神創造,文學創作是“人”主體性的最佳呈現,強調文學創作的獨特性也就是強調主體性在文學創作中的核心地位。如前所述,五十年代后文學主體性被社會話語遮蔽了,“能動的反映”似乎是癡人囈語,在極權的規制面前蒼白無力。文學創作的主體性陷入了無盡的深淵,“假、大、空”的人物形象、淡乎寡味的革命樣板戲便是最好的例證。“文學是人學”的重提、人道主義的復歸無疑再一次將“人”(即主體)置于文學的中心,主體性從“深淵”回到了文學創作的舞臺中央。
最后是啟蒙精神的復現。“五四”文學革命先哲們將啟蒙的要求與新文學相連,奠定了新文學現代性的重要價值維度和審美傳統。而這一切在“十七年”至“文革”期間被中斷了。新時期重提“文學是人學”,重塑文學中的人道主義精神。作家在文學實踐中熱心表現人情、人性、人道,揭露文革迫害、批判極左思潮,表現出新啟蒙的要求、思想解放的要求、個體自由的要求。從這一意義上說,新時期“文學是人學”的命題,實際上繼承了“五四”的啟蒙傳統,將中斷已久的啟蒙精神線索重新接入中國新時期“現代性”敘事的歷史建構之中。
(二)新時期“文學是人學”命題的局限
不可否認,新時期“文學是人學”命題論爭在客觀上糾正了“階級論”“工具論”等有失偏頗的文學觀,將文學創作從階級、政治話語中解放了出來,促進了新時期中國文學創作的健康發展。但是當離開歷史現場數十年后,重新冷靜全面地審視新時期“文學是人學”命題便會發現其局限性。
首先是命題定義的窄化。“文學即人學”并非嚴格的代換關系。將文學定義為人學,從表面上看似乎為文學的定義找到了完美的答案,實則陷入了“概念循環”的謬誤之中。從字面上看,文學與人學并不相等,一為語言藝術的范疇,一為社會學的范疇。從內涵上看,文學確實是表現人生、人性、人情,但其價值意義絕不僅限于此,它還可以表現社會、歷史、政治、審美。顯然,將文學定義為人學,有窄化文學價值的嫌疑。
其次是“人學”在此等同于“人性”。如上文所述,文學與人學的詞義其實是不對等的。在“文學是人學”這一命題中,“人學”的意義更多接近于“人性”“人道”“人情”,而并非是學術研究的意義。錢谷融等人將人道主義精神當作批判“階級論”“工具論”的強大武器,以前蘇聯高爾基“人學”論為語言表達的物質外殼,忽略了“人學”詞義的模糊性,也造成了“文學是人學”命題的理論漏洞。
四、結語
文學與生俱來的“主體性”使其每時每刻都帶有“人”的印記和尺度,在這一邏輯之下,“文學是人學”。新時期的“文學是人學”命題是五十年代“人學”論爭的余緒,是新啟蒙思想和政治“祛魅”之下的產物,是理論家批判“階級論”“工具論”的強大武器,是新時期人道主義文學興起的標志,更是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從客體論到主體論轉向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