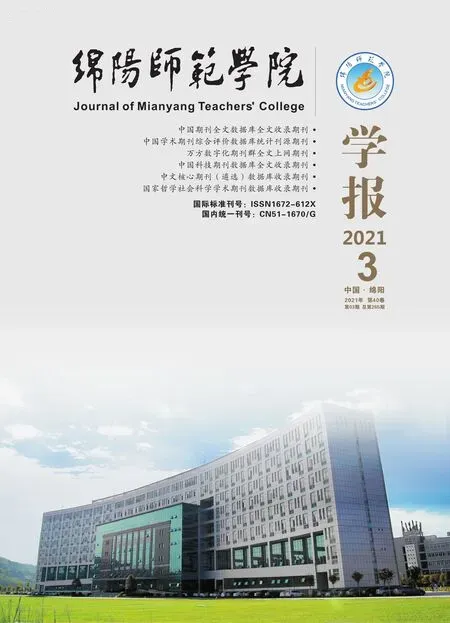淺論周梅森戰爭小說的藝術特點
徐雪濤
(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福建福州 350007)
周梅森的戰爭小說曾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引起很大轟動,其作品以對“戰爭與人”的反思將戰爭小說這一類型的創作推到歷史縱深,顯露出新的文學面相。從創作伊始,周梅森便以極強的現實主義精神向歷史深處掘進。他著重探索歷史變遷之間的偶然性、無常性以及人在歷史車輪下的脆弱與渺小。當這種歷史意識與戰爭題材相遇,更能從中顯示出悲劇情懷與人性掙扎。在《軍歌》《國殤》《日祭》《大捷》《冷血》等構成的“戰爭系列”小說中,周梅森將關注點瞄向作為“人”的獨立個體上,關注那場悲壯戰爭場景下“個體的心靈沖突與命運浮沉,以此來探究人本身”。周梅森通過對以往被遺忘的國民黨軍人群體的執著書寫塑造了新的軍人形象,摹畫了復雜多元的人性意識,流露出深沉的歷史意識和清醒的反思精神。
一、新軍人形象的塑造
(一)新軍人形象得以塑造的原因:政治與文學的互動
戰爭小說是以戰爭行動為主的文學作品,從這一釋義出發,戰爭雙方就成為了戰爭小說作家的重點描述對象與創作內容。對于經歷過漫長烽煙歲月的中華大地來說,戰爭可以算是極具現實感的文學描寫題材。在十七年時期,由于文藝方針政策的規約以及主流文藝批評價值取向的導引等原因,當時的戰爭小說多著筆于以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武裝抗擊侵略、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故事。比如《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保衛延安》《紅日》等作品,在這些以共產黨軍人為主角的文本中,國民黨軍人的形象處于一種失語或缺席的狀況。直到新時期這一情況才得以改觀,大量客觀書寫國民黨軍人抗戰的作品才逐漸出現。
這種現象首先要歸結于對國民黨正面抗戰的肯定與評價。1985年9月3日,首都各界一萬余人隆重集會,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40周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彭真同志指出抗日戰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國共兩黨合作是符合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毫無疑問,這場講話對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與意義作出了新的評價,同時也為小說創作題材的拓寬奠定了基礎。因此一批秉持客觀歷史態度的作家紛紛開始以超越階級的眼光來書寫國民黨正面抗戰的史實。也正是在文學與政治的雙向互動中,大量描寫國民黨軍人的作品問世,被遮蔽的國民黨軍人群體逐漸被還原成更具真實性的軍人群體。不過由于時代的悲劇和自身的缺陷,加之國民黨軍人所處陣營的特殊性,這些因素合力使得文本中出現的國民黨軍人的人性內涵更加復雜多元,這也在無形中為塑造新的軍人形象提供了發展契機。
張廷竹的“中國遠征軍” 系列小說、周而復的《長城萬里圖》 、王火的《戰爭和人》、江建文的《國難》等作品試圖探尋歷史真相,描寫國民黨統治區的抗日史實,為戰爭小說的題材拓寬邁出了第一步。這些作品的出現也說明更加真實、更加貼合歷史的全民族抗戰圖景正在被打開,而周梅森毫無疑問是其中的創作者和推動者之一。他的“戰爭與人”系列小說以獨特的敘述視角與描寫對象,為讀者建構了新的軍人形象,還原了更具真實感的歷史畫卷。從選取題材來看,他筆下的人物多是國民黨軍人。《軍歌》《大捷》《日祭》《事變》《荒天》《國殤》《冷血》等。這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按身份來說,都是自愿或被迫投入戰場的國民黨上下級軍人,甚至是委身附逆的偽軍群體。在這些作品中,周梅森沒有采取以往臉譜化塑造人物的方式,站在道德和民族的制高點上一味譴責其惡行,而更多的是在剝離了其身份和階級的基礎上,用一種人性的思辨角度還原了在特殊境遇下人物的言行。也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周梅森得以創造出區別于大多數戰爭小說作家的新軍人形象。
(二)新軍人形象的英雄色彩和民族氣節
首先,周梅森作品的軍人形象在打破隔閡與階級意識的屬性外,賦予了人物比以往更多的英雄色彩。周梅森小說的主角俱是國民黨軍人,但無一例外的是這些主要人物多處在一種堪稱“絕地”的場景中。《軍歌》的故事背景設定在徐州會戰國軍潰敗被俘的集中營(地下煤礦)中;《日祭》的故事背景設定在上海大部即將淪陷,林啟明所部深陷強敵環伺、注定失敗的守城戰中;《國殤》開局就是陵城保衛戰,在面對增援部隊或潰散或附敵的情況下,楊夢征的新22軍也陷入了絕境。毫無疑問,這些“絕境”的設立使得作品的可讀性大大提高,帶給讀者的直觀感受和沖擊力也不斷加強。
所謂向死而生,在這樣的險境中,作者充分塑造了一批體現英雄氣概和民族大義的軍人形象。《日祭》主要描寫的是以林啟明為代表的一批中國軍人于淞滬會戰時被迫進入租界,成為戰俘而被租界當局關入“第九軍人營”的故事。在戰俘營中他們始終不忘家國民族,以精神升旗、每日操練等活動提醒自己的身份,彰顯愛國的情懷。林啟明是作家筆下具有鮮明人物色彩的一個角色,作為國軍1776團3營營長的林啟明在德信公司領導的戰斗可以說是可圈可點,充分顯示了他出色的軍事指揮才能。面對租界軍官布萊迪克上校關于其放下武器進入租界的建議時,林啟明的回答充滿了民族氣節:“可兄弟據守的這座樓房上還飄揚著我們的國旗,中國守軍還在戰斗。”[1]192在后期被迫進入租界的記者會上,下層軍官涂國強的發言也體現了作者澆灌在國軍群體上的民族情感。在面對記者關于抗戰前途之提問時,涂國強回答道:“兄弟認為中國抗戰的前途必定光明!最后打勝的一定是咱中國!戰斗雖一時失利,弟兄們的抗戰決心偏就更堅定了,有我們國軍弟兄和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之堅強決心,哪有他媽打不敗的敵人呢!”[1]210除此之外,像《國殤》中不愿投降率部突圍的師長白云森、楊皖育;《軍歌》中雖然被俘但是一直渴望重回戰場、重拾象征軍人尊嚴的那首軍歌的炮營營長孟新澤;《事變》中一心反正帶領部隊投奔國軍的黃少雄;《大捷》中雖被迫擔任阻擊卻打得頑強勇敢的段仁義、霍杰克、方向公與卸甲甸百姓, 這些人物可以說都是充滿民族氣節和英雄基因的抗日志士。
(三)新軍人形象的失敗感和落魄感
其次,周梅森筆下的軍人形象充滿了落魄感和失敗感,是一群極具個人色彩的軍人畫像。作者描寫的國軍形象突破了以往的“臉譜化”“小丑化”的標簽,賦予了他們更多應有的家國情懷,同時因為時代的原因也給他們刻上了落魄與失敗的烙印。《大捷》中的“國民革命軍23路軍新三團”被放置在馬鞍山一帶阻擊日軍,可是這支部隊卻是由縣長、保安團長、決死隊長、小學校長、甲長、保長、鐵匠甚至瘋子臨時拼湊成的,可以說是“地地道道的烏合之眾”。《軍歌》中在臺兒莊大勝之后,因為上級的不當安排而使得孟新澤“他這個扛了十八年大槍的中國軍人竟然在日本人的刺刀下舉起了雙手”,以至于和無數個軍人一起被關押在戰俘營而“陷入了無休無止的悔恨中”[1]4。《國殤》中面對數倍于己的日軍,楊夢征率領的陵城子弟兵在援軍或被擊潰敗逃或被敵偽誘降而倒戈一擊的情況下,不得不簽下了象征恥辱的投降命令而在三顆信號彈升空之前飲彈自盡,將投降的命運留給了在世者。
《軍歌》中的主人公炮營營長孟新澤作為傳統的中國軍人,面對國破家亡的災難,他對日本侵略者有著刻骨仇恨,對剛剛過去的失敗悔愧不已。所以這也使得他對過去輝煌勝利的代表——“軍歌”——懷有一種崇敬的心情,一想起就激動不已。為了重新拾起軍人的尊嚴,也為了自己的自由,洗刷投降的恥辱,他率眾串聯起了煤礦地下的暴動,甚至“不擇手段”地欺騙戰友們外邊有游擊隊策應。在孟新澤的回憶中,激戰初期,“他和他的弟兄們情緒是高昂的,他們都下定了作為一個中國軍人以死報國的決心。因為,他們知道,他們進行的這場戰爭,是關乎國家命運、民族命運的大搏斗”[1]40。所以在開始的戰斗中,孟新澤們表現得英勇且堅韌,打出了中國軍人的骨氣和品格。但是作者卻把這些情節隱藏在人物的回憶中,更多地將情節聚焦在戰俘營的生活。正是在這樣的文本中,軍人形象被賦予了一種落魄感,始終縈繞在一種失敗和恥辱的氛圍中。可以說,這種描寫使得他身上鮮明地體現出了傳統軍人英雄形象的共同特征。但在這個基礎上,作者又賦予了他更豐富的普通人的“情感”,寫出了他在戰俘營的煎熬與掙扎,在崇高性的基礎上給人物褪去了高大的光環,還原其為惶惑、愧疚又脆弱的普通人。
毫無疑問,這些軍人與以往那些意氣風發、斗志昂揚的軍人形象相差甚遠,可以說這樣的軍人因為戰爭的失利而顯得有些過于頹敗,充滿了一種伴隨始終的落魄感。正是這種落魄感使得周梅森筆下的人物始終處在一種極強的張力中,也使得整個故事由于充滿了一種潛在的抗爭性而處在濃烈的悲劇氛圍中。這種張力一方面使得故事充滿了戲劇性,另一方面也為人物由落魄向高尚、由平凡至偉大奠定了合理的邏輯起點和故事背景。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轉變與外在的階級、政治、意識形態無關,它取決于個人的意識、尊嚴、品格,取決于人性中善與惡的博弈。在這樣充滿張力與流動性的故事下塑造出的人物以其落魄和扭曲顯示了戰爭對人性的摧殘與異化,同時由于其在故事發展過程中不斷變化的心理與言行,也讓軍人這一角色在戰爭中的成長與升華得到了進一步的肯定和贊揚。周梅森敢于把這樣身上有缺點的人物作為英雄來塑造,即便是寫正面人物,也注意到他的復雜性,不去一味美化。這一切都具有開拓新領域、沖破長期存在的簡單化、公式化人物的意義,對于戰爭小說來說無疑是一個新的發展和突破。
所以從上述兩個軍人屬性的塑造上,周梅森沒有給筆下的國民黨軍人群體簡單地作出“英雄”或者“失敗者”的歷史二分法型的粗暴評判,“而是力求立體的呈現出人性中的美與丑、善與惡的較量與消長, 刻寫出一個個正義與罪惡并存, 骯臟與美麗互現的軍人的靈魂”[2]。因此出現在周梅森作品里的國民黨軍人于民族獨立與反抗侵略的戰場上萌生出的民族正義感與反抗感,使得他們獲得了與以往國民黨軍人不同的人物屬性:在落魄中力求生存的可能,在戰亂中心懷家國的情懷。這兩種屬性在周梅森筆下的軍人形象中疊織纏繞營造了一種悲壯感。與以往書寫戰爭的悲壯感不同,《高山下的花環》《黎明的河邊》《林海雪原》等作品的悲壯感主要來源于主人公高尚的人格力量和堅定的政治信仰。周梅森塑造的新軍人形象一方面充滿了民族氣節和正義感,面對民族矛盾、國家危亡他們挺身而出,但是另一方面“又由于政府的腐敗無能,最高當局及軍事決策者的昏績自私乃至險惡用心,常常使第一線的官兵陷入困境乃至絕境”,他們“皆負著國家和民族的道義而陷入雙重的困境,這就是周梅森軍旅小說悲壯氣氛的重要成因”[3]。正是在這樣極具悲劇感的故事敘述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新軍人的形象,豐富了中國當代戰爭小說的人物畫廊。
二、復雜多元的人性意識
周梅森的小說多從歷史、現實與土地取材,由此出發他的小說注重著筆于抗戰歷史的再建構,同時又因為特定的時代使得他筆下的戰爭故事在重建與解構中蘊含了深沉的人性意識和歷史嘆息。縱觀戰爭小說的發展歷程,十七年時期的戰爭小說注重以大場面、大構架、大情勢來渲染戰爭場面的宏闊與壯烈。《紅日》《保衛延安》等作品就以“結構上的宏闊時空跨度與規模”“英雄典型的創造和英雄主義的基調”被稱為史實性作品。但是十七年時期的戰爭小說,可以稱之為“大眾文學”,卻在藝術上缺乏一種更為嚴格的文學審美追求,尤其是人物刻畫缺乏深度,影響了其文學價值。直到八十年代,更多的作家開始普遍認同“人性是最為根本的思想、認為文學的最深(也是最后)的層面便是人性之后”[4]286。因此,以周梅森為代表的一批作家不僅對題材進行了探索和創新,彌補了描寫對象上不平衡的狀態,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他以一種超越階級的眼光,在克服歷史的政治慣性和傳統的藝術思維方式上對戰爭進行了重新的審視,對于戰爭中透視出的人性的復雜和靈魂的掙扎作了文學藝術上的深刻描畫。可以說,他“在重新審視戰爭本身的諸多奧秘的同時,以更為多樣的目光致力于戰爭中的人的存在景況及各種社會人性內容的具體形態的重新發現———他們不再為寫戰爭而寫戰爭:戰爭的描寫不再是目的,描寫的目的僅僅在于:經由戰爭的洞觀而重新認識人、重新認識人類的處境”[5]。
恩格斯曾經說過,“歷史可以說是所有女神中最殘酷的一個”,是在“堆積如山的尸體上馳驅她的凱旋車的”。可以說,戰爭是人性沖突爆發的最終方式,也是人性博弈最殘酷的場地。周梅森“戰爭與人”系列小說的立意即在此,他無意于描摹戰爭場面的激烈與壯闊,而是試圖采取一種淡化戰爭場面的敘述技巧,將更多的筆墨投入在“戰前”與“戰后”心理精神的矛盾與沖突中,從而在壓抑低沉的氛圍之中展現人性的裂變。戰爭在周梅森筆下逐漸退化為人類生活的一種方式。作者在一種更宏觀也更有距離感的高度,從“人”這一族類意義上的視角去審視戰爭。經由戰爭這一顯色板,人性在偉大與高尚、黑暗與卑鄙之間的“交戰”顯得更加清晰,人性之間對于命運和無常的抗爭也就顯得更加觸動人心、扣人心弦。
(一)對于人性惡的直接展示
周梅森對于人性書寫的第一個特點即是將人物置于絕境之中,在靈魂的沖突與內心的掙扎中,寫出了生死威脅時人性的丑惡,從而指向戰爭時期人的歷史存在的災難性狀態。《冷血》的故事發生在中國遠征軍戰事失利敗退回國的途中。作者沒有著筆描寫戰爭場面的殘酷,而是將視角轉向戰后求生的故事上。在小說中作者極其巧妙地將人物引導到野人山這一生死未卜的場域之中,給了故事很強的巧妙感和可讀性,為人性在非常時期的展示提供了絕佳的場地,同時用嚴酷冷峻的敘述口吻讓讀者從故事的發展和人性的流變間體會到當時的悲壯與慘烈。《冷血》中的主人公尚武強是第五軍政治部上校副主任,從他在后面對自己前半生的回顧中——“在重慶軍官訓練團接受蔣委員長的召見”,“改變國家和民族命運的責任,一定會歷史的落到他們這代人的肩上”[1]131,可以想象,尚武強也曾經是一個充滿愿景和熱血的青年軍人,他的身上閃爍著屬于軍人的光輝。在第五軍殘部一萬七千余人奉命穿越野人山,轉進印度集結待命時,尚武強“憑借人格的力量和鐵一般的意志”奇跡般地穩定了部下騷亂絕望的情緒[1]107,順利地完成了編組進入野人山的任務。初入野人山,尚武強還能鼓勵士氣,與戀人曲萍共同扶持。但是在面臨缺少糧食給養的情況下,尚武強逐漸變成了曲萍口中的“野獸”。為了活命,他利用強權霸占了曲萍,威逼伙夫老趙睡在帳篷外。到最后,他為了擺脫曲萍自我逃生,甚至裝出中毒的癥狀,在曲萍找人解救他時悄悄溜走。最能暴露人性的就是在尚武強獨自求生遇到曲萍的路上。當時尚武強打了兩只狼崽正烤得發油,曲萍無意間與之相遇。在食物和戀人面前,尚武強的選擇讓赤裸裸的丑惡人性展現得淋漓盡致。他用手槍指著曲萍的胸膛,聲音像“一陣刮自地獄深處的陰風”,沖著曲萍喊道:“我不認識了!誰也不認識了!這個世界上只有我,只有我!給我走開!快!快!快!”“他急迫的一連說了三個快字。”[1]168尚武強的選擇是環境惡劣使然,但也是人性深處的裂變,是戰爭這一殘酷行為對人的扭曲和異化。同樣表現人性在極端場景下的丑惡還體現在作者的其他小說中,如《軍歌》中為求自保而向日本人告密孟新澤等人暴動的劉子平;《荒天》之中無視家國民族,一心只為保存實力和自我權力的形形色色人物;《孤旅》中在民族危難、國破家亡之際,卻將其所攜帶軍餉拿去做生意的少將軍需官馬炳如。這些人物的出現將周梅森筆下對于人性思考的第一個特點展現了出來,說明“人性既受文明社會的道德約束,又受人的種種本能驅使,戰爭中的人性又比非戰爭狀態下的人性更加復雜和不可捉摸,因為戰爭迫使人直接面對的是生與死的考驗。因而戰爭在某種意義上是人性的最大顯微鏡,人性的種種美丑善惡盡在它的透視下顯現出其本來面目”[6]65。
(二)對于人性善和美的肯定
周梅森對于人性描寫的第二個特點即在生存榮辱之際寫出了人對于生存和生命的渴望與追求,對于人格中善與美的肯定,對于在特殊形勢下軍人品格中英雄主義的贊美。《大捷》寫的是因為陰差陽錯的誤會,卸甲甸的百姓被編入“國軍”隊伍,奉命在馬鞍山一帶以戰死一千六百余人的代價阻擊日軍三十六個小時而取得“大捷”的故事。故事中的國軍并不是因為感受到民族危機和國家存亡才去參軍,相反在三個月前他們只是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只是因為章方正、蘭盡忠等人的一時意氣,將駐扎在縣城但是軍紀敗壞的國軍炮營“連鍋端”了,才被23路軍總司令韓培戈強行編入隊伍并被放置在最前線。前有強敵進攻,后有1761團阻隔后路,這些原本連戰壕都挖得松松散散的“烏合之眾”們硬是將日軍阻擊在戰線以外,創造了輝煌的戰績。可以說,這場所謂“大捷”的戰績出自于玩弄心計的“陰謀戰爭家”韓培戈之手,也同樣出自于每一個不屈、勇敢的靈魂。面對困境,他們開始時有著各式各樣的目的:有的想要發財,有的想要落草,有的想要投敵,有的想要脫逃。但是正如章方正在戰前會議之后所想的那樣,他“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戰爭是怎么回事。只要打起來,他們的目標就是一致的,命運就是相同的,他不能指望在一場惡戰之后,別人都死他獨生。事情很簡單,蘭盡忠的二營打完了,他的一營、侯營長的三營都要上,下崗子村前沿失守了,他們所在的上崗子就會變成前沿”[7]133-134。帶著這樣共同求生的意念,這些形形色色的想法在戰斗開始后慢慢地轉化為對于生存的希望、對于生命的渴求。他們與敵人殊死搏斗,“在無法抗拒的雙重壓榨中,他們的生命走向了輝煌,爆發出令人炫目的異彩”[7]189。最終在戰爭與生命的毀滅中實現了自我人格的升華,展現出了人性中的優秀品格。
(三)對于流動的人性的刻畫
需要注意的是,周梅森筆下人物的人性善惡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由惡向善的回歸,由獸性至人性的復蘇始終處在一種變化的過程中。在《軍歌》中,孟新澤、項福廣、王紹恒、劉子平、耗子老祁、張麻子等人,他們因為徐州的潰敗而被俘,最終都被關押在蘇魯交界的一個煤礦當苦力。極端惡劣的生存條件使得他們的生命處處受到來自煤礦底和日本人的雙重威脅,可以說戰俘營/煤礦是這些軍人的棲身之地,也是他們的葬身之地。那些建立在正常社會的秩序、規則、道義和理智在這里蕩然無存,生存的法則變為個人力量的博弈。像來自湯軍團的普通大兵田德勝,他“憑著一身令人羨慕、又令人膽怯的肌肉,贏得了又一次生存競爭的勝利”[1]13。可以說在這里,一切正常社會加之于人類的規則、秩序和等級統統被打破,弱肉強食和明哲保身成為了人人遵循的不二法則。這種極端的環境設置為作者深層次的剖析人性善惡提供了場景,也讓之后發生的故事有了合理的邏輯起點。孟新澤們在前夕還是血戰臺兒莊、保衛徐州的抗日英雄,但是一瞬間的潰敗和投降讓他們喪失了軍人所有的榮譽和尊嚴。當直面死亡,人性的丑惡便盡數展現了出來:為了逃命,項福廣向日寇告密,使得逃跑的戰友慘遭殺害;為了求得生存的砝碼,劉子平精心謀劃告密的時機;當代替老祁穿梭在坑洞之中時,田德勝對自己找到出路拋棄地下的戰友沒有絲毫猶豫和愧疚;當越獄暴動因為告密而慘遭失敗時,多數人甚至想要抓住暴動的組織者孟新澤和日本人討價還價。自私、卑劣、狡詐、猥瑣這些丑惡現象的爆發像炸彈一樣震撼著讀者的心靈。但是作者卻不是一味地去描寫人性的丑惡,而是在變化中寫人性,寫變化的人性。被孟新澤所感動,田德勝出人意料地選擇了將他藏在之前的坑洞中;為了洗滌自己內心的愧疚與惶恐,項福廣堅定地站在了暴動的行列中,提著槍走在隊伍的前列;耗子老祁在不斷的侮辱中,最終點燃了彈藥室的引線,一群即將被殺的戰俘們喊出了“打倒……”的口號。隨著環境的變化、周圍事態的發展,每個人的人性也在起著變化。正因如此,人物形象才顯得更豐滿,戲劇沖突性才更強,作品才更凝重,流動感也更強,情節進展得緊張起來,緊扣讀者的心弦。
三、深沉的歷史意識和清醒的反思
(一)深沉的歷史意識
周梅森小說的著重點除了寫活了深層心理中的人性意識外,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在深層開掘人性意識的基礎上嵌入了對沉重歲月的歷史思考與自我對于戰爭的獨特感悟。厚重的歷史感和始終清醒的對于戰爭的反省,可以說是周梅森作品極鮮明的特點,也是貫穿他作品始終的一個主題。“歷史和人的思考,確實是他的小說的潛在本文,是他創造意識上一個中心系之的情結。”[8]十七年時期的戰爭小說主要目的多是“以對歷史本質的規范化敘述,為新的社會、新的政權的真理性作出證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動對歷史既定敘述的合法化,也為處于社會轉折期中的民眾,提供思想、生活的意識形態規范”[9]95。這類作品對于歷史采取的是鞏固的手法,是起著“戰爭形式的歷史教科書”作用的,試圖以文學的形式重現那段歲月的革命史。直到八十年代新歷史主義盛行,“被現代主義思潮包圍的中國,開始接受另樣的歷史觀,并且由于長期以來文學歪曲存在的真實性而根據英雄主義的需要任意拔高人物、美化人物的做法已使人反感甚至是厭惡,文學對歷史換了觀察的眼光。而這種眼光受了新的情緒與新的觀念的影響,將歷史讀成了另外一番樣子:歷史與英雄無關,只與細民有關;歷史上本無英雄”[4]295。
在此背景下,文學不再簡單地對歷史進行重復,而是開始以一種個人性的方式參與到歷史的釋義和構造中去。正如格林布拉特所說的:“作為文學創作者的‘自我’與文化和歷史之間,都是一種相互塑造的關系。文學是攜帶多種信息的文化‘通貨’,它不斷地‘流通’進行著‘塑造’的作用。”[10]而克羅齊也曾對歷史有過經典的表述: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因此,從這個觀點出發,具有較強自主性和主體性的文學在與歷史的雙向互動中不斷解構和重構了現實的“材料”,本質主義和絕對主義的歷史觀越來越受到質疑,個人化的文學想象將歷史變為一種不斷言說和意義生成的組合形式。周梅森的作品就充分顯示了作者“想象天才的藝術結晶”,跳出了歷史法則的局限性,在充滿了不確定性與偶然性的歷史結局里找到被粉飾的多樣化的進程,發出了以往被遮蔽的聲音。
《大捷》背后因為高層的報復而喪命于日軍炮火下的卸甲甸百姓;《冷血》中輾轉回國路上像曲萍、何桂生這樣小人物的痛苦與生命的最后經歷;《事變》種砦司令治下的廣清八縣儼然半封建的舊中國;《荒天》中圍繞反正與附敵,眾人之間展開的博弈與算計,更讓人看到了歷史背后隱藏的殺機和圈套。歷史對人性的不斷深入解剖讓人不得不重新審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數《國殤》和《軍歌》。《國殤》描述的是抗戰時期國民黨新22軍圍繞陵城保衛戰的失敗過程及深埋其中的內部矛盾。作者顯然不在于著意描寫戰爭,除了開篇通過軍事會議來渲染氣氛的緊張外,更多地通過新22軍的軍官們在戰役前后的不同選擇展開了對歷史的深沉思考。小說根據戰役的不斷推進可以分為三個部分,每個部分輔之以不同的主要人物。從楊夢征到白云森再到楊皖育,從陵城起家的楊氏子弟兵最終回到了楊夢征的侄子手中,歷史在這里巧妙地形成了一個閉合的環形結構,暗示出了歷史的波詭云譎以及人在歷史面前的無能為力。小說因圍繞軍權的歸屬而不斷轉換的眾人走馬燈般出現在讀者面前,軍官們在光榮與恥辱、生存與毀滅前作出了自己的選擇,也透視出人物的性格面目和發展過程。作者以白云森的死暗示了理想主義下傳統道德歷史模式的破滅,道出了歷史無情的鐵血法則,而以楊皖育發給中央的電報作為結尾,為逝去的眾人安上了“殉國”的帽子則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給讀者留下了關于歷史的深沉思考。當然,對于歷史更直接的解構體現在《大捷》這部小說中。小說的下篇以中央社、共同社、美聯社、前線社、亞通社、《明報》等報社對于“大捷”的報道以及授勛儀式上段仁義等人對韓培戈的復仇相對比作為結尾,作者似乎在告訴我們:“真正的歷史從來不是一個個光鮮如‘大捷’‘軍歌’‘國殤’的名詞,而是一段充滿了光明與陰暗、鮮花與鮮血的冷漠殘酷的蜿蜒曲線。真正的歷史不存在結果中,而是存在于過程里。”[11]92
(二)對戰爭的深刻反思和清醒體悟
除此之外,不同于以往作家對于戰爭的禮贊和對英雄的頌揚,周梅森在作品中始終有著清醒的思考。他以一個作家的良知生動地描寫了戰爭對于美好的摧殘,同時也在思考戰爭狀態下人的個體性和自主性。在《大捷》中,團副霍杰克在最后的戰役與白潔芬相遇,在為白小姐包扎傷口時,他看到了“那只糊滿鮮血的乳房”,“他再也不會忘記戰爭對美好的摧殘,在那一瞬間使他動魄心驚。他曾在用駁殼槍對著前團副章金奎時,無意中瞥見過那乳房,并由此而生出了許多美麗的幻想,如今,幻想在嚴酷的真實面前破滅了,被槍彈毀滅了的美好,使他看透了戰爭的全部罪惡”[7]197。而在《日祭》中,作者又借林啟明這一人物的生死際遇反思了集體性與個人性之間的沖突,并且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當戰爭涌來,個人被裹挾入國家抗戰的巨大變動之間,個人性是否成為了民族的阻礙?看似是作者借助林啟明和牛康年的深層次矛盾,思考了“自己個體的生存和民族的生存是否能完全割裂開?民族的生存,是否就是個人生存的天敵和負擔?”[1]259-260這樣一個問題。但實際上作者由此上升到了一個更為宏觀的視角,那就是整個人類對于自由、個體性對于集體異化的一種反思。
但是作者認為,無論是戰斗中還是戰斗后,林啟明都活得太不“自我”,“他作為一個中國軍人,活著的時候毅然擔起了應承擔的全部責任和道義,任何人也編排不出他的不是。他沒被責任和道義壓垮,這是值得驕傲的。現在他倒下了,身上的責任和道義也就隨之消失了。他無需再代表國家和民族,無需再對任何人、任何事業負責,他將作為一個人,一個叫林啟明的中國人而邁入生死之間的門檻。這無疑是一種解脫,就象負荷重軛的牛,卸去了背上的重壓”[1]270。作者顯然對現實主義有著更為清醒的認知,才沒有使其對于個人性的思考滑入虛無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深淵。最后的結尾,作者借林啟明臨死時的獨白告慰了自我,告慰了整個在戰爭中犧牲自我的民族:“卻不悔,到九泉之下也不悔。如果來世再做軍人,再和東洋鬼子打一仗,再到這第九中國軍人營走一遭,他依然選擇這樣的活法。肩著民族苦難的人雖說注定不會有好下場,但一個民族卻不能沒有這樣的鐵肩膀,沒有鐵肩膀的民族是注定要消亡的。只有那些在民族危難時,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 才是真正的人。由這些真正的人構成的民族, 才是不可戰勝的民族。”[1]271
四、結語
總的來說,周梅森的小說習慣在沉重歷史的宏大背景下,緩緩敘述一群戰敗的中國軍人的慘痛往事,以一種低沉壓抑的筆觸描繪了極端環境下的復雜人性。在小說中,作者以粗獷的語言、精心的安排、合理的結構與穿插其中的回憶,寫出了新的軍人群像。他的作品在絕境的場域中透視了人性的丑惡,又在流動的敘述中描繪了人對于戰爭這一“大碾盤”的抗爭,寫出了流動歲月中的真實人性,也歌頌了人性中的高尚品格與偉大精神,讓讀者在人性的翻滾與變化中領悟到戰爭這一“碾盤”對于生命和美好的毀滅與摧殘。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在周梅森的作品中“深沉的歷史意識以及深沉的人性意識,是和諧地共存于一個藝術整體中的。它使得周梅森的作品具有了一種凝重厚實的史詩般品格,使得他作品中的人物大都能擺脫那種簡單化的束縛”[12]。所以,他的軍旅小說能夠在客觀的基礎上重現那一時期各階層人士的表現和復雜的心態,給讀者展示了更為真實的歷史圖景,有助于加深對民族力量的進一步認識。而寄寓在他對歷史進程和結局的演繹推想,則大大提高了他作品的思想含量和意蘊覆蓋,使得文本具有了無限的生成意義和闡釋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