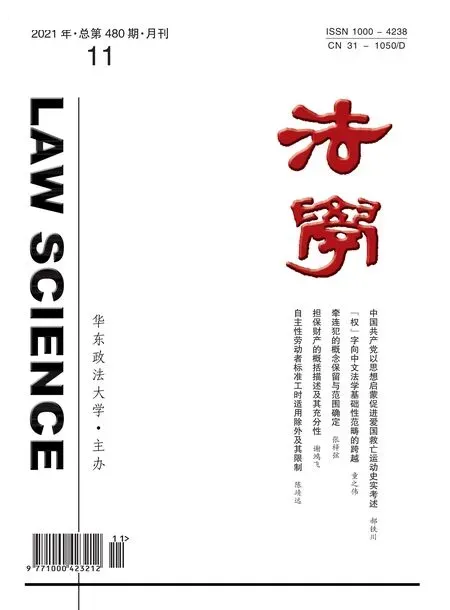“權”字向中文法學基礎性范疇的跨越
●童之偉
現代中文法學,包括憲法學,與中國傳統律學最大的不同,是前者看重從基本的法現象中提取抽象概念并用以系統解釋法現象,而后者往往只關注、研究法現象本身。現代中文法學為數很有限的基礎性概念中最重要的幾個,如權利、權力和法權,都是以古漢字“權”為根基和文化依托,在與西文法學、日文法學名詞接觸、互動和對譯過程中形成的。“權”字指稱的社會現象的范圍,在進入19世紀后經歷了幾次根本性的變化,到20—21世紀之交已經穩定下來并獲較深入的研究,終于形成了外延、實質(或內容、本質,后同)比較清晰的“權”的概念,并獲得了 “quan” 的英文譯名。〔1〕筆者做此判斷的依據,主要是如下論文和著作:童之偉:《中國實踐法理學的話語體系構想》,載《法律科學》2019年第4期,第3-19頁。Tong Zhiwei, Right, Power, and Faquanism: A Practical Legal Theory from Contemporary China, trans.Xu Ping, Leiden,Bosto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8, pp.35, 318-325.“權”這個漢字是如何跨越數以千年計的歷史,發展衍射〔2〕本文在引申意義上借用的“衍射”一詞,物理學上指從原點出發的波繞過障礙物繼續傳播,亦稱繞射。出相關的現代中文法學基礎性概念且自身也嬗變為其中之一的呢?筆者選擇考察這個問題,不是因為愛好法文化,探險獵奇,而是因為只有還原這個歷史過程,當代中國法學、憲法學才有可能基于本身的傳統和適應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需要,準確理解權、權利、權力、法權、剩余權等基礎性范疇和作為它們反映對象的那些基本的法現象。
一、“權”字起源及其同西文法學對應名詞的交匯
權(權、権)最初同“輿”組成“權輿”一詞出現在《詩經》中:“于嗟乎,不承權輿!”(《詩·秦風·權輿》)表草木萌芽狀態,引申為起始。〔3〕《大戴禮記·誥志》:“于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又《毛詩注疏·卷六·之四(國風)》:“承,繼也。權輿,始也。”權單獨做名詞時,本義是豆科植物黃花木,故中國最早的詞典《爾雅》對權的定義是:“權,黃英”( 《爾雅·釋木》)。
在先秦兩漢,除黃花木外,“權”字還獲得了數種其他意思,其中有些實際上為19世紀上中葉萌生的現代法學要素里“權”這個名詞增生新含義奠定了一些人文基礎。在數百年間,“權”字形成了以下8種含義:(1)權衡、衡量,如“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 (《呂氏春秋·舉難》);“權,然后知輕重”(《孟子·梁惠王上》)。(2)秤錘(秤砣)、秤,如“權者,銖兩斤鈞石也” (《漢書·律歷志》); “錘,謂之權”(《廣雅·釋器》)。(3)權變,如“嫂溺授之以手者,權也” (《孟子·離婁上》)。(4)不拘常規,如“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后有善者也” (《公羊傳·桓公·十一年》)。(5)威勢,如“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 (《賈誼·過秦論》)。(6)權位,如“權制獨斷于君則威”;“惟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 (《商君書·修權》)。(7)權勢,如“不肖而能服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 (《韓非子·難勢》);姓氏,即后來的“百家姓”之一。
“權”字的上述第六、第七兩重意思中包含較多合法公共強制的成分,它們為“權”字在19世紀初與西文,特別是英文名詞power、authority形成含義對應關系和互譯奠定了本土語言基礎。“權”字在先秦兩漢都不是社會生活中的常用字。東漢后期的字典《說文解字》給“權”字的定義是“黃華木。從木雚聲。一曰反常”,還加注“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等語(《說文解字·卷六·木部》)。這部字典只列舉了“權”字的兩層基本意思,其他意思未列舉,顯然其他用法比較罕見。
從《康熙字典》對權字的詞義認定和例說看,東漢之后的1500余年間,此字幾乎沒有增加新詞義。該辭典解說“權”字的含義,除說明“攝官曰權”外,所有例句都取自兩漢典籍,且即使是“攝官”中暫時代理某官職的含義,也是先秦典籍中已有的,如“敢告不敏,攝官承乏” (《左傳·成公二年》)。但是,《康熙字典》同《爾雅》和《說文解字》相對比,還是有些值得注意的不同之處:《康熙字典》列舉的含義多達11種,其中“秤錘”居首;不再“以草釋木”,改“黃英”為“黃華”,并置于最末;加進了“權柄”。“權柄”是唯一同現代法學中權力概念有直接關系的含義,在該字典權字含義中排序第五,所用例句是出自《莊子·天運篇》的“親權者不能與人柄”。〔4〕《康熙字典》,權,木部,1716年武英殿刻本之影印本,第2649-2650頁。不容忽視的是,正是該詞典對“權柄”的這一安排,使得后來英國傳教士、漢學家馬禮遜和他的《華英字典》系列可以將英文power(還有authority)在很大程度上與之對應起來,從而為“權”字向現代中文法學基本概念的演進提供了契機和動力。
“權”字同西文,尤其是拉丁文、法文相關詞語的含義在詞典水平上的對接和獲得dominium(統治)、auctoritas或auctoritat(權威)含義,是它走向廣闊中文法學空間的第一塊里程碑。歷史上“權”字與西文首次形成交流和對譯的情形,出現在來華傳教的意大利方濟會士葉尊孝編寫的《漢字西譯》(Dictionnaire chinois-latin,亦稱《漢拉字典》)中。〔5〕關于葉尊孝(1648—1704年,漢語又名葉宗賢,本名通常拼寫為Basile de Gemona)的生平和《漢字西譯》的相關情況,可參見楊慧玲:《葉尊孝的〈漢字西譯〉與馬禮遜的〈漢英詞典〉》,載《辭書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5-142頁。《漢字西譯》大體編寫于1692—1701年,收入了包括“權”字在內的9000余漢字。而《漢字西譯》所依據的漢字字典,只能是明朝梅膺祚編纂的《字匯》和張自烈編纂的《正字通》,尤其是后者。《字匯》共14卷,收入3.3萬余字,其列舉的“權”字的第一個含義是“秤鐘”(即秤錘),然后是“經權”,再然后是“權柄”,其解說為:“權是稱權柄,是斧柄,居人上者所執,不可下移也。”〔6〕參見(明)梅膺祚編纂:《字匯》(六),木部,北京大學圖書館影印本,未標示頁碼。顯然,在“權柄”這個漢字組合中,“權”已被解說為刀斧,很形象,也很暴力。《正字通》共12卷,收入約3.35萬字,其中解釋“權”字給出的詞義依次是黃英、黃華木、反常、秤鐘、權衡、反經合道、權柄、權輿、權謀、權火(烽火)和姓氏。其中對使用秤錘做權衡,該字典寫道:“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得一端者也。圣人行權酌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于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這看起來像是針對現代法學意義上的權力說的,但其實最多是隱喻。對“權柄”,該字典的解說與《字匯》相同。〔7〕參見(明)張自烈編纂:《正字通》(五),辰集中,木部,北京大學圖書館影印本,頁碼數字已模糊不清。從《漢字西譯》內容的繼受版本《漢法拉大辭典》對“權”的解說看,〔8〕當年收藏在意大利的漢語—拉丁語字典《漢字西譯》后來被拿破侖時代的法國官方借去,由曾任法國駐廣州外交代表的小金德(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奉拿破侖之命編纂成《漢法拉大辭典》(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ais Et Latin),1813年以印刷本在巴黎出版。前者對古漢字權的解說是比較簡明到位的,其中與西文法學名詞直接掛鉤的正是“權”字中“權柄”那層含義。該大辭典對權這個漢字給出的多種拉丁文解釋中,靠前的含義分別是平衡點、平衡體的重量(poids d'une balance、librae seu bilancis pondus),權且、暫時(ad tempus habitare alicubi),靠后的含義有統治、權威(dominium、auctoritas)和授權(auctoritate,是拉丁文也是法文)。〔9〕Chrétien-Louis de Guignes, 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ais Et Latin, Press of the Imprimerie Impériale de Paris, 1813, p.324.拉丁詞中,統治、權威所對應的dominium、auctoritas與potestas、potentia是近義詞,后來auctoritas等轉變為英文authority,而potestas、potentia先轉變為法文pouvoir(權力),然后又轉變為英文power(權力)。所以,“權”字與相應含義拉丁文形成交流和對譯關系,是其后來在權力的意義上同法文、英文的相應名詞交流、對譯的語言學基礎。
“權”字歷史上第二次與西語的正式對接發生在1815年馬禮遜刊印的《華英字典》系列之首卷中,具體是同英文法學名詞authority(間接同power)的含義對接,并在多種對應含義中突出此種含義,乃是它走向廣闊法學空間的第二塊里程碑。馬禮遜的《華英字典》系列影響到自19世紀初年起幾乎整整一個世紀里在中國乃至東亞涉及漢語學習的歐美人,和涉及英語學習的中國人、日本人,包括后來的傳教士兼漢學家麥都思、丁韙良和羅存德等人。其中,1815年馬禮遜刊印的“字典”是《華英字典》三卷本系列中的第一本,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漢英字典。在這本字典中,“權”字尚未列入條目,但從其他關聯條目可見其中“權”字被確定為英文authority、power的對應漢語名詞的情形,且該字典將勢、權勢、威、官看作“權”的同義詞,因而也在不同場合用authority、power來解說這些對應的漢語名詞。如:“權出于一者強,權出于二者弱/Authority issuing from one, is powerful;authority issuing from two, is weak”“權行州里力折公侯/Authority felt through all the country, and efforts which make the nobles stoop”“勢/strength, authority, power”“有錢有勢/possessing wealth and power, or influence”“權勢/authority, power”“吾官益大,吾心益小/The greater my authority in the state, I study to be less ambitions”,等等。〔10〕Robert Morrison,“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Vol. I.-Part I.,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by P.P.Thoms, 1815, p.47, 118, 273, 611, 256. 直接引語省略了注音,后同。此外,該字典還以power作為對“力”的解釋之一,以及用power譯“威”,如“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were neither intimidated by power, nor seduced by gain”。〔11〕同前注〔10〕,Robert Morrison書, 第257頁,第852頁。綜上可見,這本《華英詞典》在“權”字的全部含義中,較明顯突出了它對應于power和authority的含義。
馬禮遜正式將“權”字列入詞目并系統列舉其對應的英文詞的時間和場合,是其1819年出版的《五車韻府》,這是《華英字典》系列的第二本。馬禮遜在這本字典的“序言”中說,此書是基于已故中國學者“陳先生”遺留給其門生“含一胡”〔12〕陳藎謨,明末清初重要的易學思想家與音韻學家,《皇極圖韻》和《元音統韻》為其聲韻學著作。馬禮遜所說的“含一胡”實際上是陳藎謨的學生胡邵瑛,“含一胡”應為“胡含一”。參見王榮波:《馬禮遜〈五車韻府〉的成書過程考證》,載《淮海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第47-50頁。的中文手稿編譯而成的,該手稿形成過程甚至得到過朝廷的關注。〔13〕See Robert Morrison, “五車韻府,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Vol. I.-Part II.,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by P.P. Thoms, 1819, preface.《五車韻府》對漢字“權”給出的全部對應英文詞依次首先是“power,authority”(權力,權限或權柄),然后是“temporary or peculiar circumstances,which like authority compels one to deviate from a regular course”(權變)和“hence”(權且),所舉的漢語例詞有從權、權臣、權詐、權衡、有權、權謀等,都給出了對應的英文詞語。〔14〕同上注,第449頁。直到1865年此書再版,它對“權”字的英文解釋都未更改過一個字母。〔15〕See Robert Morrison,“五 車 韻 府,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Vol. I.-a reprint of Part II., Shanghae: London Mission Press, 1865, p.593.
1822年,馬禮遜出版了歷史上第一部英漢字典,作為《華英字典》系列的第三本。該字典對authority、power等英語詞匯所做的漢語解說,從西方人的角度直接確立了它們同漢字“權”的對應、對等關系。這本字典對authority的唯一解釋是“權柄/absolute authority”,漢語例句為“自己的權柄,凡事可以在我作主”;漢英雙語例句為“authority derived and limited by law/受于人的權柄按法而行”“國柄在手/national authority was in his hand”。另外,對“possessing authority”這個短語,還給出了“有權、有權勢、有權柄”三組例詞。〔16〕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III.,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by P.P. Thoms, 1822, p.33.該英漢字典對power的解釋用了雙語:“command,authority/權、權柄、權勢”,隨后是“strength,force/能、力、強”,接著還將power解釋為“勢”和“威”,如“勢不能/not in my power”“畏威者眾/All persons stand in awe of power”,還有“乘方”,如“六乘方/sixth power”。另外,對隨后條目中唯一的相應形容詞powerful,它給出的例詞是“having great authority/大有權柄的”。〔17〕同上注,第330-331頁。幾年之后,馬禮遜編寫的方言字典,對“勢”也是比照“權”譯為power的,如將“恃勢行兇”譯為“to rely on one’s power and act cruelly”,將“有勢不可倚盡”譯為“having power don’t depend upon it to the utmost”。〔18〕Robert Morrison, “廣東省土話字彙,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Chinese and English”, Part III.,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by P.P. Thoms, 1828. 這部詞典未標注頁碼,而是按廣東話注音順序查詞或短語,此處兩引文按漢字注音順序分別排在CHANG-NAOU-LUY-TSUNE、SHEN-MOW-LUY頁眉下的相應頁碼。這兩個漢語短語中的“勢”,顯然是權勢一詞的簡寫。但是,在新的詞典中采用此譯法擴大和強化了power同權勢一詞的聯系,豐富了power的漢語表達形式。
在《康熙字典》和陳藎謨等中國學者手稿基礎上形成的馬禮遜《華英字典》系列的兩本漢英字典和一本英漢字典,從三個方面推進了權字以近現代法學概念為取向的演化:(1)《華英字典》基于權字在先秦、兩漢的全部含義,將其本義和較為接近本義的含義擺放到了最后,而將最初的漢語字典《爾雅》不納入解說范圍,其后的《說文解字》乃至《康熙字典》雖納入解說范圍但擺放在靠后位置的權柄、權勢含義,提升至最突出的第一、第二的序位。(2)這套字典對“權”字的英語解說和對authority,特別是對power的漢語解說,在照顧這些詞的內容涉及面的基礎上,系統地闡釋和包容了先秦、兩漢及其后以權柄、權勢為主要文字符號體現的公共強制力及其社會功能的內容。“權”字從此具有了一些傳統律學不甚看重,但中國現代法學很重視的含義,如它以公共機構、公共職位為主體,同公共強制力相聯系的特征等。(3)這套字典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首次實現了權字與英文power、authority在法學領域的對接,確認了前后兩者之間含義上的對應、對等關系。此前的漢語字典中權字包含的權勢、權柄內容,主要指客觀存在的強制力、影響力,沒有或少有合法、正當的含義,而19世紀上半葉英文法學著作中指稱法現象的power,尤其是其法學近義詞authority,有較強的合法、正當的意味,可區分于violence、force等單純指稱暴力的名詞。
繼馬禮遜的《華英字典》系列之后,19世紀上半葉其他西方傳教士、漢學家編寫的華英、英華字典也在不同序位上將權勢、權柄同power、authority放在對稱、含義對等的位置上互譯,形成了中英兩種文字所載內容融合在一起的新“權”字。19世紀30—40年代的英國傳教士兼漢學家麥都思的《華英字典》對權字含義的解說在含義排序上明顯區別于馬禮遜的《華英字典》系列,但其中與power、authority對應的內容沒有明顯變化。麥都思的《華英字典》先用英文將權字解說為:“a weight; to weigh; to weigh circumstance, and act according to”(砝碼;衡量;權衡情況然后據以采取行動——引者),接著用漢英雙語將其解說為“權勢/power, authority”,然后給出例詞如“弄權/to get the power into one’s own hands”,“從權/to act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等等,而“權柄/the handle of power,power”被擺放在最后。〔19〕W. H. Medhurst, A Dictionary of Hok-k?èn of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32, p.415.這種安排說明,麥都思的《華英字典》比較傾向于依照先秦兩漢和清初《康熙字典》的詞義先后順序來解說權字,不太認同像馬禮遜那樣突出權字包含的同power、authority對應的含義。從現代中文法學的立場回頭去看,當時麥都思字典的這種安排顯得過于保守,沒有把握住中西交流背景下權字含義演進和運用的后來趨勢。
另外,19世紀上半葉乃至更晚,當時出版的各種英漢字典對power、authority的漢語解說,都同前引馬禮遜的1822年字典的解說大同小異。麥都思的《華英字典》將authority依次用漢語解說為“權勢、權柄、威權、柄權”,然后用雙語給出例詞“possessed of authority/有權;to engross authority/弄權;the national authority was in his hand/國柄在手”“to authority/移權給人”等。〔20〕W. H. 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Vol. I.,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 1847, pp.90-91.該字典對power依次用雙語加單純漢語例詞的方式做了解說:“ability/能、才能、能干;strength/力、力量、氣力、勇力;an authority/權柄;influence/勢、權勢、德”等。另外還用雙語給出了例詞,如“the power of nation/國柄;to stand in awe of power/畏威”等。〔21〕W. H. 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Vol. II.,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 1848, p.987.美國另一傳教士、漢學家衛三畏的英華字典比較簡單,它給authority的漢語對應詞是“權能”,給power的漢語對應詞是“能,力、權、權勢”和“in his power/在掌握”。〔22〕S.W. Williams, “英華韻府歷階, English &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 Macao: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4, pp.10, 217.
1868年,中國學者鄺其照出版了《字典集成》(第三版改為《華英字典集成》),這部19世紀唯一由中國學者編寫的漢英字典給authority的中文解釋是“權、權柄票、管轄、體面”,相關的例詞主要有“the national authority is in his hand/國柄歸其掌握”“authorities/官”;給power的中文解釋是“能、才能、權柄、力量”,相關的例詞主要有“full power/全權”“great power/大權”“to have power/有權”等。〔23〕Kwong Ki Chiu, “華英字典集成, 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Shanghai: Wah Cheung; San Francisco: Wing Fung, reprinted in 1887, p.21, 257.其解釋的語言有特色,內容則與馬禮遜以來的字典一脈相承。
總體說來,至19世紀中葉,“權”字的含義形成了內承先秦兩漢,外接歐美的格局,其指稱范圍和內容已經十分接近現代中文法學意義的權力概念。在此前的漢語字典中,權勢、權柄只是“權”字包含的多種含義中序位靠后的、非核心的含義,但在19世紀上半葉的英華字典中變成了主要的甚至首要的含義,與英文法學power、authority的詞性和含義相對應。
二、“權”的含義覆蓋范圍從權力延展到權利
現代漢語中權字的含義覆蓋范圍,包括當代中國法律制度里的各種權力和權利,但本文對“權”字的考察表明,截至1839年《海國圖志》面世,此前中外刊印的所有出版物,包括《漢拉辭典》《漢法拉大辭典》和幾種漢英、英漢字典,“權”的含義都只能覆蓋權力,完全不能覆蓋現代中國法制中的任何權利。〔24〕古漢語字典的“權”字詞條列舉了其兩種用法共10種含義,“權力”是其中之一,沒有提到“權利”。參見《古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1293頁。從比較法學的角度觀之,這主要體現在“權”字那時還不包含、不能用于指稱由現代漢語“權利”一詞指稱的任何法現象,〔25〕參見《辭海》“權利”條目,上海辭書出版社2019年版,第3571頁。《辭海》的“權利”條目同本文結論部分概括的現代中文法學權利概念指代的法現象殊途同歸,即權利既無古典權字指稱的權勢、權柄含義,也不指稱當代中國憲法法律中的職權、權限等權力現象。后者在一國法律體系中通常以臣民、庶民、公民等個人為主體且體現其利益,由私人財產支撐。那么,“權”字從什么時候開始既指稱現代中文法學意義上的權力現象,又在同等意義上指稱權利現象呢?
或許有學者認為權字容納權利的含義是從丁韙良翻譯刊行《萬國公法》的1864年開始的。其實不然,“權利”一詞雖首先出自漢譯《萬國公法》,但權這個漢字指稱的對象覆蓋、接納權利的時間點早于1864年,應追溯到魏源《海國圖志》刊行的1839年。《海國圖志》中的漢譯《滑達爾各國律例》首次將國際法意義上的權利納入了權字的指稱對象,較大幅度地擴大了權字的指稱范圍。該“律例”中涉及“權”的譯文,主要集中在其中的第292“條”。受林則徐委托,由當時的美國傳教士兼醫生伯駕(Peter Parker)和清廷理藩院官員袁德輝分別翻譯的這個“律例”所依據的是法文原著還是其英文譯著、何年版本等具體信息,無詳細記載。有學者撰文考證過伯駕、袁德輝和譯文相關的情況,以及他們同馬禮遜《華英字典》的密切關系,猜測兩位譯者根據基蒂(Joseph Chitty)1844年出版的“滑達爾”著作的英文譯本翻譯的可能性很大,同時還指出了他們把注釋號誤譯為“章”,把頁碼數誤譯為“條”等業務瑕疵。〔26〕參見王維儉:《關于林則徐翻譯西方國際法著作考略》,載《中山大學學報(哲社版)》1985年第1期,第58-67頁。
為了較徹底地查清“權”字容納國際法意義上權利含義的過程,很有必要考察權字含義與《滑達爾各國律例》的具體關聯。根據前引相關論文的指引,可知“滑達爾”即18世紀瑞士國際法專家瓦特爾(Emer De Vattel),而“各國律例”即瓦特爾所著、出版于1758年的《國際法》一書。按這個線索查找,可見伯駕、袁德輝所譯“律例”中第292“條”的最終依據,主要是瓦特爾著作第2卷第1章的第4節,但同時包括同一章中第1—3節的部分內容。經比對可見,伯駕譯文中唯一提及權字的地方是包含“兵權”的這句話:“蓋打仗者,有公私之分,或兩國交戰,或二主相爭,所事皆出于公。而兵權亦出于公,此是也。私自兩人相敵,此是性理之常,此之謂也。”〔27〕(清)魏源:《海國圖志》百卷本,卷八十三,1876年平慶涇固道署重刊本,第18頁。但細讀原文,這句話并不全譯自第1章第4節,而是從第1—4節(§1—§4,其中前兩節分別僅有一句話)中概括出來的。對此,人們從提示這幾節的原文標題和涉及權字的名詞中可以看出來。〔28〕這四節的標題為:§1.Définition de la guerre(戰爭定義);§2.De la Guerre publique(公戰);§3.Du Droit de faire la guerre(開戰的權利);§4.Il n’appartient qu’a la puissance souveraine(只屬于主權者的最高權力)。See Emer De Vattel, Le droit des gens, ou Principes de la loi naturelle, appliqués à la conduite et aux affaires des Nations et des Souverains, Vol. 2., Londres: 1758, pp.1-3.伯駕的譯文中相關的名詞只有“兵權”一個孤例,但他顯然是用其中的權字來統稱相應的power(或法文pouvoir)和right(或法文droit)的。
將袁德輝所譯“律例”中與權字相關的句子同法文原文對照,可見盡管兩者只算大體對應,但有一點很清楚:即使袁德輝漢譯片段依據的不是法文原本,但他的譯文中確實有“權”字既同法文原著中的pouvoir(權力)相對應,同時在多數時候還有權字與法文原文中的droit(權利)相對應。現將袁德輝譯文中同權字有密切關系的句子援引如下,并把相對應的法文原文放在注釋中,供讀者對照:“兵者,是用武以伸吾之道理”,“如此惟國王有興兵的權,但各國例制不同,英吉利王有興兵講和的權,綏領王無有此權”。〔29〕(清)魏源:《海國圖志》卷八十三,第22頁;瓦特爾著作中與之對應的法文原文為:“La Nature ne donnant aux hommes le droit d’ufer de force que quand il leur devient néceffaire pour leur défenfe & pour la confervation de leurs droits”; “Les rois d’Angleterre,dont la pouvoir est à d’ailleurs li limité, ont le droit de faire la guerre(a) & la paix:Ceux de Suède l’ont perdue.”Emer De Vattel, Le droit des gens, p.2, 3.其中,前一句中“道理”,是袁德輝對la préservation de leurs droits(即“以伸吾之道理”或自衛的權利)一語中“droits”(權利)的漢譯;第二句話中,“綏領”指瑞典,“興兵的權”中“權”的原文是pouvoir(權力),而“興兵講和的權”(droit de faire la guerre et la paix)中“權”的原文是droit(權利)。袁德輝譯文中下面這句話的法文原文是對上句說到的君主“興兵”的權利(droit)做的一個注釋,但它同樣表明袁德輝的以上譯文中權字客觀上指稱著權利:“英吉利王無有巴厘滿衙門會議,亦不能動用錢糧,不能興兵,要巴厘滿同心協議始可。” 其中“巴厘滿”是議會一詞的音譯,“興兵”的原文是droit de faire la guerre(開戰的權利)。〔30〕同上注,魏源書,第22頁;同上注,Emer De Vattel書,第3頁。
對照瓦特爾《國際法》的英譯本看伯駕的譯文可見,盡管后者只是用漢語非常粗略地概括了英文相應部分的大意,但其中權字覆蓋權利(right)的狀況非常明顯。瓦特爾《國際法》的英譯本據說歷史上曾有過十多種,但現在能看到的主要是兩種:其一為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自由基金公司基于1797年英文版的編輯重印版,其二為1844年基蒂的英譯本。據前引論文作者考證,基蒂的《國際法》英譯本最可能是伯駕和袁德輝的譯文所直接依據的版本。翻開這個版本中同伯駕譯文對應的頁碼(第292頁),雖找不到與其譯文直接對應的段落,但從他們譯文概括的頁碼內容看,伯駕所說的“兵權”一詞所概括的對象顯然只能是這頁中的“使用武力的權利”(right to employ force)、“自衛的權利”(preservation of their rights)、“主權者的權力”(sovereign power)、“開戰的權力”(authority to make war)、“開戰和媾和的權利”(right of making war and peace)、“授權開戰”(authorized to make war),及“宣戰的權利”(the right of declaring war)。〔31〕Emer De Vattel, The Law of Nations, Or, 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Nature, Applied to the Conduct and Affairs of Nations and Sovereigns, An Edition by Joseph Chitty, T. & J.W.Johnson, Philadelphia: Law Booksellers, Ccessors to Nicklin & Johnson, 1844, p.292.可見,伯駕“兵權”之中的權字在含義上明顯同時覆蓋權利(right)和權力(power和authority)。
袁德輝的譯文的相關段落與英文文本的吻合度較伯駕的略高,因而其中權字在指稱對象上覆蓋權利的情況更明顯。他的譯文寫道:對臣民與外國人發生爭執奔回本國投告、稟求保護的做法,國王“先要審定虛實,有何怨的道理,或是應該興兵,或是應該不興兵,或是須要用兵,國中方才太平,悉聽國王裁奪。無此法度,何能一國太平?如此惟國王有興兵的權,但各國例制不同,英吉利王有興兵講和的權,綏領王無有此權”。〔32〕同前注〔29〕,魏源書,第22頁。袁德輝這段譯文,實際上也主要是概述英文原著第292頁中第一自然段及其中一個注釋(137)的大意。筆者手工統計,英文原本第292頁正文加注釋共含16個right(權利),6個power(權力),3個authority(權限)和1個authorise(授權),這全部共26個表述“權”的英文詞在袁德輝的譯文中只粗略地反映為1個“道理”和3個“權”字。〔33〕同前注〔31〕,Emer De Vattel書,第292頁。所以,袁德輝在承繼馬禮遜《華英字典》系列開創的用權字翻譯power、authority的傳統做法的同時,他選用權字翻譯right的次數更多、更清晰。
從現代中文法學的角度歷史地看,伯駕和袁德輝開始用在法學領域原本僅僅指稱權力(power、authority)現象的權字來翻譯right,實際上是將“權”字的表意和指稱范圍擴大到了權利。此舉大幅度突破了先秦兩漢以來中國社會所賦予、迄那時為止的中文字典和漢英、英漢字典所記載的權字含義和權字指稱的現象的范圍,在創造包含權力、權利兩重含義的新“權”字的法學進程中邁出了一大步。走出這一大步表明,“權”字與西文法學名詞right和droit的結合,在“權”字本體中孕育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內容:體現個人利益及相應私人財產內容的元素符號已經融入其中并開始成長,恰似動物母體中的胚胎。當它成熟并從母體中分娩出來的時候,就是現代中文法學所稱的“權利”。
Right(權利)是近現代英文法學的基礎性概念,它在19世紀指稱的現象如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政治權利和自由等,已經成為那個時代歐美主流國家社會生活的基礎性內容。所以,只要中西方有接觸和交流,中國社會就不能不在觀念和文化上對rights體現的現實乃至對應的表意符號做出正面回應。將權字的表意范圍從漢語的權勢、權柄擴大到西文法學名詞right、droit指稱的現象,是中國社會在語言文字方面回應上述歷史性挑戰的種種表現中的一部分。
“權”字含義在《海國圖志》中的突破有積極意義,但局限性也比較明顯。近現代法學或法律體系中的權利,可分為以庶人、凡人、臣民、公民等個人為基本主體的人身、財產、言論出版和選舉等基本權利,及以國家為基本主體的國際法意義上的權利,前者是權利概念指稱對象的本來部分,后者實際上處在另一種體系。前引《海國圖志》第83卷中權字含義范圍覆蓋下的“right”只是國際法領域的權利的一部分。《海國圖志》刊行后,在將英文法學的right(權利)進一步納入權字含義覆蓋范圍并把相應做法推向中國和日本社會方面,丁韙良和他漢譯的《萬國公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丁韙良所譯《萬國公法》的英文原本,是美國國際法教授惠頓的兩卷本《國際法原理》,其正文有623頁,漢譯《萬國公法》只不過是原書的一個逐章展開的簡寫本。將該書英文原文轉換為可供電腦分析的文本后,可統計到原書使用power 470次,使用authority 101次,共571次;使用right 937次(作為right表現形式的liberty 16次、freedom 23次不算在內);以上總共1508次。〔34〕依據的文本:Henry 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wo Volumes, London: B. Fellowes, Ludgate Street, 1836.用同樣方法對丁韙良漢譯本《萬國公法》做統計,手工排除點校添加因素,統計到該書單獨使用權字944次,使用權利83次,總共1027次。〔35〕依據的文本:[美]惠頓:《萬國公法》,[美]丁韙良譯,何勤華點校,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對比《萬國公法》和其所譯的英文原著可以看到,由于漢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省略了占比較大的篇幅及不譯、意譯等原因,原著中有480多個可以或應該譯為權或權利的對應英文詞未被譯成漢語。實際上power、authority只要被譯出,基本上都是譯為權,無一被譯為權利。在獲譯為漢語的全部right中,絕大部分也都被譯為權,只有占比很小的一部分right被譯成了權利。將power(還有authority,下同)和right都譯為權,可能同英語歷史上形成的,現已趨于衰落的,對power和right有時不嚴格區分的傳統有一定關系。這種傳統在那時英語中的典型表現,是既區分right和power,但時而又不嚴格區分,在表意需要一個既可指稱right又可指稱某些表述power的名詞,而實際又缺乏這樣一個名詞的背景下,往往權宜地使用right一詞來替代之。這種狀況在英文字典上的反映,是某些power被列入了right的若干個含義之一。如18世紀風靡大西洋兩岸的一部通用英語詞典,在其將right作為名詞列舉的各種含義中,排在其中稍靠后位置的就有一個“power;prerogative”(權力;特權)。〔36〕Samuel Johnson,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Volume 2, London: Printed for A. Millar, 1766, RIG.此字典未編頁碼,條目按讀音拉丁字母順序排列。
漢譯《萬國公法》刊行對“權”字的影響,首先表現為沿用和鞏固了《海國圖志》開創的先例,將英文法學的right(權利)大量而且常態性地納入“權”字含義的覆蓋領域,成倍地擴大了“權”字的指稱范圍和蘊含的內容。新“權”字形成的主要法文化意義在于:體現中國傳統的權字同來自西文法學并與其對應的power、authority(或pouvoir)以及牽連其中的right(或droit)碰撞交流,促使“權”字不僅在指稱范圍和內容上超越了自己的歷史,也初步顯示出同時超越任何相關的西文名詞,形成一個全新中文法學基礎性概念的可能的前景。因為,從古希臘文、拉丁文到現代歐美語言,其中沒有任何一種語言的相關名詞在形體上獨立于指稱英文法學的power(包括authority,下同)、right而又能同時包括power、right兩重含義。雖然,英文等西語有廣義的權利的說法,但它畢竟只是對同一個文字符號(right)的多種解釋之一,并沒有形體獨立于被解釋對象的另外的文字符號或獨立概念。
漢譯《萬國公法》刊行對“權”字的另一顯著影響,是在“權”字原來權勢、權柄含義和英文法學的power一詞含義融合的基礎上,開始將英文法學right的核心部分即“庶民”“凡人”的權利納入了“權”字指稱的范圍。國際法基本主體的權利,只是在法學體系上屬于權利的范圍,若轉換到國內法角度看,它們一般而言屬于權力的范疇,表現為國家機關及代表它們的官員的職權或權限等,因而并非現代法學一般意義上的權利。《海國圖志》涉及的權利和《萬國公法》涉及的大多數權利,屬于國際法意義上的權利。但是,《萬國公法》在主要討論國際法意義的權利的同時,也論及了范圍較廣泛的國內法意義上的權利,如臣民、個人的民事權利、訴訟權利〔37〕如第2卷第2章“論制定律法之權”、第4章“論各國掌物之權”論及的權利。同前注〔35〕,惠頓書,第78-123頁,第131-138頁。和臣民、個人享有這些權利時不可能不享有的人身權利等,而且還如下文將要展示的,實實在在使用的“權利”一詞。接納這部分權利后,“權”字在指稱對象和內容上就覆蓋了全部權利現象中的基礎性部分。對“權”字指稱的范圍和包含的內容來說,這是一個根本性變化。
顯然,“權”字不僅被用于指稱現代法學意義的權力,而且用于指稱現代法學的權利,是自1839年刊行《海國圖志》時無意間啟動,1864年漢譯《萬國公法》刊行時大規模展開并有了初步結果的一個法文化發展進程。現代法學研究“權”字的起源和含義變遷,直接目的之一是系統、深入地認識“權”字在不同歷史時期指稱的法現象,把現代中文法學對這些現象的認識提升到法學基礎性概念的水平。比照這一要求,可見19世紀中葉“權”字的指稱范圍還不明確、沒有相對穩定下來,而權力和權利的內容雖已在“權”字的包容中,但它們自己獨立的語言載體即后來的權利、權力兩個漢語名詞還沒有形成。盡管漢譯《萬國公法》已經第一次開始使用近現代意義的權利一詞,但那只能算權利概念的萌芽,因為它的范圍和內容都還不甚明確,更沒有完成一個漢語名詞成為法學概念所必須經歷的社會化過程。所以,“權”在當時的指稱范圍和內容都還十分模糊,尚未具備形成現代中文法學概念的基本條件。
三、19世紀中葉以來“權”字含義的演進
按本質主義法學的要求,〔38〕本質主義法學是與經驗主義法學相對稱的,前者強調通過抽象力,通過把握現象后面決定該現象之所以是該現象而不是其他現象的根本特征的方法來認識該現象本身,后者強調通過感官自覺,通過感知現象本身來認識現象。一個法學概念,起碼要能夠反映相關法現象的外延和實質。按這個標準衡量,19世紀中葉使用的“權”字,如以《萬國公法》中的權為標本,僅僅從外延看也還處在走向法學概念的旅程中。從截至 2020年的法學研究成果看,“權”作為中文法學的一個基礎性概念,其外延包括三個部分:(1)權力,主要表現為公共機關享有的職權、權限、公職特權、公職豁免等;(2)權利,其表現形式可分為自然人和法人的權利、自由、個人特權、個人豁免等;〔39〕若考慮國際法,還有國家作為國際法主體的權利,但實際上國際法主體的權利應該在另一套話語體系中討論。(3)剩余權,即法外之權的概念化表述,包括但不限于道德權利、道德權力等。以《萬國公法》為例,其中的“權”字雖指稱權力,但涉及的權力形式還不具體、不充分,難以窺全貌;其中的“權”字雖已開始較廣泛地指稱權利,但涉及的具體對象顯得很有限,同時還因為與使用“權利”一詞指稱的那些現象界限不明而多有混淆。至于“權”字后來指稱的剩余權(即包括道德權利、道德權力在內的各種法外之權,后同),在19世紀中葉乃至之后很長時間,中文法學對之都缺乏認識和論述。所以,作為現代中文法學概念“權”的三個構成要素,較早得到研究的實際上是法權利和法權力(法字通常省略),也可以說實際上是作為二者統一體的法權。所以,也可以說權概念的外延是法權和剩余權。
基于現代中文法學的認識水準觀察19世紀的最后30年,那時的“權”至少還需要走完下列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行程,才能成為合格的法學概念:權力、權利、剩余權三者都獲得充分的展示;彼此間范圍大體清晰,擁有相應名詞作為各自獨立的文字載體;它們三者與權字的指稱范圍形成明顯、穩定的區別;對于權的實質,做過必要討論或論證,至少有初步的、言之成理的結論。
根據上述標準,雖然早在19世紀60年代中期“權”字已明確包含權力、權利,但其顯然還須完成幾個必要的認識過程才能成為現代意義的中文法學概念。其中須經歷的首要過程是權利、權力和剩余權先后從權字母體中分解出來,成為含義確定的名詞或概念。實際上,從權字母體中率先分解出來的是“權利”。1864年刊行的《萬國公法》的漢譯者丁韙良在“權”字后加一利字,形成了“權利”一詞,實現了將指稱“凡人理所應得之分”的“庶人本有之權利”從權字中分離出來的目標。此后,隨著1865年《萬國公法》引進日本,權利一詞在中日兩國上層知識分子中獲得了較廣泛的傳播,權利概念、權利觀念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中文法學中得以確立。〔40〕參見童之偉:《中文法學中的“權利”概念 起源、傳播和外延》,載《中外法學》2021年第5期,第1246-1251頁。
繼權利之后,從“權”字中完全分化出來的是權力一詞。本來,馬禮遜《華英字典》系列的第一本漢英字典中已經出現過直接與英文法學名詞authority、間接與其同義詞power對應的“權力”一詞,〔41〕同前注〔10〕,Robert Morrison書,第118頁。其中“Hēě”是俠字的注音。但這個近現代意義的“權力”是在一個解說“俠”字含義的例句中出現的,因而此后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關注。直到日本著名學者加藤弘之1874年才在其出版的著作中率先以較高頻率使用“權力”,〔42〕[日]加藤弘之:《國體新論》,東京谷山樓1874年版,第15、16、17、22、26頁,共8次出現“權力”,“權限”也出現在第16頁。稍后箕作麟祥和福澤諭吉也隨之開始日常化地使用“權力”。近現代法學意義的權力一詞在日本通行后,19世紀70年代末已在日本做外交官的黃遵憲和1898年秋開始在日本流亡的梁啟超等中國學者注意到了這一點。事實上,黃遵憲是在現代法學意義上率先使用“權力”的中國學者。〔43〕參見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三十刑法志四,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1898年版,第744頁。梁啟超于1906年初在《新民叢報》上發表《開明專制論》,集中闡述了“權力”的社會功能、存在的必要性和產生的社會根源,此文使“權力”一詞得以從此在中文法學領域扎根生長。〔44〕梁啟超:《開明專制論》,載《飲冰室合集·文集》第6冊,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1504-1509頁。
到19世紀末,在權利、權力先后從“權”字中誕出后,“權”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獨立于權利、權力但指稱范圍同時包括權利、權力含義的中文法學名詞。所以,權既能指稱權利,也能指稱權力,還能指稱權利權力統一體(即后來證成的法權),而具體所指則取決于上下文。“權”的這種全新的含義和使用方法,歷史上主要是由黃遵憲、梁啟超的著作率先體現和完成的。黃遵憲寫道:“上有所偏重,則分權于下以輕之”,“余聞泰西人好論權限二字,今讀西人法律諸書,見其反覆推闡,亦不外所謂權限者。人無論尊卑,事無論大小,悉予之權以使之無抑,復立之限以使之無縱,胥全國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之中,舉所謂正名定分,息爭弭患,一以法行之”,“權字為泰西通語,謂分所當為、力所能為、出于自主、莫能遏抑者也”。〔45〕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二十七刑法志一,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1898年版,第684、686頁。從生平和著作看,黃遵憲應該是通過日文而不是直接閱讀西文“法律諸書”的,因此,他用“余聞”來描述“泰西人好論權限二字”,“權字為泰西通語”應該也是由“聞”聽得知,極可能有一些因不能直接閱讀西文而形成的誤解。例如,那個時代中日文法學的“權限”,都只是對英文authority這一個“字”而非“二字”的翻譯。而且,從古希臘文、拉丁文到近現代歐美文字,都沒有黃氏理解的那種似乎能同時指稱權利、權力兩種法現象的“權字”。可用一個字和名詞同時指稱權利、權力乃至剩余權,是中文法學(某種程度還有日文法學)相對于西文法學的獨特優勢。
但是,上述情況并不妨礙我們結合梁啟超使用“權”字的方式梳理黃遵憲運用“權”字遵循的規則,它們同時也應該是日文使用“權”字的規則:(1)在權利的意義上使用“權”字。如前引“私訴之權”中的權字,還有黃氏在介紹剝奪“公權”和公權包括的具體范圍時使用的一系列“權”,大都是權利的意思:“國民特權”“就官之權”“編入兵籍之權”“在審廷為證人之權”“為破產者之管理人或管理會社,及管理共有財產之權”和“為學校長、教官、學監之權”等。〔46〕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三十刑法志四,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1898年版,第746頁。(2)在權力的意義上使用“權”字。如“廢刑大赦,雖殺公訴之權,不得消私訴之權”,〔47〕同上注,第687頁。其中“公訴之權”中的“權”是權力,“私訴之權”屬權利。不過,在黃遵憲這本書中,單指權力的權字出現得比較少。但梁啟超在1899年及其后的文章中,權力意義上的“權”,使用的數量很大,如“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審判之權”“政務之權”等。〔48〕參見梁啟超:《各國憲法異同論》,載《飲冰室合集·文集》第2冊,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353-361頁。(3)在權利權力統一體(或法權)意義上使用“權”字。如前引黃遵憲話語中的“分權”“悉予之權”和“為泰西通語”之“權字”中的“權”,都可以合乎邏輯地理解和解釋為權利權力合一意義上的“權”:拿分權來說,可以是個人與國家、國家機關之間分權(權利權力統一體即法權意義上的“權”),也可以是不同國家機關之間分權(權力)和不同個人之間分權(權利)。梁啟超在用“權”字分別指稱權利、權力的同時,也多有在權利權力統一體即法權意義上使用權字的情況,如他在1902年的相關文章中寫道:“嗚呼,荀卿有治人無治法一言,誤盡天下,遂使吾中華數千年,國為無法之國,民為無法之民,并立法部而無之。而其權之何屬,更靡論也”,〔49〕梁啟超:《論立法權》,載《飲冰室合集·文集》第4冊,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853頁。“文明之國家,無一人可以肆焉者,民也如是,君也如是,少數也如是,多數也如是。何也?人各有權,權各有限也。權限云者,所以限人不使濫用其自由也”。〔50〕梁啟超:《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載《飲冰室合集·文集》第4冊,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862頁。這前后兩段引文中的“權”,從上下文看都可理解為權利權力統一體或法權。實際上,權既然能單獨指稱權利和權力,在邏輯上它就一定同時包含著權利、權力兩重含義。
“權”既分別指稱權利、權力而又作為同時指稱二者的名詞單獨使用的規則,在20世紀20年代得到了進一步鞏固。那時一本有影響的法理學著作目錄中出現了“權、權利、權力和權限的用語”的節標題,其中的“權”顯然是作為與權利、權力并列的法學名詞使用的。作者在該標題下對“權”及其在法學中的用法做了簡要概括:“普通用這個‘權’字,包括極廣:獨立權、平等權……都是‘權’;用在國家對于國家(國際):統治權、刑罰權……也都是‘權’;用在國家對于國民:自由權、參政權、訴訟權……也都是‘權’;用在國民對于國家:人身權、財產權……也都是‘權’;用在人和人之間——‘權’的用法大概如此。由此看來,‘權’字用在什么地方都行,可以包括一切的權利與權力。”〔51〕楊廣譽:《法學大綱》,北京擷華書局1924年版,第143頁。這段話可以視為對黃遵憲、梁啟超完成的“權”一詞的使用范圍的總結。
可以說,到20世紀20年代,“權”的含義和用法在法學中已實現了階段性定型,即進入了權字向現代法學概念過渡的、可用權利權力統一體即“法權”來對其加以表述的中文法學發展階段。此階段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權”實際上要么指法權利,要么指法權力(法字通常省略),范圍還不包括剩余權的具體表現形式,如法外權利、法外權力等。因此,那個時代的“權”,還不具有21世紀20年代中文法學之“權”概念外延包含“法權利+法權力+剩余權”總共三要素的特征。
“權”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發展成一個成熟的中文法學概念的基本標志之一,是它的外延或指稱范圍穩定地納入了剩余權的各種表現形式,其中既包括漢譯西文法學著作所稱的道德權利、道德權力等法外之權,也包括我國學者論述的“應有權利”“社會權力”的法外部分。〔52〕關于“應有權利”,參見李步云:《論人權的三種存在形態》,載《法學研究》1991年第4期,第13-17頁;“社會權力”指“社會主體以其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對社會的支配力”,郭道暉:《論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5年第2期,第22頁。與中文法學比較,西文法學關注和討論到剩余權構成要素的時間要早許多,盡管他們使用的往往是moral right(道德權利)和moral power(道德權力)等倫理學術語。〔53〕英文moral right自由在法理學、倫理學上指道德權利,但在知識產權法學上指的是精神權利。英語世界常在后一種意義上使用moral right,較少在前一種意義上使用該詞組。至于moral power,則極少使用。“道德權利”這個詞的西文的起源或許可追尋到古希臘、古羅馬,但限于本文的主旨,本文的觸角基本只限于其譯為漢語的部分或直接涉及其起源的西文部分。現在能確切知道的是,在19世紀中葉的英國,法律學者邊沁已將啟蒙時代自然法學派所主張的自然權利視為一種法外的、道德意義上的權利并強烈否定之。邊沁認為:只有那些由政府確立和實施的權利,才具有確定的和可理解的意義,自然權利、不可剝奪的權利,都是簡單和夸張的胡說八道;所謂道德權利和自然權利,都是鼓勵內亂、不服從和抵制法律的有害虛構,是反對現政府的造反謬論。〔54〕See George H. Smith, Jeremy Bentham’s Attack on Natural Rights, ibertarianism.org/publications/essays/excursions/jeremybenthams-attack-natural-rights (26 June 2012).但什么是權利,權利與法律的關系是怎樣的呢?邊沁說:“權利是法律之果,而且僅僅是法律之果。沒有法律就沒有權利——沒有違反法律的權利,也沒有法律出現之前的權利。在法律出現之前,可能存在希望權利出現的理由——無疑這些理由不可能缺乏,而且是最強烈的那種理由——但我們希望擁有權利的理由并不構成權利。將我們希望擁有權利的理由的存在與權利本身的存在混為一談,就是將需求的存在與解決需求問題的手段混為一談。這就像是在說,每個人都會陷入饑餓,因此每個人都有吃的東西。”〔55〕Jeremy Bentham, John Bowring,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Volume III,Edinburgh, W. Tait, 107, Princes Street; London:Simpkin, Marshall, & Co., 1843, p.221.不過,在其他法學者看來,邊沁似乎只是在強辯,因為,自然權利、道德權利不過是學者們為討論相關問題方便起見,比照法權利提出的一種學理概念。因此,此前、此后和當時,都沒有誰將其比照法權利尋求司法或行政保護或予以實施,沒必要將其作為法權利批判否定一通。
不過,同樣在19世紀中葉的英國,另外一些法學者,如約翰·密爾,是承認與法權利相對稱但與道德義務相關聯的道德權利的存在并對它有所論述的。約翰·密爾說:“當一項法律被認為是非正義時,它似乎總是被認為與違反法律是非正義的情形一樣,即侵犯某人的權利; 由于在這種情況下它不能成為合法權利,因此獲得了不同的說法,稱為道德權利。”〔56〕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Parker, Son & Bourn, West Strand, 1863, p.65.他還說,“某人與道德義務相關的權利,構成了正義、慷慨或仁慈之間的具體區別。正義意味著某些事情不僅可以做,是對的,或不可以做,是錯的,而且某人可以向我們聲稱這是他的道德權利”,“沒有人擁有要求我們慷慨或仁慈的道德權利,因為我們并沒有對任何特定個人實踐這些美德的道德義務”。〔57〕同上注,第73頁。
對道德權利的以上討論,在19世紀的歐美法學界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但那時及之后的一段時期研究道德義務的多,研究道德權利的少。人們較多關注道德權利似乎是20世紀下半葉后的事情。就筆者個人有限的閱讀而言,近50年來英文法學這方面研究頗引人注目的是美國的卡爾·威爾曼,他從20世紀70年代初起的半個世紀中,發表了一列討論權利問題的著作,其中大都或多或少涉及道德權利,其中有些已有漢譯本并影響了中文法學。威爾曼的著作結合自然權利學說、美國國內法和國際人權約法討論了包括安樂死在內的各種道德權利與法權利關系的主要方面。〔58〕卡爾·威爾曼(Carl Wellma)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Theory of Rights: Persons Under Laws, Institutions, and Morals, Rowman& Allanheld, 1985; Real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Medical Law and Moral Rights, Springer, 2005; The Moral Dimensions of Human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The Proliferation Of Rights: Moral Progress Or Empty Rhetoric?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其中,他的部分著作已有漢譯本,如《真正的權利》,劉作翔等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人權的道德維度》,肖君擁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此外,自邊沁開始,討論動物“權利”的聲音早就不時有之,近些年更有專著將動物“權利”納入了道德權利范圍。〔59〕See Mylan Engel Jr. and Gary L. Comstock, The Moral Rights of Animals, New York:Lexington Books, 2016.
從現代中文法學“權”的角度看外文法學的討論,有一種現象十分明顯:西文法學歷來所討論的剩余權,往往主要涉及其中的道德權利等法外權利,較少關注道德權力等法外權力。筆者花了很大力氣,才在西文法學圈中發現有學者就國家宣稱“擁有使公民接受服從義務的道德權力”展開討論的主題。〔60〕See William A. Edmundson, Political Authority, Moral Powers and the Intrinsic Value of Obedience,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ume 30, Issue 1, 2010, p.179.
參照以上情況,回過頭看中國20世紀20年代甚至整個20世紀上半葉包括漢譯外文論著在內的中文法學出版物,我們不難發現,這階段的中文法學除偶爾提及自然權利的內容外,幾乎沒有結合“權”字從學理上討論過剩余權,不論是“道德權利”還是“道德權力”或其他法外之權,甚至也沒有翻譯引進西文法學(如英文法學)在道德權利意義上使用的moral right一詞。〔61〕筆者做出這個判斷,是以比較詳細地閱讀、核查了下列三類學者的法學論著為基礎的:20世紀上半葉出版的磯谷幸次郎、奧田義人、 織田萬、岡田朝太郎、玉川次、 梅謙次郎、穗積重遠、美濃部達吉、G.拉德布魯赫、凱爾遜、龐德等日本和歐美法學家的漢譯法理學著作;可找到的福澤諭吉、箕作麟祥、加藤弘之等日本學者部分相關論著的中日文對照本;從1908年到1947年,楊廷棟、 孟森、潘大道、楊廣譽、夏勤、郁嶷、陶希圣、李景禧、吳經熊、張映南、丘漢平、朱采真、歐陽谿、何任清等中國學者所著之法理學著作。這就是說,整個20世紀上半葉,中文法學的“權”實際上停留在權利、權力或它們的統一體法權的認識水平上。
區分“權”與權利、權力和法權,是中文法學將剩余權的各種表現納入視野之后形成的法學進步,而這個過程總體看來是在時間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后明顯起步,到21世紀10年代完成的。這階段,一方面,“道德權利”“道德權力”等依法外規則確認的各種“權”循翻譯引進外文法學著作的管道被納入了中文法學的視野。同時中國學者也以自己特有的話語獨立地展開了法外之權研究,這些話語包括前述“社會權力”“應有權利”“法外之權” 和“剩余權”等提法。〔62〕關于剩余權,可詳見童之偉:《論法學的核心范疇與基本范疇》,載《法學》1999年第6期,第8-9頁。筆者以為,這些提法都反映了中國法律學者對剩余權的獨到認識。對于各種剩余權,我國法學界過去只在研究論文中討論到,基礎性法學教材通常不提及,但這種情況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和其后有了顯著改觀。如一本發行到第四版,使用30多年,在全國很有代表性的法理學教材寫道:“在論述權利含義時,還應注意這是指什么意義上的權利。一般地說,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會接觸到幾種不同意義的權利。例如,法律、道德和宗教意義上的權利;習慣上的權利;非國家組織規章中所規定的本組織成員的權利(如政黨黨員的權利、工會會員的權利)等。這些不同類的權利,既然都是權利,自然有共同點,但卻各有不同點。”〔63〕沈宗靈主編:《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頁。實際上,在當代,剩余權存在形式是現實而多樣的,它們與法權力、法權利的邊界和關系,是法律生活實踐和法學理論研究都應該認真對待的重要問題。
上述情況表明,由于剩余權經常性地進入中文法學視野,“權”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終于穩定地包含了三重含義:法權利(簡稱權利)、法權力(簡稱權力)和剩余權。這些發展為“權”成為一個中文法學概念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和學理基礎。由于權與權利、權力、剩余權和法權概念一起,構成全面、準確反映一國或一社會全部利益、全部財產不可缺少的思維形式,因而也成為中文法學的基礎性范疇之一。
四、結論
“權”字在中國已存在差不多3000年了,同時也是當代中國法學界從書面到口語使用最廣泛的少數幾個名詞之一,但它在漢語學術層面和中文法學領域獲得的承認,都有不同程度地與其在社會實踐中的實際地位脫節的問題。在漢語學術層面,《現代漢語詞典》“權”字詞條列舉了“權”的8種含義,其中第3種是“權力”,第4種是“權利”;《辭海》“權”字詞條列舉了“權”的13種含義,其中第4種是“權力”,第5種是“權利”。〔64〕《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130頁;《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9年版,第3570頁。從中文書面表達傳統和例句看,當今有代表性的這兩部漢語詞典中的“權”字,都表現為一個多義名詞,有時可指權力,有時可指權利,但更多的場合是其他含義。在具體場合“權”到底何所指,需視上下文而定。而且,這類字典、辭書列舉的權力、權利,內容都是法權利、法權力,無涉剩余權,也未做法權與剩余權的區分,因而它們實際上不包括剩余權包括的任何法外之權含義,但剩余權是實實在在的,也是中文法學界已經普遍承認的。尤其是,人們從這兩部辭書對“權”的解說中,看不出權力與權利的任何聯系。如“權”字到底是只能時而指權力,時而指權利,時而指其他被稱為權的東西的名詞,還是一個既可籠統指稱它們,又能分別指稱其中任何一種或兩種構成要素的名詞?這些都不確定。
在這個大的漢語言環境下,“權”在法學中的地位很尷尬:一方面,憲法法律、法學論著、法律生活中大量使用名詞“權”,如 “財產權”“審判權”“你有權”“我有權”和“他有權”等詞語中的“權”,法律上時而指權利,時而指權力,社會生活中除指法權外,還指道德權利、道德權力、應有權利等剩余權;但另一方面,對于什么是“權”,數十年來法學界極少有人設法把它說清楚,以至于讀者能見到的所有中文法學辭書都不將“權”視為一個法學名詞,更不用說當作法學概念了。《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收入的詞條少,不收入“權”不奇怪,但《法學大辭典》450多萬字,11卷本的《中華法學大辭典》全書2000多萬字,它們何以也都沒有將“權”作為詞條收入并用幾百或數十字予以定義、解說,值得深思。〔65〕參見《法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版;《中華法學大辭典》11卷本(原本10卷,后訴訟法增加了“增補本”),1995-2001年陸續出齊。法學辭書不收入使用范圍如此廣泛的名詞“權”,原因何在?筆者以為,“權”沒有收入詞條的主要原因,應該歸因于在編寫那些辭書的年代及此前,無人對“權”做專題研究,以致“權”的指稱范圍一直不明確,并因此而無法確定其實質。其次,法學界對“權”字指稱或可指稱的現象已經發生的變化沒有予以及時關注、研究,學術從而滯后于法律生活和社會生活實際。
到21世紀20年代之今日,回顧歷史,尤其是17世紀末以來“權”與外文法學名詞在中文法學領域接觸互譯的歷史,直面“權”指稱的社會現象的范圍變化和中外文法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并展望其學術前景,筆者提出下面幾點總結性看法。
1.“權”是一個從整體上表述權力、權利和剩余權及它們體現的全部利益內容、財產內容的法學范疇。作為現代法學概念,“權”之外延和實質都是清楚的,在20—21世紀之交的前后20多年中已獲得了必要的論證。“權”的外延包括三部分:(1)各種權力,即法權力,如我國憲法法律上稱為權力、職權、權限、公權力的現象,還有憲法法律上沒有名稱,但實際上屬權力的表現形式的公職特權和公職豁免。權力是公共利益和公共機關所有之財產的法律表現。(2)各種權利,即法權利,如憲法、法律上稱為權利、自由的現象,還有法律上沒有名稱但實際上屬權利具體表現形式的合法個人特權(如基于考取的證照獲得的特定從業資格)、個人豁免現象。權利是個人利益和私有財產的法律表現。(3)各種剩余權,即前文有所論述的各種法外權利、法外權力,等等。剩余權是法外利益和歸屬未定財產在社會生活中的表現,也是學者對其所做的一種學理描述。權的實質是由其構成要素的實質決定的。因此,可以說權的實質或內容,即一定國家或社會的全部利益和與之相對應的全部財產。更具體地說,“權”有兩級實質:一級是一定社會或國家的全部利益,包括法律承認、保護的利益和法律未承認、不保護的利益;更深層次的實質,則是一定社會或國家的歸屬已定和歸屬未定財產之和,即現有全部財產。
法學基礎性概念是著眼于其指稱的現象的范圍及其體現的利益、財產內容的重要性認定的,它們不同于中文法學基本概念,但構成其主體。“權”的概念指稱和反映的對象在法律生活中的重要性決定了“權”在法學學科必然處于基礎性范疇之一的地位。作為中文法學基礎性概念,“權”的外延和實質到21世紀10年代即已十分清楚、確定,如果說還有不盡完美的地方,那就是用“權”這個單字名詞做其漢語載體顯得有些生硬。漢語的學術名詞和學科概念,習慣上通常采兩字或三字名詞,用一字名詞的情形雖然有(如“法”),但人們往往會感覺不太自然、不容易接受。此外,由于權的含義為漢字所獨有,西文沒有對應的名詞,故只能將其譯為quan。不過,并不是任何權字都譯為quan,是在權泛指“權利+權力+法外權利(或法外權力)”時才必須譯為quan,在其他情況下應該根據其實際所指,分別譯為right或power 等,如果所用是英文的話。
2.作為當代中文法學的基礎性概念,“權”的外延或含義是其歷經三個歷史發展階段后形成和穩定下來的。如前所述,從先秦到明末清初,“權”字形成了記載在《康熙字典》中的11種含義,其中與現代中文法學相聯系的唯一含義“權柄”排序第5。“權”字向近現代中文法學基礎性概念運動的第一個歷史階段中,原初的和關鍵的一步,是其中的“權柄”含義先與對應的拉丁文、法文法學名詞發生聯通和互譯,進而與相應英文法學名詞發生聯通和互譯,形成了近現代中文法學的“權力”含義。這一歷史階段大致起始于葉尊孝手抄本《漢字西譯》編纂完成的1692—1701年,完成于馬禮遜《華英字典》系列印刷出版的1815—1823年。在這個階段,通過與相關西文的接觸,古漢語中“權”字中的權柄含義與西文中含義對應的法學名詞相交形成了“權”字中近現代法學“權力”概念的最初胚芽。具體說來,這表現為“權”同前述拉丁文dominium、auctoritas、potestas及由其直接或間接轉化而來的法文pouvoir和英文power、authority的互譯和含義對接,使得“權”字吸納了這些西文法學名詞的內容。古漢字“權”的多種含義中與近現代法學意義上的權力最接近的是權柄、權勢。在“權”字與這些西文法學名詞的互譯過程中,“權”的含義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有了合法公共權力的意味,而且這層含義在權字多種含義中的詞典序位也有所升高。這一過程刷新了“權”的古典含義。
第二個歷史階段大體起始于1839年《海國圖志》、1864年漢譯《萬國公法》的刊行,完成于19世紀末的中國和日本。這階段的新進展是“權利”在權字中孕育成長起來并獲得了中日兩國法政知識階層的認知和承認。這一過程再次刷新了“權”字的含義,使其指稱范圍在權力的基礎上延伸到權利并囊括了權利,范圍實際上已等同于權利權力統一體,即等同于法權。
第三個歷史階段起始時間可以追溯到“自然權利”等漢譯外文法學名詞的運用,但總體上看起始于20世紀80年代,完成于21世紀10年代。這時期一批中文法學研究者吸納了漢譯引進的外文法學自然權利、道德權利、道德權力等名詞,并結合中國社會生活實際形成了宗教意義的權利、政黨和社會團體成員權利、法外之權、應有權利的法外部分等觀念,并將概括這些觀念的剩余權含義穩定地添加到了“權”字中,使“權”字的表意范圍顯著地超越了權利、權力及二者的統一體法權,從而第三次刷新了“權”字的表意范圍。這方面的情形上文相關段落已多有展示。
3.“權”字從古漢字走向現代中文法學概念的漫長道路,是在剩余權含義從“權”字中誕生出并成為獨立法學概念后才走完的,時間點大體在20世紀與21世紀交匯的前后20來年。形成包含權利、權力、剩余權三重內容的“權”字,邏輯上并不表示“權”已形成現代法學概念。因為,要成為現代法學概念,“權”字孕育的權力、權利、剩余權三種胚芽必須先行成熟并從中誕出成為法學概念,“權”本身才有可能在外延、實質兩方面實現與它們三者的區分,獲得作為法學概念的必要獨立性。
實際上,可以把“權”字走完通向近現代法學概念的歷程分為三個具體階段:(1)“權利”進入權字的最初標志是西文right、droit由袁德輝、伯駕在《海國圖志》里漢譯為“權”,而進一步進入并以“權利”的外觀誕出則是丁韙良漢譯《萬國公法》時創造“權利”一詞。而“權利”在中文法學中獲得傳播和成為近現代中文法學概念的標志則是1902—1906年梁啟超《新民說》(特別是其中《論權利思想》)的發表。(2)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漢字西譯》和19世紀初的《漢法拉大辭典》、馬里遜《華英字典》系列的相關條目讓“權”萌生了現代“權力”概念的胚芽,但權力作為近現代中文法學概念誕出的真正標志,是1874年加藤弘之的著作高頻率使用“權力”一詞及梁啟超1906年在《開明專制論》中反復使用和系統論述“權力”。(3)剩余權概念和觀念的穩定形成,如前所述,其表現包括最初的自然權利,出現得較晚的道德權利、道德權力、法外之權、社會權力、宗教性權利、社團成員權利等語言形式。這個階段拖得比較長,但無論如何,到21世紀10年代,剩余權概念應該可以算完全形成。因為雖然人們用以表述剩余權概念的語言載體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它的外延表現為“權”減去法權利和法權力兩要素后的各種剩余部分,其實質或內容是法外利益,歸根結底乃歸屬未定的財產。〔66〕參見童之偉:《法權說對各種“權”的基礎性定位》,載《學術界》2021年第2期,第120-121頁。
權力、權利、剩余權從“權”字中誕出后,“權”成為外延包括前三者但其本身又獨立于前三者的法學概念,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就像“家庭”概念外延包括夫、妻及子女,但家庭本身是獨立概念和獨立分析單元一樣的道理。
4.“權”字的含義變遷及其走向中文基礎性概念的歷史的邏輯的進程,可視為近現代意義的中文法學發生、發展和初步形成的過程的縮影。還原了這個過程,能夠幫助人們把握包括未來走向在內的中文法學發展的脈絡,在法學研究中少走彎路、少做無用功。把握“權”字含義演進和概念衍射的全過程,是把握現代中文法學內容和特點的便捷途徑。
中國近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法學,實際上都是以承認權利、權力、剩余權、權、義務共五個概念體現了法的基礎性內容為前提的。自19世紀末以降,中國的幾代法學家實際上都間接承認了這五個概念的基礎性地位:1949年前,中文法學界通行的觀點是法學乃權利義務之學;20世紀50年代及其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學界關于法學主要內容的看法,為人所知的無外乎權利—義務重心論、義務重心論、權利本位論、權利—權力—義務重心論、權利權力統一體(即法權)中心說等數種,都在這五個概念標示的現象的范圍內。中文法學的這五個概念也大體對應著當代歐美亞太法學的基礎性法學概念。這應該是同時期各國法律生活的主要領域和現象大致相同使然。所以,從古漢字“權”發展衍射出來的這個基礎性概念群的歷史,濃縮了現代中文法學的形成史,而且,它既是民族的、本土的產物,也是一定程度開放、面向西洋和東洋的結果。它的民族性、獨特性集中體現在權字的本土性上,而其開放性、西東兩洋面向性歷史地形成于它發展的幾個關鍵階段。本文展示的細節已經證明,在這些關鍵階段,中文法學的這組基礎性概念接納、包容了外國法文化和外國法學的有用要素。其中,理解中外文法學間交流互動關系及其產生的法學成果的關鍵,是還原17世紀漢字字典《正字通》、18世紀初《康熙字典》中權字與西方傳教士兼漢學家們編纂《漢字西譯》《漢法拉大辭典》和《華英字典》系列詞典和漢譯外文法學著作相互影響的歷史。
另外,“權”這個古漢字中原有的權勢、權柄含義,嬗變為包含權力、權利和剩余權三重含義的現代法學基礎性概念的過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濃縮了中國法律生活從封建專制制度向民主、法治社會轉變的漫長歷程和歷史趨勢。
此處應特別說明,歷史上的《漢字西譯》《漢法拉大辭典》《華英字典》系列,以及漢譯《萬國公法》《公法便覽》等著作,它們不論作為整體還是其中權字與相應西文名詞互譯互釋的部分,實際上都直接包含著以《字匯》《正字通》《康熙字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的成果和它們的作者以及前述陳藎謨、胡邵瑛等那樣的中國學者的勞動。其中像漢譯《萬國公法》之類的譯著尤其如此,因為,其譯者當時實際上擔任的是清政府的高官,吃的是清政府的俸祿,從法理和道義上看,其譯著應視為著作權屬清政府的職務作品。因此,這些雙語、三語字典和中文譯著,實為中外學者合作的產物,因而其整體或相關部分應被視為中文法學早期的珍貴成果。還應說明,梁啟超等中國學者在國外寫作和發表的法學論著,也不因為當時作者不在中國的土地上而喪失其中文法學的屬性。
5.循“權”字的發展衍射進程辨識、甄別、查明現有法學基本概念的“真身”“出生”時間地點和“身世”,是中國法律學者走出“法學幼稚”困局的必經之路。法學應當是而且通常是民族的,其民族性不僅表現為法系,更具體地表現為處在相同法系中的不同國家可相互區分開來的特征。各國法學都有自己獨特的形成史。概念是法學的細胞,各國法學的“遺傳密碼”等基本特征,必然高度密集地潛藏在其基礎性概念中。所以,不論中文法學還是外文法學,其精髓都只能通過考察其形成史來形塑或把握。歷史法學派的祖鼻薩維尼差不多兩世紀前就提出,對于想做好法學研究的人們來說,“第一個必要條件當然是對法律史的全面了解,以及形成(必然由此導致的)以正確的歷史眼光看待每一個概念和每一種學說的確定不移的習慣”。〔67〕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of the Vocation of Our Age for Legislation and Jurisprudence, trans. Abraham Hayward, London:Littlewood & Co, Old Bailey, 1831, p.140.這在今天仍然應該是有普遍意義的法學研究方法論原則。從這個角度看,現代中文法學的基礎性概念與西文法學的基礎性概念,盡管通常可以互譯,如現代中文法學概念的權利、權力、義務與英文法學概念right、power、duty等之間,但前后兩者的外延、內容的差別仍然比較大。其中有些差別如果研究者不能詳加辨察,可能對現代中文法學發展的全局造成相當負面的影響。
近年有學者就20世紀80年代清史專家戴逸先生提出的“法學是幼稚的”觀點做了反思,認為這個問題仍沒有解決,因而提出“中文法學要想擺脫幼稚走向成熟,就必須使自身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68〕舒國瀅:《求解當代中國法學發展的“戴逸之問”》,載《北方法學》2018年第4期,第5頁。筆者以為,此說關于當代中文法學仍然“幼稚”的認定不無道理。當代中文法學仍未完全走出“幼稚”狀態的首要表現,是對法學采用的基本概念,尤其是對作為其核心部分的基礎性概念,如權利、權力和義務,沒有在歷史深度上下足夠的辨識、甄別、查明工夫。其結果之一,是它們給學術界的感覺是無根無底、來歷不明、身份不清、面目模糊,其中尤以整個法學界都極端重視的、經常使用的“權利”一詞為甚。解決好這個問題,應該從考察“權”的概念形成史及其與權利、權力、剩余權等基礎性概念的歷史聯系著手。
6.“權”已實質性完成向中文法學基礎性概念和基礎性范疇的跨越。在此學術背景下,尊重歷史,以“權”字為根基形成和運用中文法學基礎性概念,可以順理成章地處理好當代中國法學面對的民族性與國際化之間的關系問題。中文法學的權利、權力、剩余權、權四個概念都是從先秦的“權”字直接演進和衍射而來的,其中尤其有特點的是“權”字和“權”的概念。含義歷經滄桑巨變的“權”字,以1813年《漢法拉大辭典》和稍后的馬禮遜《華英字典》系列為新起點,開始逐漸吸收歐美和日本法文化的相關成分,逐漸成為一個兼具法權利、法權力和法外之權等多重含義的法學新名詞、新概念。對于現代中文法學權的概念來說,它在內容上雖吸收了外來成分,但就其本身而言,完全是中國本土法文化發揮主體作用形成的新成果。“權”字在漢語獨特的社會環境下,在中日兩國法文化的交流互動中發展到既可同時指稱權利、權力、剩余權,又可分別指稱三者中任兩種或任一種。“權”有漢字特有而任何時代的西語(如拉丁語、英語、法語)名詞都沒有的功能表意,是任何西方語言所不能比擬的一個卓越法學名詞。“權”這個名詞和“權”的概念有確定的外延、內容卻沒有西語法學名詞、概念在含義和表意功能上與之對應,這正是“權”的概念相對于西文法學的優勢所在,它實實在在反襯出西文法學基礎性概念的相對劣勢。“權”字和“權”的概念是現代中文法學及其基礎性概念群的本源所在,也是現代中文法學民族性、本土性的標志和象征,它的學術和學科地位是歷史地形成的、客觀的。
“權”的概念完全是中國人自己創造的法學元素,可謂民族法學的象征性范疇,理應受到珍視。人們過去常說,中國法學和外文法學還不能進行對話,某種程度上說或許確實是這樣,因為,與人“對話”要有足夠“資格”或“本錢”,做現代法學我們起步較晚,還拿不出太多的真正屬于自己的東西與外國人交流、交換。但是,經過發掘、研究和合理定義的權,還有法權,完全可以成為中文法學與外文法學交流之學術、學理依托,能在很大程度上平衡、比肩諸如權利、義務等翻譯、引進的外文法學元素。這些道理對于有獨立思維和求真品格的學者來說應該是清楚明白的,但對于陷入外文尤其西文法學迷思的人說,可能仍然太復雜、太難以想象。中國法學應該努力克服西文法學迷思,對真正屬于我們本土和我們民族的法學元素有自信。
應該看到,中文法學有“權”這個概念、名詞,西文法學缺乏與權含義對等、對稱的概念、名詞,此乃漢文和中文法學的相對優勢所在,也是西文法學的相對劣勢或局限性所在。這方面最為緊要的,是萬不可將中文法學特有的優勢視為劣勢,同時將西文法學的特定劣勢看成優勢。“權”這個名詞在中國法學界尚未得到足夠重視,除上文已經陳述過的原因外,有些中國學者因為西語沒有與“權”含義對等的詞,或難以將其譯為西語而忽視它、輕視它的態度,或許也應承擔一定責任。“權”字有豐富表意效用而為中國人所創造和長期高頻率使用,已成為漢語和中文法學獨特的資源優勢,中國學術界應該對它加倍珍惜,將其作為中文法學對世界法學之林的獨特貢獻介紹給世界各國。外延和實質已經表述得很清楚的“權”的概念以其蘊含深厚的中華歷史文化底蘊和獨特、豐富的表意功能,有充分的資格擔當代表中文法學走向外部法學世界的使者。
“權”,在實質意義上說還有“法權”,完全是中國人自己新近從法現象中提取的全新法學概念。權、法權概念完全可以成為中文法學與西文法學交流之學術、學理依托,并在很大程度上平衡、比肩西文法學中諸如right、duty等元素。此外,法學界人士常說,法學基本范疇是法學理論大廈的支柱,這是很實在的判斷。但由此我們也得以知曉,如果法學整個基礎性范疇體系中沒有一兩個真正屬于我們民族自己創造的范疇支柱,如果全是外來的或舊支柱,那么,我們不論怎么描敘和涂抹這座大廈,都無法掩蓋它缺乏本土本民族氣息且過于陳舊的現狀。就實質而言,權和法權概念是全新的中文法學基礎性范疇,相信理論法學界終究會展現出接受它們的胸懷和氣度。畢竟,中文法學即使是接納外文法學、尤其歷史上日文法學的新名詞、新概念,也從來是慷慨的。
權和法權,雖已完成向現代中文法學概念的跨越,顯現出了廣闊的學術前景,但這與中國法學家們愿不愿意接納和使用它,完全是兩碼事。因此,“權”和“法權”概念的使用和推廣普及,對于熱心推進本土本民族的法的一般理論之形成的法律學者來說,依然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