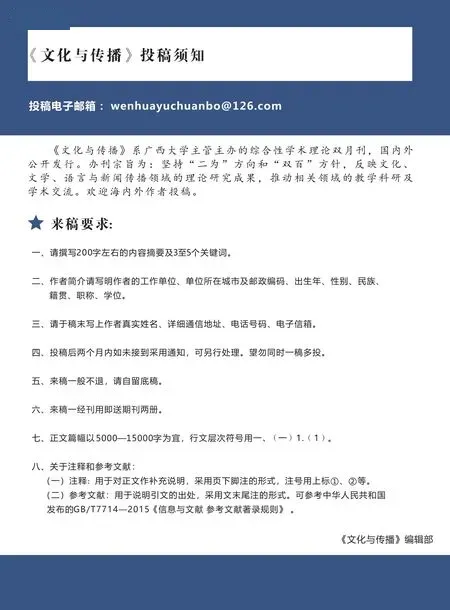魯迅雜文在當代美國的翻譯與跨文化傳播
——以《燈下漫筆》為考察中心
李紅滿
作為20世紀中國重要的文學家和思想家,魯迅的小說作品很早就在英語世界展開了翻譯與跨文化傳播之旅,目前已出版有多種英文譯本,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在1941年出版的《阿Q及其他:魯迅小說選》(AhQandOthers:SelectedStoriesofLuXun)、美國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在1990年出版的《狂人日記及其他故事》(The MadmanDiaryandOtherStories),還有英國企鵝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的《〈阿Q正傳〉及其他中國故事:魯迅小說全集》(TheRealStoryofAh-QandOtherTalesof China:TheCompleteFictionofLuXun)等,不勝枚舉。然而,相比之下,魯迅雜文雖然作為其文學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代英語世界的翻譯和研究卻付之闕如,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和重視。
近年來,美國漢學界相繼有多部魯迅研究的英文專著出版,例如莊愛玲的《文學的遺存:死亡、創傷和魯迅對哀悼的拒絕》(LiteraryRemains:Death,Trauma,andLuXun’sRefusaltoMourn)、戴維斯的《魯迅的革命:暴力時代的寫作》(Lu Xun’sRevolution:WritinginaTimeofViolence)、柯德席的《中國散文詩:魯迅〈野草〉研究》(The ChineseProsePoem:AStudyofLuXun’sWildGrass)等,其采用全新的理論視角對魯迅及其文學作品進行研究和評價,在當代美國漢學界掀起了魯迅研究的熱潮。乘著這一股魯迅作品海外研究的新浪潮,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在2017年推出了一部全新的魯迅雜文英文選集《燈下漫筆》(Jottingsunder Lamplight)。該英文選集由美國波莫納學院的莊愛玲教授(Eileen J.Cheng)和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鄧騰克教授(Kirk A.Denton)擔任主編,匯聚了14位英語世界知名的魯迅研究專家和翻譯家,包括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的寇志明教授(Jon Eugene von Kowallis)、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胡志德教授(Theodore Huters)、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胡纓教授(Hu Ying)、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安德魯?瓊斯教授(Andrew Jones)、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安敏軒教授(Nick Admussen)、香港中文大學的卜立德教授(David Pollard),以及澳大利亞翻譯家杜博妮教授(Bonnie S.McDougall)等,將魯迅在1918年至1936年所創作的62篇雜文翻譯為英文,極大地推動了魯迅雜文的海外譯介和研究,具有不可忽視的學術價值和意義。因此,本文以這部英文選集為考察中心,深入探討其主題內容和翻譯特色,揭示魯迅獨特的雜文話語和寫作風格如何在英文中進行再現與重構,以期積極促進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跨文化傳播。
一、“共同見證了一位文化巨匠的偉大”
自出版以來,《燈下漫筆》這部全新的魯迅雜文英文選集,在美國漢學界和圖書評論界均好評如潮。在圖書封底的推薦語,美國波士頓大學的哈金教授寫道:“《燈下漫筆》是一部經過精心翻譯和編輯的優秀魯迅雜文選集,這些雜文共同見證了一位文化巨匠的偉大。”①見《燈下漫筆》的封底語,中譯文為筆者自譯。美國威廉與瑪麗學院的漢學家韓嵩文教授(Michael Gibbs Hill)也予以點贊:“這本書為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和世界文學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它收錄了魯迅一些最為人所知的雜文和隨筆文章,精彩展現了魯迅作為學者的橫溢才華和作為文化批評家和政治觀察家的犀利與睿智。”②同①。
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向英語讀者大力推介《燈下漫筆》這部英文選集,在其官方網站介紹道:“魯迅被廣泛認為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作家。雖然魯迅在英語世界主要以其兩部短篇小說而聞名,然而他卻是一位多產且富有創造力的雜文家。《燈下漫筆》收錄了62篇魯迅雜文的英譯文,其中20篇雜文為首次翻譯,展現了魯迅作為雜文大家的多才多藝和作為文化批評家的卓越才華……魯迅的雜文時而帶著絕望的色彩,時而充滿著悲情、幽默和無與倫比的嘲諷和睿智,記錄著自己生活和時代的動蕩變化,為中國的社會和文化提供深刻的洞察。”③詳見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官方網站對《燈下漫筆》https://www.hup.harvard.edu/catalog.php?isbn=978067474425 7&content=review.的圖書簡介與評論,中譯文為筆者自譯。獲取時間為2021-04-18。《洛杉磯圖書評論》的評論家麗茲?卡特(Liz Carter)對這部魯迅雜文選集大加贊譽:“《燈下漫筆》經過周密的組織和策劃,精選了魯迅的一些最優秀的雜文和隨筆文章。這是一部人們期待已久的魯迅雜文選集,揭示了魯迅內心的矛盾和不確定性,而不是對此予以掩蓋……雖然大部分的英語讀者對魯迅知之甚少,但希望通過增加對他的文學作品的接觸,能夠引起人們對這位20世紀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文學大師有更多的興趣。”④同③。美國的《出版家周刊》也對《燈下漫筆》的出版進行評論:“莊愛玲教授和鄧騰克教授編輯和出版了20世紀初期中國著名作家魯迅雜文的英文選集。這些雜文多數是針砭社會時事,諷刺尖銳,言辭犀利。每一篇雜文字字珠璣,充滿了魯迅深切的悲憫情懷……總而言之,這部魯迅雜文選集是一個國家在不確定性和社會轉型中掙扎的真實寫照,不僅是關系到20世紀初期的中國社會文化,同樣也與當代西方息息相關。”⑤同③。
早在20世紀50年代,我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與戴乃迭夫婦曾先后翻譯了四卷冊的英文版《魯迅作品選集》(SelectedWorksofLuXun),由我國外文出版社在1956年首次正式對外出版,后來多次重印。該英文選集收錄了魯迅的小說作品和部分雜文,使英語讀者有機會能夠比較全面閱讀和接觸到魯迅優秀的文學作品。在《燈下漫筆》的前言里,兩位主編首先肯定了楊氏伉儷在魯迅文學作品的海外譯介和傳播中所做的重要貢獻,但是同時也直言不諱地指出,楊氏伉儷所翻譯和出版的魯迅雜文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之久,英譯文的表達有點生硬,顯得不夠自然,有些譯文甚至包含對魯迅原文的修訂和刪減;而且,由于楊氏伉儷的英譯本按照出版時間的先后順序對魯迅雜文進行編排,對于不熟悉魯迅其人及其所處的20世紀中國社會文化的西方讀者而言常常不知所云,無法對英語世界的普通讀者產生較大的吸引力[1]7。因此,《燈下漫筆》的兩位主編將國際上的優秀魯迅研究學者組織起來,形成一個高水平的學術翻譯團隊,在2017年9月出版了這部全新的魯迅雜文英譯選集,使西方的廣大讀者終于有機會走進魯迅那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精彩雜文世界。
二、“自我反思”與“文化反思”
《燈下漫筆》英譯本經過精心的策劃和編輯,主要以我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所出版的《魯迅全集》為底本,精選了魯迅最有代表性的62篇雜文作品。該英文選集按照主題思想和內容進行組織結構,分為“自我反思”和“文化反思”兩大部分,具有鮮明的主題特色,生動展現了魯迅思想的發展和嬗變及其心路歷程。20世紀中葉,楊氏伉儷所出版的《魯迅選集》英譯本按照時間的先后順序對魯迅雜文進行編排出版,然而,由于大部分的英語讀者對于魯迅及其所處的中國社會文化語境不甚了解,無法在英譯本中領略到魯迅雜文話語和筆法的精彩絕妙之處。因此,《燈下漫筆》英文譯本采用全新的組織結構,根據魯迅雜文的主題思想進行選材和歸類,簡明清晰地解釋魯迅所處的中國社會歷史背景和文化語境,以便英語讀者能夠更好地理解和欣賞魯迅的雜文作品。
第一大部分的標題為“自我反思”,收錄了魯迅20篇重要雜文的英譯文,按照不同的主題再細分為兩節。第一小節主要選錄了魯迅的一些自序、題記、書跋和自傳體文章等12篇英譯文,按照魯迅雜文發表時間的先后順序進行編排,包括《〈吶喊〉自序》(1923)、《〈華蓋集〉題記》(1926)、《〈墳〉題記》(1926)、《〈阿Q正傳〉的成因》(1926)、《我怎么做起小說來》(1933)等。在《燈下漫筆》的前言里,兩位主編指出,“事實上,我們對魯迅生平和創作動機的了解,很大程度上都來自這些前言。與魯迅作為文學戰士的公眾形象相反,他的自畫像卻常常揭示了一個飽受質疑、矛盾重重的人”[1]8。通過閱讀魯迅這些自序、題記和自傳體文章的英文翻譯,英語世界的讀者可以首先借此深入了解魯迅文學創作所處的中國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對魯迅其人其文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認識。第二小節的主題詞為“紀念”,精選了8篇魯迅回憶和悼念已故的學生、朋友和師長的雜文,例如劉和珍君、韋素園君和章太炎先生等,其中還包括當時的一些公眾人物,例如電影明星阮玲玉。在某種意義上,魯迅這些紀念性文章可以說是他關于舊日記憶的反思和議論,以表達自己對逝者的深切悼念,因此兩位編者將之也歸入“自我反思”這一大部分。
第二大部分的標題為“文化反思”,總共收錄魯迅42篇雜文的英文翻譯,按照主題再細分為三節,分別為“論傳統”“論藝術和文學”和“論現代文化”,每一節都收錄了14篇魯迅雜文的英譯文。第一小節的主題為“論傳統”,收錄了《我之節烈觀》(1918)、《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1919)、《燈下漫筆》(1925)、《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1926)、《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1935)等多篇魯迅雜文。與其他兩節相比,這一節為《燈下漫筆》所占篇幅最大的部分,長達將近80頁。在這一節的作品中,魯迅對中國傳統封建文化和禮教展開了深刻犀利的批判。第二小節的主題是“論藝術和文學”,精選了魯迅從1919年至1933年對這一歷史時期的中國文藝現狀進行評論和反思的雜文作品,例如,《對于批評家的希望》(1922)、《革命時代的文學》(1927)、《文藝與革命的歧途》(1928)、《現今的文學的概觀》(1929)、《上海文藝之一瞥》(1931)、《小品文的危機》(1933)等。第三小節的主題為“論現代文化”,主要收錄了魯迅對20世紀初期中國社會萬象進行文化批判的雜文,例如《娜拉走后怎樣》(1924)、《論照相之類》(1925)、《現代史》(1933)、《電影的教訓》(1933)、《拿來主義》(1934)等。在這些精選的雜文作品里,魯迅不時引用易卜生、泰戈爾、蕭伯納、托爾斯泰等作家和思想家的精彩言辭針砭時弊,對民國時期的中國社會文化現象展開了猛烈的抨擊。這一部分的雜文從“論傳統”“論藝術和文學”到“論現代文化”的多維主題建構,形成了綜合完整的有機體系,有助于廣大的英語讀者對魯迅的社會文化批評觀有全面的認識和了解。
三、魯迅雜文話語和寫作風格的英文再現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指出:“‘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 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2]然而,如何將魯迅獨特的雜文話語和寫作風格翻譯為英文,與西方英語讀者順暢地展開跨語言文化的交流和溝通,無疑讓英譯者面臨著高難度的翻譯挑戰和考驗。魯迅先生本人認為,“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3]。在題為《魯迅:處于“中間”的批評家》的前言里,《燈下漫筆》的兩位主編明確指出,此處魯迅雜文英文選集的編寫旨在于“提供清晰準確的翻譯,讓專業人士和廣大的普通英語讀者都能接觸到魯迅的文學作品”[1]7。為了能夠讓廣大的英語讀者閱讀到忠實準確的魯迅雜文英文選集,國際魯迅研究領域的14位資深漢學家和翻譯家齊聚一堂,攜手將62篇精選的魯迅雜文翻譯為英文,其中大部分是為這部魯迅雜文選集而重新翻譯的。由于目標讀者為英語世界的廣大讀者,這部魯迅雜文英譯本主要以英語作為語言媒介進行對外譯介與傳播,中文僅在雜文題名和附錄中零星點綴出現。
《燈下漫筆》的兩位主編也親自參與了魯迅雜文的翻譯工作,其中莊愛玲教授本人就翻譯了這部選集的17篇魯迅雜文,包括《華蓋集》題記、《且介亭雜文》序言、《小雜感》等等。莊愛玲教授曾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得中國現代文學博士學位,一直在美國高校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已發表和出版了多部魯迅研究相關的英文論著,如《文學的遺存:死亡、創傷和魯迅對哀悼的拒絕》《別求新聲于異邦:魯迅、文化交流與中日友好的神話》等。作為魯迅研究專家,莊愛玲教授將魯迅的雜文語言藝術翻譯得非常精彩。以魯迅《小雜感》中的這一段奇文為例。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殺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于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于革命的,或并不當作什么而被殺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4]556
Revolutionaries,counterrevolutionaries,those apathetic to the revolution.
Revolutionaries are killed by those who are counterrevolutionaries.Counterrevolutionaries are killed by revolutionaries.Those apathetic to the revolution or mistakenly identified as revolutionaries are killed by counterrevolutionaries; or they aren’t mistaken for anything at all and are killed by revolutionaries or counterrevolutionaries.
Revolutions,re-revolution,re-re-revolution,re-re…[1]209
由于“革命”二字在魯迅的原文以不同的形式多次反復出現,很不好翻譯。在《魯迅作品選集》英文版的第二卷,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婦直接把這一段話刪減了,沒有翻譯出來。然而莊愛玲教授卻巧妙地將魯迅這一段奇文通順流暢地翻譯為英文,并在文末注釋中向英語讀者進一步解釋“革命”二字的中文含義,并指出最后一行的原文“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意在模擬機關槍開火的聲音,這使英語讀者很容易理解和欣賞魯迅獨具特色的雜文語言藝術。再如《小雜感》的另一處文字:
劉邦除秦苛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而后來仍有族誅,仍禁挾書,還是秦法。
法三章者,話一句耳。[4]557
Liu Bang wanted to eradicate the violent ways of Qin and made a pledge to the elders that there would only be three rules.
Afterward they still executed clans and banned books,all of which were the laws of the Qin.“Rules”are just empty words.[1]210
楊氏伉儷的英譯本沒有《小雜感》這一段話的譯文,直接將之刪減了。相比之下,莊愛玲教授不僅將這一段忠實地翻譯出來,而且在注釋中詳細說明“約法三章”的典故出處及其基本釋義,幫助英語讀者更好地理解魯迅雜文中所使用的歷史典故及其內涵。此外,在楊氏伉儷的英譯本中,被直接省略了,但是莊愛玲教授按照底本將魯迅的全文完整地翻譯為英文,沒有任何增刪,使英語讀者第一次有機會可以閱讀到魯迅這篇雜文的真實全貌。
《燈下漫筆》的另一位主編鄧騰克教授(Kirk A.Denton)曾在1988年獲得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中國現代文學博士,現為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的中文教授,同時也是英文學術期刊《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ModernChineseLiteratureand Culture)的主編。早在1996年,鄧騰克教授(Kirk A.Denton)曾編著了《現代中國文學思想:1893-1945》(ModernChineseLiteraryThought:Writingson Literature,1893—1945)。這部研究專著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收入了《〈吶喊〉的自序》《論第三種人》《論照相之類》《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和《摩羅詩力說》等魯迅5篇雜文的英譯文,曾榮獲美國1996年度的最佳學術圖書獎項。此次作為《燈下漫筆》的主編,鄧騰克教授在組織和編寫魯迅雜文選集英譯本時,并沒有繼續沿用以前的舊譯文,而是積極組織和邀請不同的學者進行重新翻譯,精益求精,真實再現魯迅獨特的雜文話語和寫作風格。不妨以魯迅寫于1932年的雜文《論第三種人》為例。楊氏伉儷在《魯迅作品選集》英文版的第三卷將這篇雜文的題目譯為“ On the ‘Third Category’”。《現代中國文學思想:1893—1945》一書所收錄的《論第三種人》基本沿用了楊氏伉儷的翻譯,也是將其譯為On the “Third Category”。然而,鄧騰克教授在組織和策劃《燈下漫筆》英譯本時,特地邀請了美國康奈爾大學的魯迅研究專家安敏軒教授(Nick Admussen)來重新翻譯《論第三種人》等多篇雜文。安敏軒教授沒有沿襲以前的舊譯,而是將這篇雜文的題目翻譯為“On the ‘Third Type of Person’”,顯得更為忠實于原文。再如,《論第三種人》文中關于第三種人的定義,魯迅寫道:
但在“第三種人”,就是“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又不免有一種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壇要說他是“資產階級的走狗”。[5]
楊氏伉儷的英譯文:
But members of the “third category”,that is,those who “cling for dear life to literature,” cannot escape the bitter premonition that Left-wingers will call them “flunkeys of the bourgeoisie”.[6]
安敏軒教授的英譯文:
But the “third type of person” — that is to say,“a person who keeps a death grip on literature”— is unable to escape a stabbing premonition: that the leftist literary circle is going to brand them “running dogs of the bourgeoisie”.[1]238
若進行仔細比較,可以發現以上兩版英譯文在翻譯策略和方法上迥然相異。如“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這個詞組,楊氏伉儷將之翻譯為“cling for dear life to literature”,而安敏軒教授將之譯為“keeps a death grip on literature”;再如“資本主義的走狗”一詞,楊氏伉儷將之翻譯為“flunkeys of the bourgeoisie”(資本主義的奴才),而安敏軒教授則將之譯為“running dogs of the bourgeoisie”(資本主義的走狗)。顯然,楊氏伉儷采用了通用的歸化翻譯策略,盡量淡化魯迅原文話語的異質性和陌生感,以便保持英譯文的可讀性,力求其易解。德國哲學家本雅明在《譯作者的任務》一文中曾指出,“文學作品的基本特性并不是陳述事實或發布信息。然而任何執行傳播功能的翻譯所傳播的只能是信息,也就是說,它傳播的只是非本質的東西。這是拙劣譯文的特征。但是人們普遍認為文學作品的實質是信息之外的東西”[7]。在《燈下漫筆》雜文英譯選集中,安敏軒教授以異化的翻譯策略和方法為主,盡量不改變魯迅原文所用的修辭格和形象,傾向于在英譯文中保留魯迅雜文的異質性話語特征,積極彰顯原文內涵的語言和文化特色,使魯迅幽默、睿智和嘲諷的話語刺客精神躍然紙上,更加原汁原味地再現了魯迅雜文匕首投槍式的犀利寫作風格。
由于《燈下漫筆》的翻譯團隊主要由英語世界的魯迅研究專家和翻譯家組成,具有良好的學術研究背景和高超的翻譯技能,因此這部選集的翻譯可謂一絲不茍,精益求精,傳神逼真地再現魯迅獨特的雜文話語和筆法。例如,魯迅著名的雜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段話的翻譯:
“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道。中國最多的卻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8]
楊氏伉儷的英譯文:
“To be wronged but not to seek revenge” is forgiving.“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 is just.In China,however,most things are topsy-turvy instead of beating dogs in the water,we let ourselves be bitten by them.[9]
安德魯?瓊斯教授的英譯文:
To “bear the trespasses of others without correction” is the path of mercy; “an eye for an eye,a tooth for a tooth” is the path of justice.In China,most paths run crooked: not only won’t we beat a drowning dog,but we also get bit by it in return.[1]160
譯者安德魯? 瓊斯教授(Andrew Jones)曾在1997年獲得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中國現代文學的博士學位,現為該校東亞語言與文學系的中文教授和系主任。在此部《燈下漫筆》英譯本中,安德魯? 瓊斯教授負責翻譯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青年必讀書》《上海的兒童》《野獸訓練法》和《玩具》等多篇雜文。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的英譯文中,楊氏伉儷將“落水狗”一詞譯為“dogs in the water”,卻沒有把原文的關鍵動詞“落”字翻譯出來;而安德魯? 瓊斯教授的譯文“a drowning dog”則更加活靈活現地反映出“落水狗”的恐慌與狼狽不堪;而且,他把文中的“恕道”“直道”和“枉道”分別譯為“the path of mercy”“the path of justice”和“crooked paths”,淋漓盡致地再現了原文特有的話語和修辭特色。此外,安德魯? 瓊斯教授還在文末注釋中向英語讀者補充說明了這段話中的兩個引言出處,即分別來自《論語》和《圣經?舊約》。如此高質量的英譯文在《燈下漫筆》中比比皆是,不勝枚舉。就整體而言,《燈下漫筆》的翻譯風格與楊氏伉儷迥然不同,更加傾向于在英譯文中保留非透明的異質性話語,積極倡導異化翻譯策略及其文化實踐,盡量彰顯魯迅原文獨特的話語和修辭特征,使廣大的西方英文讀者得以有機會更深刻地去認識和理解魯迅的雜文作品。
四、余論:魯迅雜文“走出去”
隨著近年來英語世界魯迅研究熱潮的興起,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組織策劃和出版的《燈下漫筆》英譯選集匯聚了國際魯迅研究領域的14位頂尖專家和學者,精彩展現了魯迅作為20世紀初期中國文化巨匠的睿智與卓越才華。由于擁有高質量的學術翻譯團隊,《燈下漫筆》的英譯文不僅傳神地保存了魯迅雜文“原作的豐姿”,忠實準確,而且通順流暢,具有較高的可讀性,在“信”與“順”之間取得了較好的平衡,為魯迅雜文的英文翻譯設定了新的學術標準,讓魯迅優秀的雜文作品走進了廣大的英語讀者大眾的閱讀視野。
為了讓魯迅雜文更好地“走出去”,《燈下漫筆》英譯選集還在書后為西方讀者提供了詳細的注釋,多達20頁左右,補充說明魯迅雜文中所涉及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等相關信息,并引導感興趣的英文讀者進一步閱讀相關的參考文獻,開展更加深入細致的魯迅研究。該英文選集還在行文中適時穿插了8幅與魯迅相關的照片和圖像,包括魯迅的留日相片、魯迅在北京師范大學演講的照片、魯迅親筆撰寫的詩歌書法作品等,圖文并茂,無形中增加了的閱讀趣味性。
《燈下漫筆》英譯本以其一絲不茍、精益求精的英文翻譯,詳細的英文注釋和說明,無疑將極大地促進魯迅雜文作品“走出去”,吸引更多的英語讀者走進魯迅那個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精彩雜文世界,使他們得以有機會更深刻地認識和了解20世紀中國偉大的文學巨匠魯迅獨特的雜文話語和寫作風格,積極促進和推動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海外譯介與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