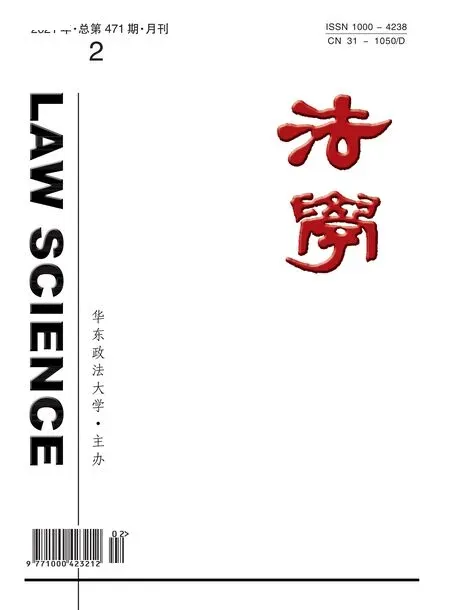《刑法修正案(十一)》對司法解釋的否認(rèn)及其問題解決
張明楷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部分條款由來于司法解釋,〔1〕本文所稱司法解釋,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的司法解釋、指導(dǎo)性案例及其與公安部、司法部聯(lián)合頒發(fā)的指導(dǎo)意見。但并沒有將司法解釋的內(nèi)容直接納入刑法條文。從法條表述上看,不管《刑法修正案(十一)》是確認(rèn)還是否認(rèn)了相關(guān)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立法機(jī)關(guān)與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都面臨著如何處理司法解釋與刑法修改的關(guān)系、如何恪守罪刑法定原則的問題。
一、從司法犯罪化到立法犯罪化
當(dāng)今社會發(fā)展變化迅速,新型犯罪層出不窮。德國學(xué)者賓丁(Binding)早在100 多年前就指出:“日常生活的浪潮(Wellen)將新的犯罪現(xiàn)象沖刷到了立法者腳前。”〔2〕Binding, Lehrbuch des gemeinen Strafrecht, Bd. 1, 2. Aufl.1902, S. 20.轉(zhuǎn)引自[德]米夏埃爾·庫比策爾:《德國刑法典修正視野下的刑事政策與刑法科學(xué)關(guān)系研究》,譚淦澤,載《中國應(yīng)用法學(xué)》2019 年第6 期,第183 頁。但在我國,由于各種原因,日常生活的浪潮首先將新的犯罪現(xiàn)象沖刷到了司法解釋者腳前。〔3〕這里所稱的司法解釋者,不是指起草司法解釋文件的個人,主要是指享有司法解釋權(quán)的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眾所周知,在我國,對于迄今為止沒有作為犯罪處理的行為,或者新出現(xiàn)的法益侵害行為,常常先由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擴(kuò)大解釋或者類推解釋為犯罪,然后由立法機(jī)關(guān)通過修改刑法的方式增設(shè)為新罪(包括修改法條增設(shè)新的行為類型)。或者說,先由司法機(jī)關(guān)進(jìn)行司法上的犯罪化,〔4〕關(guān)于司法上的犯罪化的相關(guān)論述,參見張明楷:《司法上的犯罪化與非犯罪化》,載《法學(xué)家》2008 年第4 期,第65-75 頁。再由立法機(jī)關(guān)進(jìn)行立法上的犯罪化。
最早的情形是,1979 年刑法規(guī)定了貪污罪,沒有規(guī)定挪用公款罪。但在改革開放初的一段時間,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的現(xiàn)象相當(dāng)普遍和嚴(yán)重,倘若不以刑法進(jìn)行規(guī)制,勢必形成巨大的處罰漏洞,導(dǎo)致國家、集體財產(chǎn)遭受重大損失。于是,1985 年7 月1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當(dāng)前辦理經(jīng)濟(jì)犯罪案件中具體應(yīng)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試行)》規(guī)定:“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工作人員和其他經(jīng)手、管理公共財物的人員,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超過6 個月不還的,或者挪用公款進(jìn)行非法活動的,以貪污論處。”1987 年3 月14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或者進(jìn)行非法活動以貪污論處的問題”的修改補(bǔ)充意見》規(guī)定:“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工作人員以及受國家機(jī)關(guān)、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和人民團(tuán)體委托從事公務(wù)的人員,利用職務(wù)上的便利,擅自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包括本人使用或者借給他人使用),數(shù)額較大,超過6個月不還的;或者數(shù)額巨大的;或者進(jìn)行非法活動,數(shù)額較大的;其性質(zhì)均屬于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應(yīng)以貪污罪論處。”誠然,可以認(rèn)為,上述解釋以挪用時間超過6 個月不還,以及挪用公款進(jìn)行非法活動等作為事實(shí)根據(jù),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進(jìn)而以貪污罪論處。但事實(shí)推定應(yīng)當(dāng)允許反證,而上述司法解釋并未允許反證,下級司法機(jī)關(guān)在辦案過程中也嚴(yán)格執(zhí)行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所以,必然存在將部分沒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為認(rèn)定為貪污罪的現(xiàn)象。于是,1988 年1 月21 日全國人大常務(wù)委員會《關(guān)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bǔ)充規(guī)定》第3 條第1 款規(guī)定:“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經(jīng)手、管理公共財物的人員,利用職務(wù)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jìn)行非法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shù)額較大、進(jìn)行營利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shù)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是挪用公款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jié)嚴(yán)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數(shù)額較大不退還的,以貪污論處。”類似這種先由司法解釋規(guī)定為犯罪,后由刑事立法增設(shè)為新罪的現(xiàn)象,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尤其明顯。
例一,2019 年1 月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guān)于依法懲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駕駛違法犯罪行為的指導(dǎo)意見》(以下簡稱《懲治妨害安全駕駛意見》)規(guī)定:“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駛過程中,搶奪方向盤、變速桿等操縱裝置,毆打、拉拽駕駛?cè)藛T,或者有其他妨害安全駕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yán)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的規(guī)定,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駕駛?cè)藛T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駛過程中,與乘客發(fā)生紛爭后違規(guī)操作或者擅離職守,與乘客廝打、互毆,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yán)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的規(guī)定,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的第133 條之二第1 款與第2 款規(guī)定:“對行駛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駕駛?cè)藛T使用暴力或者搶控駕駛操縱裝置,干擾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駛,危及公共安全的,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前款規(guī)定的駕駛?cè)藛T在行駛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擅離職守,與他人互毆或者毆打他人,危及公共安全的,依照前款的規(guī)定處罰。”
例二,2019 年10 月21 日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依法妥善審理高空拋物、墜物案件的意見》(以下簡稱《審理高空拋物案件意見》)規(guī)定:“故意從高空拋棄物品,尚未造成嚴(yán)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條規(guī)定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chǎn)遭受重大損失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處罰。為傷害、殺害特定人員實(shí)施上述行為的,依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的第291 條之二第1 款與第2 款規(guī)定:“從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拋擲物品,情節(jié)嚴(yán)重的,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有前款行為,同時構(gòu)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
例三,根據(jù)2018 年12 月25 日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發(fā)布第20 批指導(dǎo)性案例的通知》(指導(dǎo)案例104 號·李森、何利民、張鋒勃等人破壞計算機(jī)信息系統(tǒng)案)指出:“環(huán)境質(zhì)量監(jiān)測系統(tǒng)屬于計算機(jī)信息系統(tǒng)。用棉紗等物品堵塞環(huán)境質(zhì)量監(jiān)測采樣設(shè)備,干擾采樣,致使監(jiān)測數(shù)據(jù)嚴(yán)重失真的,構(gòu)成破壞計算機(jī)信息系統(tǒng)罪。”〔5〕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2016 年12 月23 日公布的《關(guān)于辦理環(huán)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辦理環(huán)境污染案件解釋》)第10 條規(guī)定:“違反國家規(guī)定,針對環(huán)境質(zhì)量監(jiān)測系統(tǒng)實(shí)施下列行為,或者強(qiáng)令、指使、授意他人實(shí)施下列行為的,應(yīng)當(dāng)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的規(guī)定,以破壞計算機(jī)信息系統(tǒng)罪論處:(一)修改參數(shù)或者監(jiān)測數(shù)據(jù)的;(二)干擾采樣,致使監(jiān)測數(shù)據(jù)嚴(yán)重失真的;(三)其他破壞環(huán)境質(zhì)量監(jiān)測系統(tǒng)的行為。重點(diǎn)排污單位篡改、偽造自動監(jiān)測數(shù)據(jù)或者干擾自動監(jiān)測設(shè)施,排放化學(xué)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同時構(gòu)成污染環(huán)境罪和破壞計算機(jī)信息系統(tǒng)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從事環(huán)境監(jiān)測設(shè)施維護(hù)、運(yùn)營的人員實(shí)施或者參與實(shí)施篡改、偽造自動監(jiān)測數(shù)據(jù)、干擾自動監(jiān)測設(shè)施、破壞環(huán)境質(zhì)量監(jiān)測系統(tǒng)等行為的,應(yīng)當(dāng)從重處罰。”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了《刑法》第229 條,使行為主體包括承擔(dān)環(huán)境影響評價、環(huán)境監(jiān)測職責(zé)的中介組織的人員,并且在加重構(gòu)成要件中增加了“在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工程、項(xiàng)目中提供虛假的安全評價、環(huán)境影響評價等證明文件,致使公共財產(chǎn)、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這一規(guī)定。
例四,2018 年1 月16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guān)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dǎo)意見》規(guī)定:“為強(qiáng)索不受法律保護(hù)的債務(wù)或者因其他非法目的,雇傭、指使他人有組織地采用上述手段(指軟暴力手段——引者注)尋釁滋事,構(gòu)成尋釁滋事罪的,對雇傭者、指使者,一般應(yīng)當(dāng)以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論處。”〔6〕2019 年4 月9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guān)于辦理實(shí)施“軟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也規(guī)定:“為強(qiáng)索不受法律保護(hù)的債務(wù)或者因其他非法目的,雇傭、指使他人采用‘軟暴力’手段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構(gòu)成非法拘禁罪,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尋釁滋事,構(gòu)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尋釁滋事罪的,對雇傭者、指使者,一般應(yīng)當(dāng)以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論處。”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的293 條之一規(guī)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催收高利放貸等產(chǎn)生的非法債務(wù),情節(jié)嚴(yán)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一)使用暴力、脅迫方法的;(二)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的;(三)恐嚇、跟蹤、騷擾他人的。”
例五,2005 年5 月11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 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我國領(lǐng)域外周邊地區(qū)聚眾賭博、開設(shè)賭場,以吸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為主要客源,構(gòu)成賭博罪的,可以依照刑法規(guī)定追究刑事責(zé)任。”〔7〕《刑法修正案(六)》將非法開設(shè)賭場的行為單立出來,規(guī)定為開設(shè)賭場罪,但該解釋在《刑法修正案(六)》之前頒布,故僅使用了“賭博罪”的表述。如果在《刑法修正案(六)》規(guī)定的基礎(chǔ)上加以理解,則意味著在我國領(lǐng)域內(nèi)開設(shè)賭場,以吸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為主要客源,構(gòu)成開設(shè)賭場罪的,可以依照刑法規(guī)定追究刑事責(zé)任。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了《刑法》第303 條,即提高了第2 款規(guī)定的開設(shè)賭場罪的法定刑,增加了第3 款規(guī)定:“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參與國(境)外賭博,數(shù)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yán)重情節(jié)的,依照前款的規(guī)定處罰。”
例六,2020 年2 月6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guān)于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以下簡稱《懲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意見》)規(guī)定:“……拒絕執(zhí)行衛(wèi)生防疫機(jī)構(gòu)依照傳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狀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yán)重危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條的規(guī)定,以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定罪處罰。”
《刑法修正案(十一)》將《刑法》第330 條第1 款項(xiàng)前修改為:“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guī)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引起甲類傳染病以及依法確定采取甲類傳染病預(yù)防、控制措施的傳染病傳播或者有傳播嚴(yán)重危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別嚴(yán)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外,司法機(jī)關(guān)對刑法分則并無明文規(guī)定的行為以犯罪論處,雖然沒有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但不可避免會請示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并得到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的同意。例如,“基因編輯嬰兒”案于2019 年12 月30日在深圳市南山區(qū)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法院認(rèn)為,3 名被告人未取得醫(yī)生執(zhí)業(yè)資格,追名逐利,故意違反國家有關(guān)科研和醫(yī)療管理規(guī)定,逾越科研和醫(yī)學(xué)倫理道德底線,貿(mào)然將基因編輯技術(shù)應(yīng)用于人類輔助生殖醫(yī)療,擾亂醫(yī)療管理秩序,情節(jié)嚴(yán)重,其行為已構(gòu)成非法行醫(yī)罪。〔8〕參見楊書杰、劉慧:《“基因編輯嬰兒”案一審宣判 賀建奎等三被告構(gòu)成非法行醫(yī)罪》,http://newS. cctv.com/ ARTI1G4z8Il DGxhxCUUF2Taw191230.shtml,2020 年12 月29 日訪問。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shè)的《刑法》第336 條之一規(guī)定:“將基因編輯、克隆的人類胚胎植入人體或者動物體內(nèi),或者將基因編輯、克隆的動物胚胎植入人體內(nèi),情節(jié)嚴(yán)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jié)特別嚴(yán)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這一規(guī)定既是對“基因編輯嬰兒”案的類型化規(guī)定,大體上也是對基因編輯行為構(gòu)成非法行醫(yī)罪的間接否定。
對比司法解釋與《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上述規(guī)定,對于從司法上的犯罪化到立法上的犯罪化的現(xiàn)象,大體可以看出以下幾點(diǎn)。
第一,面對新的法益侵害行為,刑事立法的反應(yīng)緩慢,導(dǎo)致司法解釋不得不“先行一步”:先由司法解釋將某種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經(jīng)過一段時間后,立法機(jī)關(guān)才將這種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可以認(rèn)為,部分司法解釋不僅成為了立法預(yù)備草案,而且成為了試行性質(zhì)的刑事法律。
第二,司法解釋所規(guī)定的行為不僅具有可罰性,而且發(fā)案率較高,一般預(yù)防的必要性較大。在此意義上說,司法上的犯罪化具有實(shí)質(zhì)根據(jù),正因?yàn)槿绱耍缎谭ㄐ拚福ㄊ唬穼⒈凰痉ń忉尫缸锘男袨榫鲈O(shè)為新的犯罪。
第三,司法上的犯罪化雖然有實(shí)質(zhì)根據(jù),但可能缺乏刑法分則的明文規(guī)定,于是,司法解釋利用刑法分則中缺乏明確性的罪名或者“口袋罪”進(jìn)行犯罪化。最典型的就是利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尋釁滋事罪。這是因?yàn)椋瑯?gòu)成要件越明確,就越容易判斷某種解釋是否屬于類推解釋;構(gòu)成要件越不明確,就越難以認(rèn)為某種解釋屬于類推解釋。〔9〕正因?yàn)槿绱耍鞔_性成為罪刑法定原則中規(guī)制立法機(jī)關(guān)的原則。例如,《懲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意見》規(guī)定:“故意傳播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病原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1.已經(jīng)確診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病原攜帶者,拒絕隔離治療或者隔離期未滿擅自脫離隔離治療,并進(jìn)入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2.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拒絕隔離治療或者隔離期未滿擅自脫離隔離治療,并進(jìn)入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顯然,難以認(rèn)為這一規(guī)定屬于類推解釋。尤其是在疫情暴發(fā)期間,人們可能認(rèn)為上述行為比放火、爆炸行為造成的危害更嚴(yán)重。但是,在《刑法》第330 條明確將構(gòu)成要件結(jié)果限定為“引起甲類傳染病傳播或者有傳播嚴(yán)重危險”,而新冠病毒性肺炎并非甲類傳染病,只是對之采取甲類傳染病預(yù)防、控制措施的情形下,《懲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意見》對引起新冠病毒性肺炎傳播或者有傳播嚴(yán)重危險的行為規(guī)定“以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定罪處罰”,便屬于類推解釋。不僅如此,即使是關(guān)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的司法解釋,也難以排除類推解釋的重大嫌疑。例如,《審理高空拋物案件意見》的上述規(guī)定,看似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因?yàn)橹挥挟?dāng)高空拋物行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時,才能認(rèn)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然而,在高空拋物的行為不可能像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zhì)那樣危害公共安全的前提下,〔10〕如果高空拋物行為引起火災(zāi)或者爆炸,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放火罪或者爆炸罪,而不可能認(rèn)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即使設(shè)想出可以構(gòu)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情形,也完全能夠認(rèn)定為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破壞交通設(shè)施等罪。《審理高空拋物案件意見》的上述規(guī)定,必然導(dǎo)致下級司法機(jī)關(guān)忽略“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要求進(jìn)行認(rèn)定,事實(shí)上下級司法機(jī)關(guān)的做法也的確如此。〔11〕參見張明楷:《高空拋物案的刑法學(xué)分析》,載《法學(xué)評論》2020 年第3 期,第12-26 頁。《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分則第六章增設(shè)高空拋物罪,便基本上否認(rèn)了高空拋物行為對公共安全的危害,〔12〕至少可以認(rèn)為,高空拋物行為通常不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因而是對《審理高空拋物案件意見》上述規(guī)定的明確否認(rèn)。
第四,司法上的犯罪化大多表現(xiàn)為將相對輕微的法益侵害行為按較重的犯罪處罰,導(dǎo)致罪刑不均衡。例如,根據(jù)《懲治妨害安全駕駛意見》與《審理高空拋物案件意見》,對沒有造成人員傷亡與財產(chǎn)損失的妨害安全駕駛行為與高空拋物行為,也必須判處3 年以上有期徒刑(有減輕處罰情節(jié)的除外)。〔13〕由于罪刑明顯不均衡,“司法機(jī)關(guān)屢屢突破最低刑為3 年的底線。此種突破可謂費(fèi)盡心思尋找給犯罪人減輕的理由,但最終結(jié)果大抵也只能是認(rèn)罪認(rèn)罰獲得被害人諒解之類柔軟說理”(參見趙香如:《論高空拋物犯罪的罪刑規(guī)范構(gòu)造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為背景》,載《法治研究》2020 年第6 期,第55-69 頁)。正因?yàn)槿绱耍缎谭ㄐ拚福ㄊ唬穼⑺痉ń忉屢?guī)定按較重犯罪處罰的行為,增設(shè)為處罰較輕的新罪。這也從一個側(cè)面表明,我國刑法分則規(guī)定的法定刑過重,同時也嚴(yán)重缺少對輕罪的規(guī)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對司法解釋的確認(rèn)與否認(rèn)現(xiàn)象,產(chǎn)生了兩個本文所要解決的顯著問題。
第一,如何避免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作出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類推解釋?表面上看,司法解釋先進(jìn)行司法上的犯罪化,再由刑事立法對司法解釋的犯罪化規(guī)定予以肯定,似乎合情合理。然而,由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對司法解釋規(guī)定以犯罪論處的行為另行設(shè)立新罪,故實(shí)際上否定了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概言之,從文字表述上看,不管《刑法修正案(十一)》是確認(rèn)了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內(nèi)容,還是否認(rèn)了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內(nèi)容,抑或修改了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內(nèi)容(部分確認(rèn)與部分否認(rèn)),都應(yīng)當(dāng)認(rèn)為《刑法修正案(十一)》就司法解釋規(guī)定的行為另設(shè)新罪的做法,間接乃至直接表明相應(yīng)的司法解釋是類推解釋:(1)如果《刑法修正案(十一)》以設(shè)立新罪的方式將司法解釋的內(nèi)容直接納入刑法分則(可謂確認(rèn)司法解釋),表明該犯罪原本并無刑法的明文規(guī)定,故該司法解釋屬于類推解釋。例如,前述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指導(dǎo)案例104 號中的被告人的行為,原本沒有破壞計算機(jī)信息系統(tǒng)本身,只是偽造環(huán)境質(zhì)量監(jiān)測數(shù)據(jù),但行為主體又不符合《刑法》第229 條的規(guī)定,故《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了第229 條的行為主體,使上述行為符合第229 條的構(gòu)成要件。這表面上是確認(rèn)了司法解釋,實(shí)際上表明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超越了司法解釋的權(quán)限。亦即,刑事立法在新增的或者修改的刑法條文中對司法解釋的確認(rèn)只是表面現(xiàn)象,實(shí)質(zhì)上都是對司法解釋的否認(rèn)。如果《刑法修正案(十一)》否認(rèn)了或者部分否認(rèn)了司法解釋,同樣表明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不能得到立法機(jī)關(guān)的認(rèn)可,而不認(rèn)可的原因,也是司法解釋規(guī)定以特定犯罪(如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的行為(如《審理高空拋物案件意見》規(guī)定的高空拋物行為)原本不屬于刑法明文規(guī)定的特定犯罪。反過來說,司法解釋規(guī)定對某種行為不以犯罪論處,而刑事立法反而將這種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的現(xiàn)象,就表明司法解釋堅持了罪刑法定原則。〔14〕眾所周知,20 世紀(jì)初的德國帝國法院認(rèn)為電不是有體物,進(jìn)而否認(rèn)竊電行為構(gòu)成盜竊罪(行為對象只能是可以移動的有體物),從而導(dǎo)致立法機(jī)關(guān)在刑法中增加“電也視為財物”或者增加盜竊電能罪之類的規(guī)定,這便說明德國帝國法院堅持了罪刑法定原則。當(dāng)然,如果電確實(shí)是有體物,則德國帝國法院的判決殊為不當(dāng)。(2)當(dāng)司法解釋規(guī)定的某種行為符合刑法分則條文的兜底規(guī)定,而刑事立法在相關(guān)法條中將該行為規(guī)定為獨(dú)立的行為類型時,不能認(rèn)為司法解釋屬于類推解釋。例如,《刑法》第182 條第1 款規(guī)定了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的三種行為類型,同時存在“以其他方法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的”兜底規(guī)定。2018 年7 月3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印發(fā)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批指導(dǎo)性案例的通知》(檢例第39 號·朱煒明操縱證券市場案)指出:“證券公司、證券咨詢機(jī)構(gòu)、專業(yè)中介機(jī)構(gòu)及其工作人員違背從業(yè)禁止規(guī)定,買賣或者持有證券,并在對相關(guān)證券作出公開評價、預(yù)測或者投資建議后,通過預(yù)期的市場波動反向操作,謀取利益,情節(jié)嚴(yán)重的,以操縱證券市場罪追究其刑事責(zé)任。”雖然《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182 條中增加了“對證券、證券發(fā)行人、期貨交易標(biāo)的公開作出評價、預(yù)測或者投資建議,同時進(jìn)行反向證券交易或者相關(guān)期貨交易的”這一行為類型,但由于指導(dǎo)性案例所規(guī)定的這種行為屬于“以其他方法操縱證券市場”,故不屬于類推解釋。換言之,這種情形下刑事立法對司法解釋的確認(rèn),才是真正的確認(rèn)而不是否認(rèn)。不過,《刑法修正案(十一)》所增加的行為類型,大多不是如此。(3)《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shè)新罪的法條,只要不是相對于普通法條的特殊法條,就意味著司法解釋規(guī)定以犯罪論處的行為原本不成立犯罪,因而可以認(rèn)為司法解釋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換言之,若某種行為原本符合刑法分則A 法條規(guī)定的構(gòu)成要件,但《刑法修正案(十一)》認(rèn)為適用A 法條導(dǎo)致量刑過重或者過輕,因而將該行為獨(dú)立出來,形成特別法條,則司法解釋并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可能違反罪刑相適應(yīng)原則)。但事實(shí)上,《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shè)新罪的法條,大多不是特別法條。〔15〕《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shè)的《刑法》第355 條之一,可謂特別法條(減輕構(gòu)成要件)。這便意味著被刑事立法變更規(guī)定的司法解釋,存在類推解釋的現(xiàn)象。反過來說,如果司法解釋不存在類推解釋的現(xiàn)象,那么《刑法修正案(十一)》就根本沒有必要對司法解釋規(guī)定的犯罪增設(shè)新的、法定刑較輕的法條。(4)《立法法》第45 條規(guī)定:“法律解釋權(quán)屬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法律有以下情況之一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解釋:(一)法律的規(guī)定需要進(jìn)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現(xiàn)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jù)的。”與此相對應(yīng),《刑法》第114 條與第115 條所規(guī)定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原本就缺乏明確性,因而需要進(jìn)一步明確其具體含義。于是,在該規(guī)定沒有被廢除的情況下,對哪些行為可以適用該規(guī)定,應(yīng)當(dāng)由立法機(jī)關(guān)進(jìn)行解釋。引起新冠病毒性肺炎傳播是刑法制定后出現(xiàn)的新情況(因?yàn)樾鹿诓《拘苑窝撞粚儆诩最悅魅静。谭ㄅc行政法規(guī)原本沒有規(guī)定,需要由立法機(jī)關(guān)明確適用刑法的依據(jù)。概言之,不管刑法學(xué)者如何判斷,從《刑法修正案(十一)》對司法解釋的“確認(rèn)”或者否認(rèn)就可以看出,司法解釋存在類推解釋的現(xiàn)象。但是,司法解釋又不得進(jìn)行類推解釋,否則就是以司法解釋的形式造法,這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所以,如何避免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作出類推解釋,是當(dāng)下及今后都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第二,如何處理司法犯罪化后刑事立法變更的相關(guān)案件?亦即,根據(jù)從舊兼從輕的原則,對于《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的行為,按司法解釋會以重罪處理,而按《刑法修正案(十一)》只能以輕罪處理的,應(yīng)當(dāng)如何適用刑法?例如,對于2021 年3 月1 日前發(fā)生的沒有造成人員傷亡與財產(chǎn)毀壞的高空拋物行為,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公布后(2021 年3 月1 日之前及之后),應(yīng)當(dāng)如何處理?如若在2021 年3 月1 日之前仍然按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認(rèn)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此之后按《刑法修正案(十一)》認(rèn)定為高空拋物罪,則明顯不公平;如若均等到2021 年3 月1 日后一概按《刑法修正案(十一)》處理,是否違反了從舊兼從輕原則?這是當(dāng)下必須解決的具體問題。
二、從緩慢修改刑法到迅速增設(shè)新罪
從前文可以看出,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作出的司法解釋,進(jìn)行司法上的犯罪化后實(shí)際上卻被刑事立法所否認(rèn),顯得“吃力不討好”。不僅如此,司法上的犯罪化被刑事立法“確認(rèn)”或者否認(rèn),有損罪刑法定原則的貫徹,不僅有損國民的預(yù)測可能性,而且影響刑事立法及司法解釋的權(quán)威性,應(yīng)當(dāng)盡可能避免。
以往的刑法理論大多期待司法解釋不進(jìn)行類推解釋。但近些年來的刑事立法與司法實(shí)踐似乎表明,在我國,只要刑法存在明顯漏洞和不明確的法條,要讓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恪守罪刑法定原則,完全不作出類推解釋,就幾乎不大可能,或者說實(shí)在強(qiáng)人所難。〔16〕或許學(xué)者們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diǎn),但在著書立說時,只是習(xí)慣于批判其他學(xué)者的類推解釋,而基本不批判司法解釋中的類推解釋。
中國社會已從傳統(tǒng)的熟人社會演變?yōu)槟吧松鐣@造成非正式的社會統(tǒng)制力減弱,對行為的規(guī)制弛緩,于是,人民群眾強(qiáng)烈要求將現(xiàn)實(shí)發(fā)生的法益侵害行為作為犯罪處理。正如德國學(xué)者所描述的那樣:“對公眾與大部分政治家來說,刑法已然成為了應(yīng)對各種不受歡迎的發(fā)展的萬能手段。”〔17〕[德]埃里克·希爾根多夫:《德國刑法學(xué):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江溯、黃笑巖等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 年版,第35 頁。但是,人民群眾一般不會閱讀刑法典,也不一定具有罪刑法定主義的觀念,大多習(xí)慣于強(qiáng)烈呼吁司法機(jī)關(guān)將某種危害行為以犯罪論處。于是,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便面臨著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一個法無明文規(guī)定的“犯罪”,卻要讓司法機(jī)關(guān)“依法”以犯罪論處,這對于司法機(jī)關(guān)來說的確棘手。“有一個古老的法律格言——棘手的案件制造惡法;這句話的意思是,案由越是讓人同情,我們就越容易為了一個特定的結(jié)果而給予救濟(jì),有時法律就因此遭到破壞。”〔18〕[美]邁克爾·利夫、米切爾·考德威爾:《搖搖欲墜的哭墻》,潘偉杰等譯,新星出版社2006 年版,第25 頁。在我國,可謂“棘手的案件制造類推解釋”。雖然日本法官三宅正太郎在就任法務(wù)省副大臣時給后輩法官留下的警言是:“法的解釋莫過于被社會輿論壓倒時危險,對法的捍衛(wèi)也沒有比此時更為重要。”〔19〕[日]山本祐司:《最高裁物語》,孫占坤、祁玫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 年版,第16 頁。但在執(zhí)法為民、司法為民的我國,要讓司法機(jī)關(guān)頂住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可能并不現(xiàn)實(shí)。平野龍一教授所稱的適用刑法面臨的第一個危險——“一旦發(fā)生引起人心沖動的案件,感情上便產(chǎn)生處罰的強(qiáng)烈要求,即使法律沒有規(guī)定處罰該行為,也要予以處罰”〔20〕[日]平野龍一:《刑法總論I》,有斐閣1972 年版,第90 頁。——在我國容易現(xiàn)實(shí)化。
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不僅面臨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而且面臨社會需求的巨大壓力。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變化,人民群眾的生活主要依賴脆弱的技術(shù)手段,個人行為所具有的潛在危險也飛躍性地增大,人們不知瞬間會發(fā)生何種災(zāi)難。〔21〕參見[日]井田良:《刑事立法の活性化とそのゆくえ》,載《法律時報》2003 年第2 號,第4 頁。人與人之間傳統(tǒng)的交往關(guān)系并不密切,但事實(shí)上越來越相互依賴,一個人的行為不再只是對個別人的利益產(chǎn)生影響,而是會影響不特定多數(shù)人的利益。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對具有嚴(yán)重危害的行為,不可能熟視無睹。在“關(guān)注需求的原則”與“關(guān)注理想的原則”之間,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不得不選擇前者。而且,在現(xiàn)行立法體例下,尤其是在刑法規(guī)定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情況下,面對一些產(chǎn)生不確定危險的行為,某些類推解釋反而減輕了對被告人的處罰。例如,倘若對于拒絕執(zhí)行衛(wèi)生防疫機(jī)構(gòu)依照傳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狀病毒傳播或者有嚴(yán)重傳播危險的行為,司法解釋不是類推解釋為以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定罪處罰,恐怕就只能按(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22〕對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2003 年5 月14 日公布的《關(guān)于辦理妨害預(yù)防、控制突發(fā)傳染病疫情等災(zāi)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可以發(fā)現(xiàn),《懲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意見》因?yàn)榇嬖谝苑梁魅静》乐巫锒ㄗ锾幜P的類推解釋,因此限制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成立范圍。導(dǎo)致行為人遭受更嚴(yán)厲的處罰。〔23〕再如,倘若不認(rèn)為危險駕駛罪包括醉酒駕駛航空器(至于是擴(kuò)大解釋還是類推解釋,則必然存在爭議),對這種行為必然會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責(zé)任。
不得不聲明的是,筆者并非為類推解釋辯護(hù),也不認(rèn)為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缺乏罪刑法定主義觀念,更不認(rèn)為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未能區(qū)分類推解釋與擴(kuò)大解釋,而是承認(rèn)在此問題上實(shí)務(wù)界與理論界的距離。正如惹尼(F. Gény)所言:“從事實(shí)務(wù)者,面對著具體的現(xiàn)實(shí),要他為維持法律上的邏輯而犧牲衡平或事物的需要,常覺為難。至于純粹的法學(xué)家,超然于事實(shí)及實(shí)際需要之上,忠于其方法,寧愿固守其原則推演出的結(jié)果。”簡言之,“實(shí)務(wù)方面多傾向衡平,而學(xué)說方面,則傾向于維持既定原則。”〔24〕轉(zhuǎn)引自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潮與中國固有文化》,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5 年版,第321-322 頁。并不直接面對社會輿論與社會需求壓力的刑法學(xué)者,大多愿意選擇“關(guān)注理想的原則”,期待司法機(jī)關(guān)對法無明文規(guī)定的嚴(yán)重法益侵害行為宣告無罪,從而歡呼罪刑法定原則的偉大勝利。可在社會生活事實(shí)變化迅速、刑事立法活動明顯緩慢、立法內(nèi)容相對滯后的當(dāng)下,面臨著各種巨大壓力的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不得不將保護(hù)法益的任務(wù)放在首位,在司法犯罪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被稱為類推解釋的現(xiàn)象。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這種先由司法機(jī)關(guān)進(jìn)行類推解釋,再由立法機(jī)關(guān)修改刑法增設(shè)新罪的做法,畢竟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不能得到認(rèn)可,更不應(yīng)當(dāng)成為常態(tài),而是需要盡可能克服。
本文的看法是,與其期待司法機(jī)關(guān)不進(jìn)行類推解釋,不如期待立法機(jī)關(guān)積極修改刑法、迅速增設(shè)新罪。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刑事立法緩慢導(dǎo)致刑法內(nèi)容滯后,不僅司法機(jī)關(guān)面臨巨大壓力(國民強(qiáng)烈要求司法機(jī)關(guān)處罰犯罪),而且立法機(jī)關(guān)也面臨巨大壓力。因?yàn)槿嗣袢罕姷陌踩虮Wo(hù)的要求,現(xiàn)在通過媒體更直接、更強(qiáng)烈、更及時地反映至立法機(jī)關(guān);國家對人民群眾的刑法保護(hù),成為一項(xiàng)公共服務(wù)內(nèi)容。〔25〕同前注〔21〕,井田良文。反之,如果立法機(jī)關(guān)積極修改刑法、迅速增設(shè)新罪,立法機(jī)關(guān)與司法機(jī)關(guān)都減輕了壓力,充其量只是立法機(jī)關(guān)可能就刑事立法活動本身存在內(nèi)在壓力,〔26〕或許工作要更忙一些,效率要更高一些,但工作總量并沒有增加。而非外部壓力。根據(jù)帕累托最優(yōu)測試,在迅速立法不僅使司法機(jī)關(guān)的狀況變好,而且也沒有使立法機(jī)關(guān)的狀況變得更糟(其實(shí)也是變好了)的情況下,應(yīng)當(dāng)選擇迅速立法。所以,就罪刑法定原則的貫徹而言,當(dāng)下需要的是刑事立法的改變。亦即,刑事立法沒有必要讓司法解釋為刑事立法準(zhǔn)備素材、提供經(jīng)驗(yàn),更不能將司法解釋當(dāng)作預(yù)備立法或試行性質(zhì)的法律,而是要積極修改刑法、迅速增設(shè)新罪。只有這樣,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才能作出真正的司法解釋,避免類推解釋,維護(hù)罪刑法定原則。
第一,在現(xiàn)行刑法原本缺乏類型性的情況下,幾年才出臺一個刑法修正案的做法,已經(jīng)明顯落后于復(fù)雜多變的時代。本文的建議是,立法機(jī)關(guān)應(yīng)當(dāng)從幾年通過一個刑法修正案的模式轉(zhuǎn)變?yōu)橐荒晖ㄟ^幾個刑法修正案的模式,如同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一年出臺幾個司法解釋一樣。
誠然,追求刑法的穩(wěn)定性一直是我國立法機(jī)關(guān)與刑法學(xué)者的基本態(tài)度與觀點(diǎn)。例如,立法機(jī)關(guān)的工作人員指出:“刑法過于頻繁的調(diào)整與修改,或者過多地干預(yù)社會和經(jīng)濟(jì)生活,也容易使社會成員的行為過于拘謹(jǐn),不利于最大限度地調(diào)動他們的積極性和發(fā)揮他們的創(chuàng)造力,影響社會活力。”〔27〕郎勝:《在構(gòu)建和諧社會的語境下談我國刑法立法的積極與謹(jǐn)慎》,載《法學(xué)家》2007 年第5 期,第62 頁。刑法學(xué)者指出:“刑事立法的活性化,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傳統(tǒng)罪刑法定原則所強(qiáng)調(diào)的刑法的安定性、穩(wěn)定性。”〔28〕孫國祥:《新時代刑法發(fā)展的基本立場》,載《法學(xué)家》2019 年第6 期,第3 頁。然而,在當(dāng)今這個復(fù)雜多變的社會中,根本不可能像在過去的傳統(tǒng)社會里那樣,強(qiáng)調(diào)刑法的穩(wěn)定性。
在傳統(tǒng)社會,由于媒體不發(fā)達(dá),國民文化水平相對低下,立法信息難以傳播到全體國民,因而需要強(qiáng)調(diào)刑法的穩(wěn)定性。但是,當(dāng)今社會各種媒體極為發(fā)達(dá),國民文化水平明顯提高,而且任何機(jī)關(guān)、媒體都在積極傳播國家法律。今天頒布的法律,國民今天就可以知道。所以在當(dāng)今社會,頻繁修改刑法、迅速增設(shè)新罪不會侵害國民的預(yù)測可能性,增設(shè)新罪不可能使社會成員的行為過于拘謹(jǐn),更不會影響社會活力。所以,過于強(qiáng)調(diào)刑法的穩(wěn)定性,已經(jīng)是一種落后的觀念。〔29〕參見張明楷:《增設(shè)新罪的觀念——對積極刑法觀的支持》,載《現(xiàn)代法學(xué)》2020 年第5 期,第160-161 頁。此外,刑法的穩(wěn)定性本身并不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內(nèi)容,罪刑法定原則強(qiáng)調(diào)的是尊重國民的自由,其前提是確保國民的預(yù)測可能性。如上所述,在當(dāng)今社會,迅速修改刑法不會損害國民的預(yù)測可能性,因而不存在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問題。況且,罪刑法定原則的思想基礎(chǔ)是民主主義與尊重人權(quán)主義。根據(jù)國民的意愿積極修改刑法、迅速增設(shè)新罪,不會違反人民群眾的意志;刑法修正案在草案階段就向全體國民公布,在頒布后經(jīng)過一段時間才開始施行的做法,不會違反尊重人權(quán)主義。
國外的刑事立法動態(tài)也說明了這一點(diǎn)。例如,在20 世紀(jì)80 年代末之前,日本立法機(jī)關(guān)“像金字塔一樣沉默”,〔30〕[日]松尾浩也:《刑事法學(xué)の地平》,有斐閣2006 年版,第48 頁。刑法修改相當(dāng)緩慢。〔31〕日本現(xiàn)行刑法典于1907 年頒布,1908 年10 月1 日起施行。“二戰(zhàn)”前僅修改了2 次(1921 年、1941 年);“二戰(zhàn)”后至1980 年修改了8 次(1947 年、1953 年、1954 年、1958 年、1960 年、1964 年、1968 年、1980 年)。“對于當(dāng)時的社會產(chǎn)生的當(dāng)罰的社會脫軌行為,都是通過對刑法的柔軟的解釋、適用來應(yīng)對的,這是日本刑事司法的一個特色。”〔32〕[日]曾根威彥:《現(xiàn)代の刑事立法と刑法理論》,載《刑事法ジャ-ナル》2005 年第1 號,第7 頁。但從20 世紀(jì)80 年代末開始,日本已從刑事立法的穩(wěn)定化轉(zhuǎn)向了刑事立法的活性化,立法機(jī)關(guān)已不再像以往那樣沉默,而是頻繁地修改刑法典。其中,一年兩三次修改刑法典,對一個法條反復(fù)修改,對某類犯罪進(jìn)行大幅度修改,一次修改時在刑法典分則中增加一章的現(xiàn)象,已經(jīng)司空見慣。除了對刑法典的修改外,日本立法機(jī)關(guān)還頻繁修改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33〕參見張明楷:《日本刑法的發(fā)展及其啟示》,載《當(dāng)代法學(xué)》2006 年第1 期,第3-12 頁;張明楷:《日本刑法的修改及其重要問題》,載《國外社會科學(xué)》2019 年第4 期,第4-21 頁。
歐洲國家也是如此。“1951年至今,德國已經(jīng)頒布了56部《刑法修正案》 和6部《刑法改革法》……結(jié)合德國學(xué)者的統(tǒng)計,自1969 年到2019 年間,德國立法機(jī)關(guān)通過各種形式對《刑法典》進(jìn)行了202次修訂,所涉及的條文難以計數(shù),其間對眾多附屬刑法的修訂就更是不勝枚舉。”〔34〕王鋼:《德國近五十年刑事立法述評》,載《政治與法律》2020 年第3 期,第94-95 頁。刑法典中的不少條文被反復(fù)修改。〔35〕例如,《德國刑法典》第261 條關(guān)于洗錢罪的規(guī)定,在1992 年之后經(jīng)歷了20 多次的修訂。在英國,“在托尼·布萊爾執(zhí)政的十年,議會通過了455 部法案以及32 000 多件文件……工黨差不多一天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犯罪”。〔36〕[英]菲利普·約翰斯頓:《惡法:關(guān)于英國工黨執(zhí)政三十年期間法律之爆炸性分析》,范進(jìn)學(xué)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7 年版,第34 頁。1979 年后,匈牙利刑法典共經(jīng)歷了約120 次修改,“而其中僅在體制變革之后所作的修訂就超過了100 次”。〔37〕[匈]珀爾特·彼得主編:《匈牙利新〈刑法典〉述評》(第1-2 卷),郭曉晶、宋晨晨譯,上海社會科學(xué)院出版社2014 年版,序言第3 頁。
我國立法機(jī)關(guān)應(yīng)當(dāng)積極修改刑法,及時應(yīng)對新型犯罪。由于新型犯罪并不是經(jīng)過幾年才集中出現(xiàn),而是每年都會出現(xiàn),所以,沒有必要經(jīng)過幾年才出臺一個刑法修正案。與其5 年增加、修改50 個左右的刑法條文,不如每年增加、修改10 個左右的刑法條文;10 個左右的條文既可以由一個修正案規(guī)定,也可以由兩三個修正案規(guī)定。只要出現(xiàn)一種新類型的犯罪,立法機(jī)關(guān)就應(yīng)當(dāng)立即增設(shè)新罪。〔38〕雖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第29 條規(guī)定,“常務(wù)委員會會議由委員長召集,一般兩個月舉行一次”,但在特殊情況下,完全可能一個月舉行兩次,而且也可以修改這一規(guī)定。立法機(jī)關(guān)不必像《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九)》《刑法修正案(十一)》那樣,每次都大幅度修改刑法條文(當(dāng)然,也不排除有時會大幅度修改);〔39〕事實(shí)上,這種由人大常委會大幅度修改刑法的做法是否違反憲法,也不無疑問。而是應(yīng)當(dāng)像《刑法修正案(二)》《刑法修正案(五)》《刑法修正案(十)》那樣,每次僅修改一兩個法條或者增設(shè)一兩個新罪(當(dāng)然也可能稍多一點(diǎn))。
概言之,在當(dāng)今社會,應(yīng)當(dāng)成熟一個法條就通過一個法條,發(fā)現(xiàn)一個法條有缺陷就立即修改該法條。例如,在發(fā)放高利貸行為的危害性已經(jīng)充分顯現(xiàn)出來時,立法機(jī)關(guān)應(yīng)當(dāng)盡快將這種行為直接納入《刑法》第225 條或者增設(shè)發(fā)放高利貸罪;〔40〕當(dāng)然,本文并不認(rèn)為2019 年7 月23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發(fā)布的《關(guān)于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因?yàn)椤缎谭ā返?25 條第4 項(xiàng)的兜底規(guī)定原本就沒有明確的外延,只能認(rèn)為該項(xiàng)規(guī)定本身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在人民群眾要求保護(hù)“頭頂上的安全”時,立法機(jī)關(guān)應(yīng)當(dāng)迅速增設(shè)高空拋物罪。不僅如此,在具有重大、普遍危險性的危害行為突如其來的情況下,也不妨立即通過并不成熟卻足以遏制該危害行為的法條。例如,在新冠病毒性肺炎暴發(fā)后,立法機(jī)關(guān)完全可以而且應(yīng)該在第一時間修改《刑法》第330 條,使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構(gòu)成要件涵蓋妨害新冠病毒性肺炎預(yù)防、控制的危害行為。
第二,通過新增法條或者修改法條增設(shè)新罪時,必須注重類型性,而不能按個別案件描述構(gòu)成要件。〔41〕參見張明楷:《刑事立法的發(fā)展方向》,載《中國法學(xué)》2006 年第4 期,第18-37 頁。這是因?yàn)椋磦€別案件描述構(gòu)成要件,必然導(dǎo)致法條缺乏靈活性,使得構(gòu)成要件涵攝范圍過窄,難以適應(yīng)不斷變化的社會生活事實(shí)。正因?yàn)槿绱耍?975 年以來德國刑法發(fā)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是,使“刑法靈活化”〔42〕同前注〔17〕,埃里克·希爾根多夫書。。只有對構(gòu)成要件進(jìn)行類型化的描述,才會給司法解釋留下合理的適用空間,避免司法解釋類推適用刑法條文。
不可否認(rèn),《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某些法條試圖盡可能類型化。例如,《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的《刑法》第280 條之二前兩款規(guī)定:“盜用、冒用他人身份,頂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學(xué)歷教育入學(xué)資格、公務(wù)員錄用資格、就業(yè)安置待遇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組織、指使他人實(shí)施前款行為的,依照前款的規(guī)定從重處罰。”這一法條并非僅針對社會上反映強(qiáng)烈的“冒名頂替上大學(xué)”這一種情形作出規(guī)定,比較符合類型化立法的要求。〔43〕參見周光權(quán):《論通過增設(shè)輕罪實(shí)現(xiàn)妥當(dāng)?shù)奶幜P——積極刑法立法觀的再闡釋》,載《比較法研究》2020 年第6 期,第51 頁。但是,如果刑法不增設(shè)偽造、變造文書罪與使用偽造、變造的文書罪等高度類型化的犯罪,仍然難以避免處罰漏洞。例如,冒用他人身份參軍的行為,就不符合上述規(guī)定。再如,如果增設(shè)偽造、變造文書罪與使用偽造、變造的文書罪,〔44〕關(guān)于增設(shè)本罪的法理依據(jù)與條文設(shè)計,參見姚詩:《增設(shè)偽造、使用偽造的文書罪:法理根據(jù)與條文設(shè)計》,載《現(xiàn)代法學(xué)》2020 年第5 期,第167-181 頁。《刑法修正案(十一)》 增設(shè)的第142 條之一第1 款中的第3 項(xiàng)規(guī)定(“藥品申請注冊中提供虛假的證明、數(shù)據(jù)、資料、樣品或者采取其他欺騙手段的”)與第4 項(xiàng)規(guī)定(“編造生產(chǎn)、檢驗(yàn)記錄的”),就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不僅如此,《刑法》第229 條則既沒有存在的必要,也沒有修改的必要。
強(qiáng)調(diào)類型性并非放棄構(gòu)成要件的明確性,也不是否認(rèn)構(gòu)成要件的具體性,而是需要正確處理類型性與具體性的關(guān)系。本文的基本看法是,對于只能科處較輕刑罰的行為,盡可能注重類型性,避免處罰漏洞;〔45〕注重類型性并不等于大幅度降低犯罪門檻(依然可以設(shè)立“情節(jié)嚴(yán)重”之類的條件),只是意味著構(gòu)成要件應(yīng)盡可能涵攝所有值得科處刑罰的行為。對于需要科處加重(較重)刑罰的行為(包括加重犯),則盡可能注重具體性,限制加重處罰范圍。〔46〕同前注〔33〕,張明楷文,《日本刑法的修改及其重要問題》,第17-19 頁。對自然犯而言(如暴行、脅迫、強(qiáng)制、偽造文書、使用偽造的文書之類的行為),盡可能注重類型性;對行政犯而言(尤其是可能給社會帶來利益的經(jīng)濟(jì)行為),應(yīng)盡可能注重具體性,防止刑法處罰有利于社會的行為。就此而言,《刑法修正案(十一)》對《刑法》第338 條的修改,值得充分肯定。反之,《刑法修正案(十一)》所增設(shè)的第134 條之一,對“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輕罪作詳細(xì)描述,則未必可取。
此外,增設(shè)新罪也不一定需要增設(shè)新的法條,而是可以通過修改原有法條,使構(gòu)成要件具有類型性,進(jìn)而能夠涵攝新的行為類型。例如,《刑法》第260 條第1 款規(guī)定:“虐待家庭成員,情節(jié)惡劣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由于虐待的行為對象事實(shí)上不限于家庭成員,《刑法修正案(九)》增設(shè)了虐待被監(jiān)護(hù)、看護(hù)人罪。其實(shí),只要將第260 條中的“家庭成員”修改為“他人”即可,沒有必要增設(shè)此罪。〔47〕參見張明楷:《增設(shè)新罪的原則——對〈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修改意見》,載《政法論叢》2020 年第6 期,第9 頁。
第三,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嚴(yán)重犯罪均已規(guī)定在刑法中,將來增設(shè)的新罪基本上屬于輕罪,立法機(jī)關(guān)對輕罪應(yīng)當(dāng)規(guī)定較輕的法定刑。如果輕罪的構(gòu)成要件具有類型性,類推解釋就基本上可以避免;即使司法機(jī)關(guān)進(jìn)行類推適用,也不至于形成過重的處罰。換言之,在缺少輕罪的刑法體系中,類推解釋的消極后果必然更為嚴(yán)重;如果刑法增設(shè)大量輕罪,那么可以減少類推解釋,減輕類推解釋的消極后果,也減輕司法機(jī)關(guān)的壓力。〔48〕同前注〔43〕,周光權(quán)文,第12 頁。
例如,《刑法修正案(十一)》之所以將司法解釋規(guī)定的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的妨害安全駕駛行為、高空拋物行為增設(shè)為輕罪,不僅是為了制止司法解釋利用不明確的法條,而且是因?yàn)樾谭ǚ謩t原來沒有可利用的輕罪法條。倘若刑法分則規(guī)定了暴行罪、強(qiáng)制罪,那么對行駛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駕駛?cè)藛T使用暴力的行為至少成立暴行罪,搶控駕駛操縱裝置的行為至少成立強(qiáng)制罪,而不至于像司法解釋那樣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
立法機(jī)關(guān)大可不必?fù)?dān)心積極修改刑法、迅速增設(shè)輕罪會擴(kuò)大處罰范圍。一方面,對于缺乏處罰必要性的行為,司法機(jī)關(guān)不僅不會認(rèn)定為犯罪,反而會作限制解釋。例如,我國的司法解釋隨著經(jīng)濟(jì)形勢的變化,多次提高盜竊、詐騙等財產(chǎn)犯罪的定罪數(shù)額標(biāo)準(zhǔn)。又如,對于刑法分則并無情節(jié)嚴(yán)重要求的法條,司法解釋為了限制處罰范圍基本上都將情節(jié)嚴(yán)重規(guī)定為定罪標(biāo)準(zhǔn)。〔49〕如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刑訊逼供罪,暴力取證罪,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jī)關(guān)公文、證件、印章罪等,相關(guān)司法解釋對立案標(biāo)準(zhǔn)都進(jìn)行了限制解釋,提高了定罪標(biāo)準(zhǔn)。另一方面,即使司法解釋沒有進(jìn)行限制解釋,司法機(jī)關(guān)也會通過相對不起訴等路徑使輕微犯罪的行為人不受到刑罰處罰。況且,與國外刑法相比,無論我國刑事立法如何迅速增設(shè)新罪,處罰范圍都不可能超過國外,仍然能體現(xiàn)我國刑法控制刑罰處罰范圍的特色。
或許有人認(rèn)為,如果刑法迅速增設(shè)輕罪,而大多數(shù)輕罪卻不受刑罰處罰,不僅沒有意義,而且有損刑法的權(quán)威性。其實(shí),這種以懲罰犯罪人和維護(hù)刑法權(quán)威性為目的的觀念,并不妥當(dāng)。(1)國外實(shí)踐證明,在刑事立法上擴(kuò)大處罰范圍,在刑事司法上限制處罰范圍,〔50〕參見日本國法務(wù)省:《令和元年版犯罪白書》,http://hakusyo1.moj.go.jp/jp/66/nfm/mokuji.html,2020 年12 月27 日訪問;郭爍:《酌定不起訴制度的再考查》,載《中國法學(xué)》2018 年第3 期,第228-248 頁。使行為規(guī)范與裁判規(guī)范存在適當(dāng)分離的做法,有利于預(yù)防犯罪。〔51〕參見張明楷:《行為規(guī)范與裁判規(guī)范的分離》,載《中國社會科學(xué)報》2010 年11 月23 日,第10 版;同前注〔29〕,張明楷文;黎宏:《預(yù)防刑法觀的問題及其克服》,載《南大法學(xué)》2020 年第4 期,第1-21 頁。另參見田宏杰:《立法擴(kuò)張與司法限縮:刑法謙抑性的展開》,載《中國法學(xué)》2020 年第1 期,第166-183 頁。既然刑罰目的是預(yù)防犯罪,就沒有理由拒絕這樣的做法。認(rèn)為只有當(dāng)行為人受到了刑罰處罰才可能吸取教訓(xùn)不再犯罪,而對之作寬大處理其必然再犯罪的想法,不符合客觀事實(shí)。〔52〕遺憾的是,我國一直沒有《犯罪白皮書》,缺乏犯罪預(yù)防與制裁的系統(tǒng)數(shù)據(jù),導(dǎo)致一些具體刑事政策沒有實(shí)證數(shù)據(jù)支撐。這是一個相當(dāng)嚴(yán)重的問題,決策者應(yīng)當(dāng)高度重視。建議司法部每年出版一本不少于100 萬字的《犯罪白皮書》。輕微犯罪的行為人大多會對自己受到的寬大處理心存感激,避免再犯罪;與此相反的是,那些進(jìn)了監(jiān)獄的犯人反而容易成為累犯、再犯。〔53〕國外的實(shí)證研究已證明:“無論是初犯還是累犯,受到罰金處罰后的再犯率低于受到緩刑處理的再犯率”(參見[美]克萊門斯·巴特勒斯:《矯正導(dǎo)論》,孫曉靂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xué)出版社1991 年版,第128 頁)。我國司法機(jī)關(guān)應(yīng)當(dāng)對輕微犯罪人大量適用單處罰金。(2)即使是故意殺人犯,也可能因?yàn)槠涮幽浠蛘邆刹闄C(jī)關(guān)未能破案等,而不能被追究刑事責(zé)任。所以,要對所有的犯罪行為都定罪處刑,只是一種不切實(shí)際的幻想,而不是維護(hù)刑法權(quán)威的路徑。(3)依照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對輕微犯罪的行為人作寬大處理,也是依法辦事,并不會損害刑法的權(quán)威性。(4)類推解釋才是損害刑法權(quán)威性的做法。在刑法增設(shè)新罪后,認(rèn)定行為構(gòu)成犯罪但不處罰,比通過類推方法將行為認(rèn)定為犯罪好得多。
第四,立法機(jī)關(guān)應(yīng)當(dāng)廢除容易被類推解釋的法條,尤其要廢除《刑法》第114、115 條關(guān)于(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規(guī)定。這是因?yàn)椋嘘P(guān)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規(guī)定,不僅缺乏明確性,而且法定刑過重,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從司法實(shí)踐來看,缺乏明確性的法條容易被類推適用。如果不廢除這一罪名,那么就不可能確保罪刑法定原則的貫徹。
立法機(jī)關(guān)也不必?fù)?dān)心廢除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后會形成處罰漏洞。這是因?yàn)椋彩桥c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zhì)等相當(dāng)?shù)男袨椋豢赡芴幱诂F(xiàn)行刑法規(guī)制之外。換言之,行為人實(shí)施與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zhì)等相當(dāng)?shù)男袨椋瑹o論如何都會成立故意殺人(未遂)、故意傷害、〔54〕認(rèn)為殺害、傷害特定的個人才成立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殺害、傷害多人就不成立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的觀點(diǎn),既不符合刑法規(guī)定,也不符合當(dāng)今時代的基本觀念。故意毀壞財物等罪,而不可能逍遙法外。例如,2020 年3 月16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頒布的《關(guān)于辦理涉窨井蓋相關(guān)刑事案件的指導(dǎo)意見》(以下簡稱《辦理涉窨井蓋案件指導(dǎo)意見》)規(guī)定:“盜竊、破壞人員密集往來的非機(jī)動車道、人行道以及車站、碼頭、公園、廣場、學(xué)校、商業(yè)中心、廠區(qū)、社區(qū)、院落等生產(chǎn)生活、人員聚集場所的窨井蓋,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yán)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的規(guī)定,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然而,一方面,即使在上述地點(diǎn)盜竊窨井蓋,也不可能產(chǎn)生后果不能控制的公共危險,認(rèn)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不合適。另一方面,如果盜竊窨井蓋的行為致人傷亡,就可以認(rèn)定為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或者過失致人死亡罪、過失致人重傷罪;在沒有造成人員傷亡的情況下,首先考慮按盜竊罪處罰;如果不符合盜竊罪的構(gòu)成要件,〔55〕司法解釋應(yīng)當(dāng)就盜竊特定對象(如窨井蓋、消防器材等)的行為,規(guī)定較低的定罪數(shù)額標(biāo)準(zhǔn)。也屬于對道路的毀壞(道路當(dāng)然屬于財物),因而成立故意毀壞財物罪,這一點(diǎn)沒有疑問。〔56〕德國帝國法院曾認(rèn)定,被告人將樹木橫在道路上導(dǎo)致車輛不能通行的行為構(gòu)成故意毀壞財物罪(RGSt 74, 14)。窨井蓋是道路的一部分,盜竊道路上的窨井蓋的行為,更是對道路的毀壞。
總之,立法機(jī)關(guān)積極修改刑法、迅速增設(shè)新罪,是避免司法機(jī)關(guān)類推適用刑法的最佳路徑。在社會發(fā)展變化迅速的時代,立法機(jī)關(guān)更應(yīng)當(dāng)積極應(yīng)對新型犯罪,而不應(yīng)先期待司法解釋,再通過刑事立法“確認(rèn)”或者否認(rèn)司法解釋。
當(dāng)然,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也需要對司法解釋持克制態(tài)度。〔57〕參見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上),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1 年版,第6 頁以下。司法解釋對刑事立法作出貢獻(xiàn)的路徑,不是制作立法式的司法解釋,而應(yīng)通過罪名的確定、個案的解釋彌補(bǔ)不明確的刑法條文或者有缺陷的刑法條文,從而使刑事立法更為完善。〔58〕刑法中已有法條的完善路徑為:立法機(jī)關(guān)制定法條后,解釋者根據(jù)正義理念與文字表述,并聯(lián)系社會現(xiàn)實(shí)解釋刑法;在許多情況下,解釋者不得不對刑法用語作出與其字面含義不同的解釋(當(dāng)然應(yīng)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經(jīng)過一段時間后,立法機(jī)關(guān)會采納解釋者的意見,修改刑法的文字表述,使用更能實(shí)現(xiàn)正義理念的文字表述;然后,解釋者再根據(jù)正義理念與文字表述,聯(lián)系社會現(xiàn)實(shí)解釋刑法;再重復(fù)上面的過程。這種過程循環(huán)往復(fù),便使成文刑法更加完善,使司法不斷地追求和實(shí)現(xiàn)正義。這也是司法解釋與刑事立法良性互動的表現(xiàn)。
例如,司法解釋對刑法分則條文中兜底規(guī)定的具體解釋,就可以為構(gòu)成要件的明確性及將來的刑事立法作貢獻(xiàn)。前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例第39 號關(guān)于操縱證券市場案指導(dǎo)性案例的頒布,以及《刑法修正案(十一)》對第182 條行為類型的增加,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diǎn)。
再如,《刑法》第237 條規(guī)定了猥褻與侮辱兩種行為,刑法理論一直認(rèn)為,猥褻與侮辱具有不同含義,〔59〕參見高銘暄主編:《新編中國刑法學(xué)》(下冊),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8 年版,第702-703 頁;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xué)》,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版,第464 頁。司法解釋也將第237 條規(guī)定的犯罪確定為強(qiáng)制猥褻、侮辱(婦女)罪。然而,一旦將兩種行為并列起來,就需要解釋兩種行為的具體內(nèi)容,提出二者的區(qū)別。可是,各種區(qū)分都不合適或者不可能,只能給司法機(jī)關(guān)徒增麻煩。更為重要的是,不管是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還是之后,《刑法》第237 條第3 款都只規(guī)定了猥褻兒童一種行為。如果認(rèn)為必須區(qū)分猥褻與侮辱,必然造成以下兩種結(jié)局之一:其一,猥褻兒童的是犯罪行為,但侮辱兒童的不是犯罪行為;其二,猥褻兒童的行為是猥褻兒童罪,侮辱兒童的行為成立第246 條的侮辱罪(侵害名譽(yù)的犯罪)。這顯然不妥當(dāng)。
正是因?yàn)樾谭ɡ碚撆c司法解釋一直明確區(qū)分猥褻與侮辱,所以《刑法修正案(九)》僅將《刑法》第237 條中的猥褻對象修改為“他人”,但沒有刪除侮辱婦女的規(guī)定,也沒有將作為侮辱對象的“婦女”修改為“他人”。據(jù)此,有些屬于侵害婦女性自主權(quán)的侮辱行為不能歸入猥褻行為;有些屬于侵害男性性自主權(quán)的侮辱行為依然不能認(rèn)定為強(qiáng)制猥褻罪。顯然,從立法論上來說,《刑法修正案(九)》的修改并不成功。立法機(jī)關(guān)工作人員指出:“婦女、兒童雖然是猥褻行為的主要受害群體,但實(shí)踐中猥褻男性的情況也屢有發(fā)生,猥褻十四周歲以上男性的行為如何適用刑法并不明確,對此,社會有關(guān)方面多次建議和呼吁,要求擴(kuò)大猥褻罪適用范圍,包括猥褻十四周歲以上男性的行為,以同等保護(hù)男性的人身權(quán)利。因此,《刑法修正案(九)》將第一款罪狀中的‘猥褻婦女’修改為‘猥褻他人’,使該條保護(hù)的對象由婦女?dāng)U大到了年滿十四周歲男性。”“本款規(guī)定的‘侮辱婦女’,主要指對婦女實(shí)施猥褻行為以外的,損害婦女人格尊嚴(yán)的淫穢下流、傷風(fēng)敗俗的行為。例如,以多次偷剪婦女的發(fā)辮、衣服,向婦女身上潑灑腐蝕物、涂抹污物,故意向婦女顯露生殖器,追逐、堵截婦女等手段侮辱婦女的行為。”〔60〕臧鐵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解讀》,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 年版,第94-95 頁。這樣的說明顯然是以舊刑法時代的司法解釋為根據(jù)的。〔61〕1984 年11 月2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當(dāng)前辦理流氓案件中具體應(yīng)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指出:“侮辱婦女情節(jié)惡劣構(gòu)成流氓罪的,例如:1.追逐、堵截婦女造成惡劣影響,或者結(jié)伙、持械追逐、堵截婦女的;2.在公共場所多次偷剪婦女的發(fā)辮、衣服,向婦女身上潑灑腐蝕物,涂抹污物,或者在侮辱婦女時造成輕傷的;3.在公共場所故意向婦女顯露生殖器或者用生殖器頂擦婦女身體,屢教不改的;4.用淫穢行為或暴力、脅迫的手段,侮辱、猥褻婦女多人,或人數(shù)雖少,后果嚴(yán)重的,以及在公共場所公開猥褻婦女引起公憤的。”但是,舊刑法流氓罪中的侮辱婦女是對公共秩序的犯罪,現(xiàn)行刑法的強(qiáng)制侮辱罪是對個人法益的犯罪。原封不動地照搬舊刑法時代的司法解釋,明顯不當(dāng)。
總之,區(qū)分猥褻與侮辱的解釋不僅不能得出合理的結(jié)論,而且導(dǎo)致《刑法修正案(九)》未能妥當(dāng)?shù)匦薷摹缎谭ā返?37 條。如若司法解釋將《刑法》第237 條第1 款規(guī)定的犯罪僅歸納為強(qiáng)制猥褻罪,除強(qiáng)奸罪外,司法機(jī)關(guān)將以強(qiáng)制方法侵犯他人性自主權(quán)的行為均認(rèn)定為強(qiáng)制猥褻罪,《刑法修正案(九)》就可能刪除本款中“侮辱婦女”的規(guī)定。〔62〕參見張明楷:《刑法理論與刑事立法》,載《法學(xué)論壇》2017 年第6 期,第16-34 頁。
三、從適用司法解釋到適用刑法
如上所述,由于刑法缺少輕罪的明文規(guī)定,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頒布之前,司法解釋對一些行為直接類推適用處罰較重的法條,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頒布和施行后,對此前的相關(guān)行為如何處理,就成為一個具體問題。本文的基本觀點(diǎn)是,不應(yīng)當(dāng)再適用司法解釋,而應(yīng)適用《刑法修正案(十一)》頒布之前或者之后的刑法。
首先,對于發(fā)生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日(即2021 年3 月1 日)之前的高空拋物、妨害公共交通安全、催討高利貸等行為,如果是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審理的,應(yīng)當(dāng)如何處理?對此,應(yīng)當(dāng)區(qū)分兩種不同情形。
第一種情形是,某種行為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屬于刑法分則明文規(guī)定的犯罪,但《刑法修正案(十一)》是通過增設(shè)新罪降低該罪的處罰程度。基于從舊兼從輕原則的要求,對于2021 年3月1 日之前的行為,都應(yīng)當(dāng)適用《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規(guī)定。
例如,如果搶奪方向盤、變速桿等操縱裝置的行為危害交通安全,即使不成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可能成立劫持汽車罪,〔63〕如果不危害公共安全,也不構(gòu)成其他犯罪,則屬于下述第二種情形。那么,在《刑法修正案(十一)》 增設(shè)了《刑法》 第133 條之二之后,根據(jù)從舊兼從輕的原則,對于《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之前發(fā)生的上述行為,就應(yīng)當(dāng)適用《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規(guī)定追究刑事責(zé)任,而不應(yīng)適用《懲治妨害安全駕駛意見》。同樣,如果毆打駕駛?cè)藛T的行為符合尋釁滋事罪的構(gòu)成要件,也應(yīng)當(dāng)適用《刑法修正案(十一)》所增設(shè)的《刑法》第133條之二。〔64〕當(dāng)然,對此可能存在爭議,需要進(jìn)一步討論。其中涉及的主要問題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所設(shè)立的輕罪與刑法原有的相關(guān)犯罪,是想象競合關(guān)系還是法條競合關(guān)系?
第二種情形是,某種行為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并不屬于刑法明文規(guī)定的犯罪,但司法解釋規(guī)定對這種行為以犯罪論處,下級司法機(jī)關(guān)按司法解釋對這種行為予以追訴,《刑法修正案(十一)》卻將這種行為增設(shè)為新罪并規(guī)定了較低的法定刑。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對于此前的行為是應(yīng)當(dāng)適用《刑法修正案(十一)》按新罪處理,還是應(yīng)當(dāng)按行為時的刑法作無罪處理,必然存在爭論。
以高空拋物為例。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高空拋物行為造成人員傷亡、財物毀壞等結(jié)果,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之前就構(gòu)成相關(guān)犯罪的(不包括根據(jù)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的類推解釋構(gòu)成犯罪的情形),應(yīng)當(dāng)適用行為時的刑法,按相關(guān)犯罪處罰。這樣處理并不違反從舊兼從輕的原則,因?yàn)椤缎谭ㄐ拚福ㄊ唬吩鲈O(shè)的第291 條之二第2 款規(guī)定:“有前款行為,同時構(gòu)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據(jù)此,高空拋物行為致人死亡,且行為人對死亡具有故意的,成立故意殺人罪與高空拋物罪的想象競合。所以,即使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之前,也應(yīng)認(rèn)定為故意殺人罪。
如前所述,如果高空拋物行為不符合故意殺人、故意傷害、過失致人死亡、過失致人重傷、故意毀壞財物等罪的構(gòu)成要件,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并不構(gòu)成刑法明文規(guī)定的犯罪,那么認(rèn)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做法,就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這是因?yàn)椋缎谭ㄐ拚福ㄊ唬吩鲈O(shè)高空拋物罪并規(guī)定較輕的法定刑,是對《審理高空拋物案件意見》的否定。反過來說,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之前,刑法并不認(rèn)為高空拋物行為構(gòu)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其他犯罪。既然如此,根據(jù)從舊兼從輕的原則,對《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之前的不構(gòu)成其他犯罪的高空拋物行為,就不能追究刑事責(zé)任,更不能認(rèn)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不可否認(rèn)的是,本文的上述結(jié)論似乎不公平。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頒布之前,就有相當(dāng)多的高空拋物行為被認(rèn)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之后,對此前發(fā)生的相同行為不以犯罪論處,似乎顯得不公平。盡管如此,本文依然主張,對于《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之前實(shí)施的高空拋物行為,不得適用《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規(guī)定認(rèn)定有罪,而應(yīng)根據(jù)行為時的刑法宣告無罪,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其實(shí),對于法無明文規(guī)定的嚴(yán)重法益侵害行為不能定罪處罰,都不符合公平原則。但是,在刑法上,公平原則的貫徹以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為前提,或者說,只能在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下貫徹公平原則。在本文看來,如果要貫徹公平原則,妥當(dāng)?shù)淖龇ㄊ峭ㄟ^審判監(jiān)督程序?qū)ⅰ缎谭ㄐ拚福ㄊ唬分罢J(rèn)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高空拋物行為均改判為無罪。
再如,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頒布之前,司法機(jī)關(guān)對于以“軟暴力”催討高利貸的行為,均認(rèn)定為尋釁滋事罪。但是,這一做法與《刑法》第238 條第3 款的規(guī)定相沖突,明顯不當(dāng)。〔65〕同前注〔47〕,張明楷文。正因?yàn)槿绱耍缎谭ㄐ拚福ㄊ唬吩黾恿恕缎谭ā返?93 條之一,并規(guī)定了低于尋釁滋事罪的法定刑。基于前述理由,對于《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之前發(fā)生的以“軟暴力”催討高利貸的行為,不得適用《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規(guī)定認(rèn)定有罪,而應(yīng)宣告無罪。
其次,對于發(fā)生在2021 年3 月1 日之前的高空拋物、妨害公共交通安全、催討高利貸等行為,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審理的,應(yīng)當(dāng)如何處理?對此,也應(yīng)當(dāng)區(qū)分兩種不同情形。
第一種情形是,某種行為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屬于刑法明文規(guī)定的犯罪(不包括根據(jù)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的類推解釋構(gòu)成犯罪的情形),應(yīng)當(dāng)適用行為時的刑法,按相關(guān)犯罪處罰。
第二種情形是,某種行為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并不屬于刑法明文規(guī)定的犯罪,但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將這種行為類推解釋為犯罪,下級司法機(jī)關(guān)按司法解釋對這種行為予以追訴,《刑法修正案(十一)》卻增設(shè)新罪并規(guī)定了較低的法定刑。人民法院在2021 年3 月1 日之前審理這類案件的,是應(yīng)當(dāng)按行為時的刑法作無罪處理,還是適用《刑法修正案(十一)》按輕罪論處,抑或適用司法解釋,必然存在爭論。
例如,承擔(dān)環(huán)境監(jiān)測職責(zé)的中介組織的人員甲,于2020 年11 月1 日通過在計算機(jī)中修改參數(shù)或者監(jiān)測數(shù)據(jù),提供虛假的環(huán)境影響評價文件,情節(jié)嚴(yán)重。人民法院于2021 年2 月1 日審理該案件。雖然根據(jù)檢例第39 號指導(dǎo)性案件與《辦理環(huán)境污染案件解釋》,該行為構(gòu)成破壞計算機(jī)信息系統(tǒng)罪,但由于該解釋明顯屬于類推解釋,已被《刑法修正案(十一)》所否認(rèn),故人民法院不應(yīng)認(rèn)定甲的行為構(gòu)成破壞計算機(jī)信息系統(tǒng)罪,而應(yīng)按行為時的刑法宣告無罪。如果人民法院在2021 年3 月1 日后審理該案,也應(yīng)根據(jù)從舊兼從輕的原則宣告無罪。由此看來,為了維護(hù)罪刑法定原則,應(yīng)當(dāng)認(rèn)為,與《刑法修正案(十一)》相抵觸的司法解釋(即前述被歸入類推解釋的司法解釋),應(yīng)當(dāng)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頒布后(而非施行后)自然失效。〔66〕也可以認(rèn)為,《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頒布否定了與之相抵觸的司法解釋的效力。
再如,行為人乙于2020 年11 月1 日實(shí)施高空拋物行為,沒有造成人員傷亡的實(shí)害與危險,也沒有毀壞財物和恐嚇?biāo)耍怀闪⑿谭ㄒ?guī)定的任何犯罪。雖然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頒布之前被司法機(jī)關(guān)認(rèn)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根據(jù)罪刑法定原則,司法機(jī)關(guān)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頒布后,不能追究乙的刑事責(zé)任。
或許有人認(rèn)為,從舊兼從輕原則是為了確保國民的預(yù)測可能性,既然乙的行為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頒布前就被認(rèn)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且行為人通過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能夠認(rèn)識到行為的違法性,那么,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頒布后,采取從輕原則,對其行為適用《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規(guī)定按照高空拋物罪處理,并無不當(dāng)。
但本文難以贊成這種觀點(diǎn)。這是因?yàn)椋J(rèn)定乙的行為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頒布前就成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類推解釋的結(jié)論,但司法機(jī)關(guān)不能將類推解釋的結(jié)論作為判斷處罰輕重的依據(jù)。況且,作為責(zé)任要素的違法性認(rèn)識可能性,是指對行為違反刑法的認(rèn)識可能性,不是指對適用類推的司法解釋的違反具有認(rèn)識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