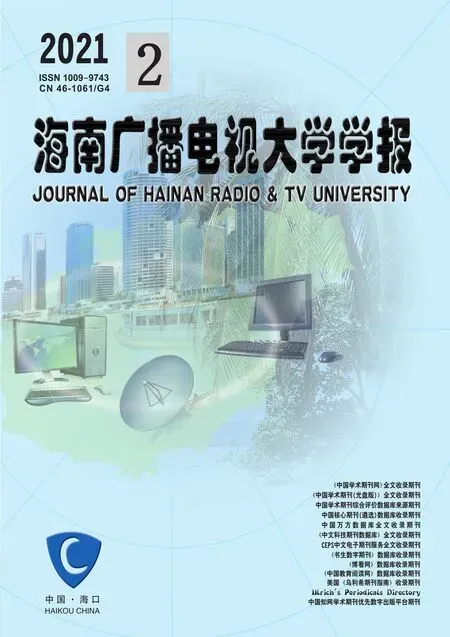論現代家庭倫理劇成功之道
——以電視劇《都挺好》為例
萬咪咪
(廣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4)
前 言
電視劇《都挺好》作為新時代家庭倫理劇典型代表至今熱度未褪,該劇彰顯著對傳統家庭倫理劇老舊模式的自覺超越和對當代倫理新秩序的審美體現。它跳脫毫無技巧、稀疏平常的生活流敘述模式,將其匠心獨運的藝術眼光聚焦于時代典型環境之下有關家庭文化變遷、性別意識較量等社會熱點問題,并透過對蘇姓人家家庭沖突的描繪來塑造藝術典型。二者相互融合,形成一個巨大的召喚結構,從而引發大眾熱議與其自覺填空行為。筆者試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對其成功之道進行分析,為當代家庭倫理劇轉型提供一定藝術啟示和經驗思考。
一、典型環境:時代的縮影與具體化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典型觀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深刻揭示了有關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的藝術問題。恩格斯在1888年《致瑪·哈克奈斯》的信中就哈克奈斯的中篇小說《城市姑娘》和對巴爾扎克創作的相關評論,集中闡述了他對文學藝術中現實主義的見解,他以唯物史觀的科學思考創造性地提出要“真實的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1)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頁。”這一重要見解。在信中,恩格斯表示“所謂現實主義的內涵不僅是要表現細節的真實,更要注重對典型環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這里的人物就其本身而言已足夠典型,但是環繞并促成這些人物行動的環境就不那么典型了(2)陸貴山,周忠厚:《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選講》 (第五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31頁。”。人物與環境相互依存,典型環境是人物生存其中并能深刻體現時代生活本質方面的環境。
(一)典型環境的呈現是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有機統一
就自然環境而言,多指促成人物行動的景物氣候、空間地域等實際環境;社會環境則指人物生存其中并得以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反映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總體形態的環境。二者相互協調,構成接受者對作品空間環境的主觀性感知與詩藝性創造。在電視劇《都挺好》中,故事是以蘇家老宅為自然環境鋪敘開來的,位于蘇州同德里的老宅承載著蘇家全體成員的集體記憶,那灰褐色的瓦礫,斑駁的墻體,狹長的胡同和幽深的天井無不見證著蘇家過往的歷史,他作為記憶空間的存在揭示了蘇家內在矛盾的根源所在。正是通過這個家庭場域的具象呈現,我們認識到蘇母趙美蘭重男輕女、偏心強勢的典型性格,為了給蘇家兄弟創造良好的生存環境,她肆意剝奪蘇家小妹明玉的生存資源,間接成為導致蘇家兄妹反目成仇、矛盾深厚的始作俑者,于此,表面風光、令人艷羨的家庭背后涌動的滾滾暗潮躍然熒幕之上。其次,劇中不僅利用自然環境映射矛盾根源,還使得都市職場成為社會環境的鏡像呈現。蘇明玉作為老蒙的得力干將在眾誠集團身居高位,其果敢剛毅的精英白領形象深入人心,但其剪不斷理還亂的家庭糾紛同職場應接不暇的工作任務相遇時,也時常令她焦頭爛額。公司內部明爭暗斗,家庭內部分崩支離,兩個場域相互交錯,共同勾勒出現代職場人在面對家庭糾紛與工作問題時的生存狀態與精神困境。
(二)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典型統一是時代歷史的縮影與具體化
環境的典型性呈現并非一系列生搬硬造的情節構造,也不是毫無生氣的描摹客觀現實的本來面貌,典型環境作為特定場域的存在不僅是促成人物行動、營造文本內部環境的客觀條件,還蘊含著對文本外部世界的現實映射。恩格斯在揭示“典型”的內在本質時,尤其注重對文本的現實品格與歷史品格的塑造,要求以獨特、鮮明的具體環境去反映現實社會大環境中的必然規律,表現出一定階級、歷史時期的社會內蘊,從而達到以局部反映整體,以個性彰顯共性、以現象凸顯本質、以微知著的藝術效果。正所謂,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家作為社會組織的最小構成單位,其成員的生存狀態、價值觀念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對社會存在的直接反映。《都挺好》作為一部現實題材的影視作品扼住了時代脈搏,它并未停留在對家長里短的表面敘述,而是引發了大眾關于“家庭”內涵的深度思考,電視劇透過對蘇姓小家內部矛盾的大膽陳述直面社會痛點,其議題涵蓋了教育、經濟、住房、養老責任等方方面面。首先,就養老問題看來,傳統養老觀念與現代價值產生了強烈沖突。長久以來,中國傳統的養老理念便是通過“互養”途徑形成的反饋模式,父輩作為資源優勢方承擔著對未成年子女的養育責任,子女成人后便接續這種模式,肩負著贍養父母的重任。然而,在社會進入后工業時代后,父輩隨家庭經濟主導地位的轉移,逐漸喪失了家庭核心主導權,開始出現養老焦慮。他們將同子女的溝通策略轉換為“以情感為主的溝通(3)袁一民:《養老焦慮與城市再融入——電視劇《都挺好》中的老年人口社會問題》,《中國電視》2020年第1期。”,以一種異化形式揮霍著子女的耐心來表現自我需求,證明自我的家庭地位,基于此,生活中便開始出現了一個個“蘇大強式的作精父親”。同時,由于老年人情緒的過度釋放也使得子女面臨忠孝兩難困境。劇中蘇明哲虛榮自大,為了對蘇父盡孝,滿足蘇父買大房子的心愿而多次舍小家為蘇姓大家,后經濟實力不允,蘇父便開始責備明哲不守信用。另一邊,為了盡量守諾,明哲無度降低其妻子吳非與其女兒小咪的生活質量,導致吳非陷入一種喪偶式婚姻境地,萬般無奈下吳非便提出離婚。一邊是生養自己的父親,一邊是相濡以沫的妻子,明哲所糾結的、渴望協調卻又無能為力的問題也正是時下年輕一代在贍養父母的過程中所兩難的。
(三)就教育問題而言,《都挺好》直面現代社會由于原生家庭之殤給子女帶來的心靈創傷而引發的家庭沖突
蘇家兄妹之間苦大仇深、無可消解的恩怨矛盾、他們各自的性格弊病都來源于其父母的區別對待和教育差錯。蘇母作為飽受原生家庭無度控制和索取的犧牲品,在其成為父母后又變成了維護這種“重男輕女”畸形邏輯的衛道士。她強勢霸道,極力壓榨明玉的生存資源,為了滿足兒子外出旅游的虛榮心,可以狠心拒絕女兒想買一本練習題的卑微請求;為了老大蘇明哲出國留學她賣了一間房,為了老二蘇明成結婚又賣了一間房,然而對于明玉,蘇母從來都是冷眼以對,全然不顧明玉渴望守護自己獨立空間的希冀,亦能罔顧明玉費盡辛苦渴望考上名校的夢想,且自作主張、肆意安排她的志愿,美其名曰一切都是為了你好。這樁樁件件并非隨意捏造的戲劇虛構,這種“重男輕女”“一切都是為了你好”的教育理念早早便在許多家庭生根發芽。隨著現代化進程加速,崇尚獨立平等和強調精神關注變成年輕一代的迫切需要。子女們妄圖掙脫這種“一切為你好”的老舊思想,跳出“重男輕女”窠臼。為了捍衛自我意識,他們開始思考父母作為家庭絕對權威的可靠性,向父母提出精神關注的強烈愿望,對家庭文化表達新的訴求。在他們看來,盡管親情血濃于水,也不容許無節制的操縱和利用;家不僅是溫飽線上的港灣,更應是心靈真正得以棲息的一方天地。
二、典型人物:符號人物的權力突圍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4)陸貴山,周忠厚:《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選講》 (第五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版,第235頁。”。典型性格在典型環境中形成,離開典型環境,典型人物便失去意義;離開典型人物,便無所謂典型環境。同時,恩格斯在充分肯定典型環境塑造人物性格、揭示生活本質方面的優勢之外,亦強調“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真實”,在對性格的要求中,恩格斯指出“每個人都是典型,但又是一定的單個人,正如老黑格爾所說的,是一個‘這個’。即典型性格既要具有鮮明的個性,又要反映所隸屬階級、階層的某些本質方面(5)陸貴山,周忠厚:《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選講》 (第五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版,第236頁。” “就人的現實本質而言,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物形成性格、采取行動的動機不只是個人欲望的作祟,而是有著深刻的時代原因,其行動的促成是從其所處的歷史潮流中而來的(6)陸貴山,周忠厚:《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選講》 (第五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版,第236頁。”。母系社會分崩瓦解后,男性憑借其先天生理優勢,逐漸成為家庭生產資料的主要創造者,并通過對教育權力的性別壟斷、經濟基礎的絕對掌控迅速占據了家庭話語權力的主體地位。就此而言,絕對威嚴、不容挑戰的父權制度在傳統文化中便根深蒂固。“女子在家從父,出嫁從父,守三綱,遵五常”等“尊父權,抑女性”的陳規舊約致使女性被先天賦予了悲劇性附屬客體的色彩,長此以往,女性被異化至邊緣的絕對第二性的境地而解放無門。然而,隨著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機器對人力的解放逐漸縮小了性別鴻溝,使平等獨立的民主新風宣揚開來,為現代化男女平權的實現奠定了基礎。在這期間,女性透過對教育平等權、工作平等權的爭取與社會價值的自我確立逐漸完成了自覺或半自覺的性別覺醒,他們對以男權為中心的話語體制發起挑戰,變被動為主動,變客體為主體,著力嘗試對傳統父權的突圍與逆反。
在《都挺好》的創作構思中,劇作者著力打破傳統家庭倫理題材男強女弱常規,對男性作為家庭支柱、話語中心的偉岸形象進行解構,將固有性別認知抽離出去,構筑起以女性為權力主體的敘事語境,且對女性家長里短、柔弱而不堪一擊的婆媽標簽、歇斯底里的妖魔化符號進行顛覆和祛除,他們發現了女性形象,并創造了具有時代意味的女性形象。劇中,以蘇家為核心建構起的敘事場域,相較于傳統劇情女性以柔克剛、同強勢男權進行對峙以實現權力轉移、取得自我確證和主導地位模式不同,《都挺好》中權力移置是通過男性失語與女性強權的強烈對比來實現的,它所營造的是一個陰盛陽衰、父權式微的世界,強權女性作為突出符號成為劇情發展重要線索,承擔著打破傳統家庭文化秩序,引發大眾思考的重任。就蘇家的權力中心蘇母而言,她一出場即存在于有別于現實世界的回憶空間,但是她在蘇父和蘇家兄妹心中一直實現著缺席的在場。她的凌厲與強勢迫使蘇家的男人們都對他言聽計從:蘇父在她壓制下一生唯唯諾諾,小心翼翼,每當家庭發生沖突,兒女向他求助,要么面對墻壁一言不發,要么逃去廁所躲開紛爭,全然被剝離到話語中心的邊緣地帶,他甘愿屈居蘇母之下,成為蘇母的附庸客體,以至于蘇母離世之后,她的霸道和積年壓迫仍令蘇父顫栗不已。但是蘇母對于父權制度的突圍仍然是不夠徹底的,或者說她在嘗試突圍的同時還在持續接受父權制的壓迫。作為女性,蘇母飽受原生家庭歧視,從小被父權制家庭男尊女卑思想荼毒,成年后,她作為維系父權制度的同謀者不但成為一個令人厭棄的“扶弟魔”,無節制地對其蛀蟲般的無賴弟弟進行經濟援助,而且還用這種落后思想繼續麻痹、迫害自己的女兒。蘇明玉在看清楚這強權表面之下隱匿的真相后毅然放棄了對蘇家的期望,成為現代版出走的娜拉。她是一個民主意識、自我精神極強的現代女性,正統的教育理念、價值觀念使其無形中被注入獨立自強的主體意識。在認識到家庭無法拯救她的人生之后,便轉向了自我解救的道路。她努力拼搏,在爾虞我詐的職場上叱咤風云、游刃有余,有一股男子氣概,行事果敢凌厲,并仰仗其杰出的銷售才能實現了對大部分男性話語權力的絕對碾壓,并通過這種社會認定的有效途徑,實現了對自我命運的完全掌控。與此同時,也恰是這個最不被家庭看好,家庭不舍投資的女兒最終卻對蘇家投入最多。蘇母的喪事是明玉一手操辦的;蘇家兄弟的工作是明玉疏通的;蘇父晚年患病最終也是明玉與之相伴。都說養兒防老,最不受待見的女兒最終卻是最有孝心、付出最多的那一個,樁樁件件無疑都是對傳統父權文化中心的絕地反擊。她的存在直擊“男主內,女主外”的老舊模式,將傳統女性應當灶前臺后,恪守本分的陳規印象進行顛覆,并憑借獨立、理性意識的覺醒與巾幗不讓須眉的氣概最終擺脫了作為男性權利附屬品的存在,她不但自我彌補了童年時期家庭話語權力缺失的遺憾,而且成功實現了話語權力變被動為主動的突圍。某種意義上說,她不僅是蘇明玉本身,更是現實社會里千萬獨立女性形象的投影和典型聚焦,是時代觀眾最熟悉的陌生人。
三、歷史趨勢:“家”題材創作思維的構筑
《都挺好》在敘事內容上的精心編排與敘事技巧中的大膽創新使各個年齡層觀眾無不拍手叫絕。它一邊行云流水,淡敘百姓日常生活點滴;一邊或隱或顯揭示社會重大議題。它的成功是建立在對真實家庭生活探索之上的藝術巧思,是符合真實生活邏輯的藝術真實。同時,它彌合了時代典型環境之下大眾對假丑惡的厭棄,對真善美的向往審美趨勢,其中的現實主義品格、人文關懷氣質以及形式美的呈現都對我們探索“家”題材劇作的未來出路大有裨益。
(一)文藝創作一定要以歷史理性求真
要能動地反映、理解與闡釋社會真實,呈現出現實主義的美學品格。馬克思與恩格斯指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作為一種精神產品是對社會存在的能動反映,其藝術表現的深度與廣度取決于藝術家認識的深度和廣度,在對生活進行藝術變形、藝術加工的同時,創作者既要明確社會生活作為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理清楚生活與文藝的源流關系;又要兼顧細節、環境與人物的典型性,揭示出時代生活的歷史真理與規律。作為2019年大獲全勝的良心劇作,《都挺好》所呈現的生活真實不勝枚舉,盡管劇作內容純屬虛構,但是創作者放棄了傳統敘事文本對時空環境架空化處理方式,選取了蘇州同德里這個現實場域進行文本敘述,虛構文本的擬真化增強了故事的真實感與情境帶入感,使觀眾生發強烈共鳴。于此,時空環境不再是一種無關緊要的間性符號,同時也是引發受眾真情實感的重要中介。此外,該劇在細節寫實方面也達到了觀眾顯微鏡式欣賞的高標準、嚴要求。劇中的道具安排貼合人物真實,明玉作為蘇家最不受待見的孩子,其家庭地位遠在兩位哥哥之下,明成和明哲的房間都有電腦,而明玉的臥室只有日常設施,寧靜樸素;蘇母去世后,明玉在車內獨自回憶往事,她拼命扯去孝布,然而幾番來回也沒能拽下,她又急又氣,無奈至極,取下之后卻又理清皺褶、疊放整齊。這一系列的精細安排在邏輯合理之外又使得人物立體起來,暗含了明玉想要遠離家庭,無奈血濃于水終不忍決絕的復雜情緒。
(二)創作者要具備尚善特征的人格力量
創作者要以高尚的品格和誠摯的情感對社會生活進行詩意的裁判。它要求作家運用內在尺度把倫理對客觀事物的主觀態度和評價融入其中,并憑借“境(典型、意境、意象)”的審美形式與“理”的藝術詮釋相交融,表現對美好事物、美好情操、美好理想的守望與追求,對丑惡、陰暗、腐朽事物的拒斥,呈現人文關懷的終極價值追求,從而激發受眾的情感經驗與審美思考,使之得到心靈的凈化、情操的陶冶與境界的提升。誠然,《都挺好》所觸碰的主要議題稍顯沉重,其審美效果大多是通過“揭傷疤”形式達到的,創作者毫不留情地將部分觀眾潛藏在內心隱秘角落里的傷口一道道扒開,蘇明玉所承受的不公和歧視觀眾與之同觴;蘇明玉妄圖逃離家的牢籠卻又無可奈何的復雜心緒觀眾感同身受。反觀自我,蘇明玉即是觀眾最熟悉的陌生人。同劇中人物一樣矛盾,他們一邊心有不甘,企圖冷漠到底,一邊又渴望溫情,想與家人和解,對過去釋懷。劇作者敏銳地領悟了這些生活真實,并以藝術眼光對其投去深沉的人文關懷,他在傷痛與圓滿中找尋一種微妙的平衡,最終通過幼有所愛、老有所養的溫情呈現對創傷心靈進行修補,引發了大眾對“家”更為理性、冷靜的思考,使之在作品的余味中得到慰藉。這種循序漸進的情感治療無疑彰顯了創作者的巨大社會責任感,顯示出為藝術為人的最高境界。
(三)文藝創作還要按照美的規律進行形式創造
藝術創造之美植根于“真”,附麗于“善”,二者的統一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文學審美的深刻價值追求。然而,這種美尚處于內容狀態,藝術家仍需對藝術內容的內在結構加以組織,即運用一定語言材料或藝術手段呈現為審美的藝術形式,它作為審美價值的最后追求,是藝術內容得以外化和體現,得以深化或升華的有效手段。近年來,規行矩步的影視橋段與因循守舊的情感對白已然成為時代的窠臼,大眾對其嗤之以鼻,并呈現出對劇作配樂、臺詞等多元素材的獨創性追求。《都挺好》并未抱令守律,采用了蘇州評彈替代流行曲目作為背景音樂,評彈一現,蘇州風情、婉約江南境界全出。其詞調不僅貼近社會真實,符合劇作的情感走向,還生發出審美新質,引發大眾對評彈這一傳統曲藝挖掘、品鑒的興趣。劇中,評彈多用語調,其詞句與劇中場景一一對應,吳儂軟語既不顯得突兀,又使得故事氛圍瞬間構筑起來。《白蛇傳——賞中秋》原曲描繪的是許仙與白娘子的美好感情,因而總是為劇中的溫馨場面做伴,當明玉與石天冬確定戀愛關系,明成一家主動承擔贍養蘇父的義務時都有出現;《長生殿——宮怨》情感悲慟,便伴以蘇父與保姆分手情節;《玉蜻蜓——庵堂認母》巧妙地設計在蘇父患病后,明玉同蘇父共聽評彈的場面,此曲伴此情,暗指明玉決心放棄過往恩怨,蘇家終重修舊好的大團圓結局,此類巧用,數不勝數。
結 語
偶然之中隱含著絕對必然,試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對《都挺好》的成功原因理性剖析,為家庭倫理題材作品的成功轉型提供可供參考的審美經驗。《都挺好》以家庭為敘事核心,憑借社會真實直擊轉型時期大眾對“家”的多元訴求和秩序表達,呈現出典型環境與符號人物的現實主義品格,表現為文藝創作向真、向善、向美的價值追求,形成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完美統一的召喚結構,引人深思,回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