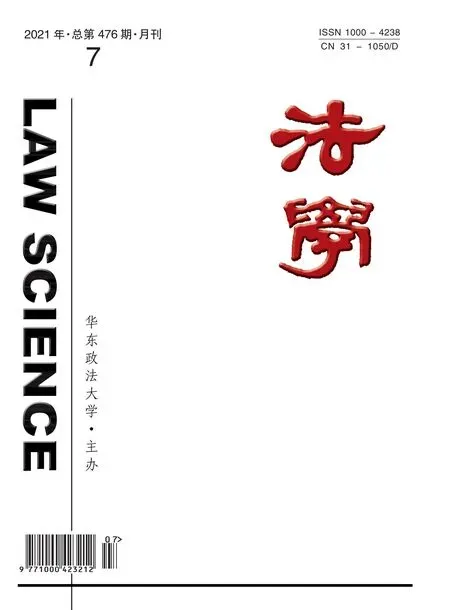刑事疑案擇一認定的規范內涵、適用立場及實質限制
●趙春玉
一、擇一認定的緣起、變遷及問題的提出
在刑事審判中,對犯罪認定具有重要意義的相關事實既無法確認其存在,也無法確認其不存在,則產生所謂的犯罪事實存疑。〔1〕參見蔡圣偉:《刑法問題研究(一)》,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版,第9 頁。面對犯罪事實存疑的案件(以下簡稱“疑案”),法官無法適用邏輯或演繹的三段論規則予以裁判,但誠如拉倫茨所言:“法官不能以‘不清楚’為由拒絕裁判,與科學家不同,他被課以裁判強制。就眼前的法律案件,他必須作出決定,因此,就既存的案件事實,他必須做出此種或彼種判斷。在這類案件中,司法裁判不可避免地會有不確定的危險,這是必須接受的。法官于此只需窮盡法律性考量可以提供的具體化手段,并借此取得‘可以認為正當的’決定,即為已足。”〔2〕[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 年版,第175 頁。在刑事程序法上,法官必須在規定的訴訟期間內平息紛爭,不能讓案件久而不決成為懸案。在刑事實體法上,法官必須對案件做出明確的定性,不能超出國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及對被告人非難可能性的范圍隨意裁判。所以,在不能運用三段論規則做出裁判的情況下,就需要引入一個特別的裁判規則來“指示法官,他在那里應如何決斷,他對于法律上重要的事實,既不能確切地肯定,也不能確切地否定,也即‘根據法律規范,無論決定的內容是否正確,至少,決定法官行為的合法性’”。〔3〕[德]卡爾·恩吉施:《法律思維導論》,鄭永流譯,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68-69 頁。這個特別的裁判規則就是所謂的“疑罪唯輕”。其中,“疑罪唯輕”包括“疑罪從無”和“疑罪從輕”兩種類型。〔4〕參見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版,第252-255 頁;林鈺雄:《疑罪唯輕原則之適用范圍》,載《臺灣本土法學雜志》2008 年第106 期,第213 頁。有學者雖然將“疑罪唯輕”表述為“疑罪從無”,但“疑罪從無”依然包括“疑罪從輕”和“疑罪從無”兩種情形(參見[德]烏爾斯·金德霍伊澤爾:《刑法總論教科書》,蔡桂生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494 頁)。值得說明的是,在我國基本上是將疑罪唯輕原則等同于應當作無罪判決的“疑罪從無”,否定疑罪唯輕原則中的“疑罪從輕”(參見張訓:《擴張解釋、存疑有利于被告與擇一認定》,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4 年第4 期,第17 頁)。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國刑事法理論上是將疑罪唯輕原則作為證據規則而非裁判規則(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上),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33 頁)。其不僅將疑罪唯輕適用于審判階段,而且適用于偵查和起訴階段。然而,如果將疑罪唯輕作為證據規則,疑案就被等同于“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參見沈德詠:《論疑罪從無》,載《中國法學》2013 年第5 期,第5 頁)。那么根據現有的事實和證據是根本不可能指控罪行的。因此,將疑案等同于“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無罪就是疑罪唯輕原則的必然結論。但筆者認為,將疑罪唯輕作為證據規則并將疑案等同于“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實屬對疑罪唯輕的歪曲和誤解。事實上,“疑罪唯輕原則并不是用來指導(事實審)法官如何評價證據證明力的評價法則,而是‘證據評價結束后’才能運用的裁判法則”(參見林鈺雄:《嚴格證明與刑事證據》,法律出版社2008 年版,第128 頁)。作為裁判規則的疑罪唯輕并不必然只會導出無罪的結論,從輕處罰也是其應有之義。在德國、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將疑罪唯輕作為裁判規則而非證據規則已成為共識。疑罪從無適用于罪的“有或無(罪與非罪)”之間的疑案。例如,警察在被告人家中查獲某珠寶店失竊的珠寶,法官窮盡所有的證據依然不能排除以下可能:被查獲的珠寶既可能是被告人偷來的,也可能是被告人明知他人偷來而購買的,還可能是善意取得的。在本案中,法官對被告人既不能形成有罪的確信,也不能形成無罪的確信,且法院又不能將無法查明的事實(證明負擔)轉嫁給被告人并讓其承擔不利的后果,因而應當判決被告人無罪。而疑罪從輕則適用于在不法上存在“大包小”位階關系的此罪與彼罪或同一犯罪的不同形態之間的疑案。〔5〕同前注〔1〕,蔡圣偉書,第15 頁。其一,在此罪與彼罪之間的不法存在位階關系的場合,例如,在強奸罪與強制猥褻罪、綁架罪與非法拘禁罪、搶劫罪與搶奪罪之間的疑案中,被告人既可能成立重罪,也可能成立輕罪,法院應當適用疑罪從輕裁判為輕罪。其二,在同一犯罪的不同犯罪形態之間的不法存在位階關系的場合,例如,甲、乙二人在互不知情的情況下同時向丙開槍射擊,其中只有一顆子彈擊中丙并致其死亡。法院無法查明,丙的死亡到底是甲的射殺行為所致還是乙的射殺行為所致。在本案中,可以肯定的是,甲和乙均不可能無罪,但法官既不能確信丙死亡的結果應該歸責于誰(甲或乙),也不能確信丙死亡的結果不歸責于誰(甲或乙)。換言之,對于甲或乙而言,無論是犯罪既遂抑或犯罪未遂都只是一種可能,并不能形成確信。因而,應當適用疑罪從輕裁判甲和乙成立故意殺人罪未遂。除既遂與未遂外,在既遂與中止、正犯與共犯(教唆犯與幫助犯)之間的不法也存在位階關系。〔6〕同前注〔4〕,林鈺雄書,第147 頁。
然而,當此罪與彼罪或同一犯罪的不同形態之間的不法不存在“大包小”的位階關系時,在它們之間的疑案并不屬于疑罪從輕的適用范圍,此時,倘若將疑罪唯輕原則作為裁判疑案的唯一規則,那么法官就只能采用分離觀察法分別適用疑罪從無予以裁判。例如,某甲在野外由于身患疾病昏迷一段時間后死亡,家屬發現其隨身攜帶的勞力士手表不翼而飛,后警察發現被告人A 手上戴著的正是某甲的勞力士手表。檢察機關以盜竊罪起訴了A,但A 卻辯稱手表是從死人身上取得的,因而其行為只是侵占不是盜竊。法官窮盡所有的證據依然無法查明被告人取得手表時某甲是否死亡,因而也就不能確定被告人A 的行為到底是成立盜竊罪還是侵占罪。但由于盜竊罪與侵占罪在不法上不是位階關系,而是相互對立的互斥關系,因而法官應適用疑罪從無分別裁判被告人A 盜竊罪的“有或無”及侵占罪的“有或無”,最后分別認定盜竊罪和侵占罪不成立。然而,事實上,“判決被告人無罪,僅缺乏有罪證明是不夠的,而是要求對無罪予以積極的確認”。〔7〕[德]萊奧·羅森貝克:《證明責任論》,莊敬華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8 年版,第50 頁。在本案中,如果適用疑罪從無裁判被告人A 無罪,一方面雖然會產生對被告人有利的結果,但也存在對被告人的過度保護之虞,〔8〕參見巫聰昌:《犯罪事實的擇一認定》,載《法令月刊》2011 年第8 期,第39 頁。使被告人逃脫原本應受的處罰;另一方面也會導致裁判結果的不正義,忽略了疑罪唯輕原則沒有給予充分考慮或注意的情形,其結論不僅嚴重背離一般大眾的法感,而且使被告人在明顯具有可罰性的行為中獲得脫免制裁的理由和不當利益,不利于實現對犯罪的預防。因此,為了避免因過度適用疑罪從無而導致無罪判決的泛濫,于是在理論上針對上述情形創設了一個作為疑罪唯輕原則例外的擇一認定(Wahlfestellung),使被告人在具有可罰性的前提下承擔應得的刑事責任。〔9〕同前注〔1〕,蔡圣偉書,第52 頁。
據奧地利學者Schmoller 考證,作為疑罪唯輕原則例外的擇一認定在19 世紀中葉發端于德國。〔10〕同上注,第50 頁。起初,擇一認定僅在司法實務中被適用于具有同等價值的同種類犯罪上,但后來其適用范圍有所擴大。例如,在盜竊與窩贓之間的疑案中,德國帝國法院在1934 年適用擇一認定將其裁判為窩贓罪。1935 年6 月28 日修正的《德國刑法》第2 條b 規定:“確認犯人違反兩個以上處罰條款中的一個條款,而事實只能擇一認定時,依照最輕的條款處罰。”該規定成為全面容許擇一認定的制度起源。〔11〕參見[日]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訴訟法》(下卷),張凌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137 頁。司法實務將發生在墮胎未遂和實施終了的詐騙、醉酒和毒品犯罪、幫助謀殺與疏于告發犯罪之間的疑案均適用擇一認定予以裁判。由于全面容許擇一認定可能嚴重侵害被告人的人權而在1946 年1 月30 日被廢除,隨之德國司法實務對擇一認定的適用又回到了有限制容許的中間立場上,認為在盜竊與詐騙、故意殺人與傷害致死等犯罪之間的疑案,由于它們不具有“法倫理和心理上的可比較性”,故而不允許擇一認定。為了避免“法倫理和心理上的可比較性”這一標準存在主觀恣意性之不足,有力的觀點認為應以“不法核心同一性”作為是否允許適用擇一認定的標準。但總體而言,隨著時間的推移,擇一認定的適用范圍正在逐漸擴大。〔12〕參見[德]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上),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 年版,第203 頁。在1960 年代初期,擇一認定受到日本學界和實務界的關注并引起了實質的爭議,這一時期能否適用擇一認定主要與訴因記載方法密切關聯。起初,擇一認定僅在同一個訴因內部的具體事項如方法、時間、地點等記載事項存疑時允許適用。在不同犯罪(如盜竊與購買贓物、故意放火與失火)之間的疑案中,則不允許適用擇一認定將兩個訴因融合起來作判斷,只能選擇其中一個訴因并做出有罪或無罪的判決。〔13〕同前注〔11〕,松尾浩也書,第136 頁。對此,有學者指出,僅將擇一認定限制在與犯罪定性無關的狹隘領域內,偏離了擇一認定的核心,應當在一定限度內允許對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適用擇一認定。〔14〕同前注〔8〕,巫聰昌文,第32 頁。直到1980 年代初期,日本的司法實務才開始逐漸承認擇一認定可以適用于不同犯罪(如保護責任者遺棄罪與遺棄尸體罪)之間的疑案。〔15〕同前注〔11〕,松尾浩也書,第137 頁。
在我國直到本世紀初才有學者開始關注擇一認定的問題。〔16〕張明楷教授在《吉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1 期發表的《“存疑時有利于被告”原則的適用界限》一文是最早涉及擇一認定問題的。但在我國應如何理解擇一認定,目前存在全面肯定和全面否定兩種做法。由于適用擇一認定和疑罪從輕的裁判結果都是對被告人從輕處罰,因而全面肯定擇一認定的觀點往往不區分擇一認定與疑罪從輕,要么主張廣義的疑罪從輕,將擇一認定作為疑罪從輕的一種具體情形,認為在此罪與彼罪之間的疑案均應適用疑罪從輕予以裁判;〔17〕參見胡云騰、段啟俊:《疑罪問題研究》,載《中國法學》2006 年第3 期,第160 頁;邵劭:《從無與從輕:疑罪理論的界分與實踐運行》,載《浙江學刊》2016 年第2 期,第165 頁;韓軼:《疑罪價值的一元化反思》,載《法商研究》2019 年第2 期,第119 頁。要么主張廣義的擇一認定,將疑罪從輕作為擇一認定的一種具體情形,例如,犯罪既遂與犯罪未遂,強奸罪與強制猥褻婦女罪,以及交通肇事罪與幫助毀滅證據罪之間的疑案均應適用擇一認定予以裁判。〔18〕同前注〔16〕,張明楷文,第61-62 頁。無論是主張廣義的疑罪從輕還是廣義的擇一認定,一方面只看到二者最終的裁判結果都是從輕處罰,卻沒有辦法最終明確在此罪與彼罪的疑案中從輕處罰的范圍。另一方面將所有此罪與彼罪之間疑案都從輕處罰,其不僅忽視了二者從輕處罰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根據的不同,而且會將既不符合擇一認定又不符合疑罪從輕適用范圍的疑案也從輕處罰,使疑罪從無在此罪與彼罪的疑案中喪失存在的空間并可能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全面否定的觀點則認為,疑罪從無是防范冤假錯案唯一正確且明智的選擇,〔19〕同前注〔4〕,沈德詠文,第6 頁。無論適用擇一認定抑或疑罪從輕對被告人從輕處罰,遵循的都是“疑罪從有”的裁判思路,因而其是“制造冤假錯案的禍根”。〔20〕劉憲權:《“疑罪從輕”是產生冤案的禍根》,載《法學》2010 年第6 期,第16 頁。尤其是近年來在對冤假錯案進行“運動式”批判的背景下,疑罪從無被視為金科玉律,任何限縮疑罪從無適用范圍的舉動,就是對冤假錯案現狀的縱容或支持,〔21〕參見王星譯:《反思疑罪從無及其適用》,載《環球法律評論》2015 年第4 期,第67 頁。進而擇一認定也就喪失了存在的空間。
在此罪與彼罪的疑案中,擇一認定只是例外的裁判規則,其目的只在于修正疑罪從無的適用范圍以避免無罪判決的泛濫并造成不公平或不妥當現象,〔22〕同前注〔4〕,林山田書,第252 頁。但其并不否認疑罪從無是裁判疑案的核心規則。對于此罪與彼罪之間的疑案,既不是一味地從輕處罰,也不是一味地從無處罰,其既可能適用擇一認定,也可能適用疑罪從輕,還可能適用疑罪從無,到底應當適用何者作為疑案的裁判規則,則取決于此罪與彼罪在實質上是何種關系。擇一認定的適用不同于疑罪從輕,二者有著各自獨立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根據。明確擇一認定自身內涵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其目的不僅在于能明確擇一認定與疑罪從輕的界限,而且在于能明確疑罪從輕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根據,進而在此罪與彼罪之間的疑案中明確從輕處罰的范圍,而不是將所有此罪與彼罪之間的疑案均從輕處罰,為疑罪從無的適用留足其應有的空間。故而,擇一認定的問題核心就不在于其是否限縮了疑罪從無及是否允許其適用的問題,而在于如何妥當地適用。在我國由于擇一認定是一個相對陌生且與疑罪從輕糾纏不清的問題,因而要妥當適用擇一認定,就必須首先厘清擇一認定的規范內涵,劃定其與疑罪從輕各自的適用范圍,明確有限制容許擇一認定的適用立場,以及妥當適用擇一認定的實質限制標準,將擇一認定的適用限制在合法且正當的范圍之內。借此,也就能在此罪與彼罪的疑案中同時明確適用疑罪從輕和疑罪從無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根據。
二、擇一認定的規范內涵
厘清擇一認定的內涵最首要的就是要明確其與相關問題的界限。其中,在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中,明確擇一認定與疑罪從輕的界限直接關涉擇一認定適用的合法性基礎,其是擇一認定的核心內涵所在;在同一犯罪內的疑案中,明確擇一認定與概括性認定的界限涉及的是擇一認定的規范類型的問題。
(一)擇一認定的核心內涵
在此罪與彼罪的疑案中,主流的觀點認為,所謂擇一認定是指被告人無罪的合理懷疑已被消除,法官窮盡所有的證據,雖然可以肯定被告人的行為必定符合處于非此即彼關系的兩個或兩個以上構成要件中的一個,但卻不能肯定其究竟符合其中的哪一個,因而容許法官在一定條件下就疑案擇一較輕的罪名予以裁判。〔23〕同前注〔4〕,烏爾斯·金德霍伊澤爾書,第495 頁;同前注〔4〕,林鈺雄書,第150 頁;同前注〔4〕,林山田書,第255 頁;同前注〔12〕,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馬斯·魏根特書,第200 頁。擇一認定與疑罪從輕既存在相同之處,也存在不同之處。二者的相同之處在于,被告人無罪的合理懷疑已被消除,其行為必定符合兩個或兩個以上構成要件中的一個,只是不能確定其到底符合其中的哪一個,在涉及不同犯罪時都應裁判為較輕的犯罪。二者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們的適用范圍和合法性根據不同,即疑罪從輕適用于具有位階(包容)關系的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而擇一認定則適用于具有非此即彼(擇一)關系的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也正是由于擇一認定與疑罪從輕存在諸多共性和易混淆之處,尤其是二者都需要對被告人從輕處罰,所以在理論上往往將二者相混淆,要么將擇一認定作為疑罪從輕的一種具體情形(廣義的疑罪從輕),要么將疑罪從輕作為擇一認定的一種具體情形(廣義的擇一認定)。筆者認為,如果僅因為擇一認定和疑罪從輕都從輕處罰就混淆二者的做法,那么其不僅混淆了二者不同的(形式和實質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根據,而且可能將從輕處罰的范圍擴張到根本不具有從輕處罰根據的疑案之中。
1.廣義疑罪從輕的質疑
在德國和日本有學者主張廣義的疑罪從輕,將擇一認定視為疑罪從輕的一種具體情形,不再區分擇一認定與疑罪從輕,〔24〕同前注〔1〕,蔡圣偉書,第55 頁。認為擇一認定的問題可以適用疑罪從輕予以解決,即將處于非此即彼關系的不同犯罪解釋為具有位階關系的犯罪。例如,在保護責任者遺棄罪與遺棄尸體罪之間的疑案中,法官對被遺棄者是“生存”還是“死亡”不能形成確信。在這種場合,可以認為“生存”與“死亡”之間存在位階關系,因而可以適用疑罪從輕裁判被告人成立遺棄尸體罪。〔25〕在本案中,日本的一審法院認為保護責任者遺棄罪和遺棄尸體罪的保護法益不同,違法性基礎相異,只將兩者都解釋為“遺棄”,忽視了具體對象和法益的不同,其實質上是一種類推。二審法院則適用擇一認定裁判被告人成立遺棄尸體罪(同前注〔8〕,巫聰昌文,第33 頁)。在我國有學者主張最廣義的疑罪從輕,不僅不需要區分擇一認定和疑罪從輕,而且將所有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都作為疑罪從輕的情形。例如,有觀點認為,疑罪從輕是指在此罪與彼罪、一罪與數罪及情節輕重之間的疑案,應當選擇法定刑較輕的犯罪予以裁判。〔26〕同前注〔17〕,胡云騰、段啟俊文,第160 頁;同前注〔17〕,邵劭文,第165 頁;同前注〔17〕,韓軼文,第119 頁。筆者認為,將擇一認定作為疑罪從輕的一種具體情形實際上偏離了擇一認定的原有面貌和固有內涵。
其一,適用疑罪從輕與擇一認定裁判的疑案在邏輯上不能等同視之。從邏輯學的角度而言,疑罪從輕和擇一認定都適用于此罪與彼罪之間的疑案,且二者在邏輯上都屬于析取式選擇關系,即二者之間的聯結式(析取式)都是“或者”。例如,在搶劫與搶奪之間的疑案中,被告人的行為可能成立的犯罪是“搶劫罪或搶奪罪”;在盜竊與窩贓之間的疑案中,被告人的行為可能成立的犯罪是“盜竊罪或窩贓罪(掩飾、掩瞞犯罪所得罪)”。然而這兩種析取式的選擇關系卻存在本質的差別。在疑罪從輕的場合,析取式的選擇關系實際上是一種非排他的相容關系(在邏輯上表述為“X v Y”,讀作“X 或 Y”)。在這種非排他的相容關系中,二者可能同時為真,但不可能同時為假。例如,在搶劫與搶奪之間的疑案中,被告人可能既是搶劫犯也是搶奪犯,也有可能是搶劫犯但不是搶奪犯,或者不是搶劫犯而是搶奪犯。然而,在擇一認定的場合,析取式的選擇關系實際上是一種非此即彼或排他的不相容關系(在邏輯上表述為“X # Y”,讀作“要么X,要么Y”)。在這種排他的不相容關系中,二者既不可能同時為真,也不可能同時為假,只可能是要么為真,要么為假。例如,在盜竊與窩贓(掩飾、掩瞞犯罪所得)之間的疑案中,被告人不可能既是盜竊犯也是窩贓犯,也不可能既不是盜竊犯又不是窩贓犯,只可能是要么為盜竊犯,要么為窩贓犯。〔27〕參見[德] 阿圖爾·考夫曼:《法律獲取的程序—— 一種理性分析》,雷磊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頁;[德]烏爾里希·克盧格:《法律邏輯》,雷磊譯,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36 頁、第44-45 頁、第56 頁。因而,雖然疑罪從輕和擇一認定都適用于具有析取式的選擇關系的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但二者在邏輯上卻不能等同視之。
其二,適用疑罪從輕和擇一認定裁判的疑案,它們所涉及的不同犯罪在規范內涵上并不相同。在疑罪從輕的場合,不同犯罪之間在規范上系位階關系或包容關系。從構成要件的角度而言,不同犯罪的構成要件之間只是存在多一些要素或少一些要素的區別,它們之間在概念邏輯上屬于階段關系或隸屬關系,相當于法條競合中的特別關系,其存在于基本構成要件與加重或減輕構成要件之間。從實質不法的角度而言,不同犯罪(包含不同的犯罪形態)所侵害的法益是相同的,只是侵害相同法益的程度(不法程度)存在差別(如強奸與強制猥褻,犯罪既遂與犯罪未遂),它們在不法上存在包容關系(位階關系),相當于法條競合中的補充關系,被包容法條的不法內涵低于包容法條的不法內涵。〔28〕同前注〔1〕,蔡圣偉書,第49 頁。然而,在擇一認定的場合,不同犯罪的構成要件上在概念邏輯上系互斥關系或擇一關系,在不法上則是等價關系。從構成要件的角度而言,不同犯罪的構成要件之間根本不存在任何階段關系,〔29〕同前注〔4〕,烏爾斯·金德霍伊澤爾書,第494 頁。而是非此即彼的擇一關系,即不同犯罪的構成要件之間既含有相互交叉的要素又含有相互矛盾的要素,彼此間屬于相互對立或排斥的關系。〔30〕參見甘添貴:《罪數理論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95 頁。例如,在盜竊罪與普通侵占罪之間,盜竊需要轉移占有他人的財物,而普通侵占則不需要轉移占有他人的財物。從實質不法的角度而言,如后所述,雖然在何種實質基準下能夠適用擇一認定存在“法倫理和心理上的可比較性說”與“不法核心的同一性說”的分歧,但其基本的前提都在于將擇一認定的適用范圍限制在不法上具有等價性的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中。
2.廣義擇一認定的誤區
張明楷教授認為,“擇一認定,是指雖然不能確信被告人實施了某一特定犯罪行為,但能夠確信被告人肯定實施了另一處罰較輕的犯罪行為時,可以認定另一犯罪的成立。”擇一認定的成立需要滿足三個條件:(1)被告人肯定實施了兩種行為之一,行為人要么成立此罪,要么成立彼罪,此罪與彼罪處于非此即彼的關系;(2)能夠排除對輕罪的合理懷疑;(3)應當適用處刑較輕的法條,不能擇一重罪論處。例如,在盜竊罪與窩贓犯罪、犯罪既遂與犯罪未遂、強奸罪與強制猥褻婦女罪及交通肇事罪與幫助毀滅證據罪之間的疑案中都可以適用擇一認定予以解決。〔31〕同前注〔16〕,張明楷文,第61-62 頁。與主張廣義疑罪從輕的觀點不同,該觀點不僅認為在疑案中最終裁判的輕罪是能形成確信的,而且將擇一認定的適用范圍擴張到屬于位階關系和異質關系(中立關系)的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中,既混淆了擇一認定和疑罪從輕的適用范圍,又混淆了擇一認定與疑罪從無的適用范圍。
其一,認為輕罪的犯罪事實是能形成確信的,不僅可能混淆疑罪從輕和擇一認定的適用范圍,而且存在以偏概全和自相矛盾的誤區。輕罪的犯罪事實可以形成確信是指行為人實施的犯罪行為能夠充足輕罪的構成要件。在不同犯罪之間屬于特別關系和補充關系的場合,由于它們在概念邏輯上存在階段關系及在不法上存在位階(關系),或許在它們之間的大部分疑案確實可能在輕罪上形成確信。例如,在故意殺人與故意傷害之間的疑案中,如果認為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之間是一種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32〕參見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687 頁。那么在二者之間的疑案似乎可以在故意傷害罪上形成確信,即故意傷害(輕罪)的事實已被排除合理懷疑,但故意殺人罪(重罪)的事實依然存疑。〔33〕參見黃常仁:《刑法總論:邏輯分析與體系論證》,自印本2001 年版,第284 頁。又如,在犯罪既遂與犯罪未遂之間的疑案中,雖然犯罪既遂的事實存疑,但犯罪未遂的事實則是能夠形成確信的。然而,如果由此就認為所有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均能在輕罪上形成確信則存在疑問。因為即使在不同犯罪屬于特別關系或補充關系的場合,也依然可能在輕罪上不能形成確信。例如,在德國刑法中的普通殺人與受囑托殺人之間的疑案中,如果法官對被告人的殺人行為是否受囑托無法形成確信,那么被告人實施的行為就不能在受囑托殺人罪(輕罪)上形成確信,反而能夠確信的是被告人的行為充足了普通殺人罪(重罪)的構成要件。如果依照能夠確信的犯罪予以裁判,那么對被告人就不能適用法定刑較輕的法條而是較重的法條。然而,這一結論與疑案的裁判結論完全相悖。
其二,在屬于擇一關系的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中,認為適用擇一認定裁判的輕罪是能夠形成確信的,則背離了擇一認定的本來內涵。在適用擇一認定的場合,認為法官對最終認定的輕罪也是能夠形成確信的,實際上是通過先假定或擬制輕罪的事實(小前提)是真實存在的,然后再試圖應用三段論規則將犯罪事實涵攝于輕罪的構成要件之下,最終得出符合輕罪構成要件的結論。如前所述,擇一認定適用于擇一關系的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中。然而,由于屬于擇一關系的不同犯罪在邏輯上是一種排他的不相容關系,法官對重罪不能形成確信并不意味著對輕罪就能形成確信,二者都只是一種可能而已。例如,被告人甲在運輸贓物時被抓獲,法官窮盡所有的證據,只能查明被告人甲運輸的贓物不是偷來的就是故意窩藏他人犯罪所得。在該案中,即使按照擇一認定裁判被告人成立輕罪(掩飾、掩瞞犯罪所得罪),也并不意味著對輕罪(掩飾、掩瞞犯罪所得罪)能夠形成確信。事實上,在該案中無論是盜竊抑或掩飾、掩瞞犯罪所得都不能形成確信,只能形成被告人的行為在二者之中必居其一的確信。因而,在擇一認定的場合,法官只能排除被告人無罪的合理懷疑,但對被告人的行為到底是符合此罪抑或彼罪的構成要件并不能達到不容合理懷疑之程度。因此,如果被告人的行為在輕罪上能夠形成確信,那么最終認定為輕罪則就是按照三段論規則予以裁判的結果,自然也不存在擇一認定的問題。
其三,在屬于異質關系(中立關系)的不同犯罪之間,雖然存在重罪與輕罪的關系,但在它們之間的疑案根本不可能適用擇一認定將其裁判為輕罪,更談不上在輕罪上能夠形成確信。主張廣義擇一認定的觀點認為,如果承認擇一認定,那么在交通肇事罪與幫助毀滅證據罪之間的疑案就應當適用擇一認定裁判為幫助毀滅證據罪。然而,交通肇事罪與幫助毀滅證據罪既不是特別關系或補充關系,也不是擇一關系,而是異質關系(中立關系)。如后所述,由于異質關系的不同犯罪的保護法益、行為手段、對象和結果均存在差異,因而被告人實施一個行為是不可能同時該當屬于異質關系的數個構成要件的,在它們之間形成的疑案也就不可能是基于一個犯罪事實或行為(犯罪事實同一性)形成的一個疑案,而是基于數個存疑的犯罪事實或行為所形成的數個疑案。法官在實體上無論是對重罪抑或輕罪均無法形成確信,在程序上也不能基于犯罪事實同一性(同一案件)的要求直接將其罪名變更為輕罪,而是應當分別判斷重罪的“有或無”和輕罪的“有或無”并適用疑罪從無作無罪裁判。
值得指出的是,在德國司法實務中,為了解決疑案的問題可能會援用截堵性構成要件。〔34〕同前注〔11〕,松尾浩也書,第135 頁。所謂截堵性構成要件實際上是對基本構成要件的補充規定,這種補充規定相對于基本構成要件而言具有截堵作用,其只有在基本構成要件得不到適用時,方得以適用,具有輔助適用的作用。〔35〕參見柯耀程:《刑法競合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142 頁。例如,在故意傷害與過失傷害的規定之間,如果以故意傷害為基本規定,那么過失傷害則是具有截堵作用的補充規定。但由于德國司法實務認為,故意和過失是相互對立的主觀違法要素,故意傷害和過失傷害在不法上不存在包容或位階關系,在它們之間的疑案并不符合疑罪從輕的適用范圍。同時,如后所述,德國司法實務還將擇一認定的適用范圍限制在具有“法倫理和心理上的可比較性”的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中,由于相互對立的主觀違法要素(故意與過失)不具有“法倫理和心理上的可比較性”,也不得適用擇一認定予以裁判。但又由于對故意傷害與過失傷害之間的疑案適用疑罪從無裁判為無罪明顯不妥。故而,司法實務就必須繞道并通過援用截堵性構成要件來達到認定被告人成立輕罪的結論。因此,援用截堵性構成要件是在沒有辦法適用擇一認定或疑罪從輕的情況下,用來裁判疑案的一種權宜之計,而非疑案的裁判規則。在此罪與彼罪之間的疑案中,不能既主張適用擇一認定或疑罪從輕,同時又主張援用截堵性構成要件。換言之,截堵性構成要件不能與擇一認定或疑罪從輕同時并用。〔36〕同前注〔1〕,蔡圣偉書,第56 頁。但如后所述,適用截堵性構成要件來解決部分疑案主要源于對故意和過失的不同體系定位和立場所導致的不得已的做法,其本身并不屬于解決此罪與彼罪之間疑案的裁判規則。
綜上,無論是在廣義的疑罪從輕抑或廣義的擇一認定中,只根據刑罰的輕重將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均納入疑罪從輕或擇一認定的適用范圍并裁判為輕罪是明顯不妥的,一方面是混淆了擇一認定和疑罪從輕各自不同的適用范圍并忽視它們不同的正當化根據;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將既不屬于疑罪從輕也不屬于擇一認定適用范圍且應當適用疑罪從無裁判為無罪的疑案予以從輕處罰,其不僅會使擇一認定和疑罪從輕的區分只具有形式意義而不具有實質意義,而且使諸多從輕處罰的疑案喪失正當化根據,其也就必然面臨著“制造冤假錯案的禍根”的指摘。因此,在此罪與彼罪之間的疑案中,明確擇一認定與疑罪從輕的界限,有助于將擇一認定的適用限制在正當的范圍內,并明確對疑案從輕處罰的范圍,為疑罪從無的適用留足其應有的空間,確保它們各自內涵和適用范圍的合法性。
(二)擇一認定的規范類型
理論上根據存疑的犯罪事實是否處于同一構成要件的范圍內,將擇一認定區分為異種的擇一認定和同種的擇一認定。〔37〕同前注〔1〕,蔡圣偉書,第53 頁;同前注〔11〕,松尾浩也書,第136 頁。異種的擇一認定是指存疑的犯罪事實存在于不同的構成要件之間。異種的擇一認定是擇一認定的核心領域,也是理論和實務集中關注的領域,其主要用于裁判此罪與彼罪之間的疑案,存疑的犯罪事實既影響對罪名的選擇,也影響對法定刑的選擇。而同種的擇一認定則是指存疑的犯罪事實存在于同一構成要件之內。其主要用于裁判犯罪事實處于同一構成要件內且在不法上又不存在位階關系的疑案,存疑的犯罪事實并不影響對罪名和法定刑的選擇。〔38〕參見趙春玉:《刑法中選擇要素的規范關系建構》,載《政法論壇》2020 年第4 期,第82 頁。
然而,正是由于同種的擇一認定并不影響罪名和法定刑的選擇,因而,有觀點認為,擇一認定僅指異種的擇一認定,不包括同種的擇一認定。因為同種的擇一認定在實質上是概括性認定。〔39〕參見[日]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訴訟法》(上卷),丁相順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189 頁。所謂概括性認定是指法官對該當構成要件的事實已經形成確信,而就無法確信的具體事實于一定范圍內采取概括的方式加以認定,并不影響對不法結果的歸責。〔40〕同前注〔8〕,巫聰昌文,第31 頁。例如,在某一故意殺人案中,法官確信被害人的死亡系被告人所致,但對被告人死亡的時間只能確定某個時間段而不能查明具體的時間點,法官對不能查明的具體時間點采取概括性認定并不影響犯罪定性。再如,甲向懸崖邊的乙開槍射擊后,但不確定乙是否死亡,又將乙推下懸崖。事后法官無法查明,乙到底是死于甲的射殺還是摔死。在這種場合,雖然不能查明乙的死亡是由甲的哪一行為所致,但其并不影響認定甲成立故意殺人罪。但如前所述,犯罪事實的存疑是指對認定犯罪有重要意義的實體事實既無法肯定其存在,也無法肯定其不存在,其是一種會直接影響到犯罪定性的類型化事實而非具體事實的存疑。在上述案件中,無論是致人死亡的具體時間還是致人死亡的具體手段都只是非類型化的具體事實存疑,其并不影響認定被告人的行為依然充足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因而,以非類型化的具體事實存疑可以概括性認定來否認同種的擇一認定,實際上是將非類型化的具體事實(如方法、時間、地點)等同于類型化事實所致,是一種邏輯錯位的表現。因此,對處于同一構成要件之內的類型化事實存疑,其雖然不影響對罪名和法定刑的選擇,但其依然會對犯罪定性產生影響,應適用擇一認定而非概括性認定予以解決。
其一,在采用選擇性構成要件要素規定構成要件的犯罪中,對于發生在選擇性構成要件要素之間的疑案,只能擇一認定而不能概括性認定。例如,被告人甲使用他人名義下的國際信用卡透支了731萬元,但法官窮盡所有的證據依然不能查明,甲到底是使用了他人名義下的偽造信用卡還是冒用了他人名義下的信用卡。在本案中,法官既不能認為使用偽造的信用卡和冒用他人信用卡在類型化上的差異是完全無關緊要的,概括性地提升其概念位階并認定“甲實施了信用卡詐騙的行為,具有信用卡詐騙的故意,成立信用卡詐騙罪”,也不能認為使用偽造的信用卡和冒用他人信用卡是完全不同的異質構成要件要素,適用疑罪從無認定甲無罪。在信用卡詐騙罪中,雖然使用偽造的信用卡和冒用他人信用卡屬于兩種不同的類型化事實,但在針對同一侵害對象的場合,兩者對法益所造成的侵害及侵害法益的程度是相同的,在不法上具有等價性。因而本案法官適用擇一認定裁判被告人成立冒用他人信用卡型的信用卡詐騙罪是妥當的。〔41〕參見陳興良、張軍、胡云騰主編:《人民法院刑事指導案例裁判要旨通纂》,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322-323 頁。
其二,在存疑的犯罪事實之間存在互斥性的場合,由于存疑的事實在邏輯上是一種排他的擇一關系,認定了一方的事實就不能認定另一方事實,因而其自始至終只存在一個犯罪事實,〔42〕參見[日]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張凌、于秀峰譯,法律出版社2019 年版,第422 頁。最終對被告人犯罪的認定是擇一認定而非概括性認定的結果。例如,在某故意殺人案中,證人甲在一審程序中提供的證言是“被告人開槍了”,在二審程序中提供的證言是“被告人沒有開槍”。對于甲在兩次審理程序中提供相互矛盾的證言,必定有一次成立偽證罪,但法官無法確信究竟哪一次成立偽證罪。對于證人甲兩次提供的相互矛盾的證言是不可能概括性認定的。因為,兩次證言中只有一次成立偽證罪,并非兩次均成立偽證罪,邏輯上相互矛盾的兩次作證行為不可能概括性地評價為一個作偽證的行為。在本案中,法官也不能因為無法確信哪一次證言是偽證,就適用疑罪從無采取分別判斷的方法否定甲成立偽證罪。因此,在同一構成要件內存疑的犯罪事實之間存在互斥性(邏輯上相互矛盾)時,既不能概括性地認定其成立犯罪,也不能適用疑罪從無否定其成立犯罪,而是應當適用擇一認定宣告其成立犯罪。
其三,在同一構成要件內不存在“大包小”位階關系的不同犯罪形態之間的疑案,不可能采取概括性認定,只能適用擇一認定進行裁判。例如,被告人在實施傷害的過程中停止了對被害人的傷害行為,法院窮盡所有的證據無法查明,被告人到底是基于主動放棄犯罪行為還是基于意志以外的因素放棄犯罪行為,因而在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之間形成了疑案。在本案中,雖然被告人成立犯罪是毫無疑問的,但法官不能概括性地認定被告人成立犯罪而不明確到底是犯罪未遂還是犯罪中止。雖然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在主觀上存在互斥性,但由于二者所侵害的法益,以及侵害法益的程度并無不同,因而二者在不法上并不是位階關系或包含關系,而是等價關系,二者之間的疑案也不屬于疑罪從輕的適用范圍,應適用擇一認定將其裁判為故意傷害罪的中止,并在刑罰裁量時援引中止犯減免處罰的規定。
綜上所述,擇一認定作為疑罪唯輕原則的例外,其目的在于限制過度適用疑罪從無并防止無罪判決的泛濫,但其并不影響疑罪從無在疑案裁判中的核心地位。在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中,不能因為擇一認定與疑罪從輕都從輕處罰就混淆二者的界限。明確擇一認定與疑罪從輕的界限,不僅在于明確二者不同的適用范圍,而且在于明確二者不同的合法性根據,更為重要的在于避免將不具有從輕處罰根據且應適用疑罪從無裁判的疑案也納入從輕處罰的范圍,維護疑罪從無自身內涵的合法性。在同一犯罪內的疑案中,不能因為存疑的事實不影響罪名和法定刑就用概括性認定去否定同種的擇一認定。明確擇一認定與概括性認定的界限,可以為不法結果的歸責提供合法的理由并避免邏輯上的自相矛盾。然而,明確擇一認定與相關問題之間的界限,更多只是從形式上限制擇一認定的適用范圍,但并未明確對擇一認定應當采取何種適用立場,以及允許適用擇一認定所應遵循的原則。
三、擇一認定的適用立場
由于擇一認定限制了疑罪從無,以及在形式邏輯、規范構造、合法性根據上也不同于疑罪從輕,因而在此罪與彼罪的疑案中是否允許適用擇一認定,存在全面禁止、全面容許和有限制容許三種不同的立場。然而,是否允許適用擇一認定的關鍵不在于其限縮了疑罪從無,也不在于其與疑罪從輕存在相同的處罰結果,而在于其自身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的根據。
(一)全面禁止立場的邏輯錯位
全面禁止的立場認為,在個案正義與刑法的安定性之間發生沖突時,應當優先考慮刑法的安定性,故不允許擇一認定。〔43〕同前注〔12〕,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馬斯·魏根特書,第206 頁。擇一認定的適用不符合形式邏輯三段論的要求,〔44〕同前注〔27〕,阿圖爾·考夫曼書,第106 頁。其不僅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和罪責原則,也違反了不告不理原則。在罪刑法定原則和罪責原則下需要獨立、個別地判斷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成立犯罪,〔45〕同前注〔1〕,蔡圣偉書,第54 頁。以及在不告不理原則下需要避免突襲性裁判并賦予被告人防御權。〔46〕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實例解析》,自印本2019 年版,第298 頁。故無論是在不同構成要件之間抑或在同一構成要件內,只要行為人的行為屬于不同的行為樣態,就不允許擇一認定。在同一構成要件內的場合,例如,在《日本刑法》第178 條第2 款規定的準強奸罪中的“利用心神喪失或使心神喪失”屬于不同類型的反社會的行為樣態。第252 條規定的侵占罪中的“侵吞、持有、行使”亦屬于不同的行為樣態。故不同行為樣態之間的疑案不允許擇一認定。在不同構成要件的場合,如放火罪與失火罪、盜竊罪與窩贓罪涉及的是兩個不同的構成要件,它們的行為樣態不同,在它們之間的疑案不允許擇一認定。總之,擇一認定是為了緩和證明程度,創設了不允許創設的A 或B 構成要件,不僅動搖了疑罪唯輕原則,更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故不允許擇一認定。〔47〕同前注〔8〕,巫聰昌文,第34 頁。有學者認為,“在面對疑案時實行疑罪從無可能是唯一正確而又明智的選擇”,〔48〕同前注〔4〕,沈德詠文,第6 頁。實際上也是全面否定擇一認定的。筆者認為,全面禁止擇一認定的立場存在諸多疑問,并不能成為否定擇一認定的理由。
其一,在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中適用擇一認定雖然不符合形式邏輯三段論的要求,且法官不能確信被告人的行為究竟符合何罪的構成要件,但法官并沒有創設新的構成要件或犯罪類型,與是否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無關。由于犯罪本身的復雜性和交叉性,同一客體往往會成為不同犯罪的侵害對象,進而在立法上可能被規定為非此即彼關系的A 罪或B 罪。例如,同一財物既可能成為盜竊的對象,也可能成為詐騙的對象。因而,在A 罪與B 罪之間的疑案中,被告人實施的某一行為才可能要么符合A 罪的構成要件,要么符合B 罪的構成要件。法官不能確信到底是將存疑的事實歸類到A 罪還是B罪的構成要件的問題,說到底其不是A 罪或B 罪本身的問題,而是小前提與大前提應當如何對應的問題。換言之,這一問題不是由于刑法規范本身(大前提)的不確定所導致的,而是由于犯罪事實(小前提)本身的不確定所導致的。在適用擇一認定的場合,法官并沒有在A 罪或B 罪以外重新創設了一個能同時包含“A 罪或B 罪”的構成要件,其最終選擇論罪科刑的依據依然是刑法明文規定的。故此,適用擇一認定,并不存在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問題。在A 罪與B 罪之間的疑案中,由于犯罪事實(小前提)本身的不確定,只是不能依據形式邏輯的三段論規則進行演繹推理并得出確定的結論而已。然而,形式邏輯三段論所要處理的并不是構成要件本身的問題,而是構成要件與犯罪事實之間的真值關聯問題,況且法律的適用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個純粹的形式邏輯三段論的推論問題,而更多是在一個評價觀點下的比較和權衡問題,〔49〕參見[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律思維小學堂》,蔡圣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114-115 頁。不能將A 罪或B 罪與存疑的犯罪事實之間的真值關聯(要么A罪,要么B 罪)問題等同于大前提(法律)的存疑問題,〔50〕有學者將犯罪事實存疑的問題等同于法律存疑的問題,認為法律存疑時也應當適用疑罪唯輕原則(參見邱興隆:《有利被告論探究——以實體刑法為視角》,載《中國法學》2004 年第6 期,第146 頁;董玉庭:《論疑罪的語境》,載《中國法學》2009 年第2 期,第104 頁),筆者認為這混淆了法律本身(大前提)的問題與犯罪事實(小前提)和法律規范(大前提)如何對應的問題。有利于被告原則只能適用于犯罪事實存疑而不能適用于法律存疑的場合(同前注〔4〕,張明楷書,第58 頁;袁國何:《刑法解釋中有利于被告原則之證否》,載《政治與法律》2017 年第6 期,第128 頁)。進而認為擇一認定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因此,擇一認定在形式邏輯(三段論)上的欠缺與是否違背罪刑法定原則并無必然關聯,不能成為宣稱擇一認定不正當的理由。
其二,雖然擇一認定的適用可能會違反不告不理原則,但不能由此就認為應當全面禁止擇一認定。如后所述,在刑事疑案的裁判中,是否允許適用擇一認定實際上屬于是否允許變更罪名的問題,而是否允許變更罪名的前提在于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是否滿足犯罪事實同一性(同一案件)的要求。換言之,如果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滿足了犯罪事實同一性(同一案件)的要求,那么適用擇一認定不會造成對被告人的突襲性裁判,并不違反不告不理原則。反之,如果對具有犯罪事實同一性的疑案全面禁止擇一認定的適用,反而可能造成更為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和方法論問題。就合法性危機而言,在處于非此即彼關系的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中全面禁止擇一認定,一方面則意味著需要適用疑罪從無并無罪開釋被告人,這不僅會將疑罪從無泛化為一種對被告人越有利就越妥當且不準反思的口號和標簽,而且會嚴重背離了一般大眾(包括被告人)的法感,讓被告人在明顯具有可罰性的行為中獲得脫免制裁的抗辯理由并得到不當利益,還會違背刑法保護法益的功能和預防犯罪的目的,有損疑罪從無自身內涵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另一方面也可能會導致法官為了對明顯具有可罰性但又不能形成確信的犯罪事實給予刑罰處罰,而刻意地選擇性忽略存疑的犯罪事實,恣意或武斷地確認其存在,可能對被告人判處比適用擇一認定更為不利的刑罰,有損刑事裁判的嚴肅性、正當性及刑法的自由保障機能。就方法論問題而言,全面禁止擇一認定并適用疑罪從無作無罪裁判則必然會將具有犯罪事實同一性且不可分割的疑案采取分離式的方法各個擊破。例如,在盜竊和詐騙之間的疑案中,法官需要通過分別認定盜竊罪“有或無”和詐騙罪“有或無”,進而分別得出無罪的結論。但這種分離式的方法會使法官將刑事訴訟法上能通過變更罪名予以解決的同一案件進行分割處理,以及將刑法上僅針對同一法益主體的同一法益所實施的同一侵害行為進行分別評價,將實質一罪作為實質數罪予以對待,導致所有的疑案都只能被認定為無罪,擇一認定或疑罪從輕都沒有存在的可能或空間,進一步強化了疑罪從無是不可反思的教條。因此,以不具有犯罪事實同一性的部分疑案可能會違反不告不理原則就全面禁止擇一認定存在以偏概全的問題。
(二)全面容許立場的合法性不足
全面容許的立場認為,在刑事政策或個案正義與法的安定性之間發生沖突時,應當優先考慮刑事政策或個案正義的需要,故應全面容許擇一認定。〔51〕同前注〔12〕,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馬斯·魏根特書,第206 頁。全面容許擇一認定發端于德國1935 年修正的《德國刑法》,其中第2 條b 規定:“確認犯人違反兩個以上處罰條款中的一個條款,而事實只能擇一認定時,依照最輕的條款處罰。”雖然這一規定在1946 年被廢除,但卻成為全面容許擇一認定的制度起源。〔52〕同前注〔11〕,松尾浩也書,第136 頁。全面容許的立場認為,只要是處于非此即彼關系的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就應當允許適用擇一認定。例如,在1946 年以前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在墮胎罪與詐騙罪、醉酒后的犯罪與毒品犯罪之間的疑案,均應當允許適用擇一認定。〔53〕同前注〔12〕,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馬斯·魏根特書,第203 頁。在我國主張廣義擇一認定的觀點實質上也采取了全面容許的立場。例如,張明楷教授認為,在處于非此即彼關系的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中,適用擇一認定并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因而,在諸如交通肇事罪與幫助毀滅證據罪之間的疑案,應適用擇一認定將其裁判為幫助毀滅證據罪。〔54〕同前注〔4〕,張明楷書,第61-62 頁。然而,全面容許擇一認定會不當擴大擇一認定的適用范圍。如前所述,在此罪與彼罪之間的疑案既可能適用擇一認定,也可能適用疑罪從輕,還可能適用疑罪從無。因而,全面容許擇一認定最根本的問題就在于,可能將部分應適用疑罪從無裁判的疑案從輕處罰并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
其一,從刑事訴訟法的角度而言,擇一認定的適用實際上屬于變更罪名的問題,而變更罪名必須以此罪與彼罪存在犯罪事實同一性為基本前提。所謂的犯罪事實同一性是指由同一犯罪主體實施的同一犯罪事實。例如,同一主體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地點盜竊和搬運贓物,同一主體盜竊和詐騙同一物品等。但如在過失致人死亡罪與包庇罪及故意殺人罪與盜竊罪之間,由于二者屬于既無對立關系也無并存關系的不同犯罪類型,不僅缺少事實上的共同性,而且危害結果也不相同,〔55〕同前注〔42〕,田口守一書,第422-426 頁。即使二者是由同一主體在同一地點并針對同一被害主體實施的,二者之間也并不存在犯罪事實同一性,而是存在數個犯罪事實。因而,在此罪與彼罪的疑案中,只有在此罪與彼罪的犯罪事實具有同一性的場合,才會出現存疑的犯罪事實既可能符合此罪也可能符合彼罪的構成要件。倘若檢察機關起訴的是重罪,法官才能在不變更基本犯罪事實的前提下依職權將起訴的重罪變更為輕罪。但如果在此罪與彼罪之間存在數個犯罪事實的場合,那么在此罪與彼罪之間的疑案就并不是一個犯罪事實的存疑,而是數個犯罪事實的存疑。倘若檢察機關起訴的是重罪,由于重罪與輕罪的基本犯罪事實不同,法官不能通過變更基本犯罪事實的方式以實現對罪名的變更,而是應當在不改變基本犯罪事實的前提下裁判重罪的“有或無”。故而,如果采取全面容許擇一認定的立場,那么則意味著法院可以不受犯罪事實同一性的限制而隨意變更罪名,其可能會將原本應當適用疑罪從無處理的疑案裁判為有罪(輕罪),使其喪失了合法性根據并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因此,承認擇一認定并不意味著應當全面容許擇一認定,而應將其限制在此罪與彼罪具有犯罪事實同一性的范圍內。
其二,從刑法的角度而言,在A 罪與B 罪之間的疑案中,之所以只能對被告人判處一罪(輕罪),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被告人只實施了一個犯罪行為,但由于這個犯罪行為的某些環節無法查清,導致這個犯罪行為既可能符合A 罪的構成要件,也可能符合B 罪的構成要件。換言之,被告人實施的一個犯罪行為中已被查清楚的部分能被歸類到A 罪和B 罪共同的構成要件要素中,沒有查清楚的部分則可能被歸類到A 罪或B 罪的特有構成要件要素中。因此,在A 罪與B 罪之間的疑案中,如果判處被告人一罪(輕罪),那么A 罪與B 罪的構成要件至少存在交叉關系。然而,如果對擇一認定采取全面容許的立場,就可能將A 罪與B 罪擴張至完全不具有共同構成要件要素或者完全不交叉的場合。例如,在交通肇事罪與幫助毀滅證據罪的疑案中,有學者認為,如果贊成擇一認定,則應當認定被告人構成幫助毀滅證據罪。〔56〕同前注〔16〕,張明楷文,第61-62 頁。然而,交通肇事與幫助毀滅證據罪雖然是輕罪與重罪的關系,但兩罪并不存在共同構成要件要素或者是完全不交叉的中立關系,屬于完全不同的犯罪類型,它們“彼此間所規范的對象具有本質性的差異存在,其差異包括行為的形式,行為主、客觀要件,因此,殊難同時存在于規范同一行為的情況,亦即同一行為并不可能同時該當具有異質關系的數構成要件。從而,如有異質關系之構成要件被該當時,則必定具有數個行為存在。……在此種關系下的構成要件,同一行為根本不可能既該當一構成要件,又該當他構成要件。”〔57〕同前注〔35〕,柯耀程書,第110-111 頁。因此,在屬于中立關系的不同犯罪之間所形成的疑案,就不可能是基于一個犯罪行為形成的一個疑案,而是基于數個犯罪行為形成的數個疑案。如果將擇一認定適用于數個疑案中,那么其不是對存疑犯罪事實獨立、個別判斷的結果,而是整體判斷的結果,則必然違背罪責原則的要求。
(三)有限制容許立場兼顧刑法安定性與個案正義
有限制容許的立場認為,在刑法的安定性與個案正義之間得到平衡的范圍內應當允許適用擇一認定。〔58〕同前注〔4〕,林山田書,第256 頁。1934 年以前德國帝國法院將擇一認定限制在行為人實施了具有同等價值的同種類犯罪上,但后來的司法實踐不斷擴大其適用范圍,1935 年修正刑法時全面容許擇一認定,到1946 年廢除擇一認定的規定之后,德國聯邦法院依然承認擇一認定,但對其采取了有限制容許的立場,認為不同的犯罪之間必須具有“法倫理與心理上的可比較性”,才允許適用擇一認定。例如,在盜竊與窩贓、搶劫與勒索、詐騙與侵占、詐騙與背信、偽證與誣告等犯罪在法倫理和心理上具有可比較性,在它們之間的疑案允許適用擇一認定。但在墮胎與詐騙、賄賂與詐騙、盜竊與敲詐勒索、盜竊與詐騙、故意殺人與傷害致死等犯罪之間由于不具有法倫理和心理上的可比較性,故在它們之間的疑案不允許適用擇一認定。〔59〕同前注〔12〕,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馬斯·魏根特書,第204 頁。
如前所述,擇一認定的適用并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在此罪與彼罪之間的疑案中,擇一認定的適用與疑罪唯輕尤其是疑罪從無的適用在形式上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在實質上卻是它們各自有著不同的適用范圍與完全不同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根據。全面禁止擇一認定必然有損于疑罪從無自身內涵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并會讓明顯有罪的人在犯罪中得到不當利益。全面容許擇一認定也有損于擇一認定自身內涵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使部分應當適用疑罪從無裁判的疑案被裁判為輕罪并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因此,在一定限度內允許適用擇一認定,不僅在于確保擇一認定適用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而且更在于維護疑罪從無的核心地位及其自身內涵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其一,擇一認定的適用不得違背不告不理原則。所謂的不告不理原則是指法院審理的犯罪應以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犯罪為限,其目的是為了防止法院的突襲性裁判并賦予被告人防御權。然而,一方面,為了避免架空控訴原則、突襲被告人并剝奪其防御權,造成法院的審理無法聚焦而拖延訴訟。另一方面,為了避免頻繁的再訴而造成訴訟資源的浪費。〔60〕同前注〔46〕,林鈺雄書,第299 頁。因而,法院審理犯罪的范圍既不可能完全脫離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犯罪的范圍,也不可能完全嚴格地限制在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犯罪的范圍內。在此罪與彼罪之間的疑案中,只要檢察機關起訴的犯罪(此罪)與法院審理的犯罪(彼罪)是圍繞著具有同一性的犯罪事實展開的,那么法院適用擇一認定予以裁判雖然變更了檢察機關起訴的罪名,但并沒有改變認定檢察機關起訴的基本犯罪事實,辯方也足以辨識檢察機關起訴的基本犯罪事實,因而其并不違背不告不理原則。例如,檢察機關起訴甲盜竊了乙的財物,但被告人辯稱該財物是自己拾得的。法院窮盡所有證據始終無法確信,該財物到底是甲盜竊的還是拾得(侵占)的。在該案中,被告人只存在一個取走他人(同一法益主體)財物的犯罪事實,具有犯罪事實同一性(同一案件),法院適用擇一認定裁判甲為侵占罪,仍然是基于甲取走了乙的財物這一基本犯罪事實,辯護方也是以這一基本的犯罪事實為前提進行防御的,因而其并不違背不告不理原則。然而,在前述的交通肇事罪與幫助毀滅證據罪的疑案中,由于兩罪并不存在犯罪事實同一性,倘若檢察機關起訴的罪名是交通肇事罪,法院適用擇一認定將其罪名變更為幫助毀滅證據罪,那么法院不僅變更了檢察機關起訴的罪名,而且也變更了檢察機關起訴的基本犯罪事實,造成了對被告人的突襲并剝奪了其防御權。因此,在此罪與彼罪不具有犯罪事實同一性的疑案中,適用擇一認定是違背不告不理原則的。
其二,擇一認定的適用不得違背罪責原則。犯罪事實存疑的問題實際上是罪責原則的問題。〔61〕參見[德]克勞斯·羅科信:《刑事訴訟法》,吳麗琪譯,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127 頁。在疑案中,被告人的不法行為是否具有非難或譴責可能性,不是因為被告人具有一般意義上的主觀惡性或者人身危險性,而是因為被告人對于實際發生的不法事實具有認識或認識的可能性,并由此創設相應的刑罰。因而,對被告人的刑罰處罰也應當與責任的量相當,即禁止刑罰超過責任的程度。〔62〕參見[日] 甲斐克則:《責任原理與過失犯》,謝佳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1 頁;張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場》,商務印書館2019 年版,第247 頁。然而,在全面容許擇一認定的場合,如果不同犯罪之間不具有犯罪事實同一性,那么實際發生的客觀不法事實與輕罪的故意或過失根本不可能建立起對應關系,即實際發生的不法事實不可能處于輕罪故意(過失)的認識(可能性)范圍之內。例如,在一個故意殺人案中,法官窮盡所有的證據只能查明,被害人要么是A 殺死的(故意殺人),要么A 知道是誰殺死的(包庇)。在該疑案中,某人被殺害的客觀不法事實根本不可能處于包庇故意的認識范圍之內,包庇的客觀不法事實也不可能處于殺人故意的認識范圍之內。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包庇行為只是指向故意殺人的中間介入因素,故意殺人和包庇之間的疑案不是基于同一犯罪事實而是基于數個犯罪事實形成的疑案。如果在不具有犯罪事實同一性的場合也容許擇一認定,那么對被告人的刑罰處罰就不是基于罪責原則的要求而是訴諸于一般的主觀惡性或人身危險性的結果,使對被告人的刑罰處罰倒退到歐洲中世紀的嫌疑刑罰(Verdachtstrafte)之中,〔63〕同前注〔3〕,卡爾·恩吉施書,第66 頁。違背了罪責原則的要求。
相反,在不同犯罪具有犯罪事實同一性的場合,適用擇一認定裁判被告人為輕罪并不違背罪責原則。例如,被害人在自己家門口的樓梯上發現自己家被摔壞的電視機,證據顯示,電視機系李四從被害人家里搬出后摔壞的。檢察機關以盜竊罪提起公訴,但被告人李四卻辯稱自己就是想毀壞電視機。法官無法查明,李四的行為到底是盜竊還是故意毀壞財物。在本案中,李四實施的行為所針對是同一法益主體的同一保護法益,存疑的犯罪事實具有同一性,且又由于二者在不法上不存在位階關系,因而法官應適用擇一認定裁判李四為故意毀壞財物罪。事實上,裁判李四為故意毀壞財物罪也并沒有超出其責任程度的范圍。因為,在本案中,法官無法確信的實際上是被告人李四到底是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還是故意毀壞的意思實施行為的,但無論是非法占有的目的還是故意毀壞的意思,都具有排除他人對財物占有的意思,〔64〕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下),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958 頁。因而法官最終無法確信的是被告人李四有無利用的意思。法官認定被告人李四只有排除的意思,缺乏利用的意思,進而裁判其為故意毀壞財物罪并未超出被告人李四的認識范圍。
綜上所述,在此罪與彼罪之間的疑案中,擇一認定的適用與是否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無關,其只是對疑罪唯輕原則的補充,以防止過度適用疑罪從無而造成不妥當的結論。全面禁止擇一認定不僅會造成對被告人的過度保護,而且有損于疑罪從無自身內涵的合法性與正當性,還不利于對法益的保護和預防犯罪的實現。全面容許擇一認定不僅會擴大了有罪認定的范圍,而且也有損于擇一認定自身內涵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擇一認定的適用必須同時兼顧刑法的法益保護機能和自由保障機能,在不違背不告不理原則和罪責原則的前提下采取有限制容許的立場,確保其在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的范圍內予以適用,維護疑罪從無在疑案裁判中的核心地位。
四、擇一認定的實質限制
在有限制容許的立場下,應采取何種實質基準限制擇一認定的適用存在“法倫理和心理上的可比較性說”和“不法核心同一性說”的分歧。為了避免擇一認定適用的恣意性,限制其適用的基準必須回到刑法規范內部并結合我國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實際予以確定,以確保其適用范圍的合法性和正當性。
(一)限制基準的分歧與確立
德國司法實務的觀點認為,在處于非此即彼關系的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中,只有不同犯罪具有“法倫理與心理上的可比較性(rechtsethisch u. psychologish vergleichbare Sachverhalt)”,才允許適用擇一認定予以裁判。所謂的“法倫理與心理上的可比較性”是指依照一般大眾的法感情,不同犯罪在倫理或道德上具有可比較的非價判斷且具有相似或相同的心理關系。〔65〕同前注〔4〕,林山田書,第256 頁。例如,在盜竊和窩贓之間的疑案中,由于“窩贓者窩贓行為的是非觀念與盜竊犯的盜竊行為一樣,同樣是反道德的”,〔66〕同前注〔12〕,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馬斯·魏根特書,第202 頁。且被告人對窩贓行為與盜竊行為具有相似的心理關系,因此,對二者之間的疑案允許適用擇一認定。
“法倫理與心理上的可比較性說”雖然將擇一認定的適用限制在不同犯罪具有法倫理上的可比較性且二者具有相似或相同的心理關系的范圍內,但其提供的是一個不可把握且難以操作的模糊標準,實質上是將擇一認定適用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根據訴諸于法規范之外的倫理或道德及讓行為人對于歸責與否或程度享有決定權,〔67〕參見蔡圣偉:《重新檢視因果歷程偏離之難題》,載《東吳法律學報》1997 年第1 期,第118 頁。可能導致擇一認定的適用具有恣意性。其一,法倫理是將社會道德這種內在的戒律作為法律上應該做什么或不應該做什么的準則并指導人們行為的動機規則。〔68〕參見[德]H·科殷:《法哲學》,林榮遠譯,華夏出版社2003 年版,第91 頁。雖然法律應符合道德的要求不應當遭到拒絕,但這絕不意味著法律必須符合道德并對道德亦步亦趨。〔69〕參見[奧]凱爾森:《純粹法理論》,張書友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 年版,第46 頁。因為包括法感情、道德在內的法倫理是一個多層次、有漏洞,以及存在內在沖突的構造物,難以提供可靠的依據,在具體應用中可能導致高度個人性的決定,并最終通過高度的主觀性去解決問題,〔70〕參見[德]齊佩利烏斯:《法哲學》,金振豹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178-183 頁。其會直接導致司法裁判的不確定性,最終反而有損刑法的安定性和個案正義的實現。其二,以心理上是否具有可比較性作為能否適用擇一認定的基準,會使得是否允許適用擇一認定裁判有罪的標準取決于被告人的主觀心理活動,導致擇一認定的適用缺乏客觀性和一致性。例如,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在盜竊與詐騙、故意殺人與傷害致死等犯罪之間的疑案中,由于盜竊與詐騙、故意殺人與傷害致死等犯罪在心理上是相互排斥或對立的,不具有可比較性和類似性,因而不允許適用擇一認定。〔71〕同前注〔4〕,烏爾斯·金德霍伊澤爾書,第496 頁。然而,以心理上是否具有可比較性作為是否允許適用擇一認定的基準必然會導致司法裁判的恣意性。因此,將是否允許適用擇一認定的基準訴諸于法規范以外的“法倫理和心理上的可比較性”,會導致擇一認定的適用陷入道德主義和主觀主義的窠臼之中,難以提供客觀有效的判斷基準。
有力的觀點認為,在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中,由于“法倫理和法心理上的可比較性”是難以掌握且易生恣意性的,因而只有在不同犯罪具有“不法核心同一性(die Identiaet des Unrechtskerns)”的場合,才允許適用擇一認定。所謂的“不法核心同一性”是指處于非此即彼關系的不同犯罪不僅侵害相同的法益,而且對相同法益的侵害程度亦相當。所有不屬于這種情形的均不允許適用擇一認定。〔72〕同前注〔12〕,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馬斯·魏根特書,第207 頁。例如,在盜竊與詐騙之間的疑案中,由于二者所侵害的都是他人的財產權,且對他人財產權的侵害程度亦相當,因而允許適用擇一認定予以裁判。〔73〕同前注〔4〕,烏爾斯·金德霍伊澤爾書,第496 頁。
筆者認為,在此罪與彼罪的疑案中,將擇一認定的適用限制在“不法核心同一性”的范圍內,實質上是要求此罪與彼罪在不法內涵上是等價的,其不僅為擇一認定的適用確立了實質的正當化根據,而且也確保了將不法結果歸責于行為人的故意或過失不違背罪責原則。
其一,作為是否允許適用擇一認定并以此裁判被告人成立何種犯罪的基準,應當回溯到刑法規范中去發現和獲取,因為任何離開規范的比較都是偶然、任意和無方向的。〔74〕同前注〔27〕,阿圖爾·考夫曼書,第51 頁。以“不法核心同一性”作為允許適用擇一認定的實質判斷基準,實際上是以犯罪的本質(法益)作為思考的出發點。一方面,誠如伽達默爾所言:“‘事物本質’這個法律概念指的并不是派別之間爭論的問題,相反,它是一種界限,用來限制那些頒布法律的立法者的專橫意志和對法律所作的解釋。求助事物本質就是轉向與人的希望無關的秩序。”〔75〕[德]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哲學解釋學》,夏振平、宋建平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年版,第72 頁。另一方面,考夫曼指出:“‘事物本質’是指向類型的。從‘事物本質’產生的思維是類型式思維。”〔76〕[德]亞圖·考夫曼:《類推與“事物本質”——兼論類型理論》,吳從周譯,新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版,第107 頁。類型式思維不僅是“是與否”(同一性)的問題,也是“或多或少(Mehr-oder-Minder)”(差異性)的問題,它通過類比的方法建立起來的具有關聯性的不同事物,具有層級性的特征。〔77〕參見[德]阿圖爾·考夫曼:《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傳》,舒國瀅譯,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112 頁。因而,以犯罪本質(法益)作為判斷的基準,不僅要考慮處于非此即彼關系的不同犯罪是否侵害了相同的法益,而且也要考慮對相同法益的侵害程度是否相當(或不法程度的差異是否可以被忽略)。在相同的法益(評價觀點)下,如果不同犯罪的不法程度是相當的(或不法程度的差異是可以被忽略的),那么則說明它們在不法上是等價的。〔78〕同前注〔70〕,齊佩利烏斯書,第310-311 頁。因此,以“不法核心同一性”作為允許適用擇一認定的判斷基準,實質上是將擇一認定的適用范圍限制在不同犯罪等價不法的范圍內,奠定了不同犯罪在不法上應當受到相同的否定性評價之基礎,進而為擇一認定的適用確立了正當化根據,提供了客觀有效的判斷標準,保證了裁判結論具有實質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
其二,犯罪事實存疑的問題說到底是罪責原則的問題。〔79〕同前注〔61〕,克勞斯·羅科信書,第127 頁。在擇一認定的場合,雖然不能像犯罪事實清楚的案件那樣,能夠直接確定客觀不法事實與責任之間明確的對應關系,但這并不意味著擇一認定的適用可以違背罪責原則。在此罪與彼罪之間的疑案中,只有以“不法核心同一性”為判斷基準才能確保擇一認定的適用依然處于被告人責任程度的范圍內,將不法結果歸責于行為人的故意或過失不違背罪責原則。因為,在“不法核心同一性”的基準下,能夠適用擇一認定予以裁判的疑案所涉及的不同犯罪在不法上是等價的,其法定刑的輕或重,就主要取決于責任程度的輕或重(責任具有創設和量定刑罰的功能)。〔80〕參見張明楷:《犯罪論的基本問題》,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399 頁。例如,被害人乙系被告人甲擊打致死,法院窮盡所有的證據,依然無法查明被告人到底是故意殺人還是過失致人死亡。然而,無論是故意殺人還是過失致人死亡,它們的客觀不法內涵(致他人死亡)是等價的,其分別與故意和過失對應并建構起了輕重不同的犯罪,雖然法院不能查明被告人對造成被害人的死亡到底是基于犯罪故意還是犯罪過失,但將被害人乙死亡的不法結果歸責于被告人甲的過失,其依然處于被告人認識可能性的范圍內,將其裁判為過失致人死亡罪并不違背罪責原則。因此,以“不法核心同一性”作為允許適用擇一認定的實質判斷基準,可以有效地將被告人承擔責任的范圍限制在被告人具有認識或認識可能性的范圍之內,并不會與罪責原則相抵牾,有效地平衡了刑法的法益保護機能和自由保障機能。
(二)限制基準的具體展開
雖然“不法核心同一性”是允許適用擇一認定的充分必要條件,但其具體內涵(侵害相同的法益且侵害相同法益的程度相當)并非不言自明的,需要結合我國刑法分則條文、相關司法解釋的具體規定,并綜合考量此罪與彼罪之間的規范關系及解釋結論的妥當性后方能得到明確。
1.相同的法益
不同犯罪具有相同的法益之所以是適用擇一認定的前提和基礎,是因為:一方面,在我國“定性+定量”的立法模式下,雖然不同犯罪存在相同的法益并不意味著不同犯罪必然是等價的,但其至少說明不同的犯罪屬于同質的犯罪類型并具有等同評價的基礎和前提,〔81〕同前注〔38〕,趙春玉文,第77 頁。進而為擇一認定的適用奠定了正當性前提。另一方面,在此罪與彼罪的疑案中,如前所述,只有此罪與彼罪存在犯罪事實同一性,法院才能對疑案變更罪名,而相同的法益則又是判斷犯罪事實同一性的實質依據。〔82〕同前注〔42〕,田口守一書,第426 頁。但問題在于,法官應當如何判斷不同犯罪存在相同的法益。張明楷教授認為,相同的法益是指在同一個罪刑規范內的保護法益,其可以是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和個人法益。一般而言,刑法分則不同章節所規定的犯罪基本上不可能具有相同的法益。例如,生產、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罪的保護法益是市場經濟秩序,詐騙罪的保護法益是財產權,二者不具有相同的法益。〔83〕同前注〔80〕,張明楷書,第389 頁。筆者認為,在疑案的場合,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如果將相同的法益僅限制在同一罪刑規范內,那么則會導致超出同一罪刑規范的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只能分別適用疑罪從無裁判為無罪。例如,在故意殺人和放火之間的疑案中,由于故意殺人罪侵害的是他人的生命權,放火罪侵害的則是公共安全,二者所侵害的法益并不相同且不符合犯罪事實同一性的要求,因而,對被告人既不能適用擇一認定予以裁判,也不能適用疑罪從輕予以裁判(疑罪從輕的適用也必須以具有相同的法益為前提),且放火罪也不是故意殺人罪的截堵性規定,因而只能采取分離式的方法交互適用疑罪從無分別判斷放火罪的“有或無”及故意殺人罪的“有或無”,最終裁判被告人無罪。再如,在盜竊與窩贓之間的疑案中,由于盜竊罪侵害的是他人的財產權,窩贓(掩飾、掩瞞犯罪所得罪)侵害的則是社會管理秩序或司法權,因而,對被告人不能適用擇一認定或疑罪從輕予以裁判,只能適用疑罪從無將其裁判為無罪。然而,上述結論是無法被接受的。因此,除非在此罪與彼罪之間的疑案中不加限制地全面容許擇一認定或者疑罪從輕,否則將相同的法益限制在同一罪刑規范內就可能帶來處理結論的不妥當性。
其二,在同一罪刑規范或者刑法分則同一章節內的不同犯罪之間即使存在相同的集體法益,在疑案的場合也不應當將其作為判斷是否存在相同法益的標準,否則在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中就可能會違背罪責原則和有利于被告原則的要求,不當加重對被告人的處罰。例如,海關查獲了被告人走私的軍用手槍,但被告人辯稱以為自己走私的是非洲象牙。法官無法查明,被告人是否認識到當時走私的是槍支還是珍貴動物制品。在本案中,無論是走私槍支還是走私珍貴的動物制品都侵害了國家的對外貿易管理制度這一集體法益,如果僅止于此,就可能產生兩種結論:一是,雖然被告人對走私的具體對象不明確,但被告人具有走私的概括故意且都侵害了國家對外貿易管理制度,應根據實際走私的具體對象將其認定為走私武器罪(我國司法解釋的做法);二是,走私珍貴動物制品罪侵害對外貿易管理制度的程度低于走私武器罪(走私武器罪的法定刑高于走私珍貴動物制品罪的法定刑),因而應當適用疑罪從輕將其裁判為走私珍貴動物制品罪。筆者認為,這兩種做法都存在問題。第一種做法將走私武器罪和走私珍貴動物制品罪僅解釋為“走私”行為,概括性地認定“行為人具有走私故意且實施了走私行為”,忽視了二者所侵害的具體客體、有責不法內容及法定刑的差異性,其實際上是一種變相意義上的類推行為。第二種做法雖然考慮到具體客體、有責不法的內容及法定刑的差異,但并沒有考慮到單純對制度或秩序的違反只存在“是與否”的問題,而不存在“多與少”的問題,〔84〕參見王瑩:《情節犯之情節的犯罪論體系性定位》,載《法學研究》2012 年第3 期,第131 頁。以及客觀不法事實與認識內容之間的對應問題。因而,這兩種做法都違背了罪責原則和有利于被告原則。或許有人認為,以對外貿易管理制度作為判斷標準,并不會形成上述兩種結論,因為無論是槍支還是珍貴動物制品都屬于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或物品,認定為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罪并不會違背罪責原則和有利于被告的原則。〔85〕在故意犯罪的場合,犯罪事實存疑和認識錯誤所需要解決的都是客觀不法事實與主觀認識如何對應的問題。在認識錯誤時,理論上普遍認為,對不同條款中的走私對象發生認識錯誤,屬于抽象的事實認識錯誤,因而應當在兩者不法重合或等價的范圍內予以認定。但筆者認為,雖然以對外貿易管理制度這一集體法益為標準可以將走私槍支和走私珍貴動物制品等同評價為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或物品,但其與走私槍支或走私珍貴動物制品之間已經不屬于疑罪從輕的問題,而是援用截堵性構成要件的問題。〔86〕援用截堵性構成要件并不限于犯罪事實存疑的場合,其核心在于確保犯罪的主客觀相統一。
為了避免適用疑罪從無而產生不妥當的結論,或者違背罪責原則無限擴大擇一認定或疑罪從輕的適用范圍,筆者認為,在疑案的場合,相同的法益既不應當限制在同一罪刑規范內,也不應當以集體法益(國家法益和社會法益)作為判斷標準,而應當以個人法益作為判斷標準。因為集體法益“可能包羅萬象:從經濟利益、國家意識到特權保障、意識形態等,甚至可以及于全球政治之策略”。〔87〕陳志龍:《法益與刑事立法》,自印本1997 年版,第129 頁。例如,《刑法》第293 條所規定的尋釁滋事罪,雖然其侵害的集體法益是社會公共秩序,但其中各項行為所侵害的具體法益又各不相同,隨意毆打他人侵害的是他人的健康權;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侵害的既可能是他人的健康權,也可能是他人的名譽權;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毀損、占用公私財物侵害的是他人的財產權;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侵害的是他人生活的安寧與平穩。因而,“從結果上來看,構成合法法益基礎的是單個的個人利益,而不是通過個人來實現其功能的群體和國家的利益。”〔88〕[德]京特·雅克布斯:《保護法益?——論刑法的合法性》,趙書鴻譯,載趙秉志主編:《當代德國刑事法研究》(第1 卷),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32 頁。因而,在疑案的場合,以集體法益作為判斷相同法益的標準,不僅可能會導致在不同犯罪中遭受侵害的相同個人法益被遮蔽(如故意殺人和放火之間的疑案),而且也可能會導致在不同犯罪中遭受侵害的不同個人法益被混同(如走私槍支與走私珍貴動物制品之間的疑案),最終導致裁判結論的不妥當性。
在此罪與彼罪之間的疑案中,相同的法益應當界定為相同的個人法益。當然,以個人法益作為判斷相同法益的標準,并不意味著需要將個人法益遞歸到不可再具體的個人法益上,否則其同樣會導致大量的不同犯罪不存在相同的法益。筆者認為,在不同犯罪的個人法益能夠形成競合或重合之處,就可以認定存在相同的個人法益。只有以相同的個人法益作為判斷的標準,才能明確不同犯罪的具體不法內涵,使被告人需要承擔責任的范圍具體化。這樣既可以防止疑罪從無的過度適用,又不至于不當擴大擇一認定或疑罪從輕的適用范圍,真正落實罪責自負原則的要求。例如,在上述走私槍支和走私珍貴動物制品之間的疑案中,從個人法益的角度而言,走私槍支侵害或威脅的是他人的生命權或健康權,走私珍貴動物制品所侵害的是與人的發展密切相關的野生動物資源,它們不具有犯罪事實同一性,法官應當適用疑罪從無將其認定為無罪。當然,檢察機關可以將起訴的事實變更為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法官可以援用截堵性構成要件將其認定為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罪。
2.相當的不法程度
在此罪與彼罪之間的疑案中,相同的法益只能確保不同犯罪具有同質性,只有它們的不法程度(侵害相同法益的程度)亦相當時,方允許適用擇一認定。在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具有犯罪事實同一性(同一案件)的前提下,不同犯罪的不法程度是否相當是從相同法益是否值得相同保護的角度而言的。例如,在盜竊罪與詐騙罪之間的疑案中,無論是盜竊抑或詐騙都侵害了值得相同保護的他人財產權,其并不會因為犯罪事實的存疑就說明其受保護的程度不同。
筆者認為,在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中,之所以要將擇一認定的適用限制在不法程度相當的不同犯罪之間,是因為:首先,相當不法程度是適用擇一認定的合法性和正當化根據所在。在此罪與彼罪之間的疑案中,此罪與彼罪具有相同的法益只能說明它們具有相同的犯罪性質(同質性),并不能說明它們的不法是等價的。不同的事物能夠獲得等同的評價,不僅因為它們具有同質性,還因為它們之間的程度相當或者差異性是可以被忽略不計的。〔89〕同前注〔70〕,齊佩利烏斯書,第310-311 頁。故而,在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中適用擇一認定,只有不同犯罪的不法程度相當,才能說明遭受侵害的相同法益是值得相同保護的,進而才能說明實際發生的不法結果無論是在此罪抑或彼罪中均應受到相同的否定性評價,從實質上確立了擇一認定適用的正當性范圍,以及對被告人予以刑罰處罰的合法性理由。其次,相當的不法程度是確保擇一認定的適用不違背罪責原則的核心。在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中,不法程度相當的不法結果,由于其與不同的罪責因素相結合,必然會形成嚴厲程度不同的刑罰處罰。例如,在故意殺人與過失致人死亡之間的疑案中,就值得相同保護的他人生命權而言,二者的不法程度并無差別,之所以故意殺人的法定刑高于過失致人死亡,是因為致人死亡的不法結果分別與故意和過失相結合所致。二者之間的疑案實際上是法官對被告人是出于故意還是過失不能形成確信,如后所述,故意與過失在責任上是一種位階關系,適用擇一認定將其裁判為過失致人死亡罪并援引相應的法定刑,依然能確保致人死亡的不法結果與過失之間存在對應關系,并未超出被告人責任程度的范圍。故而,只有在不同犯罪的不法程度相當的場合,適用擇一認定裁判被告人成立較輕的犯罪,才不至于與罪責原則相抵牾。最后,相當的不法程度是法官適用擇一認定選擇罪名和援引法定刑的重要依據。法官在適用擇一認定時,必須考慮相當的不法程度在不同犯罪中對選擇罪名和援引法定刑的意義,否則就可能沒有辦法最終確定所需要裁判的罪名和援引的法定刑。例如,甲到某珠寶店取走了該店價值40 萬元的珠寶。現有的證據可以明確排除甲是無罪的,但法官無法查明,甲到底是盜竊還是詐騙。在該種場合,法官應適用擇一認定裁判甲為輕罪。但由于立法上對盜竊和詐騙規定的類型化成立條件(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及相應的法定刑完全相同,此時法官不能隨意選擇,只能根據相當的不法程度來確定最終應當適用的罪名并援引相應的法定刑。我國司法解釋明確規定,盜竊財物的價值30 萬元至50 萬元以上為“數額特別巨大”,詐騙財物的價值50 萬元以上為“數額特別巨大”。倘若被告人甲所在的省確定30 萬元為盜竊數額特別巨大財物的起點,50 萬元為詐騙數額特別巨大財物的起點。對于甲而言,盜竊40 萬元的珠寶應當認定為“數額特別巨大”,并援引“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詐騙40 萬元的珠寶則應當認定為“數額巨大(3 萬元至10 萬元以上50 萬元以下)”,并援引“3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因此,在本案中,法官應選擇詐騙罪并援引相應的法定刑作為裁判的依據。
然而,一些客觀不法程度相當的犯罪,可能會因為評價者對故意或過失的立場和定位不同,會直接影響到不法程度是否相當的判斷,進而在疑案中會出現其到底是適用疑罪從輕、援用截堵性構成要件抑或擇一認定的分歧。例如,故意殺人與過失致人死亡、故意傷害(重傷)與過失致人重傷、(造成嚴重后果的)放火與失火的客觀不法程度是相當的。在行為無價值論中,故意和過失是主觀違法要素,如果認為故意和過失是位階關系,那么故意殺人與過失致人死亡等犯罪在不法上是位階關系,在它們之間的疑案應適用疑罪從輕予以裁判;如果認為故意和過失是對立關系,那么故意殺人與過失致人死亡等犯罪則是不法程度不相當的對立關系,在它們之間的疑案不能適用疑罪從輕或擇一認定,只能繞道援用截堵性構成要件來解決疑案的問題(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立場)。在結果無價值論中,故意和過失不是主觀違法要素而是責任要素,故意和過失無論是位階關系還是對立關系,故意殺人與過失致人死亡等犯罪在不法上都只能是等價關系,在它們之間的疑案應適用擇一認定予以裁判。上述不同立場和定位的分歧主要在于,故意和過失的體系性地位到底是主觀違法要素還是責任要素,以及故意和過失是位階關系還是對立關系的問題。筆者認為,故意和過失是責任要素,而非主觀違法要素,且二者是位階關系。囿于前者屬于刑法基本立場的問題,故本文不在此討論。至于故意和過失的關系,其核心在于如何判斷二者的意志因素。雖然故意和過失都具有創設刑罰和限定刑罰的功能,〔90〕同前注〔62〕,甲斐克則書,第1 頁。但這一功能的實現在于行為人對實際發生的客觀不法事實具有認識或認識可能性,對行為人的非難或譴責也僅限于行為人具有認識或認識可能性的范圍,意志因素僅是區分犯罪故意和犯罪過失的分界(表面)因素,其與應受刑罰處罰的必要性和嚴厲性程度沒有關系。犯罪故意和犯罪過失的關系是由二者對客觀不法事實的認識程度所決定的,因此,二者是位階關系,不是對立關系。在故意殺人與過失致人死亡等犯罪之間的疑案應適用擇一認定予以裁判。
與上述情形不同,在不同犯罪之間原本就存在互斥的不法要素(A 或非A)的場合,例如,在存在相同法益的盜竊罪與詐騙罪、盜竊罪與侵占罪、受賄罪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之間,都存在互斥的不法要素(A 或非A)。〔91〕參見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 年版,第925 頁;同前注〔30〕,甘添貴書,第96 頁。具體而言,在盜竊罪和詐騙罪中分別存在違反被害人意志并通過自己或第三人的行為取得財物和不違反被害人意志且通過被害人或受騙者的處分行為取得財物;在盜竊罪與侵占罪中分別存在他人占有的財物和自己占有或無人占有的財物;〔92〕同前注〔64〕,張明楷書,第970 頁。在受賄罪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中分別存在國家工作人員和非國家工作人員。然而,這些具有互斥的不法要素的不同犯罪雖然在不法上是對立關系,但這并不影響它們侵害相同法益的程度是相當的,因而它們在不法上是等價的。〔93〕有學者認為,在不同犯罪中規定互斥的不法要素(A 或非A)只是為了確保刑法規范的完整性,可以將其中一個要素解釋為責任要素,使不同的構成要件在不法上具有位階關系(同前注〔91〕,黃榮堅書,第925 頁)。因為,從保護法益的角度而言,在不同犯罪中規定互斥的不法要素的目的在于實現對相同法益的完整保護,不會因為它們之間存在互斥的不法要素就會將任何可罰的情形排除在外,其無論如何都會實現其中之一。〔94〕同前注〔27〕,烏爾里希·克盧格書,第56 頁。從侵害法益的角度而言,在不同犯罪中規定互斥的不法要素只能說明侵害相同法益的方法或手段不同,其并不會導致侵害相同法益的程度不同。因此,在具有互斥的不法要素的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中,不同犯罪的不法依然是等價的,并不影響擇一認定的適用。
在具有互斥的不法要素的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中,實際上是法官對被告人的行為到底符合哪一個互斥的不法要素不能形成確信。例如,在盜竊和普通侵占之間的疑案中,法官無法查明,財物到底是由他人占有還是由被告人自己占有。在盜竊與詐騙之間的疑案中,法官無法查明,被告人到底是通過違反被害人意志的方式取得他人財物,還是通過不違反被害人意志的方式取得他人財物。法官適用擇一認定予以裁判時,就需要在互斥的不法要素中選擇一個輕罪中所具有的不法要素來實現對被告人的輕判。但值得指出的是,如前所述,不同犯罪中互斥的不法要素并不會導致它們侵害相同法益的程度有所不同,藉此,不同犯罪法定刑的輕重就不是由互斥的不法要素所引起的,而是由它們輕重不同的可譴責性程度引起的。例如,在盜竊與普通侵占之間,無論是他人占有的財產還是自己占有的財產,雖然二者對于財產權的侵害程度并無不同,但二者卻可以表明被告人與法相敵對意思程度的高低及預防必要性的大小,進而說明它們可譴責性程度的高低。故此,具有互斥的不法要素的不同犯罪雖然在不法程度上并無差別,但與其相對應的可譴責性程度卻有所不同。適用擇一認定裁判被告人成立輕罪實際上是在被告人責任程度的范圍內選擇了一個對被告人更為有利的責任因素。因此,在具有互斥的不法要素的不同犯罪之間的疑案中,相當的不法程度奠定了適用擇一認定的正當性基礎并確保對被告人的刑罰處罰并不違背罪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