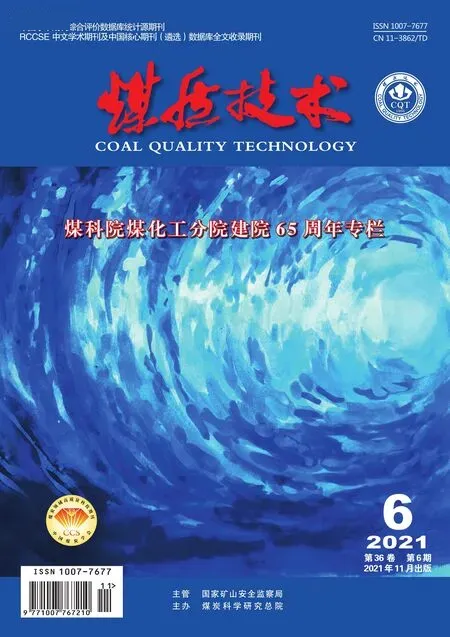雙碳背景下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方向構建
王曉磊,陳貴鋒,李文博,黃 澎,王乃繼
(1.煤炭科學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化工分院,北京 100013; 2.煤炭資源高效開采與潔凈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13;3.國家能源煤炭高效利用與節能減排技術裝備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13;4.煤科院節能技術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
0 引 言
我國能源結構正向綠色低碳轉型,但煤炭作為主體能源地位在短期內難以改變。在雙碳目標的背景下,我國加速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綠色能源轉型與保障能源安全兩者相互關聯,煤炭作為可再生能源平抑波動的穩定器,相當長的時期內將與可再生能源相互依存,并支撐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消納需求[1-2]。
我國是全球最大的能源生產和消費國。近年來,我國油氣對外依存度持續上升,能源安全面臨嚴峻挑戰。2020年,我國原油和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分別為73%和43%[3],我國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56.8%。據預測,到2030年我國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仍將約達50%。煤炭是我國能源供應的“穩定器”和“壓艙石”,起到兜底保障作用[4]。
煤炭在補充石油不足、緩解石油對外依存度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煤炭通過轉化可以生產90%以上的燃料油和化工產品,近年來煤液化、煤制烯烴等技術產業化,具備了替代5%進口石油的能力,預計未來10年左右其替代能力將達10%,煤炭正在由燃料為主向作為原料轉變。
煤炭轉化可以實現煤炭的清潔高效低碳利用[1]。煤直接液化與煤制天然氣的能效分別達58%、60%;煤炭轉化產生的CO2濃度高,利于CO2的捕集及無害化處置;在轉化過程中,煤中硫轉變成硫磺,得到資源化利用;煤制烯烴等化學品可將碳固定在產品中,從而實現減碳。燃煤發電供熱可以實現超低排放。目前,我國建成一批大容量、高參數煤電超(超)臨界機組,裝機比例超過10%,形成全球最大的煤電供應體系,污染物排放可達天然氣標準。
綜上所述,煤炭清潔利用已取得重大進展,是保障我國能源安全的基石[5-6]。但現實推廣應用中煤炭清潔利用也面臨著重大科學和技術問題,需加強頂層設計[7]并從國家層面對其利用方向進行構建。
1 煤炭清潔利用面臨的科學和技術問題
根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2020煤炭行業發展年度報告》,目前我國建成投運各種大型氣化爐320多臺(套),形成煤制油產能931萬t、煤制氣產能51.05億Nm3、煤制烯烴產能1 582萬t、煤制乙二醇489 萬t、煤制合成氨產能6 000 多萬t[8]。傳統粗放的煤炭利用方式是SO2、NOx和CO2等排放的主要來源,必須改變現有的利用方式,促使煤炭利用向高效率、近零污染和低碳排放的清潔高效利用的方式轉變。煤炭清潔利用主要包括兩大途徑:①高效率超低排放的供熱和發電;②由燃料向原料轉變,生產清潔的油氣產品、大宗化工新材料和精細化學品,同時推動煤炭轉化與可再生能源聯合制氫、制材料和化學品等。
煤炭清潔利用的核心是解決煤炭利用過程中的效率、污染控制和碳排放問題,需要從理論探索、核心技術開發、工程應用技術等方面開展研究。
我國煤炭利用的基礎理論探索、部分關鍵核心技術及裝備研制等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仍有較大差距,亟需攻關突破與進一步節能提效,以達低碳、節水以及降低成本之功效。火力發電領域靈活燃燒發電、整體煤氣化聯合發電(IGCC)均為清潔低碳需解決的關鍵技術問題。此外,各種反應器與燃燒器的研發設計、新材料研究、大型裝備與系統集成等重大工程技術問題和大型科學儀器、表征手段等也是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發展趨勢[9-10]。煤炭清潔高效利用面臨的重大科學問題主要包括以下5個方面:
(1)煤炭清潔轉化的過程調控機理、反應路徑、產物定向轉化、分子裁剪等基礎理論;
(2)催化劑界面結構調控催化特性、高碳大分子高效低碳轉化相關的碳碳鍵、碳氫鍵活化機制;
(3)各種蒸餾、精餾、加氫、裂化等關鍵反應和分離裝備的過程強化、設計方法和放大準則;
(4)單元技術耦合集成系統技術的工程科學;
(5)煤清潔轉化利用過程污染物產生和控制機制。
2 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方向
2.1 總體目標
瞄準我國可再生的清潔能源短缺、油氣對外依存度高、大宗化工材料大量依靠進口等經濟社會發展重大需求,聚焦煤炭轉化、煤炭高效燃燒和污染物控制及碳減排等相關領域,開展探索性、基礎性、戰略性研究,從原理層面解決煤炭利用碳排放和燃燒污染物排放控制問題,提供以煤為基礎的清潔能源生產與利用技術、以煤為基礎的高端材料制造技術,從而推動煤炭利用實現“零污染物排放、零碳排放”。
2.2 重點攻關方向
在2030年前“碳達峰”的歷程中,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重要作用在于保障可持續發展中減碳,從而在現有及未來的能源結構體系之間實現柔性的可持續轉變[11]。基于此,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將重點在煤制液體燃料及化工品、煤炭氣化、煤炭高效燃燒和污染物控制及碳減排等4個方向攻關。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方向架構如圖1所示。

圖1 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方向架構Fig.1 Construction framework of clean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coal
2.2.1煤制液體燃料及化工品
煤液化制油是保障我國能源供給、能源安全以及改善能源結構的戰略性舉措,可有效緩解我國能源安全帶來的挑戰,已成為我國能源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煤基油品具有大比重、高熱值、高熱容、高熱安定性、低凝點、富含高張力籠狀烴類物質等特點,相比于石油基油品,煤基油品更適于制備航空煤油等高能特種燃料;煤制化工品可將煤中碳轉移到液體產品中,從而減少碳排放。
煤炭液化包括直接液化和間接液化,兩者均實現了百萬噸級工業示范,相關設備大部分已實現國產化,但在反應過程優化、催化劑性能提升、產物精細化和高質化利用、降低水耗能耗以及固廢資源化利用等方面仍有較大提升空間;煤制化工品需進一步降低水耗和能耗,實現產品的靈活調變;煤轉化與可再生能源制氫的大規模耦合剛起步,還需在系統規模匹配、穩定運行配合、工藝優化方面加強研究[12-14]。
攻關內容:突破富油煤全過程高效利用關鍵技術裝備,攻克1批煤炭液化及低階煤分質分級利用關鍵技術,發揮煤液化油品特點,研發高端特種燃料和高附加值化工產品及功能化學品;延伸煤制烯烴、乙二醇等多元化、差異化產業鏈,開展煤基生物可降解材料項目示范[14],建設煤轉化與可再生能源制氫耦合示范工程。
2.2.2煤炭氣化
煤氣化技術是煤炭清潔高效轉化的龍頭技術。近年來,多噴嘴對置式水煤漿氣化技術、水煤漿水冷壁廢鍋煤氣化技術、東方爐粉煤氣化技術、航天粉煤加壓氣化技術、“神寧爐”干煤粉氣化技術等逐步實現自主化,已進入大型化、長周期運行階段。但現有技術和裝備與國際先進技術相比仍有差距,在雙高煤(高灰分、高灰熔融性)適應性、裝置可靠性、進一步大型化、降低投資和運行成本等方面仍有較大發展空間[15-17]。
攻關內容:系統掌握煤氣化過程中污染物遷移轉化機理,拓寬對難氣化原料煤和復雜原料的適應性,開發5 000 t/d大型氣化爐,單位有效氣成本降低20%,突破催化氣化、加氫氣化等新型煤氣化關鍵技術并優化工藝,降低裝置投資和運行成本。
2.2.3煤炭高效燃燒
高效煤粉燃燒技術及煤粉工業鍋爐系統已日趨成熟,可使工業鍋爐熱效率達90%以上[18],但技術產品相對單一;火電企業要求煤電實現深度調峰、提高機組運行靈活性;在發達國家較為成熟的生物質與礦物燃料耦合燃燒技術也面臨燃燒效率低等問題[19]。煤炭高效燃燒需向綠色、低碳、智能化等方向轉型,通過先進煤炭燃燒技術,從燃料源頭降碳、燃燒中提高能效,實現燃燒技術體系升級革新,部分替代分布式能源領域天然氣,達到與天然氣相當的燃燒和減排作用[20]。
攻關內容:研發新型煤炭清潔燃燒技術,建成百萬噸級“固體天然氣”制備示范工程,碳排放強度降低50%以上,其中固體天然氣指燃燒和排放特性與天然氣相同的人工粉體燃料;開發以煤基燃料為主的高效燃燒技術,系統綜合熱效率達到98%以上,煙氣污染物達到近零排放;在分布式用能領域實現替代天然氣燃料500億m3。
2.2.4污染物控制及碳減排
現代煤化工污染物控制技術有待進一步提升,如煤化工廢水處理技術存在瓶頸,并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零排放”[21-22]。而日益嚴格的環保要求燃煤過程中的煙塵、SO2和NOx同時達到零排放;工業窯爐煙氣量較小,現有脫硫脫硝技術投資及運行成本高,亟需開發1種投資、運行成本低的脫硫脫硝一體化新工藝技術及裝備;大量煤化工含鹽廢水及高有機物含量、高復雜有機物成分的濃鹽廢水亟需低成本的資源化利用技術[23-24]。現有低碳/脫碳技術無法支撐我國實現“碳中和”目標,CCS、CCUS技術仍為碳減排研究的主要攻關技術之一。
攻關內容:研發高效污染物脫除技術、多污染物協同控制技術,實現工業窯爐煙氣中塵、硫、硝和重金屬污染物等一體化脫除;突破煤化工高鹽廢水、高濃有機廢水深度處理技術,實現廢水零排放;研發煤化工“三廢”資源化利用技術,建立綠色現代化煤化工產業體系;有效推進甲烷和CO2自熱重整制合成氣、CO2催化轉化制高值化學品和燃料等資源化利用技術,同時通過工藝優化、提高能效等措施,盡可能減少CO2排放量。
3 結 語
經過20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煤炭轉化技術正加速邁向清潔高效低碳方向,煤化工產業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發展,燃煤發電供熱追求超低排放、極致高效,燃煤工業鍋爐污染物排放也可達到超低排放標準,充分說明煤炭可以被清潔高效利用。
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是我國“碳中和”歷程中不可或缺的板塊。不同來源的能源消費預測均指出,未來幾十年我國能源結構仍將持續富煤、缺油、少氣的格局,在進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顛覆性技術創新的同時,重視已有利用方式的更新,提高煤炭作為化工原料的綜合利用效能,從而推進我國煤炭由基礎能源向主要能源和兜底保障轉變,加速清潔高效、安全低碳的現代能源體系的建設,從而高質量保障我國能源安全和能源清潔供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