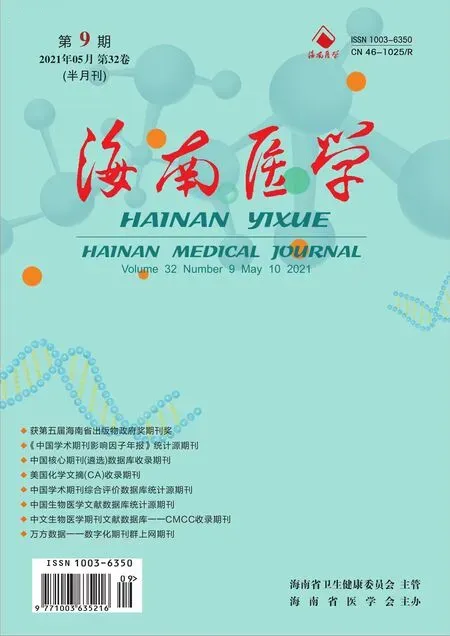HIV感染者麻醉相關問題的研究進展
揭芷萱 綜述 韓亞坤,何仁亮 審校
廣東醫科大學附屬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麻醉科,廣東 深圳 518000
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是一種由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引起的傳染病,截至2019 年10 月底,我國報告現存活HIV 感染者/AIDS 患者(簡稱HIV/AIDS 患者)95.8 萬[1]。隨著病患的增多,其病理生理進展導致的機會性感染及由其誘發和伴隨的疾病也隨之增加,需要麻醉和手術的患者越來越多。據統計,20%~25%的HIV感染者在患病期間需要手術治療,如闌尾炎、肝癌和骨折等[2-3]。圍術期麻醉和手術診療對機體的免疫功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加之HIV/AIDS患者本身免疫功能紊亂,故如何保護HIV/AIDS 患者免疫系統以防止其進一步受損,最大程度降低麻醉與手術的風險并加速患者康復,這將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對艾滋病圍術期麻醉的相關研究進行綜述,以期對圍術期診療提供參考。
1 重要器官系統麻醉前評估
1.1 心腦血管系統 隨著抗反轉錄病毒療法(ART)的問世,HIV感染慢慢轉變為一種慢性疾病。因此,據估計到2030年,73%的HIV感染者年齡將超過50 歲,78%的HIV感染者將患有心血管疾病(CVD)[4]。目前最近一項大型薈萃分析(80 項研究,793 635 例HIV 感染者以及總計350萬人年的累計隨訪)顯示,HIV感染者患CVD的風險是普通人群的兩倍,粗發病率為每萬人年約61.8%[5],其中包括急性心肌梗死[6]、伴有射血分數降低和不降低的心力衰竭[7]、心源性猝死[8]、外周動脈疾病[9]和腦卒中[10],這可能與CD4+T淋巴細胞數、病毒載量及啟動ART 時間有關。在一項對76 835 名退伍軍人(33%感染艾滋病)隊列的研究中發現,基線CD4+T 淋 巴細胞計數<200 cells/mm3和HIVRNA≥500 copies/mL 是缺血性腦卒中的獨立高危因素。有趣的是,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CD4+T 淋巴細胞計數超 過500 cell/mm3比<200 cell/mm3患CVD 的風 險 更高,作者考慮其原因可能是長期應用ART,從而引起了血脂的進一步變化[11-12]。HIV/AIDS 患者心腦血管意外風險增加,加之麻醉藥物可抑制心肌收縮力,擴張血管,易誘發血流動力學波動,故該類患者的麻醉須平穩來預防心腦血管意外的發生。
1.2 腎臟 HIV感染是慢性腎臟病(CKD)與終末期腎病(ESRD)已知的危險因素。HIV感染者出現腎功能下降或進展為CKD的發病率為(3.9~11.2)/1 000人·年,白蛋白尿水平進展至A2或A3期(>30 g/d)的發病率為非HIV 感染者的2~5倍[13]。HIV 感染的典型腎病—艾滋病毒相關腎病(HIVAN),患者通常表現為重度蛋白尿和迅速發展的腎衰竭,體外和體內研究均證明線粒體氧化應激在腎功能衰竭的發生機制和發病機制中起主要作用,而HIV感染會增加氧化應激,并且會影響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GPX)的活性[14-15],而GPX 缺乏是慢性腎臟病(CKD)誘發心臟病的重要因素[16]。在ART 問世之前,HIVAN 幾乎一律會發展到終末期腎病(ESRD),隨著ART 的引入,HIVAN 在美國的風險降低了60%,法國的一項研究也表明了自引入ART以來,HIVAN呈明顯下降趨勢[17-18]。因此艾滋病病毒治療指南建議盡早的開始ART,免疫病毒學控制是減少急性腎損傷和HIVAN 發病率的重要策略[19]。綜上,HIV 感染者麻醉前需詳盡了解其抗病毒治療方案及治療周期,并全面評估患者腎功能,圍術期應注意精確補液量、統計出入量及避免腎毒性藥物的使用。
1.3 肝臟 HIV 可感染肝臟中的多種細胞并在肝臟中復制。研究表明,包括肝臟星狀細胞(HSC)、Kupffer 細胞和肝細胞在內的多種肝臟細胞都可被HIV感染[20]。即使在ART后,HIV復制被抑制,但其仍可以通過肝細胞和HSC 上表達的gp120 與CXCR4 結合而導致肝臟炎癥和纖維化[21]。由于HIV和乙型肝炎病毒(HBV)的傳播途徑相同,二者共感染很常見。在中國,HIV-HBV 共感染的流行率約為10%,不同地區的感染率從5%~15%不等[22]。與HIV 或HBV 單獨感染相比,HIV-HBV 共感染個體的總體死亡率、肝臟相關死亡率和住院率以及患肝細胞癌的風險更高[23]。上訴研究表明HIV/AIDS 患者麻醉前肝功能可能受損,圍術期須制定保肝措施并關注患者凝血功能。
1.4 胃腸道 HIV 感染既改變了胃腸道微生物群落的結構,又對炎癥和新陳代謝功能有影響,即使啟動ART也不能恢復胃腸道微生物組的多樣性[24-25],而人類腸道微生物群的變化與肥胖[26]、心血管疾病[27]、高血壓[28]和糖尿病[29]等疾病的增加有關。值得一提的是,迷走神經功能障礙(VD)通常作為HIV相關自主神經病變的一部分,而JESSSCIA等[30]研究發現VD可以使患者胃排空延遲,進一步會導致小腸菌群過度生長而加劇炎癥反應。因此對于有自主神經病變的HIV/AIDS患者術前可能需要適當延長禁飲禁食時間,或于麻醉前常規使用超聲查探是否胃潴留(特別是對于急診患者),其受益性還需要大樣本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來證實。
2 抗反轉錄病毒治療
聯合應用ART或高效抗反轉錄病毒療法(HAART)是治療HIV 感染的一大進步。患者通過服用3 種或3 種以上的抗病毒藥物組合(俗稱“雞尾酒療法”)能夠有效抑制HIV在感染者體內進行復制,使受損的免疫系統得以重建,同時減少全身機會性感染和腫瘤的發生,顯著延長壽命[31]。但是隨著HAART 時間的延長,抗病毒治療的相關問題都顯現出來。抗病毒藥物可以直接影響血小板功能,而血小板在感染的免疫應答和促成動脈粥樣硬化的炎癥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32]。阿巴卡韋可誘發血小板反應性增加和內皮功能障礙,進而導致血栓形成增加心腦血管意外風險;而利托那韋可以刺激血小板產生如前列腺素E 等相關促炎介質[33-34]。目前幾乎所有可用的抗反轉錄病毒藥物均有腎損傷的孤立報道[35],隨著臨床用藥的不斷深入,研究表明富馬酸替諾福韋二吡呋酯(TDF)與腎毒性有明確的關系,CHIKWAPULO等[36]對非洲馬拉維439例初始治療使用TDF的患者進行為期18個月的隨訪觀察,發生腎毒性的概率為4.0%。TDF 引起腎損害的具體機制尚不清楚,國內外文獻報道的TDF 可能引起細胞毒性的機制有:TDF對線粒體的毒性和對正常功能腎小管細胞的干擾[37]。另有報道觀察156 例行HAART治療的HIV/AIDS患者中,近半年治療后均出現肝毒性反應,但多數為輕、中度肝損害,僅有5.1%的患者在治療后出現嚴重的肝臟損害,其機制可能與其誘導胰島素抵抗和血脂異常從而改變肝臟游離脂肪酸組成有關[38-39]。考慮到前述抗病毒藥物長期服用可對機體產生不同的影響,術前麻醉醫生應詳盡了解患者抗病毒治療方案,評估患者各器官系統功能,制定完善針對性麻醉方式,做到精準麻醉,這將是非常重要的。
3 麻醉藥物
藥物代謝動力學的改變是一個更為復雜的相互作用,主要是通過抑制或誘導肝臟酶,特別是CYP450(CYP)3A4酶介導的[40],這就增加了藥物相互作用的風險。抗反轉錄藥物中蛋白酶抑制劑、非核苷類反轉錄酶抑制劑和整合酶鏈轉移抑制劑均通過CYP450酶代謝[41],因此接受這些藥物治療的HIV/AIDS 患者可能需要增加經肝藥酶代謝的麻醉藥物的劑量,如維庫溴銨、羅庫溴銨、舒芬太尼等。而依托咪酯、順阿曲庫銨、瑞芬太尼等藥物不依賴于肝CYP450 酶代謝,對HIV/AIDS患者可能是選擇較佳的麻醉藥物。以下綜述常用麻醉用藥對HIVAIDS患者機體的影響。
3.1 丙泊酚 CHISATO 等[42]研究發現丙泊酚在臨床相關濃度和潛伏期下,通過靶向線粒體復合物Ⅰ、Ⅱ和Ⅲ改變細胞氧代謝,誘導細胞代謝從氧化磷酸化轉變為糖酵解,并且會增加活性氧自由基(ROS)的生成,加速線粒體凋亡。而齊多夫定會抑制肌細胞自噬,進而導致功能失調的線粒體積累,同時增加ROS的生成,引起細胞毒性蓄積,降低細胞活性[43]。綜上,丙泊酚可能協同核苷類反轉錄抑制劑影響HIV/AIDS患者線粒體功能和細胞凋亡。
3.2 苯二氮卓類 WEAM 等[44]研究顯示不同的苯二氮卓類藥物可能激活RUNX1 抑制劑,而RUNX蛋白在HIV-1 轉錄調控中起關鍵作用,苯二氮卓類通過抑制RUNX1促進STAT5在整合的長末端重復序列上的募集和變化,從而導致HIV轉錄增加。苯二氮卓類還可能會通過減緩神經認知功能、損害記憶和高階能力來增加HIV/AIDS患者中HIV相關性神經認知功能障礙的風險[45]。
3.3 阿片類藥物 體外和動物模型的數據表明,在HIV感染的情況下,靜脈注射嗎啡和HIV 反式轉錄激活因子(Tat)的小鼠與單純注射Tat的安慰劑小鼠相比,前者中樞神經系統中炎癥單核細胞數量增加,提示阿片類藥物增加了單核細胞跨血腦屏障的遷移[46]。BOKHARI 等[47]對感染HIV 獼猴的研究也證實,嗎啡會增加大腦中單核細胞和巨噬細胞的數量,這可能會加重HIV 的神經病變;還有許多體外實驗的結果表明,嗎啡增加了受感染的巨噬細胞和小膠質細胞中的HIV復制[48-49]。
3.4 骨骼肌松弛藥物 早期一項研究顯示接受ATR的HIV感染者與對照組相比,在單次給予維庫溴銨后前者的神經肌肉阻滯恢復至25%的時間顯著延長,其推斷這可能與HIV相關性周圍神經病和應用去羥肌苷治療有關[50],但該文章樣本量過小,尚需更大樣本量及相關基礎研究來進一步證實。綜上不同的麻醉藥物對于HIV/AIDS 患者的使用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可能增加或縮短作用時間,故麻醉用藥需及時調整用量。鑒于有些麻醉藥物可能會影響病毒載量,選擇恰當的麻醉藥物種類可能減少HIV病毒復制,不過還需要大量的循證醫學證據來證實。
4 麻醉方式
在HIV 感染中沒有特殊的麻醉方式,HIV 感染患者中使用的麻醉類型將主要由疾病和手術決定。然而如果患者發生HIV相關性神經病變、顱內壓增高及中樞神經系統感染等疾病,就有可能存在椎管內麻醉的禁忌證。SALMA 等[51]對100 例HIV 陽性并伴有癲癇的患者在腰穿前進行頭顱CT檢查,其中5%的患者中有腦移位,25%的患者出現占位性病變或腦水腫,所以椎管內麻醉前應詳盡了解患者有無神經系統癥狀,并完善相關系統檢查以排除椎管內麻醉的禁忌證。對于即使沒有神經系統并發癥的HIV感染者,椎管內麻醉后發生神經感染或神經損傷等并發癥的風險尚不清楚,尚需要大量高質量的研究來探討。目前建議椎管內麻醉禁忌用于晚期疾病或有神經系統癥狀的患者,此外還包括有出血傾向等其他相關禁忌證。至于全身麻醉如何影響HIV/AIDS患者CD4+T細胞數量和病毒載量,及如何加速該類患者的康復,目前相關研究報道極少。這些問題將成為以后研究的方向。
5 術中輸血
輸血本身就會使患者免疫受到抑制,KERKHOFF等[52]對585 例HIV 感染者進行Cox 回歸分析,研究發現在單因素分析中,基線血紅蛋白數和輸血與死亡率增加有關,然而,在多變量分析中,血紅蛋白數和輸血都不獨立地與更高的死亡率相關。目前仍建議臨床上對于HIV 感染者在不危及患者的安全下應該謹慎使用血液制品。
6 結語
隨著HIV/AIDS 患者的增加,其行手術的數量也隨之升高,HIV感染者免疫功能低下,各器官系統功能均能受累,術前的麻醉評估及術中不同的麻醉管理都可能會對患者的預后產生不同的影響。本文就重要器官功能評估、ART、麻醉藥物、麻醉方式、術中輸血等對HIV/AIDS 患者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綜述,其中涉及的相關研究多為體外基礎研究,而臨床上很少有大樣本量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來指導HIV/AIDS患者的麻醉管理方式,這將是未來研究的方向。綜上,為了最大限度的減少HIV感染者的麻醉及手術風險,提高患者預后,麻醉醫生應精準制定圍術期方案,不斷優化麻醉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