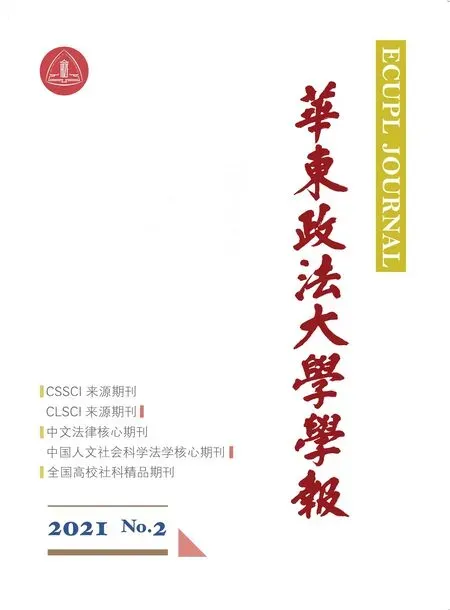從“查封”到“訴訟”:無形財產執行的制度邏輯與立法選擇
劉君博
在《民事強制執行法》起草過程中,有關無形財產執行的制度設計可謂是分歧較大的一個重要議題,圍繞可供執行的無形財產范圍、立法體例、執行措施效力等問題,各類觀點可謂見仁見智、分歧頗深。早在《民事強制執行法》起草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就啟動了對無形財產執行中爭議較大的有限責任公司股權執行問題單獨制定司法解釋的工作。不過,由于對股權的權屬判斷標準、執行的程序和順位、執行措施的效力、變價方式等問題均無法形成相對明確、統一的解釋方案,不得不無疾而終。〔1〕2018 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曾就股權強制執行問題提出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強制執行股權若干問題的規定(2018年12 月征求意見稿)》,并邀請公司法、民事訴訟法等領域的學者進行研討,但未能形成統一方案。傳統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強制執行法典以金錢債權的執行作為主要調整對象,同時,以控制和變價不動產、特殊動產為代表的有形財產作為支撐金錢債權實現的制度工具。可以說,股權執行過程中存在的疑難問題恰恰反映了以人類智力成果和信用交往所建構的無形財產在“進入”傳統民事強制執行法典時所遭遇的制度困境。一方面,有形財產是否為被執行人的“責任財產”以登記、占有等權利外觀主義原則作為判斷標準,而債權、股權、數據和網絡虛擬財產等都很難單純依據外觀主義進行權屬判斷。另一方面,作為控制性執行措施,查封、扣押和凍結的效力往往僅及于被執行人,限制其占有、使用、處分有形財產;對于無形財產而言,執行措施的主觀和客觀效力范圍(執行力及于哪些主體、何種權利范圍)則直接決定了無形財產能否被有效控制及變價。
有鑒于此,本文立足于立法論的視角,首先梳理無形財產執行立法中爭議較大的問題,其次通過歸納和分析比較法上無形財產執行法典化的基本路徑,提出無形財產執行立法應當遵循的基本思路和考量要素,最后在制度層面為我國的立法體例選擇及具體制度安排提出立法方案。
一、無形財產執行立法的主要爭議
無形財產是我國部分民法和強制執行法學者在學理上使用的術語,一直未進入現行法律,其與不動產、有體動產等有形財產相對應,意指有形財產所有權以外的所有權利和利益。作為財產形態的抽象表現形式,無形財產的類型具有多樣性,除了傳統的知識產權外,碳排放權、特許經營資格等公、私權益均可以納入其中。筆者選擇使用“無形財產”而非“財產權”主要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其一,無形財產的內涵和外延能夠周嚴覆蓋可以成為強制執行對象的各類責任財產,諸如數據、網絡虛擬財產、京滬車牌等尚未“權利化”的利益和可轉讓的行政特許資格均可以為無形財產概念所包括;其二,無形財產與有形財產相對應,可以暫時跳出傳統的“不動產—特殊動產—財產權利”的金錢債權執行客體立法模式的拘束,有助于構建平行于有形財產的執行標的體系,為理論探討預留更大的空間。
在《民事強制執行法》的立法討論過程中,關于無形財產強制執行的爭議問題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一是可以作為強制執行責任財產的無形財產范圍如何界定,在“實現金錢債權執行”的分編中如何安排;二是針對無形財產所采取的執行措施究竟具有怎樣的執行效力以及如何獲取這種效力;三是持有無形資產的執行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履行義務來源和救濟程序應當如何安排和設計。
關于第一個方面的問題,其實是關于《民事強制執行法》如何規定作為責任財產的無形財產種類及豁免財產的標準。責任財產是對被執行人可供執行財產的概括,理論上對責任財產的界定大體采取“默示歸入”原則,即除明確屬于豁免財產的,均默認歸入責任財產的范圍。〔2〕參見肖建國主編:《民事執行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第100 頁;譚秋桂:《民事執行法學》(第3 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170 頁;董少謀:《民事強制執行法學》(第2 版),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91 頁。不過,以債權、股權及其他財產利益為代表無形財產在金錢債權執行分編立法如何安排和排序卻分歧頗深。對此問題目前大體有兩種觀點,一是主張將“對債權的執行”和“對股權等其他財產權的執行”分列兩章,其中,對債權的執行包括對存款等資金、對一般債權以及對工資報酬的執行。〔3〕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強制執行法草案(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最高院建議稿”)2019 年9 月,第16 章、第17 章。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已故強制執行法學者楊榮馨教授及中國政法大學民事執行法研究團隊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執行法(學者建議稿2019 年11 月)》(以下簡稱“法大建議稿”)則力主按照責任財產執行順序安排金錢債權執行編的體例,其中涉及無形財產執行部分,按照“對現金、存款以及股票、證券等金融性資產的執行”“對收入的執行”“對知識產權的執行”“對股權及其他投資權益的執行”和“對債權的執行”依次排序并獨立成章。〔4〕參見中國政法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執行法(學者建議稿)課題組:《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制執行法(學者建議稿)》2019年11 月,第18 章、第19 章、第21 章、第22 章、第23 章;類似的章節編排亦可參見宋朝武和肖建國教授共同牽頭起草的《民事強制執行法草案(學者稿2019 年6 月)》(以下簡稱“學者建議稿”)第15 章至第19 章。應當說,兩種觀點雖然在立法章節安排上差別較大,但共同之處是立足于對無形財產執行實施便利性的視角,帶有濃厚的實用主義價值取向。與無形財產立法體例選擇直接相關的是,相較于有形財產而言,可以豁免執行的無形財產范圍有無特殊性?以“最高院建議稿”和“法大建議稿”為例,其對豁免財產的列舉性規定主要基于兩方面考量,一是保障被執行人的生存權,如為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的近親屬保留必需的生活、醫療、學習物品和相關費用、勞動工具及其他基本生產資料;二是豁免與被執行人人格、尊嚴密切相關的財產,如著作權、勛章、寵物等帶有鮮明人身屬性的個人物品。〔5〕參見“最高院建議稿”第117 條;“法大建議稿”,第170 條。至今為止,尚未見到關于無形財產豁免獨立標準的討論和研究。幾份建議稿在具體分編立法體例上的分歧及豁免財產的模糊規定其實都反映了我們對于能夠成為責任財產的無形財產的本質和類型缺乏清晰的認識。
第二個方面的問題在司法實務中爭議最大,即對債權、股權等無形財產采取執行措施時,執行效力范圍究竟有多大,是否可以“穿透”股權直接及于公司的有形財產。特別是對于有限責任公司或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凍結股權的效力可否限制股東行使表決權、轉讓股權及限制公司處置資產?有觀點主張,凍結股權的效力當然及于轉讓股權、行使表決權、分取紅利和優先認繳出資等具體的股權權能;相應地,凍結股權達到一定比例后,法院也可以對公司處置重大資產進行限制。〔6〕《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強制執行股權若干問題的規定(2018 年12 月征求意見稿)》第7 條、第8 條、第9 條。相反觀點則認為,公司通過修改公司章程或全體股東約定的方式,對股東權利進行分配和調整屬于公司自治的范疇;凍結股權并不對公司產生直接拘束力,公司處置財產亦無須法院許可。〔7〕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股權執行疑難問題研討會——討論問題清單》2018 年12 月1 日;也可參見鄧峰教授在此次研討會上的發言。在現行《民事訴訟法》執行分編及相關司法解釋一直使用“凍結+協助執行通知”的方式作為債權、股權等無形財產的執行措施。在意識到以執行客體形式區分執行措施法律意義有限后,“最高院建議稿”和“法大建議稿”已經不再使用“扣押”和“凍結”,統一以“查封”代之,但仍然懸而未決的是對無形財產“查封”的效力范圍究竟如何界定。
最后,關于持有無形財產的執行第三人在民事強制執行法上的法律地位等問題既關涉執行措施的主觀效力范圍,也與民事強制執行法對協助執行制度的定位密切聯系。司法實踐一直將銀行、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定位為“協助執行人”,人民法院需要向銀行發出協助執行通知書,銀行才協助法院實施凍結、劃扣等執行措施。不過,按照民法通說觀點,被執行人與銀行、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之間亦為債權債務關系,法院在執行其他到期債權、股權時是否也需要向次債務人、公司發出協助執行通知頗為棘手。反之,如果放棄協助執行制度,那么,究竟為何可以為持有無形財產的執行第三人設定積極的強制執行義務;又如何賦予其救濟途徑也需在《民事強制執行法》中予以整體考慮。
二、無形財產執行立法模式的類型化
比較法上的制度經驗雖然不能為解決我國無形財產執行立法面臨的現實問題提供直接論證,但仍可以從功能主義的視角拓展我們的分析思路。立足于類型化的視角,“突出”和“放大”比較法上立法例的共性部分,各國對無形財產的立法體例大體可以歸納為兩種模式,即“債權示范模式”和“分散立法模式”。其中,“債權示范模式”,即指以強制執行法典僅對金錢債權的扣押、變現作出具體規定,其他財產權的強制執行均參照對金錢債權的相關規定進行。德國、日本、韓國及我國臺灣地區等受德國法傳統影響較大的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大抵都采取此種立法模式。相應地,“分散立法模式”則是指強制執行法典對有形動產、債權、勞動報酬、股東權益、有價證券等財產的執行進行分散規定,適用不同的執行主體和扣押、變現方法。大陸法系國家中的法國及英國、美國多數州的強制執行法均可以被歸入此種立法模式。
時至今日,除拍賣以外的強制執行程序在立法體例上仍僅為德國民事訴訟法典的一編,不過,借助德國發達的法教義學理論和技術,德國無形財產執行立法形成了抽象性、體系性突出的“債權示范模式”,進而對日本、韓國、我國臺灣地區等繼受德國法的國家和地區獨立制定強制執行法產生深遠影響。具體來說,德國民事訴訟法典所采取的債權示范模式立法思路其實是以發達的債法理論和私法教義學技術作為支撐,進而不對股權、受益權、知識產權等無形財產的強制執行作單獨規定,其立法技術呈現四個特征:其一,債權示范模式一般僅對金錢債權扣押、變價進行完整規定,其他無形財產的強制執行均參照適用對金錢債權執行的規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829 條至第845 條完整、詳細地規定了對金錢債權的執行程序,第857 條則規定了對其他財產權的執行準用前述規定。在德國,動產除了包含有體動產外,還包括債權和其他財產權。〔8〕[德]格哈德·克萊夫特:《因金錢債權對有體動產、債權和其他財產權的強制執行》,載黃松有主編:《強制執行法起草與論證》(第2 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第146,138-156 頁。因此,在《德國民事訴訟法》體例中,“對債權及其他財產權的強制執行”是第二章第二節“對動產的強制執行”項下的一目。類似地,《日本強制執行法》第二章第二節第四款“對債權及其他財產權的執行”、《韓國民事執行法》第二編第二章第七節第二款“對債權及其他財產的強制執行”幾乎也都采取了對金錢債權執行作詳細規定,其他財產權執行參照適用的立法模式。〔9〕可參見《日本強制執行法》第143 條至第161 條,第167 條;《韓國民事執行法》第223 條至第241 條,第251 條。其二,明確依尊嚴和生存保護和可轉讓原則規定不得強制執行的債權范圍。對金錢債權的執行而言,被執行人的責任財產同樣采取默示歸入原則,不過涉及對被執行人的人格尊嚴保護,按照保留其最低生活限度的標準,德國基本法和法律都規定了可以豁免強制執行的財產。〔10〕[德]施特凡·古多:《強制執行中執行債務人的保護》,載黃松有主編:《強制執行法起草與論證》(第2 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第111-112 頁。《德國民事訴訟法》第850 條直至第850 條之十二通過詳盡列舉方式規定了豁免執行的債權范圍。這些豁免有些是基于債權本身的專用性,有些則是基于社會理由;即便是屬于可以強制執行的債權,比如收入,也只能實施有條件的扣押。〔11〕[德]施特凡·古多:《強制執行中執行債務人的保護》,載黃松有主編:《強制執行法起草與論證》(第2 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第115 頁。此外,《德國民事訴訟法》第851 條第1 款特別規定,扣押以債權可轉讓(讓與)為限。無論是基于實體法上的特殊規定,還是《德國民法典》第399 條對讓與禁止債權的規定,不符合可轉讓(讓與)原則的債權是不能被扣押的。〔12〕參見[德]奧拉夫·穆托斯特:《德國強制執行法》(第2 版),馬強偉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9 年版,第152-154 頁。同時,為了兼顧對被執行人(執行債務人)尊嚴和生存的保護,《德國民事訴訟法》對工資等勞動所得的扣押限制規定得最為詳盡。〔13〕參見[德]格哈德·克萊夫特:《因金錢債權對有體動產、債權和其他財產權的強制執行》,載黃松有主編:《強制執行法起草與論證》(第2 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第154 頁。其三,債權示范模式下對扣押的金錢債權變價的方式相對有限,以轉付為原則。既然債權示范模式以金錢債權作為主要調整對象,相應地,其變價方式一般不需要經由公開市場的拍賣,直接由債權人代位收取或者按照票面價額受讓債權清償;此外,對于存入指定賬戶的存款、勞動報酬等,第三債務人也可以向債權人交付或清償。(《德國民事訴訟法》第835 條、第836 條)。類似地,對有限責任公司股權的執行亦參照適用前述變價方式。有限責任公司如果想阻止“不受歡迎的人通過強制執行而成為公司股東”,只能通過公司章程規定,在此情形下,作為被執行人的股東需向公司或其他股東轉讓其股份,或者由公司回購。〔14〕參見[德]托馬斯·萊賽爾、呂迪格·法伊爾:《德國資合公司法》(第3 版),高旭軍等譯,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505 頁。其四,扣押命令的效力直接拘束第三債務人,第三債務人對債權情況負有說明義務。按照《德國民事訴訟法》第840 條規定,第三債務人自扣押命令送達兩周內,應向債權人說明是否認諾債權、認諾范圍、是否準備清償,有無其他請求或被其他債權人扣押等內容。如果第三債務人不履行說明義務或者提供的信息不準確,則可能就產生的損害向債權人負賠償責任。〔15〕W. A. Kennett,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61-262.如果第三債務人直接否定債權存在或對債權范圍提出爭議,則債權人可以代位債務人對第三債務人提起收取訴訟,債務人負有提供證明債權存在和范圍的相關文件的協助義務。〔16〕W. A. Kennett,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55-256, 263-264. 參見《德國民事訴訟法》第835 條。《德國民法典》并未規定代位權訴訟,《德國民事訴訟法》第835 條第1 款對債權人收取權的規定其實發揮了類似的功能。
德國民事訴訟典所開創的“債權示范模式”立法思路為大陸法系眾多國家和地區所繼受,充分展現了其立法技術上的合理性。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在以寬泛的所有權統領的一元化財產觀念之下,大陸法系的法國及英美法系主要國家在無形財產執行立法上均采取了“分散立法模式”,即規制重點在于拘束占有或持有被執行人有形或無形財產的第三人,同時采取列舉方式對勞動報酬、股權、知識產權等無形財產的執行與豁免作出規定。分散立法模式一般具有兩個特點。其一,一般會對占有被執行人金錢或財產的案外第三人所負執行義務和扣押程序作出統一規定。無形財產執行的核心特征是扣押不直接針對債務人,而是針對為債務人的利益持有金錢或財產利益的第三人。〔17〕參見[法]讓·文森、雅克·普雷沃:《法國民事執行程序法要義——強制執行途徑與分配程序》,羅結珍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 年,第93 頁。《法國強制執行法》第24 條第1 款、第2 款規定,第三人既不得妨礙執行,在受到依法請求時,還應該對執行予以協助。無正當理由逃避此項義務,法院可以強制履行,必要時還可以處以罰款。〔18〕參見羅結珍:《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下冊),法律出版社2008 年版,第1229 頁。在扣押程序方面,1806 年《法國民事訴訟法典》僅規定了“支付扣押(Saisie Asset)”作為無形財產扣押的一般程序;在1991 年、1992 年進行執行程序改革時,又引入了更為簡化的“歸屬扣押(Saisie-attribution)”取代“支付扣押”程序。〔19〕參見[法]讓·文森、雅克·普雷沃:《法國民事執行程序法要義——強制執行途徑與分配程序》,羅結珍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 年,第92 頁。簡化后的“歸屬扣押”程序主要包括向第三人送達文書實施扣押、受扣押第三人的申明、受扣押第三人支付及債務人異議四個程序環節。〔20〕參見羅結珍:《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下冊),法律出版社2008 年版,第1301-1313 頁。同理,在英美法傳統上,案外第三人(Garnishee)〔21〕Garnishee 是英美法系特有的概念,意指占有屬于被執行人的金錢或財產的人,或對被執行人負有債務的人。參見薛波主編:《元照英美法詞典》,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595 頁。和第三方扣押令(Garnishment Order)幾乎構成了對無形財產進行強制執行的核心。案外第三人(Garnishee)源自法語的Garnair,其本意是發出警告或通知。隨著產業革命、現代公司制度對財富控制方式的發展,第三方扣押令被廣泛適用于對股票、債券、票據和其他帶有人身屬性財產利益(personal property interests)的控制。〔22〕Philip I. Beane, “The Garnishee-A Historical Background”, 73 (2) Commercial Law Journal 42-43(1968).例如,美國紐約州《民事司法法與規則》第5201(C)條詳細列舉了可以適用第三方扣押令的無形財產類型及受到其拘束的案外第三人。〔23〕Joseph L. Marino, West’s McKinney’s Forms: Civil Practice Law and Rules, Chapter 8, p.230.其二,分散立法模式可以針對各類無形財產設置不同的執行命令(Order)獲取及控制(Control)和變現(Selling)程序。在法國,除了“歸屬扣押”外,執行程序中還分別設置了“勞動報酬的扣押與轉讓”和“股東權益與有價證券的扣押”兩編,詳細規定了勞動報酬的扣押效果、分配和轉讓及股東權益和有價證券的扣押、出售等事項。〔24〕參見羅結珍:《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下冊),法律出版社2008 年版,第1317-1323 頁,第1354-1355 頁。同時,在“保全扣押”程序中對債權、公司權益與有價證券等無形財產的扣押、變現以及程序轉換進行了單獨規定。〔25〕參見羅結珍:《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下冊),法律出版社2008 年版,第1369-1372 頁。而按照英國《民事訴訟規則》的規定,針對被執行人所有的債權〔26〕一般次債務人為銀行或者建房互助協會(Building Society,英國的金融機構,可以向會員支付利息或收益)。,證券、法院代管款、信托中的權益,收入等無形財產的執行,申請執行人需要分別申請第三方債務令(Third Party Debt Orders) 、〔27〕第三方債務令(Third Party Debt Orders)即原來的第三方債務扣押程序(Garnishee Proceedings)。押記令(Changing Order)、扣取收入令(Attachment of Earnings)等不同的命令或者令狀。〔28〕參見《英國民事訴訟規則(CPR)》Part 72 and Part 73 及Attachment of Earnings Act 1971。其中,對于股權執行,申請執行人還可以向法院申請針對公司的停付止辦令(Stop Order)或停付止辦通知(Stop Notice),防止被執行人轉讓股份逃避執行。〔29〕MaDs Andenas, “CiVil Enforcement In England And Wales”, 17 European Business Law Review 629 (2006).類似地,依據美國紐約州《民事司法法與規則》第5225b 條、第5227 條、第5231f 條等規定,法院可以命令案外第三人通過向申請執行人清償、轉付、分期付款等方式推進執行。
相較于債權示范模式而言,分散立法模式的抽象性和體系性較弱,而實用主義色彩更強。特別是在英國和美國,借助發達的執行令狀(Writ or Warrant)和執行命令(Order)制度及法院與執達員二分的執行分權體制,分散立法模式也能夠實現對無形財產的有效控制與變現。
三、財產觀念、執行體制與無形財產執行的立法思路
立足于類型化的研究視角,不同立法模式的劃分主要是為了更好地認識和理解無形財產執行立法的理念和思路,而非形式化地比較其功能優劣。對于解決無形財產強制執行的問題而言,不論是何種立法模式,其制度運行的著力點主要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執行力作用的主觀范圍,即通過何種正當程序拘束執行第三人;二是作為一種公權力,強制執行權力的行使如何更加有效率且被合理制約。在此意義上,對無形財產的執行程序更近似一種對“執行第三人”的訴訟,一方面支撐著執行力取得的正當性,另一方面防止其損害相關當事人的合法權利。
(一)財產觀念與強制執行
由于無形財產執行程序相較于有形財產執行的“訴訟化”特征,我們有必要從財產理論的視角檢視作為執行客體的“財產”與作為權利主體的“人”的關系。西方的財產觀念在理論源頭上均可以追溯到洛克的“自由意志論”和黑格爾的“社會民主論”。〔30〕參見[英]詹姆斯·哈里斯:《論西方的財產觀念》,彭誠信譯,黃文藝校,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03 年第6 期。在傳統的財產權結構中,人類對財產的認知本質上仍然還是一種“對自然狀態的模擬”。具體來說,財產權通常都被定義為“對物的絕對支配”,財產界定的標準也被設定為“物質屬性、絕對支配和所有權中心三點:財產與具體的物相聯系、財產體與財產權相等同、財產權利集中體現于所有者的所有權。”〔31〕冉昊:《財產含義辨析:從英美私法的角度》,載《金陵法律評論》2005 年第1 期。受到羅馬法“物即財產”觀念的影響,制定于1804 年的《法國民法典》采取廣義財產的概念,“現存的和未來的權利和義務的總體”即為財產。〔32〕[法] 雅克·蓋斯旦、吉勒·古博、繆黑埃·法布赫-馬南:《法國民法總論》,陳鵬等譯,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150 頁。《德國民法典》所開創的物權與債權二分模式對大陸法系財產法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并且在其嚴密的邏輯形式理性支配下,民法典所“統率”的私權結構體系被發揮到了極致。不過,正如王衛國教授指出的,“在德國民法創制之時,人類社會還處在實物經濟的時代。通過物權和債權分別建立起以有體物的享用與交換為中心的靜態秩序和動態秩序,足以滿足當時的社會經濟需要……隨著人類社會進入實物經濟、知識經濟與信用經濟三位一體的新時代,這種體系就難免在現實面前顯示出局限性。”〔33〕王衛國:《現代財產法的理論建構》,載《中國社會科學》2012 年第1 期。也是在此意義上,有學者提出,受此類財產觀念的影響,制定于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法、德、日、奧等大陸法系國家強制執行法典或民事訴訟法執行編基本上也呈現出以有體財產執行為中心的立法模式。〔34〕參見史明洲:《信息機制內部化與強制執行法的更新》,未刊稿,報告于第8 屆紫荊民事訴訟青年沙龍。不過,大陸法系的財產權概念也存在廣義、中義和狹義的區分,其中,中義的財產權就包括了物權、債權及二者間的若干中間類型。〔35〕參見冉昊:《法經濟學中的“財產權”怎么了?—— 一個民法學人的困惑》,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5 年第2 期。
和大陸法系的財產觀念類似,在洛克的“自由意志論”及布萊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在洛克理論基礎上發展出的絕對財產權觀念同樣構成了英美法系早期財產理論的基礎。〔36〕參見王鐵雄:《美國財產法理論的歷史基礎》,載《寧夏社會科學》2010 年第2 期。但與大陸法系關注邏輯形式理性和體系化的法教義學傳統不同,受到法律現實主義的影響,英美法系早在20 世紀初就開始了對傳統財產權觀念的批判和解構。耶魯大學法學院的霍菲爾德教授在1913 年提出了他的權利分析理論,并將財產界定為“有關物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37〕霍菲爾德分別在1913 年和1917 年發表了《司法推理中的一些基本法律概念》和《司法推理中的基本法律概念》兩篇論文,提出了其著名的“權利分析理論”。對霍菲爾德理論的歸納和闡釋可參見冉昊:《制定法對財產權的影響》,載《現代法學》2004 年第5期;紀格非、王約然:《霍菲爾德法律概念的原點及其邏輯展開》,載《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4 期。受到霍菲爾德觀點的啟發,法律現實主義者則提出了“權利束”理論,并成為美國財產法學界的流行觀點。所謂“權利束”理論是指不再以客體或物作為界定財產權的標準,財產權只是對資源使用或禁止的“一束”權利關系的集合。〔38〕關于“權利束”理論的形成過程和核心觀點可參見冉昊:《法經濟學中的“財產權”怎么了?—— 一個民法學人的困惑》,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5 年第2 期。隨著法經濟學研究對“權利束”理論的推崇和再發展,實證主義的財產觀念“徹底脫離了常識認知對它的自然主義歸納”,進而形成了“財產權只是特定資源的一系列使用權的集合”的觀點。〔39〕參見冉昊:《法經濟學中的“財產權”怎么了?—— 一個民法學人的困惑》,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5 年第2 期。相較于德、日等國的立法例而言,美國紐約州《民事司法法與規則》第5201 條規定,對可執行責任財產范圍的界定就比較寬泛。除非屬于執行豁免財產,“可轉讓或轉移的任何財產,不論是包含現實的或將來的權利或利益,以及不論(該權利或利益)是否已經現實授予”均屬于責任財產。〔40〕McKinney’s CPLR § 520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來美國聯邦地區法院的裁判中,已經出現將比特幣視為貨幣的裁判觀點。〔41〕US District Judge Alison Nathan in US v. Murgio et al, US District Court,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No 15-cr-00769.盡管有學者指出,早在新的無形財產形式興起之前,權利束觀念已經開始使用,而且是一個“典型的反規制(Anti-regulatory)概念”。〔42〕參見[美]斯圖爾特·班納:《財產故事》,陳賢凱、許可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9-110 頁。但經由莫里斯·R. 科恩(Morris R. Cohen)等人發展或者重新定義的財產觀念,不僅使財產超越了“人與其擁有之物之間的關系”,更被理解為“激勵經濟活動而使用的手段”。〔43〕參見[美]斯圖爾特·班納:《財產故事》,陳賢凱、許可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163 頁。因此,在英美法系的財產概念本身就沒有必要區分有形與無形,執行責任財產的范圍也不會受到財產形式的拘束。
(二)執行體制與執行分權
除了財產觀念外,影響無形財產執行立法的另一重要因素主要是執行權力的配置與制約。在民事執行制度形成初期,執行權主要表現為債權人有權對債務人的人身進行拘禁、對債務人的財產進行扣押。〔44〕參見[美]孟羅·斯密:《歐陸法律發達史》,姚梅鎮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第76 頁。隨著人權保障和權力制約等現代執行法理念的興起,各國執行立法基本上已經摒棄了通過人身拘禁或控制逼迫債務人清償債務的執行措施。不過,時至今日,學界諸多關于執行權行使市場化、職業化的討論其實都與執行活動“天生”的私力救濟性質直接相關。
因為在采取扣押動產、不動產,進屋搜查等執行措施時,執行公權力與債務人私權保護之間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沖突。在涉及無形財產執行時,執行力如何及于為債務人利益占有、管理無形財產的第三人更是關系到執行權行使、制約的正當性基礎。因此,對執行權力進行分割和制約幾乎構成各國執行體制安排的核心命題。在法國、德國、日本等主要大陸法系國家,基本上均采取了針對不同類型執行財產的“橫向”執行分權及針對不同執行主體的“縱向”模式。〔45〕參見陳杭平:《比較法視野下的執行權配置模式研究——以解決“執行難”問題為中心》,載《法學家》2018 年第2 期。例如,在法國,大審法院可以通過任命執行法官負責處理動產扣押程序中的爭議和不動產扣押程序,初審法院法官負責對勞動報酬扣押和生活費直接支付程序的執行;司法執達員(Huissiers Audiencier)則負責對動產、銀行賬戶、債權及其他財產權利的執行。〔46〕參見江必新主編:《比較強制執行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 年版,第18、25-26 頁。在德國,執行法院負責對金錢判決執行中不動產的扣押拍賣、對債務人債權及其他財產權利的扣押;法院執行員主要負責在金錢判決執行中動產及有價證券的扣押拍賣,非金錢判決執行中動產及不動產的交付、房屋騰退等。〔47〕參見江必新主編:《比較強制執行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 年版,第138、141 頁。在日本,執行機關同樣是采取二元制的模式,即執行裁判所和執行官分別負責針對不同責任財產的執行。〔48〕參見江必新主編:《比較強制執行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 年版,第203-205 頁。同時,通過執行文制度,在執行程序啟動前對執行名義的內容是否符合強制執行的要件進行審查,從而實現審執分立及法院書記官對執行權力的事前監督。〔49〕關于“執行文制度”的起源以及在法、德、日等國的制度演進可參見劉穎:《執行文的歷史源流、制度模式與中國圖景》,載《中外法學》2020 年第1 期。在許多大陸法系國家,設置多元化執行機關本身就是執行實施分權的一種體現,執行文制度又進一步通過落實審執分立原則,實現司法權對執行實施權力的監督。
英美法系國家對民事執行權的分權和制約更是貫穿了執行法立法及司法實踐。在英國,一方面,行使民事執行權的皇家法院裁判與服務署(HM Court and Tribunal Service)本就隸屬于英國司法部,進而在體制上與行使審判權的法院相分離。〔50〕參見宮雪:《英國民事執行權的運行與控制》,華東政法大學2015 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41-142 頁。另一方面,在具體執行民事法院判決、裁定的過程中,法官負責對第三方債務令、扣取收入令、押記令等執行命令申請進行審理和裁判,法院官員負責執行令狀的簽發,執行員負責執行令狀的具體執行實施。〔51〕參見張永紅:《英國強制執行法》,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第97 頁。以“第三方債務令”的執行程序為例,該執行命令的功能類似于凍結、劃扣銀行存款或對債權的執行。在程序上,第三方債務令實際上是執行債權人將次債務人列為被告,進行一次訴訟。法官在未經開庭的情況下,可以作出臨時性第三方債務令,命令銀行等第三人凍結執行債務人的存款等債權;銀行等第三人收到該命令后,應在7 日內查詢、凍結執行債務人的存款并報告法官和執行債權人。經過開庭審理,法官可以作出終局性第三方債務令,命令第三人將凍結債權轉付給執行債權人。在此過程中,如果第三人拒不履行第三方債務令,執行債權人可以向法院申請“動產扣押令狀”,再通過執行員實施扣押第三人財物、變價出售的方法來收取相關債權。〔52〕關于“第三方債務令”詳細審理流程介紹可參見張永紅:《英國強制執行法》,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第99-101 頁。易言之,法官通過訴訟或準訴訟程序的方式掌握作出各類執行命令(Order)的權力;法院相關的司法行政官員通過司法行政程序簽發各類執行令狀,執行員僅負責具體實施執行令狀。
一般來說,對于債權等無形財產的執行往往涉及執行第三人提出否認或者抗辯、申請執行人提起訴訟或準訴訟程序等內容,執達員或執行官并無資格對此進行裁判,只有法院才能行使此項權力;而法院發布相關的扣押令、執行命令又依賴于司法行政官員或執達員的具體執行實施,從而實現相互制約。
(三)我國無形財產執行立法的進路選擇
無形財產的誕生本身就是人類智力成果和信用體系制度化的結果。在理論上,無形財產的核心特征是權利無形,而非客體無形。〔53〕參見馬俊駒、梅夏英:《無形財產的理論和立法問題》,載《中國法學》2001 年第2 期。王衛國教授進一步提出,可以將無形財產分為知識財產和信用財產兩個子類,其中,知識財產包括“虛擬財產、商業秘密、特許經營權等”歸屬保護型知識財產和包括知識產權、人格標志利用權等利用保護型知識財產;信用財產則主要指貨幣、有價證券、可交易的債權和股權、金融衍生品等。〔54〕參見王衛國:《現代財產法的理論建構》,載《中國社會科學》2012 年第1 期。在我國無形財產執行立法過程中,爭議最為集中的三個問題似乎在不同的立法模式中都可以尋找到具體的參考答案。不過,為了系統地、體系化地解決前述問題,同時兼顧各類具體執行主體、客體制度設計,我們仍需要立足既有的財產觀念及執行體制機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明確我國無形財產執行立法的基本思路。具體來說,綜合比較不同立法模式對無形財產執行的共同關注點,我們可以提煉出以下三條立法思路框定我國無形財產立法制度選擇的基本方向。
其一,無形財產的可變價性與執行措施法定化原則。對于金錢債權的強制執行而言,從“人對物”的關系到“人對人”的關系的財產觀念發展極大地拓展了可供執行的責任財產范圍。不過,近年來,受到“私法新思維運動”的影響,“模塊化”財產權理論(Property as Modularity)的興起開始反思和批判“權利束”理論(Property as a Bundle of Rights)這類去結構化或者說富于彈性的財產權觀念,重新強調認真對待“私法法律概念和教義”及“概念術語和教義背后的共識性規律”。〔55〕參見熊丙萬:《實用主義能走多遠?——美國財產法學引領的私法新思維》,載《清華法學》2018 年第1 期。為了化解“執行難”,我國民事強制執行的司法實踐一直存在努力拓寬被執行人“責任財產”的邊界,比如,對北京、上海等機動車限購城市的車牌、金融牌照、燃氣石油管線、手機“靚號”等均可以采取查封、變現措施的執行標的。〔56〕相關報道可參見“全國法院切實解決執行難信息網”,網址:http://jszx.court.gov.cn/.不過,可以作為執行對象的無形財產類型越是多元化,在立法選擇上更應當堅持金錢債權執行對象的可變價化原則。〔57〕參見賴來焜:《強制執行法總論》,臺灣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 年版,第461 頁。德國《民事訴訟法》亦規定對債權的查封以可“讓與”為限,如果債權根據實體法無法轉讓、變價,也就不能查封。參見[德]奧拉夫·穆托斯特:《德國強制執行法》(第2 版),馬強偉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9 年版,第152 頁。責任財產的概念本身就意味著國家強制力對其作為財產的“資格”或“信用”認可,故而可以變價為法定貨幣或者認可其財產價值。例如,以比特幣為代表的加密貨幣則完全不以國家信用作為背書,其通過去中心化的區塊鏈技術作為運行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哈耶克提出的貨幣非國家化思想。〔58〕參見趙磊:《論比特幣的法律屬性——從Hash Fast 管理人訴Marc Lowe 案談起》,載《法學》2018 年第4 期。在理論上,不論比特幣等加密貨幣是否被接受為法定貨幣,但學界一般均認可其具有財產價值。但此類無形財產因為不符合“可變價化”的要求,故不能進入民事強制執行法的調整范圍。再者,對于無形財產而言,即便可以成為執行對象,對其采取執行措施的種類或程序還應堅持法定化原則。無形財產的控制、變價既需要控制、管理相關財產的執行第三人配合,同樣也會對執行第三人的義務履行、經營或管理行為產生影響。《德國民事訴訟法》之所以將金錢債權的變價方式原則上限定為轉付(包括債權人代位收取或者按照票面價額受讓債權清償),也有通過實體法上的“債權讓與”制度對第三人利益進行保護的考量。〔59〕參見[德]奧拉夫·穆托斯特:《德國強制執行法》(第2 版),馬強偉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9 年版,第170-171 頁。不過,德國的強制執行法中,對商標和專利等知識財產及對貨幣、股票等信用財產的執行其實已經完全“動產”化了;所謂的“債權示范模式”其實僅僅適用于尚不能充分在市場上交易的金錢債權和股權等少數無形財產。執行措施的法定化無疑會影響無形財產變價的效率,但其對執行第三人利益的周嚴保護更具實益。
其二,從“對物”執行到“對人”執行原則。傳統上,作為民事強制執行法的我國《民事訴訟法》執行編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等執行工作相關司法解釋對“財產”概念的理解仍然受到“物即財產”的羅馬法觀念的影響。按照《民事訴訟法》第244 條的規定,控制性強制執行措施包括查封、扣押和凍結三種。其中,查封、扣押和凍結分別適用于不動產、動產和財產權;查封、扣押、凍結措施的效力限于被執行人對財產進行轉移、設定權利負擔或者其他有礙執行的行為。〔60〕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第1 條、第26 條。究其本質,我國現行的執行措施體系其實是以限制被執行人對有形財產的所有權行使為主要目標構建而來,故而無法對執行第三人持有、管理為特征的無形財產產生有效的拘束力。對債權、股權、知識產權、行政特許權益等無形財產強制執行的實現并非是對有體物的實際占有,而是對執行第三人拘束力的實現,易言之,是一種“對人”的強制執行。因此,不論是債權示范模式,還是分散立法模式,均可以借助扣押金錢債權或作出執行命令等方式使執行力主觀范圍覆蓋次債務人或第三人的,進而實現對無形財產的有效控制。在此意義上,我國無形財產執行立法的核心目標其實是解決執行力拘束執行第三人的正當性基礎問題。
其三,“裁執”分離與程序保障原則。受到審執分立觀念的影響,執行分權也是近年來學界和司法改革關注的熱點。不過,相較于比較法上執行分權的制度經驗而言,國內司法實踐對執行分權的改革探索仍相對粗線條,一方面強調“審執分立”,即將審判權、執行裁決權剝離出去,純化執行實施權;另一方面將執行實施權中的執行審查權和變價權進一步剝離,方便對執行權進行優化配置、建立分段集約的執行工作機制。〔61〕參見江必新主編:《強制執行法理論與實務》,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 年版,第50-51 頁。從比較法的視角考察,強制執行權的行使代表了國家公權力對財產權的合法剝奪,故而執行分權與制約幾乎構成各國執行體制改革和執行權配置的永恒主題。對于無形財產而言,因其無法充分外觀化、公示化,所以對無形財產執行及對第三人拘束力產生的過程本質上就是一個“訴訟”程序。換言之,只有充分的程序保障才能充實拘束第三人的扣押或執行命令的正當性。當然,這種程序保障可能是事后的,比如德國法上收取之訴和第三人異議之訴;也可能是事前的,比如英美法系的各種執行命令的獲取。同時,英美法系“訴訟化”的執行命令賦予程序及法國、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普遍采取的執行文制度不僅將執行實施權進一步“分割”,更實現了審判權(包括審查權)對具體執行實施行為的制約和監督。
四、無形財產執行立法的體例與配套制度
承前所述,強制執行法的核心功能主要體現為公權力對財產的識別、控制與變現。與有形財產執行側重公權力保障下的物理“查封”不同,無形財產執行的基本制度邏輯其實就是通過構建一套“訴訟”程序,從而實現對“第三人”的正當、有效“拘束”,同時規范公權力的運行。具體到無形財產執行的立法技術而言,筆者認為,可以從體例模式和具體制度設計兩個方面予以重構。
(一)無形財產執行立法分編體例重塑
不論是最高人民法院受全國人大法工委委托起草的立法建議稿,還是專家學者獨立起草的學者建議稿,在無形財產執行立法體例模式的選擇上基本上是趨同的,即以“分散立法模式”為主,吸收“債權示范模式”的少量立法技術。以本輪《民事強制執行法》立法工作形成的較為成熟的三個建議稿為例,“最高院建議稿”對無形財產的執行區分為兩章,第16 章“對債權的執行”和第17 章“對股權等其他財產權的執行”;“法大建議稿”將無形財產執行劃分為第18 章“對現金、存款以及股票、證券等金融性資產的執行”、第19 章“對收入的執行”、第21 章“對知識產權的執行”、第22 章“對股權及其他投資權益的執行”以及第23 章“對債權的執行”共五章;“學者建議稿”則將對無形財產的執行劃分為五章,分別是第15 章“對現金和存款的執行”、第16 章“對收入、其他財產的執行”、第17 章“對債權的執行”、第18 章“對股票、股權及其他投資收益的執行”和第19 章“對知識產權的執行”。就目前的無形財產執行立法體例而言,債權與股權等財產權相分離的“分散立法模式”是各個建議稿的共同選擇;差別之處僅在于“分散”程度,即對知識財產的執行要不要相對于信用財產獨立成章,以及存款、收入、股票、債券等可采取“凍結”執行措施和協助執行制度的“動產化”債權是否也需要獨立成章。
盡管本輪立法工作啟動后的各個立法建議稿均未公布建議理由和具體條文的說明,但放棄德國、日本、韓國及我國臺灣地區等眾多大陸法系立法均采取的“債權示范模式”的立法思路,轉向體系性和抽象度均不見長的“分散立法模式”背后的理由亦不難探究。〔62〕在本輪《民事強制執行法》立法工作啟動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和部分學者曾經合作起草過六稿《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制執行法草案》,其中,直接接受德國學者建議修改而成的《民事強制執行法草案(第四稿)2003 年7 月10 日》采取了債權示范模式。不過,隨著對股權等無形財產的執行在司法實踐遭遇到的執行措施、效力范圍等技術問題日益凸顯,加之司法實務部門對銀行存款等債權的認識存在不同意見,《民事強制執行法草案(第六稿)2011 年6 月》其實已經開始轉向分散立法模式。一方面,“債權示范模式”的無形財產立法思路需要以發達的債法理論,尤其是發達的債的保全制度作為基礎。我國剛剛通過的《民法典》在形式上已經放棄了德國的“物債二分模式”。《民法典·總則》第118 條雖然規定了債權作為統攝合同、侵權行為、無因管理、不當得利及其他法定之債的上位概念,但債法思維其實并未融入我國《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之中。代位權與撤銷權僅是《民法典·合同編》第五章“合同的保全”的內容,盡管不少學者主張代位權和撤銷權客體范圍應當擴張適用于整個債之保全領域,〔63〕相關觀點可參見朱虎:《債法總則體系的基礎反思與技術重整》,載《清華法學》2019 年第3 期;龍俊:《民法典中的債之保全體系》,載《比較法研究》2020 年第4 期。但這恰恰說明我國債的保全制度的妥善適用尚且需要理論解釋。另一方面,德國法中對債權的執行本質上是對次債務人的執行。扣押命令的效力范圍(包括實體法效力的順位)、對次債務人的收取之訴都需要以德國私法教義學的解釋論技術作為支撐。〔64〕目前,僅有個別學者主張應從解釋論的視角賦予我國司法查封以私法效力,使查封債權人獲得擔保物權,可以優先受嘗。參見劉哲瑋:《論民事司法查封的效力》,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9 年第4 期。坦白地說,如此高度抽象化、體系化的立法技術與我國正在形成中的民事實體法、程序法教義學知識體系尚無法有效整合。《民事強制執行法》屬于典型的民事實體法、法院組織法與程序法交叉領域,相較于法律文化傳統,配套的實體法技術和司法體制在立法模式選擇中發揮的作用顯然更為重要。在此意義上,筆者也認同,分散立法模式的無形財產執行立法思路更符合我國的實際需要。但是,既有的無形財產執行立法體例方案或者過于細碎,或者分章標準不統一,故筆者建議作出較大調整。
金錢債權執行分編中的無形財產執行仍可以保留兩章模式,但需要按照“動產化”無形財產和一般無形財產劃分。按照執行措施法定化的原則,對執行客體進行分章的標準并非財產的形態,而是采取執行措施的種類和程序。據此,筆者建議可以將無形財產區分為“動產化”無形財產和一般無形財產兩類,前者應當貫徹封閉列舉原則,包括存款、有價證券、工資和勞動收入和知識產權四類。這四類無形財產的共同特征是權利外觀相對明確、一般無權屬爭議,較為容易控制和變現。“法大建議稿”中列舉的“現金”宜納入動產范圍進行規定,不屬于無形財產。同時,相較于存款和有價證券而言,知識產權因其執行措施并無特殊之處,故也沒有獨立成章的必要性。在此基礎上,可以按照四類無形財產具體分節,規定有價證券的變現措施、工資和勞動收入的執行比例和限制條件等內容。一般無形財產可以采取開放列舉的立法技術,包括普通金錢債權、股權、特許行政經營權益等,其共同特征是需要經過訴訟程序明確權利邊界、拘束執行第三人。“動產化”無形財產以外的新型權利和利益原則上都應被歸入一般無形財產分章。
(二)無形財產執行的配套制度實現
在采取分散立法模式的思路之下,除了區分“動產化”無形財產和一般無形財產構建金錢債權分編的立法體例之外,《民事強制執行法》通則的部分制度規范也作出相應的調整。
1. 豁免財產的立法方案
在現代社會,財產形態和社會觀念更新使無形財產的范圍日益擴大、無形財產的發現與控制難度也在增加,支撐財產存續的信用機制不一定依賴國家主權,但民事強制執行法是國內公法,以公權力保障其實現,具有鮮明的公法屬性,因此,豁免財產制度的立法方案必須為可供執行的無形財產劃定相對明晰的邊界。就立法技術選擇而言,劃定責任財產(含無形財產)的邊界有兩種方案可供選擇:一是在金錢債權執行程序中正面規定可以作為責任財產的基本原則,同時規定少數例外;二是直接反向規定豁免執行的財產范圍。“法大建議稿”采取的是方案一,其第170 條第1 款規定,債務人拒不履行金錢給付義務的,債權人可以申請執行債務人所有依法可以轉讓的財產,但法律規定不得執行的財產除外;同時,第2 款、第3 款分別就債務人是自然人或法人的情況,可以保留的財產進行概括規定。“最高院建議稿”采取的是方案二,即其第117 條通過列舉方式規定了8 項豁免執行的具體情形。“學者建議稿”則可以視為方案一和方案二的折中,其第133 條不僅從正面規定責任財產應具有可轉讓性,又以列舉方式規定了11 項豁免財產。
對于金錢債權的執行而言,理論上責任財產采取默示歸入原則,即除了法律明確規定豁免執行的財產,被執行人所有的全部財產都默示歸入執行范圍。在比較法上,《德國民事訴訟法》第811 條、第850 條至第851 條之四,《日本民事執行法》第131 條、第132 條、第152 條、第153 條,臺灣地區“強制執行法”第53 條均以詳細列舉的方式規定了不得扣押或保護性扣押的動產、債權等豁免執行財產的類型。不過,比較法上類似的制度設計并不會成為我國民事強制執行立法的必然選擇。即便未在前述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的強制執行法典中明確規定,責任財產的可變價性或者可轉讓性也是學理上對可執行對象范圍界定的共識性要求。考慮到隨著信息技術和社會交往信用體系的發展,無形財產的類型在不斷豐富,采取豁免財產明確列舉的立法技術難免掛一漏萬。而且,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的強制執行法典本就以“個別執行”作為立法本位,〔65〕“個別執行”是相對于“概括執行”存在的概念,是指執行當事人自行選擇執行標的物及對應執行程序的強制執行;而“概括執行”一般是破產程序等旨在全面清理執行債務人責任財產,以滿足全部債權人利益的程序。二者的功能界分可參見韓長印:《破產程序的財產分配規則與價值增值規則——兼與個別執行制度的功能對比》,載《法商研究》2002 年第3 期。明確列舉豁免執行財產也是為了規范具體的執行行為、限制執行實施過程中的裁量權。我國民事強制執行體制仍帶有較強的職權主義色彩,執行法院在查詢責任財產信息、安排執行順序、采取執行措施等方面仍居于主導地位。立足于構建解決執行難長效機制,本次民事強制執行立法也應向當事人主義方向過度,鼓勵當事人在財產信息提供、執行實施等方面實現權責均等。只是考慮到我國執行法院的“緊密型”組織形態〔66〕關于人民法院作為“緊密型組織”的特點及論述,可參見王亞新:《解讀司法改革:走向權能、資源與責任之新的均衡》,載《清華法學》2014 年第5 期。及通過投入大量成本建立的執行財產信息查控系統等已經在實然層面壟斷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產信息資源,民事執行立法也只能在既有司法體制框架和人民法院組織體系之下“緩步”推進當事人自負其責的制度設計。在這個意義上,正面規定執行對象的可變價性不僅是為日益豐富的無形財產預留制度空間,也是在既有司法體制和法院組織模式下,不得不為執行法院預留的裁量權力。
2. 執行第三人協助執行義務的制度重構
在現行《民事訴訟法》執行編及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建構的民事強制執行制度體系中,執行力對為被執行人占有、管理無形財產的第三人的拘束主要通過協助執行制度實現。在理論上,強制執行的協助機關或輔助機關一般僅指承擔一定公共服務職責的國家機關、團體或專業人士,其協助義務或輔助義務的產生是基于強制執行法典或其他法律的明確設定。〔67〕參見賴來焜:《強制執行法總論》,臺灣元照出版公司2007 年版,第142 頁。不過,我國現行的協助執行制度拘束的主體范圍并不限于前述負有公共職能的國家機關和單位。按照《民事訴訟法》第243 條的規定,被執行人所在單位、銀行、信用合作社等均屬于負有協助義務的單位。被執行人與用人單位、銀行、信用合作社等之間亦是債權債務關系,這些協助執行單位其實與被執行人的一般債務人無異。
立足于“分散立法模式”,學界和實務界提出的無形財產執行制度其實采取了一種獨特的“雙軌制”制度安排。一方面,不論是“最高院建議稿”“法大建議稿”,還是“學者建議稿”都繼續保留了現行的協助執行制度。除了進一步明確公安機關、不動產登記機構、基層組織等國家機關的具體協助執行義務外,對于用人單位、銀行及合法占有和管理被執行人無形財產的單位和個人,同樣規定其應當按照人民法院發出的協助執行通知書,提供財產信息、配合完成查封、扣押、凍結、劃扣。〔68〕參見“最高院建議稿”第7 章、第16 章;“法大建議稿”第5 章、第18 章、第19 章、第21 章、第22 章;“學者建議稿”第6 章、第17 章。另一方面,對于普通金錢債權的執行,則采取“查封裁定+履行通知書”的執行力賦予模式;同時,通過構建次債務人執行異議和債權人代位訴訟(收取訴訟)的方式,提供程序保障。由此,形成了對于存款、股票、股權、知識產權等財產權益和普通金錢債權各自獨立、平行的執行力賦予模式。就無形財產的執行而言,“雙軌制”模式雖然未見比較法上的制度經驗支持,但也不能說明其不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相較于普通金錢債權而言,存款、股票、工資〔69〕“最高院建議稿”第195 條將“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租金等”歸入普通金錢債權之下,并未采取協助執行通知擴張執行力的模式。等無形財產往往具有權利外觀性強、執行措施對執行第三人權利影響較小等特征。繼續通過協助執行制度實現執行力對銀行、證券公司、用人單位等執行第三人的拘束,更加符合民事強制執行法對執行效率價值的追求。然而,作為立法上的制度選擇,除了單一的價值追求以外,更應考慮其內在的邏輯性與體系性是否完備。通過協助執行制度擴張執行力的制度設計至少存在以下兩方面的障礙難以克服。
其一,銀行、證券公司、用人單位等執行第三人并非負有公共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要求其協助執行需要明確其承擔該義務的法定淵源為何。現行的《商業銀行法》《證券法》《公司法》《勞動法》等相關法律并未對銀行、證券公司、用人單位等執行第三人負有協助執行義務作出規定。《民事訴訟法》及制定《民事強制執行法》固然可以通過直接規定此類執行第三人承擔協助執行義務解決形式上法律淵源欠缺的問題,但作為以民事強制執行法律關系基本調整對象的程序法,直接為民事主體設定積極的公法義務依然缺少必要的論證與制度依據。其二,“協助執行通知+妨礙民事訴訟強制措施”的程序操作模式不能為執行第三人提供基本的程序保障。“通知”本身是國家機關之間告知或轉達相關事項的一種公文,并非是拘束特定主體的法律文書。由于法律對國家機關的職責、權限界定相對明確,人民法院可以通過發出協助執行通知告知公安機關、不動產登記機構等國家機關相關執行事項,要求其履行法定職責,這一般不會引起爭議。但是,對于銀行、證券公司、用人單位等執行第三人而言,相關法律、行政法規并未界定其履行協助執行義務的邊界,其履行協助義務不符合人民法院的要求,就可能會遭受到罰款、拘留等處罰。〔70〕參見李理等:《商業銀行須防范協助執行的法律風險》,載《銀行家》2014 年第8 期。民事執行案件一般都會牽涉多方利益主體,例如,遇到強制執行聯名賬戶等情況,銀行嚴格履行了協助執行義務,卻又會招致其他權利人的索賠。〔71〕參見潘紅星:《一起因協助執行聯名賬戶資金引發被訴案件的啟示》,載《銀行家》2016 年第3 期。究其原因,“協助執行通知+妨礙民事訴訟強制措施”的程序操作模式根本未給予執行第三人就無形財產情況提出否認或抗辯的救濟機會。同時,在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亦難以避免“既做運動員,又做裁判員”的身份沖突,一方面不斷指責“協助義務主體以內部規定對抗協助義務”,另一方面自覺“審執不分”帶來執行權力行使上的阻礙與不便。〔72〕參見高桂林、李帥:《民事協助執行中的隱性不協助研究》,載《人民司法》2015 年第23 期。
在我國人民法院組織體系和執行體制之下,通過協助執行制度擴張執行力的主觀范圍雖有合理性和執行效率方面的優勢,但基于消除體系內邏輯矛盾的立法目標和程序保障要求的考量,仍需從理論基礎和具體制度層面進行改善。
首先,執行第三人承擔協助執行義務的理論基礎在于其在社會交往生活中承擔的公共服務角色。現代社會中各類主體的牽連關系日趨緊密。很多聯結企業、市場的平臺類公司不僅是社會交往活動中的重要主體,同時也對眾多新商業形態的存續發揮著重要作用。〔73〕參見劉權:《論網絡平臺的數據報送義務》,載《當代法學》2019 年第5 期。理論上,這類平臺類公司雖然屬于“私法人”,但要求其承擔一定公法義務的理論基礎卻不難證成。普通法系上一直存在“公共承運人(Public Carrier)”的概念,指代從事電力、水、天然氣、公共運輸等壟斷公共事業的私人承攬方。作為公共設施的提供者,這些公共承運人“具有公共屬性,為一般性的對象提供服務,因此必須具備比其他行業從業者更高的責任感”。〔74〕高薇:《互聯網時代的公共承運人規制》,載《政法論壇》2017 年第4 期。在此意義上,考慮到銀行和證券公司在資金結算和金融市場中的作用,將其界定為金融市場的“公共設施提供者”并無太大爭議;〔75〕美國司法實踐中就曾將銀行業認定為“公共承運人”。參見高薇:《互聯網時代的公共承運人規制》,載《政法論壇》2017年第4 期。不過,對于用人單位而言,則一般應將其限縮解釋為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帶有“公益性”的法人團體較為妥當。
其次,執行第三人的協助執行義務應當明確限于財產信息報告和固定期限查封。就財產信息報告而言,執行第三人向執行法院開示被執行人的財產信息并不會直接減少被執行人財產,僅涉及執行第三人與被執行人之間保密義務等私法關系能否對抗國家強制執行力的問題。基于對個人信息及隱私權保護等方面的考量,部分國家和地區對被執行人財產信息的開示往往比較謹慎,一般不會對私人課以嚴重的違法義務;但對于部分法人團體或者國家機關,由于其在社會生活中承擔著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法律則規定其應當履行司法協助義務。〔76〕例如,歐盟的《電子商務指令》第12 條規定,成員國法院及行政機關有權要求網絡接入服務商承擔停止、預防侵權的責任。《信息社會版權指令》第8 條第3 款進一步明確,成員國有義務確保權利人有權針對中介服務商申請禁令,只要其服務被第三方用于實施侵犯著作權或相關權的行為,無論其是否具有過錯。See Directive 2000/3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8 June 2000 on certain legal aspects of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 in particular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Internal Market, Art.12; Directive 2001/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May 2001 on the harmoniz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rt.8(3).域外也有學者主張,在限制法院裁量權的前提下,從立法論的角度可以考慮通過強制手段保障執行第三人履行財產開示義務。〔77〕參見許士宦:《強制執行法》(第2 版),臺北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版,第73 頁。固定期限查封的主要功能在于維持無形財產的既有狀態,申請執行人通過協助執行獲取到明確的財產信息后再進一步推進執行程序。具體到制度設計層面,在維持普通金錢債權的執行力賦予和事后救濟的模式下,對存款、股票、工資、知識產權等“動產化”無形財產仍可以采用協助執行通知的方式,但將銀行、證券公司、用人單位等執行第三人的協助執行義務范圍限定于報告財產信息和固定期限查封(例如,可以明確規定為14 天)。銀行、證券公司、用人單位等執行第三人的“協助執行義務”僅限于向執行法院如實報告被執行人的財產信息及變動情況,并于特定期限內拒絕執行被執行人的財產處分行為。僅在執行第三人不如實報告或者不執行固定期限查封的情況下,執行法院方可給予相應處罰。
再次,區分執行命令權與執行實施權,落實程序保障的要求。在民事強制執行法理論上,一般將民事執行權劃分為執行命令權、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78〕參見孫加瑞:《中國強制執行制度概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 年版,第110 頁。不過,由于人民法院包攬了民事強制執行程序啟動后多數權責,執行命令權與執行實施權在司法實踐中演化為執行法官“自己出查、扣、凍的裁定,自己執行實施”,執行命令權基本上被執行實施權所“吸收”。在通過協助執行制度獲取被執行人的財產信息后,申請執行人應當就責任財產的類型選擇不同的執行程序。如果屬于存款、有價證券、工資、知識產權等“動產化”無形財產,申請執行人應當直接申請針對銀行、證券公司、用人單位、知識管理部門等執行第三人的查封裁定;經過審查后,法院可以作出直接拘束執行第三人的查封裁定。執行法院作出的查封裁定在本質上屬于執行命令行為,受其效力拘束的執行第三人對此可以進行爭執。例如,執行第三人主張存在共同賬戶或其他不宜執行情形的,可以提出執行異議尋求救濟。
最后,對“一般無形財產”執行程序進行“訴訟化”改造。具體來說,如果執行對象是普通金錢債權、股權、特許行政經營權益等無形財產,則申請執行人均應當通過債權人代位訴訟(收取訴訟)的方式獲得對執行第三人的拘束力。在訴訟前或訴訟中,如果申請執行人認為其他利益關系人,如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無形財產的共有人等可能會實施導致責任財產價值貶損的行為,則應當通過申請行為保全獲得救濟。在此意義上,即便是對股權執行而言,執行命令本身也不存在所謂的“穿透”效力,可以禁止股東行使表決權、作出股東會決議,但申請執行人通過行為保全等臨時救濟措施及代位權、撤銷權之訴完全能夠實現對無形財產價值的保護。
五、結語
雖然法典永遠避免不了“制定即落伍”的宿命,但是信息技術的發展、人民法院執行體制、機制的不斷變革仍然讓我們有機會為世界強制執行立法注入中國的制度經驗。《民事強制執行法》是典型是程序法與組織法、實體法交叉領域,公允地說,我國無形財產執行立法中涉及的種種“疑難雜癥”更加生動地反映了強制執行公權力與執行當事人私權利協調并進的復雜性。一方面,在民事強制執行司法實踐中,由于缺少精細的立法技術對執行案件進行“切割”,“審執分立”原則始終無法有效落實;另一方面,為了追求執行效率、兌現“基本解決執行難”的承諾,人民法院在財產信息查詢、執行對象選擇、執行順序安排等方面承擔了過多的職責,也更加不愿意分享乃至分割經過艱難談判獲取的網絡信息查控等權力。這種雙重制度困境在股權等無形財產執行實施的過程中得到了進一步“放大”,似乎從現代公司制度、合同制度等層層法律制度保護之下挖掘可供變價的有形財產已經是人民法院不可推卸的責任。要通過立法構建化解執行難的長效機制,就需要摒棄或者暫時擱置“執行法院包辦一切”的職權主義思維。在此過程中,殊為不易的是將集中起來的執行權能進行“分解”,裝入不同的軌道之中,使其并行不悖,相互制衡。同時,更需要通過私權保護觀念和程序保障思維來控制權力運行導軌的啟動與停止,防止其恣意妄行。在此意義上,無形財產執行程序及相關配套制度如何在我國《民事強制執行法》中呈現,在相當程度上就是我們對財產保護觀念和權力配置模式認識和理解深度的一種映射。一部好的法典不僅要有效回應實務的需求,還應反映我們的理念和追求。謹以此文祝愿《民事強制執行法》成為不朽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