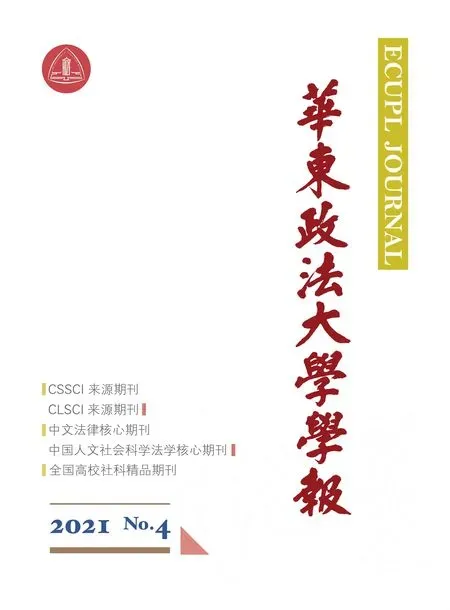重述中國法律思想史
楊一凡
中國法律史學經幾代學者歷時百年的辛勤耕耘,不斷拓寬研究領域和提升學術水平,不斷自我完善,現今已進入了“重述法史”新的發展階段。重述法史,是法史學科的自我革命和完善,是在充分尊重以往學術成果的基礎上,堅持對的,修正錯的,完善有缺陷的,開拓新領域,創立新說,力求更加全面、正確地闡述中國法律史。
為什么要重述法史?簡言之,是科研和現實兩個方面向我們提出了挑戰:一是新出土、新發現的大量法律資料和傳世法律文獻整理的豐碩成果表明,以往法史研究存在嚴重缺陷,認識誤區較多,未能全面、正確闡述古代法制和法律思想;二是傳統的法史研究思維模式已不適應法律教學和文化建設的需要。要挖掘傳統法文化的精華,借鑒和吸收古代法制的優良成分為當代法治建設服務,必須進一步開拓學術視野,改進研究方法,否則將很難交出令人滿意的答卷。
一部中華法律文明發展史,是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緊密結合不斷向前推進、不斷完善的歷史。法律史學是法律思想與法律制度有機結合的學科。重述中國法律制度史,必然涉及重新審視法律思想史的問題,只有把二者結合研究,才能對整個法律史學做出全面、系統地重述。因此,重新認識中國法律思想史,是重述法史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應予以特別重視。
百余年來,多位前輩學者為創建中國法律思想史這門學科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1936 年出版的楊鴻烈著《中國法律思想史》〔1〕楊鴻烈:《中國法律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36 年版。,1984 年、1987 年出版的張國華、饒鑫賢主編《中國法律思想史綱》(上下冊)〔2〕張國華、饒鑫賢主編:《中國法律思想史綱》(上下冊),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 年、1987 年分冊出版。,2000 年、2001 年出版的李光燦、張國華總主編《中國法律思想通史》(4 冊)〔3〕李光燦、張國華總主編:《中國法律思想通史》(4 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2001 年分冊出版。,2011 年出版的楊鶴皋著《中國法律思想通史》(上下冊)〔4〕楊鶴皋:《中國法律思想通史》(上下冊),湘潭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為形成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科體系發揮了重要作用。進入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后,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曾在二十多年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和發展。中國法律思想史作為高等法學院、校的一門課程,在近十多年越來越不受重視的情況下,對它的研究仍未停頓,一些闡發傳統法律文化的著述,就對古代法律思想作了不少新的探討,建樹頗多。然而,結合豐富的法律思想資料重新審視中國法律思想史就會發現,法律思想研究還存在“五重五輕”的缺陷,即:重儒家法律思想輕諸子各家的法律思想,重少數思想家的法律思想輕主持或參與重大立法、司法活動的官僚的法律思想,重刑法思想輕多領域法律思想的全面挖掘,研讀資料重少數文集輕基本法律文獻,重代表性人物法律思想的介紹輕結合法律實踐闡發法律思想。所有這些,都不利于開拓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難以實現全面、正確地闡述中國法律思想發展史的學術目標。本文僅就重述法律思想史談四點淺見。
一、突破“糖葫蘆”復述模式,撰寫發展變化的刑法思想史
以往研究中國法律思想史的著述,就內容而言,大多局限于刑法思想研究,會讓人誤以為中國古代法律思想發展史就是刑法思想史。就研究深度而論,先秦時期法律思想探討相對較好,而西漢以后大多是套用先秦儒家、法家的觀點“照葫蘆畫瓢”,很多學者形象地把這種研究方法比喻為“糖葫蘆”式復述。閱讀這些以復述方式形成的成果,會讓人誤以為西漢以后刑法思想沒有多大發展。這不符合歷史的實際。
(一)論述西漢以后的刑法思想,應重發展,重特色
任何重大的法制變革和法律的制定,都是以法律思想的發展為先導。法律制度不斷完善,法律思想也在不斷發展,既使同一法律術語,也伴隨著法律實踐的深化,內涵或更豐富,或發生變異,呈現出時代特色。西漢以后刑法思想的發展變化亦是這樣。
以“明刑弼教”思想發展變化為例。“明刑弼教”一語源于《尚書?大禹謨》。原文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5〕(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之二《尚書正義》,中華書局1980 年版,影印本,第134 頁。后人概括為“明刑弼教”。宋代以前,“明刑弼教”與“德主刑輔”原則相聯系,強調“先教后刑”和“輕刑”。到南宋時,經朱熹闡發,認為在治國實踐中,教化與刑罰二者同等重要,不必拘泥于“先教后刑”,主張“刑罰立而教化行”。他說:“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名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圣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6〕《朱文公文集》卷一四《戊申廷和奏札一》。朱熹的闡發使“明刑弼教”在不背離倫理綱常的大前提下,增添了新意,意味著刑罰的指導原則沿著“德主刑輔—刑教并重”的發展軌跡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就為“先刑后教”開辟了道路。明代時,朱元璋進一步發展了“明刑弼教”思想,強調“以重刑懲戒奸頑”,成為明清重刑主義的理論基礎。顯然,古代“明刑弼教”思想隨著時代的變遷,內涵有重大改變,絕不能以古代前期的“明刑弼教”理念替代中后期的“明刑弼教”思想。
從魏晉到明清,刑事法律制度的發展、完善歷時1600 余年之久。在此期間,刑名、罪名多有新創,立法內容日益健全,司法制度逐步發展,律典的法律地位和刑事法律體系也有變化,各代都曾結合國情實際,在刑事法制建設方面有所變革,與此相適應,刑法思想也多有變化和發展。因此,西漢以后刑法思想的挖掘,應當重發展,重特色。比如,魏晉至隋唐時期形成的律令關系思想,有關新創刑名、罪名的法律思想,“禮法結合”思想,就值得深入挖掘。明清兩代在刑事立法、司法實踐過程中形成的“律例關系”思想、“重典治國”思想、會審思想、秋審中的慎刑思想、反對宦官司法專橫思想等,就是有時代特色的刑法思想。
(二)結合律典地位和法律體系的變化,闡發與此相關的重大法律思想
律典是刑事法律的代表,法律體系表述的是一代法律規范的全貌及體系內各種法律形式、立法成果之間的有機聯系。魏晉至宋代,“律典”“令典”兩典并重,同為國家“大法”,分別構成了以典為綱,以其他法律形式為目的律令法律體系。元代棄律用格、例。明代變革傳統的律令法律體系,建立了以典為綱,以例和其他法律為目的法律體系。與此相適應,律的編纂方式及法律地位經歷了《諸司職掌》之目(明朝前期)——會典之目(明朝中后期至清朝乾隆)——列入《會典事例》(嘉慶至清末)的變化。明清律與刑例關系,經歷了以例為主(明洪武)——律主例輔(明永樂至弘治十三年《問刑條例》頒行)——律例并行(明弘治十三年——清)的演變,清代審判實踐中,絕大多數案件實際上是以例為法律依據判決的。這些重要的變化都是在統治者立法思想指導下進行的,其中以“大經大法”思想、“律例關系”思想和“大法”“常法”“權變之法”關系思想影響最大。
“大經大法”思想及“大法”“常法”“權變之法”關系思想。古漢語中,“經”是個多義字,常在表述“常道”“經久”“經典”等多種不同意義上使用。對于“大經”“大法”“常法”的內涵,先秦諸子已有論述。〔7〕如《左傳?昭公十五年》:“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荀子?儒效》:“法后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韓非子?飾邪》:“國家常法,雖危不亡”。“大經”,包含有“經典”和“大法、常規”等含義;“大法”,是指國家最重要的基本法律規范;“常法”,亦稱“常經之法”,是指經常施行的法律。“權變之法”,亦稱“變通之法”或“權宜之法”,是指因時因事適時制定且可變通的法律。“權”者,“變通”“機變”也,常與“經”相對。古稱道之至當不變者為“經”,“權者反于經,然后有善者也”。〔8〕《春秋公羊傳》桓公十一年。明人薛甲云:“圣人立法,有經有權。經者,一定之常。權者,不測之用。”〔9〕(明)薛甲撰《藝文類稿》續集卷一,明隆慶刻本。魏晉至宋代,統治者在立法過程中,以“大法”“常法”“權變之法”關系思想為指導,不斷完善律令法律體系。明初在創建典例法律體系時,也遵循這一立法原則,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頒行了《諸司職掌》。《諸司職掌》以職官制度為綱,下分十門,分述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和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五軍都督府的官制及職掌,把《大明律》門目收入其內,全面規范了國家的根本法律制度,是國家的“大法”。明人程敏政對明初幾部最重要的法律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做了這樣的概括:“仰惟我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海內,以文德開太平,其所以貽謀垂憲者,有《皇明祖訓》以著一代家法,有《諸司職掌》以昭一代治典,有《大明集禮》以備一代儀文,有《大明律》以定一代刑制。”〔10〕(明)程敏政撰《篁墩集》卷十,明正德二年刻本。顯然,《諸司職掌》是居于“一代治典”地位的國家根本大法,是“上位法”,而《大明律》是“一代刑制”,與《大明集禮》《皇明祖訓》一樣,是“下位法”,即“常經之法”。
“大經大法”一詞最早出于唐代韓愈的《與孟尚書書》:“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于是大壞……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11〕(唐)韓愈撰《韓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第194 頁。宋、元、明、清史籍中,有關“大經大法”的論述甚多。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用語,通常是在表述古人“治世之大道”“治世之經典”和“宏綱大法”的意義上使用。在明清立法文獻中,“大經大法”作為有特定內涵的法律用語,專指在國家法律體系中居于“綱”的地位、“經久常行”的最高法典。正德《會典》頒行后,明清人稱《會典》為“大經大法”。明清兩代在完善典例法律體系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大經大法”思想和“大法”“常法”“權變之法”關系理論。其要義是,國家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既要制定“大經大法”以規范國家的各項根本制度,也要以“常經之法”為則,規定各種具體的法律制度,并隨事勢變化制定各類權宜性質的“變通之法”,以補充“大經大法”“常經之法”之不足。這一歷史時期,《大明律》《大清律例》是《會典》之目,屬于“常經之法”,其在國家法律體系的地位較之唐、宋有所降低。
近年來,圍繞著明清法律體系是“典例法律體系”還是“律例法律體系”,學界存在爭議。律典與《會典》,哪個是國家的最高法典,是爭議的焦點。閱孝宗、武宗、世宗、神宗撰寫的《會典》御制序可知,“成一代畫一經常之典”是明代統治者對《明會典》法律地位的定位。〔12〕關于《明會典》編纂的宗旨,正德《會典》書首載明孝宗于弘治十五年(1502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發布的《御制大明會典序》云:“斟酌古今足法萬世者……而世守之”;該書前載明武宗于正德四年(1509 年)十二月十九日發布的《明會典序》云:“以《職掌》為主,類以頒降群書,附以歷年事例,使領其事,事歸于職,以備一代之制”;萬歷《會典》書首載世宗皇帝嘉靖八年四月初六日敕諭:“其修書后,二十八年之事,務要悉心考究。凡損益同異,具事繁年,條分類列,通前稡為一書,以成一代完典,使天下臣民知所趨向”;該書首載神宗皇帝萬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敕諭:“務令諸司一體,前后相貫用,不失我祖宗立法初意,以成一代畫一經常之典。”纂修萬歷《會典》時張居正《請專官纂修疏》云:“竊以《會典》所載,乃昭代致治之大經大法”。〔13〕(明)張居正撰《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四十,明萬歷四十年唐國達刻本;又見(明)過庭訓撰《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明天啟刻本。又,清人孫承澤在《春明夢余錄》一書中,對《明會典》的性質作了精辟的概括:“弘治五年,命內閣諸臣仿唐、宋《會要》及元人《經世大典》《大元通例》,編成一書,賜名《大明會典》。其書以《諸司職掌》為綱,以度數名物儀文等級為目,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于職用,備一代定制,以便稽考。嘉靖二十八年修之,萬歷十五年再修之,一代之大經大法備焉。其余諸書不具載。”關于《清會典》是國家“大經大法”的定位,乾隆《會典?凡例》明確規定:“以典章會要為義,所載必經久常行之制。茲編于國家大經大法,官司所守,朝野所遵,皆總括綱領,勒為完書。”〔14〕《大清會典》(乾隆朝)書首《凡例》,(清)允裪等纂、李春光校點,載楊一凡、宋北平主編:《大清會典》,鳳凰出版社2018年版。既然《會典》是“大經大法”,刑律是《會典》的組成部分,例是法律的核心內容,稱其為“典例法律體系”就比較妥當。如將其稱為“律例法律體系”,就存在兩個致命的缺陷,一是《會典》《諸司職掌》和《大明集禮》《大清通禮》《憲綱》等很多基本法律及吏、戶、禮、兵、工諸例等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法律,都會被排除在外。二是,《大明律》先后被列入明代大法《諸司職掌》和《明會典》,《大清律》先后被列入康熙、雍正兩朝《會典》和嘉慶、光緒兩朝《會典事例》,此說就與當時的立法實際和明清人的論述大相徑庭。
“律例關系”思想。明清例有吏、戶、禮、兵、刑、工六例之別,刑律與“刑例”之外的其他五例沒有從屬關系。詳閱明清人有關刑律與刑例相互關系的論述,可知其所說的“例”是特指“刑例”,“律例關系”是指刑律與刑例的關系。許多著述以“刑例”概述“六例”,似為不妥。
明清兩代,律例關系思想伴隨著法制變革和刑事法律體系的發展演變,內涵也多有發展和完善。明初,明太祖朱元璋認為:“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有經有權。”〔15〕(明)呂本等輯《明太祖寶訓》卷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歷三十年春秣陵周氏大有堂刻本。在刑事法律的制定和實施方面,從“用重典以懲一時,酌中制以垂后世”指導思想出發,在按“貴存中道”“可貽于后世”要求多次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治亂世”和懲治“奸頑”,行用“重典”,以“事例”形式頒布了大量的苛法峻令。〔16〕詳見楊一凡:《洪武朝峻令、重刑禁例和法外用刑補考》,載楊一凡:《明代立法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109-137 頁。洪武年間,名義上律為“常經之法”“例以輔律”,很多年間法律的實施情況實際上是“以例為主”。朱元璋死前留下遺訓:“已成立法,一字不可改易”,〔17〕《皇明祖訓》序,載楊一凡、田濤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第3 冊),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483 頁。“群臣有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18〕《明史》卷九十三《刑法一》,中華書局1974 年版,第2279 頁。故《大明律》作為祖宗成法,至明末未改。然刑書所載有限,天下之情無窮。從永樂到弘治十三年(1500 年)頒行《問刑條例》的近百年間,各朝為解決刑律無法適應審判需要的問題,頒行了大量的刑事事例,出現了“事例冗繁”的弊端。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制定《問刑條例》的呼聲越來越高,并形成了一套更加完善的律例關系思想。這一思想的核心內容可概括為三點:一是“貴依律以定例”,即刑例的制定必須符合律意;二是“立例以輔律”〔19〕(明)舒化:《重修問刑條例題稿》,載楊一凡編:《中國律學文獻》(第3 輯第2 冊),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影印本,第119-121 頁。;三是“律例并行”〔20〕《明孝宗實錄》卷四十八。。前兩點是從立法角度講的,后一點是從司法角度講的。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問刑條例》成為與《大明律》并重并行的刑事法律,通過三次修訂《問刑條例》實現了明代刑法的完善,并于萬歷十三年(1585 年)將《大明律》與《問刑條例》合編,以《大明律例》命名頒行天下。清朝沿襲了明朝的律例關系理論,作為刑事立法的指導思想。《大清律例》自乾隆五年(1740 年)頒行后,律文恒存,至清末未改。清代刑法的完善,主要是通過22 次續纂《大清律纂修條例》(乾隆二十六年前稱《續纂條例》)實現的。明代的《問刑條例》和《大清律例》中的律后附例,是刑律的有機組成部分,律與條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司法審判中,以例為依據判決的刑事案件數量居多。這一歷史時期的刑事立法之所以較好地解決了“以例破律”的難題,就與貫徹律例關系思想確立的立法原則有關。
二、突破“以刑為主”論的局限,開辟法律思想研究的新領域
傳統的“以刑為主”說,誤導人們僅從刑法角度闡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發展史,曾長期成為開拓法史研究的巨大認識障礙。現今,“以刑為主”說雖然在理論上被拋棄,但在其影響下形成的慣性思維仍未徹底清除,致使刑法思想以外的法律思想大多沒有深入研究,有些還未涉及。因此,拓寬研究領域,是深化傳統法律思想研究的重大課題。
(一)古代法律思想多元、豐富,領域寬廣
在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中,各種法律形式并存,吏政、食貨、禮制、軍政、刑事、民事等各種法律并存,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并存,共同組成完整的法律體系。與法律實踐相輔相成,多元法律思想各具特色,既有歷代都關注、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學說,如“經學與律學”“禮與法”“德與刑”“人治與法治”等,也有與各類法律相關的法律思想,如吏政法律思想、食貨法律思想、禮法思想、軍政法律思想、民事法律思想、司法思想、監察法思想、地方立法思想及法律編纂、立法技術的論述,還有創建各種具體法律制度的學術觀點等。
古代的每一種法律思想,都有與其他法律思想不同的內涵和特色。以“軍政法律思想”為例。這是與吏政、食貨、禮制、刑事諸方面法律思想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相對獨立的法律思想體系。中國古代法律起源于祭祀和戰爭。“刑起于兵”,最初的刑法是軍法。歷代頒行的法律,軍政類法律占相當比重。《周禮》采用“六卿分職,各率其屬”〔21〕(清)伊桑阿等纂《大清會典》(康熙)書前《御制大清會典序》,楊一凡、宋北平等主編,關志國等點校,鳳凰出版社2016 年版。編纂體例,《夏官司馬》為六典之一,首開記述軍政制度之先河。《大唐六典》仿效《周禮》,設“兵部”專卷,記載唐朝的軍政制度。此為后世效法,《元典章》、明初的《諸司職掌》、明清《會典》均設“兵部”,為國家軍政“大法”,并以典為綱,以其他軍政法律為目,形成了系統的軍政法律體系。如明清兩代頒行了《軍政條例》《兵部則例》《中樞政考》《兵部處分則例》等“常經之法”和諸多的軍政條例、事例。隨著軍政立法的逐步發展,古人還撰寫了許多論證軍政法律思想的著述。研讀這些文獻可知,先秦法家、兵家的“富國強兵”“以兵輔政”“以法治軍”“上下合同”“以民為本”“任賢能,明賞罰”等法律主張,不僅為西漢以前的軍政立法所遵循,而且在西漢以后融入正統法律思想,對完善各代軍政法律制度發揮了重大作用。就先秦諸子學術思想對古代軍政法制的影響看,兵、法、儒三家相對較大,但兵家思想的影響尤為突出。
每一種法律思想,在立法、司法實踐中,內涵也不斷豐富和變化。以明代刑事立法思想為例。《大明律》《大誥》《問刑條例》是明代三部代表性的刑事法律,因彼此的功能不同,立法思想也各具特色。編纂《大明律》目的是“傳之萬世”,“令子孫守之”,立法以“當適時宜,當計遠患”“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法貴簡當”“貴存中道,輕重適宜”為指導原則。頒行《大誥》的用意是“警省和懲創奸頑”,立法以“亂世用重典”“明刑弼教”“以刑去刑”為指導原則。制定《問刑條例》是為了革除前朝“條例冗繁”的弊端,立法以“革冗瑣難行”“立例以輔律”“情法適中”“經久可行”為指導原則。
古代法律思想領域寬廣,內涵豐富。要全面揭示古代法律思想的面貌,需要幾代人堅持不懈的探索。當代學者肩負的首要責任,是解決妨礙法律思想研究的重大問題,構建科學的學科體系框架。為此,必須打破“以刑為主”論的束縛,注重法律思想新領域的開拓;要加強對非刑事法律思想的研究,注重法律編纂原則、立法技術等方面論述的研究;要選擇對于學科發展、法律文化建設有重大學術和現實意義的課題,作為研究重點。
(二)開拓法律思想研究新領域,食貨法律思想研究是最佳突破口
“食貨”一詞,是古代經濟、財政、金融的統稱。我之所以提出開拓法律思想史研究新領域以“食貨法律思想”為突破口,是基于以下三點考慮。一是食貨法律與國計民生休戚相關,歷代治國“莫不以谷貨為本”,〔22〕《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六》,中華書局1974 年版,第2849 頁。都很重視健全食貨法制。食貨立法無論是立法總數還是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都遠遠超過刑法。二是較之刑事法律,食貨法律受“三綱五常”“禮治”思想的影響相對較小,食貨法律思想和管理經驗中可借鑒的優秀成分也相對豐碩。三是可供研究的古代食貨法律資料極其豐富。浩瀚的明清食貨法律文獻大多存世,明代以前的食貨法律雖已失傳,但通過輯佚仍可大體揭示古代食貨法制和法律思想的概貌。近年來,我約請十多位學者進行了金文、簡牘、碑刻石刻中食貨法律資料輯佚,秦漢至元代食貨法律一些重要領域的專題輯佚,明代食貨則例輯佚,輯佚的成果表明,這些文獻中記載了極其豐富的食貨法律思想。開拓食貨法律思想研究,不僅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而且也較易取得重大收獲。
從出土法律資料和秦漢傳世文獻的記載來看,先秦時期,伴隨著食貨法令的頒布和食貨制度的形成,產生了相適應的食貨法律思想。春秋戰國社會大變革時期,各國為富國強兵,爭奪霸主地位,改革、變法不斷。在經濟管理領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經濟政策和法律思想。比如,公元前685 年,齊桓公即位后,重用管仲主持國政,管仲在變革食貨制度過程中,針對“井田制”日漸崩潰的狀況,提出了“均地分力”等土地改革思想,其內容是在重新丈量、規劃土地疆界、依據土地肥瘠公平合理折算后,把土地直接分給農民耕種;在賦稅立法方面提出了“薄賦斂”“立關市之賦”和“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地肥瘠分等級征稅等主張;為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提出了“官山海”即鹽由國家專營的主張;為堅持“以農為本”,穩定農業階層,防止人口逃離,提出了士、農、工、商“四民定居”思想。在管仲的上述思想指導下,齊國的食貨法制變革取得成功,一躍成為強國。又如,戰國后期,商鞅主持了秦國的兩次變法。如果把變法的內容和他的法律思想結合研究,可知“壞井田,開阡陌”〔23〕(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中華書局1983 年版,第1126 頁。“獎勵農戰”“重農抑商”是他最重要的食貨法律思想。秦國變法采取的有關確立土地私有制、鼓勵農業生產、統一稅收標準及重關市之賦、重稅于商等法律措施,就是在他的食貨法制變革思想指導下制定的。秦行商鞅之法,很短時間內由弱變強,成為戰國七雄之首。
先秦時期,除法家外,儒、兵、墨、道、農、雜等各家的學術思想中,也有不少食貨法律思想或與食貨法制相關的論述,其中以儒家、農家論述最多。儒家的食貨法律思想主要是“重農”“富國裕民”“義利并舉”“薄賦斂”和提倡工商業等。“農家”是戰國時期一個有相當影響的學派,以研究農業生產和農業與國家關系為學術要旨,主張“民本”“上農”“君民同耕”“任地”“審時”“市賈不二”,其學說系融諸家學術觀點而成,其學術觀點除“君民同耕”外,大多為法家、儒家、雜家、墨家等諸子各家所吸收。先秦農家著述雖已失傳,但被儒、法、墨、雜等各家著作所記載,如《管子》《孟子》《墨子》《呂氏春秋》等書中就有不少關于農家思想的記載。
西漢以后正統法律思想中的食貨法律思想,是在融合先秦諸子各家食貨法律思想的精華的基礎上形成的。魏晉以降,各朝都重視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變革食貨法制,不僅適時頒布了大量的食貨法律法令,而且在完善田制、賦役、漕運、倉庫、商稅、捐納、賑濟等各項具體食貨制度和健全鹽法、茶法、錢法、鈔法的過程中,提出了各種有時代特色的食貨法律思想。清以前各代何以在各地自然條件千變萬化且未編纂食貨法典的情況下運用食貨令、例調節各種復雜的經濟關系,為什么中國古代的商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受到抑制,就與當時奉行的食貨法律思想有密切關系。清代乾隆時期,形成了以《會典》戶部為綱、以《戶部則例》為基本法律,以食貨條例、事例為變通之法的新食貨法律體系,并形成一套系統的食貨法理論。古代的食貨法律思想極其豐富,在不同時期又多有發展和變化,閃爍著古人智慧的光芒,有許多法律主張和立法經驗可供借鑒,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總結。
三、突破“法律儒家化”論束縛,全面挖掘法家及各家的法律思想
以往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長期停滯不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與“中國法律儒家化”論的影響密切相關。這一論斷引導人們忽視法律思想、法律制度發展演變的實際,僅限于從儒家理論中挖掘法律思想,把不斷深化、豐富多彩的法律思想史,演繹為“糖葫蘆”式的復述儒家思想的歷史。如不從“法律儒家化”論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法律思想研究就很難前進一步。
關于瞿同祖先生提出“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本意、后人的誤讀泛用及“古代法律并不是都儒家化了”等問題,我在《質疑成說,重述法史》一文〔24〕參見楊一凡、陳靈海主編:《重述中國法律史》(第1 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9 年版,第4-5 頁。中已陳述己見,本部分僅就如何打破這一成說的局限,全面挖掘法家及各家的法律思想這一議題做些探討。
(一)西漢以后的正統法律思想是各家思想融合的結晶,用“法律儒家化”表述難以自圓其說
古文獻中的“儒家”,是指孔子學派。長期以來,一些著述認為,自漢武帝采用董仲舒建議,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歷代師承孔孟道統治國,法律也“儒家化”了。然而,全面閱讀古代法律,可發現“中國法律儒家化”論存在以下三大缺陷。
其一,西漢以后各代統治者奉行的正統法律思想,是在吸收、融合先秦諸子各家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的。從先秦諸家思想對后世法律的影響看,儒、法兩家影響巨大,儒家思想在吏政類法律、禮制類法律、刑事法律領域的影響占主導地位,而戶、兵、工類法律絕大多數沒有“儒家化”特色。陰陽、墨、名、道、農、兵、醫、雜等諸子各家,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比如,戶類法律就深受法家、農家思想的影響,兵類法律深受法家、兵家思想影響,法醫類文獻則受醫家影響較多。至于工類法律的立法指導思想,以往學界未曾涉及,我最近作了初步探討,發現墨家“節用”“尚儉”和“摹略萬物之然”“巧傳求其故”和道家“法道自然”“好道進技”等思想,對這一領域法律的制定影響頗大。如此等等,簡單地用“儒家化”表述似過于絕對。
其二,西漢以后的許多法律思想,屬于后人的新創,與先秦儒家思想沒有密切的傳承關系。比如,與變革法律體系相關的“典例”“律例”關系思想,創新法律形式的思想,與創建新的行政、軍政、經濟管理具體制度相關的許多法律思想,健全少數民族地區法制的思想及清代的“行政處分與刑罰分離”思想等。這一歷史時期統治者奉行的正統法律思想,有些還與先秦孔孟儒家思想相對立。比如,西漢以后的各代食貨立法,都以“重農抑商”思想為指導,頒行了大量的限制商業發展、禁止與域外民族通商、海禁方面的法律法令。“重農抑商”思想是商鞅首先提出的,是先秦法家的重要治國主張,與儒家提倡工商業的主張相對立。又如,明清刑律采用“輕其輕罪,重其重罪”的刑罰原則。“輕其輕罪”,對于不直接威脅君主統治的“典禮及風俗教化之事”量刑減輕,這與儒家的“重禮”思想相背離。“重其重罪”,是對“賊盜及有關帑項錢糧”等直接威脅君主專制統治和經濟利益的犯罪加重處刑,這一立法指導思想是李悝《法經》中“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25〕(戰國)李悝《法經》:《盜律》,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三十《刑法志》,中華書局1982 年版,第922 頁。主張的翻版。如此等等,把這些法律思想不加分析地附會于儒家就不合適。
其三,“中國法律儒家化”論與古人的論述不相吻合。“法律儒家化”一詞在古籍中從未出現過,是近代前輩學者的首創。且不說提出此論依據的僅是刑事法律資料,用研究刑事法律的結論表述全部法律規范的特質本身屬于硬傷。就以刑事法律而言,“法律儒家化”論也與古人的論述相抵牾。以古代律學為例 。我查閱了唐至明清200 余種古代律學和司法文獻序,〔26〕張松、張群整理《古代法律文獻序跋選輯》(收入楊一凡主編《古代法律資料鉤沉》,即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收入古代法律文獻序跋213 篇,其中律例、律學類67 篇,案例判牘類57 篇,司法檢驗類19 篇,官箴政書類60 篇,其他10 篇。我在撰寫此文時檢索了該書中的“法家”“儒家”出現次數。在此向兩位整理者致謝。其中出現“法家”“儒家”字樣52 處,內有“儒家”2 處,“法家”50 處,詳閱這些文獻序跋可知,不少律學著述的作者自稱“法家”,有些律學成果索性以“法家”命名,如《法家體要》《法家裒集》《新刻法家透膽寒》等。這些法家也都很“重禮”,它們的“禮、法觀”與儒家毫無二致,并常以“外法內儒”相標榜。秦漢至宋元古籍中所見“法家”一詞,除極少數仍作為先秦諸子之一的“法家”學派詞義使用外,大多指稱“典獄職官”。明清人通常把從事法律職業且有貢獻的人士稱為“法家”,把注釋律學有重要成果的人士稱為“律家”或“法家”。如張廷驤《辦案要略》序云:“王蔭庭先生為乾隆中葉法家老手,著有《刑錢必覽》《錢榖備考》《政治集要》等書行世。”〔27〕(清)王又槐撰《辦案要略》卷首張廷驤序,清光緒十八年浙江書局刻本。金師文《律例歌訣》序云:“此《律例歌訣》一書,不詳編者姓氏,大抵名法家先輩之所為也”,〔28〕(清)佚名輯《律例歌訣》卷首金師文《律例歌訣序》,清光緒刻本。如此等等。元人柳赟在論及儒、法關系時說:“法家之律,猶儒者之經。五經載道以行萬世,十二律垂法以正人心”,〔29〕(唐)長孫無忌等撰《唐律疏議》卷首柳赟《唐律疏義序》,元至正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刻本。認為二者是“道”與“法”融合的關系。既然古人同時肯定儒、法等各派在完善刑事法律中的作用,我們在研究律學時,就應按歷史的本貌去闡述各種學派的法律思想。
考察西漢以后的法律思想,無論是立法思想,還是司法思想,無論是律學,還是統治集團代表人物的法律思想,幾乎都具有融先秦儒、法等諸家法律思想為一體的特征。
古代法律思想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西漢以后,雖然儒家學說在統治集團奉行的正統法律思想中居主導地位,但各種社會思潮此起彼伏,從未間斷,如西漢后期和東漢初中期的對讖緯神學的批評,漢末魏初的社會批判和名法思潮,魏晉時期玄學、法哲學思想和無君論思潮,東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佛教、道教的傳播,北宋仁宗、神宗時期的變法改革思潮,明清時期批判理學和宦官司法專橫、反對君主專制的啟蒙思想等。伴隨著各種社會思潮的興起及統治集團的法制變革,出現了許多與“獨尊儒術”不同調乃至對立的法律思想,如桓譚、王充反讖緯神學的法律思想,王符兼重儒法的思想,曹操、諸葛亮的“名法”思想,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法哲學思想,劉頌的重法思想,鮑敬言否定禮法的無君論思想,葛洪的道本儒末、舍儒從道思想,隋文帝的重法輕儒思想,范仲淹、王安石的變法思想,陳亮、葉適反理學的法律思想,遼圣宗的貴賤同法思想,朱元璋的重典治國思想,李贄、戴震批判理學的法律思想,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唐甄反對君主“獨治”的法律思想,遼、金、元各少數民族執政者帶有民族特色的一些法律思想等。所有這些,表明古代法律思想具有多元的特色。要正確闡述中國法律思想發展史,就應充分揭示不同歷史時期社會思潮對正統法律思想的影響,全面評述觀點相異的各種法律思想。在這方面,楊鶴皋先生《中國法律思想通史》 做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獨特的見解,其研究法律思想所持的批判分析方法值得后學效法。
(二)再識先秦法家,加強先秦諸子各家法律思想比較研究,為重述法律思想史開辟道路
當前,研究法家特別是先秦法家思想成為法史學術探討的一大熱點。2017 年,武樹臣教授所著的《法家法律文化通論》〔30〕參見武樹臣:《法家法律文化通論》,商務印書館2017 年版。出版,該書從中國法的原始基因探索法家法律文化的源頭,從春秋戰國儒家的沿革厘清法家的師承脈絡,從法家法治思想的古代中國特質尋找其社會歷史內涵,從數千年的法律實踐論證法家思想對古代法制和法文化的影響,可視為重新審視法家法律文化的首倡之作。在此之后三年來,學界發表了數十篇探討先秦法家思想的論文,發表了不少新的見解。近讀段秋關教授所撰的《再識先秦法家》一文,〔31〕段秋關:《再識先秦法家》,未發表,收入楊一凡、陳靈海主編《重述中國法律史》(第2 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即將出版。該文認為應從法家稱謂、治國思想、法的價值、學術成就等多個方面重新評述先秦法家及其法律思想,提出“‘法家’非時人自稱,實后人所授”;“法家之‘法’不等于今語法律”;“法家人士無組織有共識”;“‘法治’與‘德治’斗爭亦屬虛構”等新的論斷。所有這些,使我深切感到,先秦法家思想雖然經幾代學者的探討,仍有重新認識的必要。“再識先秦法家”,就是要摒棄“文革”以來在“評法”問題上的實用主義、形而上學的思維和方法,全面地、客觀地評價先秦法家的學術觀點。為此,評價先秦法家思想有必要強調兩點。一是先秦法家的“法”不只是表述行為規則,還用以表述他們主張的統治策略和方法。再識先秦法家,就要既重視研究其政治法律思想,也重視研究其食貨、軍政等方面的政策和法律主張,要從多元的視角全面挖掘法家的法律思想。二是要緊密結合春秋戰國時期法制變革及以后近兩千年帝制時代法制建設的實際,正確地評價法家人物的學術觀點及其歷史作用,既要肯定法家的學術貢獻和對古代法制建設的積極影響,又要揭示法家學術觀點的糟粕及對古代法制建設的消極影響。“再識先秦法家”的重大意義,不只是正確闡述法家思想,而且必將為重述先秦各家思想、西漢以后正統法律思想開辟道路。
這里還需要強調指出,在重述先秦法家思想的同時,加強諸子各家法律思想的研究,特別是開展先秦諸子各家法律思想的比較研究,對于正確認識西漢以后正統法律思想有重大意義。西漢以后形成的正統法律思想,是融合先秦儒家、法家及諸子各家法律思想的結晶。要正確揭示各代正統法律思想的內容、特色及思想淵源,就必須首先對先秦諸子各家法律思想的區別與會通有清晰的認識。
先秦諸子各學派的學術要義有別,然求“治”的目標相通。各家思想從形成之日起就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亦有互相吸收和會通之處。當時諸子各家實是各說各話。“儒家”和“法家”是后人的劃分,含有主觀因素,此兩家也是觀點相異,至多可稱為“爭鳴”,不存在所謂的“斗爭”。
司馬談《論六法之要指》對陰陽、儒、墨、法、名、道六家的評論是:“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32〕(西漢)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見《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華書局1999 年版,第3288-3289 頁。從這段評論看,司馬談對陰陽、儒、墨、名、法五家的看法比較客觀,受當時盛行的黃老思想影響,偏愛道家。司馬談評論陰陽、儒、墨、名、法五家所持的客觀態度和分析比較的方法,可作為研究法律思想史的借鑒。
司馬談評價道家時說:“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33〕(西漢)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見《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華書局1999 年版,第3289 頁。在他看來,“道家之術”的優點,是吸收了陰陽家關于四時運行順序之說,儒家、墨家之長,名家、法家之精要。其實,先秦諸家法律思想形成過程中都曾吸收了其他各家的思想。比如,兵家與法家的主要區別是關注領域的寬窄不同,而產生的淵源相同,持共同的法治觀,都強調樹立君主、將領的權威,對“勢”“術”的認識大體一致,屬于同一思想體系脈絡下的思想學說。雜家作為戰國末至漢初的哲學學派,也是博采各家之說而成。就以思想觀點分歧較大的儒、法兩家法律思想而論,既有區別,又有互相吸收和會通之處。儒家重“禮”,強調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張“德治”;法家重“法”,強調刑罰的作用,主張“法治”,“刑無等級”“以刑去刑”。但儒家并不否定政令刑罰的作用,法家也不是全盤否定道德的作用,兩家在建立統一國家和維護父權、夫權家庭秩序方面的認識是一致的,正由于儒、法兩家有其會通之處,后經荀子、董仲舒等重新整合,吸收儒、法兩家及其他各家法律思想,才形成了正統法律思想。
四、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地進行理論創新
創新法律史學,是當代法史學者的歷史責任。要實現這個學術目標,不僅要全面揭示古代法制的面貌,準確論證古人的法律思想,還需進行理論創新,即:正確闡述古代法制和法律思想發展演變的規律,科學地總結古代法制建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提煉和歸納傳統法文化的精華,在顛覆和修正舊說的基礎上創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學科理論。理論創新的意義,是既可為當代中國法治建設提供借鑒,又能為后代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
中國法律史學是法學與歷史學的交叉學科。注重史料,堅持法律實踐與法律思想相互作用的認識論,是治史的基本要求。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研究的理論創新,應是尊重歷史前提下的創新,這就要求我們在探討某一個命題時,必須盡可能地窮盡資料,把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結合研究,多方論證,去偽存真,得出符合歷史實際的結論。
在以往的法史研究中,或因資料匱乏,或因受“以刑為主”“法律儒家化”論的影響,或因未認真堅持“論從史出”的寫作原則,出現了不少論斷的失誤。這些認識上的誤區,嚴重地妨礙著法史研究的繼續開拓。顯然,修正誤判的舊說,創立新說,是重述法史、創新法史理論首先應解決的重大問題。法史理論創新是通過對歷史上法律制度、法律思想的全面考察實現的。唯有確鑿的證據,才能推翻支撐不實之論的依據;只有洞悉古人的法律學說,才能準確地進行理論概括。因此,在法史理論創新過程中,決不可把法律制度與法律思想割裂研究。顛覆舊說、創立新說本身就是理論創新,它既是法律制度史研究,也是法律思想史研究共同承擔的任務。這里僅對與重述中國法律思想史密切相關的四種觀點提出修正。
(一)成案性質“司法判例”說
以往的一些著述,把“成案”的性質界定為“司法判例”,然查閱現存的判牘案例文獻,“成案”一詞,古人通常是指已辦結的公文卷宗,也指訴訟中判定的案件或辦理的行政、經濟諸事務的先例。古代成案既有以刑案為主的司法成案,更多的是行政公務類成案,把“成案”的概念和性質表述為“司法判例”無疑是不妥當的。現存的古代成案集上百種,成案以數百萬計。何以判斷失誤?皆因只閱讀了《刑案匯覽》等幾種文獻,而未及其他文獻所致。
(二)“從令至例形成明代律例體系”說
這種觀點認為:“弘治《大明會典》的問世標志著例正式取代令成為了明代法律的基本且主要形式,明代律例法體系進而由此生成”,“明代的令到例的轉變在《大明會典》編纂之前即有一個緩慢發展的過程”。〔34〕程晶等:《從令到例:論明代律例法律體系的生成》,載《學術界》2020 年第10 期。首部《大明會典》成書于弘治十五年(1502 年),于正德六年(1511 年)頒行。按照作者的觀點,從明初到《大明會典》問世,律例法律體系的形成經歷了從令到例長達140 年左右的演變。且不說用“律例法律體系”概括明代法律體系能否成立,也不說對令的內涵的解釋是否正確,僅就明代的令、例關系而言,自洪武元年(1368 年)正月初一日頒行《大明令》后,所有頒行的法律都不再以“令”命名。以“例”代“令”,從洪武初到明末都是如此,并不存在由令到例形成法律體系的事實。何以判斷失誤?一是作者未能全面研讀明代法律文獻。在明代,“著為令”與“著為例”是同義語,《明實錄》中記載的一些“著為令”,也是“著為例”,在法律頒行時都是以“例”命名。二是作者未結合明代立法實際深入研究,不加分析地套用學界對前代令的一些論述描繪明代法律體系。這樣得出的結論,很難經得起推敲。
(三)清代條例“專指刑事法規”說
已出版的中國法律史教材、法學辭典、著作和發表的論文,凡論及“條例”內涵和性質者,除個別表述為“主要指刑事法規”外,幾乎都把它界定為“專指刑事法規”。〔35〕如陳浩、杜鵬著《法制史學習小詞典》:“清代最主要的法律形式是例,例是統稱,可分為條例、則例、事例、成例等目。條例是專指刑事單行法規”(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 年版,第89 頁);陳一容《清“例”簡論》:“‘條例’是清‘例’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和最主要的類型之一,指的是與作為清代刑事基本法律的律文相匹配的刑事法規”(《福建論壇》2007 年第7 期,第65 頁);謝天《清代條例研究》:“條例是刑事法規,也即通常所說的‘例’”(安徽大學2007 年碩士學位論文)。最近幾年出版的法史教材、法學辭典和發表的論文,凡是涉及清代條例者,都持清代條例是刑事法規專稱的觀點。然考察清代的立法實際,這一論斷不能成立。史實的本相是,從清開國到清末,不僅以“上諭”形式發布了大量的各類條例,中央各部院還就管轄的各類事務,不曾間斷地制定和頒布了各類條例。清代頒行的單行條例很多已失傳,現存于世的有《都察院擬監察職權條例》〔36〕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都察院擬監察職權條例》,清順治十八年刻本。《禮部題準更定科場條例》〔37〕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法學分館藏《禮部題準更定科場條例》,清康熙初年刻本。《欽定服色條例》〔38〕北京大學圖書館、寧波天一閣博物館藏《欽定服色條例》,清康熙十八年刻本。《吏部條例》〔39〕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吏部條例》,清抄本。等上百種。現存的清代條例匯編集也甚多,代表性的有《各部院條例冊》《上諭條例》《頒發條例》《匯刊條例冊》《匯總條例》《條例》《四季條例》《條例約編》《各部條例》等多種。這些條例集收入條例上萬件,其中多數為非刑事條例。如《上諭條例》嘉慶元年刻本記乾隆元年至十年條例共1214件,其中刑事條例272 件,占22.4%;非刑事條例942 件,占77.6%。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五朝各部院條例冊,收入條例1381 件,內有刑部條例為561 件,占40.55%。從目前見到的200 余種獨立成書的條例文獻看,清廷雖然很重視刑事條例的編纂,但刑法畢竟是法律體系中的部門之一,所占比重有限,故清代頒布的條例,多數仍為吏、戶、禮、兵、工類條例。清代條例“專指刑事法規”說之所以長期流行而未得到修正,應是在“以刑為主”說影響下,注重刑例研究、忽視對清例全面研究的結果。
(四)清代“通行”性質“成案”說、“條例”說、“章程”說、“折衷”說、“法律形式”說
清代法律文書中,“通行”作為學術用語被廣泛使用,頒行的“通行條例”“通行章程”“通行成案”數量巨大。關于“通行”的性質,學界眾說紛紜,有“成案”說、“條例”說、“章程”說、“折衷”說、“法律形式”說。〔40〕參見胡震:《清代“通行”考論》,載《比較法研究》2010 年第5 期。然查閱現存的清朝法律文獻,這五種論斷都需商榷。“通行”的本意是“通令遵行”。就“通行條例”而言,經皇帝欽準的例,有些是因特定的人或事而立,只適用于特定的對象,有些則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在全國或某一地區、某一領域通用。所謂“通行”,是專指后者。就“通行章程”而言,清朝頒行的章程,既有朝廷制定的,也有地方官府制定的,有些章程只適用于特定的狹小地區或某一地方事務,而有些章程則可在全國或某一省區適用,所謂“通行”,是專指后者。至于“通行成案”,是在律例無文或定期修例期間,為應急需要,經皇帝欽準,把一些適用于全國的典型案例冠以“通行”稱謂,在司法和行政事務中援引適用。“通行成案”雖保留了“案”的外部結構形式,卻被賦予類似定例的法律效力,不再具有純粹“案”的性質,而屬于制定法的范疇。由此可見,“通行”是朝廷下達單行法規法令的一種頒布形式,清代“通行條例”“通行章程”“通行成案”中的“通行”二字的本意和功能,主要是用以表述法律法令的效力和適用范圍,而不是一種法律形式。其實,以“通行”方式頒布法規法令至遲在唐代已經出現,明代治國實踐中就曾廣泛行用“通行條例”。清代沿襲明制,只是擴大了“通行”法律文書的稱謂和適用范圍。何以在界定“通行”的性質時出現諸多歧義?也是因未充分閱讀有關“通行”的法律資料造成的。
要全面準確地闡述中國法律思想發展史,實現學科理論的創新,除修正誤導后人的不實之論外,還應特別注意以下兩點。
其一,規范學術用語 。任何一門學問要形成科學體系,都需要對學科的研究對象、范疇、支撐學科的重大學術觀點、學術術語進行準確的界定或闡發。法律思想史研究也是這樣。從已發表的成果看,有關法律術語的使用比較混亂,歧義較大。這些術語是“法律體系”“儒家”“法家”“人治”“法治”“禮治”“禮法”“德治”“經濟法”“判例法”“條例”“令”“成案”“習慣法”“平民法”等,有些是概念混淆不清,一詞多義;有些是借用現代法學術語表述古代概念時,內涵與外延不一;有些是用古代前期的法律術語和學術觀點,推論、描述中后期法制,而忽視了中國歷史上法律術語及其內涵也在發展變化;有些則是未閱讀基本史料,憑想象匆忙下的結論。如此等等,都使我們深深感到,要開拓和正確闡述法律思想史,通過學術討論和爭鳴,去偏存正,形成共識,實現法律術語使用的科學化非常必要。
要實現法律術語使用的科學化,首先需要確定為學界公認的、大家共同遵循的學術概念界定原則。我以為,“古代法史研究中使用學術概念有必要堅持兩個原則:一是凡是今人能夠讀懂的古代法律術語,最好仍使用古人的法言法語,不必用西方現代法律用語替代;二是如果有些法律現象、法律問題的概括只能借用現代法律術語才能表達清楚,使用現代法律術語表述時,概念的內涵、外延應完全一致”。〔41〕楊一凡:《質疑成說,重述法史》,載楊一凡、陳靈海主編:《重述中國法律史》(第1 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9 年版,第13-14 頁。
其二,準確區分古代法律思想的精華與糟粕 。重述中國法律思想史,是對古代的法律觀點、理論、學說的系統梳理和總結。從總體上看,古代的法律思想是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法律制度相適應的。從現代法學的觀點看,是精華與糟粕并存。中國歷史上法律思想的許多優良成分,比如,重視法律在治國中作用的“以法治國”“明法申令”思想;“審勢立法”“變法改革”思想;法制“以民為本”“令順民心”“法信于民”思想;“法律劃一”“法貴簡當、穩定”思想;立法“法貴中道”“情法適中”“寬嚴適中”思想;注重道德教化的“先教后刑”“教法兼行”思想;“去嚴法苛刑”、反對重刑的思想;“正身守法”“明正賞罰”思想;“扶弱抑強”“輕徭薄賦”思想;“罪刑法定”“刑無等級”“詳審刑獄,糾正冤案”“公正執法”“慎殺恤刑”思想;重視民事調解和預防犯罪的思想等,對當代法治建設有重要的借鑒價值,需要我們認真研究、汲取和發揚。然而,古代法律思想畢竟是舊時代的產物,其主導思想是為維護統治者的政權和利益服務的,許多思想理念與現代法治觀念相對立。其“皇權至上,法自君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人治、禮治重于法治”“貴賤有別,良賤異法”“法為防民之具”“重懲愚頑”“族誅連坐”“以法抑商”等及其他旨在維護君主專制、等級特權和愚民、弱民、苦民、殘民的法律思想,都應堅決摒棄。準確區分古代法律思想的精華與糟粕,是重述法律思想史承擔的重大任務。
以往的法史研究,在評價古代法制和法律文化時,曾出現過兩種偏頗。一種是以現代法學理念和評價標準為坐標,全面否定傳統法律文化,把古代法制和法律思想描繪得漆黑一團;一種是挖掘傳統法律文化的優良成分時,只講精華不講糟粕。這兩種傾向都偏離了實事求是的認識論,不可能客觀反映歷史的真實。因此,研究中國法律思想史,必須摒棄實用主義和形而上學的研究方法,堅持批判、吸收的態度,準確區分其“精華”與“糟粕”。論述歷史上各種學派和不同歷史時期的法律思想,對其形成的背景、內容及產生的積極或消極作用,都應當恰如其分地分析評判。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總結古代法制建設的經驗和挖掘古人法律思想的精華古為今用,法律思想史研究才更具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五、結語
重述中國法律思想史,是法史學人自覺進行的學科革命,其學術目標是重建學科的科學體系,全面正確地闡述中國法律思想發展史。解放思想是實現學術大飛躍的前提。只有破除“以刑為主”“法律儒家化”論的束縛,修正誤導后人的成說,才能夠為“重述”鋪平前行的道路。
重述中國法律思想史,是從事法律制度史、法律思想史兩個專業研究方面的學者共同肩負的使命。離開法制變革無法深入挖掘法律思想,形成的成果也蒼白無力。離開法律思想去研究法律制度,便無法揭示法制變革的深刻內在動因和指導思想,形成的成果只能是材料的堆砌,轉化不成傳世的精神財富。只有把法律思想與法律制度結合研究,并正確地區分古代法制和法文化的精華與糟粕,法律史學才能真正成為科學。
重述中國法律思想史,也是法史學人研究思維和方法的自我改造。套用先秦諸子學術觀點,或不加分析地以儒家經學、禮治思想概括后代發展變化的法律思想,難成信史;無視史實,望文生義,套用西方現代法學術語表述中國古代法律思想,這種貼標簽式的理論創新,只能是誤判疊出,禍及學林。法律思想的產生和發展,源于法制變革和法律實踐,只有尊重歷史,注重史料,堅持“論從史出”,在扎實研究基礎上的創新理論,才能推動法律史學走向科學。
重述中國法律思想史,是長期艱辛的探索。本文所述,系一家之言,寫作的初衷是拋磚引玉。法律思想研究中的許多重大疑義或爭論問題,需要反復地探索、爭鳴才可能達成共識。我相信,學科將在探索中不斷成熟、完善,只要學界同仁不懈努力,重述中國法律思想史的學術目標就必定能夠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