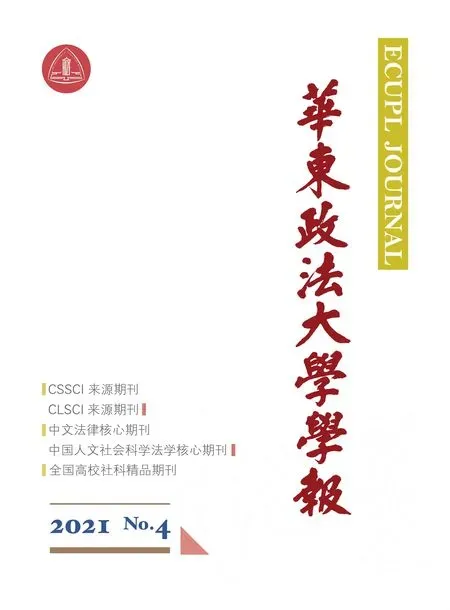名廢實存:元代格例法體系與中華法系之真實關系
宋國華
法律史學界一般從兩個角度研究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一是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角度,如秦有律、令、式、程、課、法律答問等;漢有律、令、科、比等;唐有律、令、格、式等;二是從法律內容角度研究,法律體系是由行政法、民事法、經濟法、刑事法、軍事法等共同構成的。其實,兩個角度是緊密關聯的。法律內容是以法律形式為載體的,或者說某一法律形式的功能決定了某一方面的內容。如行政方面的內容,在唐代主要以“令”“格”等法律形式規定,而有關犯罪和刑罰的刑事法則主要由“律”這種法律形式來規定。法律形式和法律內容相比較而言,法律形式及其所表述的立法成果是法律體系的基本要素,〔1〕參見楊一凡:《重新認識中國法律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版,第19 頁。故談到古代法律體系,學界首先從法律形式的角度論述。本文亦同。
學者對用“律令法體系”這一概念來分析中國古代法制史是沒有異議的。但對律令法體系適用的時期持不同觀點。劉廣安先生認為,律令法體系這一概括性說法,只適用于秦漢至唐宋時期的法律體系,不適用于先秦時的法律體系,也不適用于元明清時期的法律體系;〔2〕參見劉廣安:《令在中國古代的作用》,載《中外法學》2012 年第2 期。劉篤才先生認為,律令法體系只是在中國古代社會前期與中期存在,后期經歷了一系列的嬗變,其結果是被律例法體系所取代。律例法體系的歷史時段,至少包括明清兩代。〔3〕參見劉篤才:《律令法體系向律例法體系的轉換》,載《法學研究》2012 年第6 期。我們知道,宋依然是律令法體系,那么由律令法體系轉換為律例法體系,居于宋明之間的元代法律體系應該如何定位?日本學者石岡浩等在《史料所見中國法史》一書中認為,律令法體系完成于唐前半期,此后逐漸演變,至明清時形成律例法體系。演變過程中,元代地位如何,并未明言,僅把遼到元的法作為“征服王朝的法”加以介紹。〔4〕參見[日]石岡浩等:《史料からみる中國法史》,法律文化社2012 年版,第23-34 頁。楊一凡先生認為,元朝是中國古代從律令為主的法律體系向律例為主的法律體系過渡的時期。〔5〕參見楊一凡:《重新認識中國法律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版,第23 頁。近來,楊一凡先生對明代“律例法體系”做了修正,認為明代法律體系是按照“以典為綱、以例為目”的框架構建的,應總稱或簡稱為“典例法律體系”。(參見氏著:《明代典例法律體系的確立與令的變遷》,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7 年第1 期);陳靈海教授認為,清代的法律體系是“典例”法律體系,“律例”體系只是“典例”體系中的刑法部分,不足以全面概括清代法律體系的特征。(參見氏著:《〈大清會典〉與清代“典例”法律體系》,載《中外法學》2017 年第2 期。)樓勁先生認為,唐代的《律》《令》《格》《式》體系,形成于唐開元年間,但到中唐,此種法律體系開始瓦解,到宋神宗時確定了敕、令、格、式并行的法律體系,經過元代分部門或事類編纂各種敕例以為條法和條格的過渡,到明清形成了《律》《例》體制。〔6〕參見樓勁:《魏晉南北朝隋唐立法與法律體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版,第658 頁。臺灣學者李如鈞在《評趙晶〈天圣令與唐宋法制考論〉》一文中,期待趙晶未來回應的問題是:令典在元代以后的衰微,以及律例法在明清的興起,是否實因元代自身所致?而宋代對后世法律形式的影響,是否似學者所言如此之大?〔7〕參見李如鈞:《評趙晶〈天圣令與唐宋法制考論〉》,載《中國史研究動態》2015 年第2 期。這說明元代法律形式及其法律體系,在律令法體系“嬗變”過程中作用如何,引起了學者的關注。但是,這些學者的論述有的在《至正條格》〔8〕2002 年,元代后期編纂的法律文獻《至正條格》殘本在韓國被意外發現。《至正條格》以條格命名,但其包含“條格”和“斷例”兩部分。其中,“斷例”的篇目、條文及其形態是首次發現。發現之前,有的雖在《至正條格》發現之后,但對于其中的“斷例”部分并未予以足夠的關注,因此,囿于史料,其觀點有值得商榷之處。筆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利用新發現的史料,就元代的法律體系及其與律令法體系和格例法體系的關系做初步探討。
一、格例法體系之提出
元朝法律體系的研究一直是學界研究的薄弱之處。2007 年,李玉年先生撰文指出,唐代的法律體系是律、令、格、式,宋代的法律體系是敕、律、令、格、式,而元代的法律體系至今不明。李玉年先生在對元代法律組成解析的基礎上,構建了元代的法律體系,即:元代法律是由以大札撒為核心的蒙古法和為了滿足統治的需要而制定的條格組成的,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法律體系,即札撒、條格。又因條格具有綜合性,在條格內形成了亞系,即條格(狹義) 、斷例和制詔。〔9〕參見李玉年:《元代法律體系之構建——元代法律組成解析》,載《安徽史學》2007 年第3 期。
李氏這種法律體系的構建,的確有利于掌握元代法律的全貌及其特征,也有利于掌握各種法律間的關系。但可商榷之處有二。一是與札撒并列的“條格”,李玉年認為是廣義的“條格”。“條格的發展路徑是由條畫到狹義條格再到廣義條格,外延不斷增大,最后指所有元代立法。”李氏認為,最遲到修纂《至正條格》時狹義條格變成了廣義的條格。那么,用元朝后期廣義的條格來分析整個元代的法律體系則有不妥。二是札撒是以大札撒為核心的蒙古法。李氏將其納入法律體系主要是其“決定了國家政治面貌,是元代地位最高之法”。這是從法律效力等級而言的。條格在效力上低于札撒,是對札撒的補充。這樣,從法律效力等級的角度研究元代法律體系,〔10〕胡興東亦認為,這可能混淆了法律形式與法律效力位階兩種分類體系。參見胡興東:《元代法律史研究幾個重要問題評析(2000—2011)》,載《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4 期。與目前學者研究中國古代的法律體系的角度是不一致的。我們可否將元代法律體系的研究置于同一語境中研究。
其實,研究整個元代的法律體系是十分困難的,或者說無法對其準確概括。因為元朝歷史通常分為蒙古帝國、元朝與北元等三個時期。這三個時期的法律相差甚遠,蒙古帝國時主要是其習慣法。即使嚴格意義的元朝時期,〔11〕元世祖忽必烈定都漢地,將國號改為大元后,直到1368 年元惠宗出亡為止,共九十八年。其法律淵源也是大有不同,開始沿用金《泰和律》,直至英宗至治三年才頒行《大元通制》。〔12〕關于元初的法制狀況,參見姚大力:《論元朝刑法體系的形成》,載氏著:《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279-321 頁。而法律體系是指一定時期內的法律形成的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所以,研究元代的法律體系可研究元朝的主要時期,即嚴格意義上的元朝時期。
學界在研究元之前朝代的法律時,通常用“律令法”“律令制”等詞語。〔13〕如呂志興《宋令的變化與律令法體系的完備》,載《當代法學》2012 年第2期;張忠煒《秦漢律令法系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鄭顯文:《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張建國將律令法體系定義為:“以律令為主體、包括眾多的法形式和內容的法律體系。”〔14〕參見張建國:《中國律令法體系概論》,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 年第5期。劉篤才在研究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時,提出了“律令法體系向律例法體系的轉換”的觀點,并比照律令法體系的定義方式,將“律例法體系”定義為:“以律、例為主體而包括眾多法形式的法律體系。”〔15〕劉篤才:《律令法體系向律例法體系的轉換》,載《法學研究》2012 第6 期。作為中國古代從律令為主的法律體系向律例為主的法律體系過渡時期的元朝,其法律體系是怎樣的呢?筆者以為,從法律形式的角度來研究,可將元代的法律體系稱為“格例法體系”。〔16〕需要說明的是,王敬松先生著眼于元代法典的體例,指出了“格例體”。其認為,從法律編制體系上說,《至元新格》《大元通制》《至正條格》三部法律,都屬于格例體的法律。(王敬松:《論元代法律中沒有“十惡”體系》,載《民族研究》2013 年第5 期。)筆者則是從法律形式的角度提出元代的“格例法體系”。
“格例”一詞,最初出現于唐、五代時期,延續至宋元。唐、五代時期,格例有三方面的用法:一是一般性的法律規定;〔17〕這方面的例子如:《通典》卷十一《食貨一》載:“其商賈,準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于敕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并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唐大詔令集》卷二《中宗即位赦》云:“其應支兵,先取當土及側近人,仍隨地配割,分州定數,年滿差替,各出本州,永為格例,不得踰越。”二是指在行政過程中產生的,主要用于官吏的選舉和管理方面,大多數情形下,格例是為了保障“格”的實施而制定的,是政府部門根據格制定出來的一種區分等級次第的細則;〔18〕參見楊一凡、劉篤才:《歷代例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版,第84 頁。三是在某些場合也是格和例的合稱。〔19〕參見楊一凡、劉篤才:《歷代例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版,第84 頁。對于第二個方面,李云龍提出質疑,認為“格例是由格發展而來的,其間經過了自發地依照格所確立的規則的過渡階段,最終發展為有意識地制定以格例為名的,主要適用于官員的舉選、遷轉、管理和任用方面的規則體系”。〔20〕參見李云龍:《宋例研究》,上海師范大學2014 年碩士學位論文。
到了元代,格例大多數情形下是元代法律的總稱。如《元史?英宗本紀》云:“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條,內斷例七百一十七、條格千一百五十一、詔敕九十四、令類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21〕(明)宋濂:《元史》卷二八《英宗本紀二》,中華書局1976 年版,第629 頁。此處“格例”是斷例、條格、詔敕、令類的總稱。〔22〕有學者認為,《元史》稱“格例”,是因為《大元通制》雖分為四部分,但主體是條格、斷例。參見王敬松《論元代法律中沒有“十惡”體系》,載《民族研究》2013 年第5 期。《元史?武宗本紀二》載,尚書省臣言:“國家地廣民眾,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后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千余條,刪除繁冗,使歸于一,編為定制。”顯然,此處“格例”也是法律的總稱,主要包括“所行政令”。元代類書《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23〕關于此類書詳細介紹,參見仝建平:《〈翰墨全書〉輯錄的元史資料價值述論》,載《甘肅聯合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 期。卷二《喪禮門》記載了元代的“喪葬格例”,總名稱為“國朝頒降喪葬格例綱目”,下面有11 條內容。這11 條均可在《元典章》中找到相應史料。從在《元典章》的位置來看,1 條出自卷十《吏部?職制一?赴任》,8 條出自卷三十《禮部?禮制三》,2 條出自卷五十《刑部?諸盜二》。出自《吏部》和《禮部》的資料,都是沒規定處罰的,只是“禁治”,但出自《刑部》的資料,是規定定罪量刑的。這樣看來,《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中此處的“格例”也是法律的總稱。換言之,將關于喪葬的法律規定匯集,置于此處。元人徐元瑞在《吏學指南》中言“吏員三尚”,即尚廉、尚勤、尚能。“尚能”:“謂練習格例,曉暢行移,是非曲直,先以意決,然后取裁,凡所處畫,悉令合宜,文義略通,字無不識,寫染端正,算術精明,舉止安詳,語言辯利,無過可尋,有委可辦。”〔24〕(元)徐元瑞:《吏學指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135 頁。此處尚能的具體要求之一“練習格例”,也就是“練習法律”之意。諸多史料可證,“格例”是元代法律的總稱。
除了“格例”可作為元代法律總稱外,“條格”有時也指元代所有法律。學者認為,條格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如日本京都大學金文京教授認為:“當時條格一詞可能有廣狹兩義,狹義的條格是針對斷例而言,是嚴格的涵義;廣義則為條格、斷例的統稱,雖不確切,但是廣為流用的通俗用法。《事林廣記》所反映的就是這種通俗日用的世界。《至正條格》雖包括斷例,仍稱為《至正條格》也當為廣義、通俗的用法。”〔25〕參見[韓]金文京:《有關慶州發現元刊本至正條格的若干問題》,載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編:《至正條格(校注本)》,韓國城南影印元刊本2007 年版,第477 頁。黃時鑒、方齡貴以及日本學者安部健夫、宮崎市定等認為狹義條格是以令法規為主,并包含其他若干格、式法規。廣義條格則由狹義條格、斷例、制詔三部分組成。〔26〕參見黃時鑒:《〈大元通制〉考辨》,載《中國社會科學》1987 年第 2 期;(日)安部健夫:《〈大元通制〉 解說——兼介紹新刊本〈通制條格〉》,載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3 卷),《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宋遼西夏元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版;(日)宮崎市定:《宋元時期的法制與審判機構——〈元典章〉的時代背景及社會背景》,載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3 卷),《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宋遼西夏元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版。
學者對元代“條格”何時有了廣義,則意見不一。李玉年認為,條格的發展路徑是由條畫到狹義條格再到廣義條格,最遲到了修纂《至正條格》時,由狹義條格轉變為廣義條格。〔27〕參見李玉年:《元代法律體系之構建》,載《安徽史學》2007 年第3 期。修纂《至正條格》時,“條格”是元代法律的總稱,應無疑。《至正條格序》記載,(后)至元四年戊寅三月二十六日,“中書省臣言:《大元通制》為書,纘集于延祐之乙卯,頒行于至治之癸未,距今二十余年。朝廷續降詔條,法司續議格例,歲月就久,簡牘滋繁。因革靡常,前后衡決,有司無所質正,往復稽留,奸吏舞文,臺臣屢以為言,請擇老成耆舊文學法理之臣,重新刪定為宜。上乃敕中書專官典治其事,遴選樞府、憲臺、大宗正、翰林集賢等官明章程習典故者,遍閱故府所藏新舊條格,雜議而圜聽之,參酌比較,增損去存,務當其可。書成,為制詔百有五十,條格千有七百,斷例千五十有九。至正五年冬十一月十有四日,右丞相阿魯圖、左丞相別里怯不花、平章政事鐵穆爾達識、鞏卜班、納麟、伯顏、右丞相搠思監、參知政事朵兒職班等入奏,請賜其名曰《至正條格》。”上曰可。〔28〕(元)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七《至正條格序》,《四部最刊》影印明成化刊本。從中可看出,故府所藏新舊“條格”當包括編《至正條格》之前朝廷降詔條、法司所議格例。或許正是《至正條格》的取名,明人議起元代法律時,以“條格”稱之。如《明史》云:“元制,取所行一時之例為條格而巳。”〔29〕(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九三《刑法志一》,中華書局1974 年版,第2279 頁。“惟元以一時行事為條格。”〔30〕(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一三八《周禎傳》,中華書局1974 年版,第3967 頁。但是,根據史料,早些時候,“條格”也有廣義。如大德十一年(1307 年)十二月,中書省臣:“律令者治國之急務,當以時損益。世祖嘗有旨,金《泰和律》勿用,令老臣通法律者參酌古今,從新定制,至今尚未行。臣等謂律令重事,未可輕議,請自世祖即位以來所行條格,校讎歸一,遵而行之。”制可。〔31〕(明)宋濂:《元史》卷二二《武宗本紀一》,中華書局1976 年版,第492 頁。此處“條格”應指世祖即位以來所行的“條格”“格例”等。
筆者以為廣義上的“條格”,其“格”已與唐宋所謂的作為法律形式的“格”不同,此處是“法”的意思。〔32〕法律術語的具體含義,與當時的歷史背景是分不開的,這就決定了同一術語有多重含義。在分析其具體含義時,需要據其語境來考察。元代立國之初,沒有制定統一的法典。其同一術語往往語義不定,似此似彼,不易識判。其實,用“格”稱“法”在漢代就已存在。如漢《律》中有“廢格”之罪,“格”便是“法”之意。又如《禮記?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也。”鄭注:“格,舊法也。”魏晉時期,格和法常常互用并舉,如《魏書》卷七八《張普惠傳》:“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為世減之法。”就元代來說,廣義的“條格”也就是“條法”之意,是元代法律的總稱。由此可聯系南宋的《慶元條法事類》。《慶元條法事類》是把一百二十二卷《慶元敕令格式》和十二卷《申明》,隨事分門別類,重新組合而成,其組成部分敕、令、格、式都是“法”,故稱“條法”。《至正條格》編纂的技術也是“類集”,即將多條條文按其類別編纂,將“條格”理解為“條法”,是對各類法規的泛稱,也未嘗不可。
“條格”和“格例”二詞均有元代法律總稱之意,但前者有廣狹二義,用之來概括元代法律體系,區分性不強,故筆者選取“格例”一詞。〔33〕還有一個方面的原因是,“律令法體系”命名的原因,是律和令主要的兩種法律形式,“律例法體系”命名的原因是,律和例是明清的兩種主要法律形式,元代“條格”和“斷例”是兩種主要法律形式。
二、格例法體系之構成
在元代“格例法體系”中,其法律形式包括哪些呢?有學者將元初大量存在的“條畫”納入研究的視野,認為“條畫”也是元代的法律形式之一。如吳海航認為,條畫與斷例是元代法律體系內不同的法律形式;〔34〕參見吳海航:《中國傳統法制的嬗遞——元代條畫與斷例》,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 年版,第11 頁。魏曉欣認為,條畫是一種獨立的法律形式,它每一次出現都和“圣旨”“諸王共議”“尚書省奏準”“中書省奏準”等聯系在一起,與一般的旨奏條文不同。〔35〕參見魏曉欣:《蒙元〈條畫五章〉考論》,載《上饒師范學院學報》2008 年第2 期。此處對元代法律形式的不同理解,是由于對“條畫”的含義、“條畫”與“條格”的關系以及“條畫”與“斷例”的關系理解不同。
“條畫”一詞,在唐代已經出現。唐代李翱《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墓志》:“我將死,凡家事細大,皆有條畫在文字矣。”〔36〕(唐)李翱:《李文公集》卷十五《墓志六首》,《四部最刊》影印明成化刊本。此處“條畫”含有“規定”“條規”之意。《辭源》 解釋“條畫”為“分條規劃”之意。但如果將“條畫”分開來看,“條”可指“條文”或“條制”,“畫”則是“畫一”之意。
“畫一”與法律有關的記載與漢蕭何有關,《漢書》載“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此后,“畫一”常常用來指法律的作用。如《南齊書》“可明為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之語。
有元一代,“條畫”最早出現于成吉思汗頒行的《條畫五章》。《元史?郭寶玉傳》:“木華黎軍忽至,敗其兵三十余萬。思忠等走。寶玉舉軍降。木華黎引見太祖,問取中原之策。寶玉對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又言:‘建國之初,宜頒新令。’帝從之。于是頒條畫五章,如出軍不得妄殺,刑獄惟重罪處死,其余雜犯量情笞決;軍戶、蒙古、色目人每丁起一軍,漢人有田四頃、人三丁者簽一軍;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戶與軍戶同。民匠限地一頃。僧道無益于國,有損于民者,悉行禁止之類,皆寶玉所陳也。”
此處的“條畫”是名詞性的用法,這五章的內容,《元史》僅是舉例言之,而且從其文字風格上來說,是概述《條畫五章》的內容,故其本來是詔書的形式還是法條的形式不能做出判斷。雖然這是“新令”,但此處“令”并非唐宋時期的法律形式角度上所言的“令”,應理解為法律的總稱。但頒布條畫目的是“畫一”,應是沒有疑義的。此時元代并未統一,所以不能以律、令形式出現,更不可能制定替代前朝的律、令,只能采用過渡性的、權宜性法律。《條畫五章》是朝代更替之間的產物,滿足成吉思汗保證攻取中原的制度需要。這是成吉思汗一代頒布有系統的法令條畫唯一明文記載。這一次的條畫頒布是蒙古勢力南下,與漢文化接觸后,蒙元法律漢化的起點。〔37〕參見翁獨健:《蒙元時代的法典編纂》,載彭衛等編:《中國古代史卷(中冊)》,蘭州大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548 頁。
吳海航高度評價了《條畫五章》,其“在元代條畫立法史上開啟了一個里程碑式的階段”,使得“條畫”類特別立法與蒙元時代相始終,“成為元代后世特別立法的仿效標準”。〔38〕吳海航:《中國傳統法制的嬗遞——元代條畫與斷例》,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 年版,第5 頁。確實,在《元典章》《通制條格》《至正條格》 等元代文獻中,“條畫”一詞頻頻出現。如2002 年發現的元代后期編纂的法典《至正條格》(殘本)直接出現19 次,其中“條格”篇9 次,“斷例”篇10 次。可以推測,完整的《至正條格》中出現的次數肯定更多。另外,含“圣旨”“圣旨內一款”“圣旨節該”“奉圣旨”“詔書內一款”等用語的,也是屬于條畫。
“條畫”既出現在“條格”中,也出現于“斷例”中,這說明,不能簡單地將“條畫”與“條格”“斷例”并列。它們之間的關系,研究的角度不同,關系則不一樣。我們可從立法的角度和法典編纂的角度理解。
(一)立法的角度
元人如何理解,我們可從元人沈仲緯對“條畫”的理解窺其一二。宋太祖建隆四年(963 年)頒行《宋刑統》,宋代律學博士傅霖認為《宋刑統》不便閱讀和記憶,便將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韻文體裁撰為律學讀本《刑統賦》。
元人沈仲緯作《刑統賦疏》,“取傅氏賦文而為之疏,引據詳析,疏后有直解,概括易曉。解后有通例,則取當時罪案,斷例以為佐驗。意主戒儆,非泛作刑書也”。〔39〕《刑統賦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載《枕碧樓叢書》,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所整理標點,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 年版,第169 頁。楊維楨作序,言沈氏“以本朝律款會而通之,辯取其要,無不中隙”。〔40〕《刑統賦疏》“沈氏《刑統賦》序”,載《枕碧樓叢書》,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所整理標點,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 年版,第169 頁。沈仲緯在疏解“制不必備也,立例以為總”時,云:“制者,詔旨條畫之文;例者,為格為例之事。”〔41〕《刑統賦疏》,載《枕碧樓叢書》,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所整理標點,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 年版,第198 頁。顯然,沈氏用元朝的“詔旨條畫”“格”“例”來解釋宋代的“制”和“例”。“制”,是指天子的命令,在元代則用“詔旨”來稱謂。“詔”即“詔書”,“旨”即“圣旨”。
在元代,詔書和圣旨是有區別的。元朝官修政書《經世大典》云:“國朝以國語訓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詔書。”〔42〕(元)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卷四十《經世大典序錄?帝制》,《四部最刊》影印元至正刊本。可以看出,詔書和圣旨的區別在于,圣旨以蒙古文記錄皇帝的命令,詔書則由“史臣”用漢文代言。就其內容而言,圣旨多系因特定目的而頒與某一特定機構或人物,詔書內容所涉則多為較具普遍性的國家政策或重要事件。〔43〕關于詔書和圣旨詳細論述,參見張帆:《元代詔敕制度研究》,載《國學研究》(第10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條畫則是附在詔書或圣旨后的個別條款。可見,“條畫”一語,是與皇帝命令緊密相關的。日本學者植松正將元代條畫分為四大類,即詔書、詔敕、設立官府的圣旨條畫、特定部門的圣旨條畫,〔44〕參見[日]植松正:《元代條畫考》,《日本香川大學教育學部研究報告》1-46,1979 年。也是以條畫是皇帝的命令為基礎分類的。
元代“條畫”與“格”“例”的關系,同樣可借助宋代“制”和“例”的關系理解。沈仲緯言:“制者,詔旨條畫之文;例者,為格為例之事。蓋律有例條有制,不知例無以見法之所同,不知制無以見法之所異”。“律有條例有制,不備細,止該大節,俱在《名例》卷內,以為總要,自有各斷例生于諸條,以總其事。故制不必備,止立例而已。”〔45〕《刑統賦疏》,載《枕碧樓叢書》,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所整理標點,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 年版,第198 頁。在沈仲緯看來,元代詔旨條畫,相當于宋的“制”,是“止該大節”,元代的“為例為格之事”則相當于宋代的“立例”,但“為例為格”時,要以“詔旨條畫”為總要。“為格”的例子,如《至正條格?條格》卷第二十七《賦役?孝子節婦免役》“至元十年二月”條:〔46〕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編:《至正條格(校注本)》,韓國城南影印元刊本2007 年版,第86 頁。
至元十年二月,御史臺呈:“欽奉圣旨內一款:‘孤老幼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仰本路官司驗實,官為養濟,應收養而不收養,或不如法者,委監察糾察。’欽此。體察得,大都路左警巡院咸寧坊魏阿張,年一十六歲,適魏明子蔓。其夫荒縱,不事家業,因欠債銀,逃竄不知所往。阿張父代還所欠,本婦與姑同居,傭計孝養,甘旨不闕。十余年后,其夫還家,因病身故,并無產業,有子幼弱,其姑九十五歲,眼昏且病,不能行止,依舊孝養。遇有事出,置姑扃戶,將子寄于鄰居學舍。參詳魏阿張孝奉老姑,守節不嫁,欽依圣旨事意,官為養濟。仍令免除差役,更加旌表,以〈礪〉[勵]風俗。”都省準擬。
根據圣旨,官府養濟“孤老幼疾貧窮不能自存者”,御史臺履行“糾察”之職,在實踐中發現魏阿張孝奉老姑,守節不嫁,便提出立格建議,除了官為養濟外,對孝子免除差役,更加旌表,得到中書省批準。
“為例”的例子。如《至正條格?斷例》卷第四《職制?親故營進》“至元二十一年五月”條:〔47〕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編:《至正條格(校注本)》,韓國城南影印元刊本2007 年版,第202 頁。
至元二十一年五月,御史臺呈:“照得,圣旨條畫內一款:‘諸求仕訴訟人,若于應管公事官員私第謁托者,委監察糾察。’又一款:‘諸官府如書呈往來者,委監察糾察。’欽此。近年以來,內外憲臺按察司官吏,將親戚并營求勾當人,于各路總管府及諸衙門,囑托安插,作酒稅務課程等勾當。或轉托他人,宛轉分付。總管府等處官司,素畏風憲官吏,凡所囑托,必須安排優便。其人恃賴按察司官吏,恣行非理,實今大弊。江南諸道,此弊尤多,若不懲治,益長貪濁。今后諸憲臺提刑按察司官吏,若將親戚及營求勾當人,于各路總管府諸衙門,囑托安插,及轉托他人,情弊亦〈司〉[同]。如有首告,或體訪得知,取問是實,以故違圣旨論,聞奏斷罷。”都省準呈。
此斷例,是御史臺根據兩款圣旨條畫,對憲臺提刑按察司官吏“將親戚及營求勾當人,于各路總管府諸衙門,囑托安插,及轉托他人”的行為做出具體處罰,然后呈送中書省。從以上可以看出,在制定法律時,“條畫”是“格”“例”的總要。
(二)法典編纂的角度
元朝在其存續期間,制定了法令,編纂了法典。〔48〕詳細的論述參見翁獨健:《蒙元時代的法典編纂》,載彭衛等編:《中國古代史卷(中冊)》,蘭州大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546-565 頁;劉曉:《〈大元通制〉到〈至正條格〉:論元代法典的編纂》,載《文史哲》2012 年第1 期。但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其受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影響的同時還吸收了中原傳統文化,因而其法令的制定及法典的編纂不同于唐宋。元代沒有唐宋律令法體系下的律典和令典。一般認為,《大元通制》和《至正條格》是元代頒布的兩部法典。
《大元通制》 頒布于英宗至治三年(1323 年)二月。從立法技術的角度看,其編撰的原則為“類集”。孛術魯翀《大元通制序》:“由開創以來政制法程可著為令者,類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宏綱有三:曰制詔,曰條格,曰斷例。經緯乎格例之間,非外遠職守所急,亦匯集之,名曰別類。”〔49〕(元)孛術魯翀:《大元通制序》,載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卷三十六《序》,《四部最刊》影印元至正刊本。沈仲緯在《刑統賦疏》中疏解《刑統賦》“撮諸條之機要,觸類周知”時云:“類,事類也。”并征引元代有關法律:“斷例,即唐律十二篇名。名令〔50〕此處“名令”是“名例”之誤。提出,獄官入條格,〔51〕學者對此文做了較多的研究,但尚未涉及“名例”提出的原因。筆者以為,這與《大元通制》的結構有關。《大元通制》包括制詔、條格、斷例三部分。沈仲緯在疏解《刑統賦》中“制不必備也,立例以為總”時認為,元代的詔書圣旨條畫相當于宋的“制”,元代的“格”“例”相當于宋的“例”。此處宋“例”指的是《宋刑統》中“名例”律以下的篇章。沈仲緯在疏解“竊原著而有定者,律之文,變而不窮者,法之意”時,“舉律內七殺之事明之”。其云:“殺人者斬,此是一定之律文,若執守其文,但殺人者皆處斬刑,則又不可。蓋殺人之情,輕重不同,故例有七色,是名七殺。”接著引用《賊盜律》《斗訟律》《賊盜律》《斗訟律》《斗訟律》《斗訟律》《斗訟律》分別解釋謀殺、故殺、劫殺、斗殺、誤殺、戲殺、過失殺。顯然“例有七色”中的“例”指的是《名例律》以下的篇章。《名例律》是以下各篇的總要。元人認為,既然制詔是制定條格、斷例時之總,那么,在制詔存于法典時,與其相同作用的在古律中稱為“名例”的部分,就無存在必要。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 《大元通制》中“條格”部分,其“類”,根據沈仲緯的征引為:祭祀、戶令、學令、選舉、宮衛、軍防、儀制、衣服、公式、祿令、倉庫、廄牧、關市、捕亡、賞令、醫藥、田令、賦役、假寧、獄官、雜令、僧道、營繕、河防、服制、站赤、榷貨。〔52〕《刑統賦疏》,載《枕碧樓叢書》,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標點,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 年版,第172 頁。
吳澄《大元通制條例綱目后序》云:“制詔、條格,猶昔之敕令格式也。斷例之目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斗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一循古律篇題之次第而類輯,古律之必當從,雖欲違之而莫能違也。”〔53〕(元)吳澄:《大元通制條例綱目后序》,載《吳文正集》卷十九,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吳澄此段話涉及《大元通制》的三個組成部分。斷例的篇目容易理解,制詔、條格兩部分的性質,吳澄用“昔之敕令格式也”來類比。關于此句的含義,日本學者安部健夫認為,“猶昔之敕”之語,“其所指雖然頗顯含混,但它應理解為《制詔》《條格》具有‘敕’的性質”。〔54〕參見(日)安部健夫:《〈大元通制〉 解說——兼介紹新刊本〈通制條格〉》,載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3卷),《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宋遼西夏元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版。筆者以為,此種理解可以商榷。應理解為,制詔相當于敕,條格相當于令格式,理由有三。其一,按安部健夫的思路,《制詔》《條格》具有“敕”的性質,那么,《制詔》《條格》也具有令、格、式的性質,顯然這是講不通的。其二,現存《通制條格》和《至正條格》中的“條格”,除了與皇帝詔書有關的“欽奉詔書內一款”“欽奉圣旨條畫內一款”等條文外,還有與皇帝無關的省部擬定的條款,這些條文則不具備“敕”的性質。其三,《大元通制》 和《至正條格》 中“制詔”的作用。《元史?英宗本紀》 云:“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條,內斷例七百一十七、條格千一百五十一、詔敕九十四、令類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55〕(明)宋濂:《元史》卷二八《英宗本紀二》,中華書局1976 年版,第629 頁。此處記載,《大元通制》成書之后,頒行天下,從字面意思來看,應包括其中的“詔敕九十四”。元代后期在《大元通制》基礎上編纂了《至正條格》。《元史》對《至正條格》的編纂情況記載較為簡單,但歐陽玄《至正條格序》對《至正條格》編纂的記載較為詳細。就筆者所見,研究者大多注意了該序的前半部分。但對書名定為《至正條格》后群臣復議的內容尚未關注。群臣議曰:“制詔,國之典常,尊而閣之,禮也……條格、斷例,有司奉行之事也……請以制詔三本,一置宣文閣,以備圣覽,一留中書,藏國史院,條格、斷例,申命鋟梓示萬方。”結果,“上是其議”。〔56〕(元)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七《至正條格序》,《四部最刊》影印明成化刊本。可以看出,《至正條格》中的“制詔”部分,并未頒行,主要原因,一是制詔是“國之典常”,在國家管理中,“條格”和“斷例”就已足夠;二是,上文所論述的制詔是制定“條格”“斷例”之總;三是,下文所論,制定編纂《至正條格》時,將“制詔”中內容根據其有無罰則分別編入“條格”或“斷例”之中。
將“制詔、條格,猶昔之敕令格式也”,理解為“制詔相當于敕,條格相當于令格式”,就與唐代的法律形式有了很好的對應:元代的“制詔”對應于唐代的“敕”;元代的“條格”對應于唐代的“令、格、式”;元代的“斷例”對應于唐代的“律”。“令、格、式”在功能上雖不一致,但其在有無懲罰性內容上則是一致的,即無懲罰性的規定。我們知道唐宋律典從性質上而言是刑事法,帶有懲罰性的規定。元代編纂《大元通制》和《至正條格》時,均采取類集的方法,將詔書、圣旨中可以“永為法則”〔57〕此處,筆者借助唐格的編修方法來理解元“條格”的編寫。《舊唐書》卷五十《刑法》:“其曹之常務,但留本司者,別為留司格一卷,蓋編錄當時制敕,永為法則,以為故事。”這是把臨時性的“制敕”編入“格”中,是指具有永久效力。元代編纂法典時也是如此。的條畫以有無懲罰性內容為標準分別歸入條格或斷例的“類”中。〔58〕有學者認為,《至正條格》中,不管是“條格”還是“斷例”的法規都是通過具體判例組成的。(參見胡興東:《中國古代判例法模式研究——以元清兩朝為中心》,載《北方法學》2010 年第1 期。)這種說法似可商榷,除了具體判例之外,還有條畫和中書省等直接制定的條文。
第一,將同一詔書、圣旨中的條畫按其性質功能歸入法典中的不同“條格”篇或“斷例”篇。
如至大四年(1311 年)三月十八日《仁宗皇帝登寶位詔》后所附條畫,植松正先生搜集整理為27條,這27 條在《至正條格》殘卷中有6 條,其中“條格”部分4 條,“斷例”部分2 條。〔59〕劉曉:《〈大元通制〉到〈至正條格〉:論元代的法典編纂體系》,載《文史哲》2012 年第1 期。歸入“條格”部分的4 條如下。
其一,《至正條格?條格》卷第二十六《田令?禁擾農民》“至大四年三月”條:至大四年三月,詔書內一款,節該:“農桑,衣食之本。仰提調官司申明累降條畫,諄切勸課,務要田疇開辟,桑果增盛,乃為實效。諸官豪勢要經過軍馬,及昔寶赤、探馬赤喂養馬駝人等,索取飲食草料,縱放頭疋,食踐田禾桑果者,所在官司斷罪陪償。仍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常切糾察,考其殿最,以憑黜陟。”
其二,《至正條格?條格》卷第二十七《賦役?均當雜泛差役》“至大四年三月”條:至大四年三月,詔書內一款:“民間和雇和買一切雜泛差役,除邊遠軍人,并大都至上都自備首思站戶外,其余各驗丁產,先盡富實,次及下戶。諸投下不以是何戶計,與民一體均當。應有執把除差圣旨、懿旨、令旨,所在官司,就便拘收。”
其三,《至正條格?條格》卷第二十八《關市?禁中寶貨》“至大四年三月”條:至大〔60〕韓國發現《至正條格》本,誤“至正”為“至元”,今改之。四年三月,詔書內一款:“諸人中寶,蠹耗國財。比者,寶合丁、乞兒八答私買所盜內府寶帶,轉入中官,既已伏誅。今后諸人毋得似前中獻,其扎蠻等所受管領中寶圣旨,亦仰追收。”
其四,《至正條格?條格》卷第二十八《關市?和雇和買》“至大四年三月”條:至大四年三月,詔書內一款:“諸王、駙馬經過州郡,從行人員多有非理需索,官吏夤緣為奸,用一鳩百,重困吾民。自今各體朝廷節用愛民之意,一切懲約,毋蹈前非。其和雇和買,驗有物之家,隨即給價。克減欺落者,從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體察究治。”
歸入“斷例”部分的2 條如下。
其一,《至正條格?斷例》卷第六《職制?枉法贓滿追奪》“至大四年三月”條:至大四年三月,詔書內一款,節該:“內外百司,各有攸職。其清慎公勤,政跡昭著,五事備具者,從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察舉,優加遷擢。廢公營私,貪污敗事,陳告得實,依條斷罪。枉法贓滿者,應授宣、敕,并行追奪。吏人犯贓,終身不敘。誣告者,抵罪反坐。”
其二,《至正條格?斷例》 卷第七《戶婚?冒獻地土》“至大四年三月”條:至大四年三月,詔書內一款:“國家租賦有常,僥幸獻地之人,所當懲戒。其劉亦馬罕、小云失不花等冒獻河南地土,已令各還元主,劉亦馬罕長流海南。今后諸陳獻地土并山場、窯冶之人,并行治罪。”
此種方式,首先將同一份詔書中的條畫根據其性質拆分為條格和斷例,然后分別將歸入條格的條畫和歸入斷例的條畫再根據其所涉事項拆分,歸入已有的“篇目”中,或在不便于歸于某一“目”時,另立新目。
第二,將不同詔書、圣旨內條畫按其性質功能歸入法典中的同一“條格”篇或“斷例”篇。如《至正條格?斷例》卷第十二《廄庫》“茶課”條:〔61〕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編:《至正條格(校注本)》,韓國城南影印元刊本2007 年版,第300 頁。
中書省欽奉圣旨,節該:恢辦茶課公事,省部印造到茶引據。〔62〕韓國發現《至正條格》(校注本),“據”從下。根據上下文,點斷時“據”應從上。“引”指“茶引”,“據”指“公據”。客人赴官送納正課,買到興販茶貨引,壹道重玖拾斤。年月日料號,并依坐去條畫事理施行。
客旅興販茶貨,納訖正課,出給公據。前往所指山場,裝發茶貨出山,將元據赴茶司繳納,倒給省部茶引,方許赍引隨茶,諸處驗引發賣畢,限三日以里,將引于所在官司繳納,實時批抹。違限匿而不批納者,杖陸拾。因而轉用,或改抹字號,或增添夾帶斤重,及引不隨茶者,并同私茶法科斷。仍各處官司,將客旅節次納到引目,每月一次,解赴合屬上司繳納。
但犯私茶者,決杖柒拾,將所犯茶貨,壹半沒官,壹半付告人充賞,應捕人亦同。如茶園磨戶犯者,及運茶船主知情夾帶裝載無引私茶,一體科斷。本處官司,禁治不嚴,致有私茶生發去處,仰將本處當該官吏勾斷。
應客旅裝發茶貨車船,各處官司并不得拖拽。若必合和雇,直抵發賣地面下卸訖,方許和雇。如違,陳告得實,決杖陸拾。因而取受故縱者,與同罪。如有邀當客旅、拘買取利者,杖陸拾。茶付本主,買價沒官。
偽造茶引者,處死。首告得實者,犯人家產,并付告人充賞。
客販茶貨,若經由關防批驗官司去處,私過不批引目者,決杖柒拾。隨處官司,常切禁治,不得抑遏客旅,干要牙錢。違者,就便追斷。
客旅所販茶貨,江淮迤南依舊免稅。江淮迤北發賣去處,依例收稅。
此條所載6 款茶引條畫,并無頒行的具體時間,但檢閱《元典章》〔63〕《元典章》,陳高華等點校,中華書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相關史料,可以確定其頒行的年份,現列表如下:
就可確定的五款來看,這些條畫頒行時間不一,但在編纂《至正條格》時都納入“斷例”篇“茶課”條之中。當然,在編入法典中,對以往條畫也有所變動,以第6 款為例試做說明:至元三十年(1293 年)與第6 款相關的茶引文字為:“客旅興販茶貨,隨處發賣,依例投稅。”〔64〕《元典章》,陳高華等點校,中華書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811 頁。依此規定,江南各路府州縣商稅局,也可收茶貨之稅。大德四年(1300 年),榷茶提舉司認為這“當攔客旅,攪擾澀滯茶法,不能通行”,江西榷茶都轉運司提議將“茶貨免稅”,申覆江西等處行省,移咨都省定奪,結果“都省奏準”。戶部便“改鑄板面”,“除去至元三十年(1293 年)茶引內客旅興販茶貨,隨處發賣,依例投稅一款”,添上“客旅所販茶貨,江淮迤南依舊免稅。江淮迤北發賣去處,依例收稅一款”。〔65〕《元典章》,陳高華等點校,中華書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811 頁。
從以上論述可知,無論是立法的角度還是法典編纂的角度,“條畫”不能與“條格”和“斷例”并列,其不能作為一種獨立的法律形式存于格例法體系之中。而“條格”和“斷例”則是根據其有無罰則進行的歸類,這是元代法典的兩個主要組成部分,歐陽玄曰:“條格、 斷例,有司奉行之事也。”〔66〕(元)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七《至正條格序》,《四部最刊》影印明成化刊本。所以,“條格”和“斷例”是元代“格例法”體系中的主要法律形式。〔67〕胡興東認為,元代的法律形式主要包括格和例。例的名目繁多,在元朝達十九種之多。元朝例的基本作用是對法律的解釋和補充。(參見胡興東:《元代“例”考——以〈元典章〉為中心》,載楊一凡主編:《中國古代法律形式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392-415 頁。)胡興東在其《宋元斷例輯考》一書中更加詳細地對各種例進行了考辨。(參見氏著:《宋元斷例輯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年版,第126-143 頁)。筆者以為,其一,元代的這十九種例之一的“斷例”在《大元通制》和《至正條格》中,單獨列出,作為法典的一部分,是有罰則的條文,相當于唐宋的“律”;其二,《至正條格?斷例》篇目有“多支分例”“增起站車分例”“諸奸通例”等直接以“例”為名的條文;《通制條格》中有“戶例”“公糧則例”“衣裝則例”“大小口例”“鷹食分例”“司農事例”“典賣田產事例”“織造料例”等直接以“例”為名的條文,這說明,元人在編纂法典時,已經按照“例”的性質,把“例”歸入“條格”或“斷例”之中。
元代的格例法體系,除了條格和斷例之外,是否還包括其他的法律形式?正如我們研究律令法體系一樣,“律”和“令”只是律令法體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兩種法律形式,漢代除了“律”“令”外,還有“科”“比”等法律形式;唐代除了“律”“令”外,還有“格”“式”等法律形式。吳澄《大元通制條例綱目后序》中以為,唐代的“敕者,時君所裁處;令者,官府之所流布;格式者,各代之所造設也”。〔68〕(元)吳澄:《大元通制條例綱目后序》,載《吳文正集》卷十九,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前文已經論及元代的條格對應于唐代的“令”“格”和“式”,也就是說元代“條格”這種法律形式將唐的“令”“格”“式”這三種法律形式吸納,以“條格”為其名稱。
在《通制條格》和《至正條格》中的“條格”文本中,大部分是類似于唐的“令”文,〔69〕此“類似”并非從語言角度,而是從功能角度而言的。“條格”中的這些文本,與唐令的功能是一致的。當然,令的功能,學界頗為紛雜,但安部健夫認為,“令”大致上是“為了預防觸犯律而作的規定,即對于百姓可能遇到的一般的公事或私事,不論尊卑貴賤,規定其‘為當’或‘聽為’‘不當為’或‘不聽為’的法規”,這是不會大有出入的。(參見[日]安部健夫:《〈大元通制〉解說——兼介紹新刊本〈通制條格〉》,載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 3 卷),《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宋遼西夏元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版。)還有一部分就是“各代之造設”的法規,也就是吳澄所謂具有“格式”性質的法規。如《通制條格》中有部分內容源于《至元新格》。〔70〕具體來說,《通制條格》中源于《至元新格》的條文為:卷六《選舉?選格》方校本141(指方齡貴《通制條格校注》中華書局2001 年版,第141 條。下類推);卷十四《倉庫?關防》方校本280;卷十六《田令?理民》方校本318;卷十七《賦役?科差》方校本370;卷十九《捕亡?防盜》方校本420;卷三十《營繕?造作》方校本642。《新唐書?刑法志》 在言唐的“格”“式”時說,“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71〕(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卷五十六《刑法志》,中華書局1975 年版,第1407 頁。元代群臣在議定《至正條格》時,認為“條格、斷例,有司奉行之事也”。〔72〕(元)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七《至正條格序》,《四部最刊》影印明成化刊本。
比較唐宋對有司所行之事的言論,唐代以《格》或《式》來總之,元代以條格、斷例來言之,這也可說明,唐代由《格》《式》所規范的有司常行之事,在元代是在條格或斷例之中規范的。如元人王與撰《無冤錄》中有“檢會通制結案式”之語。〔73〕(元)王與:《無冤錄》卷上《檢驗法物銀釵真偽》,朝鮮鈔本。這似可說明,元代的條格吸納了唐的格和式。〔74〕其實,南宋時期,有些“格”編入令典之中,如《慶元條法事類》卷十一《給假》門中載有《假寧格》的內容。所以,與唐宋比較來說,元代的格例法體系主要包括“條格”和“斷例”兩種法律形式。
然而,《大元通制》編纂之后,皇帝依然因時因事而發布詔令,詔書之后也附有條畫,此時的條畫當然有法律效力,但這些條畫是“臨時性”的政令。中書省等上級官府根據對皇帝圣旨的理解或因下級官府請示而制定“條格”或“斷例”,這些“條格”和“斷例”也有臨時的法律效力。所以,元代在編纂《大元通制》之后,其法律體系是有由條格、斷例和補充修正其規定的臨時性的圣旨條畫和法司議定格例所構成的。這些臨時性的條畫、條格和斷例,既補充和修正了《大元通制》而解決新的問題,又為以后《至正條格》的編纂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在《至正條格》編纂時,它們被全面清理,或者被納入,或因與已有條畫或格例捍格而被拒,或與原有條畫或格例重復而被取舍。被納入者,編入了法典,具有了“永久”效力,被拒或被舍者,便失去了效力,不能在處理類似事件時被援引。
法律體系所包括的法律形式之間,在各自作用的領域或層次上,總會保持一定的關系。法律體系要求其構成部分互相配合,相互連接,成為一體。律令法體系下,陳顧遠先生認為,“令之所在,實以政事法為主”“律之以刑事法為主,禮之以民事法為主”。〔75〕陳顧遠:《中國文化與中國法系》,載《陳顧遠法律史論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433 頁。這是從中國式的部門法角度來解讀的。
元代格例法體系中的“條格”和“斷例”也應如此。但研讀《至正條格》,其配合程度并不高。原因在于三點。其一,元代是“因時立法”“因事立法”。其二,表面上廢棄了金泰和律令。我們知道,金代法律深受中原傳統法律之影響。中原法律至唐宋時期,律令法體系已經相當完備,作為其構成部分的律、令、格、式或敕、令、格、式已經成為一有機聯系的整體。其三,元代沒有唐宋時期居于常規法地位的“律”。常法具有基本法的地位,〔76〕參見陳靈海:《國家圖書館周字51 號文書辨疑與唐格復原》,載《法學研究》2013 年第1 期。不可動搖。唐代突破“常法”的途徑是把可以獲得君臣普遍認可的“敕”編入唐格,宋代則是“編敕”。元代編于法典之中的“斷例”雖然大體相當于“律”,但其地位并不穩定,再次編修法典時,原先的“斷例”并非不能修改、刪除。
三、格例法體系與中華法系
元朝雖是以蒙古族為主建立的王朝,其法律形式同唐宋也不一致,但元人吳澄在論《大元通制》中“斷例”時云:“其于古律,暗用而明不用,名廢而實不廢。”可見,元朝法制仍屬于中華法系的一部分。楊一凡先生認為,元朝是中國古代從律令為主的法律體系過渡的時期。〔77〕參見楊一凡:《重新認識中國法律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版,第23 頁。但如何過渡,并未詳細論述。筆者以為,其過渡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從律典和令典的分立過渡到律例合編
唐宋時期的律、令分離,形成了各自的律典和令典。北宋天圣七年(1029 年)的《天圣令》已經將具有罰則的“敕”與令合編,只不過是處于附屬的地位。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 年)詔曰:以新《令》及《附令》頒天下。始,命官刪定《編敕》,議者以唐令有與本朝事異者,亦命官修定,成三十卷,有司又取咸平《儀制令》及制度約束之。在敕,其罪名輕者五百余條,悉附令后,號曰《附令敕》。〔78〕《資治通鑒后編》卷三八《宋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高明士認為有十八卷和一卷兩種。〔79〕詳細的辨析參見高明士:《“天圣令學”與唐宋變革》,載《漢學研究》第31 卷第1 期。《附令敕》 十八卷,夷簡等撰,《官品令》之外,案編敕(敕文),錄制度,依《令》分門,附逐卷之末;又案編敕(敕文),錄罪名輕簡者五百余條,悉附令后為《附令敕》一卷(注曰:又有《續附令敕》一卷,慶歷中編)。〔80〕參見高明士:《“天圣令學”與唐宋變革》,載《漢學研究》第31 卷第1 期。《附令敕》十八卷其性質,當屬于行政法。《附令敕》一卷,則是取自真宗咸平以來到仁宗天圣年間的《編敕》,其中罪名輕簡者共有五百余條,具有刑法性質,全部附在《天圣令》最后。
元代法典的編纂將相當于律的“斷例”和相當于令的“條格”合編。《大元通制》和《至正條格》則將相當于“令”的條格和相當于“律”的斷例等而視之,并列為兩篇。日本學者安部健夫指出,從法典的本質上看,《大元通制》是“律令的法典”。〔81〕參見(日) 安部健夫:《〈大元通制〉解說——兼介紹新刊本〈通制條格〉》,載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 3卷),《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宋遼西夏元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版。這為明清律例合編提供了依據。
(二)“斷例”這種法律形式進入法典
斷例作為一種法律形式最早出現于宋代。宋代“從來律令敕式有該說不盡之事,有司無以處決,引例行之”。〔82〕《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五九《元豐八年八月癸酉》。例是在刑部、大理寺等特定的機構內部使用的,公開性極低。御史中丞湯鵬舉認為“例之所傳,乃老奸宿贓,秘而藏之,用以附下罔上,欺或世俗,舞文弄法,貪饕貨賂而已”。〔83〕(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8259 頁。這說明了例的非公開性帶來的弊端。
宋仁宗慶歷年間,由于大理寺審理的疑難案件數量上升,“艱于檢討”,王子融建議“取輕重可為準者,類次為斷例”。宋仁宗接受建言,詔“刑部、大理寺,以前后所斷獄及定奪公事遍為例”。〔84〕《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〇《仁宗慶歷三年》。這是宋代斷例編纂的開始。熙寧年間,審刑院詳議官賈世彥上奏,請求刑部“以熙寧以來得旨改例為斷,或自定奪,或因此比附辦定結斷公案,堪為典刑者編為例”,〔85〕《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五四《熙寧七年》。刑部編訂了斷例。另外,大理寺也編訂了斷例,即《熙寧法寺斷例》 十二卷。史料記載宋代的斷例還有《元豐斷例》六卷、《刑名斷例》三卷、《斷例》四卷、《刑房斷例》、《紹興編修刑名疑難斷例》、《乾道新編特旨斷例》、《淳熙新編特旨斷例》、《開禧刑名斷例》等。〔86〕具體編訂情形參見[日]川康村:《宋代斷例考》,載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研究院編:《日本學者中國法論著選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 年版,第345-358 頁。川村康指出:“熙寧以前的斷例,在刑部、大理寺、審刑院等各機關獨立編纂;與此相對,元豐以后的斷例,以各機關未編集的例和內部的例冊作為資料,由中書刑房和編修敕令所等進行統一的編纂,反映了斷例的管理已經統一化、集中化。”〔87〕[日]川康村:《宋代斷例考》,載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研究院編:《日本學者中國法論著選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 年版,第375 頁。
宋代雖然編訂了一定數量的斷例,但其是作為不完善的法的補充而存在的,即“法所不載,然后用例”。但由于經常出現“用例破法”的情況,宋代不同時期對斷例的態度不同,如政和七年下詔:“除刑部斷例外,今后官司不得引例申請。”〔88〕(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8320 頁。政和七年(1117 年)下詔:“除無正條引例外,不得引例破條,及不得引用元祐年例。”〔89〕(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8321 頁。隆興元年(1163 年)四月,下詔禁止引用例而要求朝廷指揮,詔云;“有司所行事件,并遵依祖宗條法,及紹興三十一年(1161 年)十二月十七日指揮,更不得引例及稱疑似,取自朝廷指揮,如敢違戾,官司重作施行。”〔90〕(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240 頁。隆興二年(1164 年),臣僚認為,法都是根據以往的制度而制定,大多符合人情,但例是“朝廷一時之予奪,官吏一時之私意”,“今日之弊,在于舍法用例”,要求“中外悉遵成法,毋得引例,如事理可行而無正條者,須自朝廷裁酌取旨施行”,皇帝“從之”。這說明此時否定了例的使用。〔91〕(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8259 頁。乾道元年(1165 年),下詔明確禁止斷例的使用,刑部大理寺 “見引用例冊,令封鎖架閣,更不引用”。〔92〕(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240 頁。淳熙元年(1174 年),下詔禁止六部引用例,但允許刑部用乾道所修刑名斷例。
宋代對斷例態度的不一,最終不能徹底否定斷例的運用,一是由于斷例的公開性較低和斷例之間的不一致,導致了用例的不一,甚至“以例破法”,宋代臣僚“屢有建請,皆欲去例而守法”;二是因為法是固定不變的,但人的行為是無限的,“法有所不及,則例亦有不得廢者”,法的不完備和欠缺,就產生了由判決例的應用來補充的必要性。
用例的弊端和斷例的作用是共存的,解決的方法便是將斷例歸于“通行之法”。〔93〕劉篤才認為這種方法是“將處于法律體系之外的例吸收納入法律體系之中”。參見氏著:《中國古代判例考論》,載《中國社會科學》2007 年第4 期。紹興二年(1132年),臣僚建言,“凡有陳乞申請,儻于法誠有所不及,于例誠有所不可廢者”,讓敕令司“詳酌審訂,參照前后,委無抵牾,則著為定法,然后施行。如有不可,即與盡斷,自后更不許引用”,這樣一來,所施行的都是法而不是例,由吏用例產生的弊端便自然消滅,“舉天下一之于通行之法”。〔94〕(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8268 頁。這個建議得到了批準,但這一工作是否完成,如何歸于法,是以“敕”的形式發布,還是其他方式,從現有史料來看,無法確定。〔95〕梁松濤認為,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法則》卷八中有兩則判例,是“以例入法”的表現,可為缺失的宋代“以例入法”的法典形態提供一個直接參照。參見氏著:《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法則〉卷八考釋——兼論以例入法的西夏法典價值》,載《宋史研究論叢》(第 14 輯),河北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但據史料,元代則將“斷例”這種法律形式納入法典之中,換言之,元代的斷例歸入了“通行之法”。筆者此處所言斷例是指斷罪事例。因為,元代的斷例包括斷案通例和斷案事例。〔96〕關于元代斷例的篇目和性質,在《至正條格》發現之前,日本學者安部健夫、中國學者黃時鑒、殷嘯虎、方齡貴、曾代偉、劉曉等各抒己見。具體介紹參見劉曉:《〈大元通制〉到〈至正條格〉:論元代法典的編纂體系》,載《文史哲》2012 年第1 期。從《至正條格》來看,斷罪通例,是以圣旨、詔書等形式展現的。如《至正條格?斷例》卷第六《職制?枉法贓滿追奪》“至大四年三月”條:〔97〕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編:《至正條格(校注本)》,韓國城南影印元刊本2007 年版,第219 頁。
至大四年三月,詔書內一款,節該:“內外百司,各有攸職。其清慎公勤,政跡昭著,五事備具者,從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察舉,優加遷擢。廢公營私,貪污敗事,陳告得實,依條斷罪。枉法臟滿者,應受宣、勑并行追奪,吏人犯贓,終身不敘。誣告者,抵罪反坐。”
將臨時性的圣旨、詔書等編入法典,使之具有永久效力,這種方法同唐代時將敕令編入唐格和宋時的編敕入律是一樣的。但與唐不同的是,唐代的律典和格典是分立的,元代沒有獨立的律典,其編入法典的圣旨條畫就相當于唐宋的律。前文所言,宋代的斷例,在元時只是斷案事例。
元朝建立之初,法制混亂,在無法可守的情況下,“民間自以耳目所得之敕旨、條令、雜采類編,刊行成帙,曰《斷例條章》,曰《仕民要覽》,各家收置一本,以為準繩”。〔98〕《元朝紀事本末》卷十一《律令之定》,明末刻本。這時,雖“斷例作為一種法律編纂形式”,〔99〕參見楊一凡、劉篤才:《歷代例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版,第100 頁。但只是民間的編寫,直至《大元通制》的編纂,“斷例”成為了其中一部分,至此,斷例進入了具有穩定性的法典之內。
元代將斷案事例納入法典之中,在體例上,元人吳澄在《大元通制條例綱目后序》中云:“斷例之目,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廄庫,曰擅興,曰賊盜,曰斗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一循古律篇題之次第而類輯,古律之必當從,雖欲違之而莫能違也。”這是講《大元通制》“于古律,暗用而明不用,名廢而實不廢”。〔100〕(元)吳澄:《大元通制條例綱目后序》,載《吳文正集》卷十九,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概而言之,這是不錯的,但如果聯系宋代斷例的編修來審視,則可認為元代斷例的體例直接源于宋代斷例編修之體例。宋代的斷例編纂始于仁宗慶歷年間,將“所斷獄及定奪公事”,“輕重可為準者,類次以為斷例”。〔101〕《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〇《仁宗慶歷三年三月戊辰》。如何“類次”現無從考證。但紹興三十年(1160 年)的《紹興編修刑名疑難斷例》,其編目與律的編目相同,名例、衛禁(共二卷),職制、戶婚、廄庫、擅興(共一卷),賊盜(三卷),斗訟(七卷),詐偽(一卷),雜例(一卷),捕亡(三卷),斷獄(二卷),按十二門類編為二十卷,另外還有目錄一卷,修書指揮一卷。〔102〕(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8259 頁。
元代斷案事例并不是簡單地直接進入法典,而是經過一定的刪減、修改,有的成為整齊劃一的斷案通例,如《元典章》卷四十八《刑部?諸贓三?回錢?知人欲告回錢》“延祐二年二月”條:〔103〕《元典章》,陳高華等點校,中華書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1599-1600 頁。
延祐二年二月,江南行臺準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札付:
來呈:“備監察御史呈:‘廣寧路同知耶律哈剌孫,取受行使偽鈔人石抹君寶至元鈔六十貫,閭陽縣主簿李榮,亦取受訖本人至元鈔一十貫。聞知欲告,回付過錢人傅改驢收管。取訖招伏,罪經釋免’”。送刑部議得:“諸官吏及有出身人等,因事受財,未發而自首及回付者,當許自新,準首原罪。其知人欲告,回主及有自首,蓋因事不獲已,即非悔過,合依已擬,減罪二等科斷。罪既經斷,似難復任。合準御史臺所言,解見任,別行求仕。如蒙準呈,照會相應。”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這一斷案事例,在編入法典《至正條格?斷例》卷第六《職制》時,以“知人欲告回主”為目名,其內容為:〔104〕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編:《至正條格(校注本)》,韓國城南影印元刊本2007 年版,第228 頁。
延祐元年閏三月,刑部議得:“諸官吏及有出身人等,因事受財,未發而自首及回付者,當許自新,準首原罪。如已事發,出首回付,罪合全科。其知人欲告,回主及自首者,依例減罪二等科斷,仍解見任。”都省準擬。
此條與《元典章》中的斷案事例相比較,有四點不同。其一,名稱不同。《元典章》中由于保留了人犯的具體行為是取受“至元鈔”,故以“知人欲告回錢”為名;《至正條格》舍去具體人犯具體行為,只保留刑部議擬內容,且“官吏及有出身人”不僅受“錢”,還可受“財”,但所受“錢”或“財”都是原“主”的,故以“知人欲告回主”為名,更有概括性。其二,《元典章》保留此斷案事例的公文原貌,《至正條格》取刑部議擬和中書省的批復。其三,《元典章》規定的是,“官吏及有出身人”因事受財,未發于官府,知人欲告,自首或回主的處罰,即“減二等科斷”。《至正條格》除規定未發情形下的處罰,還加入了“如已事發,出首回付,罪合全科”的規定。其四,《至正條格》語言簡潔。刪除了《元典章》中的“蓋因事不獲已,即非悔過”,“罪既經斷,似難復任”等解釋性的語言。
“斷例”作為例的一種,為明清的“例”進入法典提供了模式。明初“有律有令,而律之未賅者始有條例之名”,〔105〕(清)沈家本著,鄧經元、駢宇騫點校:《歷代刑法考》,中華書局1985 年版,第2221 頁。明朝形成了律例并行的體制。明初,例的編纂還存在于法典之外,明代中期萬歷十三年(1585 年),《問刑條例》開始進入法典之中,具體做法是將《大明律》律文逐列于前,條例附于后,形成了“律為正文、例為輔助”的法典編纂模式。〔106〕參見陳濤、高在敏:《中國法典編纂的歷史發展與進步》,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04 年第3 期。萬歷三十八年(1610 年)私人刊刻的《大明律集解附例》收入條例405 條,與官方《大明律》不同的是,這些條例逐條附于相關律文之后,律文和例文融為一體。這種形式為清代所繼承,順治四年頒布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和后來的《大清律例》都是將條例分門別類附于相關律文之后,律例并稱,例在法典中的法律地位進一步確立。
(三)條格和斷例的形態決定了其續編的可能性
《大元通制》的編纂,是對以往的圣旨條畫和百官有司制定的格例的全面清理,將它們以“類集”的方式分別納入“條格”或“斷例”之中,其結果是構筑了元代的格例法體系。從法律體系的結構來看,唐宋時期律典、令典分立,律正罪名,令定事制,二者相輔相成,皆為“常法”,其地位、權威不可動搖,穩定性極強。元代將相當于律的斷例和相當于令的條格,編入同一法典,也是二者并立,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但是無論是條格還是斷例,其條文的形態都不是律典或令典中的“法條”,圣旨條畫和有司制定的格例保留了或部分保留了原有的形態,是隨事隨時產生的,這也決定了其概括性不強,為以后發布的圣旨條畫或有司制定格例納入法典提供了方便。〔107〕唐宋時,律典制定之后,不能更改。對于隨事隨時發布的敕令,如果使其有普遍約束力,便采取編敕的方法補充律。元代相當于律的斷例,在來源上也是隨時隨事產生的條畫或有司議定的斷例,所以對于以后同樣性質的條畫就可直接編入法典。這可能也是元代除了《大元通制》《至正條格》等法典外,沒有其他形式的法律文本的原因。《大元通制》編纂之后,圣旨條畫和法司議定的格例繼續產生,它們如何歸置,對于法律體系的維護,《大元通制》的作用,以及其中的“條格”和“斷例”的權威,都是關鍵所在。或許正是這兩方面的原因,元后期的《至正條格》在《大元通制》基礎上“續纂”而成。清代《大清律例》中律條不變,“條例”是“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到同治年間,例同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條。
四、結語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得知:其一,研究元代的法律體系,與“律令法體系”“律例法體系”研究的角度一樣,即從法律形式角度研究,有助于把中國古代的法律體系作為一個整體,認識其三個階段的不同特點;其二,元代的法律體系可以名之為“格例法體系”,其是以“條格”和“斷例”為主體的,包括其他法律形式的密切聯系的整體;其三,元朝法制雖然沒有唐宋時期的“律”“令”“格”“式”之名,但其篇目和內容,取自唐宋法典,實際上仍屬于中華法系的一部分。中華法系從“律令法體系”到“律例法體系”的轉變中,元代“格例法體系”的過渡作用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從律典和令典的分立過渡到律例合編;二是“斷例”這種法律形式進入法典;三是斷例的形態為其續編提供了可能。
元朝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王朝,其法律制度與原來中原法律文化的關系是承襲還是斷層,則有不同觀點。明初認為,“元氏以戎狄入主中國,大抵多用夷法”。〔108〕《明朝典匯》卷二十《朝端大政》,明天啟四年徐與參刻本。但元人吳澄在論及元代刑律時,則認為“其于古律,暗用而明不用,名廢而實不廢”。持不同觀點的原因在于:明初主要關注元代法律的形式主要是條格、斷例,這不同于唐宋時期的律令格式等法律形式,而吳澄所關注的是法典的編纂體例和法典的內容。日本學者島田正郎,注重蒙古族的習慣、判例法,認為元代法律屬于“蒙古法系”。〔109〕詳細介紹參見徐曉光:《“蒙古法系”質疑——兼論中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法律制度與中華法系的關系》,載《比較法研究》1989 年第21 輯。
其實,研究法律體系時,形式與內容并重,才能揭示其特點。元人吳澄既考察《大元通制》的形式又注重其內容,揭示了元代法律與中原傳統法律的真實關系。然而,由于《大元通制》“斷例”之篇已經佚失,從法典編纂體系之角度而言,“斷例”的篇目和性質,學界爭論不休,在某種程度上,不利于正確認識元代法律在中華法系中的地位。
2002 年,元代后期編纂的法律文獻《至正條格》 殘本在韓國被意外發現。其存有“斷例”全部目錄,以往有關斷例篇目和斷例性質的爭論有了公斷。殘本《至正條格?斷例》存有衛禁、職制、戶婚、廄庫和擅興等五篇,共12 卷348 目408 條條文。這為我們從法典內容角度研究其與中華傳統法律關系提供了新的史料,如《至正條格?斷例》第八卷《戶婚》中有“同姓為婚”“許婚而悔”“有妻更娶”“居喪嫁娶”等目都承受自《唐律》。所以,元代法律從編纂體例、內容而言,與中原傳統法律文化是一脈相承的,其是中華法系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屬于中華法系。這對了解我國多民族國家法律文化發展的全貌和中華法系形成的整體過程有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