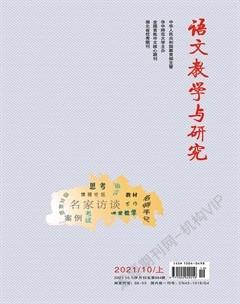“回憶性”散文中的“典型事件”
黃玨明


在八年級上冊第二單元的導(dǎo)引中提出“了解回憶性散文、傳記的特點,比如內(nèi)容真實、事件典型、注重細節(jié)等”。“典型”這一概念,是文學(xué)作品表現(xiàn)力的重要特征。其具體表現(xiàn)為:個性與共性、客觀與主觀、情感與理性的統(tǒng)一。所謂“個性與共性”的統(tǒng)一,是反映一件件具體的事件背后,凝聚著客體人物的總體形象氣質(zhì)。甚至這些個體的形象心理反映了社會、時代、文化的共性價值。“客觀與主觀”的統(tǒng)一,則是指文中描述的對象和事件具有客觀實在性。但這種描述不是純粹的模寫,而是創(chuàng)作者精心選擇、剪裁的結(jié)果,含有強烈的主體性。“情感與理性”的統(tǒng)一,則是指事件的選擇與形象的刻畫雖然含有創(chuàng)作者的主體性,但絕不是無意識地胡亂寫作,而是由創(chuàng)作主體經(jīng)過一番思索后,有意識地安排和用筆。
基于上述對“典型”一詞的解讀,下文則以本單元的四則選文為例,具體分析“典型事件”的功能與意義。
一、反映客體人物的鮮明形象
事件與客體人物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guān)系。創(chuàng)作者通過敘述事件或刻畫細節(jié)表現(xiàn)人物的形象。而這些事件,往往能精確、細致地反映人物的個性特質(zhì)。這就是“典型事件”的表現(xiàn)功能。
1.直陳式的交代
所謂“直陳式交代”,是指沒有過多文學(xué)筆法的渲染、加工,以相對直白的方式交代事件的內(nèi)容與經(jīng)過,從而反映人物形象。如朱德《回憶我的母親》中“母親是個好勞動。……母親把飯煮了,還要種田,種菜,喂豬,養(yǎng)蠶,紡棉花。因為她身體高大結(jié)實,還能挑水挑糞”一段,作者僅僅列舉幾個勞作活動的內(nèi)容,將母親家里家外,家務(wù)農(nóng)忙等辛勤勞動的形象勾畫出來。此處沒有過多渲染母親忙活時的情狀,但在有限的句子空間中一連串密集的列舉,反而體現(xiàn)出母親手腳麻利、勤勞多能、干活能吃苦的形象。
又如文中“我們用桐子榨油來點燈,吃的是豌豆飯、菜飯、紅薯飯、雜糧飯,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飯里做調(diào)料。這類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飯食,母親卻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來有滋味”兩句,則是簡單地對比了“我們”窮人家與富人家對于粗飯疏食的態(tài)度,和處理事物的態(tài)度方法,卻能突顯出母親能干、靈巧、聰慧的巧婦形象。
直陳式交代的好處,則是用簡筆畫式的寥寥幾筆,就能清晰地表現(xiàn)人物形象,語言簡潔而形象鮮明。當然,這與創(chuàng)作者的身份密切相關(guān)。朱德作為優(yōu)秀的將領(lǐng),有著非凡的軍事才能和領(lǐng)導(dǎo)力。但他畢竟不是文學(xué)藝術(shù)家,對于文學(xué)性的創(chuàng)作筆法不甚熟諳,則在情理之中。而粗獷簡約的筆鋒,不僅恰到好處地表現(xiàn)了其母親質(zhì)樸勤儉的形象,也與創(chuàng)作者身份吻合,反而給了讀者真實感。
同時,正是因為“簡潔”的筆法,卻能提供讀者無限的想象空間。讓讀者去想象,這位勤勞質(zhì)樸的究竟是怎樣的容貌?下地干活時,會是怎樣的表情?讀者的既有經(jīng)驗就會主動填補這些空白,產(chǎn)生美學(xué)的效果。
2.精細式的描刻
與上述筆法不同,精細式的描刻則是通過油畫式的筆法,把人物的細節(jié)精確地描繪出來,從而表現(xiàn)其形象。如茨威格《列夫·托爾斯泰》的第5段中描寫遠道而來的客人想象中托爾斯泰的形貌“希望看到一個美髯公,集尊貴、軒昂、偉岸、天才于一生”,鮮明地刻畫出這群俗人對于外貌的看重,甚至流露出作者對上流社會價值觀的鄙棄。同時,還刻畫了他們對想象中“貌若天人”的文壇泰斗的心態(tài)——“頷首低眉,敬重有加,內(nèi)心的期望擴大到誠惶誠恐的地步”,表現(xiàn)出一種“畢恭畢敬”“謙卑恭順”的形象。然而這種“謙卑”在見到真實的托爾斯泰時,瞬間變了臉——“什么?就這個侏儒!這么個小巧玲瓏的家伙?”創(chuàng)作者將訪客見到托爾斯泰本人的前后神態(tài)、心理作了精細的刻畫,把一群無知、傲慢,又假充有文化修養(yǎng)的世俗小丑描刻得淋漓盡致。
精細式的刻畫,與創(chuàng)作者自身的藝術(shù)修為有著至關(guān)重要的聯(lián)系。茨威格本就是筆力精到的文學(xué)家,《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象棋》等作品都能將場面、人物把控得恰如其分,精妙地表現(xiàn)人物心理和氣質(zhì)。同時,精細的刻畫筆法,給了讀者一個具象的畫面,使得讀者身臨其境,仿佛那些俗氣又媚態(tài)的小人形象就在眼前。前后對照著看,讓人有冷俊不禁,忍不住發(fā)笑的地步。這當然是作者漫畫式的夸大,突出細節(jié)的筆法呈現(xiàn),但是這些也帶了“審丑”的效果。“高貴的來客”成了丑角,帶來了辛辣無情的諷刺效果。因此具有極高的美學(xué)意義。
二、反映客體人物與創(chuàng)作主體間的關(guān)系
事件固然是反映所傳人物的形象氣質(zhì),但也是經(jīng)過作傳者裁選的結(jié)果,因此也必然反映客體人物與創(chuàng)作主體的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首先表現(xiàn)在人物對作者的影響。
1.直接影響
這主要是指所傳錄人物的言行、乃至品性對于創(chuàng)作主體的影響,促其成長。而這些影響都通過日常事件發(fā)生,即典型事件。如魯迅《藤野先生》中所記錄的幾件事情——藤野先生幫“我”改講義,當面指出解剖繪畫錯誤等事件,促發(fā)了“我”對他認識的變化。文中提及他對“我”的講義是“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改過”,那種對于治學(xué)的認真。甚至“連文法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體現(xiàn)他做事細致認真,同時也考慮“我”是外國學(xué)生的特殊情況。以至于“我很吃了一驚”“不安與感激”。在面對“我”自以為是“美化”解剖圖時,他竟然先肯定“我”畫得“好看些”,然后才指出“我”在專業(yè)意識上的不足。表明他十分尊重學(xué)生的個性,以至于后來“我”追憶時流露出“那是太任性”的自責(zé)與追悔。
同樣在《回憶我的母親》中“母親這樣地整日勞碌著。我到四五歲時就很自然地在旁邊幫她的忙,到八九歲時就不但能挑能背,還會種地了。……這個時期母親教給我許多生產(chǎn)知識”一段,交代了母親對“我”生產(chǎn)知識、勞動能力,乃至吃苦耐勞品質(zhì)影響。其實這種影響絕不是一時一地的,所以對于創(chuàng)作主體的生命經(jīng)驗有著不可取代的作用。誠如后文提及“一八九五年家里被地主逼租。年三十的晚上被迫搬家,舉家分居兩地。母親對于窮苦百姓的同情,對于為富不仁者的痛恨,啟發(fā)了‘我反抗壓迫。尋找光明。”可見,母親身上的大義情懷、艱苦忍辱為家人奉獻的精神品質(zhì),促發(fā)“我”堅持革命,堅持為底層的勞苦大眾奉獻自己的一腔熱情。而《藤野先生》的文末也提及“每當夜晚疲倦偷懶時,瞥見藤野先生的相片,想起他的話,又會促發(fā)‘我良心發(fā)現(xiàn),增加勇氣”。這都是客體人物對于創(chuàng)作主體身心思想的深刻影響。
2.間接影響
間接性影響主要是指創(chuàng)作主體與客體人物之間沒有密切的接觸,但是客體人物身上的某些氣質(zhì)品質(zhì)超越了時間、空間的局限,影響到了主體。如《列夫·托爾斯泰》中,茨威格就有大量對于托爾斯泰事跡及其樣貌的想象。如文中想象托爾斯泰作為大臣、學(xué)生、軍官、馬車夫等身份,混跡在人群中。其貌不揚,難以辨別。這對于大多數(shù)世俗庸眾眼中,是平平無奇、毫無吸引力的長相。但正是這樣一張“大眾臉”,卻能與“全體俄國人民同呼吸共命運”,這對于同樣把人道主義作為思想價值核心的茨威格,何嘗不是一種共鳴?
后文更為精彩地想象著托爾斯泰眼神的描寫,表現(xiàn)出他深邃、柔和、犀利等多元特征的統(tǒng)一。眼神,即是心靈的窗戶。茨威格藉此表現(xiàn)了托爾斯泰對于社會丑惡現(xiàn)象的敵視輕蔑,對于苦難人民深切同情哀鳴。這是一種高貴的靈魂。同為作家的茨威格贊許前輩大家的高尚和社會責(zé)任,又何嘗不是借他人之杯酒,澆心中塊壘呢?乃至于最后感嘆:“一個能看透事物本質(zhì)的人,常常會缺失屬于自己的幸福”。缺失的是什么?當然是受到世俗的排擠、格格不入!一個在莽原上奔跑的戰(zhàn)士,與整個墮落的社會作出抗爭,必然會被當時的俗人排斥。茨威格說著托爾斯泰的境遇,又何嘗不是在講述自己的遭際呢?
主體記錄描繪客體人物的事跡,絕不是單純地為其樹碑立傳,更重要的是表現(xiàn)兩者之間的交流、影響。無論是直接、抑或間接,都是觸及創(chuàng)作主體的生活,乃至生命歷程的發(fā)展。因此,閱讀“回憶性”散文,研究兩者間的關(guān)系是不可或缺的切入點。需要指出的是,間接性影響中的“想象”,不是作者胡亂的杜撰。而是基于作者對于客體人物形象的正確把握之上,而進行的藝術(shù)加工。它是假定與真實的統(tǒng)一。
三、反映創(chuàng)作主體的情感態(tài)度
上文提及的影響,如更多的是涉及性格、心理、生活、價值觀層面,那么這種深刻的影響則必然促發(fā)創(chuàng)作主體內(nèi)心世界的情感流露。這種情感的流露也可分成直接與間接兩個方面。
1.直接的情感表態(tài)
這是指創(chuàng)作主體在回憶與客體人物交往的事件時,直接表露對于對方的情感態(tài)度。如《回憶我的母親》中最后三段的抒情——“我應(yīng)該感謝母親,她教給我與困難作斗爭的經(jīng)驗。……我應(yīng)該感謝母親,她教給我生產(chǎn)的知識和革命的意志,鼓勵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這個哀痛是無法補救的。”作者非常直白地表達了對于母親影響自己一生、教導(dǎo)自己成長的感激,和對于母親溘然長逝的悲痛哀傷。需要指出的是,這份情感的抒發(fā)絕不是無的放矢,而是前文與母親交往的種種事件的必然結(jié)果。誠如前文所分析的,作者列舉了自幼目力所見母親的勤勞、忍耐、奉獻、巧智、良善與嫉惡如仇的種種事件,從而影響了作者一生的成長和價值觀。正是這些生命的經(jīng)歷,引發(fā)“我”對母親的感念,對她的追思,對她的揄揚。
而《藤野先生》中,魯迅言道“在我所認為我?guī)煹闹校亲钍刮腋屑ぃo我鼓勵的一個”。這份感激,正也是基于前文種種事件的必然結(jié)果。作為日本教師的藤野先生,沒有像其他日本學(xué)生一樣,歧視“我”這個弱國國民。反而用他的治學(xué)精神教給“我”扎實的學(xué)識,以他寬厚的長者之風(fēng),尊重“我”的個性。甚至在怕中國人“敬鬼神”的文化而使“我”不敢從事解剖的事件上,表現(xiàn)出了對于他國國民和文化的尊重。他的偉大已經(jīng)超越了一個普通的老師,而是一個尊重每個人、每個民族、乃至整個學(xué)術(shù)的人物。正是因為和他相處時經(jīng)歷的種種事件,改變“我”對他的認識,產(chǎn)生了終身敬仰的態(tài)度。
2.間接的情感暗蓄
間接情感,是指主體在敘述客體人物事跡時,沒有明顯地表露自己的情感態(tài)度。但在敘事的字里行間,能解讀出主體的內(nèi)在情感。如《美麗的顏色》中,艾芙·居里記錄了其母親在逼仄的斗室里,操作放射性元素鐳的提煉。作者描刻出屋內(nèi)夏悶冬寒,雨大霜重的種種艱苦工作環(huán)境,同時又描寫其母親在簡陋環(huán)境里樂此不疲地工作。這兩相對比,難道不是對母親專心業(yè)務(wù),心無旁騖的最大贊美嗎?她甚至還描寫了母親干著“壯漢般”粗重的體力活,在滿是刺激性氣味的實驗室里,埋頭工作。在十九世紀末,大部分女性還在極端的男權(quán)社會里備受欺壓,居里夫人卻能在頂尖的化學(xué)領(lǐng)域與男性一爭高下。這何嘗不是女兒對母親的勇敢、進步而驕傲呢?甚至文中,既不稱呼“母親”,也不稱呼“居里夫人”,而是稱呼其名“瑪麗”,不正是要強調(diào)她是一個脫離家庭桎梏、丈夫附庸,獨立自強的時代女性形象嗎?
文末作者交代了居里夫婦外出散步的事件。看似不經(jīng)意地,但細想:瑪麗對于鐳的懸心關(guān)切,就像母親對于就要出生的愛兒一樣,呵護關(guān)切。不正是瑪麗半生心血凝聚于科學(xué)事業(yè)的展現(xiàn)嗎?瑪麗將鐳的顏色視為“最美麗的顏色”,是她對科學(xué)事業(yè)鐘情的流露。而這份“最美麗的顏色”,不也是作者眼中醉心科學(xué)事業(yè),孜孜以求的瑪麗嗎?不正是作者對她一生付出的最大稱許嗎?
相較于認知、人生經(jīng)歷的影響,情感層面的影響更為深層,也更為深刻,需要透過事件敘述、人物描寫中細細開掘。
四、反映主體理性意識
我們常常會誤解——由于“回憶性”散文或傳記,表現(xiàn)了創(chuàng)作主體之于客體人物的情感。故而,文章是一種絕對情感化、非理性的呈現(xiàn)。這其實是錯誤的。理性不僅在應(yīng)用性文體中運用,在這類文學(xué)性作品中也是至關(guān)重要的。但文學(xué)性作品中的理性,不似論說文依賴概念、判斷、推理等理性思維形式的呈現(xiàn),而是體現(xiàn)在眾多事件與人物形象氣質(zhì)的統(tǒng)一,以及諸多材料之間內(nèi)在邏輯關(guān)系上,是內(nèi)在隱秘的。
1.事件與人物形象氣質(zhì)的統(tǒng)一
在“回憶性”散文中,有大量事件的呈現(xiàn)。表面上,它們是一個個獨立的內(nèi)容。實則它們統(tǒng)一與人物總體精神氣質(zhì)。以《回憶我的母親》一文為例。
從上述表格,可以看出:作者通過敘事多件事情,表現(xiàn)出母親形象的多個側(cè)面。但是這些側(cè)面又統(tǒng)一于母親的總體人物形象氣質(zhì)——平凡的勞動者,又是開創(chuàng)民族歷史的勞動者。因此,典型事件就是多樣性的統(tǒng)一。這使得看似沒有關(guān)聯(lián)的內(nèi)容,有了總的主題。同樣,在《列夫·托爾斯泰》中,作者大量描寫了“人們”眼中托爾斯泰的種種樣貌——污濁粗糙的皮膚、亂糟糟的額頭、朝天鼻、招風(fēng)耳、厚嘴唇;以及作者眼中托爾斯泰的眼神——和藹、富有情感、又犀利如刀。這看似雜亂無章的描寫,其實統(tǒng)一于作者的認識和內(nèi)在情感。他譏諷世俗人的無知,只關(guān)注樣貌的美丑。同時又贊賞托爾斯泰精神境界的高卓,因而其眼神能洞穿人心。所有描寫都統(tǒng)一于作者內(nèi)在的情感世界。
2.事件與內(nèi)在邏輯的統(tǒng)一
以魯迅的《藤野先生》為例
上述是“我”與藤野先生直接交往的事件,由此可以發(fā)現(xiàn)兩條重要的內(nèi)在邏輯:1)“我”和藤野先生的交往事件,越來越超越普通的師生教學(xué)關(guān)系,他從關(guān)心“我”的學(xué)業(yè),到關(guān)心“我”的民族文化,甚至感嘆現(xiàn)代醫(yī)學(xué)不能借“我”的力量傳到中國去。我們彼此之間的親密度越來大。2)“我”對藤野先生的認識也越來越豐富,情感也越來越親近深摯。再看文中另外幾則與藤野先生無直接關(guān)聯(lián)的事件:1)東京郊野里,清國學(xué)生的派對;2)“匿名信事件”和“幻燈片”事件。這些事反映了當時絕大多數(shù)日本學(xué)生對于中國人的輕賤、歧視和嘲弄。而中國留日學(xué)生又無自強之心,只知玩樂,不思進取,不振奮國家民族。兩類人疊加在一起,與藤野先生的博愛形成鮮明對比,更凸顯出先生的偉大,和“我”對他敬重。所以,看似無關(guān)的諸多事件,其背后是有創(chuàng)作者的理性思考和安排。它們都與人物總體形象和創(chuàng)作主體的情感態(tài)度密切相關(guān)。這就是“典型事件”的功能和價值。
綜上所述,在日常教學(xué)中需要引導(dǎo)學(xué)生關(guān)注并認識“典型事件”的意義與價值。從概括事件內(nèi)容入手,分析人物形象和作者的內(nèi)在情感。同時,還要引導(dǎo)學(xué)生梳理,眾多事件的內(nèi)在邏輯關(guān)系,把握創(chuàng)作者如此安排的寫作意圖。如此,才能真正建構(gòu)學(xué)生對于“回憶性”散文的認識體系,真正把握文章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