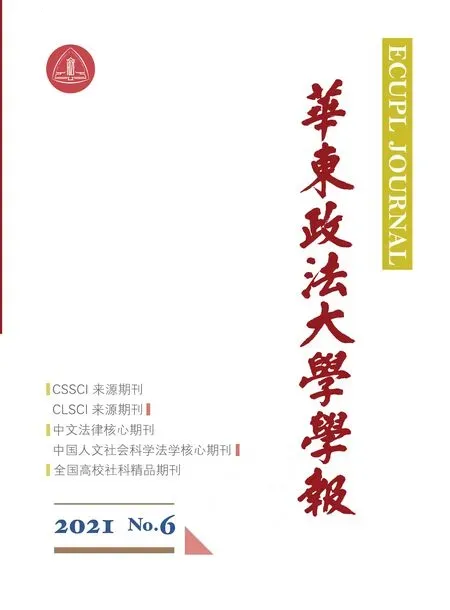高利放貸的法律規制:刑民雙重視角的考察
陳興良
目 次
一、高利放貸的立法演變
二、高利放貸的入刑之爭
三、高利放貸的變相入罪
四、高利放貸的正式入罪
一、高利放貸的立法演變
在我國,高利放貸和民間借貸幾乎是同義詞,這是因為民間借貸缺乏強制的收債手段提高了放貸成本,因而其利息居高不下。在這種情況下,民間借貸可以說都是高利貸。民間借貸是一個內涵較為模糊的概念,如果僅就字面含義而言,只要是私人之間的借貸,無論是生活性借貸還是經營性借貸,都屬于民間借貸。然而,在通常情況下,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都將民間借貸界定為經營性借貸。我國的民間借貸作為國家金融的一種補充,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無序的民間借貸又會對國家金融秩序造成破壞。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民間借貸的立法態度隨著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而不斷調整,經歷了從禁止到放開再到限制的曲折演變過程。因此,我國的民間借貸,隨著經濟發展和金融需求的起伏,始終處在管制與放開的循環之間。具體而言,我國的民間借貸管制政策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是初步放開階段。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活動對金融的需求井噴式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出現了“合會”“標會”“搖會”“抬會”等民間融資形式。特別是浙江溫州等地,在中小企業創辦和發展過程中,民間借貸十分活躍。可以說,此時的民間借貸對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資金支持。然而,民間借貸,尤其是高利貸的負面效應不斷暴露。我國學者描述了發放高利貸的三種行為方式:第一,利用自有資金直接發放;第二,以低息吸收他人資金(主要是社會閑散資金),然后以較高利率放貸,即所謂倒貸;第三,利用從國家銀行、信用社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取得的優惠貸款,高利轉貸,以取得高額利息。〔1〕參見陳正云主編:《金融犯罪透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頁。其中,第一種資金融通是狹義上的民間借貸,第二種高利放貸行為具有非法經營性質,第三種行為屬于高利轉貸。上述三種高利放貸行為中,后兩種發放高利貸行為都具有對市場經濟秩序,尤其是金融秩序的破壞性。只有第一種發放高利貸行為的副作用較小,然而其放貸的資金規模有限,難以承擔對民營經濟的金融支撐功能。
第二是嚴格管制階段。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金融立法的加強,對民間借貸的管制也被收緊。例如,我國1995年頒布了《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和《票據法》等一系列金融法。其中,《商業銀行法》第3條明文規定,只有商業銀行才具有經營吸收公眾存款和發放貸款業務的合法資質,這是授予以商業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金融壟斷權。因此,銀行從事借款業務是合法的,而以牟利為目的的民間借貸是不被允許的。1998年7月13日,國務院頒布了《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以下簡稱《辦法》),這是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為加強防范而對金融活動進行的清理整頓,針對的重點是非法金融業務活動。根據《辦法》第4條第3項的規定,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包括非法發放貸款。當然,民間借貸也在禁止之列。甚至企業之間的借貸也被法律所禁止。1996年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貸款通則》第61條規定:“企業之間不得違反國家規定辦理借貸或者變相借貸融資業務。”第73條規定:“企業之間擅自辦理借貸或者變相借貸的,由中國人民銀行對出借方按違章收入處1倍以上至5倍以下罰款。”由此可見,企業之間的借貸是違法的。在這種情況下,民間借貸更是法所不容。值得關注的是刑法對高利貸的態度。在民間借貸被禁止的情況下,所有民間借貸,凡是利率高于銀行貸款利率的,都可以稱之為高利貸。
第三是逐漸放松管制階段。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金融對外開放的壓力增加,在金融改革的背景下,對民間借貸又開始放松控制。正如我國學者指出的:“民間借貸的重要作用被重新認可,2005年國家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金融服務業,2010年國家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民間借貸再次活躍,成為眾多中小企業融資的主要渠道。中國人民銀行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2010年這一市場的資金存量就已超過2.4萬億元,近兩年來,民間借貸資金量逐年增長,存量資金增長超過28%。在中國現行的金融體系中,民間借貸在信息、交易成本、交易效率以及擔保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對經濟增長發揮了特殊的補充作用。”〔2〕參見華律網整理:《中國民間借貸的法律規制》,來源:www.66law.cn/laws/86219.aspx,2021年6月17日訪問。在這種情況下,小額貸款公司,尤其是網絡貸款等形式的放貸行為盛行一時。網絡貸款是以網絡平臺為媒介的貸款方式。校園貸就是一種典型的網絡貸款。這種網絡貸款的特點是借貸關系發生在陌生人之間,沒有傳統貸款的抵押、擔保等還款保障措施,而是以通訊錄、裸照等作為還款保障手段。在借款人不能歸還欠款的情況下,放貸人將利用向通訊錄中的人員傳播裸照或者打電話相威脅的方式追討欠款。校園貸的借款周期很短,只有7天,而借款利息很高,對急于用款的青年學生具有較大的誘惑力。除了校園貸,以網絡為平臺從事借貸的還有所謂的P2P(Peer to Peer Lending)。正如我國學者指出的:P2P是網絡版的民間借貸。〔3〕參見鄧小俊:《民間借貸中金融風險的刑法規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頁。P2P本來是一個網絡金融信息服務平臺,以撮合形成借貸關系為基本職能,由此收取一定的金融服務費。然而,在實際運作過程中,P2P發生嚴重變形,網絡金融信息服務平臺淪為網絡借貸平臺:一方面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另一方面非法發放高利貸。由此可見,由于對民間借貸缺乏有效管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非法發放高利貸等行為大肆泛濫,嚴重破壞了我國的金融秩序。
第四是全面封殺階段。高利貸對社會秩序的破壞性主要體現為其討要欠款行為具有暴力性。由于缺乏合法途徑,暴力或者軟暴力成為高利放貸者討要債務的主要手段。專門的討債公司應運而生,恐嚇、跟蹤、堵截、拘禁成為討要債務的常見手段。有時還發生殺害債務人等惡性案件。例如,浙江就曾經發生過殺害債務人沉尸案。〔4〕胡放權故意殺人、非法拘禁案,參見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浙杭刑初字第112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發放高利貸容易滋生黑惡勢力,為黑惡勢力提供經濟支持行為的性質受到高度重視。在這種情況下,發放高利貸的行為就成為刑法懲治的重點。顯然,對于高利貸討要債務過程中的違法犯罪行為,可以依據相應的刑法規定進行處罰,這是沒有問題的。然而,在當時的法律語境中,發放高利貸行為并不是刑法中的犯罪。因為在刑法中只是將高利轉貸行為規定為犯罪,因為這是一種特殊的高利貸行為,而以自有資金放貸和利用他人資金放貸這兩種行為并沒有被規定為犯罪。
二、高利放貸的入刑之爭
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民間借貸是金融活動的組成部分,受到國家金融政策的制約,與此同時,民間借貸也是一個法律問題,立法政策和司法政策對民間借貸同樣具有重大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說,法律對民間借貸的影響甚至在金融管制之上。這里涉及對民間借貸金融效果和社會效果的評價問題,同時還夾雜著金融機構壟斷金融權的利益考量,因而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如果僅僅從融資的便利性來說,民間借貸確實具有其優勢。然而,出借者的借款回收風險極大,這也正是民間借貸利率遠高于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的原因。也就是說,民間借貸的高利率中其實已經涵蓋了借款回收風險。正規金融機構主要服務于大型企業,并且貸款條件較為苛刻,如要求貸款方提供擔保和抵押等。在這種情況下,小微企業或者創業初期的企業是不可能獲得金融機構的貸款支持的,它們只能求助于民間借貸。當然,民間金融具有其顯而易見的副作用,這就是民間借貸存在的金融風險和法律風險。
從金融角度來說,缺乏有效監管的民間借貸對金融秩序會產生較大的破壞,具有較大的法律風險。這種法律風險主要來自催要債務的行為。因為民間借貸的期間一般較短,利率較高,而且缺乏擔保或者抵押等有效的債權實現方式,逾期不還的比重較高。由于民間借貸發生在私人之間,一旦發生債務逾期,債權人可能會采取非法手段進行討要,輕者對債務人進行恐嚇、跟蹤、滋擾,重者對債務人進行拘禁、毆打甚至傷害。以“抬會”等形式進行的民間借貸還會引發連鎖反應,影響地方的社會穩定。因此,從社會治理角度來說,國家更為關注的往往是民間借貸對社會秩序的影響,尤其是它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消極后果。雖然民間借貸對地方經濟發展具有正面效應,但是考慮到它對社會穩定的破壞作用,地方政府會對民間借貸保持一種戒備心理。1985年的鄭樂芬、蔡勝男利用“抬會”進行金融投機倒把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被告人鄭樂芬與蔡勝男共謀,組織“民間金融互助會”(俗稱“標會”),從中牟利。鄭、蔡為牟取暴利,將“標會”轉為以高利貸為誘餌的“抬會”,鄭充當會主。“抬會”導致高利貸活動猖獗,破壞了人民政府對民間借貸的管理秩序,造成國家銀行的儲蓄額急劇下降,信貸資金不足,影響當地的生產建設。當地人民法院以投機倒把罪判處鄭樂芬死刑立即執行,判處蔡勝男無期徒刑。〔5〕參見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編:《人民法院案例選(刑事卷)》(1992年—1996年合訂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頁以下。在上述案件中,所謂金融投機倒把實際上就是高利放貸。“標會”是我國南方較為流行的一種資金互助方式,“標會”的本質是一種儲蓄與貸款相結合的民間金融組織,其價值在于,匯聚一小部分人的經濟力量,讓群體內某個或某些成員提早獲得資金用于消費、投資等,從而充分利用貨幣的時間價值。而對應“得會”順序比較靠后的“會腳”,也可以得到一定數額的利息作為補充。因此,可以將“標會”看作一種互助性的民間金融組織。〔6〕參見王蘭等:《逐利的規制:民間借貸的法律機理與實務邏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頁。這種“標會”里的成員以一定順序輪流充當會主,享受資金使用權。然而,有些會主會以高息吸引他人進行“抬會”,在這種情況下,“標會”不再具有資金互助的性質,而成為個別人利用高利放貸從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平臺,“標會”因此成為高利放貸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結合體。
在1997年修訂刑法的時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得以順利入刑,《刑法》第176條設立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然而,高利貸是否入刑,卻是一個存在重大爭議的問題。1995年我國出臺了一系列金融法規,之后作為其刑事罰則,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同樣是被《商業銀行法》禁止從事的吸收公眾存款和發放貸款這兩項業務,《決定》只是設置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卻并未設立發放高利貸罪。1997年刑法修訂過程中,增設發放高利貸罪的呼聲較高。例如,有學者指出:“在當前的民間借貸關系中,一些不法分子置法律法規的規定于不顧,為了牟取暴利,將有益于社會生產、群眾生活,消化社會閑散資金的民間借貸變成剝削他人的高利貸行為。他們以高于國家規定的利息率幾倍,十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利率進行放貸,從中牟取暴利,‘高利貸’死灰復燃。”〔7〕陳正云主編:《金融犯罪透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頁。基于對其社會危害性的考慮,這些學者主張在刑法中設立發放高利貸罪,建議將發放高利貸罪的法條表述為:“違反金融法規,從事高利貸牟取暴利,情節嚴重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處罰金。”〔8〕趙秉志主編:《刑法修改研究綜述》,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91-492頁。然而,該《決定》沒有設立發放高利貸罪,1997年刑法也沒有設立發放高利貸罪。
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刑法設立了高利轉貸罪。根據該法第175條的規定,高利轉貸罪是指以轉貸牟利為目的,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高利轉貸給他人,違法所得數額較大的行為。這里的高利轉貸,是以套取金融機構資金為前提的,因而可以說是特定條件的高利貸入罪。當然,對于這里的高利標準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這里的高利是指高于金融機構同種貸款利率4倍以上。〔9〕參見曲新久:《金融與金融犯罪》,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頁。這里的4倍是根據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人民法院審理貸款案件的若干意見》所確定的民間借貸受司法保護的利率標準確定的。第二種意見則認為,高利轉貸是指將銀行信貸資金以高于銀行貸款的利率轉貸給他人。具體高出多少,不影響高利轉貸罪的成立。〔10〕參見周道鸞、張軍主編:《刑法罪名精釋(上)》(第4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頁。筆者贊同第一種意見,即高利轉貸罪并非一般的違反金融機構貸款使用的違法行為,而是利用金融機構貸款發放高利貸的行為,應當將高利確定為達到高利貸的程度。當然,在司法實踐中更為大家認同的是第二種意見。例如,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第52條規定:“從寬認定‘高利’轉貸行為的標準,只要出借人通過轉貸行為牟利的,就可以認定為是‘高利’轉貸行為。”雖然高利轉貸行為被規定為犯罪,但1997年刑法并沒有將發放高利貸的行為設立為犯罪。我國刑法存在非法經營罪之類的口袋罪,對某一行為刑法沒有規定為犯罪,并不等于在司法實踐中就不會被作為犯罪論處。如果要追究發放高利貸行為的刑事責任,在刑法沒有明確規定罪名的情況下,非法經營罪是一個兜底的罪名。因此,在司法實踐中還是存在將發放高利貸行為以非法經營罪入罪的案例。例如,涂漢江、胡敏非法經營案就是發放高利貸入罪的典型案例。
1998年8月至2002年9月,被告人涂漢江、胡敏為了牟取非法利益,或以賀勝橋公司、被告人涂漢江的個人名義,或假借中國農業銀行武漢市漢江支行及未經批準成立的武漢市江夏區工商聯互助基金會的名義,采取簽訂借據的形式,按月息2.5%、超期按月息9%的利率,以賀勝橋公司、被告人涂漢江的個人資金、被告人胡敏的個人資金先后向凌云水泥有限公司及龐達權等21家單位及個人發放貸款共計人民幣907萬元,并從中牟取利息共計人民幣114萬余元。本案爭議較大,經武漢市公安局層層請示,公安部在2003年4月8日發給湖北省公安廳的《關于涂漢江等人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行為性質認定問題的批復》中指出:“涂漢江等人或假借中國農業銀行武漢市某支行及未經批準成立的武漢市某區工商聯互助基金會之名,或用武漢市某貿易有限責任公司或個人的名義,以武漢市某貿易有限責任公司或個人資金,向他人非法發放高利息貸款的行為,屬于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1998年6月國務院發布施行的《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第22條規定:‘設立非法金融機構或者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涂漢江等人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數額巨大,其行為屬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項所規定的‘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應以涉嫌非法經營罪立案偵查。”這一批復征求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見。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給公安部經偵局的《關于涂漢江非法從事金融業務行為性質認定問題的復函》認為,高利貸行為系非法從事金融業務活動,數額巨大,屬于《刑法》第225條第4項規定的“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
武漢市江漢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涂江漢對外高息發放貸款,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情節嚴重,根據國務院發布的《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第22條的規定,應當追究被告人涂漢江的刑事責任。依照《刑法》第225條第4項之規定,判決被告人涂江漢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罰金人民幣200萬元。涂江漢不服一審判決上訴后,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除將涂漢江的處刑改為3年有期徒刑外,維持了一審判決的定罪。〔11〕參見鄧小俊:《民間借貸中金融風險的刑法規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143頁。
在該案中,法院將涂漢江等人的行為認定為高息發放貸款,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這里的高息發放貸款就是指高利放貸。值得注意的是,在將違法從事民間借貸活動以非法經營罪論處的案件中,除了本案是以高利放貸進行評價的以外,還存在以違規放貸進行評價的案件。例如,在邵某等人非法經營案中,公訴機關即認為,非法發放貸款屬于非法金融業務活動,被告人違法向社會不特定人員發放貸款,系從事非法金融活動,數額達300余萬元,非法獲益60余萬元,情節嚴重,構成非法經營罪。法院認定被告人違反國家規定,未經許可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構成非法經營罪。2010年11月26日,南京下關法院公開宣判:被告人邵某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罰金6萬元;被告人蔡某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2年,罰金4萬元。在該案中,司法機關認定邵某等人的行為是未經許可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即規違放貸。值得注意的是,高利放貸與違規放貸是不同的:違規放貸是指未經許可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至于發放的貸款是否屬于高利,在所不問;而高利放貸是指超過法律限制的利率標準發放貸款。因此,高利放貸與違規放貸的主要區別就在于高利放貸評價的是放貸的標準,而違規放貸評價的是放貸的資質。
該案在判決書中認定被告人涂漢江等的行為觸犯《刑法》第225條第4項,構成非法經營罪。《刑法》第225條第4項規定的內容是“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這是一個兜底條款,以往在司法實踐中一般都由各級法院自行決定其適用范圍。2011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準確理解和適用刑法中“國家規定”的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該《通知》第3條規定:“各級人民法院審理非法經營犯罪案件,要依法嚴格把握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的適用范圍。對被告人的行為是否屬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規定的‘其它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有關司法解釋未作明確規定的,應當作為法律適用問題,逐級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這一《通知》嚴格限制了《刑法》第225條第4項兜底條款的適用權限,對于限縮其范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通知》頒發以后,各級人民法院不能自行決定適用《刑法》第225條第4項。如果需要適用,則應當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在《通知》頒發一年以后,最高人民法院根據《通知》第3條的規定,對何偉光等人發放高利貸是否認定為非法經營罪的案件做了答復。
2012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關于被告人何偉光、張勇泉等非法經營案的批復》(以下簡稱《批復》),指出:“被告人何偉光、張勇泉等人高利貸的行為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但此類行為是否屬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相關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尚無明確規定,故對何偉光、張勇泉等人的行為不宜以非法經營罪處罰。”由此可見,鹽田區人民法院和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該案的無罪判決,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復》 做出的。該《批復》雖然是針對個案的,但其對處理同類案件具有參照價值。自此以后,我國司法實踐中再也沒有提起發放高利貸行為入罪的問題。可以說,《批復》直接給出了發放高利貸無罪的結論。
上述對發放高利貸行為不構成非法經營罪的刑事司法意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司法機關對民間借貸的謹慎和包容態度,也是對發放高利貸行為在刑法評價上的一個重大轉變。與之對應的是對民間借貸的民事司法意見,它涉及對民間借貸的民事法律保護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對民間借貸的利率加以規定,從而厘清對民間借貸的司法保護范圍。例如,198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22條規定:“公民之間生產經營性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于生活性借貸利率。”這一規定過于原則,只是一種傾向性規定,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1991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6條對民間借貸利率做出了明確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于銀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具體掌握,但最高不得超出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括利率本數)。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相對來說,這一規定將民間借貸以銀行同類利率的4倍為標準,劃分為司法保護的民間借貸和不受司法保護的民間借貸兩個部分,標準明確,便于適用。據此,不受司法保護的民間借貸大體上可以等同于高利貸。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該規定于2015年頒布,2020年已修訂)第26條規定:“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未超過年利率24%,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約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年利率36%,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效。借款人請求出借人返還已支付的超過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根據這一規定,對于民間借貸利率不再按照銀行貸款利率的倍數計算,而是直接按照民間借貸的年利率確定。其中,年利率未超過24%的,受司法保護;24%至36%的,不受司法保護;超過36%的,超過部分不僅不受司法保護,而且支持借款人要求出借人返還的訴訟請求。這一規定,顯然擴大了民間借貸受司法保護的范圍:年利率在24%范圍內的民間借貸屬于合法借貸,在24%以上的民間借貸屬于高利貸,不受司法保護。由此可見,民事司法對民間借貸采取了一種保護立場。我國學者對司法機關與行政機構對待民間借貸的態度做了比較,由此得出結論:司法機關對民間借貸的態度由嚴苛到有所放寬,而我國行政機關對民間借貸的態度主要還是排斥、反對、限制沒有資質的主體從事金融業務活動。〔12〕參見王蘭等:《逐利的規制:民間借貸的法律機理與實務邏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8頁。也就是說,在某個時期,司法對民間借貸的寬容態度與金融監管部門對民間借貸的嚴苛態度之間形成鮮明的對照,而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對具有發放高利貸性質的民間借貸則始終采取非犯罪化的立場。
三、高利放貸的變相入罪
高利放貸以非法經營罪論處的路徑被最高人民法院《通知》堵死后,發放高利貸行為沒有了入罪之憂,而且24%以下的利息受到司法保護,這刺激了現實生活中民間借貸的大肆泛濫。其中,大多數民間借貸都是以公司或者個人名義從事高利放貸活動。前些年隨著金融管制的逐漸放開,對小額貸款公司和典當行的設置管控也有所放松,因而各地成立了各種小額貸款公司和典當行。其中,小額貸款公司具有融資的主體資質,典當行同樣具有融資的性質,因此被確定為金融機構。這些機構在經營活動中存在某些違法行為,主要表現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高利轉貸和高利放貸等情形。除了以這些金融機構的名義從事的高利放貸行為外,還存在大量以非金融機構的名義從事的高利放貸行為。這些人員設立各種并無融資資質的公司,以民間借貸或者小額貸款的名義從事高利放貸活動。例如,從2016年3月開始,陳寅崗等人成立衡燊公司,對外以小額貸款公司的名義招攬生意,但衡燊公司實際上并未取得金融許可證,沒有發放貸款的資質。在日常高利放貸業務中,陳寅崗等人一般以“行業規矩”“保證金”等名目誘騙被害人簽訂金額虛高的借款合同、租賃合同等,并以俞果個人名義與被害人簽訂上述合同,以制造個人民間借貸假象。
除了傳統的以民間借貸形式發放的高利貸以外,利用網絡借貸平臺從事高利放貸的活動也十分普遍。傳統中的高利放貸都發生在熟人之間,即使借款人是陌生人,也會要求有熟人提供擔保,否則不會出借。因為熟人之間的借貸放貸人不僅對借款人的經濟狀況或者經營狀況有真實掌握,更為重要的是能夠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催收借款的效率。然而,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網絡借貸平臺逐漸興起。網絡借貸完全是一種陌生人之間的借貸關系,而且沒有任何擔保和合法催債手段。在這種情況下,網絡借貸的實際利率大大高于其他借貸形式。例如,2017年6月以來,犯罪嫌疑人虞某云組織人員假借網絡借貸平臺名義,發布“低利息、無擔保”等虛假信息,誘騙借款人到平臺借款,借款時索取身份信息及手機通訊錄和通話記錄,放貸時直接扣除30%“砍頭息”,要求借款人償還全款,借款人無力償還時,對借款人以及借款人通訊錄中的親友、同事采用侮辱性語言、PS圖片等軟暴力方式進行催收,迫使受害人交納高額“逾期費”。自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該團伙對913萬余人次實施“套路貸”犯罪活動,涉案金額數億元。在本案中,借貸利息高達30%,而且借期很短,有的只有一周時間。至于催收方式,就是利用借款人的照片或者通訊錄中親友、同事的電話號碼,采用各種侮辱人格的方法進行催收。
由于發放高利貸不構成非法經營罪的司法規則的確立,發放高利貸行為不能直接入罪。而在發放高利貸過程中存在民事欺詐,甚至個別設置借貸陷阱騙取他人財物,以及采用暴力或者威脅手段催討高利貸債務,觸犯非法拘禁、尋釁滋事等罪名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以打擊套路貸為名治理發放高利貸活動成為一時之選。套路貸案件最初發生在上海、浙江等地,典型的套路貸是采用欺詐手段設立虛假債務,并使用暴力和威脅手段實現虛假債務,因而這個意義上的套路貸具有詐騙的性質。其中,較早涉及套路貸的規范性文件是2018年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該《指導意見》對套路貸現象做了描述。值得注意的是,《指導意見》并沒有直接采用套路貸的概念。《指導意見》第20條規定:“對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假借民間借貸之名,通過‘虛增債務’‘簽訂虛假借款協議’‘制造資金走賬流水’‘肆意認定違約’‘轉單平賬’‘虛假訴訟’等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財產,或者使用暴力、威脅手段強立債權、強行索債的,應當根據案件具體事實,以詐騙、強迫交易、敲詐勒索、搶劫、虛假訴訟等罪名偵查、起訴、審判。對于非法占有的被害人實際所得借款以外的虛高‘債務’和以‘保證金’‘中介費’‘服務費’等各種名目扣除或收取的額外費用,均應計入違法所得。對于名義上為被害人所得、但在案證據能夠證明實際上卻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后續犯罪所使用的‘借款’,應予以沒收。”考慮到《指導意見》是一個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的指導性文件,在該文件中規定套路貸,意味著對套路貸的打擊被納入掃黑除惡的范圍內,這對懲治套路貸犯罪帶來深遠影響。及至2019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聯合發布《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正式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對套路貸作了規定。其中涉及的“套路貸”的常見犯罪手法和步驟,筆者在此做逐一分析。
(一)制造民間借貸假象
制造民間借貸假象是套路貸構成詐騙罪的核心要素,也就是設立虛假債權。詐騙罪首先必須具備詐騙行為,在刑法教義學中,所謂詐騙行為就是指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致使他人產生錯誤認識。這是詐騙罪的本質特征,如果沒有詐騙行為就不可能成立詐騙罪,而詐騙罪是套路貸犯罪的主罪,很難想象沒有詐騙罪的套路貸犯罪。因此,在認定套路貸犯罪的時候,應當將套路貸中的放貸行為與民間借貸中的放貸行為加以區分。套路貸犯罪是借用民間借貸的名義實施的,因而如何將套路貸與民間借貸,尤其是高利貸加以區分,始終是司法認定中的難點問題。筆者認為,套路貸不同于高利貸(民間借貸),二者區分的實質在于:套路貸是以民間借貸為名,而實際上實施詐騙;而民間借貸則是基于借貸雙方的真實意愿所發生的借貸關系。是否存在真實的借貸關系,就成為套路貸與民間借貸相區分的關鍵之所在。如果存在真實的借貸關系,即使在放貸過程中存在欺詐行為,也不能認定為詐騙罪。反之,如果根本就不存在真實的借貸關系,或者借貸數額很小,只是用作引誘他人的手段,以此進一步利用民間借貸實施詐騙行為的,則應當認定為套路貸詐騙罪。
(二)制造資金走賬流水等虛假給付事實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照虛高的“借貸”協議金額將資金轉入被害人賬戶,制造已將全部借款交付被害人的銀行流水痕跡,隨后便采取各種手段將其中全部或者部分資金收回,被害人實際上并未取得或者完全取得“借貸”協議、銀行流水上顯示的錢款。從形式上來看,虛假資金流水正是虛設債權的手段。然而,對此不能一概而論。虛假資金流水確實可能成為虛設債權的手段,但虛假資金流水只是一種現象,并不能得出只要存在虛假資金流水就必然構成套路貸詐騙罪的結論。虛假資金流水是在借貸人知情并且配合下形成的,其目的是掩蓋超出司法保護的高息。就此而言,在借貸人配合下的虛假資金流水具有客觀上的欺騙性,但其欺騙對象不是借貸人,而是第三人。例如,約定的借款年利率是36%,因為超出了24%的部分而不受司法保護,為了掩蓋不法高息,借款憑證記載的借款數額較高,而借款人實際收到的借款數額較小。為了消除這個差額,就需要在借款人收到較高的借款數額以后,將其中差額部分退還給出借人,由此形成虛假資金流水。如果出借人在借款人不能歸還欠款的情況下,以20%年利率的借款憑證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就可以受到司法保護。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存在虛假資金流水,但并不存在對借款人的欺騙,而是在民事訴訟中欺騙法院,因而構成虛假訴訟罪,并不構成套路貸詐騙罪。
(三)故意制造違約或者肆意認定違約
故意制造違約或者肆意認定違約是指,出借人和借貸人事前約定高額違約金,如果沒有違約,則借貸人就不用支付這部分高額違約金。在某些案件中,出借人設置違約陷阱,制造還款障礙,故意造成借款人違約,或者肆意認定違約,強行索取高額違約金。在這種情形中,如果借貸關系真實存在,則故意制造違約或者肆意認定違約并強行索要高額違約金的行為,具有一定的敲詐勒索性質。但在這種情況下,不能否認真實借貸關系,因而不能構成套路貸詐騙罪。
(四)惡意壘高借款金額
惡意壘高借款金額是指,當被害人無力償還時,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安排其所屬公司或者指定的關聯公司、關聯人員為被害人償還所謂借款,繼而與被害人簽訂金額更大的虛高借貸協議或相關協議,通過這種轉單平賬、以貸還貸的方式不斷壘高債務。惡意壘高借款金額是否構成詐騙罪,關鍵在于其中是否存在虛高的事實。所謂虛高是指超出事前約定的利息,在借款人不知情的情況下擅自增加借款金額。如果沒有這種虛增借款金額的事實,而只是轉單平賬或者以貸還貸,還不能認定為套路貸的詐騙行為。轉單平賬是指將未能歸還的本金和利息重新簽訂借款協議,以此結束上一輪的借貸關系,形成新的借貸關系。而以貸還貸是指采用貸新還舊的方式,延展借貸關系。上述兩種操作在民間借貸中都十分常見,不能直接將這種操作方法認定為套路貸詐騙行為。只有當存在虛增借款金額的事實時,才能認定為套路貸詐騙罪。
(五)軟硬兼施索債
在借款人不能按時歸還借款的情況下,索要債務是行使債權的行為,即使在索要債務過程中采取了違法犯罪手段,也只是該手段觸犯了刑法的其他相應罪名,而不能由此將真實存在的借貸關系認定為套路貸詐騙罪。只有在行為人采取非法手段索取虛高的所謂債務,行為人借助訴訟、仲裁、公證或者采用暴力、威脅以及其他手段向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特定關系人索取虛高債務時,才能在其行為構成套路貸詐騙罪的前提下,對上述索債行為所構成的其他罪名進行定性。這是套路貸的虛假債權實現行為構成的犯罪,由此與虛設債權行為的套路貸詐騙罪形成犯罪組群。也就是說,非法索債構成套路貸犯罪是以虛設債權行為構成詐騙罪為前提的,前者具有對后者的依附性。
以上五種套路貸犯罪手法中,第一種手法和其他四種手法明顯不在同一個層面上。其中只有第一種情形具有詐騙性質,其他四種手法雖然表面上似乎具有欺騙性,但都只有在虛設債權的前提下才能構成套路貸犯罪。
四、高利放貸的正式入罪
在懲治套路貸犯罪的背景下,雖然刑法沒有將高利放貸設立為犯罪,但司法實踐卻以詐騙罪對高利放貸行為進行了刑事處罰。在此,存在名與實之間的嚴重脫節。也就是說,因套路貸犯罪完全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而成立詐騙罪的案例是個別的,大量的套路貸犯罪都是以發放高利貸行為入罪,因而是在詐騙的罪名下對高利放貸行為進行刑事處罰。在筆者看來,這種做法本身是有悖罪刑法定原則的。值得注意的是,從2019年開始,我國調整了對高利放貸的民事司法政策。例如,2019年11月,《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第53條規定:“未依法取得放貸資格的以民間借貸為業的法人,以及以民間借貸為業的非法人組織或者自然人從事的民間借貸行為,應當依法認定無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間內多次反復從事有償民間借貸行為的,一般可以認定為是職業放貸人。民間借貸比較活躍的地方的高級人民法院或者經其授權的中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制定具體的認定標準。”此外,2020年修訂的《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2020年規定》)將未依法取得放貸資格的出借人,以營利為目的向社會不特定對象提供借款的,規定為人民法院應當認定民間借貸合同無效的情形,從而排除在司法保護之外。這種未依法取得放貸資格的出借人,以營利為目的向社會不特定對象提供借款的人,被稱為職業放貸人。根據《2020年規定》,職業放貸人的放貸行為不受司法保護,這使得民間借貸的范圍極度萎縮。因為民間借貸的經營性放貸,基本上都是專業放貸人所從事的放貸行為。因此,職業放貸人的放貸行為不受司法保護無異于禁止民間借貸。此外,我國司法解釋還對民間借貸利率進行了重大修改。202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修改〈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的決定》將借貸利率保護的上限規定為“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的四倍”,超過此標準的即為高利貸,不受民法保護。由此,民間借貸的利率重新回歸到以一定的倍數作為認定依據,只不過從銀行利率的倍數改為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的倍數,遠低于民間借貸24%年利率的標準,因而使民間借貸的司法保護范圍大為限縮。
在政策調整的基礎上,201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正式出臺《關于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二)》),該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將實際年利率超過36%的職業放貸行為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最終實現了高利貸入刑。《意見(二)》第1條規定:“違反國家規定,未經監管部門批準,或者超越經營范圍,以營利為目的,經常性地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發放貸款,擾亂金融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項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這一規定為處罰高利放貸行為提供了法律根據。當然,發放高利貸行為的犯罪化是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實現的,但如果采用刑法設立獨立罪名的方式也許更好。從2012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對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何偉光等人非法經營案之請示作出的批復到此次《意見(二)》規定高利放貸行為以非法經營罪論處,高利放貸行為的刑事政策發生了重大改變。根據《意見(二)》的規定,高利放貸行為以非法經營罪論處的構成要件包括以下四個要素。
(一) 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
高利放貸行為以非法經營罪論處,而非法經營罪屬于法定犯,其前置條件就是違反國家規定。在《意見(二)》出臺之前,雖然刑法和司法解釋都沒有將高利放貸行為規定為犯罪,但這并不意味著高利放貸行為是合法的。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已經將高利放貸規定為違法行為。例如,《民法典》第680條規定:“禁止高利放貸,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這是我國在法律中首次明確禁止發放高利貸。此外,1998年7月13日國務院《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以下簡稱《辦法》)第4條規定: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擅自非法發放貸款是《辦法》所稱的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可見,高利放貸行為具有違反國家規定的構成要件要素,該要素可以稱為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
(二) 客觀構成要件要素
未經監管部門批準,或者超越經營范圍從事高利放貸活動是高利放貸構成非法經營罪的客觀構成要件要素。其中,可以分為兩種情形:第一種是未經監管部門批準從事高利放貸活動,即未取得貸款發放資質的個人或者組織,擅自從事高利放貸活動;第二種是超越經營范圍從事高利放貸活動,即雖然具有金融從業資質,但超越其經營范圍從事高利放貸活動。
(三) 主觀構成要件要素
以營利為目的是高利放貸構成非法經營罪的主觀違法要素。非法經營罪本身就是目的犯,借貸的目的是獲取利息。因此,借貸活動是一種營利性的金融活動,出借人主觀上具有營利目的。
(四) 罪量要素
高利放貸構成的非法經營罪必須達到一定的數量條件才能以犯罪論處,否則就是一般的金融違法行為。這里的構成犯罪的數量條件,就是罪量要素。根據《意見(二)》的規定,本罪的罪量要素包括三項。第一,經常性地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發放貸款,即2年內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單位和個人)以借款或其他名義出借資金10次以上。如果只是偶爾向他人發放貸款,則不構成本罪。第二,以超過36%的實際年利率實施符合該意見第1條規定的非法放貸行為。構成本罪不僅要求經常性地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發放貸款,而且還必須是以超過36%的實際年利率發放貸款,因而這是一種高利貸。在認定年利率的時候要注意,根據《意見(二)》的規定,應當按照實際年利率而非名義年利率計算。因此,非法放貸數額應當以實際出借給借款人的本金金額認定。非法放貸行為人以介紹費、咨詢費、管理費、逾期利息、違約金等名義和以從本金中預先扣除等方式收取利息的,相關數額在計算實際年利率時均應計入。如果年利率沒有達到36%,則屬于一般的民間借貸,尚不構成本罪。第三,具備上述條件的,還要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根據《意見(二)》的規定,情節嚴重是指:(一)個人非法放貸數額累計在200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放貸數額累計在1000萬元以上的;(二)個人違法所得數額累計在80萬元以上的,單位違法所得數額累計在400萬元以上的;(三)個人非法放貸對象累計在50人以上的,單位非法放貸對象累計在150人以上的;(四)造成借款人或者其近親屬自殺、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嚴重后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