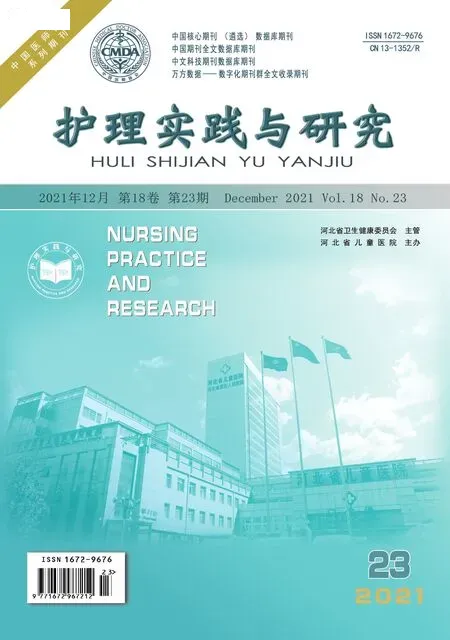Padua血栓評估模型臨床使用現狀及分析
余靜 田鵬 李玲
靜脈血栓栓塞癥(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包含深靜脈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和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 PE),它是指由于各種原因血管內的血液發生凝結,使血管部分或全部堵塞的疾病。DVT和PE是一種疾病的兩種不同階段,即患者發生DVT后,血栓脫落造成PE,PE作為DVT的并發癥,往往使患者病情復雜、兇險,可使患者突發死亡。在心血管性疾病中,VTE發生率排在第三位[1], 僅低于急性冠脈綜合征和腦血管意外。國內一項調查[2]表明VTE的發生率為2.5%,比國外報道的0.1%~0.9%更高,同樣高于亞洲人群發病率0.006%~0.02%。另一項流行病學調查顯示2007—2016年我國90家醫院住院病患VTE發病率呈升高趨勢[3],VTE具有高發病率、高病死率,且可預防的特點,因此早期及時準確評估和規范診療變得至關重要[4]。由于VTE受種族、生活方式、疾病譜的影響,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有適合他們自己的風險評估工具及診療指南[2],常見的主要有 Padua評分[5]、Geneva評分[6]、Caprini評分和Wells 評分[7]等。美國胸科醫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 ACCP)推薦使用Padua評分對內科住院患者進行VTE風險評估分層[8]。《中國血栓性疾病防治指南》2018版中亦建議使用Padua血栓評估模型測評內科住院患者VTE的發生風險[9]。本文就Padua血栓評估模型的使用現況進行綜述。
1 Padua血栓評估模型介紹
Padua血栓評估模型是2010年Barbar[5]在Kucher等[10]評分基礎上提出的一個新的風險評估模型,該模型共有11個危險因素,包含活動性腫瘤、既往VTE病史、近期(≤1月)創傷或手術、年齡和血栓傾向等,每個危險因素賦值1~3分,總分20分,根據評估得分將其分為低危(<4分)和高危(≥4分)[11]兩個危險度。Barbar使用該模型在1180例內科病患中進行了單中心的前瞻性研究,其中39.7%的患者被歸類為血栓形成的高風險,在高風險人群中,未采取血栓預防措施的患者VTE的發病率為11.0%,接受預防措施的患者中僅有2.2%出現VTE,由于采取充分的預防措施(藥物、機械預防),VTE事件的發生率降低了80%以上,而因預防相關引起的出血率僅為1.6%[5],收益遠高于風險。可見這一模型的建立,為臨床有效識別VTE高危患者提供了簡便、安全、有效的方法。
2 Padua血栓評估模型的應用
Padua血栓評估模型適用人群廣,臨床可操作性強,在國內患者中進行了較多驗證[12]。有研究[13]表明采用Padua血栓評分篩選VTE高風險住院患者的特異度高,對內科住院患者VTE的預測價值高。代俊利等[11]應用不同評估模型分別評價住院腫瘤患者深靜脈血栓形成的預測價值,結果顯示血栓組Padua、Caprini和Wells 模型所得評分均明顯高于對照組,Padua量表曲線下面積AUC 0.87±0.02最高,表明其在預測腫瘤住院患者VTE方面價值最高,這與張新娣等[14]的研究結果一致。李巍等[15]采用Padua血栓評估模型預測腦卒中并發VTE的效能,受試者工作曲線ROC顯示,當Padua血栓評估模型風險分層界值為4分時,AUC為0.762,提示Padua血栓評估模型對急性腦卒中后是否并發VTE風險具有較好的預測價值。這與Zhou等[16]、單淑慧等[17]、楊如等[18]等研究結果一致。VTE的形成條件包括血液淤滯、高凝狀態和血管壁損傷[19],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由于全身炎癥反應,組織缺血、缺氧導致血管內皮損傷及組織因子釋放,從而激活外源性凝血通路,促使血栓形成[20]。有研究[21-24]報道新冠病患中有20%會出現凝血功能障礙,且在危重癥患者中D-二聚體升高的占比更高,COVID-19患者為VTE的高危人群。高偉等[20]對212例COVID-19中PADUA評分≥4分的46例(其中22例合并VTE)患者進行研究分析得出Padua血栓評估模型能對血栓危險進行有效分級,Padua評分≥6分(AUC 0. 938,敏感度為63. 6%,特異度為95.8%對COVID-19患者的診斷有較高的特異性,較高的PADUA評分亦與COVID-19患者的院內預后不良相關[25]。PADUA血栓評估模型用于慢阻肺患者[26-27]、重癥患者[28]、老年患者[29]VTE風險研究取得相似結果。而在對糖尿病患者測評VTE風險的研究[4,30]表明Padua模型測評內科住院2型糖尿病患者發生VTE的效能較差,該評分沒有修正的Geneva評分、Wells 評分預測價值高,他們認為可能是PADUA評分系統不包含高血糖、高血脂、低蛋白血癥等2型糖尿病患者易合并的常見的VTE危險因素。而劉志英等[31]在2型糖尿病患者急性肺血栓栓塞癥的預測價值研究中卻表明Padua量表預測價值高于修正的Geneva評分,與Wells PE評分的預測價值相當;但3種評分預測價值有限。
3 PADUA評估表應用局限
世界范圍內使用的大多數VTE風險評估模型都是通過專家共識或回歸分析得出,以識別風險因素,并且都存在一個或多個缺陷。雖然PADUA血栓評估模型在內科住院患者中應用廣泛且有較高的應用價值,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該模型在臨床應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
3.1 危險等級劃分欠準確
有學者表示Padua評分對住院患者VTE的危險分層效果不理想、難以有效預測VTE的發生,PADUA評估表目前將危險度分層為低危(<4分)和高危(≥4分),在腫瘤、癱瘓等高危人群中,使用PADUA預測模型進行測評時,大部分患者評分大于等于4分,對于這樣的高危患者不能再進行具體劃分,從而可能造成治療過度。Vardi等[32]在1080例膿毒血癥患者中對該量表進行驗證,其中高危患者占71%,未采取預防措施下癥狀性VTE發病率為1.24%。在王欣等[2]的研究中也證實該模型的敏感度較好, 但特異度不高, 導致部分較低VTE風險患者被劃分至高危組,若依據指南積極預防,勢必會增加出血等不良事件。周冰榮等[3]將159例內科PTE患者納入研究, 使用PADUA量表對該159例患者進行評估,結果顯示Padua量表低危組(90例, 56.6%) 的PTE患者反而多于高危組(69例,43.4%) ,與理論結果不一致。
3.2 危險因素及權重分配不合理
VTE與種族背景和疾病譜密切相關,由于不同的人群特征和疾病譜, 會產生偏倚, 而且在人種、體質、生活習慣、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別, 故PADUA評分中的危險因素并不完全適合于我國, 在國內應用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33]。
3.2.1 危險因素較少 PADUA模型包括11個危險因素,其中雖已包括心臟衰竭、呼吸衰竭、心肌梗塞、腦卒中、感染、風濕性疾病等疾病因素,但中國已進入高齡社會,在內科住院患者中,特別是老年患者多病共存日益突顯,如伴有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高血脂等,可導致靜脈血栓形成的風險增加[34]。有研究[35-37]顯示高血壓是中老年病患發生VTE的主要原因。此外,中心靜脈置管、抗腫瘤治療、機械輔助通氣、永久性起搏器置入等在內科住院患者中是很常見的診療措施,李積鳳等[38]的研究指出中心靜脈置管等以上治療措施能夠增加VTE患病風險,危險因素與患病風險呈正相關。有Meta分析[39]亦顯示年齡、長期臥床、中心靜脈置管、1月內大手術史、惡性腫瘤、嚴重的肺部疾病、心力衰竭等是我國內科住院患者發生VTE的主要常見危險因素。而PADUA模型并未包括以上所有國內患者發生VET的常見危險因素,模型中危險因素偏少。此外,李金玉等[28]在其病例對照研究中發現女性VTE 的發病率(56.6%)高于男性(34.1%),這與國內其他研究有差異,但與國外研究結果相似,故還需進一步研究。
3.2.2 危險因素定義不夠明確及權重分配欠合理PADUA評估模型中激素治療該條目未明確給出是雌、孕激素還是糖皮質激素,故在使用PADUA血栓評估模型測評時有一定選擇偏倚。另外國內相關研究[2-3]得出肥胖與預測VTE風險無關,且西方國家肥胖標準為30,而亞洲國家以此為標準的肥胖發病率低[40],使用該量表不一定能高效識別我國VTE高危人群。韓國的一項研究修改了肥胖的定義,認為體質指數≥25為肥胖,修改后識別高危患者的比例由87.8%上升到92.9%。此外,該模型包含易栓癥、蛋白S或C缺乏、Leiden v因子、凝血酶原G20210A突變等非我國患者常規檢查項目,且相應疾病我國患者發生率極低,此條目對于我國患者形同虛設,且權重達到3分,故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該量表測評準確性[2,13,35]。Padua量表中的危險因素賦值權重比基于西方人數據建立,其中活動性惡性腫瘤/化療這一因素權重為3分, 而在王欣的研究中血液科和腫瘤科患者這一危險因素非常常見, 致使這兩個科室高危患者占比較高, 雖然這兩個科室的VTE預防率較低, 但癥狀性VTE發病率并不高, 提示該模型可能過高估計了活動性惡性腫瘤/化療的權重, 權重分布并不完全適用于我國人群[2]。
4 小結
VTE臨床發病隱匿,癥狀不顯,易造成漏診、誤診,盡早識別患者院內發生VTE的危險因素對于預防其發生具有重要意義。目前國外對于VTE風險評估模型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而國內研究起步較晚,臨床大都直接搬用國外的預測模型使用,Caprini評估表主要用于外科住院患者,而內科住院患者VTE的測評使用Padua評估量表,該量表在評估腫瘤、重癥、呼吸、老年、新冠患者VTE風險有一定價值,經采取預防措施可以降低患病率,但在實際使用中,亦發現該量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準確評估VTE風險,造成預防不足或者治療過度。VTE發生率與種族背景和疾病譜密切相關,該量表基于西方人群數據建立,其中某些條目如Leiden v因子、凝血酶原G20210A突變在我國人群發病率極低,另按此模型肥胖的標準,國人肥胖發生率亦低下;且活動性惡性腫瘤/化療這一條目的權重分配欠合理,從而影響測評準確性。PADUA評估表雖操作簡單,臨床醫務人員可操作性強,但其危險因素偏少不能真正有效識別我國高危人群,此外還有學者[41]認為VTE發生率差異的另一種可能的解釋可能是由主治醫師進行的風險評估不正確,在PADUA量表的所有11個變量中,行動不便是唯一的主觀變量(可能會被錯誤地評估),且此變量權重為3分。因此臨床應用PADUA量表時應根據不同病種患者特別是VTE高危人群的疾病特征,增加相關疾病特有的危險因素,并根據不同評定等級制訂更為詳細、更具指導意義的預防方案。
綜上所述,VTE與種族背景和疾病譜密切相關,中國人與西方人在疾病風險評估方面有所不同。因此,找到潛在的VTE危險因素并開發專門針對中國住院患者的預測模型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