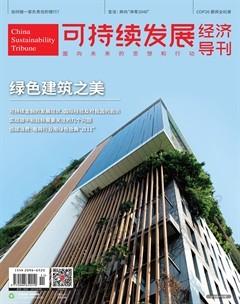以跨部門合作視角看中國生物多樣性對外援助
孫天舒

2021年10月,中國作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會議(COP15)東道國在云南承辦了第一階段的會議。會上,習近平主席宣布,中國將率先出資15億元人民幣,成立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支持發展中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中方呼吁并歡迎各方為基金出資。這一承諾使中國受到廣泛贊譽,也為COP15通過和實施一個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注入了信心。這體現了中國將生物多樣性視為對本國和全球各國攸關的重要戰略性議題,說明面對以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環境惡化為代表的共同危機,各國更需要攜手應對,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從“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的功能描述來看,其類似于中國在南南合作框架下開展對外援助的專項基金。中國生物多樣性援助于近十年才逐步開展,有援外主管部門、援外執行部門、地方政府、科研院所等多方參與,是中國對外援助工作跨部門合作的一個縮影;但同時也存在著雖“多點開花”但尚未納入援外工作“一盤棋”的問題。本文將通過跨部門合作的視角觀察中國的生物多樣性援助,以期為中國未來提升生物多樣性領域的南南合作提供有益參考。
對外援助中的跨部門合作
對外援助是中央事權,是服務中國開展大國外交、深入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因此需研判全球發展重大問題和熱點議題。落實到具體工作中,即是雙邊援助項目如何服務受援國在相關議題上的發展需求,以及多邊援助如何支持多邊機構(例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等聯合國專門機構)在相關議題上的工作。
為此,負責對外援助總體規劃和項目立項的援外主管部門(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和負責各領域事務的援助執行部門(商務部、農業農村部、生態環境部等)需緊密合作,援外執行部門需輔助主管部門做好“議題規劃”,援外主管部門需在涉及到對受援國某領域提供援助資金時,征求執行部門的意見。
在對外援助中提升跨部門合作,將專業部委對援外工作進言獻策機制化、常態化,有利于吸取相關部門長期跟蹤專業領域國際磋商談判、開展交流合作沉淀的經驗和認識,使援外項目主題更能回應國際社會關切問題、展示中國發展成果,項目設計和評估系統更體現科學性和發展性,使援外工作有力提升中國在國際議題引領和多邊機制構建中的影響力。因此,跨部門交流合作的順暢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生物多樣性對外援助可調動的資源和“施展拳腳”的空間。
生物多樣性援助在當前中國對外援助總體工作中形式新、占比小,卻是當前中國對外援助多方參與、跨部門合作的集中體現。透過生物多樣性援助之“管”,亦可一窺中國對外援助之“豹”。
多方參與的中國生物多樣性對外援助
中國的生物多樣性對外援助脫胎于林業部門的人力資源開發合作對外援助。伴隨著中國加入多個全球環境公約,林業援助逐漸納入了荒漠化治理、瀕危野生動物保護監測、生物安全等議題,生物多樣性援助也隨之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尤其在2010年之后項目數量大幅增加——從援助蒙古保護“國熊”戈壁熊種群和棲息地,到為肯尼亞野生動物保護部門提供防偷盜獵設備、建設致力于動植物多樣性研究的中-非聯合研究中心,再到連續若干年開設主題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培訓班。
當前,在生物多樣性這個議題下開展對外援助的國內部級單位至少有7家,包括但不限于:
(1)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和商務部(2018年4月18日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揭牌前)提供了對外援助資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支持了包括“發展中國家野生動植物保護管理與履約官員研修班”、援肯尼亞“中非聯合研究中心”、援納米比亞、肯尼亞“野生動物保護物資”等項目。
(2)生態環境部、林業草原局在內的“專業部委”深入參與援外項目立項意見和組織實施,下屬林業科學院、林業管理干部學院等機構長期承辦人力資源開發合作和技術合作援外項目,包括“發展中國家荒漠化防治和生態修復技術培訓班”“蒙古國戈壁熊技術援助項目”等。
(3)外交部通過“瀾滄江-湄公河合作專項基金”支持了“瀾湄合作跨境亞洲象種群調查與監測項目”等項目。
(4)科技部通過“戰略性國際科技創新合作”重點專項支持了“向巴西提供竹子培育與高效利用技術”“中國-馬爾代夫椰子害蟲聯合研究中心”等項目。
(5)中國科學院承擔了“中-非聯合研究中心”等援外項目的后續運營工作,且建立了10個海外研究中心,其中部分涉及生物多樣性和物種資源保護利用工作。
(6)部分地方政府(如云南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的商務部門、環境部門和林草部門除執行中央委派的援外項目外,還自籌資金開展跨境野生動物保護工作,或建立面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技術合作中心,例如云南省支持了“云南省-老撾南塔省環境保護交流合作技術援助項目”等。
此外,中國還通過生態環境部和林業草原局對包括聯合國環境署、亞太森林組織、國際竹藤組織在內的國際組織提供捐款、指定用途基金,或建立信托基金,由上述國際組織對發展中國家開展生物多樣性相關工作提供資助。
“援外主管部門×援外執行部門”的多種形態和機制
援外主管部門和援外執行部門之間圍繞生物多樣性議題開展不同模式的合作,可以從不同角度回應外交和發展問題。
1.援外主管部門×外交部門——踐行親誠惠容、服務大國外交
開展生物多樣性對外援助,是從多個角度服務大國外交需求,至少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元首外交:開展生物多樣性援外是落實元首外交援助承諾,踐行國家領導人重要外交講話精神。近年來,習近平主席也多次就生物多樣性和生態保護問題在包括領導人氣候峰會、中法德領導人峰會、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如,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宣布“中非合作綠色發展行動”,承諾“為非洲實施50個綠色發展和生態環保援助項目”。
多邊外交:開展生物多樣性援助是以實際行動支持全球環境治理國際條約和多邊合作成果。中國是《生物多樣性公約》最早的締約國之一,一度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援助最大的受援國,是多邊環境治理體系的受惠者,如今也成為多邊環境治理體系的堅定支持者和貢獻者。
主場外交:《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是我國重要的主場外交活動,是集中體現我國在生物多樣性方面國際領導力、影響力和吸引力的平臺。與會各方對中國作為東道國將做出的表態、承諾和倡議寄予期待,尤其關注中國將如何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生態環境保護,其中,對外援助和其他出資承諾是重要內容。
周邊外交:中國生物多樣性援助項目大部分位于東南亞和南亞地區。中國與周邊國家山水相連、文化相通,向周邊國家提供生物多樣性援助,不僅是保護物種和棲息地,也是保護對周邊國家(尤其是邊境地區)人民的生計、文化、信仰至關重要的生境。此外,生物多樣性也與生物安全、跨境河流、野生動物跨境遷徙等敏感問題息息相關,需要相關部門分享信息、聯合研判。
2.援外主管部門×業務主管部門——提升援助專業性,回應全球公共議題
生物多樣性援助是典型的以議題為引領的援助,專業性強,熱點、重點、難點問題錯綜復雜,且超越環境科學范疇,與社會發展、公共衛生、生物安全等重大議題日益深入地交織。在處理此類援助時,援外主管部門需與業務主管部門充分溝通,聽取意見。
例如,對生物多樣性議題不熟悉的人,可能會認為生物多樣性保護就是保護野生動物,尤其是虎、豹、象等大型哺乳動物。“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框架”(預稿)制定了21個需要采取緊急行動的目標,包括但不限于保護至少30%的全球陸地和海洋、減少人與野生動物沖突、降低外來入侵物種引入率、減少各種來源的污染、對生態資源可持續管理和利用、增加城市綠地面積、公正公平分享遺傳資源和傳統知識惠益等。
援外主管部門也需要聽取業務主管部門關于中國在哪些領域具有比較優勢的意見,通過援外項目分享中國的成功經驗。例如,通過與十余位生物多樣性保護專家的交流,發現了中國在生態保護紅線制度、生態扶貧、山水林田湖草綜合治理、防沙治沙等多個領域都具有世界領先且被廣泛認可的技術和經驗。
3.援助主管部門×地方政府——發揮區位優勢,踐行親仁善鄰
邊境省份是中國與其他國家開展國際交流合作的橋頭堡,在跟蹤受援國動向、收集受援國需求、研提援助方案方面具備優勢條件,處于關鍵位置。邊境省份向鄰近發展中國家“對口”開展生物多樣性援助,是對中央政府主導的援助項目的有益補充。
當前云南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都開展了自籌資金開展跨境保護或建立國際技術合作中心的實踐,對傳統對外援助“央地合作”模式進行了創新和提升,除承接和協助中央部委立項的援外項目外,地方政府還參與了申請由中央部委或國際組織提供的專項資金開展南南合作項目、以省財政資金支持對外援助及面向周邊國家的援助和南南合作工作,為其他部門開展的生物多樣性南南合作項目提供政策支持與便利條件。例如,2015年中國科學院東南亞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依托中科院版納植物園在西雙版納成立,成為面向東南亞地區的國際科教中心。
4.援助主管部門×科研院所——提升援助可持續性,助力受援國人才培養
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一大特點是需與學術研究緊密結合。同理,在開展生物多樣性相關援助工作時,援助主管部門也需與相關研究部門協調合作,以保證援助的效果和可持續性。當前援助主管部門和學術研究部門主要開展兩種形式的合作:一是學術研究部門作為援外項目的實施機構,例如2016年中國林科院森環森保所經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推薦,受商務部委托,承擔中國援蒙古國戈壁熊保護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和實施工作,在蒙古國開展物種棲息地生態環境質量評價等工作。二是學術研究部門在援助項目實施后開展后續運營工作,例如中國援肯尼亞“中-非聯合研究中心”主體建筑移交后,由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園為中心運營提供技術支持,建設了非洲生物多樣性與利用分中心、非洲生態與環境研究分中心等5個分中心,與非洲8個國家的15個科研機構建立合作關系,使中-非聯合研究中心成為輻射非洲大陸的生物多樣性研究重鎮。
對外援助呼喚更緊密、通暢、高效的跨部門合作
2021年8月31日,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外交部、商務部聯合審議通過并公布了新版《對外援助管理辦法》,并自2021年10月1日起正式實施。新辦法的鮮明特點之一便是明確了國合署作為對外援助主管部門的戰略規劃和統籌抓總角色,以及與商務部、外交部等援外執行部門之間的協作機制和渠道。新辦法要求援外主管部門在包括“推進對外援助方式改革”“建立對外援助部際協調機制”“制定對外援助中長期規劃”等多項工作中行使統籌職責,并與援外執行部門通力合作;援外執行部門在項目立項、援外規劃等方面向員外主管部門提出意見,對外援助跨部門合作交流有望得到制度保障并顯著提升。
當前,中國對外援助正向國際發展合作轉型。2021年初發布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白皮書中,以前所未有的精細度介紹了中國國際發展合作對“落實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和“攜手應對全球人道主義挑戰”的貢獻。這反映出,伴隨著中國深入參與全球治理,中國對外援助將更加重視回應全球重大發展議題、回應受援國發展需求、踐行多方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
在這種轉型過程中,中國的對外援助工作要超越傳統的“援助國”和“受援國”的關系,中國援外主管部門的工作要適應全新的寬廣度、復雜度,適應飛速變化的世界局勢和不勝枚舉的新興議題,中國的對外援助方案要生動體現中國在一些具體議題上的豐富經驗和先進方案(如可再生能源、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電商扶貧、互聯互通等),展現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活力,增進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和中國經驗的認同感。這就需要通過提升對外援助的專業度、靈活度和針對性,將中國新時代發展的成就和經驗通過對外援助工作分享給發展中國家合作伙伴。在這個意義上,建立穩定又有活力的跨部門合作協調機制,是中國對外援助向國際發展合作轉型的基石,也是檢驗對外援助方式改革成果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