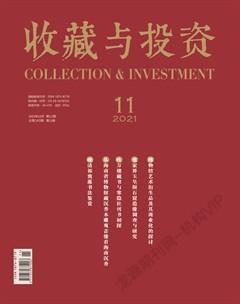兩周之際的微型青銅器與貴族生活
摘要:微型青銅器是指通高6~12厘米,寬7~13厘米,形體較小,但造型別致、紋飾精美的小型精致銅器,是兩周時期規制禮器之外的新器型,常被稱為弄器、玩器、看器。它們不僅用于把玩欣賞,還有一定的實用性,屬于盛儲類器皿。微型青銅器集中出現于兩周之際,從西周晚期晚段開始,到春秋早期大量出現,主要在山西、陜西、甘肅、河南、山東等地,其中晉陜豫交界處出土最多,甘肅東部偶見,山東南部器型自成特色,這些都反映了不同的區域文化特點以及地域、民族之間的交流狀況。兩周之際的微型青銅器,從其盛儲物、銘文及墓主的有關情況,也揭示了當時的貴族生活狀況。
關鍵詞:兩周之際;微型青銅器;弄器;貴族生活
兩周之際,大體上指西周晚期晚段、春秋早期及春秋中期前段,是一個革新的時代,是文化大融合前后兩大階段的重大轉變期[1],也是青銅器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這一時期,王室衰微,政權下移,各諸侯國既僭越禮制,又借禮制來維護自身權威,不斷地對傳統禮法進行改造和創新。社會結構和思想意識發生變化,形成不同的審美取向和文化認同,各種器物變得既新穎又貼近生活,裝飾風格更加強調藝術性和美學價值。于是兩周之際出現了規制禮器之外的新器型,微型青銅器就是其中之一。
一、兩周之際微型青銅器概況
微型青銅器是指通高6~12厘米,寬7~13厘米,形體較小,但造型別致、紋飾精美的小型精致銅器,是兩周時期規制禮器之外的新器型。其主要見于兩周之際,特別是春秋早期的山西、陜西、甘肅、河南、山東等地的20多座墓葬中,數量80余件。其中晉陜豫交界處出土最多,甘肅東部偶見,山東南部自成特色,反映了不同區域的文化特點,以及地域、民族之間的交流狀況,也為探尋當時的社會面貌提供了參考。
微型青銅器的類型主要有五種,分別是盒形器、罐形器、匜形鼎、鍑形器和異形器。其中,盒形器根據足部特征分為五種類型:人形足(圖一)、伏虎形足(圖二)、虎足夾輪、車形足(圖三)、方圈足。罐形器根據有無提鏈分為四型四式:穿帶罐、鏈式提梁罐、單把罐(又稱钅和)和仿陶銅罐,其中穿帶罐分為圈足式、無圈足式;鏈式提梁罐分“器蓋與器身均有環鈕式”和“只有器身有環鈕式”。匜形鼎根據足部特征分兩型兩式:三足型和圈足型,其中三足型又分“有流帶蓋”(圖四、圖五)和“有流無蓋”兩式。鍑形器分兩型,立耳有突和立耳無突型(圖六)。異形器主要有三足甕、鼎形器、舟形器。
在用途方面,一般認為微型青銅器相當于弄器、玩器、看器。考古發現,用途比較明確的是盒形器、罐形器,用來充當首飾盒或化妝盒;其他器型兼具水器、酒器、食器的作用,或為禮儀用器。
總體上,不同地域的出土器物特色不同。山西地區多車形或長方形銅盒、匜形鼎、鍑形器;陜西、河南地區多穿耳罐;山東地區則以提鏈罐為特色;甘肅、山東偶出方形盒。男性墓葬多為無圈足穿耳罐,女性墓葬多車形或長方形銅盒及圈足穿耳罐。
二、微型青銅器的盛儲物或銘文
五大類微型青銅器均屬于盛儲器,具有一定的實用性,有的兼有禮儀性質,或作為明器化的禮器。部分器物在出土時有盛儲物或銘文,為研究其具體功能提供了重要信息。
如晉侯墓地M63銅方盒,據簡報記述,出土時雖已銹蝕成粉末,但其內原盛滿各類小件玉器,分三層粘連在一起,有玉人、熊牛、鷹鸮和龜、罍等,且大部分為商代玉器[2](圖七、圖八)。同樣,虢國墓地M2012殘碎銅盒內有綠松石、料珠和煤精等組成的串飾一組[3],棗莊小邾國墓地M3“虎鈕方奩”內置有玉耳勺、玉玦、玉貝[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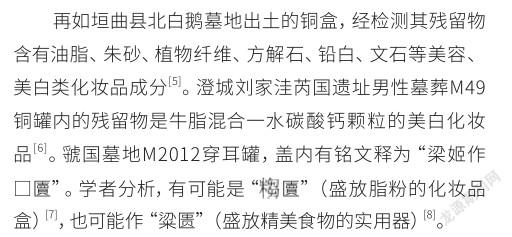
從出土文物可以看出,盒形器用來盛放小件玉器、梳妝用具或脂粉類化妝品等物,相當于古代的“奩”“櫝”“匱”這類盛儲器[7],而罐形器則用來盛放脂粉類化妝品或者糧食等物,相當于古代的“荷包”。
三、微型青銅器的使用者
在兩周之際,什么樣的人會使用這些微型青銅器呢?根據發掘簡報,墓主情況可考的有以下幾例。
(1)韓城梁帶村M26,墓主仲姜,也叫芮姜,即芮桓公夫人、芮伯萬之母。《左傳》記有芮姜事一則:“桓公三年,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有學者將墓葬所出的微型青銅器與山西聞喜上郭村的考古學文化相聯系,認為芮姜可能是由山西上郭村一帶嫁入芮國的女性[9]。
(2)晉侯墓地M63,墓主為楊姞或齊姜,即晉穆侯次夫人,文侯之母。若為楊姞,則是晉國北面的楊國之女,是楊國的最后一位公主[2]。若是齊姜,則是齊女[10]。
(3)三門峽虢國墓地M2012,墓主虢季夫人。根據出土梁姬罐,判斷墓主可能是姬姓梁國之女。又據同姓不婚原則,梁姬罐或許是梁國向虢國的助喪之物[11]。
(4)三門峽虢國墓地M1820,墓主虢姪妃。學者推測墓主人是嫁于虢國的己(妃)姓蘇國女子,字姪妃,名襄[12]。
(5)三門峽虢國墓地M1052,墓主虢太子,學者根據微型青銅器的伴出物,分析虢國太子可能是《周禮》中的“司烜氏”,生前可能是帶領族人用陽燧采擷天火、從事祭祀活動的人[13]。
(6)棗莊東江村小邾國M3,墓主秦妊或是媿霝,小邾國國君夫人。如為秦妊,則是魯國秦邑的任姓貴族之女[4]。如果是媿霝,則是郳犁來的母親,母邦為鬼方[14]。
(7)澄城劉家洼芮國遺址男性墓葬M49,墓主為士一級貴族。據墓中出土的銅鼎銘文:“大(太)師小子白(伯)□父乍(作)(尊)鼎,其萬年子(子子)孫永寶用之”[6]。可知墓主是芮國的樂官—樂大(太)師小子,是一般樂師,且這類樂師身份較低,有的甚至沒有貴族身份,和奴隸差不多[15]。
綜合來看,微型青銅器幾乎都出自貴族墓葬,所屬諸侯國也是當時頗有影響力的侯國。女性貴族多是諸侯國的宗女或大姓貴族女子,地位較高。
四、兩周之際微型青銅器反映的貴族生活
微型青銅器不僅用于把玩欣賞,也具有實用功能,是貴族階層標榜身份、地位、財富和族屬的隨葬品,它的出現離不開兩周之際社會的變革,標志著一種新的社會文化正在形成,有助于人們了解當時的社會生活。
(一)兩周之際的用玉情況
晉侯墓地M63銅方盒內所盛放的動物型玉器、玉人和仿銅禮器玉雕,小邾國墓地M3“虎鈕方奩”放置的小件玉器工具等,都展示了兩周之際的用玉情況。
周代玉器在禮制中被廣泛應用,此時也是我國古代用玉制度初步完善和發展的階段,玉器的類型、用途等方面在前代的基礎上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用玉觀念和用玉制度分多個層面,有禮儀用玉、喪葬用玉、裝飾用玉、生活用玉、玩賞用玉等。
兩周之際,社會變革,玉器使用也發生了變化。首先,宗法禮制束縛松動,玉器的使用少了一絲神秘色彩,實用性增強,玉器的風格從禮儀化向生活化進一步發展[16]。各種人形和動物形玉器,如玉人、龍、鳥、蟬、蛙、龜、魚等,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小件玉器工具,如玉梳、匕、玉耳勺(刀)等,作為日常生活用品。其次,人們越來越重視玉器的藝術價值和美學價值,佩玉成為玉器使用的主流,供日常佩戴與把玩的玉器逐漸增多。在商代具有神話傳說、祭祀和占卜意義的小件玉器如鷹、龜、熊等,到了兩周之際的墓葬中,也成了高等級貴族所喜愛的一般意義上的藝術品[17]。最后,西周晚期禮制對貴族女性在使用銅器上作出了限制,也使女性更偏向于可自由使用的玉器,因而女性墓葬中出土的玉器也較多。
兩周之際的用玉情況,表現為滿足人類愛美追求的裝飾玉、滿足生活需求的實用玉和具有藝術性的玩賞類玉器增多,說明從西周晚期開始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出現變化,人本思想受到重視,對美的世俗追求逐漸萌生。
(二)兩周之際的妝容風尚
微型青銅器中的銅盒、銅罐等器物,展現了早期化妝用具的樣式。它們制作精細,用工講究。有的銅罐、銅盒上留有絲帶、穿繩的痕跡,用于提攜;有的銅盒內發現搭配使用的銅勺,用來舀取膏狀或粉狀的化妝品。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先秦時代是我國古代化妝品的興起時期[18],此時已有潤膚、敷粉、施朱、點唇和沐澤等化妝方式。如《詩經》中的“手如柔荑,膚如凝脂”“豈無膏沐?誰適為容”,《戰國策》亦有“彼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的記載。另外,妝容也是當時的“婦學之法”,《周禮·內宰》中的“婦容”一詞,就是指宮廷女性的容顏禮儀等。
在考古發掘中,也能看出春秋早期女性所用的化妝品種類和成分已十分豐富,種類有脂、粉等,成分有植物精油、朱砂、方解石等。梁姬罐銘文表示罐內存放的是一種粉,即“濾取粉”,或為梁米制的粉英,用于涂抹皮膚,起美白、光潤的效果[7]。北白鵝墓地銅盒內殘留物含有植物精油成分,是古代售價昂貴、頗受歡迎的雪松醇、雪松烯精油。
最有意思的現象是,在周代,不僅女性用化妝品,男性也使用化妝品,而且男性最遲在春秋早期就開始使用面脂等潤膚品。劉家洼芮國遺址男性墓葬M49銅罐里殘留物為“面脂”。“脂”是動物體內或油料植物種子內的油,所以“面脂”是無色的,主要起防寒、保養皮膚的作用[19]。劉家洼遺址銅罐里的面脂是油脂加入無機粉體(一水碳酸鈣)制成,具有美白的功效。
兩周之際的妝容風尚反映出禮制社會的審美觀念。由于此時的化妝品中含有礦物成分,有學者認為這一點可能與先秦原始道教或方士采集、使用洞穴中的礦物有關,從側面說明當時貴族階層對各種思想的開明與包容。
(三)兩周之際的弄器潮流
“弄”,上從“玉”,下從“廾”,一般釋為“玩”。考古發現,弄器在商代晚期就已出現。兩周時期弄器之風較盛。“弄器”非祭器、明器,其稱謂一是源自器物上的“弄”字銘文,二是因器型小巧精致,適合手中把玩。有學者認為弄器與貴族的吃喝玩樂等奢侈享受行為有關[7],或是當時貴族舉行祭祀、宴饗等典禮所用的禮器,其用途可能與修德、敬德有關[20]。實際上,弄器也確實不只是把玩之物,還有更高層次的欣賞功效,符合當時青銅器從廟堂走向日常生活的發展特點[21]。
微型青銅器作為弄器的一種,不只是玩物、看器,還具有實用性和族屬、性別等意義,不僅滿足了貴族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也反映政治文化認同與凝聚力。微型青銅器的出現直接說明了周代貴族階層之間流行收藏、化妝的風氣,間接反映了兩周之際社會變革的主題—創新創造、復古繼承、融合禮制[1]。微型青銅器中的方盒形器、罐形器,是兩周之際的新器型,屬于創新創造;匜鼎、鍑形器則保持前代或非周部族人群的器物風格,是一種復古與繼承;這些微型青銅器雖有區域特點,但又包含周文化的共性,在遵循禮制的同時融入了地方的文化因素。
弄器幾乎都出自貴族墓葬,不僅是貴族的娛樂方式之一,還反映了新的社會文化正在形成。東周社會“以人為本、文雅風流、彬彬有禮”的思想文化,進一步提升了禮樂政治的審美意義,正如錢穆先生所說,春秋時代是中國古代貴族文化發展到一種極優美、極高尚、極細膩雅致的時代[22]。弄器潮流的背后是社會變動發展的趨勢。
基金項目
本文為山西博物院學術研究項目“兩周小型青銅器與相關問題研究”(項目編號:JBXS-2021-1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
王瑞,山西博物院館員,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史。
參考文獻
[1]劉延常,徐倩倩.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山東地區東土青銅器群的轉變與傳承[J].青銅器與金文,2017(1):323-339.
[2]李夏廷,張奎.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四次發掘[J].文物,1994(8):4-21.
[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虢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4]棗莊市博物館,棗莊市文物管理辦公室,蘇昭秀,等.棗莊市東江周代墓葬發掘報告[J].海岱考古,2011(1):141-152.
[5]楊及耘,曹俊,解宙鵬,等.山西垣曲北白鵝墓地出土銅盒[J].江漢考古,2021(2):38-45.
[6]王保平,趙汗青,張喜文,等.陜西澄城劉家洼春秋芮國遺址東Ⅰ區墓地M49發掘簡報[J].文物,2019(7):4-37.
[7]李零.說匵—中國早期的婦女用品:首飾盒、化妝盒和香盒[J].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3):69-86,160-161.
[8]查飛能.商周青銅器自名疏證[D].重慶:西南大學,2019.
[9]王洋.梁帶村芮桓公夫婦墓隨葬青銅器的性別觀察[J].考古與文物,2013(2):71-79.
[10]孫慶偉.晉侯墓地M63墓主再探[J].中原文物,2006(3):60-67.
[11]劉社剛.梁姬罐相關問題的思考[J].中原文物,2002(6):60-62.
[12]程曉丹.虢國墓地喪葬制度研究[D].開封:河南大學,2011.
[13]許永生.對虢國太子墓出土的銅弧面形器的研究[J].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3(1):53-55.
[14]袁俊杰,賈一凡.小邾國歷史文化的考古學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
[15]陸璐.說周代的太師[J].史學月刊,2009(6):39-45.
[16]刁方偉.秦西垂陵區圓頂山秦貴族墓地出土文物鑒賞[J].文物鑒定與鑒賞,2016(9):14-18.
[17]李伯謙.晉穆侯夫人隨葬玉器反映的西周后期用玉觀念的變化[M]//劉敦頤先生紀念文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8.
[18]田小娟.先秦時期婦女的化妝[J].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2014(1):260-265.
[19]王星光,宋宇.先秦至漢代動物油脂加工與應用研究[J].中國農史,2019(5):27-40.
[20]鄒芙都.銅器用途銘辭考辨二題[J].求索,2012(7):114-116.
[21]王苛.周代青銅容器自名限定語研究[D].鄭州:鄭州大學,2020.
[22]孫慶偉.最雅的中國—春秋時代的社會與文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