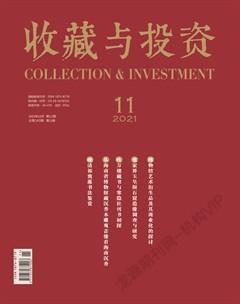從東漢五管瓶窺探漢代陰陽五行
摘要:五管瓶又稱五聯罐,始見于東漢。罐形以葫蘆形為主,罐體上部主體構造為一大四小罐,大罐居中略高,小罐繞周略低,主要有無堆塑物、有堆塑物、假圈足、雙層五聯罐四種,是江浙一帶常見的出土器型。此造型受漢代陰陽五行思想的影響,蘊含著漢代的宇宙觀,即“居中而立,以一為心”。
關鍵詞:東漢五聯罐;陰陽五行;宇宙觀
源于東漢的五管瓶又稱五聯罐,外形以兩或三節的葫蘆形為主,罐體上部主體構造為一大罐肩負四小罐,中罐突出,略高、大,四小罐略低、小,等距環繞中罐四周,間隙堆塑各色動物、植物、人物等。通過整理發現,東漢五聯罐主要分布在浙江省東北部,如杭州、上虞、紹興、嘉興、臺州、寧波等地,是江浙一帶常見的器型。
一、東漢五管瓶例述
通過對東漢墓葬發掘出土的五管瓶進行梳理,主要將其分為四類。
(一)無堆塑物
1.西漢五聯罐(圖一,浙江省嵊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藏)
該罐高約20.7 cm,口沿直徑約為7 cm,底面直徑約為14.5 cm,溜肩、棱腹、平底。罐肩處均勻堆塑有五個呈發散的梅花形的“亞”形小罐,居中一罐略高,且稍大于另外四罐,并與母罐連通,其余四罐皆不與母罐相通。五罐造型類同,皆闊口、束頸、鼓腹。母罐鼓腹斜直,底平,泥硬陶堅,素陶無釉。
2.五管瓶(圖二,浙江省上虞市文物管理所藏)
該瓶整體由兩部分構成,上部由一高四低五個罐狀物組成,居中者較高大且與母罐腹連通,其余四個罐狀物較小且矮,略向中間罐傾斜,四個罐狀物均不與母罐腹連通。五罐狀物口皆沿寬唇厚,下部為座狀,近乎垂直于底。罐腹呈鼓形,渾圓飽滿,上部和中部均有弦紋經繞其周,三道一組。通體施黑褐釉,釉面潤澤光亮,掛釉均勻致密。
(二)有堆塑物
1.青瓷五聯罐(圖三,浙江省寧波市鄞縣沙河出土)
該罐通高約為43.5 cm,口沿直徑約為6.7 cm,底面直徑約為14.7 cm。罐整體較修長,呈三箍葫蘆形,堆塑物主要集中在上中部,約占整體的一半。上部堆塑葫蘆形五小罐,中大四小,四小罐底部環繞堆塑有羊、龜、鳥、狗、鼠等動物,有呈蹲坐狀,有呈爬行狀,有呈翹首狀,姿態各異,惟妙惟肖。上部是動物天地,下部是人的主場,耍雜技、拿大頂、唱歌、跳舞,場面歡樂喜慶。
2.黑釉五聯罐(圖四,浙江省蕭山市衙前鳳凰村出土,浙江省蕭山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藏)
該罐通高約為50.2 cm,口沿直徑約為5.9 cm,底面直徑約為15.5 cm。通體由三層鼓腹狀罐體組成。最下方的較大罐腹為母體罐腹,向上依次變小的兩層鼓腹狀罐體為裝飾性罐頸。在二層鼓腹狀裝飾罐頸的四個方位,分別堆塑有一個與主體罐頸形制相一致的裝飾罐頸;且此四個裝飾罐頸口均不與母體罐腹連通,只有居中的較高口頸與母罐連通,母罐的溜肩及上腹部堆塑有猴子、爬蟲等紋飾。此類五聯罐歷經三國至兩晉時期,演變為早期谷倉。
3.青瓷五聯罐(圖五,浙江黃巖(臺州市)出土)
該罐通高約40 cm、口沿直徑約為6.1 cm、底面直徑約為13.5 cm、母罐罐腹直徑約為23.5 cm。器物整體造型呈三疊葫蘆形,口小、腹鼓、底平;肩部堆塑有四個裝飾性小罐,且均不與母罐相通。四管間均有一環形把手,胎色明灰,胎質堅硬,施以青黃色釉,垂瘤成斑。全罐整體堆塑有各色人物、鳥、獸、蟲及植物等裝飾物,器物肩部堆塑四只振翅飛鳥,鳥首對標四小罐口,其旁堆塑四只窩伏狀雛鳥。四裝飾性小罐頸部外各堆塑一鳥,呈振翅高飛狀,稍低處又各堆塑一對飛鳥。四小罐間各貼塑有“丷”字紋弧形耳。正對把手下方,罐腹部堆塑碩大桑葉各一片,葉柄正下方有直徑約1 cm左右的小孔,小孔兩邊堆貼一只雙目圓碩、作蠕行狀的蠶,桑葉間堆塑向外作屈膝狀的猴與犬,形態各異,旁立人像,懷抱一犬崽,雍冠袍服。罐頸、肩、腹部各刻有數條凹弦飾紋。
(三)假圈足
1.堆塑人物釉陶盤口瓶(圖六,浙江海鹽丁升墓出土)
該瓶泥質為紅陶,通體施青黃色釉;盤口,細頸,上腹鼓圓,中間收縮,下腹較細,圈足。上腹肩部塑五個小壺。上腹和下腹肩部堆塑人物、飛鳥、走獸、鋪首。所飾男女合掌祈禱、奏樂歌舞,百鳥引頸長鳴,獵犬搖頭擺尾,一片祥和景象,用作隨葬品中的谷倉①。
2.五管瓷瓶(浙江嘉興九里匯東漢墓②和浙江紹興縣③出土)
該瓶與上瓶相似,肩以上呈葫蘆形,中有一大管,盤口,邊有四管稍小,敞口,環置。肩部有動物裝飾,鼓腹,假圈足,平底,腹面中部有幾條弦紋,通體施釉。
(四)雙層五聯罐

典例為青釉堆塑九聯罐(圖七,江蘇省常州市新閘鄉王家塘出土,江蘇省常州市博物館藏),該罐罐體通高約為50.5 cm,口沿直徑約為6.5 cm,底面直徑約為16 cm。全器為三層,器形為葫蘆形,從下往上逐漸縮小。雖名為九聯罐,實由兩個五聯罐疊加而成。上半部分為一件完整的五聯罐形制器,盤口、方唇、束頸、溜肩、扁圓腹,肩部亦刻上、下各三道凹弦紋,中間以一道寬水波紋隔開。上下層四個小罐上口均在中間罐腹下部堆塑,各小罐間隙堆塑有豬、犬、羊、魚、鴨、鴿、鼠、龜、熊等動物,以常見動物為主,形象活靈活現,極具生活情趣。通觀上下兩層的四個小罐,發現四罐并非上下排齊,而是位于兩罐之間。上方四罐略小于下方四罐。
二、漢代的陰陽五行
中國傳統文化受漢代陰陽五行思想的影響極深,陰陽五行作為漢代思想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自鄒衍創五德終始學說,至董仲舒上《天人三策》進一步闡發,受皇帝青睞,遂風靡于后。漢代的政治、宗教、文學、醫學、音樂,無不受其影響,董仲舒《春秋繁露》、班固《漢書》《白虎通義》、范曄《后漢書》、劉安《淮南子》等典籍中都有大量關于陰陽五行的記載,可見陰陽五行思想在漢代之盛。《說文》:“五:五行也。從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凡五之屬皆從五。”④《尚書·洪范》:“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⑤陰陽相合,推動五種要素(木、火、土、金、水)運行,呈現五行之象,帶來一系列的發展變化,如五相、五音等,均可以木、火、土、金、水配屬。古人對陰陽五行的運用可謂泛濫至極,文學研究學者葉舒憲將其打趣地稱為“萬能膏藥效應”。
三、五管瓶蘊含的漢代陰陽五行思想
從五管瓶的造型可一窺漢代的宇宙觀。李約瑟曾說:“一旦像五元系統的類別方式被建立起來,事物就不能隨便作為其他事物的原因了。將宇宙萬物萬事都有系統地納入一個結構形式,由這個結構決定各部分間的相互影響。如果有一個質點占據了時空中的某一點,依前者的看法,這是因為另外有一個質點把它推到那里,而依后者的看法,則是因為他與別的一些質點構成一個‘力場,由于相互影響的結果,才把它送到那一點。”⑥如董仲舒所言:“天地之氣,合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⑦陰陽五行由“一”始,系統中的一切皆是圍繞著“一”這個中心,五管瓶的母罐即是這個“一”,整個“一”分為上下相通的“二”部分,周圍攜“四”個小罐體,四個小罐體以主罐體為中心,環繞在主罐體周圍,緊緊圍繞主罐體,形成一個“五”的統一,由大罐體產生關聯,缺一不可,但又相互獨立。中心罐體突出,高于周圍四個小罐體,凸顯其地位的重要性。
《黃帝內經》《淮南子》《春秋繁露》都將“土”和“中”作為五行的中心。“土居中央,為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⑧古人受限于知識,往往把自身所處的世界放于中心,環顧四周。商代自稱“中央商”,羅馬古城、阿波羅神壇皆為此類。在古人眼中,“中”似乎有著某種魔力,中心向四周放射出的吸引力將從屬物牢牢鎖住,中心即萬物的核心,為向心力所指,是萬物的發源和開端,又是萬物的終極歸屬⑨。
作者簡介
朱翰墨,1973年9月生,男,漢族,江蘇沛縣人,江蘇省徐州市銅山區鄭集鎮中心中學一級教師。
注釋
①彭卿云:《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陶瓷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第90頁。
②陸耀華:《浙江嘉興九里匯東漢墓》,《考古》,1987年第7期。
③周燕兒,蔡曉黎:《紹興縣出土越窯魂瓶初探》,《東南文化》,1992年第5期。
④許慎:《說文解字》,湯可敬譯注,中華書局,2018年,第3163頁。
⑤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5頁。
⑥李約瑟:《中國古代科學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6-357頁。
⑦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6頁。
⑧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6頁。
⑨文中配圖來源為朱伯謙《中國陶瓷全集3·秦漢》(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以及彭卿云《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陶瓷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
參考文獻
[1]彭卿云.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陶瓷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90.
[2]陸耀華.浙江嘉興九里匯東漢墓[J].考古,1987(7):3.
[3]周燕兒,蔡曉黎.紹興縣出土越窯魂瓶初探[J].東南文化,1992(5):175-179.
[4](漢)許慎.說文解字[M].湯可敬,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
[5](漢)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英)李約瑟.中國古代科學思想史[M].陳立夫,等,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