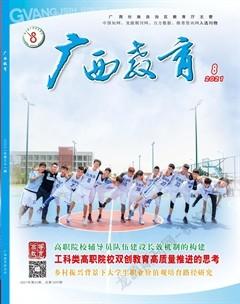最高院刑事指導性案例適用研究
劉英 班建豪
【摘 要】本文采用實證研究方法分析當前由最高院發布的刑事指導性案例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狀況,論證最高院刑事指導性案例援引數量不理想、效力不明確、援引方式不規范、缺乏監督等問題,提出明確其準法源地位、規范援引方式,把控案例生成機制、完善監督方式等完善建議。
【關鍵詞】刑事指導性案例 案例指導制度 “同案同判”? 最高院
【中圖分類號】G?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21)31-0076-03
刑事指導性案例是指最高人民法院經過規定程序選擇和發布的具有特定內容與形式的特別司法案例。而刑事案例指導制度是最高人民法院確定并統一頒布對全國審判工作具有指導作用的指導性案例的制度。我國的刑事案例指導制度建立之初是為了彌補我國成文法的不足,實現統一司法裁判的目標,實質上仍是一種法律適用的制度。我國立法機關雖然已經加快了針對新事物的立法進程,可是畢竟成文法有其自身的缺陷,其滯后性難以跟上時代的腳步從而解決新事物所引發的矛盾。當成文法不足以妥善解決新事物、新矛盾時,便需要采用一種能夠暫時替代法律的方法妥善解決問題。于是最高院在2010年發布《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在2015年印發《〈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實施細則》(以下簡稱《實施細則》),案例指導制度的建立彰顯我國對維護“同案同判”,統一司法裁判的態度和決心。
刑事指導性案例不僅需要滿足一般指導性案例的條件,其自身也要受到罪刑法定原則的制約,不能夠突破刑法文本內容而增設新的刑法規則,所以刑事指導性案例始終深受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的高度重視。自第一批刑事指導性案例發布之日到現在已經過去九年,在司法實踐中刑事指導性案例能否發揮其作用,還需要進行實證考察,進而從中分析我國目前在刑事指導性案例的適用狀況及存在問題并總結經驗,使刑事指導性案例能夠更好地指引司法裁判。
一、刑事指導性案例適用狀況
本文以刊登在裁判文書網的裁判文書為樣本來源(統計數據截止時間為2020年8月3日),在裁判文書網上以“刑事案件”為案由、“指導性案例”為關鍵詞、“判決書”為文書類型進行搜索,共檢索出84份案例。首先剔除了2例重復案例、1例裁定書,其次剔除了在判決文書中援引不符合本文研究類型的12例最高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和10例民事指導性案例,篩選得到在判決文書中援引刑事指導性案例的判決共60例。下文便以這60例樣本分析刑事指導性案例在司法實踐當中的實際適用狀況。
(一)刑事指導性案例援引數量
根據裁判文書網上2012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日的刑事案件數量統計可知,每年的刑事案件增長速度極快,2012年僅有5萬件,而2019年刑事案件高達104萬件。刑事指導性案例的援引數量也是逐年增加,從2013年的1例增至2019年的19例。但相比于每年法院審結的刑事案件的數量來說,指導性案例的援引數量難以發揮其預想的功效。截至2020年8月3日,最高院發布的刑事指導性案例共計21例。但根據每年龐大的刑事案件審判數量,加上也會有很多法官希望能夠將自己作出的判決經過遴選上升為指導性案例的積極心態,應該能夠產生很多指導性案例,可實際情況卻是非常少的。
(二)各方援引狀況
通過對60例樣本進行分析,法官主動援引指導性案例共19例,占比32%;公訴方援引的案例共5例,占比8%;當事人及辯護人援引的案例共36例,占比60%,其中辯護人提出參考或者援引指導性案例的樣本案例共34例,而當事人主動提出參考或者援引的樣本案例共2例。
公訴方作為控方,為了保護公民和國家的合法權益不受到損害,理應需要對刑事指導性案例有深入的了解,也應是促進刑事案例指導制度發展的中堅力量。而根據數據統計分析,公訴方援引刑事指導性案例的數量相當少,并且出現雖提起援引指導性案例但沒有指明哪一具體案例的情況。
(三)當事人及辯護人援引狀況
針對當事人及辯護人援引案例狀況進行分析,當事人及辯護人提出參考或援引指導性案例時,法院沒有回應并且沒有采納的占24例;法院沒有回應但實質采納的占1例;法院有回應但未采納的占4例。在現實司法裁判當中,大多數法官都回避了向當事人釋明是否援引指導性案例這一問題,且沒有給出相應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當事人及辯護人在提出參考或者援引指導性案例來作為自己的訴訟請求或者抗辯理由時,有7例并非最高院經過嚴格程序遴選出來的具有權威性的刑事指導性案例。雖然當事人及其辯護人提出援引或者參考指導性案例有27例,但是其中有16例是沒有指明具體案例,只是提出讓法官參考最高院公布的相關指導性案例,在這16例案例中有14例法官并沒有對其回應且沒有采納,只有2例法官對其回應不采納的理由。
(四)法官主動援引狀況
《實施細則》雖然對法官援引的方式做了規定,可是法官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應當參照”,案件性質、案件事實應該如何把握等都需要法官具有較高的識別、判斷能力。雖然法官對刑事指導性案例的主動援引表明了其對案例指導制度的認識以及追求“同案同判”的期望。但在司法實務中,由于主動援引的方式不規范難免使得案例指導制度流于形式。在法官主動援引刑事指導性案例的19例案例中,法官將援引案例與待決案件進行案情、法律適用問題、主要焦點進行詳細對比的只有4例,占比21%;而沒有將兩個案件進行對比,在裁判文書中沒有出現案號,沒有引述裁判要點,并直接適用的案件共15例,占比79%。
二、刑事指導性案例適用中存在的問題
(一)效力定位不明
刑事指導性案例之所以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狀況并不理想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其地位不明確進而導致其效力不足。雖然《規定》和《實施細則》當中都規定“應當參照”指導性案例。但“應當”屬于強制性詞匯,而“參照”又側重于指導性詞匯,兩者相比在拘束力強度上顯然是不一樣的,因此“應當參照”這一術語就使得各級法院的法官陷入進一步的邏輯困惑中。另外,最高院一直沒有明確,當法官在面臨應適用指導性案例而沒有適用的情況下需承擔什么樣的責任,而且我國現行訴訟法中有關二審改判、發回重審以及再審改判的事由中并沒有“違背指導性案例裁判”這一規定,這就使得上述觀點難以在實踐中真正地實現,導致指導性案例的效力不足。關于效力問題,學界也一直爭論不斷,并且給出了不同的觀點。王利明教授根據我國的司法體制、歷史傳統和案例指導制度的作用來闡釋指導性案例不能成為法律淵源。周光權教授認為由于罪刑法定原則和刑法客觀主義的約束,導致我國刑法的法源只能是成文法。泮偉江教授以“認知理解”與“政策工具”兩個方面解讀案例指導制度,認為司法先例具有某種實質性的法源地位。雷磊教授根據法源的雙層構造理論—— 法源性質論與法源分量論,認為指導性案例具備“準法源”的地位。
(二)生成機制存在缺陷
刑事指導性案例的質量和數量直接影響司法實踐中援引刑事指導性案例的運行狀況。在案例質量上,最高院發布的《規定》第1條中已經規定了指導性案例遴選標準,而第一個標準“社會廣泛關注”其實并不適合單獨作為遴選的標準,因為僅僅是社會廣泛關注的并不具備對其他案件的指引意義。而目前最高法發布的刑事指導性案例大多是以重大事件、社會關注的案件居多,更多的是重申司法解釋規定的指導性案例,并沒有發揮指導解決類似案件的作用。
在刑事指導性案例的數量上,最高院的《規定》第4條明確了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能夠向上級法院推薦優秀的判決案例,這也是許多學者詬病我國遴選指導性案例具有濃厚的行政化色彩的原因。劉樹德教授認為我國指導性案例的生成方式為權力輸出型,而不是一般判例法國家的權威主導型。
(三)援引方式不規范
裁判文書不僅體現控辯雙方的論證,還體現法院對案件事實的論證,呈現出最終的訴訟結果。在刑事案件中,關乎當事人的重大人身利益,更應如此。只有法官通過對比待決案件與援引案例才能確定兩案是否屬于相似案例時,才能使刑事指導性案例發揮其在成文法具有漏洞時填補的功能。通過上文數據分析,法官在主動援引和被動援引刑事指導性案例時說理工作仍然有很多不足,尤其體現在援引案例時并沒有與待決案例進行類案對比。法官援引指導性案例的重點在于進行類案的對比,而這種不通過案件進行類似對比的說理,只會增加當事人對司法公信力和權威的不信任,難以使待決案件得到妥善的處理。
此外,當事人及辯護人雖然注意到指導性案例并在文書中援引加以辯護,但是存在不會用的問題。其一是當事人及辯護人沒有指明哪一具體指導性案例;其二是援引了公報案例或僅具有參考性質的案例。
(四)缺乏審級監督評價
審級監督未發揮案例適用評價作用。刑事指導性案例作為由最高院發布的指導各地區法院辦理復雜疑難案件時準確適用法律的方式,同時也應兼具著監督各地區法院辦案的作用。可是在目前刑事訴訟的程序中,并沒有將指導性案例“應當參照”的效力納入二審或再審發回、改判的標準。審級監督評價缺位導致刑事指導性案例的“參照效力”剛性不足。此外,公眾作為監督司法獨立、公正的重要一環,在監督法院適用刑事指導性案例的環節中并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缺少公眾監督的溝通反饋渠道。
三、刑事指導性案例完善建議
(一)明確指導性案例的準法源地位
首先,法律淵源之所以可以成為裁判依據是因為其具備制度性權威,進而我們應當遵守并適用從制度性權威中所產生的規范拘束力。根據《規定》的第2條指導性案例實際上獲得了制定法的間接授權,具備了制度性權威的隱形認可。其次,指導性案例是由最高院的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并且最高院是發布指導性案例的唯一主體,具有制度所賦予的合法性的權威。那么指導性案例其實也就具備了準法源的地位,可以作為廣義上的裁判依據,進而具備了拘束力。
指導性案例具備了準法源的地位并具有規范拘束力,將會在之后的法官審理相似案例的時候產生拘束力。但是這種拘束力并不意味著法官必須完全遵守不可背離。當指導性案例違背制定法和司法解釋的時候,法官可以拒絕采納。當指導性案例本身并不適用待決案件并且法官具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證明,法官才能夠決定不采用指導性案例。這也說明了指導性案例的規范拘束力在適用上弱于法律和司法解釋。
(二)把控案例生成機制
首先,指導性案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并能夠指引之后的相似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是因為其不僅僅表現在案件事實、爭議點等具有以往案例中沒有出現或者沒有注意的方面,而且表現在面對這些突發的、新型的、疑難的問題可以相對于制定法給出更快的解決方案,以免出現“同案不同判”的問題,從而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所以在遴選指導性案例時,遴選出來的案例應當是能夠彌補法律漏洞,才能引導法官對類似案例具有相似的判決,應轉變工作重心,以解決普遍爭議為原則,以社會廣泛關注為輔。
其次,與其將最高院作為遴選主體,不如把高院作為遴選主體的主力。因為兩審終審制的原因,很多刑事案件會進入到高院審理,所以高院相對于最高院接觸的案例要多,高院可以有效地接納案例并處理重大疑難復雜的案例。而且將高院作為主力,可以減少行政化因素對指導性案例生成的影響,這樣就可以提高審判主體和案例生成主體的同一性。而從高院直接審判的案例中挑選具有指導性意義的、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案例報最高院備案審查后,最高院發文將其上升為指導性案例,這樣使得案例依然具有權威性且產生拘束力。
(三)規范援引方式
無論是主動援引還是被動援引,法官都需要就案件是否相似進行判斷和說理,避免直接適用而不加以對比的情形。適用指導性案例的前提是案例與待決案例相類似。可以從以下三點判斷案件是否相似:一是案件的案件事實是否相似,若裁判者發現兩案的關鍵事實存在差異,則可以直接向當事人闡明理由,并拒絕援引指導性案例;二是案件所適用的法律關系是否相似;三是案件的爭議點是否相似。
當事人及辯護人對刑事指導性案例的援引無疑是推動刑事案例指導制度進步的最主要的動因。而其不規范的援引方式并沒有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得到有效的保護。辯護律師及當事人在援引指導性案例時應注意規范其援引方式,尤其是詳細闡述裁判要點、裁判理由,不應只是模糊地提請辦案法官參考相關指導性案例。
公訴方也存在與當事人及辯護人一樣的問題,作為代表國家的一方,更應該擔負起自身的職責,努力推行和實踐國家的制度,作為發展刑事案例指導制度的中堅力量認真研習刑事指導性案例,加強業務培訓,定期開展對刑事指導性案例的學習,規范援引方式,避免出現不確定的援引。
(四)完善監督方式
當法院參照指導性案例但未釋明其理由時,應允許當事人上訴或請求再審。當二審或再審程序中發現,法官雖然沒有適用指導性案例但案件結果并沒有違背法律,則可以維持原判并指出原審法院程序上的瑕疵。若二審或再審程序中發現,法官不僅沒有適用指導性案例并且違背法律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現象,則應該改判或發回重審并對原審法官給予處理。為了追求具體案件的公正結果,法官只有在以下兩種情況下才可以向上級法院做出偏離刑事指導性案例的裁判:第一,指導性案例不正確,先例中法律適用錯誤;第二,指導性案例不相關或不充分,沒有完全相同的案件。當指導性案例與待決案件所面對的法律問題、爭議點盡管基本事實相似但先例的裁判理由并不能夠解決待決案件時可以偏離。
此外,應當鼓勵公眾行使自己的監督權,當社會公眾在查閱相關案例時,認為法官沒有規范行使裁判權時,尤其是在審理案件沒有按照規定援引或拒絕援引刑事指導性案例的,也可以向法院提出相關工作建議和意見,法院領導應該向案件的辦案法官詢問情況并要求釋明理由。
綜上所述,刑事指導性案例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情況并不理想,需對刑事指導性案例適用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梳理,采用實證研究方法總結其背后的影響及原因并提出完善建議,以期充分發揮刑事指導性案例在適用過程中的指導作用。
【參考文獻】
[1]陳樹森.我國指導案例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2]王利明.我國案例指導制度若干問題研究[J].法學,2012(1).
[3]周光權.刑事案例指導制度[J].中外法學,2013(3).
[4]泮偉江.論指導性案例的效力[J].清華法學,2016(1).
[5]雷磊.指導性案例法源地位再反思[J].中國法學,2015(1).
[6]劉樹德.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規則的供給模式:兼論案例指導制度的完善[J].清華法學,2015(4).
[7]林正雄.正本清源:刑事指導性案例功能實現之三維路徑[J].法院改革,2018(1).
【作者簡介】劉 英(1974— ),女,漢族,廣西興安人,廣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民商法、經濟法;班建豪(1994— ),男,漢族,河南原陽人,廣西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經濟法。
(責編 羅汝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