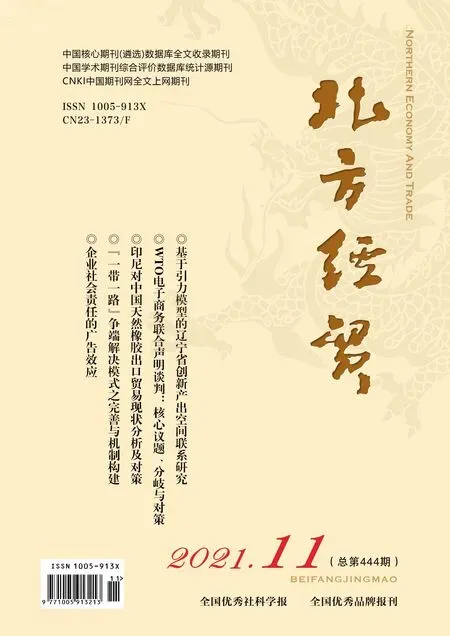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
——以陜西省為例
李泯朵,何宏慶
(延安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陜西延安 716000)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不僅影響經濟發展質量,而且會降低人民生活幸福感。經國家統計局核定,陜西省2020 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7 868 元,同比增長4.9%,而農村居民是13 316 元,同比增長8.0%,雖然農村增速高于城鎮3.1 個百分點,但城鄉收入比仍處在2.84:1 的高位。可見,陜西省在城鄉均衡發展的道路上任重道遠,而數字普惠金融的出現或許能起到助推作用。G20 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指出,“數字普惠金融”運用數字技術以負責任的、成本可負擔的、對服務提供商而言可持續的方式,為無法獲得金融服務或缺乏金融服務的群體提供一系列正規金融服務。數字普惠金融與生俱來的效率高、覆蓋廣和成本低等特征,有利于提高尤其是農村地區的金融服務可得性,進而影響其生產能力和預期收入,[1]幫助其踏出縮小收入差距第一步,但具體影響仍需實證檢驗。
宋曉玲(2017)從全國層面出發,實證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可顯著收斂城鄉收入差距。[2]在此基礎上,裴邵軍等(2019)從區域層面切入,結果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存在異質性,其中對中部地區的影響為負且最為顯著。[3]同樣基于異質性,趙丙奇(2020)實證得出,相比對較高經濟發展水平地區的負向線性影響,數字普惠金融對較低經濟水平地區城鄉收入差距存在先擴大后縮小的非線性影響,并得出該地區現處于縮小階段的結論。[4]進一步地,李牧辰等(2020)從數字普惠金融不同維度展開分析,結果發現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廣度和使用深度能夠顯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數字化程度則不然。[5]雖然諸多實證研究指向數字普惠金融的積極影響,但何宏慶(2019)認為其發展依然面臨著金融倫理意識淡薄、相關法律制度不健全及監管方式不科學等困境。[6]
學者的研究多從全國或分區域角度切入,鮮有對單個省域地區進行分類研究的文獻,因此,現以陜西省為例,研究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期許為陜西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提升居民幸福感提供可行性建議。
二、理論分析
金融資源有限且信息不對稱往往導致資源分配不均、獲取金融服務門檻較高即非均衡效應和門檻效應,而數字普惠金融通過突破地理障礙和利用貸款人在互聯網上沉淀下來的大量軟信息緩解上述效應。[7]此外,數字普惠金融所具有的覆蓋廣、成本低及效率高的特征益于強化減貧效應,減貧效應是指在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窮人也逐漸有機會享受金融服務以減少貧困發生,進而收斂城鄉收入差距。[8]綜上,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緩解非均衡效應、降低門檻效應及強化減貧效應的方式收斂城鄉收入差距,提出假設1。
假設1: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夠收斂城鄉收入差距。
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包含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及數字化程度三個維度,其中覆蓋廣度側重橫向,包括對不同人及不同方面的覆蓋;使用深度側重縱向,衡量用戶對數字金融服務的使用量和活躍度。上述兩個維度是“普”,數字化程度則是“惠”,衡量的是數字金融服務的便利化、信用化及實惠化水平。[9]由于不同維度側重點不同,其各自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也將存在異質性。因此,提出假設2。
假設2:數字普惠金融不同維度的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存在異質性。
三、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y)。通過泰爾指數衡量城鄉收入差距,公式如(1),其中i 表示地級市,t 表示時間,pij,t、zij,t分別表示i 地級市城鎮(j=1)或農村(j=2)t 年的收入和人口,yi,t、pi,t及zi,t則分別表示i 地級市t 年的泰爾指數、城鄉總收入和總人口。

2.核心解釋變量(x)。利用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及其不同維度指數體現,該指數覆蓋中國內地31個省、337 個地級市以上城市和約2 800 個縣域,研究選取其中陜西省2011-2018 年10 個地級市數據作為核心解釋變量,由于其與研究中其他指標相比較大,對其進行除以100 的處理。
3.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pgdp),采用以2011 年為基期,經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指數剔除價格因素后的實際人均GDP 衡量,并對其進行對數處理;城鎮化水平(urb),通過年末城市人口占總常住人口比重體現;對外開放水平(ope),選擇進出口總額占GDP 比重衡量;政府財政支出水平(fin),選擇一般預算支出占GDP 比重進行求得。
以上數據來自2012-2019 年《陜西省統計年鑒》、陜西省各地級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且所有變量均通過單位根檢驗。
(二)模型設定
為研究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現以城鄉收入差距為被解釋變量,數字普惠金融為核心解釋變量構建計量模型如(2)。其中,αi是各地級市差異的非觀測效應;β1-5是變量系數;εi,t是隨機擾動項,其余符號含義見變量選取。

(三)實證結果
對公式(2)進行回歸,結果如表1(1)所示,數字普惠金融在1%顯著性水平下負向影響城鄉收入差距,其增加1 個單位,陜西省城鄉收入差距將縮小0.063 個單位,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有利于城鄉收入差距收斂,假設1 得以驗證。從控制變量角度來看,經濟發展與城鎮化水平均顯著收斂城鄉收入差距,兩者每增加1 個單位,城鄉收入差距將分別縮小0.033、0.222 個單位,說明經濟發展與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尤其是城鎮化水平。2019 年陜西省城鎮化水平是59.43%,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說明其在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方面存在發展潛力。相反,對外開放與財政支出水平均與城鄉收入差距正相關,且都在1%水平下顯著,這可能是因為農村居民自身技能還無法完全適應對外開放企業對高質量勞動力的需求,同時也說明政府需要加大農村方面的財政支持。
為厘清數字普惠金融收斂城鄉收入差距效用下不同維度所做貢獻,研究分別以覆蓋廣度(x1)、使用深度(x2)及數字化程度(x3)替換數字普惠金融變量進行回歸,結果如表1(2)(3)(4)所示,覆蓋廣度及數字化程度均在5%顯著性水平下負向影響城鄉收入差距,說明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度的提高及數字普惠金融實惠化、便利化、信用化水平的上升有利于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且前者作用要大于后者。此外,使用深度系數雖然為負,卻在統計意義上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其作用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地區存在抵消現象。當以人均GDP 為標準將陜西省10 個地級市劃分為高低經濟水平兩組分別進行回歸時發現,在高經濟水平地區,使用深度顯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在低經濟水平地區,兩者關系呈正向不顯著,上述推斷得到證實,假設2 得以驗證。

表1 數字普惠金融及其不同維度
(四)穩健性檢驗
為驗證上述結論的可靠性,分別采用變量替換法和解釋變量滯后一期進行穩健性檢驗。前者保持其他變量不變的同時,將被解釋變量的測度方法更換為城鄉居民收入比,后者考慮到內生性問題,在基準回歸的基礎上對所有解釋變量進行滯后一期處理,這是由于本期的遺漏變量難以對上期解釋變量造成干擾,以此減少內生性困擾。結果,數字普惠金融依然顯著收斂城鄉收入差距,結論相對穩健可靠。
四、結論與建議
數字技術與普惠金融作為服務社會的工具,其融合為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帶來契機。聚焦陜西省得出如下結論:一是數字普惠金融通過緩解非均衡效應、降低門檻效應以及強化減貧效應顯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二是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廣度、數字化程度均顯著利于城鄉收入差距收斂,使用深度則不然。三是城鄉收入差距縮小需多方有益因素合力實現。針對這一結論,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積極發展數字普惠金融,驅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新引擎。政府應營造開放包容的創新環境、注重培養數字金融相關技術和管理人才,尤其是金融與數字技術復合型人才。[10]同時加強相關監管工作,對于數字金融活動的市場準入、行業監管、網絡信息安全等制定相對規范、穩定的規則。最后政府需在立足自身實際的同時加強省際交流合作,積極借鑒其他省份發展經驗。
第二,依據地區實際情況,尋找適當維度作為發力點。在高經濟水平地區,政府應穩步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擴大數字普惠金融覆蓋面;金融機構應創新金融產品,提供豐富的金融服務,拓展使用深度;雙方應共同促進金融領域競爭與合作,提高金融服務效率。在低經濟水平地區,政府應在著眼于覆蓋廣度及數字化程度的同時,配合金融知識培訓,加強農村居民數字普惠金融與信用觀念,并設置激勵措施將培訓效果與農民自身利益掛鉤,實現數字普惠金融的真正覆蓋。
第三,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需要發揮多方面因素的作用。首先,推動城鎮化進程,使得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得以進入城鎮參加建設,享受經濟開放帶來的好處,進而提高自身收入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其次,農村地區要發揮比較優勢,依據自身資源稟賦組織生產,解決部分因身體、年齡而無法外出打工人群的生計問題。最后,政府應通過財政支持鼓勵發展良好的農村帶動周邊農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