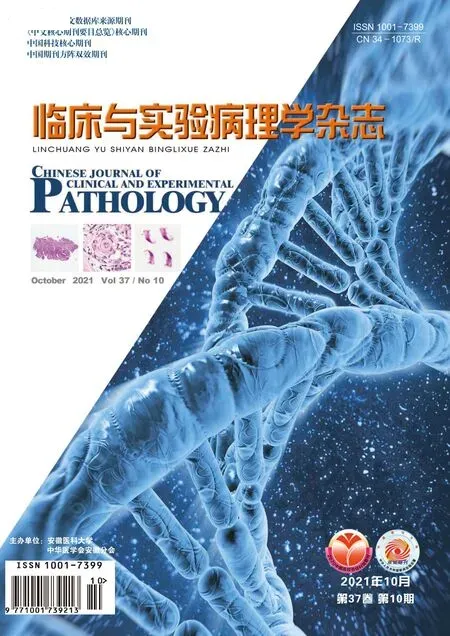胃腺癌組織中PD-L1和M2型腫瘤相關巨噬細胞的表達及臨床意義
權秋穎,曹 磊,張 閩,黃 山,黃仁鵬,陳 志,郭凌川
胃癌是起源于胃黏膜上皮的惡性腫瘤,發病率位居全球惡性腫瘤的第5位,病死率位居癌癥死亡的第3位[1]。每年中國胃癌患者的死亡人數約占全球胃癌死亡人數的一半[2]。傳統治療如手術和放、化療均無法明顯改善患者的總生存期,5年生存率不足30%[1]。程序性細胞死亡配體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PD-L1)作為負性共刺激分子,是B7家族的一員,其與對應的配體PD-1結合可造成T細胞失活[3-4]。PD-L1在多種腫瘤如胃癌、黑色素瘤、肺癌、結直腸癌等[5]中過表達。在很多實體腫瘤如黑色素瘤、肺癌中,抗PD-L1抑制劑表現出了良好的效果[6],但在胃癌中,采用抗PD-L1抑制劑總體有效率不高。研究表明,腫瘤組織中PD-L1表達、腫瘤間質中浸潤細胞的類型等均與患者采取抗PD-L1治療后的效果有關[7],因此選擇適宜行免疫治療的人群至關重要。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TAMs)在免疫微環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TAMs可分為M1型和M2型,其中M1型主要發揮抗腫瘤效應,M2型(因表達特異性標志物CD163,以下均用CD163表示)通過產生免疫抑制細胞因子如IL-10、TGF-β促進腫瘤進展,同時還可表達PD-L1/2,與T細胞結合產生免疫抑制作用[8-9]。一般狹義的TAMs即指發揮免疫抑制及促瘤作用的M2型TAMs。然而,PD-L1和M2型TAMs的關系仍需深入探討。本實驗通過觀察PD-L1和CD163在胃腺癌組織中的表達,旨在為胃癌聯合治療提供新思路和方向。
1 材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收集2011年5~12月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存檔的268例胃腺癌標本,所有標本術前均經病理確診,患者年齡33~88歲,平均(64.5±10.8)歲。所有患者術前均未行任何放、化療等其它治療。通過電話隨訪獲得患者的生存狀況,隨訪截至2017年12月,合計198例患者獲得完整的生存資料,余70例失訪。
1.2 主要儀器及試劑大體顯微鏡(CX23),購自日本Olympus公司,Dmetrix遠程醫療圖像處理系統,購自帝麥克斯蘇州醫療公司,全自動多功能染色機(ST5020),購自徠卡公司。PD-L1(克隆號SP142)、CD163(克隆號10D6),均購自北京中杉金橋公司,免疫組化用二抗HRP標記鼠/兔通用型二抗,購自福州邁新公司。
1.3 方法采用免疫組化EnVision法檢測胃腺癌癌細胞和間質細胞中PD-L1蛋白表達水平及CD163在胃腺癌間質細胞中的表達,分析兩者表達與胃腺癌臨床病理特征及患者預后的相關性。評判標準:所有切片均經兩位有經驗的病理醫師采用雙盲法閱片,對腫瘤細胞及腫瘤間質區域分別進行評分,計算陽性細胞百分率為陽性細胞平均數/所有視野內細胞總數×100。切片染色評分為0~3分(無陽性細胞為0分,陽性細胞數<10%為1分,10%~50%為2分,>50%為3分),將評分0~1分歸為低表達組,2~3分歸為高表達組;根據公式計算染色定量的組織評分(3+陽性細胞百分率)×3+(2+陽性細胞百分率)×2+(1+陽性細胞百分率)×1,免疫組化評分范圍從0~300不等[10]。
1.4 統計學分析采用SPSS 19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采用χ2檢驗分析PD-L1和CD163蛋白表達與胃腺癌臨床病理特征之間的關系,Spearman秩相關檢驗分析PD-L1與CD163在胃腺癌組織中表達的相關性,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線和Log-rank檢驗進行預后生存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胃腺癌組織中PD-L1和CD163的表達及與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52例(19.4%)胃腺癌癌細胞高表達PD-L1,167例(62.3%)胃腺癌間質細胞高表達PD-L1,PD-L1和CD163表達均可定位于細胞膜和細胞質(圖1)。胃腺癌間質細胞中PD-L1表達與腫瘤浸潤深度(P=0.010)、腫瘤分期(P=0.043)呈負相關(P<0.05),與患者年齡、淋巴結轉移無關;胃腺癌癌細胞中PD-L1的表達與各臨床病理特征均無關;CD163表達與腫瘤浸潤深度、淋巴結轉移及腫瘤分期呈正相關(P<0.05,表1)。

圖1 胃腺癌組織中PD-L1和CD163的表達:

表1 胃腺癌組織中PD-L1和CD163的表達與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
2.2 胃腺癌組織中PD-L1與CD163表達的相關性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胃腺癌癌細胞或間質細胞中PD-L1的表達與CD163表達均呈正相關(P<0.001,圖2)。

圖2 胃腺癌組織中PD-L1與CD163蛋白表達的相關性分析:
2.3 生存分析Kaplan-Meier生存曲線分析顯示,胃腺癌癌細胞中PD-L1的表達與患者生存無相關性(圖3A);胃腺癌間質細胞中PD-L1的表達越高,患者預后越好(P=0.028,圖3B);CD163表達與患者生存無關(圖3C)。

圖3 Kaplan-Meier生存曲線分析:
2.4 聯合檢測PD-L1與CD163的表達與胃腺癌患者預后的關系胃腺癌癌細胞或間質細胞中PD-L1高表達同時CD163低表達時患者預后最佳,PD-L1低表達同時CD163高表達時患者預后最差,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圖4)。

圖4 PD-L1和CD163聯合檢測與胃腺癌患者的預后分析:
3 討論
既往報道表明,通過靶向PD-1或PD-L1的單克隆抗體在黑色素瘤、非小細胞肺癌等惡性腫瘤的治療中起到了令人矚目的效果,然而,其在胃癌中的療效仍未有明確定論,PD-L1在胃癌組織中的表達及與患者預后的關系仍有爭議,其調控機制需要進一步探討[11]。TAMs在促進腫瘤增殖、新生血管形成和轉移中扮演重要角色,TAMs還可表達PD-L1/2,與PD-1結合從而抑制T細胞的激活。本實驗發現,PD-L1在胃腺癌癌細胞和間質細胞中的表達均與CD163表達呈正相關,表明通過分析PD-L1表達與CD163表達之間的相關性可進一步預測患者預后,并對抗PD-1/PD-L1免疫卡控點抑制劑的應用提供潛在研究基礎。本實驗發現,PD-L1在胃腺癌間質細胞中表達越高,患者預后越好,并與腫瘤浸潤深度及腫瘤分期呈負相關;胃腺癌癌細胞中PD-L1的表達與患者預后無關。既往研究發現,PD-L1高表達患者,生存期較短,預后較差[12-13];相反,同樣有研究表明PD-L1陽性患者預后較好[14];對早期胃癌進行研究發現,在PD-L1高表達的病例中更易觀察到血管和淋巴管的侵犯[15];而最近的一項薈萃分析結果表明,在胃癌的治療中,抗PD-1/PD-L1單克隆抗體被認為是一種具有前景的免疫療法[11]。因此,PD-L1表達與患者預后的關系存在爭議,PD-L1在胃癌組織中的表達與患者預后的關系尚需更多研究進行深入探究。
TAMs可分泌多種細胞因子,抑制效應T細胞的活性,促進腫瘤的進展,在實體腫瘤中,TAMs的表達高低可影響患者預后。本實驗結果表明,CD163的表達與患者預后無關,但與腫瘤浸潤深度、淋巴結轉移及腫瘤分期呈正相關。然而,腫瘤組織中PD-L1和TAMs的關系仍未闡明,在對乳腺癌的研究中發現,乳腺癌細胞可分泌促使M1型TAMs向M2型TAMs轉化的細胞因子,并且CD163+M2型TAMs數目越多,腫瘤分化越差,增殖更快[16]。在非小細胞肺癌中,M2型TAMs的浸潤與淋巴結轉移、病理分期及更差的無瘤生存期和總生存期相關[17];另外,有研究發現TAMs在結直腸癌中可通過產生IL-1、IL-6和TNF-α等細胞因子激活NF-κB,從而分泌VEGF促進腫瘤血管生長和轉移[9]。同時有研究表明,TAMs可通過JAK/STAT3和PI3K/ALK通路促進PD-L1的表達[18]。本實驗發現,CD163的表達與PD-L1表達呈正相關,亦發現PD-L1高表達同時CD163低表達的患者預后最佳,而PD-L1低表達同時CD163高表達的患者預后最差,這些結果表明,聯合評估PD-L1和CD163的表達可更好的評估患者的預后特征,為抗PD-1/PD-L1單克隆抗體的應用篩選合適的患者人群提供新思路,同時也為胃癌的免疫治療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向。
采用免疫卡控點抑制劑的治療方法如抗PD-1/PD-L1的單克隆抗體正在越來越多的癌種中使用,而TAMs通過表達PD-L1/2成為靶向免疫檢查點治療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一些細胞因子或缺氧條件的刺激下,巨噬細胞中的PD-L1/L2表達上調,促進腫瘤轉移和進展[19]。也有研究表明,TAMs可以促進胃癌上皮-間質轉化[20]。值得注意的是,TAMs具有明顯的異質性,且可塑性較強[21]。有報道發現,通過抑制髓系生長因子受體CSF1R的信號通路,可以增加巨噬細胞提呈抗原和抗腫瘤的能力,同時聯合PD-1或CTLA-4拮抗劑可更好的誘導腫瘤消退[22]。這些結果表明通過靶向TAMs的治療策略可能會減少PD-L1在腫瘤組織中的表達,從而激活效應T細胞,進而增強抗PD-1/PD-L1阻斷劑的效果。
綜上,本實驗結果表明,胃腺癌組織中CD163表達與PD-L1表達呈正相關,表明通過阻斷TAMs的激活通路,同時聯合免疫卡控點療法如PD-L1單克隆抗體在胃癌的免疫治療或許能起到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