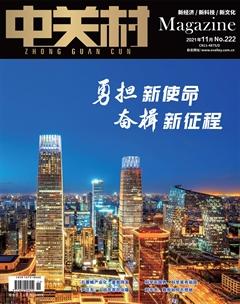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
王洪鵬 周廣剛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由于西方列強的入侵,封建統治的腐敗,中國逐漸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那時山河破碎、生靈涂炭,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難。面對苦難,中國人民沒有屈服,而是挺起脊梁、奮起抗爭。一批愛國知識分子也積極尋求救亡圖存之路,寄希望于科學救民族于危亡、攜民眾出水火。在這一過程中,一批愛國知識分子不僅形成了科學救國和科學立國思想,而且注重科學家的作用。他們認為“科學家之精神,在尋求真理;科學家之目的,在造福人類。故能稱得起科學家之人,不獨其在專門學問上,有精深之造詣,而其道德人格,亦必高尚純潔,有深邃之修養。”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最早的一批黨員中,相當一部分人具有近代科學技術背景或較早接受了民主、科學的思想,他們對于在中國發展科學技術的重要性比其同代人理解得更深切更全面。1919年,陳獨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發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大力宣揚“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賽先生”(Science,科學)。他說:“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革命老人徐特立在延安低矮的窯洞里,寫道:“科學,你是國力的靈魂,同時又是社會發展的標志。所以,前進的政黨必然把握先進的科學。”
愛國精神是科學家精神的基礎。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我國知識分子歷來有濃厚的家國情懷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等愛國思想,是一代又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人生追求。科學家是知識分子中的優秀代表。新中國建立初期,在歐美學有所成的一批科學家,他們堅信共產黨一定能夠帶領全國人民創造一片新天地,毅然放棄國外優越的生活和科研環境,回到一窮二白的祖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曾任中國科協主席的錢學森,始終把祖國和人民放在第一位,放棄在國外的優越生活條件,投入百廢待興的祖國懷抱,體現了傾盡所學報效國家、服務人民的赤子之心和愛國之情。鄧稼先從美國回來,領導找他談話干核武器事業,他毫無異議,并說“這件事很重要,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物理學家彭桓武是第一個在英國獲得教授職稱的中國人。彭桓武回國前,有人問“國外條件這么好,你為什么要回國?”彭桓武回答:“我是中國人,我要是不回國,你再問我為什么!”
愛國精神是科學家精神的基礎
愛國主義精神對科學家研究方向有著指引作用。現代科學技術在中國的發展歷程,與中國近現代波瀾起伏的歷史交織在一起,成就了一些最高科學技術獎勵獲得者豐富而跌宕的人生經歷。最高科技獎獲得者谷超豪、黃昆、葉篤正等先生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投身時代洪流,放棄以個人興趣為導向的學術專業選擇,從國家需要出發選擇自己從事的研究領域,并取得了利國利民優異成績。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100年來,黨帶領全國人民不斷創造偉大的物質文明,更鑄就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共產黨人在不同時期地區和領域形成的革命精神,總共有90多種。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到“兩彈一星”精神、科學家精神、抗疫精神,都展現了共產黨人的偉大品格。
2019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要求在全社會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并闡明了“愛國、創新、求實、奉獻、協同、育人”的新時代科學家精神。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是中國最杰出的科學家,這些科學家瞄準國際科學前沿,在各自的研究領域里做出了重大貢獻。自2000年至2020年以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已經頒獎18屆,共有33位科學家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獎金也由最初的500萬元提高至800萬元。其中,2004年和2015年空缺,2002年、2006年、2014年僅評出一位獲獎科學家。空缺并不意味著沒有,當年的空缺僅僅是客觀的評選結果,足以表明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極為嚴格的評選流程。

谷超豪夫婦教書育人
紅色詩人數學家谷超豪
紅色詩人數學家谷超豪(1926年—2012年)院士的一生就充滿了傳奇色彩。谷超豪出生于浙江溫州,家境殷實,5歲被送入私塾開始習字,7歲就讀于溫州甌江小學,11歲考入溫州聯立中學,第二年轉入溫州中學初中部。此時,我國的抗日戰爭已經爆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溫州中學的愛國學子們紛紛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運動之中,谷超豪的大哥谷超英,身為溫州中學高中部學生,是學校黨組織的創建者之一。受哥哥的引導和啟發,谷超豪閱讀了大量進步書籍,開始信仰共產主義并積極參與愛國救亡運動。他秘密參加了溫州中學黨組織領導的讀書會,利用年齡小不引人注目這一優勢,幫助高年級的進步學生們傳遞會議資料、站崗放哨。他加入了溫州中學抗日宣傳隊,離開城市到艱苦的農村宣傳抗日救國思想,以喚起民眾。
1940年,年僅14歲的谷超豪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黨組織的領導下,他更加積極投身革命之中。根據黨的指示,谷超豪和同學們利用夜幕做掩護,在溫州城里散發革命傳單、張貼革命標語,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思想。在白色恐怖時期,谷超豪受黨的委派在溫州大羅山開展地下工作,宣傳進步思想。在敵人追捕時,他憑借老鄉的幫助,隱藏在鄉親家里得以逃脫。自古英雄出少年。經過艱苦斗爭的歲月淬煉,谷超豪成為了一名優秀的共產黨人。
1943年,谷超豪就讀于浙江大學理學院數學系。大學期間,面對殘酷的對敵斗爭,他依然積極參加革命活動,因此他只能靠擠出來的時間進行學習與研究。新中國成立前后,谷超豪在浙江大學從事學生運動、科技界統戰和行政工作,幾乎成為職業革命家。1951年,谷超豪回歸數學研究,主動服務祖國建設,多次調整自己的數學研究方向,從微分幾何到偏微分方程,從偏微分方程到數學物理,三個領域都成就斐然。
2010年,谷超豪先生榮獲2009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2012年6月24日,87歲的谷超豪先生永遠離開了他所鐘愛的科學研究和教育事業。仰望星空,我們仿佛看見那顆明亮的“谷超豪星”,指引著數學后輩學者不斷前進。

潞河中學的黃昆雕塑
固體物理學的一代宗師黃昆
黃昆(1919年-2005年)是世界著名的固體物理學家、教育家。他是中國固體物理學和半導體物理學奠基人之一,不僅完成了物理學界的兩項開拓性的學術成果,還創建和發展了中國的半導體科研和教育事業,為祖國科學的發展嘔心瀝血,啟迪眾生。
1944年,黃昆被“庚子賠款”留英公費生錄取。1945年至1948年,黃昆在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師從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后來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莫特教授,并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選定為固體物理學。在博士期間,黃昆就完成了3篇論文,其中最有分量的是“黃—漫散射”,開始在理論物理方程上寫上了中國人的名字。
在國外學術研究上的豐碩成果并沒有使黃昆以此自滿。他仍然心系祖國,對于祖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心懷遠大的目標與志向。1947年4月,黃昆曾經給楊振寧寫了一封信,探討了他們那批海外留學的知識分子當時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回國,還是暫不回國?一方面,“看國內如今糟亂的情形,回去研究自然受影響,一介書生又顯然不足有挽于政局”;另一方面,“如果在國外拖延目的只在逃避,就似乎有違良心。”黃昆寫道:“我們衷心還是覺得,中國有我們和沒有我們,make a difference(還是有區別、有影響的)”。楊振寧一直珍藏著這封信,從通篇繁體字與英文單詞的雜糅之中,我們仿佛看到一個飽含愛國熱情、遠赴重洋求學深造的科學青年寫信時鄭重而誠摯的模樣。這種中國知識分子對祖國滿懷熱愛、自覺擔負起天下興亡的歷史使命的萬丈豪情,仍然讓我們感動。
1951年,新中國百廢待興,發展過程中更是急需科學技術的支持。這時,黃昆毅然中斷了多年游學生涯,義無反顧放棄了優裕的生活和美好的學術發展空間,回到北京大學物理系任教,投身于普通物理課程的教學工作。“渡重洋,迎朝暉,心系祖國,傲視功名富貴如草芥;攀高峰,歷磨難,志興華夏,欣聞徒子徒孫盡棟梁”這是北京大學物理系師生在他70華誕時贈送的對聯內容。這又何嘗不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
1956年,為了推動國家半導體科技的發展,黃昆響應國家號召,參與創建了五校聯合的中國第一個半導體專門化專業,擔任教研室主任,培養、造就了一批中國半導體技術的棟梁之才,他也成為中國半導體物理學科的開創者之一。黃昆曾說過:“近些年來,新聞界的人士多次問我:‘你沒把研究工作長期搞下來,是不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我一直不同意這種看法。因為回國后全力以赴搞教學工作,是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是一個服從國家大局的問題。這也并非我事業上的犧牲,因為搞教學工作并沒影響我發揮聰明才智,而是從另一方面增長了才干,實現了自身價值。”這是老一輩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感和愛國主義傳統的寫照,真正地將個人發展與國家興亡緊密結合在了一起。
2005年7月6日,黃昆在北京與世長辭。2010年,國際小行星中心發布公報,將第48636號小行星永久命名為“黃昆星”。半個世紀以來,黃昆先生作為一名科學家、教育家,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我國的科技和教育事業,兢兢業業,任勞任怨,為我國的半導體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讓中國氣象與世界同步的葉篤正
陰晴雨雪的天氣是怎樣形成和記錄下來的?天氣預報的制作和播放又是怎樣的一個過程?我國從無到有的氣象理論和天氣預報的形成,都離不開一個人的貢獻,他就是葉篤正院士。葉篤正是著名氣象專家,中國現代氣象學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國大氣物理學創始人、全球氣候變化研究的開拓者。“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是他名字的由來。
葉篤正出生在一個封建大家庭里,有十四個兄弟姐妹。他性格溫和,學習最用功,常常被先生和父親當做榜樣說服其他孩子。14歲以前,葉篤正接受的都是私塾教育,14歲那年,他考入了天津南開中學。在南開中學的那段日子里,他逐漸知道了官僚的驕奢淫逸、民生的艱難困苦、國家的多災多難、民族的存亡絕續。這段學習生涯對葉篤正的一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期間由于他課業努力上進,直接跳級上了初三,進入南開中學人才濟濟的“1935年班”。在這個先后出過3位中科院院士的班級里,他是公認的佼佼者。1935年,他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在那“華北之大,卻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的年代,熱血愛國的他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大一即參與了一二·九運動,1937年“七七事變”后又積極加入抗日行列。后來的一系列變故讓他開始審視自己的人生,明白要想救國必須先要武裝自己的頭腦,憑著一腔熱血一味盲目地革命注定不是救國之路。之后他便回到西南聯大繼續學業,就是在那里,他放棄了自己原本特別喜愛的物理學,選擇了當時對國家更有實際用途的氣象學研究作為自己的終身職業。
葉篤正于1945年赴美留學,1948年博士畢業并留校工作,在美國氣象學界逐漸嶄露頭角,獲得業界廣泛贊譽和尊重。留美期間,葉篤正發表多篇重要學術論文,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博士論文《大氣中的能量頻散》,這篇論文被譽為動力氣象學的三部經典著作之一,是長波理論的第二個里程碑,并成為現代天氣預報的重要理論基礎之一。
1949年,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后,身在異鄉的葉篤正便義無反顧地做出了回國的決定。他對導師說:“我覺得新中國是有希望的,我想為自己的國家做點事。”回國后,他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主任,在北京西直門內北魏胡同一座破舊的房子里開始了艱苦的創業。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當初只有十幾個人的科研小組,已經發展成現在國際知名的大氣科學研究所。

葉篤正獲1980年度中國科學院先進工作者
1958年8月,葉篤正與他人合作出版的《大氣環流的若干基本問題》,是大氣環流動力學方面最早的著作,也是大氣環流演變過程和維持機制的經典著作之一。1959年,葉篤正出版的《西藏高原氣象學》一書,對青藏高原氣象學研究進行了系統總結,是當時國內外唯一的西藏高原氣象學專著。在葉篤正的努力下,中國氣象局于1969年正式發布短期天氣預報。70年代末,提出并支持建立中國的氣象數值預報業務,進一步提高了短期預報信息準確性。
2020年9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指出:“科學成就離不開精神支撐。科學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長期科學實踐中積累的寶貴精神財富。新中國成立以來,廣大科技工作者在祖國大地上樹立起一座座科技創新的豐碑,也鑄就了獨特的精神氣質。”“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我國科技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報國的科學家前赴后繼、接續奮斗的結果。”
一言以蔽之,科學家的愛國精神從根本上決定和影響著創新精神、求實精神、奉獻精神、協同精神、育人精神的形成和發展,而這些精神又處處彰顯和體現著科學家的愛國精神。愛國是科學家精神的第一要義,愛國主義精神強化科學家的精神動力、指引研究方向,是科學家協同共進的價值共識。愛國主義精神不僅源于國家認同的本能和中華文化的熏陶,還受到中國現實情況與國家建設需要的使命感召,沿襲了強烈的時代責任感。從李四光、錢學森、錢三強、鄧稼先等一大批為建設新中國不懈奮斗的老一輩科學家,到谷超豪、黃昆、葉篤正等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他們無一不是愛國科學家的典范。他們秉持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主動肩負起歷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學追求融入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偉大事業,鞠躬盡瘁、矢志報國,為祖國和人民作出彪炳史冊的重大科技貢獻,以實際行動為“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做出最生動注腳,譜寫了精彩的人生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