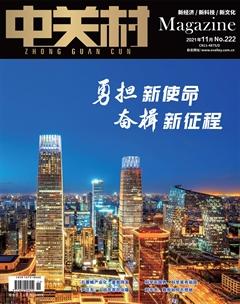侵犯商業秘密罪“重大損失”的認定
楊光 曹紅坤

基本案情:
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A公司系主營技術開發、計算機系統服務、銷售軟件等業務的國有控股公司,被告人李某某于2009年入職該公司,擔任業務分析師并簽訂保密協議等文件。工作期間,被告人李某某參與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等項目的數據架構工作。
2013年,被告人李某某在A公司在職期間,出資成立B公司,經營范圍包括計算機軟件開發,計算機系統集成,計算機信息領域內技術開發、技術服務、技術咨詢,計算機軟件銷售等。2014年,李某某自A公司離職,于同年擔任B公司法定代表人、總經理。
2013年,B公司以人民幣57.15萬元的價格向X銀行北京分行銷售軟件,經鑒定,軟件結構目錄與A公司的某平臺軟件相同,有188個源代碼與A公司的某軟件的非公知源代碼具有同一性。
2015年,B公司以人民幣65.7萬元的價格向Y銀行上海分行銷售軟件,經鑒定,軟件有106個源代碼與A公司的某軟件的非公知源代碼具有同一性。
2016年,B公司以人民幣30萬元的價格向Z銀行銷售軟件,經鑒定,軟件有122個源代碼與A公司的某軟件的非公知源代碼具有同一性。
2018年5月12日,被告人李某某被民警電話傳喚到案。
案件焦點:
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中,權利人“重大損失”如何認定。
裁判要旨:
法院經審理認為:關于辯護人認為B公司已分別于2013年及2015年取得相關系統軟件的著作權登記證書,故在此之后簽訂的合同不應作為計算損失依據的辯護意見,經查,著作權登記證書雖可以作為證明著作權歸屬的初步證據,但鑒于我國著作權登記制度并不對登記人是否享有著作權進行實質審查,結合被告單位在2013年至2014年無任何研發支出,以及證人曾篡改字符串的證言,且在案無其他證據佐證的情況下,無法將被告單位取得的著作權登記證書單獨作為認定著作權權屬的依據。辯護人的相關辯護意見,法院不予采納。
關于辯護人認為B公司的軟件銷售金額不能作為認定A公司實際經濟損失金額的辯護意見,經查,首先,本案存在商業秘密。根據公安機關向A公司調取相關軟件的源代碼并委托鑒定機構進行鑒定,得出兩個項目軟件源代碼在2017年9月4日、2018年8月9日之前不為公眾知悉的結論。結合公安機關調取的A公司的保密制度、與被告人李某某等人簽訂的保密協議、公司內部權限、軟件銷售合同等材料,足以證明涉案軟件是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并經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是商業秘密。
其次,被告單位B公司及被告人李某某實施了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根據在案鑒定意見,無論是被告單位銷售給X銀行Y銀行還是Z銀行的軟件,均與A公司相關非公知軟件具有同一性。同時,被告人李某某作為B公司2013年的實際經營人、2014年后的法定代表人,應當知曉公司銷售的涉案軟件的來源及銷售情況。其在A公司任職期間,曾參與過某軟件前期數據模型開發,對該項目是A公司的商業秘密其亦具有明知。雖然被告人李某某辯稱涉案軟件系找外包團隊研發,但其始終無法就此提供任何證據,相關公司賬目亦證明其間B公司沒有任何研發投入。綜上,被告單位B公司及被告人李某某的行為應當以侵犯商業秘密論。
第三,被告單位及被告人的行為給商業秘密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已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侵犯商業秘密罪是結果犯,侵權行為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是犯罪的構成要件。一般說來,計算侵犯商業秘密造成的重大損失可遵循以下原則:第一,對于能夠計算權利人損失的,以權利人實際損失數額作為計算金額;第二,對于權利人損失數額難以計算的,以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犯商業秘密所獲得的實際利潤計算權利人的損失數額。本案中,A公司的損失數額和B公司所獲得的實際利潤確均難以查實。A公司的損失方面,因為被告單位及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可能會造成其市場份額被削減,可能會造成其競爭力減弱,還可能造成其產品在市場上的地位遭受打擊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具體數額難以計算。對于B公司來說,完全將本案的銷售金額認定為被告單位所獲取實際利潤亦不客觀。對此,法庭認為,本案在認定重大損失時綜合考慮權利人的行業地位及研發成本,保護商業秘密的合理支出費用以及侵權人所取得商業秘密的成本,侵權人使用商業秘密之前的經營情況與使用之后的獲利大小等綜合評判。本案中,B公司在2013年至2014年間無實質研發投入的情況下,仍對外售出多筆金融軟件產品,且此種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持續多年,銷售金額達150余萬元,也正是這種犯罪行為為公司帶來“第一桶金”,對該公司成立初期經營情況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綜上,可以認定B公司及李某某給商業秘密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辯護人的相關辯護意見,法院亦不予采納。


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第二百二十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五十三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單位B公司犯侵犯商業秘密罪,判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
二、被告人李某某犯侵犯商業秘密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二個月,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
后B公司提起上訴。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后語:
科技的發展和專業分工的細化,帶來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的辦理難度的不斷加大。本案認定的難點在于侵犯商業秘密罪的“重大損失”的認定,此外本案具有軟件源代碼專業性強、電子數據提取鑒定難等特點。基于本案審理過程中對證據的綜合判斷,本文對侵犯商業秘密刑事案件的證據審查重點予以提示。
1.“重大損失”的認定
根據1997年修訂的《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侵犯商業秘密罪要求侵權行為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根據2004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規定,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損失的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的屬于“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給權利人造成的損失數額在二百五十萬元以上的,屬于本罪規定的“造成特別嚴重后果”。本案的認定難點在于在案件審理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三)》尚未出臺,是否可以將侵權單位違法所得認定為“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存在爭議。
侵犯商業秘密罪是結果犯,侵權行為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是犯罪的構成要件。一般說來,計算侵犯商業秘密造成的重大損失可遵循以下原則:第一,對于能夠計算權利人損失的,以權利人實際損失數額作為計算金額;第二,對于權利人損失數額難以計算的,以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犯商業秘密所獲得的實際利潤計算權利人的損失數額。本案中,A公司因為被告單位及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可能會造成其市場份額被削減,可能會造成其競爭力減弱,還可能造成其產品在市場上的地位遭受打擊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具體數額難以計算。而完全將本案的銷售金額認定為被告單位所獲取實際利潤亦不客觀。因此,在認定侵犯商業秘密罪的重大損失時,應綜合考慮權利人的行業地位及研發成本,保護商業秘密的合理支出費用以及侵權人所取得商業秘密的成本,侵權人使用商業秘密之前的經營情況與使用之后的獲利大小等綜合判斷。
2020年9月12日,最高法、最高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三)》,該解釋第四條明確了因侵犯商業秘密違法所得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的,應認定為“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違法所得在25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的造成“特別嚴重后果”。該解釋的出臺,也為該類案件的審理進一步明確了思路和標準。
2.鑒定結論的重點審查
知識產權案件具有很強的專業性,侵犯軟件類商業秘密案件尤為專業。基于行業特點和商業秘密的特有表現形式產生的技術難題,給案件的事實認定制造了天然的鴻溝。偵查機關辦理案件過程中委托專業知識產權鑒定機構作出的非公知鑒定和同一性鑒定,是此類案件的核心證據。但由于偵查機關在電子數據提取及委托鑒定過程中存在相關問題,導致鑒定結論有時存在瑕疵或問題。因此,審判機關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應注重審查鑒定結論,理解本案商業秘密的存在形式及技術表現等,如本案涉案軟件的非公知密點選取、目標代碼與源代碼的對應關系等重點問題需要深入了解。辦理案件過程中有時可以與鑒定機構、鑒定人員進行溝通交流,有助于輔助理解技術事實等關鍵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