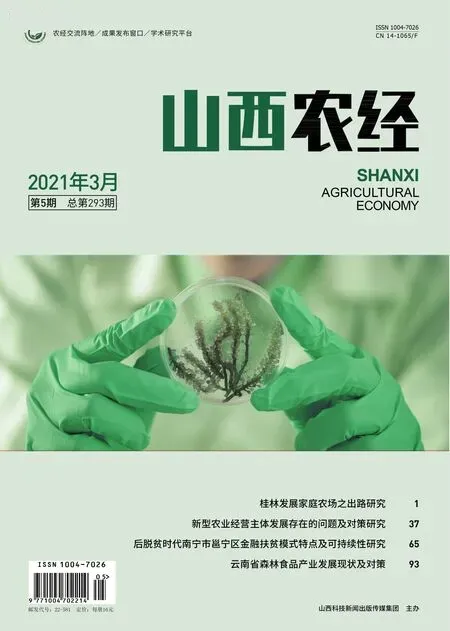精準資助視野下高校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次生災害”解耦
□向科衡,梁鐘兒,蔣淑慧
(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往往具有突發性、彌漫性和擴散性,給高校帶來較為嚴峻的管控局面。由于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周期長、結果不可控,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特殊人群——家庭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往往會遭到接二連三的“次生災害”。這些“次生災害”的影響面廣和深度深,可能影響到高校整體工作安全穩定展開和疫情聯防聯控的效能。這對高校在聯防聯控中把控“最后一道防線”提出了更高要求[1-2]。
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前、中、后,如何實現對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的專項資助精準公平,如何識別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的困難級別和影響程度,如何構建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次生災害”防御應急體系,高校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下的精準資助如何實現高效運作,具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以微觀社會學視角解耦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下高校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次生災害”,具有現實意義。
1 高校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資助研究綜述
目前學界對于高校困難新農人學生資助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在宏觀政策和年度數據方面,韓麗麗等(2018)分析了改革開放近40 年我國高等教育資助體系的政策演變。
在資助體系建構方面,張永(2017)以脫貧攻堅視角提出高校困難新農人學生精準資助的實踐路徑。展偉(2018)以高校困難新農人學生精準育人轉向的實踐向度構建了精準育人的現實路徑,這響應和契合了代蕊華等(2017)、曲紹衛等(2018)[3]提出的困難新農人學生精致資助育人的成效和目標路徑。
在育人體系構建方面,姚臻(2014)提出了創新舉措,包括建立責任追究機制、完善資助信用機制、建立就業幫扶機制、讓資助工作與感恩教育相結合等。
在高校困難新農人學生資助模式創新和路徑優化方面,王秀珍(2015)在分析我國困難新農人學生資助模式存在的問題及原因的基礎上,提出優化資助模式的對策,包括更新資助理念、重建資助原則、優化資助方式、創新運行機制、典型帶動等。
綜上所述,目前學界對于困難新農人學生資助相關研究依然以政策比較研究、框架模式探索及對策研究為主,研究方向較為宏觀,缺少對于微觀視角的研究。困難新農人學生在公共衛生事件下遇到的“次生災害”不僅是經濟方面的影響,也會影響到困難新農人學生的心理、行為和價值觀。因此擬通過微觀社會學的理論嘗試解決精準資助育人過程中的內在互動儀式,從而提升高校扶貧及精準資助工作的效能。
2 研究方法與研究過程
研究響應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應急管控的要求,采取“隔離法”,針對浙江省某高職院校92 名申報家庭經濟困難補助的大學生,進行網絡視覺民族志的定性研究。網絡視覺民族志體現了地點和材料分析的差異。Crotty(1998)提出視覺民族志作為一種體驗、解釋和描繪經驗、文化、社會物質和感官的方法,由不同議題和理論制約的原則所構成;而pink(2006)提出攝影、錄像和其他數字與膠片媒體實踐以各種特殊方式被體驗并被理解。網絡視覺民族志調研分析受訪者提供的攝影照片、拍攝的短視頻,根據視覺與感官經驗其他元素的不可分割性,處理和建構視覺元素所構成的理論,理解視覺和數字媒體。
本研究以某高校資助政策的發布和申報流程為研究的時間區間,以92 名受訪大學生提交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家庭經濟困難的“云家訪”照片和證明家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佐證短視頻為樣本,對照片和短視頻進行定性分析。
研究采用MAXQDA2018,依據照片和短視頻對信息樣本進行歸類、編碼、逐個比較。為了確保92 名大學生的隱私,研究采用了匿名定性分析方式,隱去所有大學生的私人信息,只留存視頻和照片的編號。
3 研究結果
基于92 名大學生的佐證短視頻材料和“云家訪”照片材料,將樣本分為3 組,A 組30 名,B 組30 名,C組32 名,逐一導入到MAXQDA2018 進行視覺材料分析,通過對視覺材料中出現的構念和概念進行篩選并分組。
通過詞頻統計可見,家庭勞動力無收入、家庭勞動力疾病、原生的經濟困難在每個組中占比均較高。其中,原生的經濟困難主要由于該生來自貧困村或貧困鄉,而更多的申報原因在于隔離期勞動力缺少工作機會或家庭無任何收入。通過對視覺材料樣本的分析與內容編碼的建構,得出以下基于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下困難新農人學生“次生災害”儀式影響路徑的機制和互動儀式與資助供給的理論框架。其中,困難新農人學生“次生災害”儀式影響路徑的機制參考了互動儀式鏈內容生產與輸出的原理,結合樣本編碼而得出框架模型。
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次生災害”儀式影響路徑分別為起源、組成要素和結果。在起源過程中,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遭受隔離并且有短暫的情感刺激,容易產生二次傷害,因此原生困難是互動儀式起源的一個重要誘因。緊接著,在“次生災害”逐步蔓延之后,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會產生集體的情感聚集,共同關注政策焦點,如學校或社會的經濟困難資助政策等。他們此時共享一種求助、擔憂和茫然的情緒狀態,并伴隨著反饋的強化,對資助政策的渴望以及對規則的強烈需求,在該階段形成了互動儀式的組成要素。當越來越多的集體關注到資助政策和扶貧政策后,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的互動儀式演變為各種結果,如集體關注到資助政策、對次生災害凝聚力的關注、對資助規則和行動違反的憤怒等。該階段均體現出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對于資助政策高度關注以及情緒高度共享的狀態。
通過對視覺材料樣本的構念進行組合并提煉核心的價值訴求,提煉了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下互動儀式與資助供給的理論框架。互動儀式是由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的情感能量(需求飽和、需求聚焦、需求迫切度)和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訴求的統一團結、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的身份符號協同組成。該互動儀式是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主動參與到資助申報的具體體現。資助審核有一定的標準,而此時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對于自身所陷入的“次生危害”產生自我評估、自我認知和價值觀嵌入。作為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的身份符號,他們既是大學生,又是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又具有次生災害受害者的新身份。因此,資助規則和扶貧空間的嵌入,需要互動儀式來順利完成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的訴求。資助體系的公平公正以及材料審核、審查、溯源是資助規則和體系的必要前置條件,而資助動機與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的身份符號緊密關聯。
4 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下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次生災害”解決對策
目前,各高校復學以來,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的“次生災害”影響依然存在。“次生災害”是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下不可避免的一個災害類型,也是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所要面臨的心理挑戰。解決“次生災害”,需要結合互動儀式進行群際情緒和輿論的引導。
其一,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的集體情緒比較敏感,容易引發大面積的群際情緒。在精準資助政策和規則制定方面,需要加強案例引導和實際樣板宣傳,讓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能夠有一個自我表達和自我傾訴的機會。在資助政策實施方面,采取多媒體實體記錄能讓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有一定自我內容輸出的“儀式感”。這種儀式感能夠提升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對資助政策的參與度和參與感。
其二,公正的資助評審規則和公開的資助評審過程,便于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對照條目進行一一核實,也能夠對他人的材料進行對比。通過材料提交和互相審核的對比,可以提高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對“次生災害”的同理心,實現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對自我認知的清晰定位及對他人互動價值的喚醒,提升資助政策的實際效能和價值觀傳達效果。
其三,通過互動儀式重塑和重建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的自我認知和自我認同,使其從短期的強烈情感中脫離出來。家庭經濟困難新農人學生在各種資助的互動儀式和活動中逐步脫離原來的自我定位,通過自我賦能和幫扶周圍其他學生來實現集體認同和自我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