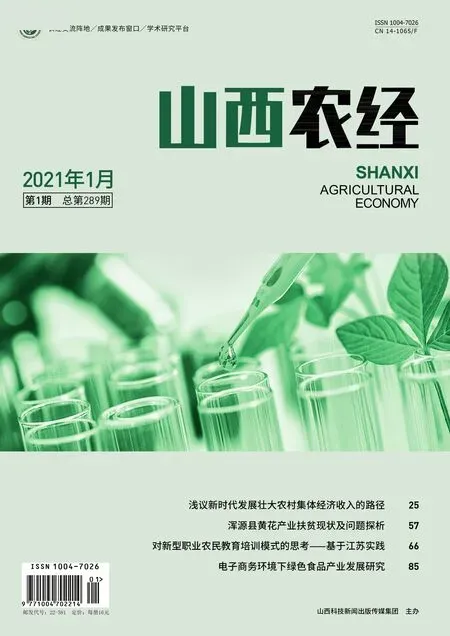“楓橋經驗”對鄉村振興工作的啟示和應用
□徐千航
(黑龍江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1 研究背景
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是針對我國當前發展現實制定的一項基本國策。十九大報告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其中提出了“七條發展之路”,最重要的一條是鄉村善治之路。所謂鄉村善治之路,即開辟我國鄉村基層社會治理的新道路,改變原有發展困境,采取創新的基層治理社會方法,為鄉村振興注入新動力。
“楓橋經驗”源于20 世紀60 年代的浙江諸暨,后經多年發展,形成先進的基層治理理念,“要充分珍惜楓橋經驗,大力推廣楓橋經驗,不斷創新楓橋經驗”。“楓橋經驗”作為一種歷久彌新、不斷創新的基層治理的探索實踐,在今天仍有其時代價值,為我國鄉村善治之路提供先進的指導。
黑龍江省是我國農業大省,截至2019 年末,鄉村人口共1 466.8 萬,占全省總人口的39.1%,鄉村人口數量龐大,村落眾多。雖然近年來大量鄉村摘掉了貧困村的“帽子”,但是不乏出現“返貧”的情況。同時,由于基層社會部分管理人員觀念陳舊、經驗不足、積極性不高等,導致黑龍江省基層社會治理中部分鄉鎮問題頻發。改變這種現象迫在眉睫,首要任務是學習先進經驗模式,“楓橋經驗”具有極大的研究價值與實踐意義[1]。
探究“楓橋經驗”中值得借鑒的經驗,結合其他地區發展實際情況,提出針對鄉村治理問題的新思路,形成具有新時代特征的鄉村治理經驗模式,解決鄉村發展動力不足等問題,開辟一條特色明顯的鄉村善治之路,對各個地區的鄉村振興有所啟示。
2 “楓橋經驗”和鄉村振興的有機結合
2.1 人民主體——高效辦事,增進福祉
人民是鄉村振興工作的主體。如何服務好人民、建設好基層高效政府是當前鄉村振興工作的重中之重。基層政府應強化為人民服務的意識。一些鄉鎮的村民辦一件事要跑七八個部門,花費近半個月時間,這與人民主體價值觀背道而馳。哈爾濱市某村兩位70 多歲的老人辦理鄉村低保有關事務,輾轉了多個當地政府部門才完成,其中一位老人的關節炎病復發,給家庭造成了極大困擾。
浙江省發揚“楓橋經驗”中的人民主體精神,搭建一站式黨群服務中心,讓老百姓最多跑一次即可辦完所有業務,極大促進了服務型政府的構建。“楓橋經驗”通過轉變基層政府職能,把政府由行政型轉變為服務型。上級政府將財政支出下沉到基層,利用互聯網平臺促進辦事效率提高,盡力實現人民需求的就地解決,營造“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的基層治理新局面[2]。
在基層實施鄉村振興工作時,必須把人民主體價值觀作為具體工作的指導。鄉村善治中需要把握好以人為本的理念,這同樣是黨和政府工作的核心宗旨和原則。
2.2 “三治”融合、“四防”并舉——創新基層治理路徑
“楓橋經驗”中所提到的“三治”融合即“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楓橋經驗”是我國基層治理中首次提出將“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到一起的治理方法。“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產生于“桐鄉經驗”,被譽為“楓橋經驗”的精髓,是我國新時代轉型時期鄉村治理的新思維。我國古代就有鄉賢治理社會的傳統,由鄉鎮中有威望的鄉紳或者是長者來仲裁當地發生的一些矛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就通過將一些鄉賢組織起來對當地社會進行教化管理,有效保證了基層社會穩定[3]。
桐鄉市屠甸鎮榮星村在全國率先成立鄉賢參事會,至今開展村級管理近百次,當地鄉賢在基層治理中建言獻策、示范引領、溝通村民,起到了很大作用。當時村里決定建設一個公園,但是當地部分村民因為風水問題對這件事持有很大反對意見。在這個基層矛盾將要激化時,鄉賢參事會出面協調,順利化解了矛盾,使公園順利落成。
在其他地區也同樣有著類似的情況。東北地區鄉村普遍存在著人情社會、關系社會現象。以哈爾濱市為例,某村的村民大部分是原住民,只有少部分外來村民。在這個村的村民間存在著很大的親緣關系,當地村委會成員也主要由他們構成。從管理學角度來看,不利于社會的治理,極易產生矛盾。可以考慮在各村構建鄉賢理事會,由當地村鎮中有威望、年長的長輩處理鄉村中的矛盾,化解治理危機[4]。
“四防”并舉是通過“人防、物防、心防、技防”創新鄉村善治的手段。調動社會力量組建基層隊伍,采用先進科技手段組建基層鄉村智能化治理平臺,組織心理咨詢服務,創新基層治理措施。
杭州市拱墅區有一個愛心科技體驗館,以實現“前端普遍服務”為目標,組建3 級社會心理服務平臺陣地建設,輻射帶動全區心理服務陣地建設。現在杭州共有100 多處心理服務實踐教學基地,擁有200 多人的心理服務專業團隊和法律服務專家團隊。同時,當地還著力探索“互聯網+科技”等社會治理新模式[5]。
將“三治”融合、“四防”并舉應用于其他地區,可以從以下4 方面入手。
一是發揮鄉賢治理的作用,激發基層治理的活力。組建鄉賢理事會、鄉賢議事會,會談解決鄉村中出現的問題與矛盾。基層問題在基層中解決,就地化解,矛盾不上交。充分培養和鍛煉基層鄉賢自主管理當地社會的能力,激發治理活力,改變原有治理困境[6]。
二是做好普法工作,組建法律服務團。基層政府依托當地律協、律所、高校組建法律知識宣講團,定期到基層村鎮進行普法教育和調研,考察當地群眾的法律常識水平,不斷提高群眾的法律意識,做好鄉村善治中的法治建設[7]。
三是創建鄉風文明,弘揚良好鄉風文化,鑄造“鄉魂”。良好的鄉村文化能對村民起到教化作用,對村鎮青少年的社會化過程和價值觀構建有所幫助。
四是利用互聯網技術構建智能社會治理平臺。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和互聯網技術可以構建起智能平臺,讓基層社會群眾足不出戶就能居家辦事[8]。
2.3 共建共享——鄉村善治新格局
培養鄉村基層社會村民的“共建共享”觀念,讓他們一起參與到基層社會的管理與建設中去,共同享受建設成果。城鄉社區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構建狀態,直接關系著社會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目標的實現。社會治理本身又是國家治理的組成部分,關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升與完善。以哈爾濱市為例,基層鄉村目前仍然存在不少閑置人口,大多是失業人員或者年紀稍大的人。調動村民積極參與到鄉村建設管理中,有利于激發內生動力,提高村民的自發性、自覺性,更有利于政府落實政策。
鄉鎮中的大事小情可以通過村民自主團體決策,決策后共同實行建設。一些地區城鎮已經采取了“民生實事項目代表票決制”,決策由“為民做主”轉向“由民做主”,大大提高了基層鄉村治理的效率和管理水平,提高人民滿意度。
3 啟示
以人民為主體的工作理念,有利于化解基層治理中的矛盾,形成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的新局面。將鄉賢治理、基層普法等工作引入鄉村,創建了基層治理新途徑。共建、共享理念讓基層群眾深刻參與到基層治理過程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將“楓橋經驗”轉化為鄉村振興工作的動力,是創新鄉村治理體系、走鄉村善治之路的一個新思路。
進入新時代,我國鄉村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變化。鄉村人口大量外流,人才引進困難,集體化生產程度不高,產業結構失調,成為了制約鄉村振興的重要因素。“楓橋經驗”提倡的人民主體模式有效調動了基層治理的積極性,在堅持司法主導作用的同時,始終堅持共建、共治理念,并且不斷融入新時代的理念,煥發出新的生機,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的解決機制,更加符合當前農村的現實需要;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促進農村的社會和諧與經濟發展,發展一種新的鄉村治理模式,產生一種示范性作用。
“楓橋經驗”符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強調基層治理、提高治理能力的需要。學習推廣“楓橋經驗”利于探究出符合國家發展方向的治理理論,豐富對于鄉村治理的理論與經驗,為鄉村振興的實踐提出更多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