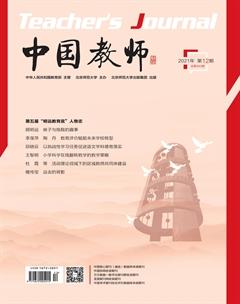草根教師的教育突圍
向其坤
工作的33年里,我在3所鄉村學校總計工作了28年,從小學教師到初級中學教師、校長,我不停地變換著身份角色。在瀾滄江沿岸那所薄弱的山村中學—大朝山中學工作過15年。仔細回味,這15年就是我的教育覺醒之年。
一、師生之橋
最初,校園環境異常惡劣:體罰成風,教師和學生之間缺少基本的信任,學生甚至在墻壁上偷偷寫出謾罵教師的污言穢語;課堂上教師與學生之間也只是機械生硬的關系—教師盯著天花板“講”,學生瞅著窗外“聽”。自言自語的教師,呆若木雞的學生,這一切都說明:課堂已經失去了本身的價值和意義!
面對這種境況,我開始了“師生之橋”的書信活動。第一次以“老師,我想悄悄對您說” 為題,采集學生的真實想法。學生們在撕下來的鋸齒形作業紙上努力地訴說他們天真直率的想法,他們渴望理解、渴望得到教師的關愛啊!后來,我自費給每位學生配一個信封,信封上標注“魅力師生之橋? ×××同學”。再給全體同學寫了一封公開信,向他們敞開我的真實想法,提出我對他們的希望,說明“師生之橋”的意義等。在公開信里面我強調,只要有疑問、想法都可以寫成信或字條放到我辦公桌上,我再找同學給予針對性的答復。對學生在信中提及的所有問題不向任何人公開,即便是違紀違規的事情。
于是,新型的師生關系在我和學生之間悄然形成。漸漸地,我成了受歡迎的老師,有學生對我表示“不滿”:“向老師,您為什么不擔任我們的老師啊?是不是看不起我們?”“迫于”學生的信任、希望,我只能悄悄收下這部分愿意追隨的“編外學生”。看著他們歡呼雀躍的樣子,我品嘗到了師生之間暖暖甜甜的味道。師生關系的調整、升級也讓我的課堂教學發生了質的變化:同學們能針對教學問題搶答、討論、爭論,伴隨和諧愉快的笑聲,我們的課堂開始飄出了振奮人心的掌聲。
每學年,我都會調整“師生之橋”的實施細節,使之更加貼近教育和教學的需要。多年下來,數千個信封塞滿了我的抽屜,每一個信封里都是學生的涓涓心聲。這些原生態的細流沐浴著我的心靈,時時警醒、潤澤、滋養著我。多少次搬家,其他物件損毀、遺失我都可以不顧,唯獨這些成了我的第一隨身寶貝。
二、教育場
從師生關系逐漸改變的過程中,我看到了學生們心門敞開的美好過程。這種美好的變化激勵著我對教學進行思考,也促成了我的基本教育教學風格的形成。我是一名物理教師,得益于對磁體及磁場的課堂教學的頓悟,我嘗試提出了“教育場”的育人理念。簡單說來,“教育場”就是教師周圍存在的育人之“場”。教師自身建構起來的“場”總是學生心向往之的無形氛圍,它比一般所言的“氣場”更高級之處在于“教育場”是以教師個人的性格、氣質、學養、魅力影響與改變學生的。
“教育場”應該包含兩方面重要內容,一是“師生合一”的和諧關系的締造,這是“教育場”存在的物質基礎,反映的是人和人(教師和學生)之間的親密關系;二是“教育場”在課堂教學里的呈現,反映的是人與物、人與事件(教師與學生形成一個共同體如何面對課程、教材等)的融合關系,即轉化為它的子場—教學場,這是“教育場”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因此可以說,我的教育道路就是不停地探索和實踐“教育場”理念的人生之路。
三、優秀鄉村少年
我出生于鄉村,成長于鄉村,從事教育工作也服務鄉村近30年。鄉村文化的變異、頹廢、衰落,特別是留守兒童大量產生的現象引發我對鄉村少年、鄉村未來的焦慮與思考。也是在大朝山中學,我開展了“優秀鄉村少年”評選的探索。“優秀鄉村少年”評選是針對鄉村少年,特別是留守少年精神扶植的育人探索行動,旨在塑造鄉村少年健康、樸實、堅毅、果敢、智慧、自信的精神形象,為未來鄉村的經營、建設打下堅實的基礎力量,為未來鄉村文化的復興、鄉村人才的儲備、鄉村經濟的振興貢獻力量。“優秀鄉村少年”的基本標準是:
1.從小生活在農村,帶有濃厚的“泥巴泥土味”,沒有嬌生慣養的習慣。
2.具有良好的身體素質和健康活潑的童年野趣。
3.不說謊,不給家庭添亂,不給家庭惹事,不只顧自己,具有初步的家庭責任感。
4.會干好農村最常見、最基本的農活,吃苦耐勞,初步體驗勞動成就感,懂得所在村寨的文化禮儀及習俗,村民反映良好。
5.孝敬父母,不與父母頂嘴,聽從父母安排,周末和寒暑假期間幫助父母做好農活,汗流浹背,用心體驗“汗滴禾下土”的勞動生活。
6.即便是單親家庭的孩子或留守兒童甚至是孤兒,也不自暴自棄,有自理、自立的意識和能力。
7.無論貧困還是富裕,都始終如一地愛自己的家庭;無論是怎樣的父母,都始終如一地孝敬他們。
我意圖通過這個探索活動塑造鄉村未來的家長(即現在的少年)。實際一點說,就是擁有這樣少年的鄉村的未來才會有希望!“優秀鄉村少年”的評選給留守兒童的精神培育、未來鄉村文化的重建開掘了新的路徑。也正因如此,擔任這所中學校長之后,我把“發現自己,發現師長,發現同學,發現鄉情,努力做一名有精神底氣的朝山好少年”定為該校學生的成長目標。
《人民教育》2019年第1期,刊登了我的小文《鄉村學校特色發展需要三個意識》。我以為,這是對我28年鄉村教育探索和實踐的最高認可!
四、創造教育現象
純凈的、至上的教育總是與經典的閱讀相伴共舞的。我讀到了蘇霍姆林斯基關于“創造教育現象”的論述:“教師在觀察、研究和分析事實的基礎上去創造教育現象,這正是創造性研究的最重要因素—預見性之所在。不研究事實就沒有預見,就沒有創造,就沒有豐富而完滿的精神生活,就不會對教師工作發生興趣。”以此分析,我的教育實踐活動都穿著“創造教育現象”的外衣!我在教育科研上曾存在不小的誤區,認為研究就是鴻篇巨著的論文撰寫、痛癢難辨的課題研究……事實上,創造教育現象是另一種更簡易、更靈活、更能貼近基層教師、更契合教師當前的“最近發展區”的教育科研活動。蘇霍姆林斯基說:“一個教師可能在創造性地進行工作,但他并不從事那種從研究事實中引出科學結論的意義上所說的研究。我們在這里所指的是研究一些這樣的問題,這些問題雖然在教育科學上已獲得解決,但是當一個創造性地工作的教師一旦成為理論和實踐之間的中介人,這些問題就經常以新的方式出現在他的面前。”創造教育現象的產生已經相當明白了,即起于教師對教育教學“遭遇”的困惑。無論“遭遇”引出的問題前人有無研究,教師都要用心對待它,變“遭遇”的困惑為研究的對象。教師展開行動研究,適時作好手記、札記、隨筆、研究筆記等文字記錄工作,根據研究對象的反饋情況靈活調整教育教學行為,直至困境的消除。基礎教育教師專業發展的羽翼更多的是在創造教育現象中豐滿起來的:每一次創造教育現象的行為之后,教師就能長出一批羽毛;所遭遇的困境完整解決之后,教師的羽翼就會豐滿起來,翅膀就會硬朗起來,教育教學的內心也就異常地強大起來。
以書面形式反思、整理這些研究過程、心得,就是一篇篇實踐性極強的好文章,這樣的文章就具有較強的生命力,適合向更多更廣的教育同行分享,這是創造教育現象外在的價值體現。這種結果的出現,將從本質上開啟教師的教育專業發展的自覺之路。創造教育現象的實踐研究,其價值還在于研究過程里面的新的教育意蘊、新的育人規律等的觸及與發現。
五、好奇心保衛戰
無論是學生還是教師,都需要“好奇心”支撐起學業、事業。沒有好奇心的激發、呵護、培養,“見證奇跡”的時刻不可能發生。
“奔六”的路上,創造教育現象,于我而言,依然成就著我的職業幸福。幾百號學生中,總會有那么幾個特立獨行的學生,他們的稟賦優于常人,行為也異于常人,喜歡搗鼓物件,喜歡閱讀科幻小說;敢大膽地向我的講解或教輔資料的解答提出質疑并展示他們自己的“想當然”;能無視周遭環境的喧鬧而安靜地享受“孤獨”的樂趣:思考、深度閱讀等。這就是“精英”學生,是十年難遇的,更不是可以“教”出來的。作為一名普通教師,我需要對他們采取“另眼相看”的策略和措施:告訴他們,好奇心比分數重要,考上頂尖的大學的根本目的是與那些頂尖的學界大師相遇。有了大師的引領,這些“精英”才能為國家、社會、世界作出最有價值的貢獻。作為給他們的“獎勵”,我也只能悄悄地送上一本雜志社寄送我的樣刊,再寫上一句讓他們納悶的話—請你確信:善良是一種方法!四年之中,通過對特別在意的幾個“精英”學生的行動觀察,我形成了一篇感性小文,2021年8月9日,光明社教育家公眾號“聽雨”欄目推出了我的文章《離開“好奇心”,我們將失去教育的星空》。
我本身對教育也是存有“好奇心”的,這就導致了我那些“好玩”的教育之事的發生,關于教育探索、實踐的一些研究性文章的誕生。
“好奇心”讓我看到了學生的未來,也體會到了自己“功利”的現實—心是如此愉悅、透亮!
我是特級教師嗎?不是,我就是一個80年代中期的中師生,偏僻廣袤的山村就是我的重要教育領地。再高的榮譽于我而言都是身外之物,我更注重的是內心的豐盈與安然,連續十多年沒有“被優秀”是我非常平穩的表現,我慶幸因此不被紛擾的世事影響而能安靜地進行思考與探索。于永正老師說教師“終究把自己教成了孩子”,我深以為然。成為孩子意味著什么?“兒童急走追黃蝶,飛入菜花無處尋”,隱藏著多么深厚的教育意蘊:稚化為“兒童”的教師追逐的“黃蝶”應該是什么?“菜花”是什么?“黃蝶”為何要“飛入菜花”?更有意思的是,明知道“無處”,為何要“急走”而“尋”?我以為,教師的極致世界就在這里—追尋到“無處尋”的境界:只有“尋”,你才知道“無處”,而“無處”并非“無用”。這是一個美妙的教育的涵泳過程。像這樣,我這個普普通通的草根老師,能享受到沉潛教育的樂趣與幸福:
第一,樂此不疲的思考是我不會改變的習慣;
第二,“土”味,是所有中師生的命運,也是我一生都喜歡的味道。
草根的最大夢想就是這樣通過層層的突圍,向領袖的“葦草”—思想者靠近、再靠近!
(作者單位:云南省臨滄市云縣第一完全中學)
責任編輯:胡玉敏
huym@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