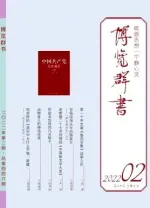發現周氏兄弟與碧云寺關系后
錢振文
壹
這些年,去香山的次數是很多的,但我一直沒有去過碧云寺。在香山玩的時候也曾向人打聽怎么去碧云寺,有人說往北走一出北門就到了。但也就是說說,真去碧云寺看看的興致還是沒有。想起碧云寺,印象里只有孫中山以及和孫中山有關的那個造型很特別的塔。
最近看周作人日記中周氏兄弟和祿米倉胡同的關系,再次發現周氏兄弟尤其是周作人和碧云寺的關系。就覺得該去碧云寺看看了。
周作人1920年底得了肋膜炎。從1921年年初開始治病。開始是山本醫生到家里診病,3月29日以后進山本醫院住院,直到5月31日出院。出院后的周作人有很長一段時間到西山碧云寺靜養。時間是從6月2日到9月21日。周作人6月2日的日記有:
二日?陰。下午移往香山碧云寺養病,重君先在,大哥、三弟及豐一同乘自動車送來,五時回去。晚雨。
從魯迅日記中可以知道,在6月2日送周作人來之前,魯迅已經來過兩次碧云寺了。一次是5月24日,這天的魯迅日記記
二十四日?晴。上午齊壽山來,同往香山碧云寺,下午回。
《魯迅全集》對“碧云寺”的注釋說:
碧云寺在北京西郊香山東麓,又稱西山碧云寺。始建于元至順二年(1331)。原名碧云庵,明正德年間擴建后改名。周作人病稍愈,魯迅于是日租定寺內般若堂西廂房,供他養病。
過了兩天,5月27日,魯迅又去碧云寺,整理收拾給周作人住的屋子。這天的日記說:
二十七日?晴。清晨攜工往西山碧云寺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經海甸停飲,大醉。
周作人在碧云寺過了差不多四個月清凈日子,但并不寂寞。雖然不近,家里人還是經常有人去看他。母親妻子兒子大哥三弟都去過。魯迅大概上去七八次。妻子信子還每過段時間就到山上給他理理發。除了家里人,周作人的北大同事李大釗、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等也頻繁到碧云寺看望周作人。和周作人平常來往密切的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更是多次到香山碧云寺看周作人。8月份周作人有兩次坐轎到香山甘露旅館,都是和沈氏兄弟聚會。其中一次是8月26日。這次來,沈氏兄弟還帶著剛到北大任職的張鳳舉:
上午信子來。士遠、尹默偕張鳳舉(君黃)來訪,五人同往甘露午餐。
張鳳舉是剛從日本回國的年輕人,這是他第一次見到周作人。在拜見同事周作人之前,張鳳舉先認識了魯迅。8月22日,在沈尹默召集的一次飯局上就有同時出席的魯迅和張鳳舉。這次聚會的前一天是星期天,魯迅剛剛到山上看過弟弟周作人。在這次聚會上,他們的談話肯定會說到在西山養病的周作人,甚至就是在這次聚會上幾個談話的人說定近期上山去看周作人。所以8月25日魯迅給周作人的信里說:
前天沈尹默紹介張黃,即做《浮世繪》的,此人非常之好,神經分明,聽說他要上山來,不知來過否?
從日記看,前兩個月周作人主要是待在自己住的地方。八九月以后,大概是環境逐漸熟悉了,他開始到寺廟里各處游覽。日記中記載了他曾經去過的各個地方如“下午至塔下一游”“至西邊山上一游”“下午至寺后山上一走”“往水泉一轉而返”等。
如果不到現場去,周作人日記中說的這些地名就只是個字眼而已。
貳
過去到香山都是從買賣街上去進香山東門,這次我們的目標是碧云寺,所以從香山站下車后的分路口往西北方向去。從這開始,路面換成了用大塊石條鋪砌的石板路。鋪砌用的石條一般都有一米多長、幾十厘米寬。路邊有個說明牌介紹說這條路叫煤廠街,過去這里建有煤廠,囤積銷售從門頭溝運過來的煤。20世紀50年代,好像是1953年吧,為了方便群眾前往碧云寺紀念孫中山先生,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把這條街鋪砌成了幾米寬的石板路。鋪砌這種高等級的石條做路面,現在在北京能看到的也只有天安門前的一小段。說明在某段歷史時期,碧云寺的地位是很高的。
碧云寺的東門和香山的北門左右相望。
香山的門票是5元錢,而碧云寺的門票是10元錢。
眼前的碧云寺和想象中的碧云寺完全不同。想象中的碧云寺就是個單體建筑,也就是廣為宣傳的和孫中山先生有關系的那個造型特別的金剛寶座塔。這種造型的塔在北京還有一座,在動物園后面的五塔寺。除了那個金剛寶座塔,我以前沒有看到過碧云寺其他建筑物的影子。
也就是說,眼前的碧云寺是陌生的,但又不是完全陌生。我知道終會看到我熟悉的那座塔。但我又并不急于看到那座塔。眼下這些陌生的建筑每一座足夠精致、耐看。碧云寺不是只有一座塔,它是一座結構完整的寺廟。一般寺廟里的內容這里都有。我們沿著寺廟的中軸線一點一點看過去。山門和山門里的哼哈二將、四大金剛,彌勒殿,釋迦牟尼殿,菩薩殿。殿堂大多是明代遺物,設計簡樸。殿堂外松柏夾道,環境清幽。山門外的一對石頭獅子、彌勒殿里銅質彌勒佛等都是精致的古代文物。
最后一進院是中山堂。中山堂是1925年祭奠孫中山的地方。正殿里有孫中山雕像,兩側廂房是孫中山生平展覽。從這兒開始,和我們過去對碧云寺的了解開始對接起來了。
所有的整座寺廟依山而建,每穿過一座殿后拾級而上,便會到達下一進院子。從中山堂再往后就是我們熟悉的金剛寶座塔了。剛才在中山堂看展覽的時候對這塔就了解很多了。但不知道為什么,我們去的時候,塔基外面正攔著一道隔離帶,讓我們不但不能靠近石塔,也不能到石塔周圍去轉一轉。周作人日記中說的“塔下”大概就是這里了。“塔下”應該是一個面積不小的院子,我們沒能到塔后去看,也就不知道從塔院后面能不能到周作人說的“西邊山上”“寺后山上”。
沿中軸線往上走的時候,我已經注意到了中軸線兩邊的跨院。我猜想,周作人那時候肯定和中軸線上這些殿堂關系不大,他住宿和活動的區域應該是在兩邊的跨院。現在,中軸線看完了,我此行的真正目的才剛剛開始。
但我們去的時候并不知道周作人住過的般若堂是在中軸線左邊還是右邊。我們先去的是右邊的卓錫泉。這里據說是乾隆的行宮,也是乾隆很喜歡的地方。周作人日記中說的“水泉”應該就是這里了。水泉院真的有流水淙淙,是不是泉水不敢說。這里是一處山崖的背后,山崖上面好像就是塔院。這里最奇特的景觀是從崖壁上長出來很多的松樹柏樹。當然這種景觀在香山是很多的。我早就注意香山各處墻壁上生長的古柏。當然,崖壁下、溪水邊更有很多高大的老樹。我近距離觀察一棵粗壯的柏樹,樹上的標牌說這棵樹的樹齡是310年。
看完水泉院往下走,到一個展廳外邊,問一個站在廳外的工作人員般若堂在哪兒?她稍微一想說:“就沒這個地。”這話挺讓人失望。但也在意料之中。來碧云寺之前我就擔心周作人當年住的應該是寺廟里的寮房,現在說不定早拆了。或者是成了非開放區域的辦公用房,就算還有,也沒辦法識別。你想想,周作人到碧云寺休養是1921年的事,整整100年了。
我們決定到對面的跨院去看五百羅漢堂。橫著走到對面的跨院卻是羅漢堂下面的一個院子,有主殿和左右廂房。屋子里面都是圖片展覽。在院子門口我看到掛著牌子上寫是禪堂院。我們就琢磨這個“禪堂”和“般若堂”莫非是一個意思?用手機上網一查,果然。有人在文章中說:“宋朝著名的大慧宗杲禪師云:禪乃般若之異名。”這就是了!從門口回到院子左右兩邊的廂房,但我顧不上細看這些展覽的內容,我腦子里盤旋的一個問題是,周作人當年住的是這里的哪個屋?其實《魯迅全集》的注釋里說得很清楚,周作人住的是般若堂西廂房,但我上山的時候只記住了般若堂。我站在院子里的時候,左手的廂房正在暖陽的包圍中,看起來挺舒服,我便推測,周作人大概會選這個向陽的屋吧。
禪堂院也就是般若堂院子寬闊、高敞,院子里有兩棵巨大的國槐。1921年6月17日,家里人給周作人送來了“藤榻”,當天晚上他就沒回屋里睡覺,而是“晚臥院子里”。想來就是躺臥在這兩棵槐樹下。
從院門前的高臺階走下去是個大小和禪堂院差不多的外院,沒有房屋,只有花草樹木。
從禪堂院的外院走出去,已經是寺廟的山門外了。
周作人到西山養病這件事已經100年了。100年前的歷史發生地還好端端地存在著,這真出乎意外,令人欣喜。
叁
去過碧云寺后,想起來再看看周作人的《知堂回想錄》。《知堂回想錄》其中的一節題目就叫《西山養病》,對在碧云寺所住的屋子說得很清楚。他說:
我于六月二日搬到西山碧云寺里,所租的屋即在山門里邊的東偏,是三間西房,位置在高臺上面,西墻外是直臨溪谷,前面隔著一條走路,就是一個很高的石臺階,走到寺外邊去。這般若堂大概以前是和尚們“掛單”的地方,那里東西兩排的廂房原來是“十方堂”,這塊大木牌還掛在我的門口,但現在都已租給人住,此后如有游方僧到來,除了請他們到羅漢堂去打坐以外,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安頓他們了。我把那西廂房一大統間布置起來,分作三部分,中間是出入口,北頭作為臥室,擺一頂桌子算是書房了,南頭給用人王鶴招住,后來一個時期,母親帶了她的孫子也來山上玩了一個星期,就騰出來暫時讓給她用了。
這和《魯迅全集》那條注釋的說法是一樣的,都是“三間西房”。但這里周作人大概是把方向弄錯了。實際上碧云寺是坐西朝東而不是常見的坐北朝南,所有的正房都是西房,般若堂里的兩個廂房就應該是北房和南房。周作人所說的“三間西房”實際上一個是三間南房。不管是三間西房還是三間南房,總之就是我那天在禪堂院里看見的三間背陰的屋。至于為什么魯迅他們選擇這個屋而不是對面向陽的屋就不得而知了。可以確定的是,魯迅租定這個屋的時候,對面的三間屋也還是閑著的。周作人在《山中雜信》的第二封信中說到了他對面的屋:
近日天氣漸熱,到山里來住的人也漸多了。對面的那三間屋,已于前日租去,大約日內就有人搬來。
“天氣漸熱”提示我們,對于避暑度假來說,選擇背陰的屋也許是對的吧。
《山中雜信》是書信體的散文,以給晨報副刊編輯孫伏園寫信的形式報告他在西山的所見所聞,從6月9日開始分六次刊登在《晨報副刊》上。《山中雜信》的風格相當輕松隨意。《知堂回想錄》說到了《山中雜信》:
在五月與九月之間一總給孫伏園寫了六回的《山中雜信》,目的固然在于輕松滑稽,但是事實上不得做到,仍舊還回到繁雜的時事問題上來。
除了《山中雜信》,周作人在西山期間,還有兩個工作也冠以“雜”字。一個是《雜譯日本詩三十首》,一個是《山居雜詩》。《雜譯日本詩三十首》的按語說到了“雜”字的一個意思:
今年春間臥病,偶看日本詩,譯出若干首,近時轉地療養來西山中,始能整理錄出,并加入舊譯數則,共十三人,詩三十首。這并不是正式的選粹,只是隨意抄譯;有許多好詩,因為譯語不愜意,不能收入,所以仍舊題作雜譯詩。(《新青年》第九卷第四號)
這里“雜”是說選擇翻譯對象的隨意。而《山居雜詩》和《山中雜信》的“雜”則是寫作對象選擇的隨意。《山中雜詩》包括七首小詩,內容都是他在般若堂所看見的景象,主要是身邊所見動植物的細微情調。比如6月17日晚上寫的(四),把槐樹上不知什么蟲子的鳴叫和枯焦的氣味聯系了起來:
不知什么形色的小蟲,
在槐樹枝上吱吱的叫著。
聽了這迫切尖細的蟲聲,
引起我一種仿佛枯焦氣味的感覺。
我看了這首小詩,就想起來我在禪堂院看見的那兩棵老槐樹。院里的老樹,周作人當年有可能“看到“的老樹,除了這兩棵槐樹還有一棵柏樹。周作人8月10日所寫的《山居雜詩》(一)寫到了這棵柏樹和攀附在柏樹上的藤蘿:
一叢繁茂的藤蘿,
綠沉沉地壓在彎曲的老樹枯株上,
又伸著兩三枝粗藤,
大蛇一般的纏到柏樹上去,
在古老深碧的細碎的柏葉中間,
長出許多新綠的大葉來了。
而根據周作人日記,他曾在院里的藤蘿前照過相片,而照相的時間正是他寫《山居雜詩》(一)的同一天:“同豐一及鶴招在院中藤花北照相,八寸一枚。舊七夕。”可見,照相這種特殊的視覺活動,很大程度提高了景物的可見度。
除了院里的動植物,周作人也關注特殊環境中的人,包括游人。在《山中雜信》(四),他寫到了轉悠到般若堂的不多的游客,而且注意到一般游客都愛關注老樹的樹齡:
我前回答應告訴你游客的故事,但是現在也未能踐約,因為他們都從正門出入,很少到般若堂里來的。我看見從我窗外走過的游客,一總不過十多人。他們卻有一種公共的特色,似乎都對于植物的年齡頗有趣味。他們大抵問和尚或別人道,“這藤蘿有多少年了?”答說,“這說不上來。”便又問,“這柏樹呢?”至于答案,自然仍然是“說不上來”了。或者不問柏樹,也要問槐樹,其余核桃石榴等小樹,就少有人注意了。我常覺得奇異,他們既然如此熱心,寺里的人何妨就替各棵老樹胡亂定出一個年歲,叫和尚們照樣對答,或者寫在大木板上,掛在樹上,豈不一舉兩得么?
這是的確的。到現在,人們還是對老樹的年齡感興趣。碧云寺有很多老樹。我印象深刻的是煤廠街邊上的老槐樹和水泉院里的老柏樹。
不過,現在公園里的古樹都是登記在冊的,游人只要看樹上的標牌就能知道這樹的名稱和年代,這倒的確是解決了一個周作人當年觀察到的總是困惑人們的問題。至于樹齡是怎么測定出來的,我們外行的人也說不上來,但總不至于是周作人說的“胡亂定出一個年歲”。
(作者系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