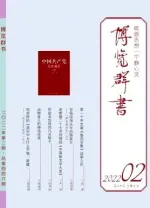“不足為外人道”的體會
王瀚洋
2017年9月8日,孫老師面向北大8000入學新生,發表了題為《珍惜》的演講,轟動全國。“珍惜當下,珍惜他人,珍惜健康,珍惜內心的渴望,珍惜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言簡意賅,發人深省。坐在臺下的我第一次近距離聆聽北大大師的教誨,暗自慶幸來燕園求學的選擇。而更加幸運的時候,在《珍惜》演講不久之后,我居然能入孫老師門下,成為老師門下最年輕也是最后一位博士生。也許是上天的眷顧,更大的幸運接踵而至。我在孫老師身邊受教四年有余,得恩師各種點撥,對四年前的五個“珍惜”有了“不足為外人道”的體會。
秋季學期,孫老師有一門《保險學專題》討論課,每次課要求一位博士生圍繞保險學前沿的學術研究,進行兩個小時左右的匯報。匯報過程中,老師和同學們可以隨時打斷提問。可以說,這是我們博士期間壓力最大的一門課,本來頂級期刊的研究就難以駕馭,隨時打斷、刨根問底的節奏更是讓人如履薄冰。大家在課堂上就學術問題,爭得面紅耳赤,老師則從旁進行引導和指導,最后做全面點評。不過,壓力歸壓力,我們從這門課中收獲也頗豐:從研究能力到展示、交流能力,都得到了全方位的訓練,因此,哪怕根本不計學分,幾乎每一位博士在學期間,年年都會上這門課。而相比于其他同學,我對這門課更是多了一份期待:因為每次課,主講的同學都會準備各種零食,供大家邊吃邊聊。我作為標準的吃貨,自然不想錯過這樣的機會。有些師兄聽說后,揶揄道,果然是關門弟子,老師越來越心慈手軟了。擱在我們那時候上課,誰敢在孫老師邊上吃東西?我心里清楚,并不是老師對我這個最年輕的博士生——關門弟子的偏愛放縱,而是老師奉行嚴慈相濟的教育理念:在學術、做人方面嚴格要求學生,并監督學生完成要求。而在生活、家庭方面,尊重學生的習慣,給予學生最大的幫助。老師對我這個關門弟子的嚴格要求,師兄們并不知道。
剛入師門的時候,我并不期待孫老師會非常細致地修改論文。畢竟老師太忙了,既是學術領域的領軍人物,又是學院院長,而直到我把第一篇論文發給孫老師以后,我才對老師有了新的認識。老師在回復中,首先從標題、理論深度、案例選擇、行文邏輯等方面,給出了八點明確的修改方向。然后從正文開始,逐字逐句修改,小到標點、措辭,大到文字表述,光成段的修改就多達14處。看到老師的修改,我在汗顏的同時,也由衷地佩服。老師后來和我說,她希望每篇寫出來的東西,都像抽絲一般嚴謹,環環相扣。在老師的指導下,這篇關于巨災保險的理論評述,我前后修改了十稿,我們師生的往來郵件近三十次。最后定稿的論文發表于國內財政學權威期刊《財政研究》,這對還在讀博的我來說,真是一種莫大的鼓舞。
在全球博士生培養體系中,有兩種典型模式:一種是導師給學生一些研究方向,學生自己探索,確定研究的路徑,導師糾錯提出建議。還有一種是導師像家長一樣給學生全面而細致的指導,手把手帶學生做研究。孫老師是后者的踐行者,她愿意用自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幫助學生全方位地成長,盡量少走彎路,而我在這個過程中真是獲益良多。除了論文之外,孫老師對我其他培養的環節,都有嚴格而全面的指導。比如,應該如何尋找“真問題”,如何寫好一篇論文,如何與學術同行進行有效溝通;甚至,如何訓練標準的英文發音。
學術上的嚴謹,老師不僅言傳,而且身體力行,把“優秀是一種習慣”這句話落實到每一篇文章,每一次演講。2021年北大經濟學院畢業典禮,孫老師受邀作為研究生導師發言。老師在寫發言稿過程中,準備引用一篇文章中的“前喻文化”和“后喻文化”這兩個概念,來表達她的一些觀點,但因為這不是她自己熟悉的經濟學領域的東西,老師不敢隨意引用,就去查閱這兩個詞對應的英文原文。這一查老師才發現,這兩個名詞的英文原詞和中文翻譯似乎是相反的,其中prefigurative 被譯成“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被譯成 “前喻文化”。老師感到不解,就去網上訂購這兩個名詞的來源書:瑪格麗特·米德所著的《文化與承諾—一項有關代溝問題的研究》,但沒訂上。于是,老師給我打電話,請我去北大圖書館查閱一下。我記得特清楚,當我在電話上告訴老師,我在圖書館借上了這本書時,電話那一頭的老師極其興奮,連聲說“太好了,太好了”。老師查閱了圖書館的中文譯本以后,發現中譯本的翻譯也是如此,仍不放心,生怕“以訛傳訛”,于是,又讓我幫忙下載英文原版電子書。這之后,老師又就這兩個概念與外國語學院、社會學系和經濟學院的相關教授討論。經過反復琢磨和思考,老師最后做了確認。老師這股子較真的勁,真是極大地震撼到了我。老師讓我明白,做學問不能隨隨便便,不能淺嘗輒止;一定要認真嚴謹,一定要尋根溯源。
培養是嚴格的,但在生活中,孫老師對我的關愛無微不至。像每一次出去開學術會議,無論是國內會議還是國際會議,老師都會和我確認經費來源,如果沒有來源的話,老師都會用她自己的經費來支持我參加各種學術活動。過節的時候,如果我不回家,老師都會邀請我們一起聚餐,分享節日的喜悅。這四年多,凡是我家里的大事,老師都會密切關注,并表示需要的地方都可以提供幫助。很多人戲稱博士生導師為“老板”,但孫老師在我心中,是一位關注、關愛學生的園丁,不管我遇到什么樣的困境,想到孫老師,就感到暖暖的,心里會很快平靜下來。

要說這四年最讓我受教的一件事,當屬2021年春季學期,我擔任老師《國際保險理論與實踐》課程助教時發生的“抑郁學生事件”。學期剛開始的時候,班上有個學生因患抑郁癥,申請長期病假。在看到醫院的證明后,孫老師考慮到學生的身體狀況,批準了她的請假,并囑咐她一定好好治病,早日康復。學期快要結束之時,這位同學向我表示,打算自學課程內容,參加期末考試。說實話,面對這種情況,有很多老師,或是出于同情,或是怕承擔責任,對患病學生通常是能“放水”就“放水”的。但在我和孫老師匯報了情況之后,老師表示,該生一學期沒有上課,也沒有完成平時作業,如果靠期末考試“放水”通過,這既是對這位學生的不負責,也是對其他辛勤學習這門課的學生不公平,更是對學校制度的不遵守。更何況,學生本身就患抑郁,課程內容如此之多,期末突擊自學,很有可能加劇學生的病情。因此,老師不允許學生以這種方式來參加考試,而是建議來年重修。在得到老師的答復后,我有些驚訝,卻十分佩服老師的原則性。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則讓我更加感嘆和敬佩。孫老師親自找抑郁的學生談話,給學生講她為什么要這樣做的道理。在了解她的病情之后,又幫忙聯系了一位優秀的醫生為她治療。得益于孫老師的安慰和醫生的醫術,學生的抑郁癥有了明顯的好轉。而我作為這件事的見證者,再次體會到老師嚴慈相濟的風格:堅守教學的底線,但這種堅守以愛護學生為前提,以公平、公正為前提。老師總是強調有教無類地對待每一個學生,但絕不搞簡單的“一刀切”。在“抑郁學生事件”中,如果老師“放水”,那么,對其他學生來說是不公平的。而如果老師只是堅持規定,而并不在意學生如何,那么,這對患病學生來說多少有些殘酷。老師如此處理,不能不說是一種智慧。而這一智慧來源于老師對教育真諦的深刻領悟,來源于老師對學生的大愛。我如果今后有幸成為一名老師,就有了一個行為的準則。
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如果今天“揶揄”我的師兄們回到燕園上課,孫老師一定會同意,讓他們邊吃邊聊,用最自在的方式上課。但要是誰言之無物,討論前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老師一定會不留情面地批評,指出問題的所在。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博士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