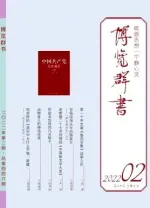讓“有溫度的田野”講中國(guó)
胡彬彬 郭炳亮
中國(guó)傳統(tǒng)村落是中華民族先民由采集與漁獵的游弋生存生活方式,進(jìn)化到農(nóng)耕文明定居生存生活方式的重要標(biāo)志,是各民族在歷史演變中,由“聚族而居”這一基本族群聚居模式發(fā)展起來的相對(duì)穩(wěn)定的社會(huì)單元,是中國(guó)農(nóng)村廣闊地域上和歷史漸變中一種實(shí)際存在的、歷史最為悠久的時(shí)空坐落。作為社會(huì)單元內(nèi)在結(jié)構(gòu)最為緊密的小群體,中國(guó)傳統(tǒng)村落的空間形態(tài)多樣、文化成分多元,蘊(yùn)涵著豐富深邃的歷史文化信息。通過其相互關(guān)聯(lián)、內(nèi)在互動(dòng),不斷傳承內(nèi)部文化、發(fā)揮社會(huì)功能,成為了社會(huì)有機(jī)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最根本的基礎(chǔ)。
我們常常說“中華民族”這個(gè)詞。“中華民族”是怎么來的?“中華民族”的構(gòu)成就是由無數(shù)個(gè)氏族和家族構(gòu)成,家族上面就是氏族,家族的下面就是家庭。村落是國(guó)家和社會(huì)最基本的構(gòu)成單元,家庭是民族最基礎(chǔ)的構(gòu)成單元。由于村落文化具有聚族群體性、血緣延續(xù)性的特質(zhì),并承載了中國(guó)久遠(yuǎn)悠長(zhǎng)的文明歷史,因而極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傳承性;村落成員的生產(chǎn)生活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有形或無形的文化形態(tài),從表面化一般形式的呈現(xiàn),到隱性化深層次的內(nèi)在文化結(jié)構(gòu)與內(nèi)涵,代表著國(guó)家和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體現(xiàn)著“社會(huì)人”由單一個(gè)體到家庭家族,進(jìn)而到氏族,最后歸屬于民族范疇,再直接引申到“國(guó)家”概念的文化層面的全部涵義。
如果想要知道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本真樣貌,我們需要到廣袤的鄉(xiāng)村當(dāng)中走一走。可以說,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根脈在鄉(xiāng)村。要探究行進(jìn)中的中國(guó)村落文化,則非走出書齋,走向田野不可。《村落中國(guó):中國(guó)大學(xué)生田野考察札記》(以下簡(jiǎn)稱《村落中國(guó)》)即是一部在田野之中誕生的書。
自2012年傳統(tǒng)村落保護(hù)被納入國(guó)家文化保護(hù)戰(zhàn)略以來,傳統(tǒng)村落消亡程度明顯放緩,部分還為地方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及文化的傳承保護(hù)提供了強(qiáng)有力的支持。但值得憂慮的是,傳統(tǒng)村落在保護(hù)的過程中仍然存在著諸多問題——同質(zhì)化現(xiàn)象嚴(yán)重,原住民參與感不強(qiáng),與本地原生文化的剝離等——讓人十分憂慮。有鑒于此,中南大學(xué)中國(guó)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先后于2016年7-8月、2017年7月對(duì)我國(guó)長(zhǎng)江、黃河流域的18個(gè)省的1569個(gè)傳統(tǒng)村落、200多個(gè)歷史文化名城進(jìn)行了田野考察。《村落中國(guó)》的編纂,即是從這兩次田野考察筆記之中遴選出來的精品。全書分上、中、下三冊(cè),根據(jù)田野考察點(diǎn)所屬的地區(qū)或文化區(qū)分為粵鄂皖地區(qū)等十二篇,每篇文章則由單人或團(tuán)隊(duì)完成。全書近90萬字,較為全面的記錄了這次考察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
田野考察札記的寫作在人類學(xué)等社會(huì)科學(xué)領(lǐng)域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jì)初,馬林諾夫斯基等早期人類學(xué)家在異民族地區(qū)考察時(shí),就已經(jīng)開啟了這一傳統(tǒng)。他提倡長(zhǎng)期參與觀察法后來成為現(xiàn)代人類學(xué)的方法標(biāo)志,并誕生出了《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這一經(jīng)典人類學(xué)著作。追溯到我國(guó),則至少可以到太史公寫作《史記》之時(shí)。“網(wǎng)羅天下放佚舊文”的司馬遷,曾經(jīng)親自到多地進(jìn)行考察,以求書寫內(nèi)容的生動(dòng)詳實(shí)。我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進(jìn)行田野札記的寫作,一方面繼承了現(xiàn)代人類學(xué)的書寫傳統(tǒng),一方面則來自我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札記寫作,既不像一般意義上的隨筆寫作般自由隨意,也不像學(xué)術(shù)論著般嚴(yán)肅,是一種介乎二者之間的調(diào)查報(bào)告。這樣的小文章,既能記錄研究者在調(diào)查過程中的靈光一閃,又能對(duì)調(diào)查對(duì)象的情況做一目了然的記錄,對(duì)于捕捉學(xué)術(shù)生長(zhǎng)點(diǎn),記錄研究者的思考過程等都大有助益,因而在田野作業(yè)過程中被廣泛采用。
“當(dāng)你進(jìn)入田野時(shí),民俗就與你迎面相撞”,董曉萍在《田野民俗志》中的這句話,可以說是對(duì)田野考察狀態(tài)的最好注腳。不僅是民俗,其他任何待研究的文化事象,如果一頭霧水地進(jìn)入田野,也容易丟三落四,甚至讓自己陷入到無窮無盡的困境之中。盡管在田野考察之前,各學(xué)科的慣例是要做各類“預(yù)案”,但就好比老師備課,預(yù)設(shè)的課堂與生成的課堂之間往往差距甚大。預(yù)設(shè)是為了減少意外,但田野之中卻處處皆有意外。做足預(yù)案,寫好考察日記,對(duì)于應(yīng)對(duì)書齋和田野、預(yù)設(shè)與生成等之間的差距,有著相當(dāng)?shù)谋匾浴T凇洞迓渲袊?guó)》之前,學(xué)界已經(jīng)有過類似的考察札記出現(xiàn)。不過,比較起來,《村落中國(guó)》更著力于學(xué)理性思考,在傳統(tǒng)村落考察的地域方面也更為全面。
田野,對(duì)于廣大的科研從業(yè)人員而言,既散發(fā)著無窮魅力,又讓人望而生畏。田野作業(yè)可以發(fā)現(xiàn)新材料、新問題,高質(zhì)量的田野是高質(zhì)量科研成果的基礎(chǔ);田野的復(fù)雜,在于所面對(duì)的自然環(huán)境、社會(huì)環(huán)境的復(fù)雜。我們面對(duì)的田野場(chǎng)域,迥異于學(xué)校簡(jiǎn)單的幾點(diǎn)一線的生活——活生生的人,基于各種利益的考量,需要我們?cè)谔镆翱疾鞎r(shí)做相應(yīng)的甄別。人類學(xué)、民俗學(xué)等的田野考察,不同于考古學(xué)、歷史學(xué)等學(xué)科對(duì)于文獻(xiàn)、文物等靜態(tài)資料的關(guān)注,它既要考察有形文化事象——建筑形態(tài)、藝術(shù)作品、儀式展演等,又要對(duì)無形文化事象——技藝、口傳文學(xué)等進(jìn)行深入考察。只見村落不見人的時(shí)代已然過去,“有溫度的田野”成為了新時(shí)代社會(huì)科學(xué)田野作業(yè)的追求。
村落研究,自然離不開對(duì)村民的研究。在《村落中國(guó)》這部書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對(duì)于村落有形文化的記錄,也可以看到對(duì)于村落當(dāng)中人的描摹——住在老宅中的村民、堅(jiān)守鄉(xiāng)村小學(xué)的教師……在《村落中國(guó)》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作為生活家園中的村落,也可以看到村落中守候家園的人。村落是活的,那么家園中的人呢?他們有的因?yàn)榧亦l(xiāng)貧窮落后而離開了家鄉(xiāng),有的因?yàn)榧亦l(xiāng)的旅游開發(fā)而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有的則因?yàn)檎w搬遷而成為了鄉(xiāng)土社會(huì)的“邊緣人”……念茲在茲的村落與世居于此的村民,讓人憂慮鄉(xiāng)村振興的可能性,讓人感喟村民艱辛的生活狀況,也讓人思考政府施政的成效與可行性。

總之,在編纂《村落中國(guó)》這部書的過程中,我們關(guān)注村落當(dāng)中有形的文化遺產(chǎn)與無形的文化資源,更關(guān)注村落中的人的生產(chǎn)生活狀態(tài)。沒有人,鄉(xiāng)村無法振興,鄉(xiāng)土文化無法傳承,鄉(xiāng)村也將成為空殼,而我們也將成為無家可歸的漂流者。“有溫度的田野”這一學(xué)術(shù)主張,就是為了避免我們與田野點(diǎn)對(duì)象之間機(jī)械、冷漠的取用關(guān)系。取代這種關(guān)系的,應(yīng)是一種溫情的、充滿憂患意識(shí)的田野倫理。我們不僅要憂慮我們的學(xué)術(shù),更要憂慮我們的田野和田野中的人。這也恰是《田野中國(guó)》這部書在著力追求的。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不同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書齋學(xué)問,研究村落與保護(hù)村落,必得深入到田間地頭,真聽真感受,才能收獲真知。當(dāng)今社會(huì)發(fā)展迅速,傳統(tǒng)的價(jià)值觀念、生活方式受到了巨大的沖擊,無論合理與否,傳統(tǒng)的村落文化都面臨著外來文化、城市文化的沖擊。想要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中國(guó)夢(mèng),勢(shì)必要以我們的傳統(tǒng)村落文化中的合理基因?yàn)榛A(chǔ),構(gòu)建屬于有民族氣派與民族特色的文化體系。這也正是《村落中國(guó)》編纂的初衷。
傳統(tǒng)村落中的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具體指的是什么?通過幾十年的考察經(jīng)驗(yàn)與理論思考,我們認(rèn)為,傳統(tǒng)村落文化當(dāng)中,至少應(yīng)當(dāng)關(guān)注如下方面的內(nèi)容。
首先是傳統(tǒng)的民居古建資源。國(guó)家層面對(duì)于古城鎮(zhèn)、古村落民居資源的保護(hù),往往都是將之納入各級(jí)別的文物保護(hù)單位之中。但也正如《古寺廟作為文保單位和宗教載體的身份博弈》一文中講到的,在廣大鄉(xiāng)村地區(qū),古廟宇數(shù)量龐大到保護(hù)不過來的程度,加之文保單位資金籌措困難,鄉(xiāng)村文保員待遇偏低等問題,讓人在揪心之余,也為如何建立好的民居古建保護(hù)制度而思考。在這篇文章中,考察團(tuán)隊(duì)對(duì)古寺廟“活態(tài)保護(hù)”的方式進(jìn)行了介紹——由僧人入駐古寺廟,一切運(yùn)營(yíng)由他們負(fù)責(zé),受政府監(jiān)督。
其次是傳統(tǒng)技藝與產(chǎn)業(yè)資源。鄉(xiāng)村振興的關(guān)鍵在于留得住人。傳統(tǒng)鄉(xiāng)村由于曾經(jīng)的區(qū)位優(yōu)勢(shì)不再,資源枯竭等歷史性原因,漸漸走向了衰落。“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xiāng)愁”是鄉(xiāng)村文化振興的目標(biāo),但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傳統(tǒng)技藝因?yàn)槭杖氲臀⒌痊F(xiàn)實(shí)因素,讓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背景離鄉(xiāng),長(zhǎng)此以往,鄉(xiāng)村振興定然后繼無人。對(duì)于傳統(tǒng)技藝而言,培養(yǎng)傳承人的訴求愈發(fā)強(qiáng)烈;對(duì)于鄉(xiāng)村產(chǎn)業(yè)來說,要吸引大量的勞動(dòng)力。當(dāng)然,我們還可以看到,許多的傳統(tǒng)村落由于旅游開發(fā)等原因,吸引年輕人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讓我們看到了鄉(xiāng)村振興的希望。
傳統(tǒng)村落當(dāng)中道德教化資源亦屬于傳統(tǒng)村落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村落文化的無形資產(chǎn),道德教化關(guān)乎村風(fēng)村治,是鄉(xiāng)村治理的重要手段。在《村落中國(guó)》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篇關(guān)于村落村規(guī)民約、族規(guī)等的調(diào)查報(bào)告——《關(guān)于古村落村規(guī)民約的對(duì)比思考》一文,作者通過對(duì)戴家山、石舍村兩村村規(guī)民約的對(duì)比,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宗族在村風(fēng)村俗方面依然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家訓(xùn)與信仰:基于福田鎮(zhèn)傳統(tǒng)村落的考察》一文,考察團(tuán)隊(duì)發(fā)現(xiàn)宗族家訓(xùn)中居然有保護(hù)古樹的條目,讓人著實(shí)驚訝于古人環(huán)保理念在當(dāng)代社會(huì)的傳承。
村落是一本厚重的書。在城市文化方興未艾,鄉(xiāng)村振興后勁不足的今天,村落的保護(hù)和發(fā)展面臨著重重困難。也正因?yàn)槿绱耍瑸榱耸刈∥覀兊奈幕},為了助力鄉(xiāng)村振興,村落文化研究必得下大功夫。一言以蔽之,不進(jìn)入田野,就無法了解村落;不了解村落,就無法認(rèn)識(shí)中國(guó)。
(作者簡(jiǎn)介:胡彬彬,中南大學(xué)中國(guó)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郭炳亮,中南大學(xué)中國(guó)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