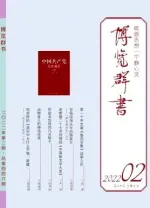孫崇濤——用學(xué)術(shù)吸引戲曲外行
陳建平

南戲是種什么樣的藝術(shù)?它的前世今生如何?它和當(dāng)代戲曲又有什么關(guān)系?問到這些,可能很多人會一臉茫然。而戲劇史家孫崇濤先生所著的《南戲論叢(增訂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20年版,以下簡稱《增訂本》),卻可以深入淺出、生動明快地告訴你關(guān)于南戲的奧秘。
《南戲論叢》初版由中華書局于2001年出版,初版自問世以來,就在戲曲界引起了廣泛關(guān)注;這次增訂,即應(yīng)讀者之需,除對舊版適當(dāng)訂正外,又增加了有關(guān)高則誠及其《琵琶記》、溫州地方戲、錢南揚(yáng)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等研究的幾篇文章,全書共分五部分:一、南戲研究述評;二、南戲通史通論;三、南戲作家作品研究;四、南戲理論研究;五、南戲劇評書評。這些文章是作者從事南戲研究四十年的論著選粹,基本代表和概括了作者研究南戲的觀點、方法、成果、范圍及歷程。雖然這是一本將文獻(xiàn)考證和史學(xué)研究相結(jié)合的學(xué)術(shù)專著,卻并不高深莫測、晦澀難懂,而是一部從形式到內(nèi)容都很“好看”的史論著作。謂予不信,請分述之。
通俗易懂、深入淺出的寫作觀念
一提到學(xué)術(shù)專著,往往會讓人望而生畏、高山仰止。作者卻一向主張:“學(xué)術(shù)表達(dá)方式應(yīng)該盡量做到通俗明白,面向大多數(shù)讀者”,并且認(rèn)為:
戲曲學(xué)術(shù)研究不應(yīng)該躲進(jìn)象牙之塔,與大眾尤其是廣大戲曲業(yè)內(nèi)同人及愛好者隔絕,成為孤家寡人式的圈子學(xué)術(shù),而應(yīng)該設(shè)法讓更多的人去關(guān)注它,讀懂甚至喜歡讀它的研究成果,使之真正成為戲曲文化建設(shè)的一翼。(《我與南戲研究(代序)》,《增訂本》P12)
為了打破“隔行如隔山”的固有觀念,為了讓更多的普通讀者愿意走進(jìn)并關(guān)注戲曲,為了讓枯燥乏味的學(xué)術(shù)書寫變得趣味盎然,作者做出了多種努力和嘗試。比如,在序言中,作者一開始就用飽含深情的筆墨追憶了自己的父親、兒時的生活、鄰里的鄉(xiāng)風(fēng)民俗、母校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從這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畫卷上,我們仿佛看到了一個鄉(xiāng)下的“無知頑童”一步步成長為聞名海內(nèi)外的“南戲?qū)<摇钡那逦壽E。這里,沒有端著架子的高臺說教,只有娓娓道來的親切敘談,卻把一位乍一聽也許會讓人敬而遠(yuǎn)之的學(xué)者一下就帶到了讀者身旁,也在無形中拉近了普通人和“南戲”的距離。
南戲是我國最早成熟、流傳最為悠久、影響最為深遠(yuǎn)的戲曲藝術(shù),從南、北宋之交最初形成,到明嘉靖末期由傳奇繼而代之,歷史跨度長達(dá)400余年,占去中國戲曲全部歷史的“半壁江山”。今天中華大地上流行的數(shù)百種地方戲曲,不少就是由南戲演變、繁衍而來的,與古南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因南戲最早起源于浙江溫州,故又叫“溫州雜劇”或“永嘉雜劇”(溫州古名“永嘉”);又因它主要用南曲演唱,故又稱“南曲戲文”“南戲文”“南曲”等。“南戲”,因言簡、意賅、稱便,遂廣為傳稱。南戲在整個中國戲曲發(fā)展過程中,有著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研究南戲不僅是總結(jié)戲曲歷史經(jīng)驗與充分利用戲曲寶貴遺產(chǎn)的需要,同時也是直接關(guān)系現(xiàn)今戲曲改革與今后戲曲發(fā)展命運(yùn)的重要課題,是中國戲曲史學(xué)中的“大軸”。但這方面的研究力量,卻比較薄弱。
有鑒于此,出生于南戲故鄉(xiāng)——溫州瑞安的作者,對較少有人問津的作為綜合、立體舞臺藝術(shù)的南戲藝術(shù)本體,一直保持著濃厚的興趣。從關(guān)于明成化本《白兔記》的系列論文、關(guān)于《南詞敘錄》《曲律》《梨園原》等的理論研究,到《風(fēng)月錦囊考釋》《風(fēng)月錦囊箋校》《金印記校勘》等,一直筆耕不輟。迄今為止,作者已出版專著十多種,發(fā)表各類文章 300 余萬字,曾獲中國出版政府提名獎、全國優(yōu)秀古籍圖書獎、王國維戲曲論文獎及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優(yōu)秀科研成果論文獎等獎項。這些學(xué)術(shù)成果都得到了海內(nèi)外同行的一致認(rèn)可,但作者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試圖打通行內(nèi)與行外的“鴻溝”,力圖讓更多圈外的人也了解南戲、了解戲曲,甚至喜歡上戲曲。所以,他的論述文字從不拿腔作勢、故作高深,而總是力求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比如《中國南戲研究再檢討》一文中對中外戲劇比較學(xué)的研究現(xiàn)狀的評述:
即以目前比較時興的中外戲劇比較學(xué)而言,綜觀有關(guān)研究成果,給人總的感覺是:言能中竅或有,無端類比則多。進(jìn)行中外戲劇比較,不是搞中西餐拼盤,也不是去追逐流行趨勢,主要是為了揭示中外戲劇文化發(fā)展的異同規(guī)律,使中國戲劇學(xué)能進(jìn)入世界學(xué)術(shù)對話的更高層次。不然的話,哪怕你耗盡心力,用丘比特的神箭猛射王十朋的戀妻情結(jié),憑伊甸園的快樂想象劉智遠(yuǎn)別妻的瓜園凄楚,叫月下顧影自憐的王瑞蘭去跟勇敢走出家門的娜拉互通心曲,讓蓬頭垢面的趙五娘穿上洋式時裝到各國瀟灑走一回……也終屬徒勞。(《增訂本》P49)
對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一旦理論儲蓄不足,往往會流于表面,帶有很大的貼標(biāo)簽式的隨意性。中外戲劇比較學(xué)方法的運(yùn)用,即是一例。戲劇比較學(xué)的理論和方法本非三言兩語就能講清楚的問題,但作者借由丘比特與王十朋、伊甸園與劉智遠(yuǎn)、王瑞蘭與娜拉、蓬頭垢面的趙五娘與身著洋裝的趙五娘的形象對比,仿佛談笑之間,就輕松地化解了這一難題。即便是行外人,對此亦不難理解。
又如,關(guān)于“南戲”與“傳奇”這對概念范疇的厘定和名稱使用的規(guī)范問題,學(xué)界向來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如果把“南戲”的范圍拉得過長、過寬,就與明清傳奇、近代地方戲以至當(dāng)代地方戲曲“難分難舍”了。對此,作者在《關(guān)于“南戲”與“傳奇”的界說》一文中,用形象的比喻做了明確的闡述:
我以為“南戲”與“傳奇”的不同,就好似一個人的青年與壯年的區(qū)別,而非如一個先死、一個后生的兩個人。(《增訂本》P96)
兩個聯(lián)系緊密、有時甚至難辨雌雄的專業(yè)術(shù)語,通過這樣明白如話的解釋,立刻就給人一種清晰直觀的印象。這正如作者所一貫堅持的:
學(xué)術(shù)表達(dá)者的本事,我認(rèn)為是把作者經(jīng)過研究而明白的原本復(fù)雜、深奧的道理,盡可能地簡單化、淺顯化,使更多不明白的他人也同樣明白;而不是相反,把原本簡單、淺顯的道理,有意變得玄虛和深奧,去嚇跑別人。(《我與南戲研究(代序)》,《增訂本》P12)
作者是這樣呼吁,也是這樣身體力行的,收錄在《增訂本》中的每篇文章都是本著盡可能讓行內(nèi)、行外人皆能看懂而且愿意看、喜歡看的寫作初衷而結(jié)撰的。是為“好看”之本義:通俗易懂、深入淺出。
靈動多樣、不拘一格的寫作模式
近現(xiàn)代以來,西式論文的寫作模式逐漸占據(jù)了天下“霸主”的地位。雖也曾有學(xué)者質(zhì)疑過西式論文的“負(fù)面影響”(謝泳《西式論文格式流行的負(fù)面影響》,《北京日報》2014年11月3日),但學(xué)界之一大“怪現(xiàn)狀”仍是:“寫的人和讀的人全是同樣的那幾個人;甚至讀的人還不如寫的人多。”(孫崇濤《戲緣·題記》,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P2)何以如此?西式論文單一、刻板的表達(dá)方式恐難辭其咎。我國古人歷來倡導(dǎo)考證、義理、辭章三者統(tǒng)一的好文章,而中國歷代的文史、學(xué)術(shù),也向來具有多樣化、散文化、形象化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如何把這一優(yōu)良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研究結(jié)合起來,《增訂本》做了一個很好的表率。
作者長期以來一直致力于讓學(xué)術(shù)文風(fēng)文體回歸傳統(tǒng)的實踐,尋求多樣性,增強(qiáng)可讀性,嘗試采用多種文體,盡力把理論文章寫得生動、形象,接“地氣兒”。如該書所收《關(guān)于“南戲”與“傳奇”的界說——致徐扶明先生》《關(guān)于奎章閣藏本〈五倫全備記〉——致吳秀卿女士》《關(guān)于蔡伯喈疑案——復(fù)孫玫先生》《寒山譜·錦本與戲文輯佚——致黃仕忠博士》等多篇文章,就是采用與學(xué)術(shù)同人對話的通信方式來寫的,諸如“三月十六日大札誦悉”“四月二十二日惠函拜讀”“五月二十九日大函已收悉多日”“盼待您的糾謬駁正”“以上看法及各例對否,請您匡正”等的書信文體,不僅讓人耳目一新,而且這些信件本身,也化作了歷史的一瞬,給人以身歷其境的代入感。于是,本來莊嚴(yán)凝重的專業(yè)話題,就這樣悄無聲息地融化在了和風(fēng)細(xì)雨般的輕松表述中。
《世紀(jì)回眸:中國戲曲史學(xué)斷想》一文則嘗試吸收了古代辭賦的表達(dá)方式。如在論述中國近代戲曲史學(xué)的紛繁局面時,作者借鑒了賦體文學(xué)的駢偶、排比手法:
此外,還有從語匯訓(xùn)詁入手,研治歷史脈絡(luò)者;有據(jù)輯佚文獻(xiàn),升級到史論層次者;有從劇本校勘起步,漸入史學(xué)堂奧者;有憑借別種藝術(shù)或問題,追溯源流發(fā)展者;有依據(jù)實地調(diào)查,創(chuàng)為一己之說者;有立足音樂聲腔,探求歷史流變者;有鼓搗戲曲文物,追蹤歷史脈絡(luò)者;有考察宗教、民俗,破譯古代戲曲密碼者……(《增訂本》P400)
用這種精煉工整的語句總結(jié)近代戲曲史學(xué)五花八門的研究套路,既切中肯綮,簡潔明了;又不乏氣韻生動、氣勢強(qiáng)烈的文學(xué)之美。
在論文分論點的設(shè)置上,亦能看出作者繼承中國文史優(yōu)良傳統(tǒng)、追求多樣化表述方式的良苦用心。比如《中國南戲研究之再檢討》的三個小標(biāo)題:
一、一支新軍,兩次盛會,三種專著;
二、重心漸移,材料益富,交叉日多;
三、幾多迷離,幾多缺憾,幾多期望。(《增訂本》P27、34、43)
作者把對數(shù)字的精心設(shè)計,對學(xué)術(shù)熱點的提煉,對研究得失的梳理,巧妙地融匯在這三句排列整齊的文字組合中,既給人重點突出、條理清晰的理性之美,又不乏類似文學(xué)讀物的清新、優(yōu)美之感。
以上種種突破西式論文格范、“敢為天下先”的嘗試,貌似削弱了學(xué)術(shù)專著的學(xué)術(shù)性,實則卻把原本束之高閣的深奧理論,用大眾更易接受且樂于接受的方式,“潤物細(xì)無聲”地播撒在了讀者的心田。因其寫作筆法之靈活多樣,變動不居,故曰“好看”。
平易近人、生動凝練的語言風(fēng)格
該書“好看”的原因之三,是其語言平易近人、生動凝練。這樣的例子在書中比比皆是,試擷取一二觀之:
中國古代戲劇藝人叫“弟子”,編劇者叫“書會才人”,他們靠演戲、編劇謀生。高則誠參與戲劇創(chuàng)作不是為了謀生,而是為了寄托個人的思想精神。《琵琶記》處處打上了高則誠本人的人生體驗與思想烙印,表達(dá)了他對社會現(xiàn)實的深刻理解。劇中描寫的男主人公蔡伯喈的矛盾和彷徨,體現(xiàn)了功名利祿和家庭幸福的沖突和對立;他的苦悶和窘境,是元朝知識分子進(jìn)退維谷的命運(yùn)寫照;他的懦弱和屈從,是封建正統(tǒng)教化和嚴(yán)酷現(xiàn)實威逼的投影。因此蔡伯喈的形象,客觀上起著揭露封建社會現(xiàn)實黑暗、封建教化桎梏人心和封建科舉制度制造人生悲劇的意義。于是,戲劇創(chuàng)作不僅是梨園勾當(dāng),同時還是作者抒情、言志、評騭的工具,使它與詩詞、散文、小說并列,躋身于中國文學(xué)創(chuàng)作四大板塊行列。明代中葉以來出現(xiàn)大批有地位、有文化的文人投身戲劇創(chuàng)作,他們都把戲劇作品當(dāng)作嘔心瀝血的“千古文章”來做,這種局面的開創(chuàng)者就是高則誠。(《中國戲劇文化史上的豐碑》,《增訂本》P264)
這里,對中國古代戲劇演員和戲劇編劇活動的介紹,對中國古代戲劇創(chuàng)作功能的揭示,沒有華麗堆砌的辭藻,沒有高深莫測的專業(yè)語匯,只有明白曉暢、如話家常的平實講述,卻把一代戲劇大家高則誠的崇高歷史地位,清晰、有力地刻在了讀者的腦海里。
又如對中國戲曲史學(xué)研究之繁雜的體認(rèn):
做一名稱職的戲曲史學(xué)家確實不易,史學(xué)家的眼睛、理論家的神經(jīng)、雜學(xué)家的胸藏、樸學(xué)家的腦袋和藝術(shù)家的細(xì)胞,缺一不可,現(xiàn)代科學(xué)的發(fā)展,還需添生操作智能工具的科技家式的雙手。(《中國南戲研究之再檢討》,《增訂本》P49)
戲曲史學(xué)內(nèi)容龐雜,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戲曲加上歷史。作者以自己切身的體會,把它所涵蓋的目錄、版本、音韻、文字、訓(xùn)詁、考據(jù)、名物、典章、制度、宗教、民俗、詩詞、文賦、經(jīng)史、方志、稗乘、水文、地理、方言、俗語、碑銘、譜牒、考古、文物、音樂、表演、美術(shù)、雜技等林林總總的知識和技能,僅用幾個形象貼切的短語,就概括得淋漓盡致。
再如對中國戲曲史的學(xué)科定位:
以梳理文獻(xiàn)、闡釋史實為使命,它是歷史學(xué)的分支;以研究文體為宗旨,它是中國古代文學(xué)研究的重要構(gòu)成——若與雅文學(xué)對應(yīng),是“俗文學(xué)”研究的主要對象;若與舊詩學(xué)、舊詞學(xué)比肩,是韻文學(xué)的延伸;若以文體分類,是中國文學(xué)樣式研究的主要部類——以藝術(shù)性質(zhì)審視,它是中國民族戲劇學(xué)研究對象的代表……此外,還可從音樂學(xué)、表演學(xué)、劇場學(xué)、觀眾學(xué)、民俗學(xué)、人類學(xué)、宗教學(xué)、文獻(xiàn)學(xué)、文物學(xué)、美學(xué)等入手,分別構(gòu)成各學(xué)科研究范疇的部件。(《世紀(jì)回眸:中國戲曲史學(xué)斷想》,《增訂本》P400-401)
鑒于中國戲曲史學(xué)性質(zhì)的多重性和復(fù)雜性,很難用一句話對其蓋棺定論。這里,從不同角度分別予以簡明扼要的判斷,三言兩語就廓清了我們思想上關(guān)于這門繁雜學(xué)科認(rèn)知上的迷霧。
因為一向秉承著通俗易懂、深入淺出的寫作觀念,始終堅守著靈動多樣、不拘一格的寫作模式,所以在寫作時,孫先生從不故弄玄虛、故作“高深”,從不做拿腔作勢的高頭講章,而是總想著如何讓更多的人來關(guān)注戲曲、讀懂戲曲,甚至喜歡戲曲,故而形成了這種平易近人、生動凝練的文風(fēng),是為該書“好看”之又一深意。
堅守真理、獨辟蹊徑的學(xué)術(shù)見解
該書之所以“好看”,并非僅限于上述咬文嚼字的“外表之美”。內(nèi)核的“好看”,才是一部學(xué)術(shù)著作的真正生命力之所在。作者素來不喜重復(fù)前人,他的學(xué)術(shù)研究都是建立在對戲曲現(xiàn)象的深入考察和對戲曲本質(zhì)的深刻體認(rèn)基礎(chǔ)上的,因而往往能思人之所未思,言人之所未言。《增訂本》中的許多篇章都閃爍著這樣新人耳目的真理之光,絲毫沒有拾人牙慧的學(xué)舌之感。
比如,根據(jù)自己對一手文獻(xiàn)的審慎分析,孫先生否認(rèn)了蘇復(fù)之作《金印記》(見《〈金印記〉的演化》)、丘濬作《五倫全備記》(見《關(guān)于奎章閣藏本〈五倫全備記〉——致吳秀卿女士》)、李日華作《南西廂》(見《南戲〈西廂記〉考》)等陳陳因襲的記載,而是把這些作品放在戲曲不斷流變的動態(tài)中,窮本溯源,全面考察,從而對其作者問題做出符合實際的定位。
又如,學(xué)界對中國戲曲歷史發(fā)展段落的劃分,長期以來沿襲著“宋元南戲—元明雜劇—明清傳奇—近現(xiàn)代地方戲”的結(jié)構(gòu)模式,中間遺漏了從宋元南戲終結(jié)到嘉靖末期真實、嚴(yán)格意義的明傳奇形成之前兩百多年的一大段明代戲曲歷史。作者經(jīng)過長年研究認(rèn)為,“宋元南戲”基本是個“空殼”概念,現(xiàn)存的所有南戲文獻(xiàn),全部來自明清兩代;真實的南戲史況,大部分見于明初迄嘉靖兩百余年間,即作者提出的“明人改本戲文”階段(見《明人改本戲文通論》,《增訂本》P73-75)。因此孫先生的南戲研究重點,不放在人云亦云的“宋元南戲”方面,而是側(cè)重對“明人改本戲文”歷史狀態(tài)與作家作品樣貌的考察和研究,這與傳統(tǒng)的南戲研究大相徑庭。
再如,針對各地方往往被鄉(xiāng)土觀念綁架,偏好將當(dāng)代地方戲都?xì)w入“南戲遺響”的崇古傾向,孫先生進(jìn)行了認(rèn)真辨析,得出了實事求是的結(jié)論。他通過深入調(diào)查研究,不贊同溫州地方戲仍舊保留“南戲遺響”的見解,而認(rèn)為“想從溫州近現(xiàn)代戲曲中,去搜尋‘南戲遺響,看來只能是一種良好愿望”。主張“溫州南戲研究,自有途徑,不宜采取所謂根據(jù)‘遺響進(jìn)行‘新證的辦法”(見《溫州地方戲概觀》,《增訂本》P396-397)。這對于出身溫州籍的作者來說,是難能可貴的。這類例子,書中遍見,不勝枚舉。
因了思想之獨立,思考之深入,故而能堅守真理,揚(yáng)棄逐流——這種與眾不同的獨創(chuàng)精神,可謂該書“好看”的根源之所在。
綜上所述,由于作者始終秉持學(xué)術(shù)著作應(yīng)該通俗曉暢、面向大多數(shù)讀者的創(chuàng)作理念,堅持回歸中國文史傳統(tǒng)的多樣表達(dá)方式,再加上語言的平易近人、生動凝練和觀點的打破傳統(tǒng)、獨辟蹊徑,使得《增訂本》這本南戲史論著作,既有著讓人賞心悅目的外在美,又有令人回味無窮的內(nèi)在魔力,堪稱一部真正“好看”的戲曲史論力作。
(作者系中國戲曲學(xué)院戲文系副教授,戲文系戲曲史論教研室主任,碩士生導(dǎo)師,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戲劇戲曲學(xué)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