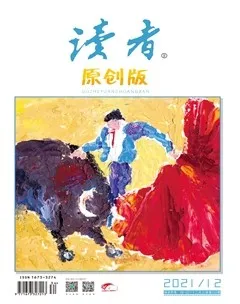看電影
柴嵐綺
在儲物柜里翻到20多年前和丈夫去看電影的票根—光明影都,70毫米電影廳,12排17號,12排19號。
那時常常經(jīng)過電影院門口,看到海報,一拍腦袋:“哦,今天上映這個!”也沒得到過什么劇透,恰好有時間,就彎腰在那頂部半圓的小小窗口買了最近場次的票,心中滿是即將走進一個陌生故事的期待。
現(xiàn)在看電影,比過去方便多了,手機下單電影票,趕去電影院的路上還不時收到距離電影開場還有多少分鐘的提醒。電影院也不是過去那樣的一幢單獨的建筑了,而是位于城市里某座大型商場的樓上,坐電梯要上好幾層,再經(jīng)過健身房、溜冰場、美食區(qū)。在自助取票機上輸入取票號,電影票就由旁邊那扁扁的洞口整齊地吐出來。
電影票是熱敏紙打印的,所以過一段時間,上面的字就會模糊;再過一段時間,就成了空白。拿著空白的電影票,家人共同啟動大腦里的搜索程序—我們當時到底看了什么電影?
當那部電影的名字完全從票根上消失時,我們會就此遺忘那些看電影的時光嗎?不,怎么會?
記得表姐和表姐夫第一次見面就在電影院。那是20世紀80年代,相親的方式之一就是男女雙方一起去看場電影。
一共4張電影票,座位分別在前后兩排。表姐和當時初次見面的表姐夫坐在前面,我和我哥被派去坐在他們后面。
不知是不是因為當時年紀尚小,身材也矮小,總覺得電影院里每一排座位都漫長而壯觀,如果有人抖腿,整排椅子都會跟著搖晃。中途上洗手間的人,也必須在黑暗中一路低頭、彎腰,摸索著擠出去,走到出口處撩起厚重的門簾,觀眾的眼角會掠過一道刺眼的白光。
上班以后,特別喜歡看電影。那時正置身于無知無畏的青春之中,父母也正爬至人生的頂峰,撐起庇護我們的濃蔭。
每個周末,我都和好友相約逛街、看電影,從本市的三孝口一路逛到四牌樓,然后在解放電影院坐下來。記得有一回,電影看到一半,好友忽然小聲地說:“外面下雨了。”我低頭,在銀幕忽明忽暗的光影中,用力感受—那是四月,春天的下午,外面的雨水落在泥土上,土地與青草混合的氣息被風裹挾著,自門縫緩緩鉆進場內(nèi)。那天看的是什么電影呢?不記得了。但只要想起那天,就好像又坐進黑暗的電影院里,在光影里聞到那股屬于春天的清新濕潤的泥土味。
成家,結(jié)婚,有了孩子,生活帶我們駛?cè)牒恿魍募钡乃颉儆谧约旱臅r間就是孩子晚上睡著以后,趁洗衣機洗著衣物,在燈下翻幾頁書。假如深夜去樓下24小時便利店買東西,遇到帶一身涼氣匆匆晚歸的人,我就猜想,他是剛看完電影回來嗎?
那時和媽媽住得近,她白天幫我照顧孩子,有時孩子晚上就住在她家。有一次正上映一部大片,看到離家最近的電影院晚上10點還有一場,于是我下了決心去看。等孩子上床睡覺以后,囑咐好媽媽,和丈夫溜出來,一路夜奔,帶著做學生時翹課去玩的忐忑又雀躍的心情。
那家電影院是新開張的,在一個還未完全結(jié)束施工的商場里。我們從一堆建筑材料間小心地繞過去,終于找到隱蔽的、還沒有醒目標識的電梯。有幾個年輕人也是這樣一路尋過來,電梯里我們相視一笑,都為觀影而來。久違的光影里,我的心跟著故事情節(jié)一起起伏跌宕。等放映結(jié)束,已是深夜。然而,我和丈夫在路上討論的不是劇情,而是孩子今晚睡得好不好,擔心她醒來問我們?nèi)ツ睦锪恕槿烁改福磮鲭娪耙矡o法完全沉浸。
孩子長大了,我們一起結(jié)伴去看電影。正片前的廣告結(jié)束了,頂燈熄滅了,前奏的音樂響起了,我們在黑暗中目光炯炯。每當想和孩子討論一下劇情時,頭剛側(cè)過去,孩子就已嚴肅地把手指豎在嘴唇中間,示意看電影的時候絕對不要說話。
看電影,也是孩子讀書時期的調(diào)劑和放松時刻。每次孩子大考結(jié)束,我都是以“我們?nèi)タ磮鲭娪鞍伞弊鳛楠勝p,就如同跑馬拉松時,途中的一個個補給小站。
直到她高三畢業(yè)的夏天,那天她說:“媽媽,我想去看電影,但這次我想一個人看。”
那天她選擇一個人看電影,是她的獨立儀式吧?電影散場遲,說好了差不多看完的時候,我們在商場外面的馬路邊等著,接她回家。那個商場人氣很旺,但那會兒早已打烊,店鋪都黑下來,只剩各種綠植披掛著暖色調(diào)的燈串,晶瑩地閃爍著。我想,這個還從未離開過父母的孩子,她今天獨自去看了場電影,而8月,就要背起包離家去1000多公里以外的城市讀書了。
散場的人們陸續(xù)走了出來,我和丈夫看到孩子也走了出來,斜背著白色的小包,在遠處向我們大力搖擺著手臂—那是我不曾參與觀看的一場電影,卻比任何劇情都讓我眼眶濕潤。
孩子去外地上大學以后,我以為閑暇時間自此會有很多,然而似乎不是這樣。當把孩子送去大學之后,我們不僅要更努力工作,還要更多地陪伴開始年邁的父母,以及花更多精力應付逃不掉的瑣碎雜事。有一天和丈夫終于決定去看場電影,把各種事情排除之后,選定了周五晚上9點的場次,那是一部3個小時長度的電影,看完已是深夜。
也在家里看過VCD、網(wǎng)絡(luò)電影,但終究還是喜歡坐進電影院里,因為我真正喜歡的是“看電影”這件事的過程。比如,坐在座位上,看到進來七八個年輕人,領(lǐng)頭的那個看看手里的票,豪氣一指—“從那里到這里,都是我們的座位,隨便坐吧”;又或者影片結(jié)束后,頂燈亮起,從造夢空間里不舍地回過神,旁邊站起來的竟是腳上打著石膏、拄著單拐的人—這樣也要來看電影啊,心里既驚訝又驚喜。
而那天,看完那部3個小時的電影,走出來時已是深夜12點—布置第二天露天車展的人在叮叮當當?shù)匕惭b,穿著制服的搬運師傅在馬路邊卸貨,出租車亮著“空車”的綠燈,清潔車清洗著路面上的污痕,路上還有三兩行人,甚至有一家理發(fā)店還燈火輝煌……那些人們努力工作的場景,令我印象深刻。
看過的電影,或許就像那褪色的熱敏紙,被我們漸漸忘掉了名字。但當時和電影有關(guān)的時光,都成為一幀幀畫面,疊加在一起,成為屬于我們自己的有溫度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