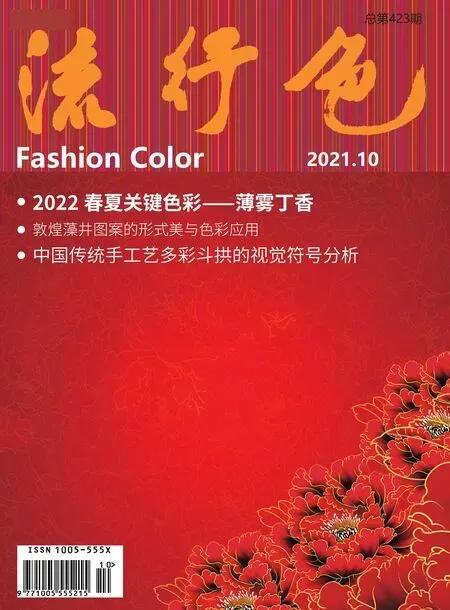宋代瓷器美學風格探析——以青瓷與白瓷為中心
趙爭強
Zhao Zhengqiang
淮陰工學院 設計藝術學院,江蘇 淮安 223000
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Design and Art,Huai'an Jiangsu 223000
中國瓷器自宋代而始經元代、明代而到清代,取得了極其顯著的設計與制作成就,在藝術與技術方面發展巨大,對后世陶瓷燒制有著深遠的影響。縱觀幾個歷史時期的發展,宋代瓷器與宋代繪畫一樣進入中國藝術史上的鼎盛階段。除技術上的成就外,宋代瓷器以它獨特的造型與審美風格成為中國瓷器發展史的巔峰。宋代瓷器分為官窯與民窯兩個系統,而無論是官窯還是民窯,雖因為性質與地域不同而有相應的各自特點,不過綜合而言,整個宋代的瓷器展現出了高度的素潔與簡約風格,從而構成了宋代瓷器美學的典型特點。而其風格的形成,與宋代政治、文化、美學與思想等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系。
一、宋代政治與宋代藝術發展
960年,后周趙匡胤在陳橋發動兵變,建立宋朝。因趙匡胤是以禁軍大將的身份而采取武力奪得政權,所以為了防范武將,宋朝建立之初就制定了“崇文抑武”的治國方針。這一國策經北宋初期至宋仁宗時期極大促進了宋代文人地位的提升。宰相文彥博對神宗說:“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以此中大臣所道君主應當與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之論,這是宋朝之前與之后的歷代臣子所不可能也不敢言明。由此可見,宋代士人群體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已經占據了重要的位置。余英時就此論為宋王朝為了重建文治秩序而要依賴于士人階層,而士人階層又對政治表現認同的互動成為君臣“同治天下”局面的制度性基礎。[1]而這番言論不僅體現出宋代士大夫重要的政治地位,同時也展示了他們的高度自信。
宋代文人政治地位的提升又促使其主體意識隨之提升,體現在藝術上的表現即是創作者主體精神與意旨的高揚。宋代“崇士”國策與社會環境不僅在根本上促進了宋代文人藝術的發展,也反之深刻影響了君主的文藝趣好。北宋在開國不久,宋太宗趙光義即設立畫院,由此開創了中國古代歷史上運作最為專業性的皇家畫院。《宋會要》對此記載:“翰林圖畫院,雍熙元年置在內中苑東門里,咸平元年移在右掖門外,以內侍二人勾當。待詔等舊無定員,今待詔三人,藝學六人,祗候四人,學生四十人為額。舊工匠十四人,今六人。”[2]宋代畫院的建立在完成帝王與宮廷的繪畫需求同時,也對帝王與宮廷產生了重要影響。宋徽宗作為一代書畫皇帝,其藝術喜好與風格一直波及南宋諸位皇帝而尤其是宋高宗。宋末元初鑒藏家周密曾道:“思陵(宋高宗廟號)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余力。清閑之燕,展玩摹拓不少怠。”[3]

圖1 《龍泉窯青釉鳳耳瓶》,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除書畫藝術的發展,宋代商業與城市的繁盛以及市民階層的崛起促成了工藝美術的極大發展,而宋瓷無疑是其中成就最高的品類。宋代瓷器突破了唐代“南青北白”相對單一的燒制情況,在其時全國眾多地區窯場林立而局面龐大。這一時期的宋代瓷器以北方定窯、磁窯、耀窯、鈞窯與南方龍泉窯、景德鎮等為代表窯系,其產品種類繁多而各領風騷。定窯、磁窯與耀窯等以白瓷為勝,而除以越窯與龍泉窯以青瓷著名外,地處福建沿海的建窯黑瓷以其獨特的色釉與工藝而在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代全國窯場眾多,概括而言以其中的汝窯、官窯、哥窯、定窯與鈞窯五大名窯最為著名。五大名窯一說最早見于明代《宣德鼎彝譜》:“內庫所藏柴、汝、官、哥、鈞、定各窯器皿,款式典雅者,寫圖進呈。”[4]《宣德鼎彝譜》為明宣德中禮部尚書呂震等奉敕編撰,進呈皇帝以供宮廷之用。此中所謂的宋代名窯流傳頗廣,清末民初許之衡在《飲流齋說瓷》中也道:“吾華制瓷可分三大時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有五,所謂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鈞窯,亦甚可貴。”[5]《宣德鼎彝譜》與《飲流齋說瓷》作為具有影響力的兩部陶瓷論著都提到宋代柴窯、汝窯、官窯、哥窯、鈞窯與定窯,于是成為迄今而來宋代諸多窯場的代表。而因為在陶瓷史上知名度極高的柴窯在今天并未有實物可見且未發現到窯址,因此通行說法則將柴窯去除不計而將汝窯、官窯、哥窯、定窯與鈞窯稱為宋代五大名窯。
二、宋代青瓷美學風格
宋代瓷器的素潔美學在色彩方面體現為單色釉的用色上,因此無論在北方窯還是南方窯皆呈現出頗為統一的風格傾向。宋代的汝窯、官窯、哥窯、定窯與鈞窯均以單色釉為主,其中代表性瓷器為白瓷與青瓷。通常而言,裝飾色彩中除黑色與白色并無色彩傾向外,其他或為冷色或為暖色而皆為彩色。然而,以青瓷為例,在宋代素潔為美的審美觀念影響下,其所謂彩色的色彩卻并非光彩照人之類,而是呈現出高貴的單純這一獨特的宋代審美文化特質。宋代青瓷在唐代青瓷的燒制成就基礎上更有著技術與審美上的突破發展,宋代“汝官哥鈞定”五大瓷窯中除定窯以白瓷為主外,其他四窯皆出品青瓷。而宋代人士對青瓷也是情有獨鐘,如楊萬里《道旁店》詩:“路旁野店兩三家,清曉無湯況有茶。道是渠儂不好事,青瓷瓶插紫薇花。”詩人在詩中寫道路旁的小店雖是鄉野人家而在他人看來或許并無多少雅致,不過店家卻是極富審美地在青瓷花瓶中插入紫薇花點綴房間。由此詩可見,不僅宋代文人對于青瓷喜愛有加,而普通的民眾也是如此。
宋人以素潔為美的青瓷喜好與宋代文人在審美方面的強大影響力有著密切關系。當文人成為主流政治階層后,其精神、思想與文化品味等便會在一個朝代與時代的文化性格上深層地折射出來。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這是對宋代與宋代文化極高的評價。相比于唐代文化,宋代文化表現出截然不同的風格特征。唐代文化如盛唐書法體現為規則,宋代文化無論是繪畫、書法還是瓷器則更體現為對意趣的關注,所謂“唐尚法,宋尚意”。[6]而宋代文人關于意趣的論述幾比比皆是,如蘇軾稱:“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撻、皮裘、槽栃、芻秼,無一俊發,看數尺便倦。”[7]蘇軾在此處說道欣賞文人畫如同觀看馬匹一樣,應該更關注其意氣風發的,而畫匠則往往是將馬鞭與馬槽等一一畫出,從而全然失去了其本應重點表現的神態。這是宋代文人對于強調形式與強調意趣的藝術觀念與審美觀念極有代表性的例子。
宋代是極其重視藝術鑒賞與文化趣味的朝代,其詩詞、書畫與器物的創作與制作無不深深體現著這一特點,而士大夫階層的精神內涵與文化趣味深層影響著有宋一代的風氣。在宋代士大夫文化的影響下,審美情趣由文人階層而做兩個方向的影響延伸,一是向上影響宮廷,一是向下影響民間。因此,南宋楊萬里得以寫出“青瓷瓶插紫薇花”這樣反映宋代市民階層喜好素潔青瓷的趣味。而相比于明清宮廷奢華艷麗風格瓷器的盛行,宋代瓷器的宮廷品味則與其市民格調一樣而同樣極為難得。作為宋代宮廷瓷器以至整個宋代青瓷的重要代表,《天青無紋水仙盆》(圖2)可謂極其體現了宋代瓷器雅致素潔的美學風格。《天青無紋水仙盆》高6.7厘米,深3.5厘米,長23厘米,寬16.4厘米,為宋徽宗時期官窯汝窯燒制。天青瓷是青瓷中以幽淡色調著稱的一個種類,尤為宋代文人所喜好。

圖2 《天青無紋水仙盆》,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2中天青瓷為橢圓形,侈口、深壁,整件瓷器釉面光潔無開片而極其難得。其溫潤素潔的均勻色調正是宋代清淡明凈的美學風格體現。據傳天青瓷得名于五代后周世宗柴榮,《五雜俎》記載:“世傳柴世宗時燒造,所司請其色,御批云:雨過青天云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8]柴榮為后周第二位皇帝,歐陽修在《新五代史?周本紀》中寫道:
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為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其英武之材可謂雄杰,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9]
此中,歐陽修盛贊柴榮為一代賢達英武之君,而從“延儒學文章之士”一句可看出其對于文化與文人的推崇。而其以“雨過青天云破處”此詩意化的比喻而命名為天青瓷,亦顯示出對于雅致與素潔的瓷器美學理解。而北宋汝窯此件宮廷水仙盆瓷器,則更為典型地代表了宋代瓷器尤其是天青瓷的最高燒制成就與美學高度。從另一方面而言,這也是宋代帝王藝術格調與宮廷趣味的體現。
而頗可作為比對的是,此水仙盆瓷器在清代內府則曾一度被當作貓狗食盆。清代宮廷本即有參照宋代瓷器的形制與顏色而進行仿制的傳統,而在所仿制的瓷器中除了日常陳設器外,還有日用器等,在乾隆朝近二十年間掌管瓷窯事務的官員唐英在《陶成紀事碑記》中就記載到“仿宋器貓食盆”。[10]然而,在宋代宮廷的用瓷中,并沒有貓食盆一類瓷器,把宋代宮廷某一瓷器當作貓食盆完全是對其最初作用的錯誤認知。而唐英所記載的“仿宋器貓食盆”所仿造的宋瓷原型就是這件“天青無紋水仙盆”。除了宮廷仿制外,乾隆還為這件《天青無紋水仙盆》作詩一首:
官窯莫辨宋還唐,火氣都無有葆光。便是訛傳猧食器,蹴秤卻識豢恩償。龍腦香薰蜀錦裾,華清無事飼康居。亂碁解釋三郎急,誰識黃虬正不如。[11]
乾隆在此詩中寫道“官窯莫辨宋還唐”,官窯與汝窯、哥窯、定窯以及鈞窯并稱為宋代五大名窯,然而這件“天青無紋水仙盆”本為宋代汝窯燒制而非官窯,因此乾隆所謂“官窯莫辨宋還唐”實際是將汝窯產品與官窯產品混為一談。乾隆以詩評論宋代瓷窯燒制的瓷器與唐代瓷窯燒制的瓷器不易辨別,而其在此之外對于宋代汝窯與官窯亦不甚明晰。再有,其“便是訛傳猧食器”雖糾正了這件“天青無紋水仙盆”并非用來喂養犬狗,然而其“蹴秤卻識豢恩償”一句卻仍是將其說成是寵物食器,而唐英《陶成紀事碑記》所記“仿宋器貓食盆”則明確了當時清宮普遍將這件宋代汝窯“天青無紋水仙盆”當作貓的飯盆。在清代皇帝主導下的這一認知與宋代皇帝的藝術趣味相比,實在是差距極大。
三、宋代白瓷美學風格
除青瓷外,宋代素雅簡約的瓷器美學風格同樣體現在白瓷的成就上。在中國陶瓷史上,向來便有“南青北白”一說,這是指在瓷窯的分布與瓷器的制作上,南方以青色瓷為代表而北方以白色瓷為代表。陶瓷燒制由唐到北宋發展蓬勃,宋代北方瓷窯以邢窯與定窯為代表的白瓷取得了極高的工藝成就。邢窯白瓷胎質厚實而定窯胎質則相對較薄,其釉色素潔晶瑩,與青瓷同為單色瓷而又呈現出有所不同的視覺美感。

圖4 《定窯瓜式提梁壺》,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在中國古代史上,對于白色的推崇在南北朝時的南朝便很是盛行,《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傳》記載:
宋元嘉世,諸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上與嶷同生,相友睦,官內曲宴,許依元嘉,嶷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待宴焉。[12]
由此可見,白色是南朝齊上層階層尤其喜歡的顏色而成為社會時尚。南宋程大昌在《演繁露》中引《隋志》記載:“宋齊之間,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太子在永福省則白紗帽。”[13]中國古代喜好白色的風氣頗有歷史,而到宋代則因文人不好奢華并且占據文化的主流地位,所以同樣影響到陶瓷的制作與欣賞方面。
唐人李肇在《唐國史補》中道:“內丘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14]內丘也就是今天唐代與宋代的邢窯所在地,甌本義為盆盂類瓦器,后代指瓷器。李肇在其書中稱,邢窯生產的白瓷器皿在當時無論貴族還是百姓階層都普遍使用,由此可見邢窯白瓷在當時的影響力。邢窯白瓷在其后的宋代又逐漸為定窯白瓷所取代,而其廣泛的實用性與審美性可謂是一脈相承。今天留存的邢窯與定窯白瓷多為日常生活品,如碗、盤、壺、杯、盒、甌、盞等。此類器皿的實用性功能與整個宋代社會審美決定了邢窯與定窯白瓷更具有樸素無華的風格特點。比較而言,這兩座瓷窯的白瓷風格又稍有區別,邢窯白瓷在整體上以沒有紋樣裝飾為主,而定窯則在保持基本的質樸風格上采用紋飾。
以故宮博物院所藏宋代定窯燒制的刻花折腰碗(圖3)白瓷為例,其為典型的生活日用器,敞口造型使其能夠有更大的使用空間,淺式構造在敞口造型而能確保功能的基礎上又利于日常使用方便。除了簡潔實用的形式外,這件白瓷碗在碗內壁與外壁都裝飾以蓮花與蓮葉紋。因為高潔清純的人格象征精神,因此宋人對于蓮花與荷花頗為喜愛,此從北宋周敦頤《愛蓮說》中最能感受到:

圖3 《定窯白釉刻花折腰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以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15]
宋代文人對于蓮花與荷花的喜愛,在日用器物制作上的影響就是大量的蓮紋裝飾的應用。而北宋定窯白瓷則突出呈現出這一特點,定窯白瓷的裝飾紋樣多是用刀劃刻出,如這件白釉刻花折腰碗。匠工在碗的內壁與外壁都刻劃出蓮花與蓮葉的圖案,線條精致而造型圓轉,這種在內壁與外壁都刻劃以裝飾紋樣的白瓷在宋代很是少見,從另一方面也可想見制作者的匠心。北宋白瓷這種以刀刻出圖案裝飾的風格,而非如同明清景泰藍、粉彩、五彩等這類使用多種工藝與繁復的技術手段的器皿制作,在工藝層面體現了宋代瓷器與眾不同的特有品質。而在美學風格上,宋代白瓷又以刀刻劃而不施顏色的裝飾方式呈現了與白瓷單一釉色珠聯璧合的一致性。
結語
宋代建國后結束了唐末以來長期的分裂局面,經濟、商業與城市迅速發展,制瓷業也進而成為中國陶瓷史上的高峰。宋太祖所確定的以文治國的方針使得宋代士大夫階層成為政治生活的主要力量。文人的藝術趣味隨著其政治地位的提高而因此向上影響宮廷與向下影響民間,對宋代瓷器的制作與欣賞而言則形成了不同于唐代與明清的獨特審美精神。而宋代青瓷與白瓷以其素雅同時兼有質樸的造型與色彩特性,尤其成為宋代瓷器美學素潔、清雅與簡致風格的代表。這種代表性地位的確立一方面體現在匠人所受到的文人趣味影響,從而在青瓷與白瓷的形制制作與釉色運用上追求風格的傾向;另一方面體現在廣泛的社會層面的審美風尚上。而除了士大夫階層與宮廷素雅崇尚的風格,普通市民因宋代文化在相當層面上的普及亦是有同樣的審美標準。總之可見,以青瓷與白瓷所最為代表的宋代瓷器美學風格的形成是在宋代士大夫、帝王與庶眾的共同參與下而被塑造出來,由此深刻拓展了中國宋代以后的美學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