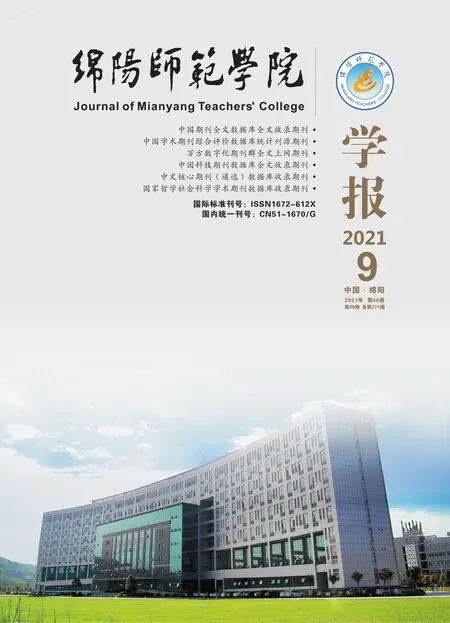巴蜀文化與美學精神研究的新成果
——評譚玉龍《巴蜀美學史稿》
郭碧琪
(重慶郵電大學傳媒藝術學院,重慶 400065)
在自然地理上,巴、蜀兩地毗鄰,地處盆地,四面環山;在歷史上,兩地一直以來在經濟、技術、文化等方面交流密切,自戰國起逐漸形成“巴蜀文化”。美學作為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會受到不同時代、空間的影響而呈現出不同的地域特點和傾向。譚玉龍的新著《巴蜀美學史稿》(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21年版),作為中華地域審美研究的最新成果,從歷史自然地理、歷史人文地理與巴蜀文化的密切聯系出發,對兩漢三國時期、隋唐五代時期、宋元明清時期巴蜀中人的美學思想進行了探究與闡釋。該著作者自小生活于巴蜀之地,對巴蜀文化有著較為深刻的領悟和體會,近年來,他又對中西方美學有所鉆研。所以,本書是作者親身體驗與學理探索相結合的產物,并且具有以下特點。
一、以新視角切入
“地域文化是形成民族審美心理結構的重要條件,也是構成一個民族的美學思想獨特性的基礎。”[1]19在該著中,作者將地域文化和巴蜀中人的美學思想相結合,書中提到由于巴蜀位于盆地,四周被群山環繞,但巴蜀先民并不屈服于盆地環境的束縛,“開辟道路,向外發展”,沖破險惡的環境給他們帶來的重重阻隔,在他們身上體現出頑強不息的樂觀精神。這種對自然環境的態度深深積淀在巴蜀先民的心底,進而轉化為勇于開拓創新、不受陳規舊制束縛的文化精神,而這種巴蜀文化精神又深深影響到巴蜀美學精神和藝術觀念,在明末巴蜀學者來知德身上就得到了體現。他提出的“得意而忘象”“舍象不可以言《易》”“格物者,格去其物欲也”以及“文能載道,何害于文”等美學命題,體現出了巴蜀人不畏懼權威、勇于開拓創新的特點。此外,巴蜀之地處于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之間,具有同時吸收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先天地理優勢,在獨特的地理環境之中,巴蜀文化具有了包容的精神,明代學者楊慎的美學思想中就蘊含著這一點。他提出“有諷諭而不露”的審美教化論,既有易學、莊學的特色,又具有儒學倫理教化論的傾向,是一種融合儒、道、易的新型審美教化論。法國學者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提出了影響藝術產生、發展的“三因素”說,即種族、環境、時代。其中,環境包括自然地理和氣候等。德國哲學家康德在《自然地理學》中基本上也是從自然地理環境對人審美觀念的影響來論述“鑒賞力批判”的[2]。在該著中,作者同樣是結合地域特征,對巴蜀美學及審美意識進行探討、研究,不同的地理環境給身處當前環境中的美學家所帶來的獨特影響。
二、對材料的細致挖掘
作者在研究巴蜀美學史的過程中,非常注重從各個時代各具特色的美學家身上,包括他們的美學著作中,去探索、研究、發現這些美學家們的美學創見。作者善于思考,重視思辨,在該著中運用了大量的古文資料來展現、論證相關理論,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在該著開篇提到的司馬相如引用大量《子虛賦》《上林賦》中的原文,用“齊王之樂”“楚王之樂”以及“無是公之樂”三種“樂”的對比,進行深入討論,呈現出司馬相如獨特的審美追求。“齊王之樂”與“楚王之樂”雖有不同,但從本質上說,都是“淫樂”“奢靡”,以物質欲望的滿足為樂,司馬相如借“無是公之樂”表達自己反對“奢侈”“荒淫”“獨樂”的審美觀。此外,在該著中作者展示了理性思辨的力量,在對每個時代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學家的美學理論進行論述,對他們的審美意識進行觀照時,作者的敘述清晰流暢,用深沉的邏輯折服讀者。如在該著提到“蜀中通儒”譙周的美學思想中,魏晉時期玄風興盛,在藝術審美方面,魏晉美學體現出對超越有限的無限的追求,但巴蜀之地被群山環繞,且偏居西南,中原文化難以及時進入,所以,在譙周的美學理論中仍以儒學為重,無論是對“喪而歌”的反對,還是他所推崇的“君子之樂”都體現出儒家美學觀念。作者從譙周的美學觀引入,再提出巴蜀的思想文化與美學的特質,即“變”中的“不變”。以小見大,由點入面,一目了然。
三、新觀點的提出
在巴蜀美學史上,有許多美學家都提出了自己獨到的美學觀點,作者在選擇最具特色的美學家,對其觀點進行論述的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從更深的層次進行發掘。在該著中,作者對司馬相如、嚴遵、揚雄、譙周、李榮、歐陽炯,“三蘇”、魏了翁、蒲道源、楊慎等美學家以及他們的美學思想都提出了新的看法,做出了新的研究。作者從陳摶的美學思想中,挖掘出了“醉”在陳摶蜀學美學中的獨特含義,即消除欲望得失、利害計較,從而達到對自然而然、逍遙無為精神境界的追求。在此基礎上,作者在“三蘇”蜀學美學中提出了“醉”在藝術創作活動中所具有獨特的作用。蜀學美學尊情、尚情,為“醉”的藝術創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作者認為,“三蘇”引“醉”入藝術與人生,將“醉”提升為一種即工夫即本體的蜀學美學范疇,成為了宋代美學中一個獨特的美學流派。一方面,“三蘇”蜀學以“醉”觸情,倡導藝術創作超越技法,彰顯“天真”的審美風格;另一方面,蜀學美學強調以“醉”為人生的修為方法,強調使人“忘”的功效,使人達到“曠然天真”的審美境界。同樣將“醉”引入美學理論當中的還有元代的蒲道源,在他看來,“醉”是一種自由創作的方法,是一種超越技法、規則的無法之法,更是一種主客合一的境界。在“醉”這樣的狀態之中,人可以進行自由、超脫的創作,從而達到“主客合一”“天人合一”的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
四、結語
巴蜀美學是中華美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巴蜀美學精神也是豐富多彩的中華美學精神的有機組成部分[3]220。譚玉龍的《巴蜀美學史稿》,在對大量歷史文獻挖掘的基礎上,結合巴蜀之地獨有的地域文化特色,分析歷朝歷代巴蜀美學家們的美學思想,對巴蜀美學、巴蜀區域審美意識提出獨到的看法、觀點,體現出作者的創見性和深刻性。該著具有以新視角切入、對歷史材料的細致挖掘和新觀點的提出等特點。作者對巴蜀美學的思考和對巴蜀美學的研究,本身也是巴蜀美學的發展與進步。此外,在該著中,作者對過去一些未曾被人注意或重視到的美學思想進行了深入挖掘,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這對巴蜀美學史的豐富和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簡言之,譚玉龍的《巴蜀美學史稿》無論是在內容的挖掘、研究的深度,還是在理論的建樹上,都具有其特色,作為我國第一本對巴蜀美學史進行較為系統研究的著作,具有開創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