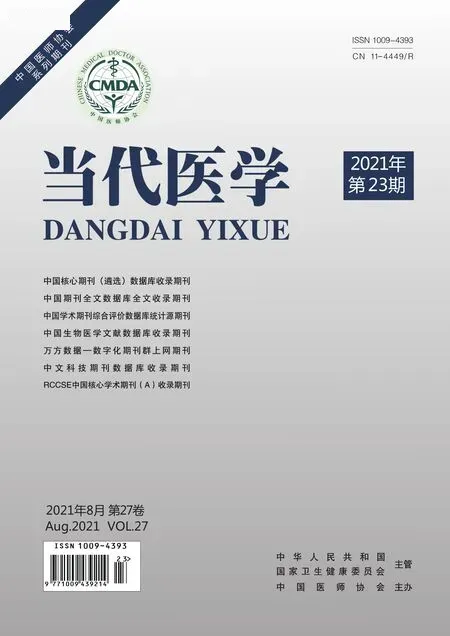超聲造影引導下肝病變的穿刺活檢檢測方法探究
黎坤儉,吳金蘭
(1.福建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超聲科,福建 廈門 361004;2.三明市中西醫結合醫院超聲科,福建 三明 365001)
超聲能顯示肝內1 cm 左右的占位病變,但小占位的聲像圖特征通常不典型,良、惡性定性診斷困難。自20世紀70年代初Holm 和Goldberg 同時發明穿刺探頭以來[1-2],在臨床診斷肝惡性腫瘤檢查方面,超聲引導下經皮穿刺抽吸細胞學檢查方法優先選擇。北京市腫瘤防治研究所自1980年開展該項工作,證實該方法安全、簡便、準確性高,并能迅速獲得細胞學檢查結果,但一般難以作出組織學診斷,故存在局限性。通過采用改進針尖和穿刺技術細針方法進行組織活檢取得成功,推進了超聲造影引導下肝病變的穿刺活檢檢測技術的發展[3]。近年來,細針組織活檢在肝病變的應用中取得較滿意的效果,不但能對其病變的程度做出鑒別診斷,而且能檢查肝病變腫瘤的組織學類型、分化程度和良性病變的組織病理變化情況,活檢針的改良、在取得組織學診斷的同時,亦能獲得細胞學診斷,顯著提高了診斷的可靠性[4]。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討超聲造影引導下肝病變的穿刺活檢檢測方法的診斷價值,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2017 年1 月至2019 年12 月廈門和三明兩所地方醫院收治的臨床確診為肝臟占位性病變患者122 例,共 192 個病灶,其中男 79 例,女 43 例;年齡 36~80歲,平均(58.1±5.1)歲;平均病程(10.2±2.5)個月;原發性肝癌22 例,肝轉移瘤17 例,肝血管瘤40 例,肝局灶性脂肪變性22 例,肝局限性增生6 例,肝膿腫3 例,肝癌介入治療后評估12例。
1.2 納入及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疑肝細胞肝癌需確診者;肝惡性腫瘤,需明確是原發或繼發者;肝晚期惡性腫瘤,為非手術治療須確診并了解腫瘤的組織學分型及分化程度者;疑診肝良性病變但惡性腫瘤待排除者;介入治療前明確診斷,治療后療效評價者。排除標準:灰階超聲顯示病灶或目標情況不明者;有可能或大量出血者;腹腔積水嚴重者;穿刺路徑必須經過重要血管、器官者;感染上化膿者。本方法無絕對禁忌證,相對禁忌證同針吸細胞學檢查。臨床疑診為各型肝炎患者或肝硬化等肝良性彌漫性病變時,因細針活檢的標本過小,往往難以滿足組織學診斷的要求,宜選用粗針活檢。
1.3 方法
1.3.1 儀器設備與材料 西門子Acuson S2000(德國)高檔彩色多普勒超聲并配套有超聲造影軟件,探頭采用4C1,探頭頻率為2~4 MHz。造影劑為SonoVue(意大利)超聲造影劑,造影微泡為磷脂微囊的六氟化硫(SF6),平均微泡直徑為2.5 μm,pH 4.5~7.5。穿刺針采用21G 手動抽吸活檢針(日本)和20G自動活檢針(英國)。
1.3.2 檢查方法 用普通探頭掃查病灶,并選擇穿刺途徑。按穿刺部位選擇適宜體位,右葉腫瘤常采用右前斜位。常規消毒皮膚,鋪上治療巾。換上無菌穿刺探頭及引導裝置,再度確認穿刺點、途徑;可用彩超引導以避開血管。局麻注射2%利多卡因3~4 mL。將引導針注入壁側腹膜或胸膜層。選擇適宜的活檢針刺入肝內腫瘤表面。拔起針栓針芯后刺入腫瘤內,并在上、下范圍內提拉2 次,然后旋轉拔針(需保持負壓)。推進針栓針芯以推出針管內組織條,置于紙片的1 cm范圍內,盡量保持組織條完整集中,并立即固定于甲醛溶液中。取出針芯,針管接上注射器,加壓反復推2~3 次,盡可能將殘留在針管內的液體推在玻片上,立即固定染色。無負壓活檢針穿刺法:檢查方法同上。但取樣操作不同,如秦氏多孔針,帶針芯插入腫塊內,拔出針芯后在腫塊內來回提插3~4次,最后拔針,再用針芯將組織塊推出,標本處理同上。槽式自動活檢法:方法基本同負壓抽吸法,選用Tru-cut內槽針,接可調試活檢槍,其針芯前段有1.52 cm長、0.2 mm寬的切割槽。活檢時帶針芯刺入腫塊表面,根據腫塊大小確定射程長度;繼而打開保險閥,按動開關取材;拔針后從針芯凹槽中取出組織條,并取出針芯,外套管接注射器反復推,以獲得滿意的細胞學診斷。標本處理同上。細針組織活檢可在常規門診進行,術后留觀1 h,觀察患者的脈搏、血壓以及腹部情況,無異常即可離去。
1.4 觀察指標 比較兩種方法敏感性、特異性及診斷正確率。特異性=超聲呈良性病灶/病理良性病灶總數×100%;敏感性率=超聲呈惡性病灶病灶數/病理惡性病灶數×100%;診斷正確率=超聲與醫院病理一致的良、惡性病灶總和/總病灶數×100%。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表示,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n(%)]表示,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122例患者中,兩種超聲檢查結果,見表1。超聲造影引導穿刺法檢查特異性為91.3%,敏感性為96.7%,準確率為93.4%,高于常規超聲的57.4%、66.4%、61.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1 兩種方法檢查結果比較[n(%)]Table 1 Comparison of inspection results between two methods[n(%)]

表2 兩種檢查方法診斷率比較(%)Table 2 Comparison of diagnostic rates between two examination methods(%)
3 討論
肝內腫塊細針活檢通常選擇途經正常肝組織再刺入腫塊,以減少出血可能。肝血管瘤患者中約50%可獲得成功的組織病理切片;其他50%患者效果則與針吸取樣相似。根據穿刺取材決定穿刺次數,一般為2~3 次;若取材滿意有時1次也可獲得診斷。盡管經皮腹部病變細針穿刺活檢安全性較高,但可能發生并發癥,嚴重者甚至會威脅患者生命,因此,穿刺前應嚴格掌握穿刺活檢的適應證和禁忌證。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在10 766~66 397 次穿刺活檢后死亡率為0.006%~0.031%,33 例死亡患者中,肝病變穿刺21 例,胰腺穿刺6例,21例肝穿刺中繼發出血17例,6例胰腺穿刺中有5例為胰腺炎穿刺活檢后針道種植發生率為0.003%~0.009%。另有其他腹部穿刺活檢的大樣本研究結果顯示,1 060~3 500次穿刺活檢后死亡率為0.028%~0.096%,但無針道種植發生[6]。穿刺活檢后引起出血的發生率較低,為0%~1%。而脾穿刺后出血發生率為1%~2%,略高于其他腹、盆腔器官穿刺。Quaia等[7]采用14~22G的Chiba型穿刺針對麻醉豬的肝和腎進行穿刺活檢,結果顯示,在進行肝穿刺時粗針出血量多于細針,在進行腎穿刺時18G、20G和22G出血量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腎活檢出血量多于肝活檢,故腎活檢宜采用更細針,如采用Tru-cut 活檢針和end-cutting活檢針進行活檢,針道種植發生率為0.76%(8/1055),使用Tru-cut活檢針的433例患者無1例發生針道種植,發生種植的8例均系采用end-cutting活檢針[8]。表明,穿刺操作者應意識到穿刺活檢可能引起包括死亡在內的嚴重并發癥,應嚴格掌握穿刺適應證并具備合理的預防措施;穿刺時應盡可能減少穿刺次數;對于有出血傾向及惡性可能的肝病變進行穿刺活檢時應仔細掃查、盡可能采用細針并減少穿刺次數,避免直接穿刺位于表面的病變,經過正常肝組織穿刺病灶可減少出血。
超聲引導經皮細針組織學活檢優于常規細胞學檢查,避免了粗針穿刺時的所存在的并發癥和危險性,使細針活檢突破了細胞學診斷的限制,推進到組織學水平[8],值得在肝病變尤其是局限性實性占位病變的診斷中應用。在對液性、血性或壞死成分為主的病變取樣不滿意時,細胞學檢查仍可作為一種補充方法,兩種方法結合互補,診斷正確率高于其中任何一項單獨檢查方法。此外,某些彌漫性肝病,如慢性肝炎、肝硬化等,有些細針所取活檢組織并不能滿足組織病理檢查的標準,稍粗針(18G)仍是組織活檢中較安全的確診方法。
隨著超聲、CT 和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等影像技術的飛速發展,診斷正確率逐漸增高,但仍未達到100%,必要時還需進行經皮穿刺活檢[9]。因此,影像引導下的經皮穿刺活檢對病變的診斷仍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影像技術的發展使腫瘤穿刺引導更加精確,使組織的經皮活檢達到小型外科手術所不能達到的最低程度的侵害,雖然手術切除活檢仍適用于一些病例,如乳腺和腦腫瘤,但經皮穿刺活檢已經成為全身大多數腫瘤的診斷標準,與手術切除相比,經皮穿刺活檢具有時間短、費用低、并發癥少等優勢,超聲造影引導經皮穿刺活檢檢測技術是至今為止臨床獲得肝腫瘤組織病理學診斷中使用最多的一種技術,因此,被稱為檢測肝臟良性和惡性占位病變的金標準。有文獻[10]報道,穿刺活檢的敏感性為86.0%~95.1%,特異性可高達100%,診斷正確率為88.0%~93.0%,但取材不足發生率可達到10%~15%,必要時需二次穿刺活檢,約10%的穿刺活檢結果是不確定或假陰性的。
穿刺盡可能途經正常肝組織穿刺病灶(包括表淺病灶)以減少針道種植,如周圍無正常肝亦可采用21G細針穿刺并減少穿刺次數。目前一些先進超聲儀器配備實時雙幅諧波灰階超聲造影軟件,可同時顯示組織諧波成像模式和造影諧波成像模式。啟動程序后,造影諧波成像幾乎看不見肝的灰階圖像,僅能接收來自造影劑的二次諧波信號。而組織諧波成像仍可顯示肝及病變的情況,并監視穿刺過程。注射造影劑并啟動內置計時器后,根據造影顯示的病變異常增強或退出區域,在造影同時進行穿刺活檢,組織諧波成像可清晰顯示病變和穿刺針的位置,使穿刺活檢更加準確。
綜上所述,超聲造影引導下肝病變的穿刺活檢檢測方法具有更高的特異性、敏感性、檢查準確率,應用優勢明顯,最終診斷結果相較于常規超聲檢查更加接近病理檢查,臨床應用效果顯著,具有較高應用價值,值得臨床推廣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