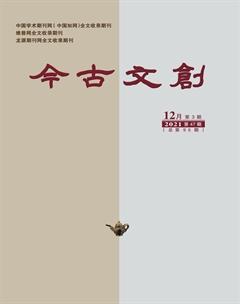論《黔小景》中生命的悲劇與價值
方婉蓉
【摘要】 《黔小景》是1931年沈從文發表在《北斗》第一卷第三期的一篇短篇小說,講述了三月貴州的深山里,一條“官道”上發生的故事。小說用散文化的筆法、遠近景轉換的敘事方式向讀者展現了貴州深山的現實環境和人們的生活狀態,表現了特定歷史環境下人們的生存困境和生活悲劇,體現了作者獨特的人文關懷,以及對悲劇背后生命價值的思考。
【關鍵詞】 《黔小景》;生命;悲劇;價值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47-0004-02
《黔小景》是指黔地的一處小景,即文章開篇提到貴州深山里的一條官道上。在這條普通的官道上,綿綿的小雨、泥濘的道路、來往的行人、鋒利的刀劍、血腥的人頭……交錯在一起,構成一幅悲涼的畫面,展現了特定歷史環境下人們的生存狀態,以及這種生活背后呈現出濃郁的悲劇性,體現了作者對生命價值的思考和關懷。
一、普通人的生活狀態
貴州,簡稱“黔”或“貴”,地處西南腹地,屬于云貴高原地區,地形復雜,氣候潮濕多雨,與外界的交流較少,形成了一個比較封閉的社會環境。小說首先用遠鏡頭的方式展現出一幅煙雨蒙蒙的畫面,隨后鏡頭慢慢移動,在雨中可以看到“爛泥般的路”“崩壞的坎”“挨餓的黑老鴉”“憔悴的婦人”……構成了一幅蕭索荒涼的農村景象,讓人感到濃濃的愁緒,奠定了文章悲涼的情感基調。
接下來鏡頭拉近,將畫面轉到深山里的官路上,在這條泥濘的路上,仍然有不少行人在雨里奔走,他們都行色匆匆,在這條路上度過一個又一個春秋。他們憑借“并不有十分把握的命運”,沿襲父兄傳下的習慣,遵循著生活的常態,“這條長長有名無實的官路,折磨他們那兩只腳,消磨到他們的每一個日子中每人的生命。”
雖然道路艱難,工作重復乏味,但是這些商人們也有自己的生活樂趣。他們在出發后,平時寂寞冷清的官路上,也開始熱鬧起來。當地人在官路的小站上,開了很多家客舍,這些客舍是商人們漫長旅途的落腳點。客舍主人“預備水,預備火,照料一切”,客人們在歡笑中,似乎忘記了旅途的疲倦,享受著這一刻的安寧與美好。
然而,在這美好的時光背后,卻隱藏著血腥與殺戮。白天,商人們在往來的路上,常常可以看到“路旁有時躺的有死人,商人模樣或軍人模樣”,他們有可能是遇到了土匪,或者搶劫的軍人,或者其他意外事故。這與前面人們在客舍里把酒言歡的場面形成鮮明對比,商人在這條路上隨時都可以感受到死亡與殺戮,但他們只需要考慮如何走過這條官道,至于路上的事情,則與他們無關,即使這些事情很有可能預示著他們的明天。
《黔小景》中的景是悲涼殘酷的,給讀者呈現的是一幅慘烈的歷史畫卷,在這幅畫卷中,自然和社會無形中壓迫著每一個人,他們的生存一開始就是悲劇的。但是這些人并沒有因此放棄生活,面對著死亡的威脅,他們無法改變,只能淡然面對,努力過好自己的每一個日子,努力地活著,這就是他們的處世之道,也是他們的生存智慧。
二、生命存在的悲劇性
隨后文章將鏡頭慢慢拉近,用特寫的方式將畫面定格在一個小客舍里,展現了一個飽受喪子之痛的老人的孤單和寂寞,表現了生活的殘酷性和生命的悲劇性。兩個商人到了“一個孤單的客棧”里。這里有一個孤單的老人,這天是他的生日,他熱情地招待了兩位客人。老人像小孩子的神氣自言自語地說著:“晴了,晴了,我昨天做夢,也夢到今天會晴”,老人心想著晴天、想著客人,在他生日的這天都已經實現了,這對老人來說是最大的安慰。
當客人問到老人的生活狀況時,老人答道:“我一個人。”老人看著這個和自己兒子有些相似的年輕人,本來要說“兒子死了”,但忽然又說道:“兒子上云南做生意去了。”這里老人的話是給自己留了一份念想,在他孤孤單單的時候,這兩個旅客給他帶來了一絲溫暖,但不管是晴天還是這兩位客人,都只是短短的一瞬間,天氣可能隨時變壞,客人們第二天也會重新上路,老人仍然是孤單一人。
這天老人說了很多,他明明已經一個親人都沒有了,可是“就像為哄騙自己的樣子,把一些多年來已經毫無消息了的親戚,一一數著”,他看著這兩個年輕人,痛苦的生活仿佛注入了新的動力,老人不知不覺給自己編織了一個個謊言,這些都是老人記憶中的模樣,他在回憶中尋找期望和依靠。但今晚一過,客人們就要走了,他又要孤零零地守在深山里,倒還不如就在自己的夢中離去。
老人的死亡對他而言是一種解脫,他一直都是孤獨的,但他把孤單埋藏在心里,過著普通的日子,慢慢地麻痹自己。在老人生日的這天,他自欺欺人地和客人們聊天,說著不可能實現的謊言,隨后又在謊言中去世。沈從文在文中這樣安排老人的去世,看似殘酷,其實卻是一種悲憫。對老人來說,此時離世,也許是命運最好的安排,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終于可以不再孤獨。就像《賣火柴的小女孩》在火柴中看到祖母一樣,老人或許也在燃燒的火爐中看到了去世的兒子,也許就像他之前說的謊言一樣,兒子只是去云南做生意了,過不了多久,他們就可以團聚,老人也就不再孤獨了。
在老人身上,可以看到深山里無數人的影子,在這個混亂的年代,當他們年老時,也有可能會變成老人這樣,一個人守著房子,悄無聲息地死去。也許不僅局限于老人,在這深山的官道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艱辛和苦楚,他們的命運早已不在自己手中,所以當他們面對死亡和殺戮時,他們的態度是冷漠和淡然的,因為生命中無處不充滿悲劇,而他們能做的僅僅是按照自己本分好好地活著。
三、生命悲劇的價值與關懷
“那么老了一個孤人,自然也很應當死掉了”,當老人去世后,鄉下人很自然地這么想著,兩個商人也是這么想著。沒有人覺得奇怪,也沒有人覺得可惜,這本就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商人和鄉下人的想法看似有些無情和冷漠,可這也是自然本身的規律,生老病死,人之常情。
在這條官路上,每天都有著各種各樣的故事,往來的人對這些事情早已麻木,這條泥濘的官道折磨他們那兩只腳,消磨著他們每個人的生命。死亡無處不在,作者用最平緩低調的敘述,表達生命的悲傷與無奈。在深山里的人們,“他們全部的人生哀樂,他們埋藏在心底的所有期待與想望,全部像荒蠻山中的草木,隨著季候的變換,周而復始默無聲息地自行榮枯。”對他們來說,無需思考生與死,順其自然便好,默默地承擔著自己的那份責任,責任卸下,死亡就來到了。
生命本就是這樣,縱使有再多的感情,命運總是在無形中給每個人分擔了一份責任。這兩個商人在這條官路上,可能又會繼續看到尸體、人頭、看到無人祭拜的荒冢。他們或許依然像之前千千萬萬個商人那樣,依然是默默地看看,又默默地走開了。對他們來說,“在路上所見的雖多,他們卻只應當記下一件事,是到地時怎么樣多賺點錢。”對商人來說,做生意就是他們的本分,他們不關心其他的事情,他們只需要按照規矩,將貨物送達,然后再換取自己的那份利益。在那個混亂的年代,生死不是他們可以控制的,對普通人來說,活著已經是最大的幸福。
《黔小景》中一直籠罩著血腥、死亡的陰影,無論是開頭黔地景色的描寫,還是中間對老人故事的敘述,以及結尾商人們的重新上路。這條深山里的官路上,景悲、人悲、情更悲。雖然悲傷,但是卻不悲痛,在文中對死亡的大量書寫,除了表現人們深刻的悲劇性以外,更透露出了生命的價值——生存,即人要生存。無論有多少殘忍和悲傷,人總是要活著。官道上的行人,即使知道這條路上有很多危險,但是為了生存還是要繼續在這條路上行走;路邊的客舍,即使面對著軍隊、土匪的剝削,還是一樣守著自己的房子,默默地過著自己的生活。而那位老人,在兒子去世后,在所有親人都失去聯系后,還是守著房子。
海德格爾指出:“日常生活就是在生和死之間的存在。”這些深山里的人,他們都是最底層的普通人,他們見過太多的生死,所以他們在生與死之間,把一個又一個日子消磨。對他們而言,生與死只是一個輪回,這輩子的責任盡完了,死后又去完成另一份責任。
沈從文曾說:“我是個對一切無信仰的人,卻只信仰生命。”《黔小景》的故事是悲傷的,在那個歷史環境下,每個人都生活在重壓之下,他們承受著歷史、社會、環境的重擔,在夾縫中苦苦生存。但是這些人又是十分堅強的,他們“各按本分”生存下去, 承擔著人生中必須承擔的一切,雖然有痛苦,但是在旅人們圍著火爐談話的夜晚,兩個和老人的相處,以及老人最后一夜的幸福,這些歡樂都是無法否定的。對這些人來說,他們只需繼續保持著“人生本來如此”的平和心態,承擔著各自的那份責任,默默地生活下去,這就是他們全部的生活意義。正如民間的那句諺語一樣“好死不如賴活著”,雖然生命中充滿著悲傷和無奈,每個人都要在困境中苦苦掙扎,但是只要活著便還有希望。
在沈從文的筆下,這些鄉下人看似愚昧,卻活得清楚、明白,他們的人生是最真實的狀態。他們在生活的困境中,在死亡的陰影下,仍然各按本分地生存,沒有怨天尤人,沒有自暴自棄。所以文章在“苦難的敘事”中呈現出一種悲涼的詩意,讓人在惋惜生命的悲劇時,也多了一份對生命價值的思考,讓讀者在小景的苦難中尋找希望。
參考文獻:
[1]沈從文.黔小景[A].邊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8:57-68.
[2]凌宇.沈從文傳[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1988:39.
[3]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280.
[4]沈從文.水云[A].劉洪濤,楊瑞仁編.沈從文研究資料(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