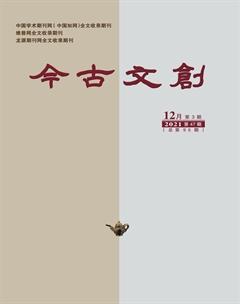試論日本翻案小說中的詩
李奕璇
【摘要】 翻案小說是日本一種獨特的小說創作方法,在日本一直備受青睞。其中,中島敦的《山月記》、芥川龍之介《杜子春》都取材自中國唐代傳奇小說,兩部作品在與原作的對比上具有較多的相似點,譬如兩部作品都保留有原作的題材,有著與原作大致相同的情節和故事走向。在這兩部作品中,都引用了詩句穿插其中,為作品增添了亮點。但是,在作為原作的《人虎傳》和《杜子春傳》中,卻并沒有詩句的出現,即在作品中穿插詩句的方式是日本作家在改寫中自行添加的一筆。日本作家在改寫過程中對詩的添加亦是對原作的“翻案”之一,在翻案小說中的詩句,或有更甚原作的精彩之處和其重要作用。本文將以《山月記》和《杜子春傳》為例,對其中增添的詩進行解析。
【關鍵詞】 翻案小說;詩;中島敦;芥川龍之介;《山月記》;《杜子春》
【中圖分類號】I313?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47-0014-02
翻案小說是一種形成于日本的獨特的創作小說的方法。隨著日本的開放,外來文化的相繼涌入,日本作家力圖創新,通讀中、西方文學作品,對外來文學作品進行翻譯、研讀和深入挖掘。他們在保留原作主要情節的前提下,加之自身的理解和想象進行改寫,于是誕生了全然不同的新的文學作品,這就是“翻案小說”。日本翻案中國文學作品而來的文學作品時常廣受推崇,歷代翻案自中國傳奇小說的作品也層出不窮。
近代以來,該類作品依然備受青睞。太宰治《魚服記》、森鷗外《寒山拾得》、芥川龍之介《杜子春》、中島敦的《山月記》等皆是改編自中國文學作品的佳作。其中,中島敦的《山月記》、芥川龍之介《杜子春》都取材自中國唐代傳奇小說,字里行間不乏中國古典的風采。兩部作品在與原作的對比上具有較多的相似點,譬如兩部作品都保留有原作的題材,有著與原作大致相同的情節和故事走向。并且,在這兩部作品中,都引用了詩句穿插其中,為作品增添了亮點。《山月記》中,李征在變虎遇友后大抒心中苦悶,作詩云:
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
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
我為異物蓬茅下,君已乘軺氣勢豪。
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嗥。[1]
《杜子春》中,鐵冠子為杜子春的決心打動,收其為徒并攜杜子春前往峨眉,途中詩曰:
朝游北海暮蒼梧,袖里青蛇膽氣粗。
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2]
但是,在原作《人虎傳》和《杜子春傳》中,卻并沒有詩句的出現,即在作品中穿插詩句的方式是日本作家在改寫中自行添加的一筆。日本作家在改寫過程中對詩的添加亦是對原作的“翻案”之一,在翻案小說中的詩句,或有更甚原作的精彩之處和重要作用。此處筆者將以《山月記》和《杜子春傳》為例,對其中增添的詩句進行解析。
一、《山月記》及其中的引詩
中島敦的《山月記》,改編自中國唐代傳奇小說《人虎傳》。《人虎傳》作者張讀,字圣朋。該篇原載于《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七,題作《李征》,注出《宣寶志》。《人虎傳》描寫李徵一心向往仕途、追求功名利祿,但卻為人清高孤傲,不甘與世俗為伍,又因縱火殺人,違背了封建倫理道德,最終淪為虎身。中島敦則將其“翻案”成李徵既懷才不遇又不甘沉淪,著重刻畫內心世界,揭示出其強烈的自尊心和巨大的羞恥心并存,正是這種難以調和的矛盾使他最終承受不住外界的壓力而喪失自我,從而摒棄原先宣揚因果報應的主旨,突出了人性和人性異化這個主題[3]。中島敦將中國原本的歷史故事加入了作家自身的理解,融入了作家的個人體驗,使故事內涵更加豐富。
《山月記》中,化身為虎的李征在一夜忽遇奉旨前往嶺南的舊友袁傪,李征為老虎的獸性所控,險些傷害到舊友,為此十分懊悔,藏身草叢發出陣陣悲泣。聽這聲音,袁傪竟認出此為自己的舊友李征,并與他交談。先是李征訴說了自己變成老虎的經過,然后傾訴了自己變成老虎后的遭遇,然后講了自己想要成為詩人的抱負。如今已經變成老虎的李征,唯能委托舊友幫助自己記下詩作,以暫且消去心中執念。在記詩最后,李征難掩心中的苦悶與悲痛,當即作了一首詩:
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
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
我為異物蓬茅下,君已乘軺氣勢豪。
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嗥。[1]
這首詩引自唐代詩人李微創作的《無題》,題注李征的事跡。該詩的大意如下:我發狂變成了兇猛的異類(老虎),這樣的災難恐怕是難以逃脫的宿命。如今化身為老虎的我兇猛無敵,就像曾經為人的我擁有的聲望一樣。如今身為異類的我躲在茅草之下,而我的朋友你已經功成名就前途光明。這一晚在這山間野嶺空對明月,我想仰天長嘯卻只能發出野獸的嚎叫聲。
這首與李征的遭遇十分契合的詩放在小說中,作為李征的詩作展現給讀者,強烈總結了李征化虎的玄奇經歷并強化了此時此刻李征內心的煎熬悲痛以及面對事實無可奈何、面對未來無所憑依的感情。在《山月記》中,李征的形象被塑造為愛詩癡狂,成為詩人名留青史是李征畢生的追求和抱負。為了作詩,李征甚至放棄仕途,中島敦的“翻案”中將李征對詩的執著表現得淋漓盡致。正是因為有這樣愛詩成狂的先言,在這里中島敦將詩作《無題》添入小說中則顯得更為高明。因為這將是變成老虎的李征的最后一首詩作,也象征著李征的詩人生涯到此結束。李征以這樣一首詩來結束自己追求詩的作為人的一生,更添悲劇性,與“翻案”的內容渾然呼應。并且,詩作之后的小說內容是李征訴說自己變成老虎的原因,直到最后李征才將自己的妻兒托付給袁傪,又消失在了草叢中。以小說中的詩為分界,其前講述了李征化為老虎的經歷,其后分析了李征變成老虎的原因。李征甚至將妻兒置位在自己的詩作之后,連他自己都為此感到羞愧。中島敦的《山月記》中表現出了更為復雜的人性與感情,其中添入的詩作《無題》更為小說平添了一抹色彩。
二、《杜子春》及其中的引詩
芥川龍之介的《杜子春》改編自中國唐代傳奇小說《杜子春傳》。《杜子春傳》節錄自《玄怪錄》,而《杜子春傳》又是由是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七婆羅痆斯國《烈士池及傳說》改編[4]。原作《杜子春傳》表現的是道教思想下人難以舍棄七情六欲因而難以修煉成仙的觀念,表達了人應該放下感情,追求大道的態度。而芥川龍之介的《杜子春》雖沿襲原作脈絡,但在對原作的“翻案”過程中將意義帶入了另一個方面,通過杜子春在母親的愛面前重新認識并接納人性、放棄修仙踏實做人的行為表現了“愛”這一不同的主題。
小說《杜子春》中,窮困潦倒的杜子春在洛陽城門下為生計發愁時,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告訴他了地點,杜子春挖出了金銀財寶,變成了富甲一方的大富豪。然而變成富豪的杜子春卻揮霍浪費,很快復歸貧困,在洛陽城門下嘆氣發愁。這時那位老人又出現并使他再次成為富豪。如此反復了三次。杜子春覺得在他富有的時候人人擁簇,在貧困的時候無人問津,實在人性冷漠。便不想做人,請求老人帶其求仙。而這位老人是住在峨眉山的仙人鐵冠子。鐵冠子同意了杜子春的請求,收他為徒并攜杜子春前往峨眉山接受成仙的考驗,于是鐵冠子在駕馭竹杖飛行之際,吟唱了幾句詩詞:
朝游北海暮蒼梧,袖里青蛇膽氣粗。
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2]
“朝游北越暮蒼梧”原句出自唐代呂洞賓的《絕句》,元曲《呂洞賓三度城南柳》中引用后,將北越改為北海。小說中引用的詩句首句為“北海”,因而芥川龍之介在創作的時候應當是引自元曲《呂洞賓三度城南柳》。小說《杜子春》中引用的這四句詩的大意如下:早上還在北海游玩,傍晚就到了蒼梧,袖中收服了一條青蛇使我膽氣壯大。我三次醉倒在岳陽樓無人理會,在吟詩之際就已經飛越了洞庭湖。
從這幾句詩中,不難體會到一種“快”。詩中“朝北海,暮蒼梧”兩者跨越萬余里,非常人可以做到。而芥川龍之介的《杜子春》中,仙人鐵冠子攜杜子春駕竹杖御風而行,轉眼間就從洛陽來到了峨眉山上,地理跨度亦是很大。兩者所要表達的空間跨越的移動感近乎相同,芥川龍之介在這里引用這首詩,將這種“快”以另一種形式展現了出來。在“朗吟”之際,杜子春從洛陽到達了峨眉山頂,實現了快速的空間跨越。再來看杜子春在洛陽的經歷,本來一貧如洗的杜子春三次受到鐵冠子的幫助成為大富豪,期間人們在他富有的時候紛紛與之結交,在他貧困的時候卻棄之不顧。“三醉岳陽人不識”暗示的似乎就是杜子春得如此經歷,貧貧富富之于他仿佛一場場夢一般,他看到的是人性的冷漠。另外,中國唐代傳奇《杜子春傳》實則是一則道教的故事,其所傳達的也是道教的思想觀念。芥川龍之介在對《杜子春》故事的“翻案”中,其中仙人鐵冠子吟誦道教宗師呂洞賓的詩,正是體現了道教的色彩。
三、結語
如上所述,翻案小說名作中島敦的《山月記》和芥川龍之介的《杜子春》在其作者進行改寫的過程中,引用了原作中并未出現過的詩句。此處,筆者關于在對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翻案”中引用詩持有積極的肯定態度,認為詩的引用或可貼合情節,或可表傳達情感,或可在小說結構中起到相應的作用,能夠作為小說中的精彩之處被接受。此外,上述兩部翻案小說對古詩的引用與中國古典傳說題材相得益彰,對于讀者來說,能夠更好地感受到源自中國古典文化的魅力。特別是中國讀者在閱讀此類小說的時候,或更會對其中的詩抱有親切感。對中國古代詩詞的引用在日本文學作品中屢見不鮮,亦可見中國古典文化在日本廣受歡迎,影響深遠。
參考文獻:
[1]中島敦.山月記[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
[2]芥川龍之介.芥川龍之介全集[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
[3]陸求實.日本作家迷上中國古典文化,寫“翻案”小說致敬唐代傳奇[N].文匯報,2019-07-13.
[4]陳詩堯.淺論《大唐西域記》中“烈士池傳說”的再創作[D].浙江大學,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