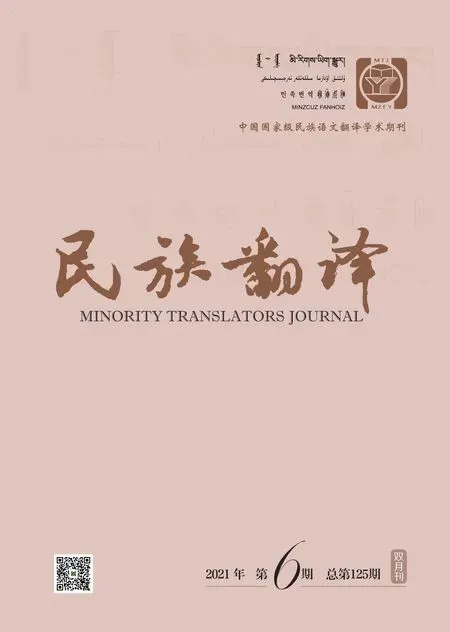王宏印“創作型回譯”理論與實踐的新探索*
——基于《〈阿詩瑪〉英譯與回譯》的學術考察
⊙ 王治國 蘇佳慧
(天津工業大學人文學院,天津 300387)
王宏印(1953—2019)長期從事中外文學文化典籍翻譯與中西翻譯理論教學與研究。他堅持詩歌創作,以中西結合的學術素養和對譯詩的親身體驗,從紐馬克(Peter Newmark)《翻譯教程》提煉出“檢驗型回譯”,隨后提出“研究型回譯”并回譯霍克思英譯《紅樓夢》詩詞10首,繼而又對彝族敘事詩《阿詩瑪》進行“創作型回譯”。通過“創作型回譯”實踐而形成的回譯成果,既可以作為獨立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可以通過與原作對比產生差異性理解,并對《阿詩瑪》撒尼文化做出解釋。通過對回譯作品的閱讀可以發現回譯的奇妙之處,幫助讀者更好地賞析《阿詩瑪》這部彝族民間敘事詩。
一、回譯之源:《阿詩瑪》傳承與戴乃迭英譯
《阿詩瑪》是一部彝族支系撒尼人口頭流傳的民間敘事詩,也是撒尼文化的重要內容。在集體創作和流傳過程中,不同演唱者不斷對其進行改造,呈現出口頭傳承、彝文文本記錄、現代漢語整理及眾多影視戲劇改編等多媒介傳承與傳播景觀。已發現的《阿詩瑪》彝語本就有20多個版本,后來經過整理出版了現代漢語版《阿詩瑪——撒尼人敘事詩》。《阿詩瑪》長詩一共分為13節,通過敘述主人公阿詩瑪、阿黑等人的遭遇,歌頌了勞動人民的勇敢和智慧,批判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殘暴和冷酷。《阿詩瑪》至今仍保持多樣式的口頭演述形式,已被列為國家級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是唯一入選《中國百年百部經典文學作品》的民族民間文學作品。
《阿詩瑪》民間敘事詩具有文學人類學的文化功能和民俗意義,眾多異文本流傳進一步證明了《阿詩瑪》不是一個簡單的愛情故事。《阿詩瑪》既具有撒尼族文化表征功能,又有民俗儀式意義和世俗藝術化等多重特征。因此,敘事詩《阿詩瑪》的整理和編寫應該符合人類學詩學原則。著名作家和學者李廣田針對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的搜集整理和創作問題,提出了4條原則,既需保留原作的思想內容,又要原汁原味地呈現“民族民間創作中那些特殊的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表現手法”的個性化特征。[1]19一定意義上而言,這些原則是為了呈現民族敘事詩的文化意象與文化表征而保留文本的民俗意義的人類學翻譯操作規范,凸顯了早期民族志翻譯的人類學詩學翻譯特征和要求,是學界對少數民族文學與文化文本整理、翻譯和出版的可貴學理追求,今天看來依然意義重大。然而,要完全實現這幾條原則是十分困難的。
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民族文學界整理并翻譯成漢語以來,《阿詩瑪》現代版已被改編成多種藝術形式并被翻譯為英語、俄語和日語流傳世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1957年,英籍翻譯家戴乃迭(Gladys Yang,1919—1999)的《阿詩瑪》英文全譯本出版,至此《阿詩瑪》真正走向世界。1981年,戴乃迭根據《阿詩瑪》國內整理、修訂情況,重新修訂了英譯本。《阿詩瑪》英譯本是我國較早出現的少數民族典籍外譯本。[2]
戴乃迭英譯《阿詩瑪》,使其脫離了原生態封閉的民間口頭敘事演唱形式,走向開放、動態的世界,同時也激活了這個詩歌文本的有機活性,為民族文學享譽世界文壇樹立了榜樣,贏得了廣泛的國際聲譽。戴乃迭英譯本采取了獨立的文學翻譯立場,借助于有改變的英國民謠體,對漢語本進行了若干形式上的歸化處理,但在基本內容和文化因素上,有效地保留了《阿詩瑪》原貌。總體而言,這是一次成功的長篇敘事詩翻譯嘗試。戴乃迭認為英國民謠和彝族撒尼敘事詩都是口頭傳唱藝術,二者都是敘述本民族喜聞樂見、世代相傳的故事,她以經過調整的英國民謠體翻譯《阿詩瑪》,為這部詩找到了對應的最佳形式。[3]
20世紀60年代關于《阿詩瑪》漢語文本的翻譯整理和民族語言文本研究,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缺少文化人類學、文學人類學以及人類學詩學的理論指導和民族志寫作、民族志深度翻譯等方法的介入和有效運用,當然這也是受制于當時的學科發展。進一步對敘事詩漢譯、英譯及其多語種、多維度的創造性改編等作出民俗學和文化學意義上的闡釋,則構成了《阿詩瑪》后續研究的重要課題。最新的《阿詩瑪》翻譯研究成果當屬崔曉霞專著《〈阿詩瑪〉英譯研究》。該著作考察了彝族撒尼文化和《阿詩瑪》文本的形成和傳播過程,對照20世紀60年代漢譯本與基于該本的戴乃迭《阿詩瑪》英譯本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闡述了利用英國民謠體形式翻譯《阿詩瑪》體例的得與失,并對《阿詩瑪》翻譯現象進行了理論升華和思考。[4]
二、回譯之本:《阿詩瑪》人類學詩學書寫
《阿詩瑪》是云南彝族撒尼人的長篇敘事詩,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不僅受到中國各族人民的喜愛,而且先后被翻譯成英、法、德、日、俄、羅馬尼亞等國文字出版。《阿詩瑪》走向國際文壇的過程中,戴乃迭的英語翻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長期以來,《阿詩瑪》翻譯作品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研究,鮮見有對其經由漢語到英語以及反向的英語再到漢語翻譯現象的雙向闡發。
《〈阿詩瑪〉英譯與回譯:一個人類學詩學的回譯個案》是王宏印“創作型回譯”的第一項完整成果,是民族史詩和長篇敘事詩《阿詩瑪》翻譯研究領域的重要成果。王宏印在該著作中對回譯理論、回譯定義、分類與功能進行了介紹,而對戴乃迭《阿詩瑪》的回譯實踐是國內第一個民族文學作品外語本回譯的漢語范本。該著作包括上編和下編兩部分。上編是傳說與傳承,重新追溯彝族撒尼人的歷史文化和習俗文化。內容包括三章:第一章是對阿詩瑪民間傳說的介紹、彝語版本的搜集整理以及現代民歌體版本的呈現;第二章是對戴乃迭《阿詩瑪》英譯本及其副文本的研究;第三章是戴譯《阿詩瑪》的回譯,分別介紹了回譯的分類與功能、《阿詩瑪》回譯本的語言表現、價值和局限性。下編是文本與翻譯,包括《阿詩瑪》漢語回譯本和對《阿詩瑪》多語翻譯與多媒體傳播的討論。戴乃迭英譯《阿詩瑪》的全文回譯,是王宏印完成的第一部回譯作品,也是“創作型回譯”的典型文本,是他對回譯理論研究的創新發展和實踐體驗,因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文學創作意義。
《阿詩瑪》英譯與回譯重新闡釋了彝族撒尼人的歷史文化和習俗文化,進而說明了一個完整“回譯”本對撒尼民間文學和漢族文學可能產生的互文影響。無論是對典籍翻譯研究領域的拓展,還是彝族撒尼文化的弘揚,該著作都是功不可沒的。因此,從“創作型回譯”出發,將《阿詩瑪》回譯本與原作漢語本進行對比,從回譯本語言表現來挖掘譯者是如何再創作譯本以及回譯本自身存在的價值,就顯得尤為重要。限于篇幅,僅舉原詩《馬鈴響來玉鳥叫》一章中原詩、英譯文和回譯進行比照,詳見下例。
《阿詩瑪》原詩、英譯、回譯比照
原文(三處均一樣)
玉鳥天上叫,
太陽當空照,
阿黑滿身大汗,
急追猛趕好心焦。[1]64英譯(三處均一樣)
The jade-white bird is crying still,
The sun shines in thesky;
His body dripping sweat,Ahei,
Comes riding madlyby.[2]50
回譯一
玉鳥喳喳叫,
太陽當頭照。
阿黑滿身汗淋漓,
急急地追上來了。[5]140回譯二、三
玉鳥天上叫,
太陽當頭照。
阿黑滿身汗淋淋,
一路催馬向前進。[5]142
關于玉鳥叫這節小詩,在原文中重復出現三次,英譯也重復三次,沒有變化。但是在回譯中第二、三次和第一次有所不同。第一次回譯為“阿黑滿身汗淋漓,急急地追上來了”,第二、三次改為了“阿黑滿身汗淋淋,一路催馬向前進”。原詩中“玉鳥”襯托阿黑縱馬追趕,既吉祥又動態,“叫、照、焦”均押韻。英譯中運用民謠體“sky”和“by”押韻。回譯一中“玉鳥喳喳叫,太陽當頭照”,是為了和后面“急急地追上來了”相聯系,突出的是追上來的開端動作,此處“淋漓”和“急急”頂針押韻,“叫、照、了”均押尾韻。而第二次和后續出現的時候,便是比較平穩的“一路催馬向前進”,此處“叫、照”押尾韻,且“汗淋淋”和“向前進”押韻。毋庸置疑,王宏印在進行創作型回譯時是通過語詞置換、使用修辭技巧等策略重新創作《阿詩瑪》,重新追溯撒尼歷史文化。一定意義上而言,從現代漢語本到戴乃迭英譯本到回譯本,讓我們得以回顧和觀照自己的傳統,管窺民族敘事詩在英語文學世界里會有什么樣的景觀。下文將敘述的重點置于王宏印對戴乃迭《阿詩瑪》英文“創作型回譯”的評介,以期推動對回譯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
三、回譯之創:回譯研究新境界
“回譯”,顧名思義,指將譯為其他語言的文本再譯回源語言文本。回譯現象在中國翻譯史上自古有之,最早可追溯至唐玄奘回譯印度佛教哲理著作《大乘起信論》。然而,對于回譯的重視卻遠遠不夠。回譯被視為翻譯技能訓練而未得到應有的學術關照,國內有關回譯的真正研究要晚至21世紀初。回譯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前一翻譯過程的回逆,同一般的翻譯過程相比較,回譯的自由度相對較小,譯文具有明確的規定性,排斥描述性,表現形式也傾向于原封不動的“還原”。
(一)回譯研究之話語嬗變
回譯概念的模糊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回譯研究的發展。而令人欣慰的是,回譯文本作為翻譯實踐中的一種文本類型,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回譯研究最早見于英國翻譯理論家紐馬克編著的《翻譯教程》,其中有一章專門論述了回譯問題,紐馬克認為,回譯的一種基本功能,就是為了檢驗譯文的質量。[6]Shuttle Worth和Cowie在《翻譯研究詞典》中,認為回譯是“將翻譯成指定語言的文本重新譯回源語的過程”。[7]馮慶華指出,“回譯是一種翻譯,它的源文本是另一種目標文本。”[8]方夢之認為“把譯寫成另外一種文字的內容再轉譯成原文的表達”[9],強調經過回譯的成品。
回譯基本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陳志杰和潘華凌從翻譯與文化關系出發,對回譯重新進行了定義:“回譯是指通過回溯擬譯文本與目的語文本間內在的語言和文化聯系,把擬譯文本中源自目的語的語言文化素材或文本重新譯回源語的翻譯活動。”[10]將文化因素納入到了回譯研究范疇。梁志芳將回譯稱為“跨國文學作品或跨文化文學作品”,即“將用A國語言創作的有關B國文化的作品翻譯為B國語言”。[11]聶家偉將回譯稱為“文本語言的復歸”,狹義回譯是“A文本—B文本—A文本”的過程,廣義回譯是“A文化—B文化—A文化”的過程。[12]不難發現,現有研究基本是圍繞回譯現象、回譯界定和類別展開,沒有突破回譯的質性研究和文化功能闡釋。
(二)創作型回譯之新境界
王宏印把檢驗譯文質量的回譯稱為“檢驗型回譯”(back translation for testing)。他認為,回譯不僅是為了檢驗翻譯的質量,甚至不能檢驗翻譯質量,因為回譯本身是有問題的翻譯行為。[5]后來根據自己的翻譯經驗以及對回譯的理論思考,他在《關于回譯與其他》一文中提出一種新的回譯類型“研究型回譯”(back translation for research),該文收錄于《“紅樓夢”詩詞曲賦英譯比較研究》一書中。在這篇文章中,王宏印提出文學作品中的回譯不可能完全回到原文,也不可能完全體現譯文,只能是在中間的一個什么位置上,既像原文,也像譯文,也就是說,回譯本是一種雜合的文體。[13]此后,王宏印把回譯作為一種研究手段,經常運用于翻譯研究中。逐漸地,他覺得回譯作品自身有獨立的文學價值或文獻價值,應當作為一種類型而得到保存或研究,于是提出了“創作型回譯”(back translation for creation)的概念。早在研究林語堂的《京華煙云》時,王宏印就提出“無根回譯”或“無本回譯”,是對回譯種類的推進和精細研究。2015年他在《上海翻譯》發表《從“異語寫作”到“無本回譯”——關于創作與翻譯的理論思考》一文,對回譯現象做進一步理論探索,提出了“無本回譯”的概念。[14]這次對《阿詩瑪》的回譯則是對其翻譯研究思路進行拓展的一次身體力行的實踐行為。這一點正如王宏印為《〈阿詩瑪〉英譯研究》所作的序中指出:
就我的認識而言,現在的翻譯,應當以人類學詩學為學科基礎,吸收民族志寫作的方法,借鑒韋努蒂異化翻譯的基本策略,注意彝語和漢語的比較和溝通,實現有效的翻譯詩學的語言轉換,達到較為理想的翻譯目的。[4]7
在《〈阿詩瑪〉英譯與回譯》中,王宏印立足于彝族撒尼文化,又兼顧阿詩瑪的文化形象,既深入《阿詩瑪》英譯本作細致的賞析,又跳出文本作整體對比分析,這種既見樹木又見森林的闡釋、比較、賞析,帶領讀者徜徉在民族詩歌美的境界中,顯示出王宏印扎實的文學修養和理論功底。王宏印在論著中常常對回譯和原文進行比較,目的在于使回譯文本的闡釋清晰而簡練、生動且形象,避免帶給讀者晦澀枯燥的閱讀感受。
在《阿詩瑪》回譯本中,王宏印結合彝語、英語、漢語三種語言的特點,進行了創作型回譯實踐,旨在使回譯本既注重詩歌對音樂美、韻律美、形式美的審美要求,又兼顧傳達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中包含的民族特色文化,再現阿詩瑪這一美麗的形象。王宏印回譯本價值在以下幾個方面是不言而喻的:第一,這部民族史詩有了五言、七言、雜言等不同的句長,也有漢語詩的流水對和英語詩常用的折行,從而帶來了豐富的詩歌呈現效果;第二,回譯本相比原文有些地方有了明顯改進,在一些著力不夠的地方,英譯者有意識地進行了變化,以求最佳的翻譯效果,回譯本在文字表達手法上也積極汲取英譯本的長處;第三,回譯本巧妙地將戴譯本的創造性翻譯成果體現出來,把英譯本中對意象的保留和邏輯的規整化處理都體現了出來,和原文相比更加合理;第四,回譯本還將撒尼文學和漢族優秀文學有機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新的語言風格和文本類型;第五,回譯本積極吸收原詩和英譯詩的長處,構建了一個理想的再造文本,成為原文和英譯本折中的產物,達到詩歌的最佳表現;第六,為《阿詩瑪》多模態傳播提供了參考,為我國其他民族詩歌的回譯提供了典范。
王宏印創作型回譯本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翻譯事件,其重要意義的闡發目前還不能完全窮盡,但回譯受制于英譯也是顯而易見的。按照嚴格的回譯規則,英譯無法顯示的地方,回譯也無能為力。因此,根據英譯本創作的回譯本,本身由于中西文化的差異,在兩次翻譯過程中會與原作有差異,導致了回譯本也不會嚴絲合縫、無懈可擊。那么,一個必然的改變和必要的提升就是走向創作以及再創作。翻譯從創作開始,經過不同的翻譯層次,又回到了創作,正可謂“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四、回譯之旨:民族文化雙向呈現
優秀的翻譯著作應達到翻譯與研究的完美結合。回譯的核心宗旨在于,如何將外語文本中描寫的中國文化形象通過回譯,在中國讀者心中還原或建構為符合中國歷史、社會和文化語境的形象,達到民族文化在譯入語和源語語境中的雙向呈現。目前翻譯研究領域中,國內各語言間的“內譯”研究,以及響應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將中國形象翻譯成外文的研究都成果豐碩,而反觀將以外國視角和外文創作的有關中國形象的敘事回歸中國文化的回譯,研究卻不夠充足。
王宏印的回譯比較研究,旨在推動民族文學通過雙向呈現,進入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之林,最終進入到國際文學人類學視閾。通過文本研究、比較研究的多重維度闡發,為類似《阿詩瑪》少數民族敘事詩的研究提供一個努力方向和可行途徑。回譯本質上是一種符號媒介和文化記憶雙重轉換的過程,民族典籍回譯則是以譯文為對象的逆向翻譯過程。回譯研究要突破對譯文的糾錯和翻譯標準的討論層面,譯文的學術性、準確性、可追溯性和注釋性固然是一個重要的維度,而民族文化的雙向呈現更應得到相應的學術觀照。
“創作型回譯”是為了創作目的而進行的回譯。“創作型回譯”不僅僅是從原文到譯文,再從譯文到原文的簡單一次性工作。一個文本在翻譯進入目的語文本后,在滲透、吸收、利用后又可能重新翻譯回源語文化,并對源語文化產生影響。“創作型回譯”并不是簡單地把一個文本譯成另一種語言就了事,而是一個有著明確創作目的的活動。所以,王宏印在努力重構出原文文本產生時的歷史語境,力圖使原文本產生的社會文化語境呈現在讀者面前,以幫助讀者更深入地理解撒尼文化,讓讀者感受到原詩和英語世界中關于撒尼文化、婚俗習慣以及人物原型等更深刻的內涵,使民族文化得以雙向呈現。“創作型回譯”是創作和再創作的過程,《阿詩瑪》通過回譯,經過一個循環,使得原始古老的彝族撒尼文化呈現在雙語讀者面前,完成了對撒尼文化的雙向呈現。
縱觀王宏印回譯《阿詩瑪》敘事長詩,是創作型回譯的典范和代表,對其展開的翻譯研究不僅僅屬于文學之間相互影響和交流的問題,而且還涉及文化交流的問題。回譯本中譯者再創造和再現原作的技巧、風格以及整體思維的意合性和深層的邏輯性,是無可比擬的。根據戴譯本,我們得以了解英語世界的阿詩瑪是什么樣的。回譯本將英譯本與彝族撒尼敘事詩傳統相結合,既順應了讀者的接受能力和閱讀習慣,又保全了《阿詩瑪》民族文化本質,這都體現了王宏印對原作的深度把握及其深厚的文化修養、詩歌藝術鑒賞力和審美能力,成功地向讀者傳達出《阿詩瑪》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和斗爭意義,將彝族撒尼文化中所特有的阿詩瑪形象展現出來,為讀者送去了濃厚的異域風情和彝族撒尼民族特色。
五、結語
“創作型回譯”是譯出語文本到譯入語文本的雙向轉換。王宏印先深入研究《阿詩瑪》,搜集彝漢各種版本,然后根據對原文和戴譯本充分地理解,按照詩歌翻譯需要,選擇恰當的詩歌形式加以重新表達,創作出一部完整的《阿詩瑪》回譯本。“入乎其內”之后,則“出乎其外”,即譯者將原詩的內涵進行恰當的表述,再創造出概括性、理想性的藝術意象。王宏印對《阿詩瑪》英譯本的回譯,可以作為一個文學作品回譯的典范,為民族典籍回譯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基于此形成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有助于推進基于典籍翻譯之回譯話語體系的形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雙向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從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