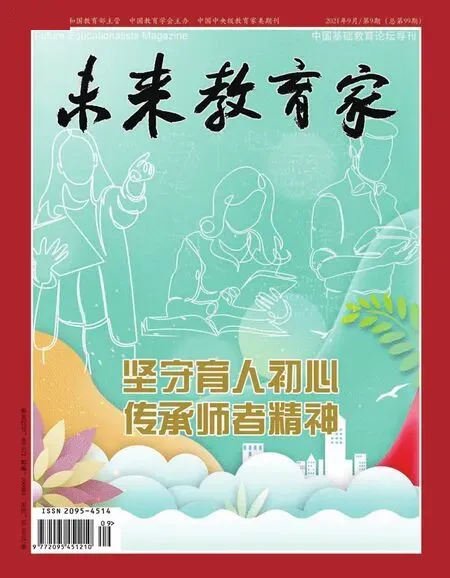于漪教育教學思想的當下意義
蘭保民/上海市浦東教育發展研究院教師發展中心副主任
“人民教育家”于漪的教育教學思想十分豐富,這些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在這里我只能管窺蠡測,從對四組關系的思考和把握來談談我的粗淺理解。
學科教學與立德樹人
進入新世紀以來,于漪將很多精力放在了“學科育人”的工作中,因為她認識到,教育事關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是為學生“樹根立魂”的事業。為此,在“兩綱教育”(2005年3月14日,上海市科教黨委和市教委聯合頒布《上海市學生民族精神教育指導綱要》和《上海市中小學生生命教育指導綱要》,簡稱“兩綱”)推進過程中,她是號角、是旗幟;從2008年起,她不顧耄耋高齡,連續主持了三屆“上海市語文學科德育實訓基地”的工作,為各區縣培養了100多名學科德育骨干教師。
于漪畢業于復旦大學教育系,她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敏銳地認識到,我國從近現代延續至今的學科課程設計,基本上是向西方學習的產物,這當然有其積極意義,但是由于各學科有其獨立的話語體系、知識結構,在實踐中一旦陷入學科本位而非學習者本位的誤區,就會帶來弊端,那就是過于重視學科知識的傳授,而忽視每個學科自身所蘊含的豐富而又獨特的育人價值,從而形成“智育”與“德育”兩相分離的狀態。因此,她旗幟鮮明地指出:課堂是落實德育的主陣地,學科教學是落實德育的主渠道。為此,她從實踐探索與理論建構兩個層面發力,努力實現語文課程的“德智融合”。在理論建樹上,她1964年的《胸中有書,目中有人》《把語文課上得樸素一些,實惠一些》、1979年的《既教文,又育人》、1989年的《立體化與多功能》、1995年的《弘揚人文,改革弊端》,都體現了她學科教學與學科育人相融合的“德智融合”的思想。在實踐探索中,她強調語文課要立體化施教,多功能育人,追求“大象無形”的教學風格,讓每堂課的每一個教學環節都具有多功能的育人價值。
于漪“德智融合”的教育教學思想,在課程改革不斷深化的當前背景下,對于如何貫徹落實教育的“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如何在核心素養視野下充分彰顯各類課程的學科育人價值,具有極其深遠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她的許多教育教學思想,如“營造生命涌動的課堂”“語文教育是民族文化之根的教育”“語言和思維融合發展”“在美的熏陶感染中塑造心靈”等,對于當前語文教師正普遍感到困惑的“語文學科核心素養如何落地”的問題,不僅具有價值引領的意義,而且具有極其豐富的方法論意義。
問題意識與學行建設
于漪曾經說:“在教學的過程中,我腦子里總是不斷地有新問題,正是這些問題,讓我在教育教學之路上不斷探索前行。”回顧于漪的教育教學思想發展軌跡和實踐探索之路,我們會發現,她有一條非常清晰的、不斷演進的路線,而這條演進路線背后的一個推動力,就是她的問題意識。
這正是于漪的可貴之處,她決不將自己定位在批判者的角色上,她絕不把自己置身于教育發展的滾滾洪流之外,而全身心地把自己投入進去,從學術思考與行動探索兩端發力,尋求解決問題的路徑。以語文學科為例,20世紀70年代末,針對語文學科教學去思想化的現狀,她提出“既教文,又育人”;80年代,針對語文教學過于強調文章學、語言學、文學等靜態知識而忽視學生思維訓練的情況,她提出“語文教學應以語言和思維訓練為核心”的語文教學觀;90年代,針對語文學科片面強調工具屬性而忽視其人文屬性的思潮,她通過深入研究,撰寫《弘揚人文,改革弊端》等一系列文章,鮮明地提出語文課程“工具性與人文性相統一”的觀點,推動“人文性”寫進語文課程標準;到新世紀,針對片面追求升學率的“育分不育人”的情況,她出版了《教育的姿態》一書;針對一些唯西方話語馬首是瞻的教育不自信言論,她也撰寫了大量文章,疾聲呼吁“以教育的自信創建自信的教育”。

2014年,蘭保民與恩師于漪參加上海市人民政府慶祝教師節座談會后留影
于漪的這種基于問題意識而致力于學行建設的教育者姿態,在當前同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習總書記說:“空談誤國,實干興邦。”教育是一個不斷追求理想境界的事業,是永遠追求完美的事業,但它的發展,注定也是一條永遠綿延不盡的“光榮的荊棘路”,如果只是批判,只是抱怨,只滿足于當教育教學領域里的“憤青”和“噴子”,這也瞧不起,那也看不慣,卻不愿去做踏踏實實的建設工作,恐怕對于教育的發展而言并無實際意義。真正有意義的是,在認清方向的基礎上,披荊斬棘,走出一條路來,這樣才能不斷前行。
民族立場與世界視野
2017年1月,于漪在《人民教育》雜志發表了一篇長文《以教育自信創建自信的教育》,明確提出了“教育自信”的命題,引起了國家領導部門的充分重視,這是“四個自信”在教育領域的思想回聲,也是當下教育領域的黃鐘大呂。
我們知道,民族主義與全球主義是當今的兩大思潮,也是教育界的兩個很重要的思想表征。特別是全球主義,在我國當下的教育界——尤其是基礎教育界影響甚劇,有個別的研究者和一線教師,有意無意地以效仿西方為時尚,仿佛一談傳統就是落后,一談民族就是保守。
于漪的“教育自信”思想,彰顯了作為一名中國教師旗幟鮮明的國家民族立場。她始終站在國家與民族發展的立場上,牢記母校鎮江中學那句“一切為民族”的校訓,她的“明燈陪我過半夜”的孜孜矻矻的敬業精神,她的“站上講臺,就是用生命在歌唱”的忘我精神,她的“讓生命與使命結伴同行”的使命精神,她的“教師責任大如天,一頭挑著學生的未來,一頭挑著祖國的明天”的責任意識,她的“一輩子做教師,一輩子學做教師”的進取精神等,都是源于為國家的強大、民族的復興的偉大使命。這在別人看來可能有喊口號的嫌疑,但在于漪那里,卻是扎扎實實、令人信服的課堂教學、學校辦學、教師培養、教育建言、著書立說的實踐文本。
但是,于漪同時又具有非常開闊的世界視野。一方面,她對教育目標的思考,是放在當下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競爭、交流、碰撞的世界格局中來展開。因此,對“我們的教育究竟應該培養怎樣的人”這一問題,她的回答擲地有聲:“培養有一顆中國心的現代文明人。”另一方面,對于世界上從蘇格拉底、柏拉圖,到赫爾巴特、布魯姆,乃至日本的佐藤學等各個國家、不同流派的教育教學思想,她都有深刻的理解,因此,在“怎樣培養人”的思考上,她又廣收博取,并進行實踐性的轉化。這種轉化,不是在名詞術語上標新立異,而是著力于“中國本土教育學”的創建。她曾多次語重心長地說:“我一直有一個夢想,就是要創建中國的現代教師學,創建我們中國本土的教育學。”
在如何處理“民族”與“世界”的關系上,于漪就像一棵大樹,她將根系牢牢地深扎在國家和民族的沃土里,而她的枝葉同時又時刻感受著世界的風云。于漪教育教學思想體現了“變”與“不變”的辯證法,她的“變”,是源于現實思考而貢獻出的理論資源和實踐智慧,因此她的教育教學思想永遠是與時俱進的;而她不變的永遠是前進的方向,具體來說,就是對中國這片土地上的基礎教育和學科教學的本質的理解、目標的理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她既是“堅守者”,又是“超越者”。或者也可以說,正因“堅守”,所以“超越”。
仰望星空與腳踏實地
于漪的身體一直不是很好,只要讀過她的《歲月如歌》這本書的老師都知道,她年輕時就得過兩次重病,忍受了常人未曾經歷的病痛的折磨,再到后來,心臟、血壓、肺功能、腎功能都出現問題,還曾經因為心臟病而被送進重癥監護室。但是,人們在講臺上看到的,永遠是精神飽滿、激情洋溢的于漪形象,神采總是那么意氣飛揚,思路總是那么敏捷順暢,語言總是那么富有吸引力。卻很少有人知道,當走下講臺,回到家后,于漪總是要大把大把地吃藥。她的確是一位“用生命在歌唱”的“人民教育家”。
于漪經常說:“教師,就是用生命在歌唱。”她還說:“我們教師,不僅要腳踏實地唱人歌,還要仰望星空奏神曲。”
就我體會,“用生命”這三個字是很有力量的,因為它詮釋了一名“草根教師”究竟應該怎樣“腳踏實地唱人歌”。于漪經常引用當代作家汪曾祺的一句話:“人總要把自己生命的精華都調動出來,傾力一搏,像干將、莫邪一樣,把自己煉進自己的劍里,這,才叫活著。”于漪就是把自己生命的精華全都調動起來,在講臺上用生命傾力相搏的,正因如此,張志公先生才深有感觸地說:“于漪教書簡直著了魔!”
“歌唱”,既是于漪對生命、對教育的一種審美定位,又是于漪教育教學思想的隱喻性表達。教育不只是簡單地傳授知識,而是生命境界的提升。因此,教育一定是美的,是能夠令人感動的,這大概也是很多對于漪不太了解的人給她貼上“情感派”標簽的原因吧。
于漪“用生命歌唱”的姿態,就是“腳踏實地”與“仰望星空”的融合,她認識到了教師這份工作對于國家發展與民族振興的重要意義,并用生命來歌唱、來踐行,她這位“草根教師”就成為了“人民教育家”。由此我們不難認識到,教師的確是一個很平凡的崗位,我們在這個崗位上當然要腳踏實地地上好每一堂課,做好每一件事;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我們所做的每一項工作,哪怕再細微、再渺小,都事關學生的未來,都事關祖國的明天,必須有教育意義,必須合乎教育的方向。所以,我們不僅要做腳踏實地的實干家,同時還必須是仰望星空的探路者,這樣才能保證我們所做的辛苦的工作,不至于迷失了教育的方向,違背了教育的規律,背離了教書育人的初心。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從哲學的高度論述了“一個人的覺解程度對于他所做之事的重要意義”,于漪也反復呼吁:“生命賦予了我們一種責任,就是精神的覺醒與成長。”他們都強調“精神覺醒”的重要意義,道理就在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