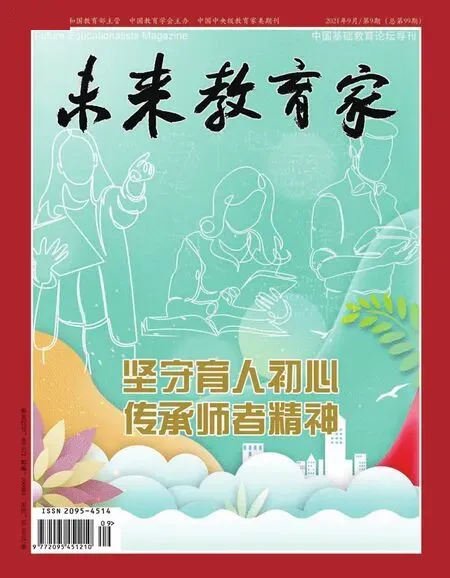記我的老師劉安林先生
陳娟/山東省臨沂市臨沂第三十九中學教師

劉安林
我的啟蒙老師叫劉安林。
劉老師是個殘疾人,他沒有右手。至于為何失去右手,老師諱莫如深,從不曾提及,我們也尊重他的隱私權,從不多問。但是,在我以及我的村人們的印象中,老師卻是一個完美的人,是值得崇拜和敬仰的人。在我們的心目中,最好的老師的樣子,就是他的樣子;最好的字也就是他寫的字——他用左手寫出的字,橫都是用手腕推出去,蒼勁有力,有如刀削。
可以想象,對于沒有右手的老師,竟寫得一手好字:粉筆字、鋼筆字、毛筆字,是何等不易!老師的板書、老師的作業批語,以及我們村每家每戶的大門上他寫的對聯,都是我們偷偷模仿的對象。劉老師就是一個“活樣板”,他給我們村的每個孩子埋下了苦練三筆字的種子。我們村的每個孩子能寫出一手挺拔有力的字,劉老師功不可沒。我哥、我姐都寫得一手好字,雄渾飄逸。我的字也充滿了剛性,風骨凜然,當然也是他指點的碩果。
讓我意想不到的是,沒有右手的老師,竟然會拉二胡!如果不是親眼所見,你一定覺得這是天方夜譚吧?但,拉二胡算什么!我老師吹、拉、彈、唱樣樣精通。我老師的唱功也很棒,當年曾經是鄉宣傳隊的頂梁柱,據說他曾一夜記住了整本詞譜!曾想我的老師,如果妝扮成楊子榮的樣子,右手叉腰,左手做戲,一定是器宇軒昂、威風凜凜。據說就是在鄉宣傳隊里,老師遇見了溫柔善良的師母,并成就了一段轟轟烈烈的愛情。四肢健全的師母要嫁給一個殘疾男人,當時引起了家人的巨大不滿,受到了父母的強烈反對。但愛意已決,我老師便帶著師母輾轉到我們村安營扎寨,安心做起了我們村的啟蒙教育。
曾經是樣板戲臺柱子的劉老師,自然不會讓我們的音樂課形同虛設。至今我還記得老師教我們唱歌的情形,課本上的唱遍了,就教經典傳唱歌曲,比如《送別》《送戰友》,他都教我們習唱。老師還教我們樂理知識,合唱分聲部等,在四十多年前的偏僻小村里,能有如此水準的老師,我們真是太幸運了!
老師的美術設計能力也不同凡響,他揚起左手,呼啦一陣子就能在黑板上勾畫出一些圖形,畫狗是狗,畫貓是貓,惟妙惟肖!有一次,老師在我的美術本上三五下畫出一只蝴蝶,真是像極了,我凝視著撲面而來的蝴蝶,竟然欣喜地張開小手去撲打它……惹得老師哈哈大笑。這竟成了我記憶里珍貴的保藏,時至今日我還因此保有那份對蝴蝶的喜愛情結。兒時的記憶會影響一生,直到現在,我還清晰地記得我們教室的板報欄上“可喜的進步”幾個大字。那個“喜”字的“口”都是笑咧著嘴的美術體,結構安排得是那樣合理,上下錯落,總之,太好看、太喜人了,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們還有實踐課。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老師帶我們去學校西面的空地里種蓖麻的情景,每人分幾粒種子,各自挖坑種上,然后澆水。還記得蓖麻后來長得很高,葉子像是楓樹的葉子,但已記不清后來是否收獲了。但那已經不重要,戶外活動給我們帶來的樂趣,勞動實踐給我們帶來的成長,才是最重要的。



劉安林老師的作品
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們學校也有震感,在那些家家門口倒豎著瓶子防震的日子里,我們的課卻沒有停下,老師帶著我們到長滿蘆葦的地方,把小黑板掛在樹上,給我們上課。一下課,我們便去采蘆葦葉編小鞋子,剝了蘆葦尖做聲音細細的小哨子,疊蘆葦船,沿河漂流,追著看能漂到什么地方……傍晚時分,還會在荊條梢上捉蜻蜓,蘆葦叢中有一種特別的蜻蜓,個頭比常見的蒼黃色的蜻蜓小,翅膀泛著寶藍色的光,飛得很快,轉眼便不見了,但總能又看見,卻始終捉不住。
去年見到劉老師時,他還說:“那時候,一個小村子三個老師都包班,開齊開全所有的課程,每個人都是全科、全能教師,而且教學質量還是全鄉鎮首屈一指的,那真是難能可貴。”
初中,我去區里讀書,巧的是,那就是我老師的老家,離我們村子有十里路。在隨后的不久,老師也離開了我們村子,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教書了。后來,我考上師范離開鄉村,我老師又到了中心中學任教,他的學校離自己家也有十幾里路,來回一定很不方便。可以想象,當遇到下雪、下雨的惡劣天氣時,老師一只手騎車往返一定很艱難。
一個曾與劉老師相伴過的朋友談到劉老師的時候,他說:“你老師對待工作特別認真,不管下雨還是下雪都風雨無阻,上課前一定會站在教室門口,不耽誤學生一節課。”我聽了覺得心酸,腦海中立刻浮現老師被風吹倒地、雨中腳滑、冒風浴雪艱難前行的身影……
從小學畢業到2020年,我與老師闊別已經四十多年了,雖然心里想念,卻沒能再見老師一面。想念老師的時候也會想:老師還記得小時候那個扎著三個小辮,胖胖的小女孩嗎?我小時候的成績算不上最優秀,平時寡言少語,他一定不會記得我了吧?
不知道老師還記不記得那次罰我?那是一次上數學課,老師讓做完作業的同學直接交由他當面批改,我的同桌“四哥”抄了我的作業,然后先交上去了,遺憾的是我做錯了,同桌也抄錯了,可偏偏我倆錯得一樣,而且是他先交上去,于是老師就認定是我抄他的作業。
但這不是事實,所以老師問我的時候我堅決否認,一口咬定是他抄我的。那時候覺得“抄”是一個極其羞辱的字眼,做錯了題事小,抄作業事關重大,因此打死也不會承認。當時鬧得動靜不小,加上我小時候的外號叫“慣鼻子”,超愛哭。于是,后來我便被請出門外,在大太陽下罰站,邊曬邊哭……
直到現在,我仍記得那天的陽光特別晃眼,我在大太陽下站了很久很久。直到中午放學,老師說,只要承認錯誤就讓我進屋、讓我回家,可我偏不。于是,我一直餓著肚子在大太陽下站著,一邊流汗、一邊抹眼淚。后來,我媽去找我,說我像個大花貓,把我領回了家,但我始終沒有承認抄作業的事。多年后的現在,每逢我回老家的時候,常常會看到抄我作業的同桌“四哥”,他還是小個子,只是頭頂變成了“地中海”,想必他也一定會記得那件事吧!
抄襲事件給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創傷,老師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大打折扣,那時我想,我離開他之后,一輩子也不想再看到他,讓他后悔一輩子。
但是,后來發生了一件事,讓我的心思全然改變。
我初中畢業沒考上學,面臨復讀和去村里當幼教老師的選擇,這時候,我的老師來了,勸導我媽讓我繼續上學。他說的其中一句話我至今還記得:“你們家這個孩子聰明伶俐啊,不上學可惜了!”
老師的一句話再次成全了我的學業。后來,我考進了師范,成了村子里第一個“吃國庫糧食”的人。我高興極了。
后來,我常常想,如果我的老師不來勸導我媽,我無法再讀書,現在的我會是一種什么樣的生活狀態?毋庸置疑,我不可能擁有現在這份讓我喜歡的工作,也不會取得現在這些小小的成果,是劉老師在人生的關鍵點上,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他就是我人生中的重要他人,我自當銘記終生!
這份感激我默默地藏在心底,也常想去拜見像親人般的劉老師,但礙于失聯數十年,音信難尋,因此每每落空。直到去年的一天,偶然間聯系上了我的小學同班同學——劉老師的兒子,我拜見老師的夙愿才得以實現。
這個世界太大了,這個世界太小了!原來,我朝思暮想的劉老師,就與我住在同一座城市的不遠處。這么多年,我竟然沒有碰到過他一次……
那天,我終于見到了劉老師——在他簡樸的家里。劉老師頭發已經花白,臉上已是溝壑縱橫,他的手——那只神奇的左手,瘦了……瘦骨嶙嶙,如同枯枝一般,但卻依舊靈便,手指微微顫動,翕張有致,似乎在撫琴,又似乎在懸腕書寫……劉老師的記憶力好得驚人,他很快想起了我,記起了我的父親和母親、大伯、大娘、哥哥、嫂嫂和我的左鄰右舍……恍然間,封存在記憶深處的那些人和事立刻活了過來,如此親切、如此清晰……我的父母,也儼然站在我的面前,沖我微笑。那短短的幾個小時,多年來我一直不敢觸碰的痛竟成了我喚醒過往的暖。我這才發現,我的童年、我的村莊、我的父母、我的鄉鄰,并沒有全然消逝,竟然都鐫刻在老師的記憶里。
這讓我突然發現自己對老師的了解很粗淺。沒有想到的是,我的老師還對詩詞歌賦有很高的造詣,而我才剛剛認識到。那天,老師給我看了他的《休閑集》。這是他老人家2004年退休后積累的自寫集。仔細拜讀,簡直瞠目結舌。
光是第一本“詩詞歌行”就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詩詞歌行”里,五言詩占大多數,內容涉及家國情懷和對自我感情的抒發;辭賦寫得也是風生水起,浣溪沙、滿江紅、菩薩蠻……竟然還有藏頭詩、回文詩……
第二本是“曲藝類”,有快板、山東快書、對口快板、戲曲、小品……內容豐富多彩,可排性極強,拿來就可用,聽說當地鄉間小劇團就以此為演出藍本,豐富著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更多的驚喜是老師自撰的對聯,喜聯、挽聯、春聯,特別是春聯,什么豬鼠交替、鼠牛交替、牛虎交替、虎兔交替、兔龍交替……每一個交替都創作出十幾聯,想來這么多年老師也是一直為眾人撰寫對聯的高手。
不僅如此,老師竟然還會作詞譜曲,他寫了厚厚一摞的歌曲集,讓我幫忙請我們學校音樂組的老師替他修改。但是,老師不知道的是,即便是專業出身,現在的年輕教師也鮮有幾個能夠作詞、譜曲。他們那一代人的文學修養、才藝功底,已是我們不能望其項背的。而我這個學生,更是連他的九牛一毛都不如,老師他老人家單用左手,不用打格子,就可以在墻上書寫幾米高的大字,而我,因為習慣電腦打字,偶爾寫備課教案,字寫得歪七扭八,難以示人。
有您這樣的老師,何其幸運!您才是我們大寫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