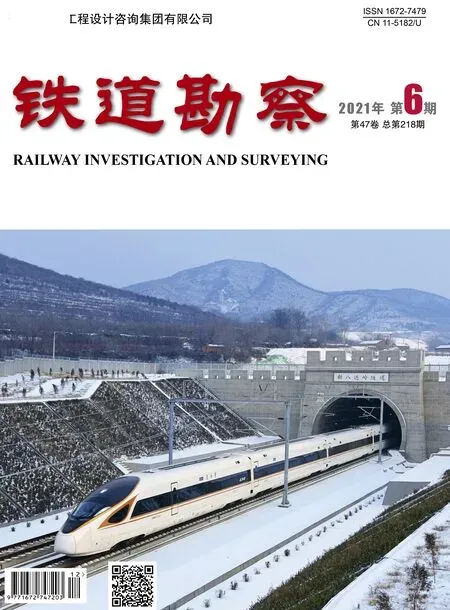上覆路塹開挖對既有下臥大斷面隧道影響研究
王德偉
(廈門路橋工程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廈門 361026)
隨著我國交通運輸事業的高速發展,受地形、地物和地質條件等因素限制,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新建路塹上跨既有公路隧道的現象。當路塹土方開挖卸載后,由于隧道上方的荷載減小,原來的土體平衡將被打破,可能出現土體隆起現象[1]。國內外已有學者對此問題展開探討和分析。王衛東等結合實際工程案例進行數值分析,認為由于地鐵隧道上方土體卸載,將會產生明顯豎向上抬現象[2];張玉成等采用數值方法,研究某營運地鐵隧道上方基坑開挖對隧道變形和應力的影響,發現基坑下土體具有垂直方向卸載作用,同時隧道管片的應力狀態也有所改變[3];DOLE?ALOV等研究基坑開挖對鄰近隧道變形及受力特性的影響,并對加固方法和保護措施進行研究[4-7]。
陳郁等研究基坑開挖對下臥隧道隆起的變化規律,并通過實測進行驗證,結果表明隆起曲線接近正態分布,基坑開挖中心的隆起值明顯大于其他部位[8];劉國彬等依托上海市地鐵1號線衡山路站,研究上部土層開挖卸載對下臥隧道隆起量的計算方法,探討應力路徑與變形模量的關系[9];吉茂杰等提出基坑卸載引起下臥地鐵隧道隆起量的計算方法,并通過工程實踐驗證[10];魏綱收集國內外14個不同的基坑開挖實際案例,分析下臥隧道的變形機理,并通過現場實測進一步驗證[11];郭鵬飛等對39個基坑開挖上跨隧道工程展開了統計研究,全面總結隧道豎向最大隆起量與各影響因子的關系,認為工程地質對隧道隆起影響較大,并提出隧道最大隆起變形預測模型[12-13];葉均良以佛山某建設項目為背景,研究上部明挖隧道開挖對下臥地鐵盾構隧道上浮影響,并提出相關的控制措施[14];張鑫海等研究基坑下方盾構隧道的圍壓變化、襯砌內力以及縱橫向受力關系,并對基坑空間開挖尺寸進行影響因素分析[15]。
上述案例中,多以地鐵隧道上方開挖基坑為研究對象,而對扁平大斷面隧道上方開挖卸載問題研究較少。以下依托廈門翔安機場高速公路內厝互通工程,研究匝道路塹開挖卸荷對隧道結構受力及變形影響,分析隧道變形與卸載量的關系,并通過監測動態監控隧道的安全。
1 工程概況
翔安機場高速公路(沈海高速—翔安南路)為雙向八車道,路基寬41 m,設計速度100 km/h,新建的內厝互通B、D匝道上跨既有下沙溪隧道,存在近接施工的現象,其平面關系如圖1所示。

圖1 平面位置關系
對既有下沙溪隧道拱頂的土方進行挖方,挖方深度為0~19.1 m,該段隧道覆土厚12~31 m。挖方最深處斷面如圖2所示。

圖2 D匝道DK0+620斷面(單位:m)
既有下沙溪隧道為雙向六車道,二襯采用鋼筋混凝土結構,混凝土等級為C25,防水混凝土,抗滲等級為P8。
2 數值模型設計
2.1 模型建立
選擇挖方段研究區間,建立匝道公路DK0+540~DK0+680區間段的邊坡與隧道模型,模型匝道道路縱向尺寸(y軸方向)為140 m;為盡量削弱模型邊界效應對計算結果的影響,同時考慮計算成本和效率,沿匝道橫向總尺寸(x軸方向)也取140 m,約為隧道跨度的10倍;模型深度方向(z軸方向)自地表向下取90 m,模型底面距隧道基礎約2倍隧道跨度。該區間段邊坡開挖卸載位于下方斜交隧道的正上方,挖方邊坡高度達34 m。而下方隧道拱頂距離邊坡坡腳最小值為16.5 m。劃分網格時,在隧道、路面附近適當加密網格,共劃分114 127個實體單元,181 805個節點,如圖3所示。

圖3 數值分析網格模型
2.2 材料模型及參數
山體主要地層有強風化花崗巖、中風化花崗巖等,采用摩爾-庫倫本構模型;隧道二襯采用60 cm厚C25鋼筋混凝土;初支采用板單元模擬27 cm厚C20混凝土,板單元不占用實體網格,不考慮附加重度。護坡采用板單元模擬,等效為10 cm的混凝土。材料參數見表1、表2。

表1 土體材料模型參數

表2 結構材料模型參數
2.3 模擬計算方案
根據施工工序,對道路邊坡開挖過程進行適當簡化,分5步開挖到底。邊坡開挖前,進行山體初始地應力平衡,再進行既有隧道開挖和初期支護,然后進行二次襯砌施工。開挖邊坡前,將位移重置為零。施工模擬過程見表3。

表3 施工模擬過程
3 計算結果分析
3.1 隧道整體變形分布規律
針對最不利位置,提取隧道的變形、應力、隧道外土壓力變化,如圖4所示。

圖4 雙線隧道總位移云圖
從圖4可以看出,下沙溪隧道左洞在DK0+620附近出現最大影響區,總位移極值達7.025 mm;右洞在DK0+580位置出現最大影響區,總位移極值達4.218 mm。左洞與挖方邊坡的距離較右洞近,位移也顯著大于右洞。
3.2 隧道關鍵位置剖面變形規律
左洞DK0+620剖面變形情況如圖5所示。

圖5 左洞隧道變形規律
從圖5(a)可以看出,上方邊坡開挖完成后,既有隧道主要變形是向正上方(z軸正方向)隆起。將隧道沿底部仰拱中心點斷開,展開成直線,得到該隧道隨著開挖過程變形發展規律。不難看出,最大位移出現在拱頂附近,且開挖4級臺階時,變形增長量最大。如圖5 (b),且隨著開挖,拱頂的極值位置向(三維模型)x負方向移動,這是山體形態特征決定的。越向下開挖,邊坡開挖臺階的重心越向y負方向移動(小里程方向),這也說明隧道變形最大位置總是向著上方已經開挖土體的重心位置發生偏轉。
3.3 隧道關鍵位置剖面應力
左洞DK0+620關鍵剖面應力云圖如圖6所示。

圖6 左隧道關鍵位置剖面應力云圖
從圖6可以看出,總平均應力最大值出現在隧道側壁內側,為1 427 kN/m2(受拉);隧道頂和底部受壓,偏應力最大值也出現在側壁內側。因此,隧道上方開挖最容易受影響的位置是既有隧道側壁內側。對比第一~第三主應力變化,開挖引起第三主應力變化最大。
左洞DK0+620附近剖面應力監測點第一主應力和第三主應力曲線如圖7所示。

圖7 左洞關鍵位置剖面應力監測點曲線
圖7(a)顯示,隧道左洞頂部和底部內側第一主應力隨著開挖壓力不斷增大,增量為700 kPa左右。而隧道左、右內側壁第一主應力相對較小,且隨上方匝道邊坡開挖過程變化不大。
圖7(b)顯示,隧道左洞左、右內側壁第三主應力隨著開挖拉力不斷增大,增量為2 600 kPa左右。而隧道頂部和底部內側第三主應力較小,且隨上方匝道邊坡開挖過程變化不大。
綜上所述,上方匝道邊坡開挖引起左洞隧道側壁內側壁受拉,成為主要偏應力來源,易導致二次襯砌開裂等病害。
3.4 隧道關鍵位置剖面外土壓力
左洞DK0+620關鍵剖面外土壓力隨開挖臺階的變化如圖8所示。

圖8 左洞土壓力隨開挖變化曲線
圖8顯示,隧道外側土壓力隨著上方邊坡開挖而減小,在拱腳位置土壓力集中。開挖結束后,側壁外土壓力從500 kPa降低到279 kPa。
雙隧道受影響最大的區域,4個位置的變形與應力極值統計見表4。

表4 雙隧道變形與應力統計
從表4可以看出,左隧道變形和應力變化都顯著高于右隧道。隨著開挖,左隧道左壁外部土壓力降低,第三主應力隨之顯著增加,偏應力達到較高值。應力狀態處于拉剪不利狀態,左隧道雙側壁和右隧道左側壁需重點監測。
4 實測結果分析
4.1 監測布點
在下沙溪隧道內布設監控點,按隧道前進方向分左洞與右洞,恰好與前面數值模擬的左右洞相反,具體布設監測點如下(見圖9)。

圖9 下沙溪隧道測點布置示意
①以右洞DK0+620為中心點,間隔10 m布置1個拱頂沉降監測點,共布置11個監測點。
②以左洞DK0+539為中心點,間隔10 m布置1個拱頂沉降監測點,共布置11個監測點。
4.2 監測結果分析
圖10為下沙溪隧道左洞上方土體開挖期間(2021年5月21日至8月13日)變形-時間曲線。

圖10 下沙溪隧道沉降變形曲線
從圖10可以看出,隨著卸載量增大,隧道發生隆起,最大隆起值為6.2 mm,發生在ZK0+966處;右洞的變形更小,最大值僅為4.0 mm。總體來說,至土方開挖完,最大值不超過控制值(20 mm),故隧道變形處于可控狀態。
5 結論
利用有限元軟件構建現狀山體-隧道整體三維數值模型,研究山體開挖卸荷對隧道結構受力及變形的影響,分析隧道變形與卸載量的關系,結論如下。
(1)數值分析表明,下沙溪隧道左洞DK0+620附近出現最大影響區,總位移極值達到7.025 mm;右洞DK0+580位置出現最大影響區,總位移極值為4.218 mm。
(2)與道路開挖地表最大位移的位置距離越近,隧道變形越大;在開挖過程中,邊坡地表和隧道最大位移位置動態變化,隧道變形最大位置總是指向地表最大位移位置。
(3)數值分析表明,DK0+620剖面總平均應力最大值在隧道側壁內側1 427 kN/m2(受拉);隧道頂和底部受壓;偏應力q的最大值也出現在側壁內側,為4 007 kN/m2。上方匝道邊坡開挖過程引起左洞隧道側壁內側受拉,容易導致隧道二次襯砌的內側開裂等病害。
(4)數值分析表明,隧道外側土壓力隨上方邊坡開挖而減小,側壁外土壓力從500 kPa降為279 kPa。隨著左隧道左壁的外部土壓力降低,隧道第三主應力隨之顯著增加,偏應力達到最高值。其應力狀態處于不利的拉剪狀態。右洞在DK0+580側壁第三主應力最大值為1 300 kPa,約為左洞極值的1/2。
(5)現場實測結果表明,隨著卸載量的增大,最大隆起值為6.2 mm,未超過2 cm的控制標準,而且處于漸變,一般不會導致錯臺現象,故未針對不均勻變形產生錯臺或開裂現象的問題作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