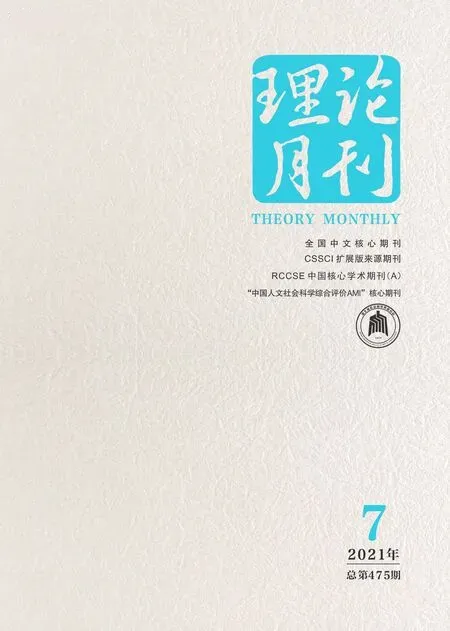悖謬與自由:論偶發藝術的“不確定性”
□曹曉寰
(河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24)
偶發藝術的創始人阿倫·卡普羅在《紐約藝術中的“偶發藝術”》(“Happenings”in the New York Art Scene,1961)一文中表述:“偶發藝術,就是事情的發生。”[1](p61)“是描述那些最具冒險性、開拓性及挑戰性的東西。”[1](p61)他在《無題文章和其他作品》(Untitled Essay and Other Works,1967)中透露:“我一直夢想一種新藝術,一種真正的新藝術。”[2](p4)“我們是冒險家。我們不必‘希望’任何東西。”[2](p7)可見,卡普羅認為的偶發藝術是一種新藝術,這種藝術在于冒險地探索一條完全自由創作的道路。
自由創作意味著掙脫傳統創作規范的約束。對此,偶發藝術進行了一系列叛逆求新的實踐,消除了藝術與非藝術、藝術家與非藝術家的界限,導致藝術在定義、形式、內涵上的“不確定性”。在一定意義上,藝術的“不確定性”與其他學科的“不確定性”具有同構性。學界通常將偶發藝術作為研究現代藝術和后現代藝術的一個論題,對偶發藝術在哲學層面的內涵并未足夠重視。因此,對偶發藝術的“不確定性”以及“不確定性”本身進行思考成為值得學界關注的問題。
一、偶發藝術及其思想來源
偶發藝術(Happening Art)指具有即興表演性質的活動。該活動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美國產生并盛行。“偶發”一詞原是美國拉特格大學《人類學家》雜志的一個欄目標題。1959年,阿倫·卡普羅(Allan Kaprow)在論文《杰克遜·波洛克的遺產》(The Legacy of Jackson Pollock)中使用該詞描述藝術創作的一種狀態。此后,“偶發”便用以指代具有偶發性、開放性、不確定性特征的藝術現象。同年,卡普羅在紐約魯本畫廊(Reuben Gallery)策劃了一場偶發活動“6部分中的18個偶發事件”,引發了一股偶發風潮。進行偶發創作的還有吉姆·戴恩(Jim Dine)、克萊斯·奧爾登堡(Claes Olden?burg)、羅伯特·惠特曼(Robert Whitman)、喬治·西格爾(George Segal)等人。
偶發藝術產生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社會發展的分水嶺時期。一方面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個頂峰,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社會中潛藏的重重危機面臨爆發。此時西方社會原有的后現代力量獲得了發展條件,并對傳統的現代或現代性進行了批判和挑戰。這一時期被相當多的學者看作現代與后現代的分界,如提出“后工業社會”概念的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論述后工業社會來臨的阿蘭·圖海納(Alain Touraine)、論述后現代性狀況的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自此,后現代主義從審美領域向哲學領域擴散,最后進入人文、社會等領域。
偶發藝術在產生之日便浸染了歷史和文化上的復雜性,其藝術探索是在各種矛盾形態的碰撞、交鋒中進行的。簡單來說,對偶發藝術產生啟示和催化作用的路徑主要有兩條:一是杰克遜·波洛克(Paul Jackson Pollock)的行動繪畫,在一定程度上行動繪畫被認為處于“改變繪畫定義的邊緣”;二是約翰·凱奇(John Milton Cage)的偶然音樂,偶然音樂的理念涉及東方的佛教禪宗思想。
杰克遜·波洛克是抽象表現繪畫的奠基人之一。他采用滴畫法(drip painting)創作了一系列姿態性作品,這些具有即興、隨意、無中心、無空間特征的作品就是為人熟知的行動繪畫(Action Paint?ing)。該術語在1952年由藝術批評家哈羅德·羅森博格(Harold Rosenberg)提出。羅森博格認為行動繪畫是從政治、美學、道德價值中解脫出來的一種行動實踐。
波洛克在《我的畫》(My Painting)一文中有過表述:“我的畫不是來自畫架。在繪畫前,我幾乎不去繃畫布。我寧愿把未繃緊的畫布釘在堅硬的墻壁或地板上。在地板上我感到更加自在。我覺得這樣更接近我的畫,我更能成為畫的一部分,因為我可以繞著它走,從四個側面入手,然后真正走入畫中。”[3](p33-34)“當我在繪畫時,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有經過一段時間‘熟悉’后,才明白自己在做的事。”[3](p34)這種行動繪畫的方式在他的諸多作品中都有體現,如《整整五潯》(Full Fathom Five,1947)、《作品1號》(Number 1A,1948)、《作品31號》(Number 31,1950)。1950年波洛克在接受威廉·萊特(William Wright)采訪時,針對其提問:“是否可以說無意識是藝術家的創作源泉?”他答道:“無意識不僅是現代藝術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并且無意識的驅動力在看畫的時候也很重要。”[1](p6)“在我看來,可能性是無窮的。”[1](p10)正是對無意識、可能性的重視,促使波洛克賦予了行動繪畫一定的自由度。
1959年卡普羅在《藝術新聞》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杰克遜·波洛克的遺產》。文中他對波洛克的繪畫進行了從形式到內在的分析,認為波洛克的繪畫突破了自古希臘以來的創作傳統,這種突破可以看作藝術發展的一個轉折。就此,卡普羅指出:“有二種選擇。一種是繼續這個方式。在既不偏離也不深化的基礎上變化波洛克的美學原則,也許能創作許多好的‘接近繪畫’的作品。另一種是完全擺脫繪畫,我指的是我們熟悉的那種單一的、平面的、矩形或橢圓形的繪畫。”[1](p57)卡普羅的論點不僅反映了他對20世紀60年代西方藝術變革的預言,同時反映了現代性與后現代性之間的某種交錯,以及后現代藝術的反藝術思想如何從現代性中孕育而來。隨后,卡普羅舉辦了一些突出行動且擺脫繪畫的活動,這些活動初步具有了偶發性質。
約翰·凱奇是美國先鋒派作曲家、哲學家。1952年他在黑山學院組織了一場演出,旨在探討有目的的無目的性(purposeful purposelessness)。演出由一些不相關的“事件”組成:舞蹈家默斯·坎寧安(Merce Cunningham)跳舞、鋼琴家大衛·圖多爾(David Tudor)彈琴、詩人查爾斯·奧爾森(Charles Olsen)朗讀、畫家羅伯特·勞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白色繪畫作品展覽。凱奇則做了一場演講并以“一根琴弦、一次日落皆為演出”為結尾。這場由門類不同、樣式不一的“事件”組成的演出呈現出偶然性、隨意性、不確定性性質,與偶發藝術的風貌十分契合,因此,常被學界看作偶發藝術的真正開端。
約翰·凱奇從勞森伯格的《白色繪畫》(White Painting,1951)中看到了變幻的光影,體會到禪宗“空”的思想,受此啟發創作了鋼琴曲《四分三十三秒》(4′33″,1952),由大衛·圖多爾在伍德斯托克的音樂會上進行了演奏,鋼琴曲總長度4分33秒,演奏的規則是無聲,過程充滿不確定性。該作品被認為是機遇音樂(Chance Music)的典型作品。此后凱奇創作的作品《鋼琴曲4—19》(Music for Pia?no 4—19,1954)與《鋼琴與管弦樂隊音樂會》(Con?cert for Piano and Orchestra,1958)是對機遇音樂的進一步發揮。機遇表示契機、時機,具有不可預料、不斷變化的特點。“空”來源于緣起論、三法印、萬法皆空思想。凱奇對禪宗的理解雖遭到美國學者阿倫·瓦茲(Alan W.Watts)的指責,認為其利用禪宗思想來“反抗文化和社會習俗”[4](p199)。然而,凱奇對禪宗的調和性藝術轉化對偶發藝術的產生和發展帶來了直接影響。
1957—1958年,卡普羅進入凱奇開辦的社會研究新學院學習音樂創作。凱奇提示卡普羅使用錄音帶預先制作聲音,以某種隨機順序進行播放。卡普羅接受了該建議,對創作過程中的隨機性加以了關注,并嘗試將創作拓展到一切可能的范圍。例如,將聲音、燈光、氣味作為創作元素,將空曠的田野、沙灘、樹林作為創作場地,逐漸發展出一種“對繪畫的多種層次的空間再現”的藝術形式,即偶發藝術。同凱奇一樣,卡普羅善于從禪宗中獲取靈感。他通過禪宗的冥想練習創作“基于呼吸的繪畫”,這種具有沉思意味的繪畫具有不可捉摸、無法確定的特征。
此外,偶發藝術還從更早的達達主義中汲取養分。達達主義具有反叛性、非理性特點,馬塞爾·杜尚(Marcel Duchamp)是代表人物之一。杜尚創作的《下樓梯的裸女》(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No.2,1912)以連續重疊的形象表現了運動中不同瞬間的美,對運動中的不穩定性和瞬間的模糊性進行了渲染。此后,杜尚創作了《泉》(Foun?tain,1917)、《帶胡須的蒙娜麗莎》(L.H.O.O.Q,1919)等作品,其另類的創作方式推進了西方藝術形態和美學觀念的發展。卡普羅表述過杜尚帶給自己的影響,尤其“藝術是任意性的”[5](p222)方面,他認為“我對藝術專一而又持久的興趣是有哲學基礎的”[5](p222)。結合上述路徑,不難看出卡普羅認為的哲學基礎同“不確定性”是息息相關的。
二、偶發藝術的“不確定性”
由波洛克的行動繪畫發展到動作拼貼,由約翰·凱奇的偶然音樂、劇場化表演發展到“行動的舞臺”,卡普羅開創的偶發藝術使創作成為一種即興表演活動,從而“超越了‘僅體現在繪畫中’的嘗試,繪畫的‘動作’已被戲劇和生活取代”[6](p106)。自此,作為即興表演、生活化、媒介融合的偶發藝術背離了西方的藝術傳統。“不確定性”是偶發藝術進行新藝術探索的主要策略,也是偶發藝術進行反形式、非理性、游戲性、無目的性等反藝術實踐的總體反映。
“不確定性”在偶發藝術的首次活動中便得到充分體現。1959年,卡普羅在魯本畫廊進行了一場活動“6部分中的18個偶發事件”(18 Happen?ings in 6 Parts)。“6部分”指的是將畫廊分為3個房間,每個房間分為2個部分,共為6部分。“18個事件”指的是每個部分安排3場活動,共構成18個“事件”。“偶發事件”的具體表現為:在“事件”開始前,人們獲得相關的計劃和指示,這些計劃和指示沒有特別的意義,就像日常生活中隨時可能遇到的事情,如坐下、行走、說話、畫畫、擠橘子汁。活動過程充滿隨意性、自由性。正因如此,“偶發事件”顯示出生活的真實狀態,體現出卡普羅所推崇的普通的事、普通的意義。
卡普羅曾使用“質樸”“直接”“孩子氣”等詞語形容波洛克的繪畫,認為作品的“坦白”帶給自己啟發。卡普羅也從凱奇的課堂上獲得關于生活隨機性、開放性的啟發。這些啟發使卡普羅將直接、隨機的事物視為主要藝術元素。例如,一種被壓碎的草莓味道、一道被抓傷的痕跡、一聲嘆息、一場沒完沒了的演講、一道掠過的閃電、一張古琴的輕顫、跳躍的投影。
吉姆·戴恩將繪畫、表演等媒介進行了融合。1960年他在賈德森畫廊(Judson Gallery)開展了一場“偶發事件”《微笑的工作者》(The Smiling Work?man)。“事件”中戴恩身穿紅色工作服,用橙色和藍色“顏料”寫下“我喜歡我所做的”幾個字,過程中他不僅將“顏料”(番茄汁)喝下去,還將“顏料”澆在腦袋上,任其隨意流淌。其滑稽的行為凸顯出創作的偶然性和游戲性。這種方式貫穿于他此后的創作中,如《齜牙咧嘴的巨大鬼臉》(The Enor?mous Grimace of Teeth,1960—1961)、《兒童的藍色墻》(Child’s Blue Wall,1962)、兩幅《名字畫》(Name Paintings,1968—1969)。吉姆·戴恩將創作視為生活的延伸,而生活是包羅萬象、千變萬化的。因此,他不得不將生活中變化、混沌、不確定以及無厘頭的思想和行為搬進藝術中,他在介紹自己的“偶發事件”時坦言:“我并不確定它意味著什么。”[1](p68)
《如何制造偶發事件》(How to Make a Happen?ing,1965)是卡普羅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演講。在第一部分他列出了偶發藝術的11條規則,將偶發藝術定義為一種開放式表演,目標是對既定傳統的瓦解。例如,第1條是“忘記所有標準的藝術形式”[7](p1)。他強調,關鍵是要創造一些新東西。第2條是“可以通過將偶發事件與生活相混淆來避開藝術”[7](p1)。他解釋道,創作需要模糊藝術與生活的界限。在第二部分他列舉了幾個實例,如《肥皂》(Soap)、《呼叫》(Calling)、《下雨》(Rain?ing),將之作為粗略的創作指南。次年,在《近期的偶發事件》(Some Recent Happenings,1966)中卡普羅總結了一些已經發生的“事件”:《鳥類》(Birds)由南伊利諾伊卡本代爾大學委托,1964年2月16日在校園邊的樹林進行;《家庭》(Household)由康奈爾大學委托,1964年5月3日在一個垃圾場進行;《肥皂》(Soap)由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委托,1965年2月3日至4日在薩拉索塔進行。這些“事件”無須排練也不必重復上演,它既可以作為一幕出現,也可以作為連續劇形式出現。卡普羅認為:“偶發事件是把不同時間和地點發生的許多場面進行的集合”[8](p5),“它是藝術,但似乎更接近生活”[8](p5)。這種接近生活的藝術在其另一篇文章《不能成為藝術的藝術》(Art Which Can’t Be Art,1986)中進行了更為肯定的表達。的確,卡普羅將日常生活中的刷牙、肘部運動稱為“做藝術”。
奧爾登堡的代表作《在商店的日子》(Store Days,1961)就屬于接近生活的藝術。該“事件”發生在紐約東二街107號的一個商店里,店內是甜餅、漢堡、襯衣等項目的陳列。“事件”展示目錄上登載著他的一篇文章《我追求一種藝術》(I Am for an Art)。“我追求一種從生活本身獲取形式的藝術,它曲折、延伸、積聚、下雨、下雪,它同生活本身一樣沉重、粗糙、遲鈍、甜蜜、愚蠢。”[1](p98)“我追求雨水淋濕面包的藝術。老鼠在地板上跳舞的藝術。我追求蒼蠅在燈光下光滑梨子上走路的藝術。我追求潮濕洋蔥和堅硬綠芽的藝術。我追求在蟑螂爬行時咔噠咔噠敲堅果的藝術。”[1](p101)此后,奧爾登堡進行了諸多生活化的創作,如《印第安人》(In?jun,1962)、《自體》(Autobodys,1963)、《電影院》(Movie house,1965)。透過奧爾登堡的創作及表述,可以看出藝術家對創作開放性、不確定性的追求。
縱觀偶發藝術種種不合時流的實踐,無不反映出明顯的“不確定性”特征。“不確定性”是偶發藝術進行反藝術創作的有力武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藝術的真正含義。“不確定性”建立在破壞傳統藝術規范以及“毀棄他人已建構之物”的基礎上。一般來說,傳統藝術的建構從審美性出發,以審美性指導創作。偶發藝術對審美性卻加以弱化,認為審美性并非是唯一的,而是多元觀念中的一種。1988年卡普羅在接受小約翰·霍爾德(John Held Jr.)采訪時表示“我的興趣不是否定繪畫,而是增加畫家當時的選擇余地”“打開另一個大門”。
概括地說,偶發藝術的“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第一,主張反形式,拒絕將形式加以形式化。針對形式在傳統藝術中的必要性,偶發藝術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態度將其揚棄,使形式不再具有必要意義。第二,推崇創作中的非理性。體現在藝術家把一些雜亂無章或自己都無法理解的思想注入創作中,借此表達非理性與理性具有同等的地位。誠然,非理性作為主宰人類行為和決策的隱形力量,是不應回避的。第三,重視藝術的生活性和游戲性、生活的藝術性和開放性以及觀眾的參與性。游戲作為一種自由愉快的活動,會以自身規則沖撞到統一規范,觀眾的參與行為則會削弱藝術的權威性及藝術家的合法性,從而拉近藝術與生活的距離。第四,倡導創作的無目的、無意義。無目的在偶發藝術看來恰恰是合目的性的,但藝術慣于遭受規范、準則的干預,逐漸被剝奪了自由表達的樂趣和話語權。對此,偶發藝術提倡創作的多種可能性,以維護創作的自由。
可見,偶發藝術極力想從確定的、限制性的思想桎梏中掙脫出來,以方便自身在不確定性、開放性、自由性中前行。德國哲學家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Adorno)在1969年出版的《美學理論》中指出,藝術的自明性或自身的可理解性已消失殆盡。德國哲學家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美學研究過程中提出了一些前后不一的觀點,使他的美學思想呈現出某種含糊性。他在1977年出版的《德國悲劇的起源》中強調了寓意、諷喻、模棱兩可在社會和藝術中的重要性。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生存美學試圖將生活的無規則納入美學范疇。因此,如何看待對待“不確定性”不僅限于藝術層面,還延展至其他層面。
三、“不確定性”的哲學內涵
主張“不確定性”的偶發藝術以藐視安穩的勇敢向傳統藝術發起了攻擊,成為推動西方后現代藝術進程的中堅力量。“不確定性”作為一種反叛性策略,是對關于藝術的悖謬性與悖謬的普遍性、創作的游戲性與自由的可能性等問題進行思考的出發點。從哲學層面看,作為偶發藝術內在結構和方法論基礎的“不確定性”并非是孤立的,它與悖謬、自由、多元等形態是交織并存的。
(一)“不確定性”作為反叛性策略
“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也就是不可界定、無法確定。19世紀現代派代表人物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在《1845年沙龍》中提出創作的三大原則:過渡性、逃脫性、偶然性。這些原則影響了印象主義、象征主義。進入20世紀,阿多諾反思了現代派原則,在談論現代藝術的審美性時表述了一個觀點“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統一”,從而使其美學兼具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雙重性。本雅明雖受法蘭克福學派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卻不主張用本體論原則探討藝術問題,他對藝術問題的觀點往往前后不一。和阿多諾一樣,他的美學在保留現代美學特點的同時夾雜了后現代美學特點。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反文化”“非主流”運動風靡一時,這些運動向傳統文化提出了質疑。作為反叛性文化策略的“不確定性”,勢必對傳統意義上的理性主義、邏輯主義進行攻訐。大致來說,“不確定性”源自現代性,經過一系列反叛性的批判活動,顯示出對現代性的超越。
后現代主義學者伊哈布·哈桑(Ihab Habib Has?san)將“不確定性”提煉為后現代主義的核心傾向之一。康德就美的“不確定性”使用過兩個隱喻:一是爐膛中搖曳不定的火苗的不確定性,二是小溪流水淌過后不規則的痕跡。康德的觀點得到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利奧塔的高度評價,利奧塔認為康德將美與自由同等重視。解構主義哲學家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強調“延異”的自我生成性質,“延異”有差異和延宕雙重含義。它作為一種散布和播散,代表了一個無限區分、無限推延的過程,這一過程導致中心/邊陲、正常/異常、平衡/失調的秩序遭到破壞,從而成為不確定、無中心、模糊化的運動。吉爾·德勒茲和費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提出“根莖”概念來暗喻世界,“根莖”具有非中心、無規則、不確定的形態。“根莖”是一種游牧思想方式即開放的、充滿差異的、非地域化的、多元的。美國哲學家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Hartman)發揚了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批評,他認為,當代批評的目的就是要對“不確定性”做出解釋。
此外,“不確定性”存在于以嚴密著稱的數學、物理、科學領域。如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原理,庫爾特·哥德爾的不完全性定理,普里高津的耗散結構理論,托馬斯·庫恩的科學革命與范式的不可通約性。科學知識不會永久地擁有可信度,任何追求確定性、完整性、穩定性結論的知識都面臨難圓其說的風險。
(二)藝術的悖謬性與悖謬的普遍性
悖謬,就是悖論、荒謬。悖論,是集兩組相悖命題于一身的奇妙力量,它伴隨人類思想特別是語言的形成而出現。早在古希臘的前蘇格拉底時代,芝諾就提出阿基里斯追不上烏龜,飛矢不動命題,反映出語言系統隱含的“確定性”和“含糊性”同在的特征。18世紀,康德在其著作《純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二律背反命題:有限與無限,可分與不可分,自由與不自由,神的存在與不存在。這幾組命題展現出悖論的難以克服性。19世紀以來,不乏展現悖論命題的學者、藝術家。荷蘭版畫家埃舍爾(Maurits Cornelis Escher)用藝術形式表達了悖論思想,其作品《高與低》《畫手》引導人們通過一步步富有邏輯的推理推導出毫無邏輯甚至完全相反的結論。20世紀中后期,偶發藝術代表卡普羅在思考藝術與生活的關系時,意識到不被視為藝術的藝術實踐與其說是悖論,不如說是矛盾。
伴隨悖論而來的還有荒謬。荒謬,即不分真假、混淆是非。意大利戲劇家路伊吉·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lo)在其著作《幽默主義》中強調了邏輯合理性的虛假性及世界的不可知性。法國荒誕派劇作家歐仁·尤內斯庫(Eugène Ionesco)認為世界始終是荒謬的。從認識論和方法論角度講,荒謬具有普遍性。當人類從試圖探究世界和人生的合理性開始,便發現世界和人生的荒謬性不可避免。這是因為世界是遼闊無邊的,且處于永恒的運動中。人類世界不過是無限宇宙的一個局部,人類所掌握的知識也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而,荒謬與真實未必對立,它們之間還充滿各種錯置和例外。換句話說,很多時候荒謬等于真實,真實等于荒謬。
利奧塔提出了概念悖謬推理(paralogy),也就是以異質標準對歧見進行探求。他認為連續的、不可區分的功能已失去其優越性,知識正將自己的進化推理為不連續的、不可修正的、差異的、悖論的。悖謬作為人類思想危機的根源之一,實際上是一種不可能的可能性,它是在人類思想活動中嵌入難以解決的問題,使思想在反復的矛盾穿梭中形成一種“不確定性”狀態。偶發藝術將創作當成某種矛盾、混沌的行動,正是以荒謬的普遍性為基石的。如此一來,蘊含著思想內容的藝術創作觸及具有悖謬性的主體結構后,又通過反映主體結構的悖謬性進一步構成創作上的悖謬性。
(三)創作的游戲性與自由的可能性
藝術創作是人的思想尋求自由的表現之一,而思想的自由是不確定和含糊的。早在1952年的黑山學院“事件”中,藝術便開始探討有目的的無目的性,嘗試以游戲否定目的,以無目的否定意義。這樣做顯然不是為了實現傳統藝術關于形式美、結構美、現象美的目的,恰恰是為了突破那些限制。這是偶發藝術顯得反常、粗糙和突然的原因。例如,忽視形式甚至反形式,忽視主題和風格甚至刻意模糊主題和風格,忽視理性和邏輯甚至主張非理性和反邏輯。偶發藝術的冒險活動無疑是為了在無目的的游戲中尋求自由的可能性。
法國哲學家薩特(Jean-Paul Sartre)在《什么是文學?》中論述了創作自由的無止境性質。他認為一個有創作使命感的作者是一個無止境尋求創作自由的人。薩特關于自由的觀點對新小說派、荒誕派戲劇及后現代藝術產生了啟迪。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在《真理與方法》中論述了游戲的自由性質。他認為:“游戲本身對游戲者來說,其實就是一種風險。我們只能與嚴肅的可能性進行游戲。這顯然意味著,我們是在嚴肅的可能性能夠超出和勝過某一可能性時才參與到嚴肅的可能性中去。游戲對游戲者所展現的魅力就存在于這種冒險之中,由此我們享受一種做出決定的自由,而這種自由同時又是要擔風險的,而且是不可收回地被限制的。”[9](p494)。美國心理學家弗蘭克·巴倫(Frank Barron)在其著作《獨創性與個人自由》中將獨創性與含混、復雜、自由進行了關聯。
自由,有時也被看作無政府主義。科學哲學家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在《反對方法》中通過否認理性和經驗表明科學的無政府性,并指出一個不抑制進步的原則“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他還將無政府主義與藝術中的達達主義加以類比,從而成為一個科學的達達主義者。對偶發藝術產生直接影響的作曲家凱奇在1961年為《沉默》一書寫序言時自稱無政府主義者。從藝術層面看,無政府主義指代的是對反主流、自由精神的瘋狂擁護,一定意義上被看作激進的后現代主義,美國批評家哈爾·福斯特(Hal Foster)稱之為反作用的后現代主義,它同樣預示著“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10](p145)。“怎么都行”囊括了多種不確定性和可能性。偶發藝術開展的無固定形式、無固定原則、無確定目的,以及無完整體系的批判活動,實際上追求的就是自由的可能性,換句話說,就是“不確定性”本身。
簡言之,“不確定性”是偶發藝術的主要策略,也是后現代藝術進行反藝術、反美學實踐的主要動力。利奧塔認為后現代藝術“不受預先定下的規則的主宰”“拒絕正確的形式”,善于表達“不可表現之物”[11](p118),因而具有深刻的哲學內涵。源于此,他認為藝術家常常處于哲學家的位置。德里達提倡的“解構”使創作成為一種不具固定結構、不含確定意義且無始無終的自由活動,為文化的自由發展開辟了無限前景。與偶發藝術有所交疊的還有同期的波普藝術和激浪派。吉姆·戴恩的《車禍》(The Car Crash,1960)、奧爾登堡的《在商店的日子》(Store Days,1961)既可看作波普偶發藝術,亦可看作激浪派的即興活動。當然,與偶發藝術有所交疊的還有隨后的身體藝術、大地藝術,這些運動是對偶發藝術的繼承和發展。
四、結語
“不確定性”用美國學者哈桑的話總結就是:“含混、不連續性、異端、多元性、隨意性、叛逆、變態、變形。”[12](p186)嚴格地說,偶發藝術的“不確定性”不應被“確定”,而應采用斷裂、碎片、開放、無中心等方式探析,才能最大可能地顯現其“事件”性質。偶發藝術的作品亦不能固定化、永久性地看待,它是自身不斷更新和再生的一個過程,“是持續不斷地、反省性地與世界發生碰撞,其中,作品遠不是這一過程的終點,而是其意義的后續研究的發起者和焦點”[10](p245)。
誠然,世界萬物都是在“褶皺”式的運動中滲透和交錯的,其中充滿著數不清的不可確定的“事件”。這些“事件”沒有黑格爾認為的那種“必然性”。這是由于“不確定性”存在于一切“必然性”之中,任何一種“必然性”都有可能遭遇“不確定性”的侵入和干擾。就此而言,“不確定性”彌漫于知識現象的種種層面。因此,以“不確定性”面對文化現象的復雜多變,才能不斷探索新的可能性,并開辟多元的解釋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