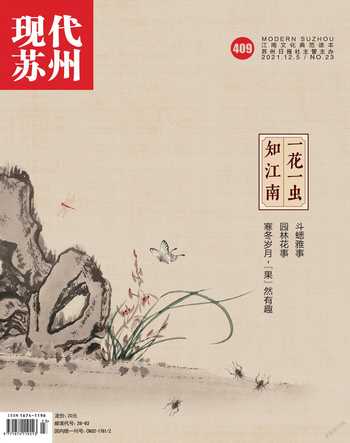收養:南蟲不及北蟲矣
丁云

真正達到大將級的蟋蟀,數量比例不及萬分之一。由古至今的《蟋蟀譜》上雖記錄了大量品種,但在市面上幾乎看不到。唯有大比賽開斗時,上陣的選手大多就是譜上極品。
高手收蟋蟀,那只消一眼,瞬間就判定優劣,決定取舍。而高手之間的較量,不給對方看“底牌”,斗前看不到。待到兩只蟋蟀都落了斗柵,輸贏基本已定。
蟲打哪兒來?主要出自山東、河北、河南一帶,以及安徽北部。受到氣候、農業、城鎮化等因素影響,南蟲個小難覓,早已無法與北蟲抗衡。南北玩蟲,收的都是北蟲。
去齊魯淘蟋蟀
山東是蟋蟀的一大產地。最早是上海人到當地派發網罩,雇傭當地人去捕捉,捕到的蟋蟀也由他們全部買下,帶起了這門買賣。之后,捕蟋人越來越多,對蟋蟀也有了一知半解,會專門挑出大一些的,自認為好一些的,區別開來賣。
下田捕捉蟋蟀的,往往都是年輕壯漢,在第二天睡飽之后,會親自去市場出售挑出的蟋蟀,而普通的則交由老婆以隨意價格售出。忙活了一晚上,看走眼是在所難免,普通蟋蟀里可能潛藏著優秀的蟋蟀。況且,捕蟋人對蟋蟀的了解,終究只是摸個輪廓。那時的蟋蟀價格也不是很貴。
再到后來,捕蟋人組成團隊,7至10個人一組,從玉米田里出來就開始比劃蟋蟀的等第,之后內部標價。出貨時,在經歷了買家團七嘴八舌對著第一等的蟋蟀“吹毛求疵”、搗糨糊之后,一旦捉到第一等蟋蟀的捕蟋人松口降價,那么原本定好的階梯價格也就分崩離析了,捕蟋團內部為此也時有埋怨。當然,也有很多第一等的挺住了賣價。
當地的蟋蟀交易市場就像夜市,可以綿延十幾里路長,兩旁擺放著一張張桌椅。“蟋蟀是很難抓的,玉米田里一簇簇的玉米葉子又非常割人,”邊先生說,所以捕蟋人都穿著迷彩服下地捉蟲,各地來的買家就沿路相蟲。
一方水土養一方蟲
捕到的蟋蟀,山東那邊擱瓷罐里,蘇滬這邊帶去竹筒,杭州人玩紫竹筒。瓷罐的優點是查看起來方便,“杭蟲跟紹蟲,在竹罐與網罩之間拍進拍出,有時會把蟋蟀的大腿拍下來,出各種事故,那就得賠錢。”邊先生說,瓷罐沒這問題,最多跑了蟋蟀。
蟋蟀不好分辨,蟋蟀盆倒是比較好分,北盆壁厚,南盆壁薄。南盆適合早秋,透氣性好,到了晚秋,厚壁的北盆保溫性佳。
陸續弄回來的蟋蟀先靜養。古法養蟲不夠注重營養,“喂半粒到一粒米飯,不給蟲子多吃。這種養法控制得住分量,蟋蟀看上去大,實際并不重。”邊先生說。但從營養學的角度不行。“北蟲一定得有肉,沒肉就空;南蟲可能因為土地本來較肥,能吃的東西多,加上水分充足,稍好一點兒。”因而同樣的控制,南蟲核下來的分量高點兒。
“水靈靈”的南蟲斗不過“干老”的北蟲。邊先生說,以杭蟲為代表的南蟲還有一點遜于北蟲,牙短,“同等分量,人家北蟲個頭大牙狠,更沒法斗了。”一方水土還真是養一方風物,包括蟲子。
現在養蟲主要喂投飼料。邊先生有獨門食譜:將毛豆煮得爛爛的,去掉上面一層衣后給蟋蟀喂食。實踐下來,吃了植物蛋白的蟋蟀確實體力好。這種飼養方法也是有據可查的。一位最早實踐營養法的養蟲名家曾撰文道,蟋蟀只要前三招不輸,越往后打越定心。可見,蟋蟀也靠日常營養均衡維系打斗時的爆發力和持久力。
未養蟋蟀先養雌
邊先生讀小學時,鎮上有個也玩蟋蟀的老頭,霜降之后帶著一只蟋蟀來找他外公,悻悻講起前晚上斗輸了。外公看這蟋蟀很是不錯,未料竟會遭遇更厲害的對手,細問對手來路之后,判斷照理不至于會輸。外公于是問,盆里有沒有三槍(雌性),說有,看后就讓朋友打他那兒捉幾只元雌(處女三槍)去,并關照朋友隔3日再斗。此后那只蟋蟀場場大捷,再無遭遇對手。原來,早前是那二槍(雄性)嫌棄三槍老了,激不起斗志,致使斗場落敗。
八月初剛有蟋蟀那會兒,先不管二槍,捉三槍要緊,古譜云:“未養蟋蟀先養雌”。早養的雌蟲,多為元雌。一直到大冬天,這些雌蟋蟀就這么養著、候著,等派用場。一口大缸,放幾塊瓦爿,再放些泥巴,從早秋開始,邊先生外公就這么將三槍養在里面,直到二槍沒了,才把三槍放走。
用雌蟋蟀來激發雄蟋蟀的斗志,屬于蟋蟀“三反”里的“一反”。“蟋蟀入門,一要知道‘青黃紫’。二要知道蟋蟀是‘三反’”。邊先生說。怎么叫“三反”?一般動物輸了叫,蟋蟀是勝了叫。人類運動員賽前禁欲,但蟋蟀斗前必須有雌,不能斷。“蟋蟀出場時,都看后面的蛉,見蛉才能出斗,不見不斗。”再有“一反”,雌上雄背。“蟋蟀交配時,雌在上,雄在下。不懂的人,見三槍中間有一根長長的,就以為是雄的,實則不然,卵從里面排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