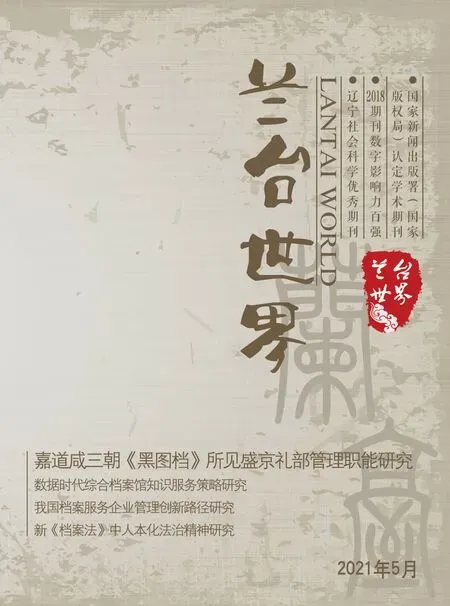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集成管理平臺(tái)的構(gòu)建
劉雨珊 張佳佳
一、前言
我國檔案集成管理研究最早始于對(duì)文檔一體化管理的理論關(guān)注和實(shí)踐探索。2002年,航空企業(yè)開始了技術(shù)圖檔動(dòng)態(tài)管理電子化集成系統(tǒng)框架模型的構(gòu)建和實(shí)踐探索[1]13。2003年,安小米教授主持的國家自然科學(xué)基金項(xiàng)目“城市建設(shè)文件、檔案信息的集成管理與集成服務(wù)研究”,主要針對(duì)城建檔案信息的持續(xù)發(fā)展進(jìn)行學(xué)術(shù)理論研究,將信息集成服務(wù)與集成管理的概念融入到城建檔案管理與建設(shè)中,提出城市建設(shè)文件檔案信息的集成管理與集成服務(wù)模式。蘇珊珊的《我國檔案集成管理研究現(xiàn)狀述評(píng)》對(duì)2012年之前的我國檔案集成管理研究進(jìn)行了詳細(xì)述評(píng),她認(rèn)為我國檔案集成管理大致可分為兩個(gè)階段:2002年至2003年是檔案集成管理的萌芽時(shí)期,是集成管理在檔案研究領(lǐng)域的初步探索與應(yīng)用;2004年至2011年是檔案集成管理的初步發(fā)展時(shí)期,檔案管理部門及其研究人員在檔案集成管理的實(shí)踐探索基礎(chǔ)之上進(jìn)行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并開展了關(guān)于檔案集成管理概念的內(nèi)涵與外延、原則與方法、標(biāo)準(zhǔn)與規(guī)范、集成系統(tǒng)構(gòu)建模型等眾多方面的熱烈討論[2]14。在此基礎(chǔ)上,2012年至今有關(guān)檔案集成管理的文章研究更加細(xì)化,研究客體涉及大型工程、少數(shù)民族、企業(yè)人力資源、地質(zhì)科技、方言數(shù)字檔案等多個(gè)方面。
1988年,吳寶康最先在《檔案學(xué)概論》一書中明確指出:“檔案是貯存和傳播知識(shí)的一種形式。”這一論斷揭示了檔案的傳播性是其重要屬性和要求。自此,檔案學(xué)界開始將傳播學(xué)原理和方法引入檔案信息傳播領(lǐng)域。當(dāng)前,對(duì)于檔案信息傳播的相關(guān)研究主要集中在傳播模式、檔案信息傳播媒介(尤其是網(wǎng)絡(luò)媒介)、傳播功能分析等方面[3]16。
檔案集成管理與檔案信息傳播的研究隨著時(shí)代的發(fā)展不斷地創(chuàng)新,但是缺乏借助集成管理模式推進(jìn)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傳播的相關(guān)研究。本文在當(dāng)前檔案集成管理與檔案信息傳播研究的基礎(chǔ)上,將檔案集成管理與檔案信息傳播融于一體,并具體作用在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上,構(gòu)建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集成管理平臺(tái),實(shí)現(xiàn)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效益最大化。
二、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集成管理平臺(tái)構(gòu)建的必要性
1.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是向社會(huì)傳播檔案信息高效優(yōu)質(zhì)的方式。陳永生在其文章《從信息傳播的角度看檔案編研的意義》中說道:“一般說來,檔案信息可通過三種主要渠道傳播給利用者:一是移動(dòng)檔案原件本身,即包括閱覽服務(wù)、外借服務(wù)和舉辦展覽三種形式;二是以照相、靜電復(fù)印或者其他方法進(jìn)行復(fù)制;三是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4]24通過閱覽服務(wù),利用者可以與檔案原件或經(jīng)過數(shù)字化處理的檔案圖像進(jìn)行直接接觸,利用者可以獲得真實(shí)性最大的信息,但是檔案信息只有在利用者到館情況下才能被發(fā)掘使用,這種渠道下檔案信息傳播受到很大局限。受資金、人力、場(chǎng)所等因素的限制,展覽的檔案信息可能不夠全面。而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是以提供客觀的檔案信息為基本出發(fā)點(diǎn)的產(chǎn)物,經(jīng)過編者所做的查選、考訂、加工等一系列工作之后,檔案信息的整合度較高且更容易利用,而且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是檔案機(jī)構(gòu)主動(dòng)向社會(huì)提供利用的重要方式。
2.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更加豐富。隨著社會(huì)的發(fā)展以及社會(huì)信息需求的擴(kuò)大,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不斷豐富。首先,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的內(nèi)容形式不再局限于文字與圖片,以音視頻、紀(jì)錄片等形式傳播的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日益增多,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的內(nèi)容表現(xiàn)形式不斷呈現(xiàn)出豐富化、多樣化的趨勢(shì)。其次,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的表現(xiàn)形式不再局限于傳統(tǒng)印刷型檔案文獻(xiàn)出版物,音像型與數(shù)字型出版物的數(shù)量逐年上升。最后,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的載體由圖書、期刊、報(bào)紙等紙質(zhì)載體發(fā)展到廣播、電視等電子媒介載體,再到包括網(wǎng)絡(luò)、移動(dòng)端、新媒體在內(nèi)的新型載體形式。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從形式到載體都得到了極大豐富,但是當(dāng)前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仍需依賴出版商、新聞媒體等傳播形式,傳播結(jié)果不盡如人意,耗費(fèi)時(shí)間、人力、物力編纂出來的檔案文獻(xiàn)成果引起關(guān)注與評(píng)價(jià)的范圍較小。
3.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的傳播是檔案文獻(xiàn)編纂學(xué)學(xué)科價(jià)值訴求的體現(xiàn)。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是整個(gè)編纂工作的核心,直接關(guān)系到整個(gè)編纂工作和編纂學(xué)研究的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在以往檔案文獻(xiàn)編纂學(xué)的體系內(nèi),透過教材中“出版?zhèn)鞑ァ鳖愃普鹿?jié)以及文獻(xiàn)計(jì)量的分析,不難發(fā)現(xiàn)編纂成果的傳播研究常常被認(rèn)為是可有可無的存在,在其內(nèi)容、價(jià)值乃至是否屬于檔案文獻(xiàn)編纂學(xué)研究任務(wù)上,仍無清晰的理論認(rèn)識(shí)和足夠的學(xué)科自信[5]112。再加上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在傳播實(shí)踐中受到市場(chǎng)運(yùn)行機(jī)制等因素影響,傳播效果以及對(duì)社會(huì)貢獻(xiàn)度無法衡量,由此檔案文獻(xiàn)編纂學(xué)的學(xué)科價(jià)值受到了一定的影響。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集成管理平臺(tái)的建構(gòu)可以根據(jù)相應(yīng)的績效評(píng)估體系與傳播體系,對(duì)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的傳播與評(píng)價(jià)進(jìn)行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與分析,通過數(shù)據(jù)分析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的社會(huì)影響力,通過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的傳播驗(yàn)證并提升檔案文獻(xiàn)編纂學(xué)的學(xué)科價(jià)值。
4.集成管理平臺(tái)的構(gòu)建是我國檔案事業(yè)總體規(guī)劃的要求。2011年,《全國檔案事業(yè)發(fā)展“十二五”規(guī)劃綱要》提出:利用先進(jìn)技術(shù),為社會(huì)各界提供快捷、便利的檔案利用服務(wù);加強(qiáng)檔案編研工作,挖掘檔案信息資源,開發(fā)、提煉檔案信息產(chǎn)品,出版檔案史料匯編,使“死檔案”變成“活資料”,努力把“檔案館”建成具有特色的“思想庫”。201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wù)院辦公廳印發(fā)的《關(guān)于加強(qiáng)和改進(jìn)新形勢(shì)下檔案工作的意見》要求各檔案館(室)加大檔案信息資源開發(fā)力度,實(shí)現(xiàn)檔案價(jià)值最大化;拓展服務(wù)渠道,緊緊圍繞黨委、政府、本單位和其他單位及人民群眾的需要,主動(dòng)開發(fā)檔案資源,積極提供檔案信息服務(wù),通過報(bào)送或推介相關(guān)檔案信息、編輯出版檔案選編、舉辦檔案展覽、制作電視節(jié)目、發(fā)布網(wǎng)絡(luò)視頻、發(fā)行音像制品、送檔案信息進(jìn)農(nóng)村和社區(qū)等多種形式,全方位為社會(huì)提供檔案信息服務(wù)。2016年,《全國檔案事業(yè)發(fā)展“十三五”規(guī)劃綱要》提出,創(chuàng)新服務(wù)方式,多渠道開發(fā)檔案資源,不斷向社會(huì)推出精品力作和舉辦受公眾歡迎的活動(dòng)。以上《綱要》與《意見》中均提及檔案資源的開發(fā)利用,而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是檔案資源開發(fā)利用最有效的方式,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集成管理平臺(tái)的建構(gòu)是為了更高效地傳播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從而促進(jìn)檔案資源的開發(fā)利用。
三、構(gòu)建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集成管理平臺(tái)的制約因素
1.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數(shù)量較少。檔案文獻(xiàn)編纂是對(duì)檔案信息進(jìn)行深度開發(fā)、客觀呈現(xiàn)、科學(xué)加工的復(fù)雜的系統(tǒng)工程,該項(xiàng)工作的開展受到機(jī)構(gòu)人員設(shè)置、人員知識(shí)結(jié)構(gòu)、經(jīng)費(fèi)等多項(xiàng)因素的影響。檔案文獻(xiàn)編纂工作對(duì)于人員的知識(shí)結(jié)構(gòu)有較高要求,需要相關(guān)人員具備歷史文獻(xiàn)學(xué)、文書學(xué)、傳播學(xué)、校勘學(xué)、計(jì)算機(jī)等多學(xué)科的知識(shí)體系。檔案文獻(xiàn)編纂從選題至出版?zhèn)鞑ザ夹枰?jīng)費(fèi)的投入,而檔案館作為事業(yè)單位,經(jīng)費(fèi)受限于國家與當(dāng)?shù)卣耐度搿J艿揭陨隙喾N因素的影響,加之檔案文獻(xiàn)編纂工作難度較大、耗時(shí)較長,因此檔案文獻(xiàn)編纂的成果數(shù)量較少。
2.缺少系統(tǒng)性規(guī)劃。首先,近年來,國家和一些省市的檔案行政管理部門陸續(xù)出臺(tái)了有關(guān)檔案事業(yè)管理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和辦法,鼓勵(lì)檔案資源的開發(fā)利用,但有關(guān)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的整體規(guī)劃仍然較為缺乏。其次,長期以來各檔案館雖然建立了各種區(qū)域或者業(yè)務(wù)往來的合作關(guān)系,但是在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的展示方面卻無明確的合作關(guān)系,多數(shù)檔案館都是各自為政,基于本館館藏進(jìn)行檔案文獻(xiàn)編纂工作,缺乏系統(tǒng)的檔案文獻(xiàn)編纂工作合作性的規(guī)劃。最后,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有與出版商合作出版的、與媒體合作公開播放的、借助官方網(wǎng)站傳送的、需要去檔案館主動(dòng)查閱的,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的傳播方式各異,缺乏系統(tǒng)性規(guī)劃的整理與公開的平臺(tái)。
3.各檔案館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差異較大。我國各地區(qū)檔案信息化建設(shè)發(fā)展水平不均衡,西部地區(qū)受技術(shù)、資金、人才等因素制約,檔案信息化建設(shè)發(fā)展較慢,而檔案館信息化建設(shè)情況會(huì)影響編纂人員對(duì)檔案館館藏的認(rèn)識(shí),對(duì)自身館藏?zé)o全面認(rèn)識(shí)與掌握則會(huì)影響檔案文獻(xiàn)編纂工作的進(jìn)程與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的質(zhì)量。
4.檔案人才隊(duì)伍建設(shè)機(jī)制不健全。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集成管理平臺(tái)的建構(gòu)是一個(gè)涵蓋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國家行政管理體系及各級(jí)檔案機(jī)構(gòu)網(wǎng)絡(luò)體系的復(fù)雜的工程。這一工程涵蓋了收集、整合、發(fā)布、評(píng)價(jià)等各項(xiàng)業(yè)務(wù)工作,其后需要網(wǎng)絡(luò)連接技術(shù)、系統(tǒng)創(chuàng)建與更新技術(shù)等多項(xiàng)技術(shù)的支撐,而在業(yè)務(wù)工作開展與技術(shù)支撐的背后是專業(yè)型人才的組合。各專業(yè)型人才的高效組合與合理分工、人才的培訓(xùn)與提升、人才管理方式等問題都需要逐步完善。
四、建構(gòu)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集成管理平臺(tái)的策略
1.豐富檔案信息資源。豐富的檔案信息資源是開展檔案文獻(xiàn)編纂工作的前提,也是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質(zhì)量的保證,各檔案部門應(yīng)以實(shí)施《全國檔案事業(yè)發(fā)展“十三五”規(guī)劃綱要》為契機(jī),加大檔案資源收集力度,擴(kuò)大檔案收集范圍,既要豐富資源內(nèi)容,又要注重豐富資源特色,既要滿足當(dāng)前需要,又要兼顧長遠(yuǎn)利用,保證檔案信息資源充分而豐富。
2.加快各區(qū)域信息化建設(shè)的步伐。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集成管理平臺(tái)的構(gòu)建離不開計(jì)算機(jī)技術(shù)、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以及相應(yīng)完善的基礎(chǔ)設(shè)備,只有在信息化技術(shù)設(shè)備齊全的基礎(chǔ)上,才能完善集成管理協(xié)作技術(shù),將各檔案部門的成果通過統(tǒng)一技術(shù)導(dǎo)入到集成管理平臺(tái)當(dāng)中,實(shí)現(xiàn)跨區(qū)域、一體化的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服務(wù)體系。
3.加強(qiáng)檔案人才隊(duì)伍建設(shè)。首先,應(yīng)重視檔案人員繼續(xù)教育和職業(yè)發(fā)展,鼓勵(lì)高等院校、職業(yè)院校和檔案部門深入合作,豐富檔案人才隊(duì)伍的專業(yè)結(jié)構(gòu)。其次,應(yīng)啟動(dòng)全國檔案教育培訓(xùn)網(wǎng)建設(shè),開展遠(yuǎn)程網(wǎng)絡(luò)教育培訓(xùn),建立全國檔案教育培訓(xùn)合作機(jī)制,提升檔案人員的業(yè)務(wù)能力和與時(shí)俱進(jìn)的創(chuàng)新精神。最后,各級(jí)檔案館應(yīng)不斷優(yōu)化人才的管理方式,促進(jìn)檔案人才隊(duì)伍建設(shè)。
4.檔案工作主管機(jī)構(gòu)加強(qiáng)領(lǐng)導(dǎo),統(tǒng)籌規(guī)劃。檔案行政管理部門應(yīng)會(huì)同學(xué)者、檔案從業(yè)人員成立相應(yīng)的研究小組,結(jié)合理論與各地區(qū)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傳播的需要,明確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集成管理平臺(tái)的發(fā)展目標(biāo),加速推進(jìn)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集成管理平臺(tái)的體系建設(shè),制訂有關(guān)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集成管理平臺(tái)構(gòu)建方面的法規(guī)和技術(shù)標(biāo)準(zhǔn),統(tǒng)籌規(guī)劃平臺(tái)的發(fā)展。
社會(huì)轉(zhuǎn)型浪潮下,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集成管理平臺(tái)的構(gòu)建對(duì)于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的傳播、檔案文化的傳播以及提升檔案機(jī)構(gòu)的社會(huì)價(jià)值等方面具有極大現(xiàn)實(shí)意義。社會(huì)公眾對(duì)于信息的需求不斷增加與先進(jìn)技術(shù)的不斷更新也為集成管理平臺(tái)的建構(gòu)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以開放的姿態(tài)來集成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用發(fā)展的眼光實(shí)現(xiàn)人才、資金等全方位的集成,用共享的思維來促進(jìn)集成管理平臺(tái)的建設(shè),就能為檔案文獻(xiàn)編纂成果搭建一個(gè)開放的平臺(tá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