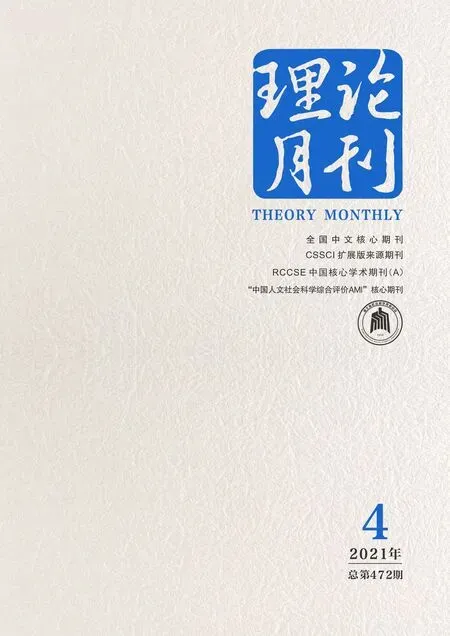整體治理與精細(xì)治理:“十四五”“放管服”改革的雙向進(jìn)路
□李彥婭
(1.南昌大學(xué) 公共管理學(xué)院,江西 南昌330031;2.南昌大學(xué)黨風(fēng)廉政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330031)
一、“十三五”“放管服”改革回顧
“放管服”改革起源于20世紀(jì)末的行政審批改革,李軍鵬認(rèn)為我國(guó)“放管服”改革經(jīng)歷了面向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的“放管服”改革階段、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完善時(shí)期的“放管服”改革階段、市場(chǎng)決定性作用時(shí)期的“放管服”改革階段三個(gè)階段[1](p2936)。到“十二五”末,分散的行政審批改革、監(jiān)管改革和服務(wù)型政府等改革逐漸統(tǒng)籌為“一盤棋”,統(tǒng)稱為“放管服”改革,并成為“十三五”期間政府職能轉(zhuǎn)變和政府改革的重頭戲和先手棋,與營(yíng)造良好的營(yíng)商環(huán)境、發(fā)揮市場(chǎng)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實(shí)現(xiàn)以人民為中心的政府改革初衷相契合。黨的十八大以來,“放管服”改革進(jìn)入全面推進(jìn)階段并取得了巨大成績(jī)。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huì)將“放管服”改革寫入《決定》,并指出深化“放管服”改革是“堅(jiān)持和完善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行政體制”和“政府治理體系”的重要舉措。在國(guó)務(wù)院統(tǒng)一部署下,各地自上而下開展行政審批改革,列舉了權(quán)責(zé)清單;推行審管分離,構(gòu)建政府服務(wù)體系,創(chuàng)新性地推動(dòng)“最多只跑一次”“一次都不跑”“延時(shí)錯(cuò)時(shí)服務(wù)”“代跑代辦”等服務(wù)舉措;按照“雙隨機(jī)、一公開”“誰審批誰負(fù)責(zé),誰主管誰監(jiān)管”的原則降低市場(chǎng)準(zhǔn)入門檻,強(qiáng)化事中事后監(jiān)管;推進(jìn)線上線下服務(wù)與監(jiān)管的融合,搭建了政務(wù)服務(wù)平臺(tái)和部門監(jiān)管平臺(tái)、中介服務(wù)超市等,構(gòu)建“掌上辦”“網(wǎng)上辦”“云監(jiān)管”平臺(tái)和體系;初步運(yùn)用大數(shù)據(jù)技術(shù)、區(qū)塊鏈和人工智能等先進(jìn)技術(shù)打破部門壁壘和數(shù)據(jù)煙囪。諸多創(chuàng)新舉措之下,“放管服”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2020年全球營(yíng)商環(huán)境報(bào)告顯示,中國(guó)營(yíng)商環(huán)境連續(xù)兩年入列全球營(yíng)商環(huán)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經(jīng)濟(jì)體,由2019年的第46位躍居至第31位,躋身全球前40強(qiáng),企業(yè)和人民群眾的獲得感顯著提升。
隨著改革的深入推進(jìn),改革紅利已得到大幅釋放,但是也出現(xiàn)了一些阻滯現(xiàn)象和困境。如對(duì)“放管服”改革認(rèn)識(shí)不到位[2](p3-8);在簡(jiǎn)政放權(quán)方面,缺乏系統(tǒng)規(guī)劃和設(shè)計(jì)、選擇性下放[3](p274-281),權(quán)力下放后基層接不住、用不好[4](p29-36),或使“放管服”變成了“管卡壓”[5];在監(jiān)管過程中監(jiān)管不到位、部門難協(xié)同[6](p13-14);在優(yōu)化服務(wù)方面,無個(gè)性無差異的服務(wù)供給、參差不齊的服務(wù)平臺(tái)和機(jī)制,增加了群眾的困惑,也造成不少資源閑置或浪費(fèi)。這些問題表現(xiàn)為地區(qū)割裂與重復(fù)建設(shè)并存、審批權(quán)空放與變相審批并存、審管分離與數(shù)據(jù)煙囪并存、監(jiān)管碎片化與無執(zhí)法權(quán)執(zhí)法并存、事前審批大大削減與事中事后監(jiān)管服務(wù)未能緊密銜接,使得整個(gè)改革在不少領(lǐng)域呈現(xiàn)出不均衡、不協(xié)調(diào)、破碎化、粗放化、“一刀切”、無特色的特點(diǎn)。“十四五”時(shí)期是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huì)到基本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的開局五年,“放管服”改革也到了必須直面阻滯、啃硬骨頭的階段了。針對(duì)“十三五”期間“放管服”改革的問題,為突破改革瓶頸,總體上看改革應(yīng)在整體治理與精細(xì)治理雙向進(jìn)路上努力。
二、整體治理視野下的“十四五”“放管服”改革推進(jìn)
(一)整體治理內(nèi)涵與研究現(xiàn)狀
整體治理體現(xiàn)了21世紀(jì)以來各國(guó)政府改革與社會(huì)治理的一個(gè)共同趨勢(shì),它是指基于信息社會(huì)下的網(wǎng)絡(luò)互動(dòng)模式,強(qiáng)調(diào)政府內(nèi)部機(jī)構(gòu)和部門的協(xié)同,強(qiáng)調(diào)政府與社會(huì)和市場(chǎng)的合作,以公眾為中心取代“管理主義”的價(jià)值取向,在組織上強(qiáng)調(diào)“按照傳統(tǒng)的自上而下的層級(jí)結(jié)構(gòu)建立縱向的權(quán)力線,并根據(jù)新興的各種網(wǎng)絡(luò)建立橫向的行動(dòng)線”[7](p8-14),強(qiáng)調(diào)中央控制能力和聚合能力,避免過度分權(quán)與碎片化;在技術(shù)上強(qiáng)調(diào)整體主義,將資源、信息與數(shù)據(jù)進(jìn)行整合,在產(chǎn)出上旨在“為在復(fù)雜而且常常分散化的治理中各機(jī)構(gòu)和層次實(shí)現(xiàn)共同的目標(biāo),為越來越有鑒賞能力的公眾提供高質(zhì)量的服務(wù)”[8](p8),這種高質(zhì)量服務(wù)是“無縫隙”“一站式”的。一般認(rèn)為,整體治理思想源于對(duì)新公共管理運(yùn)動(dòng)的揚(yáng)棄(曾令發(fā),2010),不少學(xué)者認(rèn)為整體治理契合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要求(吳瑞堅(jiān),2012),成為一種包含整合、協(xié)同、網(wǎng)絡(luò)化等價(jià)值意蘊(yùn)的新的行政范式(李瑞昌,2009),并成為國(guó)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一個(gè)重要方向。在我國(guó),不少學(xué)者思考2008年開始推進(jìn)的大部制改革邏輯時(shí)將整體治理理論作為改革的理論基礎(chǔ)(常玉紅,2010),從而將它引入到政府改革研究中。2012年以來,在推進(jìn)國(guó)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背景下,隨著大數(shù)據(jù)、區(qū)塊鏈和人工智能等技術(shù)日益廣泛運(yùn)用,旨在去中心、協(xié)同、整合、聯(lián)動(dòng)的整體治理無論是在政府管理還是在社會(huì)治理中都變得更為切實(shí)可行。整體治理理論作為對(duì)信息時(shí)代的挑戰(zhàn)和破解碎片化管理困境的有效路徑,在很多領(lǐng)域得到運(yùn)用,如環(huán)境治理(涂曉芳、黃莉培,2011;蔡嵐,2014)、智慧城市建設(shè)(吳瑞堅(jiān),2012;吳躍文,2011)、地方政府合作(張秋梅,2012)、危機(jī)管理(盛明科、郭群英,2013)、公共安全(胡穎廉,2015)、社會(huì)保障與扶貧(程哲,2018;劉艷,2020;柴佳慧,2019)等。一些學(xué)者就具體領(lǐng)域的整體治理開展了國(guó)際比較研究并嘗試借鑒解決治理碎片化問題中的經(jīng)驗(yàn)(黃莉培,2012;翟云,2019)。黨的十八大以后,隨著“放”“管”“服”逐漸成為中央統(tǒng)一推進(jìn)的政府改革“一盤棋”,整體治理也被運(yùn)用到改革環(huán)節(jié)具體推進(jìn),如蔡延?xùn)|(2017)等人基于整體理論以浙江為例探討省級(jí)政府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碎片化治理,常存平(2012)等將之用于食品安全監(jiān)管體制改革分析中,李勇(2016)探討了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政府服務(wù)的整體政府建設(shè)方向。
盡管目前圍繞整體治理的理論與應(yīng)用的相關(guān)研究日益深入豐富,整體治理甚至被譽(yù)為公共行政的新范式,也有學(xué)者觀察到其在“放管服”改革具體環(huán)節(jié)和領(lǐng)域中的運(yùn)用。然而隨著改革的推進(jìn),越來越多的改革阻滯表現(xiàn)為各個(gè)環(huán)節(jié)不夠銜接,審批監(jiān)管服務(wù)機(jī)構(gòu)與平臺(tái)的碎片化。在新時(shí)代,理論和實(shí)踐都應(yīng)將整合與協(xié)同的范圍擴(kuò)大到“放管服”改革整體推進(jìn)以及政府與市場(chǎng)、政府與社會(huì)的調(diào)整中。
(二)整體治理視野下的“放管服”改革成效與困境
“簡(jiǎn)政放權(quán)、放管結(jié)合、優(yōu)化服務(wù)”本身就是對(duì)政府職能轉(zhuǎn)變和機(jī)構(gòu)調(diào)整相關(guān)改革的一個(gè)整體性的描述。用“放”“管”“服”三個(gè)字分別概括這一系統(tǒng)改革的出發(fā)點(diǎn)、手段和目的,反映了政府在與市場(chǎng)、社會(huì)關(guān)系調(diào)整過程中的整體轉(zhuǎn)型。從我國(guó)改革開放以來的政府改革歷程來看,長(zhǎng)期以來,我國(guó)政府職能調(diào)整與機(jī)構(gòu)改革出現(xiàn)“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迷局,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改革聚焦于政府本身而非與市場(chǎng)和社會(huì)關(guān)系的調(diào)整上。2013年以來的“放管服”改革是對(duì)以往分散式改革的反思。“十三五”期間在推動(dòng)政府改革整體化、平臺(tái)化、協(xié)同化方面取得較大成績(jī),在權(quán)責(zé)梳理、平臺(tái)構(gòu)建與引用先進(jìn)技術(shù)以推進(jìn)改進(jìn)政府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落實(shí)責(zé)任主體、創(chuàng)新服務(wù)模式等方面取得了傲人的成績(jī),但是在推進(jìn)部門之間、平臺(tái)之間、地區(qū)之間、主體之間的協(xié)同與整合等方面仍有較長(zhǎng)的路要走,這對(duì)于為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發(fā)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提供公正、公平、有序的政策環(huán)境,為滿足人們多樣化的需求等方面有至關(guān)重要的意義。
(三)整體治理視野下的“放管服”改革進(jìn)路
1.權(quán)責(zé)清單無縫隙。早在“放管服”改革推行之初,人們就認(rèn)識(shí)到權(quán)責(zé)清單是劃定政府行政邊界、規(guī)范行政機(jī)關(guān)行為的前提。十八屆三中全會(huì)后,地方各級(jí)政府及其工作部門就開始推行權(quán)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quán)力運(yùn)行流程。2017年的《法治政府藍(lán)皮書:中國(guó)法治政府發(fā)展報(bào)告(2017)》中就已提出“搭建全國(guó)性的權(quán)力清單平臺(tái),對(duì)各地方政府的權(quán)力清單運(yùn)行平臺(tái)進(jìn)行規(guī)范和統(tǒng)一”,提出權(quán)力清單頂層設(shè)計(jì)、由國(guó)務(wù)院甚至人大自上而下編制,既是政府依法行政、公共服務(wù)的保障,也是公民辦事、監(jiān)督的依據(jù)。但是從實(shí)踐操作層面看,目前權(quán)力清單依然是行政機(jī)關(guān)內(nèi)部列出的。在這個(gè)過程中國(guó)務(wù)院及各部門雖然從整體上劃定了權(quán)力類型和大致范圍,但是具體事項(xiàng)較多,各個(gè)地區(qū)、各個(gè)層次、各個(gè)部門在本地區(qū)、本層級(jí)、本部門的權(quán)力清單似乎都合理合法,但是相互對(duì)照之下,彼此權(quán)力名稱、權(quán)力范圍、權(quán)力類型、具體權(quán)力屬性差異較大,這直接為跨地域、跨層級(jí)、跨部門的權(quán)力歸屬、政府監(jiān)管、社會(huì)監(jiān)督帶來了權(quán)責(zé)難題。可以說從權(quán)責(zé)清單的角度來看,部門之間、層級(jí)之間、地區(qū)之間的這種權(quán)責(zé)清單的整合與統(tǒng)一是“十四五”期間“放管服”改革整體化進(jìn)路上的首要任務(wù),也是改革在其他環(huán)節(jié)中走向整體治理的基礎(chǔ)。
2.“審”“管”“服”不脫節(jié)。“十三五”期間,各地“放管服”改革秉著“審管分離、放管結(jié)合”“誰審批誰負(fù)責(zé)、誰主管誰監(jiān)管”的基本原則對(duì)行政審批部門、行政執(zhí)法部門、政務(wù)服務(wù)部門進(jìn)行了機(jī)構(gòu)改革和調(diào)整,三者之間權(quán)責(zé)劃分在不同地區(qū)形成了不同模式。有些地區(qū)采用政務(wù)服務(wù)部門囊括行政審批業(yè)務(wù);有些地市專門成立行政審批局主要負(fù)責(zé)行政許可事項(xiàng),其他政務(wù)服務(wù)事項(xiàng)仍歸各部門;有些地區(qū)設(shè)立綜合行政執(zhí)法局,專門對(duì)接審批開展相應(yīng)項(xiàng)目監(jiān)管、執(zhí)法;有些地區(qū)推動(dòng)線上線下審管與服務(wù)融合,將信息中心、大數(shù)據(jù)服務(wù)等機(jī)構(gòu)與政務(wù)服務(wù)、行政審批或綜合執(zhí)法部門并列。這幾種模式有時(shí)在同一省甚至同一市并存。我國(guó)地區(qū)發(fā)展不平衡、各地改革背景和條件有異,出現(xiàn)不同模式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為了避免出現(xiàn)某一層次某一部門承接不了下放權(quán)限或責(zé)任過重難以擔(dān)負(fù)或“審”“管”“服”脫節(jié),這種差異性應(yīng)建立在兼容性、適應(yīng)性和動(dòng)態(tài)性的基礎(chǔ)上。這要求條塊審管權(quán)限緊密對(duì)接,條條和塊塊都要根據(jù)改革后的行政職能和行政權(quán)力進(jìn)行機(jī)構(gòu)設(shè)置和編制。如簡(jiǎn)政放權(quán)情況下,省部級(jí)的行政審批和直接社會(huì)服務(wù)職能大大削減。地市層級(jí)的行政審批職能和社會(huì)服務(wù)職能往往集中在行政審批部門或政務(wù)服務(wù)中心,而這兩個(gè)部門在地市相應(yīng)編制有限且呈壓縮態(tài)勢(shì),不堪重負(fù)。最基層的鄉(xiāng)鎮(zhèn)街道往往在很多領(lǐng)域并沒有執(zhí)法權(quán)限和執(zhí)法軟硬件與人才儲(chǔ)備,因而基層便民中心應(yīng)以高頻簡(jiǎn)易即辦許可和服務(wù)事項(xiàng)為主,不宜承擔(dān)復(fù)雜審批事項(xiàng)和監(jiān)管事項(xiàng)。總之,“十四五”期間審管服機(jī)構(gòu)設(shè)置與編制都應(yīng)因地制宜、動(dòng)態(tài)調(diào)整以使權(quán)限、責(zé)任落地。
3.監(jiān)管綜合化。“放管服”改革在行政審批方面確有諸多創(chuàng)舉,如承諾制的推進(jìn)有助于實(shí)現(xiàn)企業(yè)群眾“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都不跑”,但審批之后不少地區(qū)并未設(shè)立專門的綜合執(zhí)法部門,審管互動(dòng)與執(zhí)法監(jiān)管及相應(yīng)的社會(huì)監(jiān)督薄弱;在事中事后監(jiān)管方面,如何達(dá)到有效監(jiān)管的同時(shí)避免“擾民”、減輕基層工作人員的工作量等需要制度創(chuàng)新。各個(gè)監(jiān)管部門在事中事后監(jiān)管中應(yīng)推進(jìn)項(xiàng)目型監(jiān)管與職能監(jiān)管相結(jié)合,同類項(xiàng)目合并執(zhí)行,推進(jìn)綜合執(zhí)法,減少對(duì)同一組織或事項(xiàng)的多次執(zhí)法。如一民辦教育機(jī)構(gòu),在經(jīng)審批允許成立后,對(duì)其監(jiān)管涉及包括財(cái)務(wù)、消防、食品安全、教育等相關(guān)部門職責(zé),以往的監(jiān)管模式是圍繞職能部門開展,即一個(gè)職能部門根據(jù)自身的工作安排和實(shí)際情況一次性監(jiān)管若干類似教育機(jī)構(gòu)。類似監(jiān)管以后應(yīng)轉(zhuǎn)向多個(gè)部門圍繞該教育機(jī)構(gòu)或該類型行政審批事項(xiàng)提供一次性的聯(lián)合監(jiān)管或執(zhí)法,且部門之間及時(shí)即時(shí)互通監(jiān)管信息,實(shí)現(xiàn)塊塊之間的融通與整體治理。強(qiáng)化信用監(jiān)管平臺(tái)在各領(lǐng)域的運(yùn)用和共享互動(dòng),深入推進(jìn)個(gè)人誠(chéng)信體系建設(shè),借助不斷健全的信用監(jiān)管體系讓數(shù)據(jù)跑路,推動(dòng)審管銜接、監(jiān)管綜合化。
4.平臺(tái)統(tǒng)一化。“十三五”期間各級(jí)各地紛紛通過政府采購(gòu)搭建了各種辦事平臺(tái)、審管平臺(tái)、監(jiān)督系統(tǒng)。幾乎所有政府部門都構(gòu)建了自己的電子政務(wù)網(wǎng)站,不少省市構(gòu)建了中介服務(wù)網(wǎng)上超市,一些行政審批部門為便于審管結(jié)合構(gòu)建了審管互動(dòng)平臺(tái)及時(shí)推送審批信息督促職能部門監(jiān)管,各級(jí)政務(wù)服務(wù)部門添置了“好差評(píng)”系統(tǒng),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不少地方充分挖掘健康碼功能并將之與相關(guān)移動(dòng)政務(wù)平臺(tái)相結(jié)合以推進(jìn)全省通辦甚至跨省通辦。這些平臺(tái)的引入本意在于提高管理和服務(wù)效率,使政府行為更公平公開,使改革順利開展。然而截至“十三五”末,各地的平臺(tái)建設(shè)五花八門,各級(jí)各部門的平臺(tái)及數(shù)據(jù)彼此不兼容難以共享,呈現(xiàn)較為嚴(yán)重的碎片化的局面。無論對(duì)于公民還是政府工作人員來說,最能讓他們感受到改革效果的應(yīng)該是辦事更便捷了、管理更有效了、服務(wù)更貼心了。碎片化的平臺(tái)建設(shè)和服務(wù)一方面徒增民眾辦事的選擇困惑進(jìn)而導(dǎo)致民眾“不愿用”“不會(huì)用”,另一方面使工作人員重復(fù)勞動(dòng),對(duì)新制度新平臺(tái)產(chǎn)生排斥。如中介服務(wù)超市,可能存在市級(jí)超市、省級(jí)超市、部門超市并存的情況;又如“好差評(píng)”系統(tǒng)往往置于各地政務(wù)服務(wù)部門下,各個(gè)職能部門往往有自己的服務(wù)評(píng)價(jià)系統(tǒng),為了使“好差評(píng)”制度落實(shí),就需要各職能部門將政務(wù)部門傳送過來的“好差評(píng)”結(jié)果再次錄入,增加了工作量。“十四五”期間,推進(jìn)各種各級(jí)平臺(tái)、系統(tǒng)、設(shè)備的統(tǒng)一不僅是減少資源浪費(fèi)、集約使用財(cái)政資金的重要途徑,也是使“放管服”改革獲得實(shí)質(zhì)性成效、提升群眾獲得感的突破點(diǎn)。
5.硬件軟件的標(biāo)準(zhǔn)化。“十三五”期間的“放管服”改革是一個(gè)各種改革創(chuàng)新舉措眾彩紛呈、政府服務(wù)模式猶如雨后春筍不斷產(chǎn)生、軟硬件平臺(tái)紛紛建設(shè)的階段,展現(xiàn)了各級(jí)各地各部門落實(shí)和推進(jìn)改革的努力,政府管理和服務(wù)質(zhì)量、效率、作風(fēng)大有改觀,企業(yè)群眾的滿意度顯著提升。但是,信息大爆炸的時(shí)代,如果缺乏統(tǒng)一的標(biāo)志、規(guī)范的禮儀、共同的話語(yǔ)與溝通符號(hào)——標(biāo)準(zhǔn)化的軟硬件,就意味著“放管服”改革的相應(yīng)成果不具有顯著的辨識(shí)度和共通性,相關(guān)信息和流程也就難以成為“常識(shí)”和“慣性”而僅僅是短時(shí)記憶并消弭在信息海洋中,改革成效難以被人們持續(xù)性感知,難以沉淀為制度。因此,“十四五”期間,推進(jìn)“放管服”改革的整體進(jìn)路必然要求推進(jìn)軟硬件的標(biāo)準(zhǔn)化。這包括政務(wù)服務(wù)大廳標(biāo)準(zhǔn)化建設(shè),使用至少是全省統(tǒng)一的政務(wù)服務(wù)標(biāo)識(shí)。統(tǒng)一名稱、統(tǒng)一LOGO、統(tǒng)一著裝、統(tǒng)一流程、規(guī)范禮儀,實(shí)現(xiàn)功能標(biāo)準(zhǔn)化、布局標(biāo)準(zhǔn)化、服務(wù)標(biāo)準(zhǔn)化。
三、精細(xì)治理視角下的“十四五”“放管服”改革推進(jìn)
(一)精細(xì)治理內(nèi)涵與研究現(xiàn)狀
精細(xì)治理由精細(xì)化管理引申發(fā)展而來。泰勒在《科學(xué)管理原理》中最早提出精細(xì)化管理概念,后來這一思想在日本企業(yè)管理中發(fā)展成為“一種管理理念和管理技術(shù),通過規(guī)則的系統(tǒng)化和細(xì)化,運(yùn)用程序化、標(biāo)準(zhǔn)化、數(shù)據(jù)化和信息化的手段,使組織管理各單元精確、高效、協(xié)同和持續(xù)運(yùn)行”[9](p116),相應(yīng)的改革包括流程再造與標(biāo)準(zhǔn)化、質(zhì)量管理、員工參與等,這一思想后來被廣泛運(yùn)用于企業(yè)管理(張廣安,2009)、醫(yī)護(hù)管理(趙莉麗等,2006;蔣聯(lián)群、朱迎陽(yáng),2007)、教育培訓(xùn)(李強(qiáng)等,2010)、建筑工程(羅洋,2010),突出對(duì)包括人(王麗靜,2011)、財(cái)(巫升斌,2009)、物(曲桂賢、張劍飛,2006)開展精細(xì)管理。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隨著強(qiáng)調(diào)“顧客導(dǎo)向”“績(jī)效責(zé)任”的政府再造運(yùn)動(dòng)的推進(jìn),與改革相契合的精細(xì)管理的思想從企業(yè)管理逐漸被引入到公共部門管理(麻寶斌、李輝,2009)與公共服務(wù)供給(何軍,2007)中。在這個(gè)過程中,伴隨社會(huì)分工的細(xì)化、人們需求的多樣化、數(shù)字治理模式的興起,精細(xì)化管理漸漸演變?yōu)榫?xì)治理,管理思想轉(zhuǎn)向更多地強(qiáng)調(diào)基于需求導(dǎo)向的共治網(wǎng)絡(luò)(王陽(yáng),2016;蔣源,2015)。相比精細(xì)化管理,精細(xì)治理在管理規(guī)范化、作業(yè)精深化的基礎(chǔ)上,更突出個(gè)性化與人性化[10](p15-16)。
總體上,精細(xì)管理理念運(yùn)用從私人管理到公共部門、從精細(xì)管理到精細(xì)治理,它們強(qiáng)調(diào)的“人性化、精準(zhǔn)化、差異化”成了包括“放管服”改革在內(nèi)的公共行政發(fā)展方向。李剛強(qiáng)認(rèn)為近年來政府改革目標(biāo)中突出精細(xì)治理是由于十九大以后對(duì)“以人民為中心”的價(jià)值強(qiáng)調(diào)使然[11](p15-20+37)。盡管如此,對(duì)于改革中通過哪些具體途徑和路線來實(shí)現(xiàn)政府管理與公共服務(wù)的精細(xì)化,相關(guān)探討卻較為零散。其中,汪智漢、宋世明對(duì)我國(guó)政府職能精細(xì)化治理與流程再造的主要內(nèi)容和路徑選擇開展了探討[12](p22-26),此類研究為“十三五”期間的“放管服”權(quán)責(zé)清單與政務(wù)流程梳理提供了理論指導(dǎo)。但如前所述,隨著數(shù)智政府的打造、改革的深入推進(jìn),改革在精細(xì)治理的推進(jìn)路徑上還有更廣闊的探索空間。
(二)精細(xì)治理視野下的“放管服”改革成效與困境
如果說“十三五”期間的“放管服”改革主要舉措包括梳理權(quán)責(zé)清單、流程再造、推進(jìn)審管分離與運(yùn)用先進(jìn)技術(shù)搭建各種機(jī)制平臺(tái),以提升政府管理與服務(wù)標(biāo)準(zhǔn)化、網(wǎng)絡(luò)化、智能化,那么“十四五”期間的“放管服”改革的推進(jìn)方向就應(yīng)更多關(guān)注管理過程中的人性化、差異化、精準(zhǔn)化,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從各種機(jī)構(gòu)、平臺(tái)、制度“有沒有”“有多少”到企業(yè)群眾覺得“好不好”“適合不”轉(zhuǎn)變,這也是避免各種精細(xì)化改革舉措走向形式主義、“作秀式”行政的關(guān)鍵所在。
(三)精細(xì)治理視野下的“放管服”改革進(jìn)路
具體來說,“十四五”期間“放管服”改革的精細(xì)化進(jìn)路包括:
1.需求導(dǎo)向,統(tǒng)一推進(jìn)與地區(qū)部門差異相結(jié)合。運(yùn)用大數(shù)據(jù)深入分析群眾企業(yè)的需求,根據(jù)需求進(jìn)行差異化的機(jī)構(gòu)、設(shè)備、平臺(tái)頁(yè)面設(shè)計(jì)等。結(jié)合區(qū)域、部門特征與社會(huì)主體的需求,進(jìn)行精細(xì)化配置。我國(guó)地區(qū)發(fā)展不平衡、人口分布不均勻,有著世界上最為繁華的超級(jí)大都市,也有著日漸凋敝的空心村。目前基層行政區(qū)劃主要按照面積和地勢(shì)來劃分,相應(yīng)的機(jī)構(gòu)、人員、設(shè)備等軟硬件也按行政區(qū)劃來配備。這就造成一方面,在一些城市,僅僅在政務(wù)服務(wù)大廳設(shè)置便民軟硬件、改進(jìn)辦事流程等改變不了高峰時(shí)期辦事排隊(duì)的狀況;另一方面,在一些人口外流嚴(yán)重鄉(xiāng)鎮(zhèn),便民服務(wù)中心或者沒有足夠人手辦事,或者沒有足夠來辦事的人,或者設(shè)置了一體機(jī)卻由于鄉(xiāng)村留守人員不懂用、不會(huì)用而閑置浪費(fèi)。針對(duì)類似情況,在“十四五”期間,“放管服”改革精細(xì)化的重要方向是,運(yùn)用大數(shù)據(jù)等進(jìn)行人群需求計(jì)算,精準(zhǔn)投放推送相應(yīng)的軟硬件。在城市人流量大的商圈、交通站臺(tái)、大學(xué)城與住宅區(qū)推進(jìn)24小時(shí)便民服務(wù)自助終端和服務(wù)專區(qū)建設(shè),并根據(jù)場(chǎng)景與地點(diǎn)的不同進(jìn)行差異化硬件配置與智能服務(wù)配置,推進(jìn)就近辦、馬上辦、網(wǎng)上辦、隨時(shí)辦。深化與國(guó)有商業(yè)銀行、郵政公司等機(jī)構(gòu)合作,充分發(fā)揮金融、郵政機(jī)構(gòu)網(wǎng)點(diǎn)多、自助終端成熟優(yōu)勢(shì),打造多級(jí)聯(lián)動(dòng)的“自助服務(wù)圈”“就近辦事圈”。對(duì)于偏遠(yuǎn)地區(qū)和人口流出為主的空心地區(qū),采用設(shè)置本地高頻事項(xiàng)一體機(jī)的模式機(jī)動(dòng)設(shè)置,并大力推進(jìn)“幫辦”“代辦”業(yè)務(wù)。
2.關(guān)照弱勢(shì)群體,科學(xué)化與人性化相結(jié)合。一方面,從全國(guó)范圍來看,2020年11月23日,我國(guó)832個(gè)國(guó)家級(jí)貧困縣全部脫貧。但是,在成就的背后我們看到仍然存在各種弱勢(shì)群體,他們或者經(jīng)濟(jì)狀況不佳或者在社會(huì)中被邊緣化或者存在身心殘障或者遭遇天災(zāi)人禍。2020年初我國(guó)經(jīng)濟(jì)遭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創(chuàng),失業(yè)率猛增。在此背景下,李克強(qiáng)總理在多個(gè)場(chǎng)合提出給地?cái)偨?jīng)濟(jì)松綁,稱其為“人間煙火氣”,很多城市監(jiān)管對(duì)地?cái)偨?jīng)濟(jì)由“驅(qū)趕型”向“規(guī)勸型”“服務(wù)型”轉(zhuǎn)變,回應(yīng)性、包容性的監(jiān)管和服務(wù)已見端倪。另一方面,“十三五”末智慧城市建設(shè)和智慧社區(qū)建設(shè)方興未艾,“網(wǎng)上辦”“掌上辦”在各地各部門開展得如火如荼,政務(wù)服務(wù)便民服務(wù)中心深入各鄉(xiāng)鎮(zhèn),不少地區(qū)政務(wù)服務(wù)大廳引入了各種服務(wù)一體機(jī)、智能導(dǎo)引機(jī)器人并將之推廣到社區(qū),這些新技術(shù)、新設(shè)施的啟用確實(shí)契合了信息社會(huì)下數(shù)字治理的基本要求。但是,自從互聯(lián)網(wǎng)誕生以來,數(shù)字鴻溝日益深長(zhǎng);2010年以來,智能設(shè)備的日漸普及并未抹平數(shù)字門檻。可以預(yù)見,未來的各種不確定性事件、非線性危機(jī)仍然會(huì)層出不窮。“十四五”期間的“放管服”改革也應(yīng)更為人性化,在推進(jìn)智能政府、數(shù)字政府、城市大腦建設(shè)等的同時(shí),也要考慮數(shù)字門檻另一側(cè)的弱勢(shì)群體。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wù)不能搞“一刀切”,對(duì)信息時(shí)代、智能時(shí)代的弱勢(shì)群體,在進(jìn)行幫助和宣傳的同時(shí)也應(yīng)保留線下特別通道或人工服務(wù)與傳統(tǒng)途徑。
3.以智慧政務(wù)為契機(jī),推進(jìn)智能化與個(gè)性化相結(jié)合。推進(jìn)各種平臺(tái)、終端、大廳服務(wù)的整合。推動(dòng)各種途徑方式的整合,建設(shè)統(tǒng)一身份認(rèn)證模塊,實(shí)現(xiàn)各種智能終端之間的數(shù)據(jù)對(duì)接共享,真正實(shí)現(xiàn)各種平臺(tái)、終端、窗口兼容,推進(jìn)各項(xiàng)監(jiān)管和服務(wù)的跨部門、跨層級(jí)、跨區(qū)域的通辦、聯(lián)辦、合辦,真正做到群眾少跑、工作人員也少跑的“數(shù)據(jù)跑路”。根據(jù)事項(xiàng)類型,對(duì)于高頻簡(jiǎn)易事項(xiàng),一次不跑或承諾制;簡(jiǎn)易事項(xiàng)即時(shí)辦,實(shí)現(xiàn)對(duì)人工服務(wù)的分流,使政務(wù)服務(wù)人員集中于復(fù)雜事項(xiàng)或特殊事項(xiàng)的審批與服務(wù)。借助區(qū)塊鏈技術(shù),擴(kuò)展移動(dòng)監(jiān)管與服務(wù)平臺(tái)等平臺(tái)服務(wù)功能,完善政務(wù)服務(wù)大廳智能化建設(shè),將更多部門政務(wù)服務(wù)一體機(jī)納入政務(wù)服務(wù)自助廳中,促進(jìn)一體機(jī)的更新?lián)Q代,推進(jìn)一機(jī)通辦、部門聯(lián)動(dòng)、智能跳轉(zhuǎn)、個(gè)性服務(wù);在智能服務(wù)方面,在智能迎賓、政務(wù)咨詢、引領(lǐng)導(dǎo)覽、數(shù)據(jù)分析基礎(chǔ)上,大量增加智能互動(dòng)與簡(jiǎn)易審批模塊,提供訂單式精準(zhǔn)服務(wù)。擴(kuò)大宣傳教育,實(shí)現(xiàn)能自助辦盡量自助辦,不能或不愿自助辦工作人員幫忙辦的多樣化的服務(wù)供給。
四、“整體治理”與“精細(xì)治理”的關(guān)系
從字面上看,“十四五”“放管服”改革中的“整體治理”與“精細(xì)治理”似乎存在悖論,如一體化的頂層設(shè)計(jì)梳理與地區(qū)部門自主性差異性之間,平臺(tái)整合標(biāo)準(zhǔn)化規(guī)范化與監(jiān)管服務(wù)供給模式多樣化之間,政府內(nèi)部層級(jí)效率責(zé)任機(jī)制與需求導(dǎo)向民主回應(yīng)價(jià)值之間似乎難以兼顧。但是結(jié)合“十四五”改革背景、細(xì)致分析雙向進(jìn)路要求,可以發(fā)現(xiàn)二者之間并非是背道而馳而是相輔相成的。
(一)整體治理與精細(xì)治理是“十四五”所處時(shí)代背景下政府改革的共同要求
一是整體治理與精細(xì)治理都是在對(duì)已有改革暴露出來的不足和問題進(jìn)行總結(jié)反思過程中補(bǔ)齊改革短板、糾正改革偏差中的一種政策調(diào)適。二是“十四五”是國(guó)家社會(huì)發(fā)展的重要交匯點(diǎn),信息社會(huì)為“放管服”改革整體推進(jìn)提供了各種可能性和機(jī)遇,應(yīng)對(duì)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的漸增不確定性和非線性危機(jī)使“放管服”改革在整體推進(jìn)時(shí)必須具有靈活性、多樣性。三是這一時(shí)期政府也必須滿足人們對(duì)包括民主、富強(qiáng)、和諧在內(nèi)等基本價(jià)值追求的美好生活需求,實(shí)現(xiàn)各個(gè)環(huán)節(jié)的銜接和協(xié)同,實(shí)現(xiàn)治理的科學(xué)化,同時(shí)政府又必須傾聽所有聲音,接受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下的公開監(jiān)督,追求治理的人本化、個(gè)性化。
(二)整體治理與精細(xì)治理之間是互為條件、相互促進(jìn)的
一方面,整體治理依賴改革中每一個(gè)元素、每個(gè)環(huán)節(jié)的精細(xì)化。無縫隙的權(quán)責(zé)清單、全過程的監(jiān)管服務(wù)、標(biāo)準(zhǔn)化的軟硬件設(shè)施、網(wǎng)絡(luò)式的多元主體互動(dòng)與協(xié)同由每個(gè)節(jié)點(diǎn)、每個(gè)平臺(tái)、每個(gè)組織匯聚聯(lián)結(jié)而成。整體治理的關(guān)鍵就是借助先進(jìn)技術(shù)的融合運(yùn)用進(jìn)行“TOP-DOWN”的頂層推進(jìn),突破各個(gè)平臺(tái)、各個(gè)部門之間的壁壘,實(shí)現(xiàn)數(shù)據(jù)共享、多元互動(dòng)與協(xié)同治理。另一方面,“放管服”改革的精細(xì)治理進(jìn)路體現(xiàn)了新時(shí)代下政府行政價(jià)值從“執(zhí)行效率”到“社會(huì)效率”、行政方式由“科學(xué)管理”到“人本管理”、監(jiān)督主體從“層級(jí)監(jiān)督”到“社會(huì)監(jiān)督”、評(píng)估標(biāo)準(zhǔn)從“領(lǐng)導(dǎo)滿意”到“人民滿意”的轉(zhuǎn)變。政府監(jiān)管服務(wù)平臺(tái)“好不好”的前提是“有沒有”,是在“有”而且是有比較完整、健全的機(jī)制體制平臺(tái)模式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細(xì)化,進(jìn)一步人性化、個(gè)性化的。
五、“十四五”期間“放管服”改革雙向進(jìn)路的可行性與支撐
(一)黨和中央政府的頂層設(shè)計(jì)與系統(tǒng)推進(jìn)
繼十九屆四中全會(huì)將“放管服”改革寫入全會(huì)《決定》后,2020年十九屆五中全會(huì)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ān)于制定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發(fā)展第十四個(gè)五年規(guī)劃和二〇三五年遠(yuǎn)景目標(biāo)的建議》,建議中第24條專門圍繞“放管服”改革指出:“十四五”時(shí)期政府改革應(yīng)“加快轉(zhuǎn)變政府職能。建設(shè)職責(zé)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深化簡(jiǎn)政放權(quán)、放管結(jié)合、優(yōu)化服務(wù)改革,全面實(shí)行政府權(quán)責(zé)清單制度。持續(xù)優(yōu)化市場(chǎng)化、法治化、國(guó)際化營(yíng)商環(huán)境。實(shí)施涉企經(jīng)營(yíng)許可事項(xiàng)清單管理,加強(qiáng)事中事后監(jiān)管,對(duì)新產(chǎn)業(yè)新業(yè)態(tài)實(shí)行包容審慎監(jiān)管。推進(jìn)政務(wù)服務(wù)標(biāo)準(zhǔn)化、規(guī)范化、便利化,深化政務(wù)公開。深化行業(yè)協(xié)會(huì)、商會(huì)和中介機(jī)構(gòu)改革。”十九屆五中全會(huì)是處于“兩個(gè)一百年”歷史交匯期的中國(guó)在遇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召開的,充分展示黨和國(guó)家動(dòng)員群眾、團(tuán)結(jié)人民實(shí)現(xiàn)民族復(fù)興和人民幸福的堅(jiān)定決心和信心,“十四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huì)后的開局五年也是二〇三五遠(yuǎn)景目標(biāo)的第一個(gè)五年,有了黨和中央政府對(duì)“放管服”改革的頂層設(shè)計(jì)和系統(tǒng)推進(jìn),促使政府職能轉(zhuǎn)變、提升政府整體治理和精細(xì)治理能力就有了方向和動(dòng)力。
(二)新時(shí)代不斷推進(jìn)的技術(shù)融合與數(shù)字政府構(gòu)建
近年來,我國(guó)數(shù)字技術(shù)與實(shí)體經(jīng)濟(jì)加速融合,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數(shù)字化、網(wǎng)絡(luò)化、智能化水平不斷提升。數(shù)字經(jīng)濟(jì)對(duì)GDP增長(zhǎng)的貢獻(xiàn)已超六成①2020年11月20日廈門國(guó)家會(huì)計(jì)學(xué)院院長(zhǎng)黃世忠在美國(guó)會(huì)計(jì)師協(xié)會(huì)舉辦的第七屆管理會(huì)計(jì)高峰論壇上的講話。。前瞻產(chǎn)業(yè)研究院日前發(fā)布的《2020年中國(guó)數(shù)字經(jīng)濟(jì)發(fā)展報(bào)告》(以下簡(jiǎn)稱《報(bào)告》)顯示,當(dāng)前,我國(guó)數(shù)字經(jīng)濟(jì)發(fā)展已進(jìn)入成熟期,數(shù)字經(jīng)濟(j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升,由2005年的14.2%提升至2019年的36.2%。以人工智能、移動(dòng)通信、工業(yè)互聯(lián)網(wǎng)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shù)加速突破,充分運(yùn)用大數(shù)據(jù)、區(qū)塊鏈、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量子技術(shù)等技術(shù)建設(shè)數(shù)字政府,打破部門數(shù)據(jù)壁壘,推動(dòng)數(shù)據(jù)共享開放,為“十四五”各地區(qū)、各部門、各層級(jí)社會(huì)主體與政府之間的協(xié)同與合作,實(shí)現(xiàn)整體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技術(shù)支撐。同時(shí)各種智能化設(shè)備、友好的人機(jī)交互界面、VR技術(shù)、全息與3D打印技術(shù)等融合在各領(lǐng)域、各環(huán)節(jié)的充分運(yùn)用又能更好地實(shí)現(xiàn)監(jiān)管和服務(wù)的個(gè)性化與人性化,為實(shí)現(xiàn)精細(xì)化治理提供堅(jiān)實(shí)的技術(shù)保障。
(三)以人民為中心的政務(wù)服務(wù)與監(jiān)管治理評(píng)價(jià)機(jī)制
“放管服”改革是在政府角色重新定位,調(diào)整政府與市場(chǎng)和社會(huì)的關(guān)系中起步的。新時(shí)代改革要在整體治理和精細(xì)治理上取得真正的突破,整合各種資源、融合各種技術(shù)、協(xié)同各方力量,首先就是要突破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真正將人民的整體利益、長(zhǎng)遠(yuǎn)利益與需求放在核心的位置。既要朝上看以貫徹黨和中央政府的政策、完成上級(jí)交代的任務(wù)和工作,又要向下看以回應(yīng)民眾的呼聲和監(jiān)督。這種轉(zhuǎn)向已經(jīng)在“十三五”末變得日趨明朗:習(xí)近平總書記在多個(gè)場(chǎng)合強(qiáng)調(diào)“十四五”規(guī)劃要“問政于民”,2019年以來政務(wù)服務(wù)“好差評(píng)”制度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推行,《國(guó)務(wù)院關(guān)于切實(shí)解決老年人運(yùn)用智能技術(shù)困難實(shí)施方案的通知》等關(guān)照改革中某一類弱勢(shì)群體政策火速落地……諸此種種都可以看出黨和中央政府在推動(dòng)這種轉(zhuǎn)變中的魄力和努力。當(dāng)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作為一種頂層要求和上級(jí)任務(wù)來實(shí)施時(shí),對(duì)于各級(jí)政府及其部門來說,就意味著強(qiáng)制性地將層級(jí)責(zé)任與民主責(zé)任統(tǒng)一起來:在制定政策和梳理權(quán)責(zé)清單時(shí)傾聽民意;在政務(wù)服務(wù)和市場(chǎng)監(jiān)管、社會(huì)治理中回應(yīng)民眾;推進(jìn)政府公開接受民眾監(jiān)督……唯有經(jīng)過如此的轉(zhuǎn)型,改革才能提升政府在新時(shí)代的公信力和認(rèn)同度。因此,正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價(jià)值調(diào)整倒逼各級(jí)政府及其部門“放管服”改革沿著整體治理與精細(xì)治理的雙向進(jìn)路前行。
六、結(jié)語(yǔ)
從關(guān)注政府內(nèi)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的大部制改革到強(qiáng)調(diào)政府與市場(chǎng)、政府與社會(huì)關(guān)系調(diào)整中轉(zhuǎn)換政府角色與政府職能,從行政審批改革、行政監(jiān)管體制改革與服務(wù)型政府建設(shè)分步進(jìn)行到“十二五”以來統(tǒng)一推進(jìn)全盤布局,從注重標(biāo)準(zhǔn)與流程再造到“十三五”以來強(qiáng)調(diào)公民滿意度和民眾參與、技術(shù)融合,我國(guó)政府改革整體化和精細(xì)化的趨勢(shì)日益明朗。在歷史交匯的新時(shí)代,“放管服”改革應(yīng)沿著“整體治理”與“精細(xì)治理”的具體路徑持續(xù)推進(jìn),以突破改革瓶頸、進(jìn)一步釋放改革效能,實(shí)現(xiàn)優(yōu)化營(yíng)商環(huán)境,發(fā)揮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滿足人們對(duì)美好生活需要的改革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