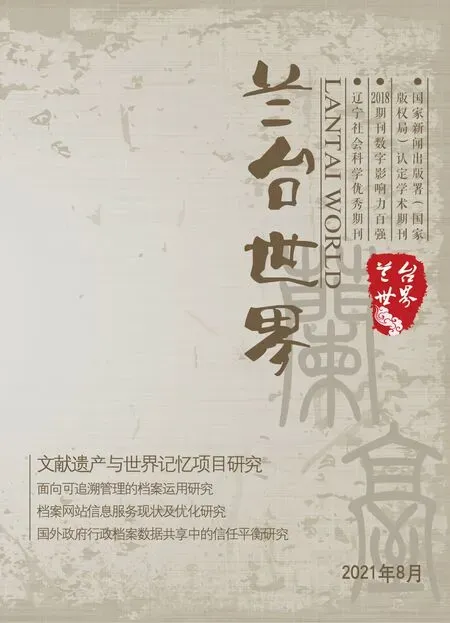《黑圖檔·咸豐朝》所見清代盛京祭祀制度探微
藥正陽
“國家典制,祭祀為重。”[1]祭祀不但位列五禮之首,而且被認為是與軍事活動同等重要的國之大事,是現實世界人們與鬼神進行交流的中介。人們舉行祭祀活動的目的是多種多樣的,其可以概括為三類: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即祈求、報答和攘災。但在早期社會中,祭祀并不是一種規范的制度,只是人們驅災避禍的一種手段,但隨著社會的進步、朝代的更迭,祭祀的地位逐漸提升,被上升為一種制度、一種規范,成為統治階級進行精神統治的工具。《黑圖檔》是清代盛京內務府形成的公文抄存檔案,是盛京內務府同北京總管內務府、北京六部等衙門之間,以及同盛京將軍衙門、奉天府、盛京五部等衙門間往來公文原件抄錄后形成的[2]。《黑圖檔·咸豐朝》收錄咸豐元年(1851)至咸豐十一年(1861)京來檔 6 卷、京行檔 6 卷、部來檔 24 卷、部行檔24 卷,合計60 卷,檔案原件滿漢文各半,每件檔案都編譯了中文目錄,這為學術界研究盛京內務府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史料[3]。它包括了關于祭祀制度方面的內容,這些檔案很好地彌補了咸豐時期盛京地區關于祭祀制度相關內容的空白,為我國清朝盛京祭祀制度的研究創造了條件。
一、祭祀禮儀制度
祭祀是一種崇拜祖先、崇拜自然的禮儀,祭祀者對于祖先等情感的表達要借助一定的物質手段與特定的符號以及程序才能夠實現。因此,在長期的祭祀活動中,就逐漸形成了一些有關祭樂以及紀律等方面的程式及其規則。
1.祭樂制度。我國自古以來就非常重視禮樂之間的關系,禮儀活動往往會伴之以樂,樂舞逐漸成為中國古代禮樂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等級、不同形式的禮儀活動有不同的樂曲與之相配,這一習俗延續至清朝時期的盛京地區。
如《盛京將軍衙門為關帝升入中祀樂章添入禮節事》中記載:“祠祭司案呈前經本部會奏關帝升入中祀遣官事宜一折并禮部條款夾片二件,於具奏后業經知照在案。今據翰林院將樂章擇擬送部,相應抄錄樂章,通行各直省添入禮節遵照辦理可也。”[4]這則檔案體現了在關帝進入中祀后,較之前的祭祀樂章及樂器陳設都有了極大的調整,這是清朝實行森嚴等級制度在祭祀禮儀方面的一個體現。又如《盛京將軍衙門為抄送關帝升祀樂章新譜事咨盛京內務府》中記載:“又準閩浙兩廣各總督咨請示,覆各等因前來查樂章新譜制自太常山東,未折他省可知,現經本部重加校正音律,既協字句無訛相應通行直省文武各衙門,即遵照此次□□定本轉傳所屬敬謹將事可也。須至咨者等因前來相應照依原咨樂章新譜抄單,咨行盛京內務府可也。”[5]這表明在關帝升入中祀之后,對于樂章要進行修改并先后與山東、閩浙總督請示樂譜,最后于本部校定,體現了咸豐時期盛京地區祭祀樂曲的修訂不僅要與祭祀對象的尊卑等級相符合,還注重各地區之間的溝通協調,從而使祭樂更好地流傳使用。
2.紀律制度。清朝的祭祀共分為九個儀程,即迎神、奠玉帛、進俎、初獻、亞獻、終獻、撤饌、送神、望瘞等。每進行一項儀程,皇帝都要分別向正位、各配位、各從位行三跪九叩禮,歷時兩小時之久。咸豐時期盛京地區的祭祀活動有著比較嚴格的紀律,官員必須虔誠整肅,不許遲到早退、不許咳嗽吐痰、不許紊亂次序、不許越級等等。
例如,《盛京禮部為知會先師孔子誕辰之日不理刑名禁止屠宰事咨盛京內務府》中記載:“盛京禮部為知會事檔房案呈,查得本年八月二十七日先師孔子誕辰,此一日齋戒,不理刑名,禁止屠宰,知會盛京內務府可也。須至咨者。”[6]這則檔案表明了在祭祀孔子之日,不能宰殺牲畜,不處理刑事案件。又如《禮部為奏準恭送宣宗成皇帝圣容至盛京鳳凰樓供奉禮儀事咨盛京內務府》中記載:“設皇上拜褥于香案前,親王以下、侍郎副都統以上咸蟒袍補服集彩棚外,祗俟工部預設彩亭亭于乾清門門外,太監舁請至乾清宮檐下。”[7]這表明皇帝、親王以下和侍郎副都統以上等不同的祭祀主體在祭祀活動中所處的位置有明確的規定。這都體現出咸豐時期盛京地區對祭祀活動有著嚴格的禮儀規則和程式規定,這已經形成了較為嚴格的紀律制度。
二、祭祀規則制度
祭祀規則制度規定了如何舉行祭祀活動以及祭祀活動應該包含的具體內容。《黑圖檔·咸豐朝》涉及了許多關于祭祀的規則制度。
1.祭祀的對象。國家祭祀禮儀根據祭祀對象及其地位的不同,分為三等。“天壇、地壇、祈谷壇、太廟、社稷壇為大祀”;“朝日壇、夕月壇、歷代帝王廟、文廟、先農壇為中祀”;“太歲、神袛等壇,先醫、東岳、城隍等廟為小祀”[8]。這種分類在以后歷朝均有所損益。
(1)祭祀先王。在咸豐時期盛京地區的諸多祭祀活動中,對先王的祭祀是一種重要的常規性祭祀活動。歷朝歷代的開創者在建立其國家政權的時候,都注重對先王的祭祀,以此來表明其繼承人的合法身份并為后代君主立下典范。
如《盛京禮部為分撥兩陵大祭抬桌官員事咨盛京內務府》中記載:“盛京禮部為咨派抬桌官員事檔房案呈,七月十五日兩陵大祭應用抬桌官員,先經本部分晰開單移咨盛京將軍、四部、內務府、府尹衙門。”[9]又如《盛京禮部為知會世宗憲皇帝誕辰日禁止屠宰事咨盛京內務府》中記載:“盛京禮部為知會事檔房案呈,查明得本年十月三十日世宗憲皇帝誕辰,此一日禁止屠宰之處,相應知會盛京內務府查照可也。”[10]這兩則檔案體現了咸豐時期的盛京地區,統治者注重對先王的祭祀,始終在奉行“以孝治天下”的理念,把先王祭祀作為國家禮制建設的重中之重,通過祭祀來鼓勵后代勵精圖治,擴大宗族宏業。
(2)祭祀社稷之神。祭社稷之神是清代祈求風調雨順、農業豐收的祭祀禮儀。由于我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歷朝歷代統治者對農業生產都十分重視。在咸豐時期的國家祭祀體系中,社稷之神作為祈求農業豐收的重要神袛而備受尊崇。
正如《盛京戶部為將慶安呈控張萬才盜典祭田一案銷案事咨盛京內務府》中記載:“雍正五年冊載正黃旗,李奉祖牛錄束拉張自亮,一領地畝均未注寫墳丁祭田字樣,查明本處漢軍正黃旗佐領特樸欽報稱,該旗新陳仆丁冊內并無張萬才及其祖父張進祿、張印、張自亮等名。”[11]這則檔案記載了咸豐時期盛京地區統治者對田地社稷之神的祭祀,表明了統治者對農業生產的重視,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
(3)祭祀孔子。我國古代祭祀先師孔子有著悠久的歷史。自西漢漢武帝以來,儒家思想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一直延續到清朝時期。因此,清朝統治者將祭祀孔子視為厲行教化、維護統治的重要手段。
《盛京戶部侍郎等為恭祭先師孔子事咨盛京內務府》中記載:“為知照事照得本年八月初九日上丁,例應寅正會集恭祭先師孔子,除應備祭品等項,檄飭承德縣遵照定例動項備辦外,相應移咨為此合咨,貴衙門查照施行,須至咨者。”[12]又如《奉天府衙門為恭祭先師孔子事咨盛京內務府》中記載:“奉天府府尹衙門為知照事,照得本年二月初六日上丁,例應寅正會集恭祭先師孔子,除應備祭品等項,檄飭承德縣遵照定例動項備辦外,相應移咨。”[13]可見咸豐時期的盛京地區將祭孔這一行為推向了一定的高潮,他們在尊孔的同時,也將自己塑造為儒家的道統傳人。
(4)祭祀關帝。在咸豐時期統治者所提倡的道德準則中,“忠”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忠孝的觀念起源于夏朝,“夏道尚忠,復尚孝”[14],這里“忠”是指君主及官吏之忠于民,臣忠于君。關羽就是忠君愛國的一個典范,因此祭祀關帝也是清代祭祀活動中的一項。《盛京將軍衙門為知會關帝升入中祀并祀禮條款事》中記載:“關帝升入中祀,遣官事宜一折并禮節條款,夾片二件,于咸豐三年(1853)十月二十三日奏,二十四日內閣抄出奏,上諭禮部等衙門議奏關帝升入中祀禮節一折,我朝尊崇關帝,祀典攸隆,仰荷神威疊照顯佑,本年復加崇封號。”[15]又如《盛京將軍衙門為抄送關帝升入中祀告察祝文事咨盛京內務府》中記載:“盛京等處將軍衙門為咨行事。左禮司案呈準禮部咨開為移咨事,祠祭司案呈,恭照關帝升入中祀遣官事宜,并禮節夾片于具奏后業經知照在案。”[16]這兩則檔案體現了統治者將關帝升入中祀并對其施行更為厚重的禮節,說明了咸豐時期盛京地區統治者對忠義觀念的認同。
2.祭祀的時間。
(1)以我國傳統的二十四節氣為基準確定祭祀時間。這是最主要的一類祭祀時間。由于我國是傳統的農業社會,人們根據長期農業生產活動而制定的二十四節氣對于農業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所以,咸豐時期盛京地區多數的重要祭祀活動都發生在這二十四節氣當中,例如清明節、冬至。
清明節是氣清景明、萬物新生的時節,是自古以來人們祭拜先人的傳統節日。例如,《盛京禮部為分派清明兩陵大祭應用抬桌官員事咨盛京內務府》中記載:“盛京禮部為分派抬桌官員事檔房案呈,查得本年二月十五日清明兩陵大祭應用抬桌官員,先經本部分晰開單,移咨盛京將軍各部衙門。”[17]冬至作為我國民間的傳統節日,也是國家舉辦祭祀活動的一個時節。因為冬至的來臨,子孫們會覺得在冥界的祖先也正面臨著寒冷的威脅。例如,《盛京禮部為分派兩陵大祭抬桌官員事咨盛京內務府》中記載:“盛京禮部為分派抬桌官員事檔案房呈,查得本年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兩陵大祭應用抬桌官員,先經本部分晰開單移咨盛京將軍衙門四部等衙門。”[18]從這兩則檔案中可以看出,咸豐時期盛京地區非常重視清明節、冬至等二十四節氣的祭祀,這些制度是由民間習俗的不斷影響而形成的。
(2)授權主體確定的祭祀時間。受到傳統祭祀習俗的影響,祭祀活動都必須在吉日舉行,因此在清代盛京地區,授權主體有權利對祭祀的時間進行一定的規定,它已經形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行為規范。
例如,《盛京禮部為知會十月初一日三陵贊祭事咨盛京內務府》中記載:“照得每年十月初一日永陵、福陵、昭陵贊祭,久經辦理在案。今本年十月初一日應行贊祭之處盛京內務府可也。”[19]這就說明十月一日是每年祭祀三陵的節日,必須要遵照執行。又如《禮部為知會祭祀各壇廟日期事咨盛京內務府》中記載:“正月十一日祭祈谷壇,自初八日齋三日。二月初三日祭文昌廟,承祭官于初二日齋二日。二月初八日祭先師孔子,自初六日齋二日。二月初九日祭社稷壇,自初六日齋三日。神袛壇二月十三日祭,昭忠祠二月十五日祭……”[20]在這則檔案中,禮部明確地規定了對文昌廟、孔子、社稷、神祠等祭祀的時間。在《黑圖檔》的記載中,統治者每年還會對先皇帝、先皇后、孔子的誕辰日進行祭祀,這就表明了咸豐時期盛京地區在祭祀時間上已經形成了一種較為完善的制度。
3.祭祀的場所。祭祀活動的莊重性和嚴肅性決定了祭祀的場所必須進行嚴格的選擇,不能任意為之。在咸豐時期的盛京地區,祭祀活動都在固定的地點舉行。如《工部為奏準修繕太廟配殿應需工料款項等事咨盛京內務府》中記載:“工部為咨行事,管繕司案呈,內閣抄出,盛京將軍宗室奕□等奏會同勘驗太廟東西配殿未逾保固各應修情形,請旨飭交欽天監選擇吉期動支。”[21]可見太廟是最基本的祭祀祖先的場所,并且咸豐時期統治者非常重視對太廟的修繕。又如《欽天監為奏準祈谷壇改于正月十八日次辛致祭事咨盛京內務府》中記載:“所有本監于咸豐六年(1856)十月二十五日具奏,咸豐七年正月初八日上辛祭祈谷壇改于十八日次辛致祭等因一折,本日奉旨依議,欽此。查本監咸豐七年時憲書內齋戒日期向于日傍加圈作記,今既經奏準改于十八日次辛大祀祈谷壇。自應通行遵照可也。”[22]可見祭壇也是祭祀神明的一個重要場所。
三、祭祀保障制度
作為統治者非常重視的一項活動,祭祀并不是一項孤立的活動,需要有一些前期的準備活動、專業人員的參與以及各部門的上傳下達,才能使其順利進行。
1.齋戒活動。齋戒是祭者在祭祀活動前必不可少的一個流程,其要求歷代皆同,具有濃厚的神秘色彩,受到人們的重視。例如,《盛京禮部為仁宗睿皇帝誕辰日齋戒禁止屠宰等事咨盛京內務府》中記載:“盛京禮部為知會事檔房案呈查得本年十月初六日,仁宗睿皇帝誕辰此一日。虔誠齊戒,不理刑名,禁止屠宰之處知會盛京內務府可也。”[23]這則檔案表明了在仁宗睿皇帝誕辰之日的齋戒活動中,不應該處理刑事案件,不應該屠殺牲畜,這就說明咸豐時期盛京地區在齋戒期間有著比較嚴格的禁忌和規定。
2.專業化人員的參與。在咸豐時期的盛京地區,國家對祭祀事務有專門的機構進行管理。盛京禮部是清朝皇帝為突出陪都盛京的重要性,管理盛京地區的祭祀禮儀事務而設立的,而禮部負責掌管全國的五禮之儀制及學校貢舉之法[24]。例如,《盛京禮部為咨取昭陵大祭抬桌官員銜名事咨盛京內務府》中記載:“盛京禮部為咨取抬桌官員事檔案房呈查得本年四月十七日,昭陵忌辰大祭咨取抬官員前來,相應照例行文盛京內務府。”[25]這就體現了禮部具有管理祭祀活動的職能,這一時期還有專門負責抬祭品的人員,禮部與抬桌官員的設置就體現了咸豐時期對祭祀活動的重視以及人員設置的專業化。
3.各部門溝通協調。由于祭祀活動事關重大,因而活動細則在許多情況下也需要各部門文武百官的參與,集思廣益,形成結論之后再提交給上一級的統治者。例如,《盛京禮部為分派兩陵大祭抬桌官員事咨盛京內務府》中記載:“盛京禮部為分派抬桌官員事檔房案呈查二月二十九日清明兩陵大祭,(應用)抬桌官員先徑本部分晰開單,移咨盛京將軍、四部等衙門,委員送部去后,今準盛京內務府委定筆帖式銀文萃,德昌庫使崔玉、春暉、馬永祥、克什布等,俱徑簽掣得福陵抬桌官員。”[26]又如《盛京內務府為奏準鳳凰樓供奉圣容位置交回朱批原折事咨總管內務府》中記載:“除原圖留中,今將硃批原折、請安黃折一并咨行盛京將軍衙門查收外,仍希貴衙門回繳硃批時合并知照總管內務府。查照暨知會禮部,其禮部公文一角咨行盛京兵部,由驛轉遞可也。”[27]這兩則檔案表明了委任抬桌官員、奏準鳳凰樓供奉圣容位置這些事需要盛京將軍衙門、總管內務府、禮部等不同部門的協商才能實現。這都體現了咸豐時期盛京地區祭祀活動的開展注重多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
四、祭祀物品制度
祭祀物品是祭祀活動得以順利開展的前提條件。《黑圖檔·咸豐朝》有專門的檔案對祭祀所用物品進行明確的規定。
1.祭祀供奉。祭品自古以來就是祭祀活動中人與神靈進行交流和溝通的重要媒介和象征符號。在咸豐時期的盛京地區,祭祀過程中使用的祭品種類較多,主要包括神御物、天尊佛像與犧牲。
正如《為奏準敬繪供奉圣容之金龍柜排列圖恭呈御覽事》中記載:“咸豐八年(1858)五月初九日準禮部來咨,內稱仁宗睿皇帝圣容恭送,盛京請典現辦恭送之玉冊玉寶,并實錄圣訓玉牒。”[28]在祭祀活動中,將玉器作為祭品,這一行為沿襲古制。如《檔案房為繪送尊藏冊寶位次圖奏請欽定事呈請咨總管內務府》中記載:“檔案房呈,為咨報事。本衙門具奏為恭請欽定尊藏寶冊位次敬謹繪圖恭呈御覽仰祈圣鑒事竊奴才等,準禮部移咨內稱擇吉,於咸豐三年(1853)三月初八日恭逢寶冊至盛京太廟尊藏。”[29]這則檔案體現了在咸豐朝時期的盛京地區,繪制的尊藏寶冊也是一種重要的祭品。牛、羊也是統治者在祭祀活動中使用的重要祭品,是滿族人傳統飲食習慣的真實寫照。人們正是通過這些祭品來表達對神明祖先的虔誠敬畏,確保祭祀活動的順利開展。
2.祭服。據史料記載,早在商周時期我國就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冠服制度,每逢祭祀時節的到來,統治者就會根據祭祀禮儀的不同及祭祀對象的尊卑穿不同形式的祭服以及佩戴不同形式的佩飾。根據《盛京禮部為知會孝穆成皇后忌辰日應穿服色事咨盛京內務府》中記載:“是日正值孝穆成皇后忌辰,查九年、十年均于正月二十一日開印。所有應穿服色曾經付知各衙門查照。此一日,仍穿朝服。拜印時作樂,開印后不穿褂,穿常服,散署后再換素服。相應預咨盛京內務府查照,須至咨者。”[30]這一件檔案表明了在孝穆皇后的忌辰這一天,祭祀前、拜印后、散署后不同時段的服飾都有不同的規定。又如《盛京將軍衙門為皇帝謁慕陵十一日禮成官員釋服事咨盛京內務府》中記載:“本衙門接閱邸抄內閣,皇上于初六日啟鑾恭謁慕陵,十一日行釋服禮,禮成后回鑾等因,相應咨行盛京內務府轉飭所屬文武官員,即于十一日釋服更換天青褂,掛朝珠可也。須至咨者。”[31]這一檔案體現了祭服作為一種象征,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統治者強化文化認同、推行森嚴的等級制度、鞏固延續其統治的重要手段。
祭祀是基于人們的鬼神信仰而產生的崇拜方式。清朝皇陵每年有五次大祭,即清明、中元、冬至、歲暮和忌辰,每月朔、望皆有小祭。除固定的祭祀以外,國家重大慶典、武功告成等皆有祭陵之舉[32],可見祭祀一直受到統治者的高度重視。清朝咸豐時期,盛京地區的封建統治達到一定的高度,祭祀作為一種精神統治的工具也必然形成一種較為完整的制度。本文通過對《黑圖檔·咸豐朝》所記載的有關祭祀制度的內容進行梳理,從禮儀制度、規則制度、保障制度、物品制度進行整理分析,不僅可以完善咸豐朝時期盛京地區祭祀制度的研究,使我們深入了解祭祀制度,讓我國祭祀制度發揮其應有的社會價值,而且對于目前的歷史學、文獻學及史料編纂學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對當今構建和諧社會、進行社會治理也帶來一定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