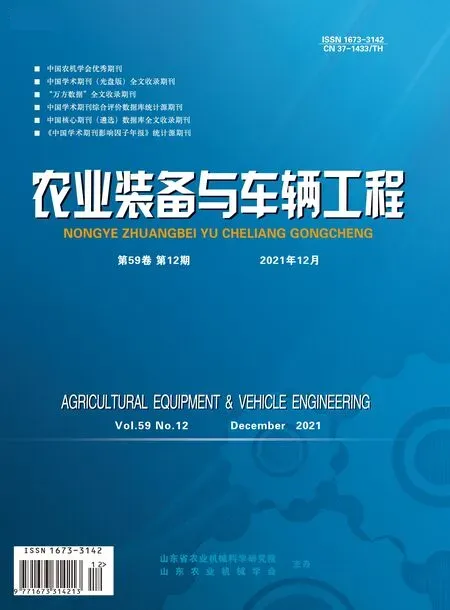風冷翅片用于鋰電池組散熱性能的數(shù)值模擬研究
劉業(yè)鳳,孫偉,荊巖巖
(1.200093上海市 上海理工大學 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2.200093 上海市 上海市動力工程多相流動與傳熱重點實驗室)
0 引言
電動汽車的核心技術包括電機控制技術、能量管理技術、整車控制技術和電池管理技術[1],其中電池熱管理技術直接影響電動汽車的性能。鋰電池由于具有電壓和比能量高、循環(huán)性好、自放電小、無記憶效應、無污染的特點,在電動汽車中得到了廣泛應用,是電動汽車的動力來源。電動汽車的行駛里程取決于電池的壽命。電動汽車電池模塊的價格更是占整個電動汽車總價的33%,所以研究電動汽車電池模塊的性能、減少電池模塊的更換頻率、提高電池模塊的使用壽命能夠有效降低電動汽車的價格,有利于推動電動汽車產(chǎn)業(yè)在城市的推廣。
鋰電池的特性的好壞主要取決于電池的溫度特性[2]。電池模塊的散熱十分重要,電池溫度過高或者過低,對電池都有很大的影響。高溫對動力電池的影響是“雙刃劍”,一方面,電池溫度升高,電池的活性增強,離子擴散得更快,相應的電池內(nèi)阻會減小,所以從這方面看,電池溫度高能改善電池的性能;另一方面,電池溫度高電解液會分解產(chǎn)生有害氣體,對電池造成永久性損害,降低電池的使用壽命[3]。
研究表明,電池工作的環(huán)境溫度越高,電池內(nèi)部化學反應速率越快,溫度每升高10 ℃,化學反應的速度增加1 倍;在高倍率下充電時,溫度升高5 ℃,電池壽命減少一半。在45 ℃的環(huán)境溫度下工作時,鎳氫電池循環(huán)壽命次數(shù)大約減小60%[4-5]。不同種類的電池的最佳工作溫度范圍不同,目前關于新能源汽車電池的最佳工作范圍并沒有明確的標準。文獻[6-12]的研究總結出:鎳氫電池的最佳工作溫度范圍是20~40 ℃,鉛酸電池的最佳工作溫度范圍是25~45 ℃,鋰電池普遍認為的最佳工作溫度范圍是18~45 ℃。對于溫度控制要求較高的電池模塊的散熱系統(tǒng)來說,最好將其溫度控制在25~45 ℃[9]。
本文三元鋰電池21700 的散熱目標:溫度范圍25~45 ℃,電池模塊的溫差控制在5 ℃以下。
1 單體鋰電池熱特性模型的正確性驗證
本文的實驗對象是三元鋰電池21700,它相對于其他鋰電池具有電池能量密度更大、低溫放電性能更好、充電效率更高等優(yōu)點。正是由于三元鋰電池有這么多的優(yōu)點,它在電動汽車領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應用,比如特斯拉應用的就是三元鋰電池。本文研究的三元鋰電池21700 單體電池的基本參數(shù)見表1。

表1 三元鋰電池規(guī)格表Tab.1 Specification of ternary lithium battery
1.1 單體鋰電池溫升實驗
本次實驗選擇了學校的冰箱性能實驗室作為高低溫環(huán)境室。該實驗室可以提供的環(huán)境溫度的范圍是-20~70 ℃,溫度波動范圍不超過 ±0.5 ℃。實驗所用的放電儀器是廣勤KL5102 電子負載儀,它可以完成常規(guī)的電池測試。數(shù)據(jù)采集采用的是K 型熱電偶,其控制精度為±0.4%,在電池正極,負極和中間各布置一個熱電偶,并以其平均溫度作為電池表面溫度,使用安捷倫采集實驗數(shù)據(jù)。控制參數(shù)如表2 所示。電池在自然對流條件下進行放電,測得上中下3 個測點的溫度,并對數(shù)據(jù)進行處理分析。

表2 溫升實驗基本實驗參數(shù)Tab.2 Basic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of temperature rise experiment
1.2 單體鋰電池仿真模型
由于鋰電池的熱特性非常復雜,需要對電池的發(fā)熱模型進行簡化[13]。Chen[14]等人對電池分層模型和不分層模型進行了研究,結果證明電池熱仿真時無論采用分層模型還是不分層模型對于電池溫度場影響不大,因此本文選擇電池內(nèi)部不分層模型。為提高模型準確性和精度,還提出了一些假設:(1)電池內(nèi)部材料均勻,電池密度、比熱容不隨溫度、放電倍率和SOC 變化;(2)電池內(nèi)部電解液流動很小,電池內(nèi)部不存在對流換熱;(3)電池是透明的固體材料,電池內(nèi)部不存在輻射換熱;(4)電池在同一方向上熱導率相同,且電池各個方向的熱導率不隨電池溫度和SOC 的變化而變化;(5)電池在恒流放電時各個部分生熱速率相同,認為電池是一個恒熱源。
基于以上假設,再結合前面的分析以及傳熱學基本原理,可以建立圓柱形鋰離子電池在圓柱坐標系下的導熱微分方程,圓柱型鋰離子電池在圓柱坐標系下非穩(wěn)態(tài)傳熱的數(shù)學模型如下:

式中:ρ——流體密度,kg/m3;Cp——電池的比熱容,J/(kg·K);T——溫度,K;t——溫度,℃;q——電池產(chǎn)熱速率,W/m3;λ——各個方向上的導熱率,W/(m2·K)。
電池相關的全部的熱物性參數(shù)如表3 所示,由此獲得電池溫度的解。

表3 溫升實驗基本實驗參數(shù)Tab.3 Basic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of temperature rise experiment
1.2.1 單體鋰電池網(wǎng)格劃分
單體鋰電池的三維模型及網(wǎng)格劃分如圖1 所示。基于單體電池結構規(guī)則,為提高計算精度、減少計算時間,采用結構化網(wǎng)格。建立block 區(qū)域模塊,并將模型中的點、線、面進行關聯(lián),其中上下底面采用O 型網(wǎng)格。

圖1 單體鋰電池三維模型及網(wǎng)格劃分Fig.1 Three-dimensional model and grid generation of single lithium battery
單體電池網(wǎng)格的尺寸大小設置為1,最終得到的網(wǎng)格數(shù)量是50 184,節(jié)點數(shù)是47 144。將ICEM 中劃分的網(wǎng)格導入到Fluent 中仍需要進行網(wǎng)格質(zhì)量檢查,本文的檢查結果是最小面網(wǎng)格是2.346 13×10-7,最小體網(wǎng)格是2.346 126×10-10,沒有出現(xiàn)負值,因此不需要重新劃分網(wǎng)格。
1.2.2 仿真模型的設定
模型主要研究的是電池溫度隨時間的變化以及隨著生熱速率的變化電池溫度場的分布,因此在物理模型中要開啟能量方程,勾選Energy-On。另外,在進行單體電池的模擬時,選擇基于壓力的瞬態(tài)計算3D 隱式算法。電池的熱物性參數(shù)需要根據(jù)表3 參數(shù)在Materimals 中定義,包括密度、比熱容和導熱系數(shù)等,方法是Materimals-Solid-Create/Edit Materimals,導熱系數(shù)選擇Cylinderical Orthotropic Conductivity。在Boundary Conductions 中將電池表面選擇為自然對流,對流換熱系數(shù)h 一般為h=3~10 W/m2·K,本文選擇h=5 W/m2·K。設置初始電池表面溫度為15 ℃,對整個流場(All Zone)進行初始化。再對計算的時間步長和迭代次數(shù)等進行設置:1C 放電倍率下時間步長為3 600 s,1.5C 為2 400 s,2C 為1 800 s,步長設置為1,最大迭代次數(shù)為20 步。
藏族前半段舞段充滿著儀式感,開場展現(xiàn)的是一位老者給一頭耗牛的牛角上系紅繩,在此處并沒有用很實的光斑給老者做定點,而且采用了電腦染色燈給老者抹出了一塊橙紅色的區(qū)域,加上對亮度的控制,讓觀眾既能看見老者與耗牛的表演,又能不破壞儀式中的神秘感。之后的一段耗牛群舞,首先是一位演員的前區(qū)舞段,演員手中拿著一對牛角,此時也沒有按部就班地上一個傳統(tǒng)的光圈定點,而是利用電腦切割燈,雕刻出一個半月牙形狀的區(qū)域來模擬牛角,演員在這個牛角里完成獨舞舞段,這樣不僅沒有破壞舞臺燈光本應有的強調(diào)區(qū)域和演員的作用,更是在形態(tài)上與整個舞段相呼應。
1.3 單體鋰電池仿真與實驗對比
為了確定熱模型的準確性,將環(huán)境溫度為15 ℃下單體電池表面中心位置測點的溫度導入到CFD-Post 中擬合出溫度曲線,并與單體電池溫升實驗的結果對比,仿真和實驗提取數(shù)據(jù)的時間間隔都是120 s,對比的結果如圖2 所示。

圖2 15℃模擬與實驗數(shù)據(jù)對比Fig.2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and experimental data at 15 ℃
由圖2 可見,環(huán)境溫度為15 ℃時,仿真結果與實驗結果都比較接近,因此建立的鋰電池熱特性模型是正確的。在同一環(huán)境溫度下,放電倍率越低,實驗結果與仿真結果越接近。誤差最大的時間是放電后期,放電完成后仿真溫度都大于實驗溫度。原因可能是電池在實驗過程中自然對流的換熱系數(shù)并不是定值,而仿真時電池的換熱系數(shù)為定值;電池實際放電過程中生熱速率并不是定值,仿真是按電池內(nèi)熱源為定值進行的;實際實驗過程中電池的比熱容也不是完全不變的,比熱容也會隨溫度發(fā)生微小的變化,模擬過程中比熱容為定值;電池在實際放電過程中會與外界之間輻射換熱,仿真沒有考慮輻射換熱的影響。
2 鋰電池模塊的模型建立
考慮到實際應用以及電腦配置,本文選用4×3 的電池模塊,電池模塊之間以四串三并的方式連接,建立強制風冷散熱模型以及風冷鋁翅片強化散熱模型,由于風冷鋁翅片散熱模型較強制風冷散熱模型多了翅片設定,因此本節(jié)列舉風冷鋁翅片散熱模型。
2.1 幾何建模及網(wǎng)格劃分
如圖3 所示,將12 節(jié)電池和3 片翅片組合在一起,形成風冷翅片電池模塊。張寧[15]等研究發(fā)現(xiàn),翅片厚度為0.5 mm 時,電池模塊的最大溫度和溫差明顯高于其他情況,但翅片厚度在1、2、3 mm 之間變化時,電池模塊的溫度相差不大,因此本文選取的鋁翅片厚度為2 mm。其中,電池箱體PVC 尺寸為113 mm×89 mm×72 mm,翅片側面與電池箱體PVC 容器的距離是5 mm,電池長70.9±0.2 mm,翅片等間距布置。

圖3 鋰電池模塊風冷翅片強化散熱三維幾何模型圖Fig.3 3D geometric model of air cooled fin for lithium ion battery module
在SolidWorks 畫出三維模型,保存成x.t 格式并導入到ICEM 進行網(wǎng)格劃分。在ICEM 中設置電池模塊模型的邊界與計算域,包括進風口、出風口、電池壁面、流體域、固體域、耦合面、電池箱體壁面,由于風冷鋁翅片強化散熱模型的網(wǎng)格比較復雜,因此在這里采用的是非結構化網(wǎng)格,為了降低網(wǎng)格的數(shù)量,采用網(wǎng)格組裝的方法劃分網(wǎng)格。分別畫出風冷鋁翅片電池模塊和風冷流場的網(wǎng)格。風冷鋁翅片電池模塊的網(wǎng)格如圖4左側所示,組裝好的網(wǎng)格如圖4 右側所示。網(wǎng)格數(shù)量為1 907 305 個,經(jīng)檢查電池模塊的網(wǎng)格質(zhì)量滿足CFD 仿真網(wǎng)格質(zhì)量的要求,然后將網(wǎng)格導入到Fluent 中進行溫度場的仿真。

圖4 風冷翅片電池模塊網(wǎng)格示意圖Fig.4 Grid diagram of air cooled fin battery module
2.2 模型求解參數(shù)的選擇與邊界條件的設定
本文采用冷風散熱,空氣參數(shù)直接采用Fluent 材料數(shù)據(jù)庫中默認的air。電池模塊產(chǎn)熱速率和其它參數(shù)和單體鋰電池相同,由于電池箱體與外界空氣的散熱是自然對流散熱,其散熱量很小,可忽略,因此電池箱體設置為絕熱。選取的放電倍率分別是1.0C、1.5C、2.0C,風速選擇3~5 m/s,環(huán)境溫度分別是15,25,35 ℃。電池箱的進口邊界條件為Velocity inlet,出口為Outlet-vent,并設置回流溫度為25 ℃,表壓為0,損失系數(shù)為1。由于鋰電池模塊和冷卻空氣之間的換熱是流固耦合換熱,接觸面設置為Coupled。選擇標準模型湍流模型,仍然選擇瞬態(tài)仿真,其他的設置和單體鋰電池相同。
3 仿真結果及分析
3.1 放電倍率對風冷散熱的影響
控制環(huán)境溫度為25 ℃,風速為3 m/s,翅片數(shù)為3 片,改變放電倍率1C、1.5C、2C,得到的模擬數(shù)據(jù)如表4 所示。

表4 25 ℃,3 m/s 不同放電倍率下強制風冷與翅片風冷最高溫度/最大溫差對比Tab.4 Comparison of maximum temperature/maximum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forced air cooling and fin air cooling at 25 ℃,3 m/ s and different discharge rates
由表4 可知,相比于強制風冷散熱,翅片風冷的最高溫度分別降低了1.31、2.65、4.09℃,溫差分別降低了3.24、6.79、10.75℃。由此可見,將鋁翅片應用于鋰離子電池模塊能有效降低電池模塊的最高溫度與最大溫差。當環(huán)境溫度相同時,放電倍率越高,對鋰離子電池模塊最高溫度和最大溫差的改善越明顯。
3.2 環(huán)境溫度對風冷散熱的影響

表5 2C,3 m/s 不同環(huán)境溫度下強制風冷與翅片風冷最高溫度/最大溫差對比Tab.5 Comparison of maximum temperature/maximum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forced air cooling and fin air cooling at 2C and 3 m/s
由表5 可知,相比于強制風冷散熱,翅片風冷的最高溫度分別降低了4.95,4.09,3.72℃,最大溫差分別降低了13.05,10.79,9.81 ℃。放電倍率相同時,環(huán)境溫度越高,最高溫度和最大溫差的改善越不明顯。這是因為環(huán)境溫度越高,電池內(nèi)阻越小,電池產(chǎn)熱越慢,因此翅片從電池模塊導出的熱量越少,電池模塊最高溫度和最大溫差的改善越不明顯。
3.3 風速對風冷散熱的影響
結合3.1,3.2 得出的結果,控制放電倍率為2C,環(huán)境溫度為35 ℃,翅片數(shù)為3片,改變風速3、4、5 m/s,得到的模擬數(shù)據(jù)如表6 所示。

表6 2C,35℃不同風速下強制風冷和翅片風冷最高溫度/最大溫差對比Tab.6 Comparison of maximum temperature/maximum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forced air cooling and fin air cooling at 2C and 35 ℃ with different wind speeds
由表6 可知,相比于強制風冷散熱,翅片風冷的最高溫度分別降低了3.72,5.70,5.21 ℃,最大溫差分別降低了9.81,8.39,6.67 ℃。翅片風冷的最高溫度和最大溫差都低于強制風冷散熱的電池散熱系統(tǒng),且隨著風速的增加電池模塊的最高溫度和最大溫差會進一步降低,但是降低的速率變慢。這是因為,增加風速,電池箱體中空氣的雷諾數(shù)增加,湍流程度增大,電池模塊與冷空氣換熱更充分,因此電池模塊最高溫度和最大溫差降低;電池箱內(nèi)空氣的湍流程度達到一定程度后,再增加風速,對電池模塊和冷空氣的換熱影響不大,還會使流場中的流動阻力增大,對散熱不利。因此本文模擬的最大進口風速為5 m/s。
3.4 翅片數(shù)對風冷散熱的影響
結合上述結論,控制放電倍率為2C,環(huán)境溫度為35 ℃,風速為4 m/s,改變翅片數(shù)3、5、7,得到的模擬數(shù)據(jù)如表7 所示。

表7 不同翅片數(shù)下強制風冷和翅片風冷最高溫度/最大溫差對比Tab.7 Comparison of maximum temperature/maximum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forced air cooling and fin air cooling under different fin numbers
從表7 可知,相比于強制風冷散熱,翅片風冷的最高溫度分別降低了5.7,6.37,7.16 ℃,最大溫差分別降低了8.34,8.61,9.23 ℃,隨著翅片數(shù)增加,換熱效果有所提升。雖然沒有繼續(xù)增加翅片的個數(shù)進行研究,但從傳熱學的知識可以知道,翅片個數(shù)不能無限增加,因為電池模塊本身就重量很大。隨著翅片個數(shù)的增加,翅片和電池模塊對流場的阻力增大,這對散熱也是不利的。綜上,風冷翅片在環(huán)境溫度為35℃,放電倍率為2C 的惡劣工況下,通過調(diào)節(jié)風速和翅片數(shù)可以滿足電池的散熱需求
4 結論
本文先論證了鋰電池熱模型的準確性,然后以一個四串三并的電池模塊為研究對象,對鋰電池模塊的散熱性能進行了仿真,對比分析了強制風冷散熱模型和風冷鋁翅片強化散熱模型的散熱性能,研究的環(huán)境溫度為15,25,35 ℃,進口風速為3~5 m/s,翅片個數(shù)為3、5、7 片,放電倍率為1C、1.5C、2C。
研究表明,翅片應用于鋰離子電池模塊散熱能夠降低電池模塊的最高溫度與最大溫差。具體如下:(1)環(huán)境溫度和進口風速相同時,放電倍率越高,相對于強制風冷散熱,最高溫度和最大溫差的降低越明顯。(2)放電倍率和進口風速相同時,環(huán)境溫度越高,相對于強制風冷散熱,最高溫度和溫差的降低越不明顯。(3)隨著風速的增加,翅片散熱的電池散熱系統(tǒng)的最高溫度和溫差會進一步降低。(4)在研究的翅片個數(shù)的范圍內(nèi),增加翅片的個數(shù)也能夠使翅片散熱的電池模塊熱管理系統(tǒng)的最高溫度和溫差進一步降低。(5)風冷翅片在環(huán)境溫度為35 ℃,放電倍率為2C 的惡劣工況下,通過調(diào)節(jié)風速和翅片數(shù)可以滿足電池散熱目標:溫度范圍是25~45 ℃,溫差在5 ℃以下。